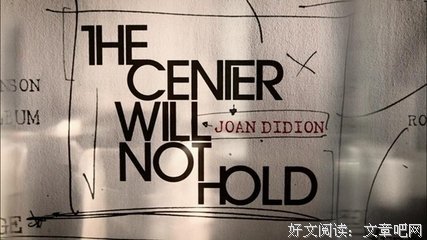
《琼·狄迪恩:中心难再维系》是一部由Griffin Dunne执导,琼·迪丹 / 汤姆·布罗考 / 格里芬·邓恩主演的一部纪录片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观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琼·狄迪恩:中心难再维系》观后感(一):Movie Review
某天我发现一个和我同龄的好莱坞小美女办了一个在线读书俱乐部。可爱的网站首页贴了一大篇人物专访,小美女兴奋不已地写道能够采访自己的偶像Joan Didion荣幸之至,并向所有关注该读书俱乐部的人们推荐Didion的新书,<South and West>。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Didion的照片,浅金色波波头,洞悉一切的大眼睛,一位瘦削优雅的老太太。我读了网上能找到的所有她写的文章,书本节选,读了<South and West>。Google她时,发现这位老太太不久前还当过Celine代言人,又时髦又酷。
90分钟的影片按时间叙事,简练没有任何冗余,访谈间融进了许多老照片和影像资料。已八十多高龄的Didion,依旧衣着讲究,读书看报,欣赏一丛丛花朵,在厨房耐心地一片一片切三明治,回忆往事,思维迅捷而嫌言语太慢似的用手臂比划。那些黑白照片分明地展示着不同年龄Didion的美。
遇到疼她保护她的丈夫John,和后来又加入的家庭成员养女Q,Didion的家庭生活美满幸福;当记者,写电影剧本,Didion无须为生活发愁为生计写作。这个热爱写作的加州女孩,写加州,写朋友,写政治事件,写悲伤、失去。她的文字一如其人,纤细敏感,优美克制。多看,再把看到的写下来。
尤其喜爱影片中Didion自己念的旁白。Remember what it is to be me.
《琼·狄迪恩:中心难再维系》观后感(二):Remember what it is to be me.
镜头里的她八十多岁了,极瘦,脖子周围和手臂上皮包骨头,风度仍然很好。我着迷于她说话的样子。不全像Anna Wintor的那种带着气势的气定神闲,也更不像Hedy Lamarr的表演气息,也许可以形容为智慧沉淀之后的平静。说话时有停顿,但没有支支吾吾的声音,也许是注意过公众表达的良好基本功。手臂不时挥舞,像是要把那些语言从身体里推出来。(看到另一篇影评也注意到这一点,解读为思维太快言语跟不上,同一个特质有不同的解读,这很有意思。)
照片上年轻时候的她真的很好看,特别是眼神,时而很深,像山峦之间平静的湖面;时而疏离,是处在旋风中心的置身事外。看起来内敛也不爱社交的人,但是在书写中又十分开放。说只能通过书写才能梳理思绪和感情。非常迷人。
我在想,在经历了动荡的六十年代,看尽了洛杉矶的繁华,在那样的大起大落时刻,她是如何看到在客人把海洛因落到自己女儿的房间那一刻之后,仍然保持这得体的沉静。
她和伴侣,女儿以及朋友之间的关系都很耐人寻味。看起来和伴侣之间并不是最和美的那一种,但又实在志趣相投一生相伴;和女儿琢磨不透说不清,和朋友们倒是保持着温情(想起那个剧院角落里,朋友们给她设置了一个cafe didion)。
结尾的半个小时格外的抓人。我说不出话来。说起《异想之年》,说起《蓝夜》,说起人的离去像光芒消逝。她像是游客一般在教堂里走动着,旁白说,她是相信人类成就的人,这样的她又如何面对自己心中的这一份罪恶感。
《琼·狄迪恩:中心难再维系》观后感(三):Notes about Joan
“Things fall apart, the center cannot hold.” Joan Didion的纪录片标题选取了叶芝这句诗作为标题” 。她说,“I am talking about the time I began to doubt the premises of all the stories that I’d ever been told or told myself.”
对Joan 印象最深的是她爱穿各种款式的羊绒羊毛衫。开衫,圆领,样式简洁而材质极好。喜欢长短的裙子,喜欢在耳畔别一朵花:白色栀子花和热带扶桑花。她的衣着风格中包含一位小女生,纽约时期vogue编辑,摇滚乐手女友,比弗利山庄party host,战地记者和作家。曾经读到一位专栏作者写的“That time I let Joan Didion pack my weekend bag”,里面包含:浅米色套头毛衣,两条短裙(麝皮包身短裙,黑白条纹伞裙),黑白色T恤,黑色长筒袜,两双皮鞋(一双中跟黑色凉拖,一双浅米色高跟),一双米白色家居皮拖鞋,真丝吊带睡裙,浴袍,黑色胸罩,mini 装Jack Daniel booze. Joan 的女友回忆,不知为何曾有段时间跟Joan夫妇同住在他们Malibu的住宅。早晨在厨房做早饭时,Joan直到很晚才从楼上慢慢走下来,戴着墨镜,直接走到冰箱从最底层摸出一罐冰可口可乐。就着盐杏仁吃。杏仁是她妈妈不间断寄来的。Joan坐在那里吃杏仁喝可乐,戴着墨镜,彼此不说话。纪录片中被问及冰可乐的事,Joan说,我每天早晨必须喝可乐,必须非常冰。“if someone took the last can of my coke, we would have a scene at the kitchen”。我想到自己每天早晨的酸奶燕麦或者炒饭,感到人和人的差别真是很有意思。
镜头中Joan回答问题的姿态是手舞足蹈的,仿佛被密布的乌云或者纷繁的念头笼罩,必须努力把它们抓开才能清晰地将自己的回答呈现出来。Joan给人一种果断的印象。每个问题落音时,她会毫不犹豫的一口报出答案,挥舞着双手说出答案,然后陷入沉默,一种哀悼式的沉默。仿佛问题和答案将她扯回曾经境地。唯有被问及写作 "Slouching Towards Bethlehem" 的1960年代,当她看见嬉皮士盛行时新闻爆出三岁孩子坐在地板上手拿迷幻药是什么感觉,她挥舞着手,琢磨了片刻,回答,“Gold”,又补充,“good or bad. For someone who was working on a piece, it was gold.” 这种近乎冷酷的状态,我曾她对自己私人生活的描写中也读到过。记者问道,John(Joan的先生 John Dunne,同为作家,剧作者,文学批评家)有没有读过你对婚姻生活的描写,对此有没有意见?Joan说,he edited it. We didn’t have any type of agreement, we were just working on our own materials.她的许多作品都经过先生阅读和编辑,"They were the type of couple who finishes each other's sentences”. The type of couple who finishes each other's sentences. 她曾说,一直知道自己的婚姻伴侣也会是一位作家,否则会很难有耐心。她也说到,John不是脾气那么好的人,容易生气,“什么样的事情令他生气呢” “一切都令他生气。”
读过Joan作品的人知道他们之间的情感和彼此依赖。她说 “I enjoyed being a couple”,喜欢有个人在身旁。想到在“the year of magical thinking”里她如何送走挚爱,承担生活变故,无时无刻的变故。让人很心疼镜头中这位瘦瘦小小的白发女子。纪录片讲述到2003年圣诞,新婚的女儿Quitana被送入ICU,我按下了暂停没有再看下去,不忍心,也没有做好准备。 镜头中Joan的客厅摆放着成堆而整齐的书。从匆匆一瞥的镜头中辨认出: "The Catcher in the Rye", J.D. Salinger "100 Selected Poems", E.E. Cummings "Later Poems", W.B. Yeats "Soul on Ice", Eldridge Cleaver "Leaves of Grass", Walt Whitman, "The Captive", Marcel Proust "Against: Interpretation and Other Essays", Susan Sontag.
Joan的书单令我仰慕且感到亲近——她对诗歌的态度,尤其是对Edna St. Vincent Millay的热爱。“Childhood is the kingdom where nobody dies”, 在“The Last Love Song: A biography of Joan Didion” 中记载,面对死亡她总会想起米莱的这句诗。纪录片在呈现她写给 Vogue的第一份专栏文章(“Self-respect: Its source, Its power”)时 ,贴出了一系列给予Joan启发的作家,诗人,和艺术家——其中第一位出现的便是Edna St. Vincent Millay。作为米莱的读者,和首次将米莱处女座诗集《新生及其他》译介为中文的译者,我仍感到中文阅读世界对于Millay的认知处于低估阶段。对于Joan也是。
7/3/2020 Sources mentioned: Documentary, “Joan Didion: The Center will not Hold”, 2017, Griffin Dunne “The Second Coming”, 1919, W.B. Yeats “Childhood is the Kingdom Where Nobody Dies”, 1937, Edna St. Vincent Millay All photos were shared from the Inter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