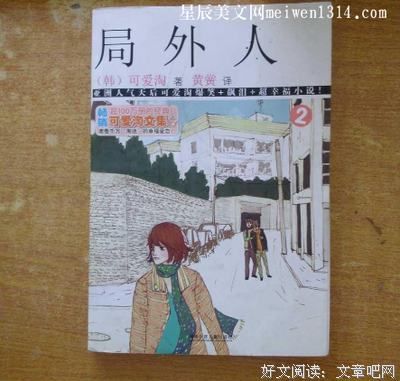
《寻找《局外人》》是一本由[美]爱丽丝·卡普兰著作,新星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98.00元,页数:36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寻找《局外人》》读后感(一):与《局外人》同行,与加缪同行
《局外人》是阿尔贝·加缪的经典作品,它早早奠定了加缪在法国乃至世界文学殿堂中的地位,至今仍以深刻的内涵引发众多读者的思考与讨论。
真正深刻的作品往往却以简约的表象为载体。《局外人》一书文字洗练,故事情节简单,人物关系也不复杂,但其中饱含寓意的景物描写、直触人心的人物语言和内心活动、意味深长的比喻,都让人读后不禁久久回味,同时也会好奇这些没有雕琢痕迹的内容究竟出于作者在何种境况下的何种心境。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爱丽丝·卡普兰对《局外人》的探源可能会充分满足“加缪迷”的好奇心。她在加缪的书信、笔记、有关档案中寻找加缪酝酿《局外人》的思想痕迹,从加缪的生平经历中发现作者在作品里有意或无意的自身投射。
通过卡普兰教授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到:《局外人》的成型是长期的过程;加缪和《局外人》的联系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加紧密;我们对于二者的之间某些猜想也得到了证实;作品的问世并非一帆风顺。
卡普兰教授发现,加缪早在1937年7月的旅行中就写下关于“局外人”的第一条最明显记录:“一个男人,在人们通常视为人生大事的地方(婚姻、社会地位等等)寻找人生,然后某天在翻阅一本时装目录的时候,突然醒悟他对于他自己的人生是怎样的一个局外人……”
当然,加缪脑中关于这部作品的零星想法一定更早出现,但看见纸面的痕迹令人更加兴奋,让人仿佛参与到作家的创作中。而最激动人心的痕迹是加缪于1938年8月写下的开头,与作品完稿的开头一字不差。《局外人》的开篇简练却深刻,印入读者的内心。如果不是读到卡普兰教授的研究,相信很多读者都未想到如此经典的开头却这样早地被一气呵成。
小说开头提及的丧母事件实际上影响了主人公的命运,也隐隐贯穿整部小说,“母亲”的概念是小说的重要元素。加缪一生面对着因家庭压力和疾病而寡言少语的母亲,贫困与疾病使他跟不得不跟着叔父生活并成长,他也有些像小说主人公默尔索那样经历母亲在日常生活的失位,至少与母亲若即若离。
小说中关于主人公直面母亲死亡及丧礼的描写也令人印象深刻,其他人的表现和谈话,出丧时的炎热与沉闷气氛,都让读者感同身受,从而似乎也更能理解主人公的感觉。而这些也能在加缪的笔记中找到痕迹。他在1938年5月参加了一场在老人院的丧礼,之后两次在笔记本中记录了一个小个子老头,描写其跟随送葬的队伍,踩着泥泞的小道走到教堂,到达墓地。他的记录与小说中相关情节如出一辙,我们可以肯定这场丧礼给作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为他盘旋在脑中的小说原始画面提供了定格的思路,那个后来闻名于世界文学史的开头则是他自信决定的“开机画面”。
小说的另外两个重要元素分别是默尔索卷入与阿拉伯人的纠纷、庭审中的辩论现场。而这些都与他在《阿尔及尔共和党人报》任法庭记者的经历有关。在庭审现场,加缪多次见证阿尔及尔社会中欧洲人与阿拉伯人的冲突,也熟睹法庭辩论的众生百态,这些也最终都反映在小说中——默尔索莫名其妙地纠缠到朋友与阿拉伯人的矛盾中,在法庭受审期间,律师与检察官自我表演式的发言,用语言和所谓正义操控陪审团的决定,同时,媒体舆论也在引导和煽动民众情绪。
卡普兰教授从加缪的记录和生平中找到了对应《局外人》主要情节的部分,像为寓言找到现实中的化身。其过程不仅为我们带来“原来如此”的畅快,还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作品的现实意义和加缪的心路历程。而卡普兰教授发掘《局外人》成书、出版的过程,则像是给《局外人》的拥趸以“额外奖励”。
加缪对于自己从事写作曾犹有信心,在成名后也愈加意气风发,但我们可能难以想到,当他将《局外人》初稿寄给自己引以为重的文学老师格勒尼埃时,却遭遇了严厉批评,加缪倍感失望,不过,万幸的是,加缪的好友帕斯卡·皮亚阅读后却坚信这部作品是“最顶尖的”,并将手稿交给当时的法语文坛领袖人物安德烈·马尔罗,后者同样赞赏这部作品,不仅为提出修改意见,还将其推荐给法国著名的伽利玛出版社。加缪成名由此开始。
如果说加缪的老师的眼光和批评差点扼杀未来的世界著名作家,那么纳粹出版审查机构则很可能改变《局外人》的文学史轨迹,延宕加缪之后的创作,甚至扭曲作家命运。加缪于1940年5月1日凌晨完成书稿,而法国于其后数十天便全面沦陷,所以《局外人》的出版不得不由纳粹来左右,并同样幸运的是,纳粹审查人员认为这部作品并未犯禁,故而放其完整出版。1942年,经历波折的《局外人》终于出版,时年29岁的加缪迅速成为法国作家的新星,真正开始在文学史上写下了属于他的一页。
几十年来,一定有众多读者从《局外人》里寻找加缪的影子,也一定有不少人认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作者的“传记”,只是这些都存在于猜想之上,而《寻找<局外人>》则是令人兴奋的验证之旅,找寻之旅,解密之旅,更是与加缪同行之旅。
《寻找《局外人》》读后感(二):经久不衰的《局外人》,加缪是怎么写出来的?
加缪和《局外人》,早已融为一体。提前者,必接后者。举后者为例,定不离前者。这也难怪,毕竟此小说对加缪的意义颇大。是它,让他跻身文坛。此后,论及作家,绕不过加缪;谈及作品,亦舍不下《局外人》。
向来,一部影响时代的作品,不禁会勾起读者的好奇:它是怎么进入作者头脑里的?不知你在读《局外人》时,是否有此疑惑?想我初读那年,若不看创作年代,或不识作者,会误以为是当下某个作者所写,字里行间的情绪竟毫不陌生,透着荒诞与滑稽。
加缪在写默尔索的故事前,已经完成了《快乐的死》。然而这本书并不令人满意,他曾在手记里写道:重写小说。至于重写一说,是继续完善《快乐的死》吗?彼时他并不确定。而此时答案已揭晓,这本重新写就的小说,将以《局外人》的新面貌出现。
“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在昨天,我搞不清。我收到养老院的一封电报:‘令堂去世。明日葬礼。特致慰唁’。它说得不清楚。也许是昨天死的。”熟悉的开篇,加缪写于1938年,他只有25岁。
开篇已定,接下来的故事碎片,紧紧拉扯他的神经。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加缪为默尔索安排了一系列言行,可能不符合常理,但符合主人公的性格。他将现在时、过去时和将来时混杂起来,时间的谜团耐人寻味。
加缪时刻在思考,或内容,或结构,因而仅是完成第一章,以极费心力。毕竟灵感不易得,更多时候写作是凭借坚持。
他发觉:“真正的艺术,是说的最少的。”表达情绪不必句句写透,笔调简明并非无情。有此经验后,接下来只需耐心写下去。
时间一晃有两月,《局外人》已写到第六章,第一部分即将完结。作为全书的中点,作者想给读者一个喘息的空间,他如此比喻:“这就像在苦难之门上急促地叩了四下。”默尔索的命运暂时停住,读者也别心急,不妨多看几眼毁灭的命运。
加缪用小说的第一章,给读者介绍了一位新朋友。又用小说的第一部分,让读者与这位朋友熟络起来。我们无法中途弃之不顾,更不想沦为他生命里的局外人。仿佛成为他生命的见证者,比生死本身重要。
1942年,《局外人》出版了。随之而来的有褒奖,亦有批判,都属正常现象。书籍一经出版,即便作者不想置身事外,大约也只能本着顺其自然的心态。在众多的批评者中,萨特的评价影响力最深远。
日后,人们将加缪和萨特看作“双子星”,想当然的认为两人的观点一致。但实际上,加缪主张:“人是其自身的目的。”他认为自己的书是“反存在主义的”。他所探讨的是:“人在世界这个背景下的渺小,自然对人无动于衷的敌意。”至于萨特,他认为:“重要的是人的意识,人们之间相处融洽,或无法相处。”
以萨特的代表作《恶心》,加缪的代表作《局外人》为例,前者的主题是对他人的厌恶,后者则是表达世界对人的漠不关心。可见无论两位作者,还是两个作品之间,都没有外界认为的紧密的关联。
即便有,如果通过将两人的作品进行对照,提升一方,打击一方,实在是没必要。
我仅以一家之言,谈谈加缪写《局外人》时的三个“密码”。
他的小说离不开真实生活,比如:加缪曾在1935年阿尔及尔的一份报纸上,读到某个故事,让他无法忘怀后,在《局外人》里他会提到这件事;再比如:默尔索来到塞莱斯特的咖啡店吃东西,大肚子的塞莱斯特和加缪的叔叔神似......
类似取材于生活的人物或片段,经过加缪的细心观察和刻意保留,当他们出现在小说里时,竟有种化腐朽为神奇的意味。有些人事你也见过或听过,但作家与你不同,他们不会让所见所闻如风拂过,而是会将这些人事制作成印戳,再按下用思想制成的印泥,而后以各种图样存于纸上。
一旦开始创作,加缪的脑海里便时时刻刻都有一根无形的笔,日夜写着。他已在脑海里修改过无数次,添添减减,时间已融入写作里。创作的恒心最难得,加缪日复一日地写,已然化作时间。
加缪所创作的人物绝非毫无目的,谈及默尔索,他说:“我从他的身上看到了某些正面的东西,那就是他的拒绝,拒绝死亡,拒绝说谎。说谎不光是指说出一件不实的东西,也指为了迎合社会而接受说出一些自己并不知道的东西。默尔索不在法官的一边,也不在社会的一边,也不在传统感情的一边。他存在,如同太阳底下的一块石头,风,大海——这些东西从不说谎。”
不了解作者的创作原因,就像吃一道美食仅关注感官带来的感触,而忽略与其相关的种种先前或当下的故事。假如始终不解也不碍事,断不会影响味道或口感,但倘若知道更多,体验总归会不同。
写到这儿,我便要再提本书,因为它能帮你解密《局外人》,日后你想起或重读,收获必将不同。
《寻找《局外人》》读后感(三):《局外人》的前世今生
文艺小青年们,一定不会对“加缪”这个词汇陌生。哪怕以前没听说过,2020年,你也一定在铺天盖地的公号文章中注意到一本书《鼠疫》,没错,她的作者就是加缪。
加缪在1960年去世,如果按照《寻梦环游记》中的说法,人只有被整个世界忘记了,才算真正的死亡,那我们可以说,加缪在1960年肉身活过,但是1960年以后,他不但不会死亡,而且会迎来一个又一个精神在世的高光时刻。
伟大的作品,之所以伟大,大概就是以一己之力诠释“永恒”,虽然它本身,并未希求过永恒。在当下的时代里,人们可能还认识不到其作品的永恒价值,但是时间不会说谎,时光会自证。加缪的文学,还不完全属于那种属于未来的,因为,在他作品一问世,他便跻身那个时代最著名的作家行列,而且加缪本人还很帅,放在我们这个时代,就是妥妥的流量扛把子。外界一直有一种看法,也是本书作者所认同的:加缪太耀眼、太迷人——他是一位政治活动家,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这令其写作生涯与他的人生故事相比黯然失色。假如他相貌平平或为人凡庸,或许人们会更关注他的写作。
人到底和他的文是分不开的,但是到底是文成就人,还是人掩盖了文的色彩,这种吊诡的迷惑感一直在加缪这个人身上存在,他本人就是个充满神秘气质的人,是个可以无限探究的宝藏,所以,当你看到一本写加缪传记,写加缪其人其事的书这太正常不过了,寻找《局外人》的作者爱丽丝·卡普兰却是另辟小径,她要写的是加缪的小说的传记,或许就是为了把他的写作从他人的耀眼下拽出来,让世人看到小说的耀眼。所以,在这本传记里,疏离感一直是存在的,绕不过去谈加缪其人,但是又不愿意放更多笔墨在他的人身上,以防喧宾夺主。对世人最好奇的加缪八卦——他的死亡,仅是一笔带过,要知道,这场车祸,直到今天都是民间谈论最多的一个悬案。加缪的政治生涯,他是否一个存在主义者,这些,作者都没有进行深入地解读,请记住,这本书,洋洋洒洒三百多页,只为探寻《局外人》的前世今生,甚至,连《西西弗的神话》和《鼠疫》都只是提到。
一部作品的生命到底是如何来的呢?作者探究到一个结论:普鲁斯特在盖尔芒特家的下午茶会上提出,我们的在艺术作品面前根本没有自由可言,我们不是依据我们的意愿去塑造它,因为它先于我们而存在,这既是因为它是不可避免且隐藏着的,也因为它是,它原本就是自然的法则,我们需要去发现它。
这就可以理解在写出《局外人》之前的加缪的焦虑了:每发现一个热爱的作家,加缪常常感到一阵强烈的嫉妒(这大概是作者主观的臆想,毕竟我们普通人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对那些伟大的作家产生这种具有平等性质的情感的),还剩下多少自己能说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小说家感到欧洲模式已经穷尽,1944年,爱尔兰英国裔批评家康诺利曾精准地表达了这种情绪“福楼拜,亨利·詹姆斯,普鲁斯特,乔伊斯,弗吉尼亚·伍尔夫已经终结了小说。”
在整个文学界,都认为小说已经写到顶了,世界需要一个爆发,需要“推倒重来”,《局外人》有些时势造英雄之感,世界需要这个爆发点,它是历史的必然,先于《局外人》问世之前,《局外人》就存在了,加缪是发现它的介质,它是自然法则。《局外人》属于历史,属于自然,属于时代。
甚至加缪本人也时而困惑,作家一旦进入这个神奇的文学世界里,他并不能很确定地说他创造了什么,还是书里的人物自然推动着他来讲述。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活着是为了讲述。到底作家和他的伟大作品之间谁从属谁,传记作者也不可能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因为本来就没有答案,答案就是在这个亟待一部伟大作品的爆发点上,《局外人》横空出世。1940-1942年,世界乱得可以,《局外人》的出版也不是一蹴而就,手稿绕了欧洲一大圈,有人为此激动得发狂,而加缪想要得到肯定的老师却很克制,给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纠结的评论,这一段读起来不啻于一部惊险小说,它让人想到了《最危险的小说》——为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而战,整个过程中你都很担心这部伟大的小说手稿遗失,被政治迫害,被时代所误,甚至被他人盗用,被不懂行的人嗤之以鼻——虽然,2020年的我们,常识告诉我们,这些都没发生,感谢这些在这本书出版过程中出力的人们,虽然历史记不得他们的名字,但是爱丽丝·卡普兰挖出来了,厚厚的一沓感谢名单,作为读者,我们也应该感谢他们。
及至现在,《局外人》已经成为独立的生命个体,一本书,它是可以傲然独立存活于世的,它的生命力,显然比作者本人要长许多,未来的日子,作者还要依仗它的生命力活下去。这是传记作者宏观的认知,显然,我们不能盖棺定论说,既然一本书是历史必然是自然存在,那我们大家都躺在床上等待它出现吧,这终于是绕不开加缪一直否定的存在主义,萨特说,懦夫使自己成为懦夫,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历史的必然必然也是需要人的主观能动的,加缪发现《局外人》之路,值得用一部书来书写,但是他内心的波折、痛苦与矛盾,却只有他自己知道。
我们看到,他写了一部不成功的书,最终没写完,但是部分元素融入了《局外人》;他做过记者、编辑,他随时随地观察生活、记录生活,他在不喜欢的地方孤独地与疾病独处……林林总总,任何人都不可能说哪一个细节造句了《局外人》,但是没有哪一个细节,又可能指不同结果。
这本属于所有人,属于人类的书,值得有一本这样的传记。
《寻找《局外人》》读后感(四):为《局外人》立传
这是一部传记,传主是一本书。
自1942年出版以来,加缪的《局外人》被翻译成六十种语言,累计售出上千万本。在中国,几代翻译家翻译过多个版本,即使你没读过,也一定听说过。阿尔贝·加缪,这个阿尔及尔贫民窟里走出的孩子,如何能在二十六岁就拿出这样一部震撼世界的作品,并且在七十多年后仍然被不断地阅读?加缪尽管已经去世六十年,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重新被讨论,进入人们的视野,而围绕《局外人》似乎总有无法穷尽的迷等着人们去揭开,这本薄薄的小书到底为何有这样的魔力?
爱丽丝·卡普兰是耶鲁大学法语文学教授,著名法语文学研究者和译者,她在大学里开设法语文学阅读课,常常会带领学生用一个学期的时间完成全部加缪作品的阅读。其中,尤以《局外人》的讨论最为激烈。“阅读《局外人》犹如一场成人礼,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将这本书与自己的成长紧紧相连,借此展开对存在的艰难追问。”最近对作者的专访中,她提到她的一个学生将《局外人》中海滩谋杀的场景纹在了自己身上。
关于阿尔贝·加缪,那么多的作家、批评家已经说了那么多,还有什么可说的?作者认为,对作品的理解还有不少东西是缺席的,一直以来,人们把《局外人》这本书的存在当做是理所当然,并且常常不自觉地,对作品的讨论变成了对作者的关注。所以,这部书值得有一部传记,作者说:
“从加缪的手记与书信中第一次出现这部小说的蛛丝马迹开始,我逐年追寻着它的创作历程,从写作中的作者,到落在纸上的字句。我采用的方法接近虚构类写作者所说的“近第三人称叙事”(close third person narrative),我一连数月追踪着加缪,仿佛从他肩头看下去一样,尽力用“他的”而不是我的视角来叙述这本书如何诞生。我力图最大限度接近和还原加缪写作《局外人》、将手稿发出请人评估、在战时法国出版等等经历,以及他的心理历程。”
作者的连续追踪,让我们能体会“创作”这一神秘过程的有迹可循。贫病童年经历,对荒诞的感悟,父亲留下的唯一“遗产”——关于死刑的记忆,大学文学圈子的相互激励与启发,那部无论如何也不成立、躺在抽屉里的失败之作《快乐的死》……这些都慢慢积攒在年轻作家的心底;一次偶然的葬礼见闻,朋友在海滩上的一次打斗的经历,当上记者的加缪见证的不公正的庭审,以及忙碌的记者闲暇时的阅读和观看的流行电影,在作家不自知的情况下悄悄进入了他的笔记、他的构思。如同拼图般,创作的历程被一块一块地复原和完整了。
作为从业者,我也特别关注到《局外人》出版的过程是一个出版史上尤为惊心动魄的故事。伽利玛和《法兰西文学评论》在二战时期的艰难历程,几乎是法国知识界抵抗运动的缩影,而新书能够越过封锁线、避开审查得到出版本身,似乎也象征着某种胜利。
对不少读者来说,“马尔罗因素”这一章详细评述了安德烈·马尔罗对《局外人》手稿的修改,可能是一个令人满足的惊喜:这段故事并不那么广为人知,而这个修改的过程,不光体现马尔罗的激情,也是文学修改的极好案例。“马尔罗建议,也许,只需要再添加一小段,强调一下强烈的阳光和阿拉伯人的刀子。”而同样,在《局外人》出版后,著名哲学家萨特对其发表的重要评论《〈局外人〉解说》,几乎是一锤定音地将其提升到法国文学殿堂的一流地位,“他写道,小说的每一个句子都是一座岛,相邻的句子被虚无隔开。”用这样的句子,加缪创造出一个“被动的、无动于衷的、拒绝交流的、闪光的”世界。萨特熟练的评论,尤其是对加缪语言风格的分析,对我们如何定义“好文字、好作品”带来不少新的思考。
作为美国人的作者并未止步于此,确实,假如《局外人》只讲法语,它远远不会到达今天所到达的地方。《局外人》在美国和英国的同时出版也同样有趣,尤其是,为何在美国被翻译成The Stranger,在英国被翻译成The Outsider,这个问题得到了回答,原因竟完全不是文学的考虑;还有,一直声称自己不是存在主义者的加缪为何被认为是“存在主义”作家?这竟与1946年美国出版社对他的宣传有关。加缪的美国之行还惊动了FBI,那位负责的探员为完成任务不得不研究存在主义哲学的主要主张……此外,中国读者可能很少意识到,民族问题在这部小说中是一个重要的暗线,那么阿拉伯世界是如何看待这个“杀死一个阿拉伯人”的小说的呢?
当然,这部“书的传记”本身也是文学批评,也可以为理解《局外人》提供不少帮助。《局外人》不同于《鼠疫》,是一部矛盾的书,我们可能都见过一些人读后觉得很不以为然甚至被激怒: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这个人杀了人还毫无悔意?作为道德完人般的加缪为何会写这样一部作品?它的复杂难懂,令人困惑,才赋予它文学的生命力。文学批评也有潮流,通过展现而不是武断地加上自己的评判,作者带我们领略七十年来这本书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起伏变迁。
作者使用她出色的文献资料的耙梳能力,几乎穷尽加缪及师长友人的书信、日记、手稿中关于《局外人》的蛛丝马迹,再加上同时代的其他文献资料:电影、报纸、杂志专栏、地方志、出版史等等,并用令人惊叹的叙事性手法将它们编织在一起。
当时在正文翻译完成之后,我鼓了很长时间的勇气才去继续翻译“致谢”,为何作者的“致谢”会如此之长,其实这长达六页半的致谢,展示了她的资料来源和研究过程:三个大洲的学院和文学研究室、图书馆、资料中心的资料查询,写作期间的学术讨论和交流,与研究者和专家以及见证者的访问和座谈,以及带上摄影师对加缪居住之处、所到之处的探访。所有这一切都是专业性的保证,即便你是“像集邮一样收集加缪”,也能在这本书里发现你此前不了解的东西,同时,也能给有志于学术研究的同学们提供不少有趣有益的启发。
然而,只是资料的罗列是不远远不够的,这是一部像推理小说般的文学史,它不乏细节,也不乏令人感动的相互呼应。我想作者文笔的特点可说是“绵密周到”。她运用同情的联想,来阐释安排这些资料。我会建议大家读的时候不要忽略注释,注释里不光指出了资料的出处,也有不少有益的补充,放进正文中似乎会偏离文意,但对关心《局外人》或加缪的读者来说又是非常有趣的线索,例如,加缪作为《阿尔及尔共和党人报》的记者去报道著名的“奥克柏案”时,看到治安官威朗法官对着被告挥舞一个十字架,正文中引用了加缪为报纸写的报道,同时,在注释中,作者补充道:“在后来的法庭审议中,有位聪明的律师指着那个十字架提醒陪审团注意,耶稣基督本人就是不公审判的第一个受害者,加缪对此事乐不可支。”
再举一例,这个片段也出现在注释之中:
十年后,加缪将把他创作《快乐的死》时痛苦的失败经历用于塑造他最心爱的人物之一,约瑟夫·格朗,即《鼠疫》中的一位公务员,此人发誓要成为作家,每天都在为寻找合适的词语而寝食难安,总是把开头的一段话重新写了一遍又一遍。在《鼠疫》的结尾,从鼠疫中奇迹般生还的格朗终于对他的第一段感到满意了:他删去了所有的形容词。很难不做出这样的结论:加缪在向十年前的自己眨眼,他仍能清楚地记得自己的痛苦,过于浮夸的风格,最终又是如何矫正了它。
这些当然可以单纯只看做是对文学创作手法的追踪,然而我们会关注到这些细节并为之心中一动,正是文学对我们的馈赠。
作者的“同情的联想”最大地体现在终章。加缪研究者们似乎都知道《局外人》中,海滩斗殴谋杀是有原型的(甚至那个海滩成了“局外人海滩”),作者找到了斗殴事件的报纸报道,并去寻访了那次事件中的阿拉伯人。那个阿拉伯人有了名字,前所未有地变得具体了:他属于当地望族,英俊异常,能说四种语言,有一个欧洲人女朋友,他的姐姐还健在,说着优雅的法语,用精美的点心招待一个从遥远的大洲来的文学研究者……而且,他与加缪一样身患肺结核,曾经在法国山区疗养。作者”情愿用这样一种和解的幻想来结束对《局外人》的探寻:卡杜尔·多依和阿尔贝·加缪,他们在各自的山居疗养院内,疗愈着。“在七十多年后,这种幻想令人满足,给人安慰。
文学给人留下的空白就是需要用这种同情的想象去填补吧。这次我征得父亲的同意,使用他的小名”琴岗“做笔名。这个名字是我的祖父给他起的,祖父年纪轻轻就去世了,“琴岗”与加缪一样,是失去父亲的孩子,母亲给与的是一种沉默的爱。如今父亲已经比祖父母活过的年纪加起来还要多。当我第一次读到《第一个人》中,”葬在这块石板下的男人,那个曾是他父亲的人比他还年轻“那一段动人的陈述时,不可抑制地想到我的父亲与祖父。祖父盛年去世的原因?正是肺结核。
《寻找《局外人》》读后感(五):加缪:做一回《局外人》的局外人
我有一个突发奇想:加缪荒诞意识的最初萌芽,可能首先源自于他的肺结核病。
默尔索多次提到自己因为身体的疲惫、厌倦、不舒服导致了他一些行为在常人看来的“不可理喻”,比如他走了很长的路疲惫不堪但又要为母亲守夜,比如早上没有吃饭空腹去下海游泳导致身体不舒服,被毒烈的太阳刺激到杀人,比如在庭上本来想说什么又觉得说不说无所谓。
这种“生理”因素导致的厌倦、冷漠,事事将自己抽离出来的行为反应可能与加缪本人的肺结核病有某种关系。年轻时代的加缪深受肺结核病的折磨,这让他无法参军,甚至无法取得教师职业资格。这种病症所带来的生理上的不舒适可能深刻地影响了默尔索的行为和思想。
一个人的行为受制于自己的身体,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并不是说,这只是一种机械的、朴素的并无深意的肉体反应。人如何会感到疲倦、厌烦和冷漠,从而以让自己抽离的状态去忍受或者不再忍受某些事情,这即便不是必然包含着荒诞意识的觉醒,也在为认出世界的荒诞提供一个契机。
有些书因为过于经典,常常被长久地放在“看过”一栏里,以为是已经翻篇的阅历而不必去调动,但如果有一次机缘让你重读,却像是在读一本从来都没有看过的书。最近重读《局外人》,就是这样一种感觉。
促使我重读这本书的机缘来自《寻找<局外人>》。简单说,这是《局外人》这本书的传记。为人做传很容易理解,为书做传就需要稍作停顿,然后想这也许是个好主意,但未必很讨好。直觉上讲,这很像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学评论或者作家评传,它也许充满了真知灼见也可能枯燥无趣。特别又是《局外人》这本篇幅不长的经典名著,能有什么可写的呢? 就像这本传记的作者所说,我们知道这只是来自“一个二十六岁、充满抱负的年轻写作者”的成名作,他“来自荒僻的阿尔及利亚,没有名气也没有其他作品,这故事似乎过于简单直接、不太容易血肉丰满”。
但作者同时认为像《局外人》这样一部革命性的文学作品,应该有一部与之相匹配的传记。因为它从诞生至今已经具有了独立的生命,这生命虽与加缪的人生相关,但他们已经是“不同的生命”。
而且作者认为,《局外人》从某种角度上说已经被加缪这个人的耀眼魅力所遮蔽了。“加缪太耀眼、太迷人——他是一位政治活动家,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这令其写作生涯与他的人生故事相比黯然失色。假如他相貌平平或为人凡庸,或许人们会更关注他的写作。”
这是一本关于《局外人》的真实传记,但它更像一本寻找局外人的悬疑小说。这是一个独辟蹊径的角度,作者“从加缪的手记和书信中第一次出现这部小说的蛛丝马迹开始”入手,采用一种近似小说的叙事方法,跟踪这加缪的生活轨迹,“仿佛从他肩头看下去一样”,所以这更像一次探险。读者可以跟在加缪的身后,看到他真实的母亲,而玛丽或许是他众多风流韵事中的一桩,那个发生了凶杀案的真实的海滩,被毒辣的太阳炙烤着的海浪和岩石,你可以找到那一年真实发生在海滩上的斗殴事件,甚至找到当事人的亲属与他们交谈。那个没有名字的阿拉伯并有死,但是他的命运却与加缪产生了某些神秘的关联。还有当地一位作家因为愤愤不平于阿拉伯人没有名字,而创作的一部《局外人》的同人文,为那个阿拉伯人创造了一个新的故事……
加缪所奉献给人类的价值远远大于一本《局外人》,但毫无疑问,是《局外人》首先在读者心目中点燃起魅力的火炬,在他还在偏僻的阿尔及利亚,尚未来到舞台中央的时候。所以当加缪出现在巴黎的报馆、剧院和咖啡馆,出现在抵抗运动的中心,出现在众人面前时,人们很容易把《局外人》的存在看做一个已经存在且“理所当然”存在的事物,而忘掉追究加缪究竟怎样写出来这么一本书。
事实上,这本书从写作到出版都关联着一个巨大的历史背景和作家特殊的个人命运。它的诞生隐含了一个法属阿尔及利亚底层白人的殖民地生活史和精神史,它的出版过程则和纳粹占领巴黎之后的出版审查、战时物资的管控等息息相关,这里面牵涉着复杂的人和事。
《局外人》完稿于1940年5月1日,十几天后,纳粹德国攻破法国并占领巴黎,而《局外人》则出版于1942年纳粹治下的巴黎。尽管它的出版得到了几个重要和关键人物的支持,但在战时的背景下,因为作者当时身在地中海对面的阿尔及利亚,联系和沟通非常困难,因为编辑拿到稿子的渠道来源不一,仅仅手稿的最终定稿就变得异常困难,还有战时纸张的紧张,使得这本书的出版变得困难重重。
而且,就算一切准备就绪,还要最终面临纳粹宣传部门的审查。有趣的是,这本书的审查异常顺利,纳粹审查官认为这本书没有必要做任何删节,因为这本书“缺乏社会性”,且“与政治无关”。而接下来要出版的《西西弗神话》则没有这个幸运,里面涉及到一篇关于卡夫卡的文章(《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与荒诞》)必须删除(不必点明因为卡夫卡是犹太人)。小说的“深意”在审查官看来不必深究,哲学论稿只要不涉及犹太人也予以放行,不得不说,纳粹的审查尽管严酷,还貌似还蛮有“可操作性”的。
《局外人》的写作与《西西弗神话》几乎是同步的。也就是说,当加缪在思考“荒诞”问题的同时,也在写作这样一部表达“荒诞”的小说。而这部小说对对命运,同时也在验证着这个世界的荒诞。我们尤其能够从这本《寻找局外人》中体会到这一点。
在“荒诞”被发现之前,加缪曾生活在一个“纯真”的年代,不过这个年代无比短暂。有趣的是,这本书中也几次提到“纯真年代”一词,但是作者和译者似乎都没有给出一个注释,纯真年代是指什么。我们或许可以想当然的认为纯真年代指的是德国发动战争之前那短暂的几年。但我觉得,这个“纯真年代”,在这本书中,也可以指加缪写作的不成功的早期,也就是《局外人》诞生之前的年代。这个年代结束的标志是他开写《局外人》和《西西弗神话》的时候,只是恰在此时,战争也爆发了。荒诞时代随着荒诞意识的觉醒而到来。
人们常常会思考《局外人》主人公默尔索与作者加缪的关系。主人公所生活的环境无疑与加缪重叠的,而默尔索的思想和处事原则代表了加缪的早期思想。默尔索的形象整体给人的感觉是隔膜的,模糊的,这个在当时是如此,但是当下的读者可能并不觉得默尔索的处事方式有多么“陌生”。这是因为默尔索从他诞生之后,已经开始在繁衍自己的人格世系。我的再次阅读《局外人》,与其说是对默尔索的一次唤醒,不如说是对之前印象的再次印证,默尔索已经不再模糊,他实际上早就无比清晰地生活在我们的体内。
默尔索身上最突出诚然是冷漠,抽离、与自己无关的处事态度,但是他对世界其实还有着某种最低限度的温柔。这个温柔的体现就在于,他感觉到世界其实和他一样是冷漠的,“我体验到这个世界如此像我,如此友爱融洽,觉得自己过去曾经是幸福的,现在仍然是幸福的。”在这里,默尔索的思想完成了和西西弗的对接:“他觉得这个从此没有救世主的世界既非不毛之地,抑非渺不足道。那掩饰的每个细粒,那黑暗笼罩的大山每到矿物的光芒,都成了他一人世界的组成部分。攀登山顶的拼搏本身足以充实一颗人心。应当想象西西弗是幸福的。”(《西西弗神话》)所以我们也就应该理解,为什么默尔索“为了善始善终,功德圆满,为了不感到自己属于另类”,而期望被处决的那天,“有很多人前来看热闹,他们都向我发出仇恨的叫喊声。”
加缪在西西弗与默尔索的双重探索中,完成了他的荒诞哲学的建构。从《寻找局外人》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默尔索如何从胚胎到成人的这么一个复杂而曲折的过程,在他生活的这个短短六万字篇幅的无限精微的宇宙中,从所有言说不尽的细枝末节里面,我们看到了加缪以无比清澈的眼睛所洞察到的世界的本质。
一部成功的作品传记,就是要让这部作品的作者成为这部传记的“局外人”,从而更加专注于作品而并非作家。假如我们承认一部作品在作家身体内部是先验性存在的,作家穷其一生只是要从自己身体内找到这部作品,那么,作品传记的目的就是从作品的视角去窥视那个作家的来路。《寻找局外人》就是这样一本书。
而年轻的小说作者或许能从这本书获得如下启迪:
第一,一个作家如何勇敢地否定自己最初的“成就”,哪怕那里面有很多自己无比珍视的“优点”和仅属于自己的“特性“,烧掉那些早期的失败之作,投入新的创作。
第二,对作品的反复修改,重写。“重写。重写的努力总会给你带来一些什么,不管是什么。对没能成功的人来说,问题就在于懒惰。”
第三:每天沉浸在自己的状态里,依靠手记保持自己的状态,记录自己关于写作的思考,或者一些日常观察到的片段的文学性练笔。你将从这些积累中慢慢发现那部期待你很久,等待你去发现的作品。
第四,当你终于找到它的时候,当你将那部原本就存在你身体内的小说发掘出来的时候,不要再怀疑,坚信自己的判断,以坚强的意志去忍受别人的质疑和否定,哪怕这些否定来自于你最信任的师长和朋友。
第五,交给最信任的人,放手,让它独自去面对所有的赞扬、批评和误解,并勇敢地为带来的一些可能的社会后果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