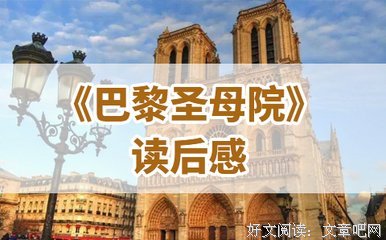
《巴黎印象记》是一本由陈季同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7.00元,页数:18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巴黎印象记》精选点评:
●译笔相当好,第二个序很雷,百年前的人尚且知道直腰,百年后还有人以折腰为傲,羞煞人。
●文字 老道。
●法季同法文作品之一
●2017.04.14。读的时候一直在感慨自己到底是中国人。
●读之恍若穿越的感觉
●前人的视角,还是不大容易理解
●很有趣,看一個清朝的人的紀事
●林则徐被贬边疆的时候曾经给朋友写信,说到对付英国的枪炮,关岳束手矣,同时小心地不得了地告诫朋友千万别把这件事告诉别人以免影响民心士气。中国西化西华,西化了近两百年,总到时刻给师傅交出点东西吓一跳了吧。
●被吹毛求疵的民族自尊心吓到了,虽然时代在那摆着,可是。。。
●清朝人眼中的巴黎
《巴黎印象记》读后感(一):[阅览室]
今天刚从图书馆借了这本书,只看了一篇【阅览室】,欣赏它对未来文化潮流的分析,信息时代人们的创作狂热达到了最高潮(比如博客),涨潮过后就会退潮;渐渐的,高潮过去了,狂热和仓促的创作就会停息下来了,一种新文学将会出现,它对自己的目的和方法,对自己的看法和倾向更有把握,它将浓缩这个精神生活极为活跃的世纪里最好的和最杰出的东西。
我很期待这个时刻的到来,同时将以此为勉励,减少低俗的文字作品.
《巴黎印象记》读后感(二):通过两位画家的故事来讲述印象派的由来
这本书是围绕两个人物的故事来讲的。他们代表了两种对立的审美追求,两个人的命运也是截然相反。
一个是法国传统画法的大师梅索尼埃,守旧派。选择了极致的精确,赌大众的审美不会变。
另一个是印象派的先驱法国人马奈,革新派。选择了模糊的印象,赌大众的审美会变。
只不过,马奈能赌赢,今天我们当然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他用全新的方式去描绘新时代的主题,好像提前预见了新世界的到来。但是马奈并不是先知,这中间有太多无法预计的偶然因素,像是拿破仑三世的政治意图,普法战争中法国的失败。
犹豫一些偶然因素,促成了两次“落选者”的沙龙,让主流审美本来不可能接受的主题和画法,展现在大众面前,转动了历史的车轮。
第一次意外的画展是1863年的巴黎的“落选者沙龙”。马奈那张本来在任何一届沙龙都不可能展出的作品《草地上的午餐》,就因为拿破仑三世这一转念,注定要跟大众见面了。1863年的“落选者沙龙”,放大了马奈的影响力,影响了一大批年轻的印象派画家,同时扰动了原有的审美体系和市场标准,但是未来要往哪个方向走,其实还不明朗。
1873年这届沙龙重复了1863年的剧本,又有一大半的画家没有入选。这群被沙龙排斥的画家,呼吁要再次举办落选者沙龙。但是,这次可没有拿破仑三世给他们助攻了。于是,一部分落选的年轻画家自己筹资举办了画展。当时有记者写文章嘲笑这群自不量力的画家说:这些马奈先生的门徒们,只会画朦胧的印象,就是“印象派”。没想到,嘲笑声居然定义出了这个伟大的艺术流派,让这群画家结成了一个团体,开始以画派的身份举办巡展,向世界宣扬自己的审美主张。
《巴黎印象记》读后感(三):高雅的使者
在索邦大学的阶梯教室里,在法语联盟的课堂上,一位中国将军——陈季同在讲演。他身着紫袍,高雅地端坐椅上,年轻饱满的面庞充溢着幸福……他的演讲妙趣横生,非常之法国化,却更具中国味,这是一个高等人和高等种族在讲演。透过那些微笑和恭维话,我感受到的却是一颗轻蔑之心:他自觉高于我们,将法国公众视作孩童……着迷的听众,被他的花言巧语所蛊惑,报之以疯狂的掌声。
——罗曼·罗兰
摘自1889年2月18日的日记
在罗曼·罗兰看来,我们的外交官(将军)的形象大概也符合他心目中的中国形象:高雅而又高傲。不过在我们的外交官心里,又是怎样的一种感觉呢?要知道,他的朝廷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局,而这个大变局的另一个参与者正是认为他有些高雅又有些高傲的罗曼·罗兰所在的西方,这时候,我们的外交官该如何“高雅”,又凭什么“高傲”呢?
问题就在这里,在强势的西方近代化浪潮下,一个看起来古老而又显得封闭停滞的文明,凭什么表现出一副“高傲”、“高雅”的姿态,尤其是在强势的西方面前……他们认为自己才是世界上最文明最先进的代表,才有资格“高雅”而又“高傲”。也许你会想起那些井底之蛙,一无所知却也敢在别人面前趾高气扬。但在这里,陈季同的境遇就不一样了,因为他是在欧洲的法国、法国的巴黎,能让他见识埃菲尔铁塔以及各种欧洲近代文明成果的巴黎(陈季同参观过巴黎的万国博览会)。
如果是我,我会怎么想呢?其实,一百年过去了,我觉得我们的问题还是没有什么变化。西方依旧“引领”着全球的“进步”,中国依旧在自己的文化建设之路上蹒跚而行。于是乎,我要问一下自己:我敢在西方面前表现出即使没有达到“高傲”的程度也至少显得有些“高雅”的样子吗?可能我别说是回答这个问题,甚至连什么是“高雅”也弄不清楚,并且我已经没有办法回到过去再问一下罗曼·罗兰为什么会觉得陈季同“高雅”。
我没有底气,是因为我对自己一无所知。我对自己一无所知,是因为我一无所有,因为我跟自己所在的群体之过去断绝了,我仿佛变成了一个毫无来头的野孩,在旷漠里一遍一遍呼唤着妈妈的名字……我是谁?!但陈季同和我们不一样,他还有着这样一个可以回答他的母亲,他和母亲还没有断绝。罗曼·罗兰说他“高雅”,至少说明罗曼·罗兰识得“高雅”,并且还看出了这“高雅”背后的“高傲”。我说过,陈季同不是井底之蛙,也没有办法装糊涂作井底之蛙,他必须在法国人、欧洲人以及被称为“西方人”的所有人面前,让他们“报之以疯狂的掌声”。
《巴黎印象记》读后感(四):曾经,有那么一座桥……
十九世纪末,历经两次鸦片战争,中国与欧洲的关系日趋紧张,欧洲人对中国普遍存在着明显的蔑视与敌意,中国被妖魔化为一个独裁专制的国家,国民愚昧无知,男人狡猾懒惰,女人则干脆就是缠着小脚、连路都不能走的怪物。这时,一位来自于中国的外交官,不遗余力的做讲座、写文章,力图消除加于中国头上的一切误解与诬蔑,将一个真实、美好、善意的中国展现给欧洲。他,就是陈季同。
陈季同(1852-1907),字敬如,福建侯官人。1867年,陈季同考入福建船政局法文学堂,1875年毕业后随即在船政局洋监督日意格的带领下赴法国学习一年。随后,在1877年,福建船政局正式选派陈季同等35人作为清政府首批派往欧洲的留学生赴英、法学习,这其中还包括许多日后的风云人物,如严复、马建忠、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萨镇冰等。和大部分留学生进入海军学校或船厂不同,陈季同与马建忠受命进入巴黎政治学堂修习“公法律例”,同时担任留学肄业局文案和使馆翻译。数年之内,陈季同历任翻译、武官、代办,最终被任命为中国驻德、法使馆参赞。由于法语的娴熟、对欧洲文化的深入了解以及开朗热情的个性,陈季同逐渐成为当时欧洲外交界的活跃人物,与俾斯麦(1815-1898)、甘必大(1838-1882)等德、法政界要人关系密切,还曾经受邀和时为皇储的德皇弗雷德里希三世一同骑马散步。从1884年起,陈季同以法文陆续出版了一系列介绍中国的著作,并很快被翻译为英、德、意、西、丹麦多种文字,引起了欧洲社会的极大关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时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1]
在这些书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出版于1892年的《吾国》。《吾国》收录了陈季同在欧洲撰写的十一篇文章,第一篇是曾经于1890年出版过单行本的《中国的社会组织》。在这篇长文中,陈季同将家长制作为中国社会组织结构的核心,将孝道作为社会的根本基础,基于这些原则,陈季同不露声色的就倍受欧洲人抨击的封建专制、司法上的连坐制度、溺婴、包办婚姻、多妻制等等弊端陋习一一予以辩护。对于今天的读者,这些制度本身是否合理已并不重要,而陈季同立足于文化本质的论述则显示出独特的逻辑魅力,其中最典型的是对于多妻制的解释。
多妻制历来为西方人所诟病,如何解释这种制度的合理性是很困难的问题,林语堂就曾说:“辩护娶妾制度是废话,除非你准备同时辩护一妻多夫制。辜鸿铭……曾经辩护过多妻制度,他说:‘你们见过一把茶壶配上四只茶杯,但是可曾见过一只茶杯配上四把茶壶吗?’这一个比喻最好的答辩莫如《金瓶梅》里西门庆的小老婆潘金莲说的那句话:‘哪有一只碗里放了两把羹匙还会不冲撞的吗?’潘金莲当然不是无意义的说这句话的。”[2]
但是林语堂说出这段话的时候恐怕并没有读过陈季同的书,陈季同将多妻制归因于中国人的祖先崇拜。在陈季同看来,传统是一种强大的道德力量,而祖先崇拜是其实现的重要形式,作为一个宗法制社会中的中国人,其“身后有列祖列宗促使他承担一个君子的责任”,而其自身,也将是其子孙的榜样,因此,对于一个中国人而言,“最不幸的莫过于承认自己的宗族不能传宗接代,如果那样,其祖先就无人祭祀了。”(13页)基于这个原因,多妻制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抛开现代的男女平等观念不谈,这个从文化传统出发的辩护简直无懈可击,况且,陈季同还捎带着用《圣经》里没有孩子的撒莱将自己的使女夏甲赠给亚伯兰从而使后者有了一个儿子的故事讥讽多妻制同样也是西方的传统,甚至可能还更早!与此同时,与后来辜鸿铭强调妇女被动的无我和牺牲精神不同,陈季同否认中国的妇女是没有感情的男人的附庸,正相反,他引用了《诗经》以及唐诗、宋词中大量的从女性角度写作的诗歌来说明中国妇女其实也有着自己的爱情观和责任感。
在第一篇文章之后,另外十篇文章分别从婚姻、家庭、科举、监察、商业、宗教、水利等角度详尽介绍了中国的制度与文化传统,虽然各自独立成篇,但是从某种程度而言,都可以作为第一篇文章的注解或是进一步阐释,从形而上的仁义道德到具体的制度风俗,展现了中国独特的文化内涵。虽然陈季同对中国的描述难脱过度美化之嫌,但是矫枉难免过正,况且,在当时充满敌意的环境下,这样的描述恐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与《吾国》等单纯介绍中国的著作不同,陈季同还有一本专论法国的著作——出版于1891年的《巴黎印象记》。这本书从一个中国人的视角描述和评论了对巴黎人的日常生活,内容涉及法国的司法、婚姻、家庭、交通、商业、娱乐、文化设施等等,由于主题不一、形式不拘,作者广征博引,文笔更显得轻松灵动。然而,一切评论都涉及立场,这本书与其说是对巴黎的印象,倒不如说是以巴黎为引子,阐述了一个中国人的文化观,并且,往往在只言片语之间流露出作者的深刻思考。
即使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陈季同的态度也是公允的,对于巴黎,他并不掩饰他的好感。巴黎的博物馆和图书馆让他赞叹不已,并意识到随着与外部世界交流的与日俱增,中国也需要建立类似的机构以便深入的认识外国的历史、文学、科学;对于新闻业,虽然他指出报纸造成了人们狂热的心态,但是,同时也为其思想传播中的巨大作用而深深感动;甚至对于咖啡馆,他在指出它和中国的茶馆不同之后,也指出了它的亲和力,并加深了对法国人的认识,即,这是一个“愉快、亲切、忙碌和有说服力的民族”(145页)。
然而,对于巴黎的好感并不意味着对西方文化的全盘接受,相反,多年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让陈季同看到更多的是中西方文化间差异,并随时将两者加以比较。
在《狂热》中,他略带尖刻的讽刺赌马的人“他们的欢喜或忧愁取决于一匹马的鼻子超过了另一匹”(12页)。 在《决斗》中,陈季同直接斥责决斗为野蛮的陋习,并用中国以调解来解决争端的例子对欧洲人反唇相讥——“你们会说欧洲人常常将我们视为野蛮人,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这样说的权利,我们以淳厚的民风和真正符合人性的道德而超凡出众。”(69页)在《乡村》中,他批评了欧洲人对农业的忽视,以及政府的土地私有化制度和税收制度,并极有见地的指出,“漫漫数千年来,中国政府是一个庞大的农业部”(120页),将农民的富足归因于政府兴修水利、强调土地公有制等与农业相关的一系列政策。《参观法院》中,他对中国审判中的肉刑避而不谈(或许在陈季同看来,肉刑乃是审判应有之意),反而用中国式的快速高效的判决来批评西方法律制度的拖沓与形式主义;同时,对于其朋友将西方的诉讼程序称为“中国式的繁文缛节”而愤愤不平。事实上,在之前的《中国影子》中,陈季同已经就西方人对事物的命名方式表示了自己的不满,他指出,对于火药、指南针这些源自中国的伟大发明,欧洲人并不在前面加上“中国”这个定语——“这些原籍的分配本着一个哲学的原则:对于所有严肃的发明,人们喜欢让它们的出处保持匿名状态;至于那些无价值的、讨人喜欢的、轻松愉快的小玩意儿,人们则乐于将它们的来源划归别人,有时也划归自己。”——于是,“一切奇怪的、钻牛角尖的、扭曲的东西,就成了中国玩意儿。”(55页)(不过话说回来,直接引发陈季同这一番感慨的“中国影子”,即皮影戏,恐怕倒确实没有叫错,它至少在北宋时期就已出现,并于元代传至西亚以及欧洲,只不过由于大多流行于北方,不为生长在福建的陈季同所知罢了。)
作为一本法语著作,陈季同的目的显然在于告诉法国的公众,欧洲的文化并非尽善尽美,它也存在着在中国人看来野蛮与冷漠的成分。但是,对于东西方文化间的巨大差异,陈季同并不争论孰优孰劣,他说:“在所有这一切事情上,我们的两种文明是矛盾的,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都不同于欧洲人。好耶?坏耶?我一无所知,唯有未来才能加以证实。”(13页)在他看来,不同的文明并没有优劣之分,重要的是相互理解与包容——“我尤其明白了一个道理,世界上的一切民族都将在战争中消亡,它们之间相互厮杀显得多么疯狂;若想免于灭顶之灾,只有一个办法:各民族友好相处。”(80页)
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深刻认知和对欧洲文化的深入了解,使得陈季同成为第一个用外语写作并获得巨大成功的中国作家。虽然他因为官场的倾轧而早在1891年就被召回国,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是,毕竟以其努力,在中西方交流中架起了一座另后人瞠目的文化之桥!
百余年后的今天,陈季同在其著作中所辩护的制度和风俗大多已不复存在,但是,陈季同的价值正在于他的文化眼光——不同于国粹派的论调,却有着充分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在针对西方的偏狭认识作出的反驳的同时,他也认识到西方文明的长处并意识到它将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的强大冲击,正如他在《火车上》一文中所预见的,“这个喷烟吐火的庞然大物将横空出世,用烟囱的吼叫和汽笛的嘶鸣,打破直到那时为止一直宁静的夜晚。它将一路掀起漩涡,带走我们古老社会延续千百年的习俗。”(94页)在中西方文化交往愈加密切的今天,我们该以怎样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又该如何构建与坚持自己的文化逻辑,或许我们可以从陈季同的身上得到些许启发。
参考文献:
[1]有关陈季同的生平,来源于《晚清一个外交官的文化历程》(李华川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林语堂.《吾国于吾民》.长沙:岳麓书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