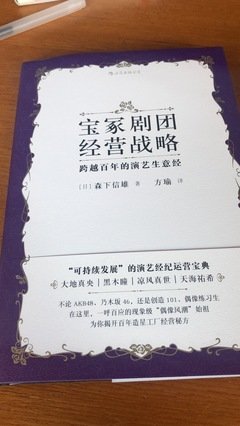
《笔底波澜》是一本由傅国涌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6.80元,页数:28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笔底波澜》精选点评:
●血墨交融的言论史。今日之中国又有何异哉??
●有点粗糙
●百年言论史的一种读法,亦是百年近代史的一种读法。|二〇一二|四|
●只是史料和对论证文人的仰视尊敬。看不到更多别的东西。史料也不够学术和严谨。感觉一般。
●这是中国百年反言论自由简史,但不包括反得最严密的当代历史
●不如预想的那般好
●青姨
●资料扎实,分析不多
●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
●浅显的读本,普及类读物吧
《笔底波澜》读后感(一):顾其自由不及前清远甚
近代中国言论史,就是一部几代知识分子以笔为枪抵抗强权的历史。从晚清到民国,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对言论的压制如出一辙,文人论政的空间一直都是那么严峻,沈草、邵飘萍、林白水、交量才,以及那些连名字都已被湮没无闻的知识分子,分别在不同的年代惨遭杀戮,他们的斑斑血迹使一部近代言论史总是笼罩着一种悲怆的气氛。但怀抱言论报国理想的知识分子始终没有低下他们高贵的头颅,没有停下手中的笔。从19世纪70年代起,王韬、梁启超、鲁迅、胡适、邹韬奋、张季变、王艺生、博斯年…他们用笔呼吸,以笔抗争,他们的笔下既流墨也流血,不断地寻求“笔的解放”,一次次掀起“笔底波澜”,书写了言论史上一个个有声有色的时代。
记得三年前的一个暑假,晚上和人长谈,我说要文明与进步,一是制度,二在新闻,教育第三。今天的中国是没有声音的中国。百年前,那叫睡狮,或者叫作万马齐喑。可是回想百年的言论史,却不得不令人惊讶。原来中国人曾经这样漂亮过,曾经有这样漂亮的中国,曾经有这样漂亮的中国人。阿啃说,如果开放了报禁,就是已经70岁了,也要出来办报。严复说“身贵自由,国贵自主”梁启超在《爱国论》一文中说:“国者何?积民而成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生则国权立;民权无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记住这“刀架在脖子上还是要说”的人,记住“苏报案”,记住被仗责血肉模糊的沈荩“怎么还没死?”记住被暗杀明杀的所有史量才们。又:袁世凯“暌丑报灾”之后黄远生叹到:“顾其自由不及前清远甚”。列出目录,记在这里。
《笔底波澜》读后感(二):知而不言是一种罪
读《笔底波澜》这部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年言论史读得荡气回肠、热血沸腾。
从晚清到民国,从袁世凯到蒋介石,从一百多年前中国第一批近代报刊的诞生到1949年一个风雨飘摇的大时代的落幕或者一个更恐怖的极权时代来临的前夜,无论是暴风骤雨来临前的黑云压城,还是弥漫着大屠杀血腥的白色恐怖,中国近代早期几代知识分子以笔为枪,对抗强权,为后来者留下了最为宝贵的传统——争取言论自由。他们在大时代的沧桑风雨中上演了一部至今听来仍令人壮怀激烈的百年言论史。
从《申报》、《循环日报》、《时务报》、《大公报》、《新青年》、《生活》、《观察》……..王韬、梁启超、英敛之、黄远生、陈独秀、胡适、邹韬奋、张季鸾、于右任、储安平………几代知识分子秉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情怀,不畏强权,被拘捕、被流放、被暗杀、受尽严刑拷打,不惜以死抗争,以求“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风雨苏报案,章士钊、邹容、章太炎被捕 ;北京报馆访事沈荩因报道中俄密约而惨遭杖刑,“血肉飞裂、骨已如粉” 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杀戮的新闻记者;《京话日报》彭翼仲“刀架在脖子上还是要说”被袁世凯当局流放新疆 ;于右任“监视政府,为民请命”,创刊不久即遭火灾 ;一部百年言论史上浸染了无数被钳制言论的政府杀害的记者的鲜血。极权算什么?白色恐怖怕什么?言论钳制又如何?知识分子们指点江山,挥斥方遒,视极权政府的严刑拷打如无物。其浩然正气和伟岸人格令后来人无限神往。
然而很快,这一阵激荡与神往在1949年,随着一轮红太阳的升起,像彗星一样陨落了,《观察》的绝响仅成那个时代最后一抹光焰。在新中国的历次改造运动中,中国知识分子出现了百年言论史上前所未有的奇怪现象,没有被腐朽的满清政府、袁世凯的独裁政府、以及蒋介石的白色恐怖所吓倒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在一夜之间被阉割掉了,他们昂首走进体制的牢笼,集体噤声了。国家意识形态有如一部巨大的绞肉机,而这些知识分子们就像一个个螺丝钉,严丝合缝地镶嵌进体制机器。于是,国家利益代替了个体诉求,主流意识形态屏蔽了个人思想,领袖振臂一呼,个人只需要做那应合的十几亿分之一。
对这些被改造的知识分子投医不屑的眼光和讥讽的言语或者将当下的言论现状归咎于他们那一代言论自由传统的断裂都是廉价且毫无意义的。他们为时代左右,禁忌太多,除了顾准、储安平、马寅初、林昭极少数人以超出常人的勇气突围出去,其余太多人都在时代大潮中沦陷,只在中国的言论史上留下一串串暧昧不清的省略号和感叹号。
即使是储安平这类在百年言论史上大放异彩的人物,其呕心沥血创办的承载其新闻理想的《观察》在1949年复刊后,也在短时间内迅速变成了一个“以宣传党的意志、方针政策为主要内容,以劳苦大众为读者的刊物”。复刊后的《观察》还做过以《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为专栏,并配有郭沫若长诗《我向你高呼万岁》的专辑 。但是,在1957年夏天,储安平却石破天惊,发出了“党天下”的言论,随即惨遭噩运,以死捍卫了言论自由。
“人为天地心,心生万物”是《市民》 杂志创刊词。可惜创刊不久即遭封杀。引用这句话无非是想说,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是最个体也最私人的事情,谁也无法剥夺个体思想者的权利。能否延续百年来争取言论自由的传统,取决于言者的理想和情怀,道义与担当。在当今的言论环境下,言者“失语”,或是无知,或是知而不言。无知,是一种罪过。宪政学者、基督徒王怡说,知而不言更是一种罪过 。知而不言,割断了百年言论史上知识分子、新闻人争取言论自由的传统,是一种深重的罪过。作为知识分子,作为言者,当怀璧其罪。
《笔底波澜》读后感(三):暗暗沉夜,笔底波澜
近代中国一直徘徊在幽暗长夜,从晚清到民国,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对言论的压制如出一辙。但怀抱言论报国理想的知识分子始终没有低下高贵的头颅,他们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在开启民智的同时,以笔抵抗强权。从《申报》、《大公报》到《新青年》,从梁启超、史量才到邵飘萍,他们一次次掀起笔底的波澜,在幽暗浑浊的年代发出了绚烂之光。
本书作者傅国涌用编年体的方法,钩沉将近代中国知识界、新闻界的旧人旧事。尽管对庞杂史料点到为止的记录方式让人坠入浩繁的史实堆砌,失去阅读兴趣。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重温历史、寻迹先辈踪迹的过程中,读者一次次被那些可歌可泣的言论和故事打动。
作者在《序》中对近代言论史进行了梳理,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首先是梁启超的《时务报》和《新民丛报》,为中国言论史拉开了精彩的序幕,他汪洋恣肆的文字使“举国趋之,如饮狂泉。”接着陈独秀和胡适为代表的《新青年》举起了“科学”和“民主”的大旗,成为“五四”运动的重要阵地。而新记《大公报》自是在中国言论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中国公民之独立言论机关”。最后储安平的《观察》被喻为“全国自由思想分子的共同刊物”,为中国近代言论史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一代代知识分子相继登上言论舞台,创造了光彩夺目的言论史。他们不仅仅以荡气回肠的文字对沉睡的国民进行精神洗礼,发出振聋发聩的思想,同时以笔抵抗强权,争取言论自由。五四前后反对北洋军阀对言论的压制,1933年对国民政府发出言论自由的呼吁,抗战胜利之际的“拒检运动”,一次次的抗争都以胜利告终。胡适、蒋梦麟等人在《晨报》上发表的《争自由的宣言》犹如空谷足音,至今余响不绝:“我们本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是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我们相信人类自由的历史没有一回不是人民费取一滴一滴的血换来的,没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出现。”
这部编年史每年都有一个小标题,从它我们可以一窥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不屈不淫正气性,敢言敢怒见精神。”如:“刀放在脖子上还是要说”(1906年)、“不自由,毋宁死”(1927年)、“经济独立,无党无偏”的《新闻报》(1938年)等等。在以笔抵抗强权,发出独立言论的故事里,史量才与蒋介石“你有枪,我有报”的对话流传至今:蒋介石曾找史量才谈话,蒋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 他们用笔呼吸,用笔抗争,他们的笔下既流墨也流血,书写了言论史上有声有色的时代。
直至今日,他们的文字读来仍别有一番滋味,仍具现实意义。比如现今新左派和自由派经常争论的国家利益和民众利益孰轻孰重的问题,具有“言论界骄子”之称的梁启超在八九十年前就说:“国者何?积民而成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古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无,则国权亡••••••故言爱国者,必自兴民权起。”
书的封面赫然写着“百年中国言论史”,但事实上只写到了1949年。这一年,新华社发表了那篇有名的社论《笔的解放》,储安平的《观察》完成了言论史最后一幕而完美谢幕,长期称雄的《申报》、《新闻报》相继停刊,永远地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本书带给读者的思考并不会因为1949年这个特殊的年份戛然而止。跟风雨飘摇年代的军事独裁相比,僵固且强势的意识形态似乎更能禁锢知识分子的思想,腐蚀他们独立的人格。曾经写下《且看今日之蒋介石》和《我离开蒋介石之后》的郭沫若咏出“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红旗插遍全世界,红旗插在天顶上”的惊人之作;曾经以“独立的、客观的、超党派”为追求的《观察》在复刊后还做了以《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为专栏,并配有郭沫若长诗《我向你高呼万岁》的专辑。
曾经追求独立精神,自由言论的他们最终在幽暗长夜里看到希望,却怎么没料到又落入了另一种禁锢。《中学生》杂志曾向鲁迅提问,“假如先生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处此内忧外患交迫的非常年代,将对他说些什么?”“假如先生竟以‘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之名,一定要逼我说一点,那么,我说: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这是鲁迅的回答,也是无数知识分子的希冀。
《笔底波澜》读后感(四):以自由为名
——读《百年中国言论简史》有感
身处乱世,最重要的是存一颗清明的心,否则如何不被历史洪流裹挟了去?乱世,人民如草芥,却偏有人要扎紧了根,蓬勃生长。百年前一群报人,于黑夜中汲取着微弱的光,向阳而生。他们才华横溢,更拥有非凡的人格,更是,对祖国的未来抱有美好的期望。他们为自由奋斗终生,却不是为一己的自由,而是千千万万大众的自由。正如梁启超在《新民报》中提出的关于现代报纸两大“天职”说:一曰,医院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立其为向导者是也”。 报人们的灵魂生而便自由,而纸报生而就是要与黑暗势力做斗争的。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总是有一群人,他们前仆后继地为践行自己心中的信念而勇往直前,哪怕等待他们的是无情的杀戮。晚清,一批人放弃了传统仕途,转而走向以笔救国之路。他们的脊梁不会弯,以生命为筹码,以秃笔为武器,批黑暗之政治,描绘中国之未来。谭嗣同 “且外国革命未有不留学者,中国以变法流血者,自谭嗣同始。”,沈荩因报道《中俄密约》被仗毙,更有1913年的”癸丑报灾”,邵飘萍、林白水的相继遇难。在日帝国主义刺刀的威胁下,张季鸾等人选择停刊,“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强硬地表达了当时一众报人的态度。但正因为有他们的报道,当时仍在“昏睡”中的人们才得以知晓当时局势的严峻,又从报人们描绘的救亡存国的道路上看到一丝丝光亮,不至于在黑暗中踽踽独行;一些读者甚至被唤起了心中的爱国热情,找到了才华施展之地,加入了用笔与黑暗势力做斗争的阵营之中。报人们的灵魂是自由的,任任何强制势力也不能禁锢。它们散发着强烈的光和热,但愿在茫茫黑夜中燃尽最后一丝光亮,温暖一个苦难民族的灵魂。
言论史自在历史之中,作为主人公的报人也是在不断前进之中。经历了张勋复辟,陈独秀深感即便是所谓的”英雄””伟人”的军阀,也未必信仰什么共和,只有”党派运动”而无”民国运动”, 一切如走马观花般的变化都与大众无关,所以他与他的同志要通过办刊物,写文章,引进新思潮,期望用《新青年》开创一条除政治之外的言论新道路。梁启超早在《变法通议》中便指出:“变法之本,在于育才。”我们应当庆幸有如此一批人让报纸的精神薪火相传。梁启超、康有为等的君主立宪,从他们来而又赶超他们的于右任,宋教仁等的革命,创办“民呼” “民吁” “民立”的竖三民时代,还有陈独秀等人创办的《新青年》时代,而张继鸾等人也接过《大公报》的担子,提出“四不”——不党” “不卖”,“不私”“不盲”,作为撰写报文的原则。
令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新青年》时代”。彼时仿佛回到了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思想争鸣的那个年代,各种言论互相碰撞,各报的人们有各自不同的观点,有时甚至是论战。然正如周作人所写,“我们的个人思想性质不同,但与一切专断与卑劣者之反抗则没有差异——唯一的条件便是大胆与诚意”。
自由在不同时代对不同事物都有不同定义,而对于百年前的报人们来说,言论自由便代表着能够无拘无束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不用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纯信之士,骨骾之臣,忧国如家。”他们深知言论自由对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他们为之奋斗了百年。但言论自由并非是他们最终的目的,而是他们信仰的原则之一。百年间,他们发乎于心地谈论政治经济文化,只是用一个报人身份说话,尽自己的责任而已。如此,即便是随时可能落入“危在旦夕”的境地,报人们依旧描绘心中之蓝图,因为他们的终点是启迪民智,救亡图存。
这份斑斓的画卷,既有《新民从报》《大公报》的铁骨铮铮,也不乏《新月》《语丝》疏林映射的雅致。将百年历史梳理,我们会发现言论在时代巨变中的重要性,因此(也)知晓了当时的统治者和入侵者为何宁愿暴露出残暴的一面也要控制言论:因为他们知道言论力量之大,报人意志之不屈。他们的气节可以仅是从他们的文字中也体现出来了,而他们却义无反顾地担上了道义的担子,便投入到为人民的自由而不懈的奋斗中去了。
《申报》的接班人史量才曾写过:“国有国格,人有人格,报有报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非国。”报格光耀百年,他们是自由的。
《笔底波澜》读后感(五):中国人站了起来,然后后退了几步---韩寒
能使荆棘化堂宇,下视官爵如泥沙
《笔底波澜 百年中国言论史的一种读法》是我最近看的最揪心的一本书,作者从1872年《申报》的创办开始讲起中国近代的言论发展史,一年一个代表事件,一年一群死在刀下的文人,一直讲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对于读者来说,这是多么的揪心啊,这边历史正讲到高潮呢,新中国都成立了,那边新的言论史却泄了没有下文了。这对作者来说,那是更加的揪心啊,自己的“拙作”被迫阉割去了精彩的部分不说,连标题都要暗示委屈,“我的这个书啊,只是百年言论史的“一种读法”,谨代表个人,仅供参考哈,大家主要还是参考适合中国国情的“另一种读法”哈”。
这里抄点里面好玩儿的东西:
1899年,梁启超在《爱国论》一文中清楚地阐明了“国”和“爱国”关系,“国者何?积民而成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无,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在《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趋势及中国之前途》文中,他首先提出了“国民”概念,他认为中国几千年来只知有“国家”,不知有“国民”,无国民,则只有奴隶。
1908年,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就《民报》案开庭对章太炎进行公开审理,日语流畅的宋教仁出庭担任被告翻译。因“苏报案”儿名动天下的章太炎再次在法庭上慷慨陈词:“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文明国家法律皆然,贵国亦然,我何罪?”
1910年,2月20日,曾开创过一个时代的“言论界骄子”梁启超虽然还在流亡之中,却借清廷预备立宪的东风,在上海创办了《国风报》(旬刊),以“忠告政府,指导国民,灌输世界之常识,造成健全只舆论”为宗旨。
1912年,经参议院通过,孙中山正式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中第六条第四项确认“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
1915年双十节那天,《四川群报》主编樊孔周在门口张贴了一幅这样的对联:
庆祝在戒严期间,半时欢欣,半是恐惧;
言论非自由时代,一面下笔,一面留神。
1920年,《晨报》刊载了国务院通令全国邮电检查的通电:“现在过激潮流深延滋蔓,妨碍地方秩序,影响国家安宁……为防范过激意见,对于往来邮件各地应施以检查。”
1925年,视自由为第一生命的胡适写信给昔日的《新青年》同伴陈独秀:
《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里为是为非,决没有“该”被自命为争自由地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地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着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以是必即是,而众人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但我唯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地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残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地人怕没有容身之地了。
1926年,北京阴雨低垂,段祺瑞政府悍然杀害了47个和平请愿的学生和民众,伤200多人。有国民党背景的《国民新报》连续发辫《段祺瑞之大屠杀》,《段祺瑞应受人们审判》等社论。
1928年,胡适在日记中说:“上海的报纸都死了,被革命政府压死了。只有几个小报,偶然还说说老实话。”
1930年,郁达夫《薇蕨集》在北新书局出版,书前有一篇《题辞》:
三四年来,不晓得为了什么,总觉得不得安居乐业,日日只在干逃亡窜匿的勾当.啊啊,财聚关中,百姓是官家的鱼肉,威加海内,天皇乃明圣的至尊;于是腹诽者诛,偶语者弃市,不腹诽不偶语者,也一概格杀勿论,防患于未然也,这么一来,我辈小民,便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了.”最终北新书局怕以文字贾祸,抽去了这篇虽短小却足以让全书生色的题辞.
妇人醇酒近如何?
十载狂名换苎萝.
最是惊心文字狱,
流传一叙已无多。
1931年,邹韬奋在《信箱》发表言论说:“在做贼心虚而自己丧尽人格者,诚有以为只须出几个臭钱,便可无人不入其毂中,以为天下都是要钱不要脸的没有骨气的人,但是钱的效用亦有时而穷……
1931年,南京政府公布《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1,2月间,南京政府相继颁布《电影检查实施细则》;电影检查委员会组织章程》。舆论控制延伸到了当时新兴的电影业。
1932年,元旦,《中学生》杂志向鲁迅提问,“假如先生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处此内忧外患交迫的非常时代”,将对他说些什么?“假如先生竟以“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之名,一定要逼我说一点,那么,我说: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这是鲁迅的回答,也是无数知识分子的选择。1
1933年,陈独秀“危害民国案开庭审理,并最终以“文字判国罪之宣传”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但当时的《申报》《国闻周报》等都详细,真实地报道了这一案件,《益世报》等大报还全文发表了他们的精彩辩护,乃至判决书,上诉状等。
1938年,《新华日报》发表两篇社论:《查禁书报问题》和《抗战期中言论与出版的完全自由》。7月29日,又发表专论《反对查禁救亡书报》。共产党人正是充分利用《新华日报》这个公开的载体,高举民主大旗,大力呼唤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以反专制,反独裁,争民主,争自由地面目,倾倒了无数知识分子赢得了万千人心。
1939年,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公布《印刷所承印未送审图书杂志原稿取缔办法》11条。29日,军委会公布《邮电检查实施规则9条。7月19日,国民党中宣部制定了《抗战时期宣传名词正误表》,“拥护抗战到底”,“劳苦大众”,“救亡运动”等词语一律不准用。
1946年,蒋介石郑重承诺:“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然而话音未落,1月11日就传出羊枣(杨潮)猝死狱中的不幸消息。
今天同学跟我说,其实曹操是个好人啊,当初他也带着百姓逃走白马城啊,我跟他说,毛腊肉当初还高举XX大旗呢。所以说哪个政权在建立之初没有扯过弥天大淡呢?政治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玩弄你的,跟你画个大饼,说有一天我能带着你去吃大饼,其实他做的只是让这个画的大饼更真实而已,今天是3D效果的大饼,明天就是杜比数字5.1 声道解码的了,画着画着,你发现你根本吃不到大饼的时候,要么你可以就地换一个给你画大饼的,要么你发现你只能就地变成一个大饼了。
现在看看当初他们画的大饼你没希望吃到了,你是不是很唏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