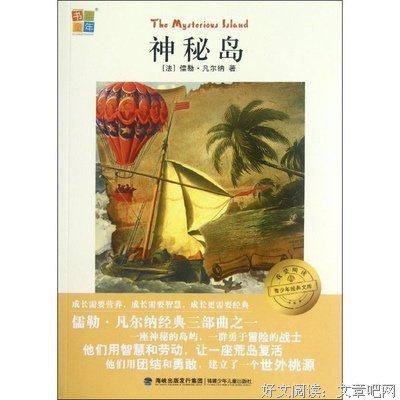
《文学“爆炸”亲历记》是一本由何塞·多诺索著作,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塑封图书,本书定价:8.60,页数:21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文学“爆炸”亲历记》精选点评:
●他太太的那一段访谈更加有意思,果然是一个聪慧的女人。这个普林斯顿的学生对文学爆炸的态度非常温和。
●有些有趣的八卦
●作家们的生活也是鲜活生动,可惜对拉美的作家们还不是那么熟悉,读来多少有些距离。等我通读他们的作品后再来看这本书,可能就像看作家们的八卦新闻一样有趣。
●当我们谈论文学爆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在座的各位有人会写字吗?”
●非常生动。何塞·多诺索理性地分析将作家们共同标签化为“文学爆炸”的三个原因,又天真得像个小孩子一样希望“文学爆炸”不要太快消散,我想他真正在意的是那一个十年中拉美作家之间真诚而亲密的友情。附多诺索夫人《“文学爆炸”的家长里短》同样很有意思,八卦爱好者必读。
●好多八卦。。。
●写得一般。全是段子和八卦,牵涉到的人有富恩特斯、马尔克斯、略萨、科塔萨尔、多诺索、萨瓦托、奥内蒂、鲁尔福、博尔赫斯、聂鲁达、弗朗基……反正能想到的人几乎都在这儿了。卡斯蒂利亚语美洲文学我还能再爱一万年。
●纠正了一些对拉美文学的看法,比如拉美文学爆发得成功不是地区性特色,反而是一种国际化写作。喜欢拉美那片把作家当作神祗的土地。拉美作家是拉美土地上养育的欧美现代派的继承人。多诺索写得比较客观,但是没有他妻子写得那部分有趣。
●多诺索很会八卦。
《文学“爆炸”亲历记》读后感(一):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这下可以了解基本面貌了。怀念和羡慕那样的年代,大师辈出,眼花缭乱,并且居然互相都是朋友,还被混不进圈子的人忌妒地称为黑手党.....
不过,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终于都消逝了。
《文学“爆炸”亲历记》读后感(二):不是中国小说已死
阅读此书,大致知晓拉美文学爆炸的前因后果与过程,作为大爆炸的大师之一的何塞·多诺从自己的角度去观察与理解那一场惊天动地的文学运动(也许这个词欠妥,但色彩却较合适),于是便有了《文学“爆炸”亲历记》一书,其中有自己的看法,自己历经的历史细节,再加上他的夫人撰写的一篇细节性的文章,全书读起来颇为生动有趣。
阅读此书,再次加强了我对中国小说界的鄙视(就象每看一场足球会坚信中国足球永远是弱智,每看一场大陆电影会更坚信中国人在电影方面永远是白痴),中国小说家还没进化好,只进化到“讲故事”这个低级阶段,他们理解的小说就是故事。写小说就是“讲故事”,要分析其原因,与中国重视“历史叙事”有关系,更与《红楼梦》《西游记》这类三流而被当作一流的小说的影响有关系,与苏俄文学的影响也有关系。不能说这些影响没有有益的部分,但更多的影响是让中国小说陷入了讲故事的可怕恶习中。我不反对小说讲故事,但故事只是小说的一个元素,小说可以没有故事,但故事却不是小说。从我的观点来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小说,其实都是故事,能称得上小说的没有几部。
在语言上,中国小说家大多未写过诗歌,对语言质地没有感觉,语言在他们手中只是一种日常工具,而不是小说所存在的世界,中国现当代小说中的语言,除了在孙甘露刘恪等少数几个作家的笔下保持着质感之外,一律都是混凝土般实用而无质地的言说。
仅从文本上而言,“用日常的工具性语言讲故事”——这是对中国小说最好的也是最恰当的定义。至于为何会出现这种小说大垃圾的现象呢?与小说家们被养起来有关系,也与他们要发表有关系。被养起来的小说家没有紧迫感,写作变成了他们的职业而非事业,能隔三叉五出本书混个脸熟、不被人遗忘就算万事大吉。而那些未被养起来的边缘小说家,因为要靠稿费为生,所以在写作上被文学杂志那些老朽的编辑们牵着鼻子走,中国的文学杂志,基本都是垃圾,除了《山花》等一二份另类杂志之外,所有的文学杂志都是“故事会”的另一种版本,尤其以影响最大的《收获》《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为甚,这些文学故事会以其影响力一再向作家们灌输:小说,就是讲故事。
于是,就算受到西方现当代文学的冲击,在中国所激起的也不过是死水微澜,小说家们仍然保持在固步自封、心不在焉地讲故事的低级阶段。相比之下,当西方文学冲击到拉美时,激起是“文学大爆炸”!为世界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言说方面,更提供了我们的另一种观察世界与进入世界的新方式、新角度。略萨、科塔萨尔、马尔克斯、富恩特斯、多诺索等大师的出现,就是大爆炸的成果之一。中国也经历过改朝换代、也经历过文革那样的荒诞岁月、更经历着社会阶层大变动的改革时期,但是,中国的小说却没有刻下时代的烙印,更没有表现出新的美学倾向或新的美学法则,反而,一再退缩到讲一些老掉牙的故事的历史尘土中。
中国小说家们不过都是一些蹩脚的“故事大王”,中国的小说不过都是些无聊的“民间故事”,中国的小说杂志不过都是些胡弄人的“《故事会》”。不是中国小说已死,而是中国小说从来就没有活过,一直是躺在美丽想象中的“僵尸”罢了。
对中国小说,我永远竖中指!
《文学“爆炸”亲历记》读后感(三):形形色色出书法
所有的文人都向往出书,这应该是不太好怀疑的结论。
当然也有文人不愿出书,我一朋友便是。她说掏钱出书多划不来,书出来后还得觍着老脸送人,求人看书,简直把脸面都丢尽了。她先生是画家,印了很多画册,家里堆得到处都是,那时候就把她搞怕了。她说她有生之年绝不出书,可说归说,她还是出了几本书—不过,那是印客网上印的书。有她印度游记,也有西藏游记。一次印一本两本的。因为稀缺,凡见者皆奇之,纷纷向她索取,每每这时,她便不无得意地说,只有一本,盖不外借。散文集她印的多一点,三四本吧,因为图的是有趣轻松,文字便多少沾点邪性,这让见者更喜欢,没多久,这三四本书旋即被人强行抢走,再也讨不回来。
这,其实也是一种出书法。
朋友丙丁,是个文学发烧友,散文、小说写得甚妙,他出过几本书,最让我感兴趣的是他的两本集子,白皮,书名是某某小说集,“土狼工作室”印制。这”土狼“,是他网名。也就是说,这书从编排到校对,都是他一人所为。他也不要什么鬼书号。出书就是为了玩嘛,反正也不图名不图利的。送送朋友,自己留点念想而已。
能让出版社看中给你出书,当然是天大的运气。可这样的运气,大部分文人都轮不到。于是,只好自费出书。有本事的,出了书后不但能把本捞回来,还能狠狠挣上一笔。当然,这要看他的运作能力了。周围人中,就有自费出书挣上几万十万的。当然,有顶官帽子戴着出书更方便。销路不愁啊。但私底下,总是有人瞧他不起,说,这跟受贿区别不是太大。呵呵。最令人心动的,是你找到一个好角度,为富家写传或为企业写书,那样的话,写书者总能挣上些银两。可这样的钱也不是好挣的啊。一个作家朋友说,每次写那些“报告文学”,都让她头疼,差点写到呕吐。不是因为穷,还真不想挣这钱。那钱不是不干净,而是因为你在写作时得委屈自己。
其实,港台那边的文人出书,也多半是自己掏钱买单的。不久前一个笔会,碰到两个港台大学的教授,他们来出席笔会也带了书来,碰上合适的,他们就送书送文章给你看。然后说,他们出书也是自费的。这在那边非常正常。送书时很自然,毫无委琐样。看不到“觍着脸”的样子。偏巧我看到时,教授们带来的书已送完了,见我想要他书,就说回香港后寄我。半个月后,一本名《翠微回首》的书果真寄到了我报社。他们一诺千金的做法让我非常感慨。
最近在读智利作家何塞·多诺素写的《文学‘爆炸’亲历记》一书,他说到的拉美作家当年的出书样,也和我们很相像。
何塞·多诺素这一代作家,在智利,被称为“50年代作家”。1955年他出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消夏》时,很多出版社都不敢冒险出书,怕发行得不到保证。他只好找到10个女朋友(幸亏女朋友多),让她们每个人,在印书之前售出10张图书征订单,拿到了这笔现金,交付了出版社要求付清的第一笔款子,书才印出,印数为1000册。销售书时,他和朋友们分头站在街角,把书塞到熟人手中,说服他们买下。这就是他的第一次出书经历。
1957年虽然他的短篇已获得市级文学奖,但要出书还是很困难。为他的小说《加冕礼》寻找出版社的时候,接连找了几家,有的不敢为一本“难读的书”投资太大,有的要求删去许多,最后一家勉强同意了,但有一个附加条件:三千册书中,要自己接受700册。并且放弃稿酬。这一次他又动员很多男女朋友,到大街,到学校,到集会场所,到咖啡馆,卖他的书。他父亲则向他的牌友们兜售儿子的书。就这样,书总算卖掉了,据说,当年拉美国家他的那些文学同道们,几乎都是这种窘迫的出书法。
这就是他们当时的命运:自费出版,然后顶风冒雨地去卖书。碰上好运气 ,会有国内评论家对它关注。再走运点,会被推荐到外交界,走出国门。
那时候整个南美国家,文学界都很闭塞。作家们都很贫困。包括《百年孤独》的作者。何塞·多诺素回忆说,他们读到其他作家的作品并不是在书店里买到的,而是靠作家们自荐或互相推荐才传播开来。很多作家往往边旅行边带书来,像“信使”一样,这就是他们的书传播开来的唯一办法。到60年代上半叶都这样。国家不出口书,也不出口书。“幸好那时我曾经并且继续到处旅行。”很多作家也在旅行。“我们在自己的行李里装上书好送给朋友。朋友们念了书,就写文章,发表评论。”
其实,所有的文坛都是相似的。智利文坛如此,中国文坛也如此。作家们出书,然后互相送书,看了书后,就写评论。如果你有著名的作家朋友,那你的书一经他们推荐很可能销量迅速改观,难怪现在无名者出书,都要拉有名者推荐。虽然有人恶意抨击,这是作家们在“互相吹捧”,不过,不这样做,作家们的作品又怎么走出去呢?“吹捧”本身也有正面意义吧。毕竟好书也是作家们首先发现的。比如六十年代下半叶,拉美文学“爆炸”被全世界瞩目,也是拉美作家们首先自我介绍、推荐的结果。
也因此,什么样的出书法都不必奇怪。不但古已有之,别国也是如此。我的一位也算著名的作家朋友,要出一本散文集,出版社早答应了,可迟迟不开机,一年两年,作家等不及了,说我自己买回一千册书。一听这话,出版社迅速同意开机。哈。真是说不尽的出书事。
《文学“爆炸”亲历记》读后感(四):《“文学爆炸”亲历记》:就像在写一段自传
原文地址:http://www.qh505.com/blog/post/5669.html
但是,我说,他们主要是继续分散,继续个性化,把“文学爆炸”甩到后头。 ——《十年之后》1982年的何塞·多诺索显然是以被唤醒的方式写下了《十年之后》这篇文章:在时间意义上,动笔于“十年”之后,无疑是回到了作为起点的1972年,正是在那一年里,何塞·多诺索写下了《“文学爆炸”亲历记》,当亲历的“文学爆炸”在十年之前发生,“十年之后”无非是一种夹杂着尾音的附录;而在1972年的文章里,何塞·多诺索就预言了“文学爆炸”“很快就会过时”,他甚至在那时就清晰地标注了这一运动的起始和终结:1965年,“始于在卡洛斯·富恩特斯家里那穿得珠光宝气裹着裘皮形象严肃的丽塔·马塞多主持的那个庆祝会”,而1970年除夕,在在路易斯·戈伊蒂索洛在巴塞罗那的家里,由玛丽亚·安东尼娅主持的盛会就标志着它真正的结束。
始于“珠光宝气裹着裘皮形象”的庆祝会,终于辞旧迎新的巴塞罗那圣会,当何塞·多诺索以这样的方式书写“文学爆炸”的履历,显然有些戏谑的味道,仿佛一场波及美洲、影响世界的文学运动只是一个沙龙式的讨论:既起始于文豪的讨论中,又消失于贵族的狂欢里。但是,何塞·多诺索却也不是心血来潮定义“文学爆炸”的时间,即使撇出和沙龙有关的定义,他也认为,当70年代所有人都想挤进“文学爆炸”队伍之中,都想为自己的创作贴上标签,都将其视为荣耀的象征时,一切就真的发生了质改变:“最后进入70年代一切都变了,变成一个大杂烩,很难弄清其价值,难以判断。”而即使在“十年之后”,何塞·多诺索被唤醒重新关注“文学爆炸”,他也依然认为,70年代就应该画上一个句号。
但是矛盾似乎在那里,何塞·多诺索为什么要写作《十年之后》,将目光再次聚焦“文学爆炸”?因为这一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凭借《百年孤独》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无疑是一次重要的标记,无论对于美洲文学来讲,还是对于“文学爆炸”来说,“就像是给一个情节复杂且千头万绪的故事带来一个圆满的结局”,何塞·多诺索这样说,而在十年之前,何塞·多诺索也有过预言,在他看来,《百年孤独》标志着“文学爆炸”进入了第三时期——第一时期的标志人物是卡洛斯·富恩特斯,何塞·多诺索认为,“他是第一个与欧美大作家建立友谊的人——第一个被美国评论家视为第一流小说家,他第一个察觉他那一代的西班牙语美洲小说正在发生的事情的重要性,并且第一个慷慨而又文明地让人们知道这一点。”而第二时期的代表人物则是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这个当时年仅24岁的作家的作品获得了巴塞罗那塞依克斯·巴拉尔出版社的“小丛书”奖。
“以我的眼光来看,第三时期——也许是西班牙语美洲‘文学爆炸’作为‘爆炸’的决定性时刻——是随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的发表到来的。”《百年孤独》的发表标志着“文学爆炸”进入了决定性时刻,《百年孤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标志着故事走向了“圆满的结局”,其实完全契合何塞·多诺索对“文学爆炸”一贯的主张和判断,圆满即结束,决定性时刻即退出舞台的时刻,当他在1982年再次回望“文学爆炸”,其实对于这一运动的想法还是清晰的,在他看来,这个已经达到鼎盛的文学将会“不时兴”了,甚至《百年孤独》在文本以外也推动了“文学爆炸”的终结:“所有这一切:诺贝尔文学奖,中学和大学需要这本书,出书有利可图,很能说明近十年来那个曾经是有争议、并且被诅咒的‘文学爆炸’的际遇。”
“十年之后”无非是何塞·多诺索的一种坚持,在他看来,“文学爆炸”有过红火,甚至产生了排山倒海的气势,甚至小说一时取代了诗歌在拉美文学的垄断地位,但是在70那个除夕之后,“文学爆炸”就走上了末路——加西亚·马尔克斯能够在十年之后还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只是因为他和科塔萨尔等人一样忠于某种革命事业,而更多的人“凑热闹地摇摇摆摆而已”。这里的一个认识是:当“文学标签”成为一种集体的标签,是走向整体性的文学标志?还是为它本身带来了危机?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是,一位住在巴黎的巴拉圭作家,当他获得了一项“美洲作家”的奖项之后,郑重宣布,凭借获奖的作品,自己已经跻身于“文学爆炸”行列了,对于这样一种沽名钓誉的人,何塞·多诺索用嘲讽的口吻说:“真是个傻瓜……太天真了。这就像相信有圣诞老人一样。”
让自己贴上标签而成为“文学爆炸”作家,这是“十年之后”很多人的功利目的,这是“文学爆炸”利益化、商业化的可悲。但是撇除这些沽名钓誉者,其实何塞·多诺索认为“文学爆炸”会过时,更在于他对曾经坚持着创新和革命的作家的担忧,本来“文学爆炸”就是不是以整体性观念和纲领统领的一个流派和运动,分散性是它的主要特点,但是当人们以“个性化”为借口从事创作活动,当“文学爆炸”失去了秩序和准绳,其实在创作主体上自行解构了“文学爆炸”本身:很多人搬了家,换了妻子,儿女长大,不断出书,“他们走到全世界的大街上都有人认出他们,请他们签名。”最后的“文学爆炸”真的变成了一个只是贴着标签、低价的包裹。
十年之后认为“文学爆炸”必被甩到后头,十年之前认为“文学爆炸”处于危机中,这一切都是源于何塞·多诺索的忧患意识,而当他真正亲历了“文学爆炸”的时候,其实对这一切是充满了希望——时间仿佛很规律地划分出三个时间点:1982年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使“文学爆炸”走向圆满的结局;时间往前推10年,1972年写作《“文学爆炸”亲历记》时,他已经预判了危机将会出现;时间再往前推10年,正是1962年,康塞普西翁大学召开知识分子代表大会——当何塞·多诺索得知富恩斯特将参加大会时,他打听了飞机到达的终点,像一个崇拜者一样,胳膊底下夹着富恩斯特的《最明净的地区》,希望他能给自己签名——“我有点失去了我为人有点矜持的本性”,这对于何塞·多诺索来说,是多么富有激情的举动,是多么珍贵的个人回忆。
而这种激情和珍贵,似乎也说明那时的何塞·多诺索对新时代的文学充满了期望,富恩斯特以及他的作品何以让何塞·多诺索丢掉了矜持,甚至有些疯狂地只求得一个签名?对于作家和作品来说,何塞·多诺索是赋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富恩斯特“给予我一种新的眼光”,这种眼光使自己获得力量,“使我感到有必要将此观念化为已有,运用于纯粹文学的范围,也运用于最世俗的各个领域。”而那部《最明净的地区》,在他看来是属于拉丁美洲特色非常突出的书籍,这种书籍具有一种使命:“挖掘我们的城市和我们国家的深层,以揭示实质和灵魂。墨西哥人、利马人、阿根廷人的实质是什么?当今的作家很少有人劳神去探究英国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的实质是什么。”所以到机场等候、签名,对于何塞·阿多诺来说,更具有一种追随的意义,那就是像富恩斯特一样,拒绝表面虚伪的东西,“他采取的态度,不是像束缚着我的范围之内的小说那样是一种文献式的,而是质询式的;是指出问题,而不是回答问题。”
挖掘深层次的东西,触及实质和灵魂,以质询的方式指出问题,这一切在何塞·多诺索看来,就是代表着文学的希望,而这个文学,就是基于这块大陆生长、突围和创新的“西班牙美洲小说”。将这块大陆的文学命名为“西班牙美洲小说”,其实是一种对于地域的突围,而“文学爆炸”的真正意义就是寻找和实践一种国际化的思维,“我觉得最近西班牙语美洲小说最有意义的变化总是与国际化进程联系在一起。”要走向国际化,就必须超越地域限制,就必须扩大范围,就必须有开放性视角,而这些对于“西班牙美洲小说”来说的使命,正是源于60年代的美洲文学处在一种自我封闭、各自割裂,甚至臣服在权力之下。
克里奥约主义作家、地方主义作家、风俗主义作家和社会现实主义作家,在何塞·多诺索看来,都是60年代横亘在美洲文坛上的路障,他们的共同标准就是写作“我们的事物”:“他为自己‘教区’写作,写自己的‘教区’里的事情,用他那‘教区’里的语言,面向他‘教区’提供给他的读者——读者的数量和质量大不相同,巴拉圭的不同于阿根廷的,墨西哥的不同于厄瓜多尔的——除此之外,不能有更多的奢望。”这便是现实,关于社会问题,关于种族,关于风景,都成为衡量文学质量的尺度。无疑,“我们的”、“教区”都反映的是地方性事物,也就是他们以贫乏、短浅甚至闭塞的视角来写作;另外一方面,从何塞·多诺索自我经历来看,真正的小说创作遇到了太多的困难,当时的命运就是自费出版,就是顶风冒雨去卖书,“在智利这个环境中我感到窒息”。
正如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对作家的定义是:“为自己驱魔的人。”所以在60年代的时候,美洲迎来了一种开放,欧美外国文学影响了这片大陆,“这些新作家一方面使我们眼花瞭乱,另一方面又渐渐造就了我们。”
他们是萨特和加缪,我们刚刚挣脱他们的影响;还有君特·格拉斯、莫拉维亚、兰佩杜萨;不管是好是坏,还有达雷尔、罗伯-格里耶以及他所有的追随着,塞林格、凯鲁亚克、米勒、弗里施、戈尔丁和卡波特,以帕韦泽为首的意大利作家,以“愤怒的青年”为首的英国作家,他们与我们年龄相仿,我们觉得自己和他们一样,这一切都是至少是在虔诚地生吞下并消化了“经典作家”如:乔伊斯、布鲁斯特、卡夫卡、托马斯·曼、福克纳的作品之后。无疑这正是美洲文学的契机,而对于何塞·多诺索来说,是找到了自己“文学上的父辈”。也正是在这一机遇的造就下,1962年在康塞普西翁举行了知识分子代表大会,虽然在大会上一些讨论的创造性建议并没有完全被采纳,但是何塞·多诺索认为,它的最大意义是国际主义思维,“说到‘我们的’这个提法,已不光是指智利的事物了,而是指我和智利能够实现的,也必然会让成千上万组成讲卡斯蒂利亚语世界的读者感兴趣的事物,从而打破那些划得如此分明的国界,创造一种更广泛、更国际化的语言。”“我们的”不再只是“教区”,不再只是智利,甚至不再只是美洲,而是世界;不仅是地域意义的世界,也是人与人敞开的世界——何塞·多诺索对于富恩斯特近乎崇拜的表现其实真正的意义在于:“我第一次真正体验到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的鼓舞。”
打破地域限制,创新创作手法,更具世界目光,这种革新意义其实不光是指思维习惯,1962年的大会有一个非常政治化的时代背景,那就是古巴革命事业,而当时参加大会的作家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古巴革命事业的信念,而这种信念在何塞·多诺索看来,也构成了“文学爆炸”统一性的一个方面——现实层面的革命事业,一样被归为文学的一种实际行动,而作家们之后集体式的“流亡”生活,则成为他们不竭的创作源泉,这种“流亡”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逃离“我们的”封闭世界,以一种自由、开放甚至牺牲的方式站在世界主义的高度,所以何塞·多索诺总结出“文学爆炸”真正的同一性特点便是:流亡、世界主义、国际化,“所有这些或多或少有联系的因素,构成了60年代西班牙语美洲小说的相当重要一部分。”
1962年的大会在何塞·多诺索看来,才真正标志着“文学爆炸”的开始,从富恩斯特到略萨再到马尔克斯,当“文学爆炸”经历了三个时期,辉煌也就意味着结束,“文学爆炸”如此昙花一现,当然更多是何塞·多诺索自身对于这一运动的考量,在他看来,帕迪利亚事件产生的幻灭使得古巴革命的激情消失,从而使得“文学爆炸”失去了外在的革命热情;“文学爆炸”本身缺乏统一的理论和立场,分散化的状态没有使之具有完整的总体性;缺乏秩序和准绳则使得“文学爆炸”成为了一种标签,在利益化、商业化的驱使下慢慢失去了创新意义;而流亡的作家在政治性为中已经不能回家,它使得“西班牙美洲小说”真的变成了一种没有归宿的流亡文学。
何塞·多诺索是忧患的,也是悲观的,而作为见证者和亲历者,他的这种忧患意识和悲观心情也是站在自己作品立场上,对整个时代做出的判断,从自费出版到街头卖书,再到从富恩斯特等前辈身上吸取经验,打开世界的目光,何塞·多诺索就是为了打破困囿于自身的一切限制,在和莉莉·乌尔迪诺拉会见时,他指出智利令他感到忧虑,其中的士气、混乱、谎言和公众的不信任感,使自己感到压抑,“在智利,无法与一个和自己不一样的人交往……”希望作家是人民的一部人深入到人民中去,最后却只能在隔阂中,所以何塞·多诺索把内心的希望寄托在小说创作中,在谈及《污秽的夜鸟》时,何塞·多诺索就说,“我想损坏,碾碎,摧毁那东西,并且弄明白它究竟是什么,并且达到什么程度,弄得我的生活荆棘丛生,把我也变得有如魔鬼。可以这么说吧,这反映了我自己变得像魔鬼。”所以他对“伪装”感兴趣,所以对人造的东西寄予厚望,所以会创造对称,这一切都是对现实的解构,都是想用“文学爆炸”来摧毁一切。
在“文学爆炸”的亲历中,何塞·多诺索无疑感觉到自己在整个过程中都在自我意义上实现了“爆炸”,这是对“我们的”狭隘目光的超越,这是对“教区”的贫乏世界的突围,这是对国际主义的构建,所以,在康塞普西翁知识分子代表大会十年之后,在《百年孤独》获诺贝尔文学奖十年之前,何塞·多诺索说:“我觉得,自己与60年代的小说的国际化的进程是如此密切相关,因此当我写自己关于国际化进程的亲身见闻时,写着写着,就觉得是在写自己的一段自传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