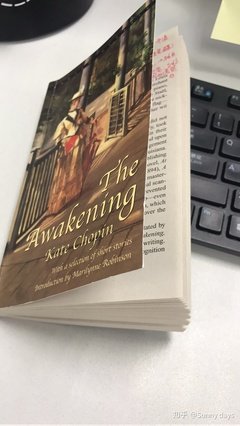
《德国与中华民国》是一本由[美] 柯伟林著作,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6.00元,页数:35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德国与中华民国》精选点评:
●2.8星 只关注了第六章 算是比较粗略的介绍 草草翻过 似作者大饼摊的太大 多而不精 广而不深 另一星扣给翻译
●译者已经很努力了,但全篇充斥着英氏中文,让我这个对中文有洁癖的普通人,无法享受阅读本身的快感。柯伟林的观点和论据令人耳目一新,四十页的参考书目可见柯氏治学之严谨,我辈后学受益匪浅。
●: D829.516/4924-2
●1930年代的德国与“中国法西斯运动”p177-199。德国究竟是如何影响中国?中国人究竟如何看待德国?两边的复杂势力都考虑到了。
●太难读了,读完一遍也没记住什么。不读史,我好像也没法明志了。
●思路清晰,主次得当。不过55-70页印重复了,太不小心
●一般。
●关于所谓“黄金十年”里,德国跟中国关系史的名著。充分运用德国、美国和中国海峡两岸的历史档案,详细论述德国在民国政权建设、经济军事发展和意识形态构建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书中关于两国关系的分析,都基于各自国家利益和国内外形势的变迁而展开,更结合国民性与国民心理进行论述,非常让人信服。
●一段被忽视的历史
《德国与中华民国》读后感(一):中规中矩,也有缺憾
读了作者的中译本序言,击节赞叹,期望值陡然升高。
但读完全书,多少有些失落。不知道是柯先生所受的经济统计知识训练不够,还是受困于原始统计资料的缺乏,一些及重要的经济数据缺乏参照对比性。比如,作为重点话题的矿产钨,柯先生只列举了中德钨交易的绝对数量(还是二手数据);但是,这些钨价值几许(提到了价格暴涨10倍,但无具体数值)?占中德易货贸易的价值比例是多少(或者说,相当于换回了多少飞机大炮)?各年度中国钨在德国军火工业中的地位与重要性如何?等等。没有这些数据,就失去了理解当时的中德政治军事关系的价值参照系,也失去了作者阐述观点的必要佐证,不能不说是种遗憾。
总之,这篇中规中矩的博士论文,前言与后记都很犀利,目前尚无可替代的论著,可列入近代史必读书目。
《德国与中华民国》读后感(二):最后的结语看到两句话挺好玩儿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云云……蒋介石想用将军队之舟与水相分离的办法,避免这种危险。他对军队的社会作用有如下看法:军队可以成为全民团结与遵守纪律的道德楷模,它的“精神”足以成为民众的榜样。更重要的是,他试图通过集中供应和使用所有物资的办法,从物质上把军队与社会分开,以此来改变中国军队有史以来的地下地位,军队历来是靠人民供养的,人民视之如瘟疫。回顾过去,人们就会发现,这是所有力图创立一支成功军队的中国当权者所能选择两条途径之一。另一条是毛泽东的路线,要使军队成为人民的一部分。毛比荀子更高明,把军队融入民众之中,他说:“军队是鱼,人民是水。”
…………
今天的中国仍面临同样的问题:没有一支用世界级水平训练和装备起来的职业化军队,能够抵御现代化军队的入侵吗?或者说,在中国相对贫穷但人口资源丰富的条件下,防御性的“人民战争”真实合乎逻辑,且在政治上也算是明智的选择么?
作者是个美国人,从这些文字也能从一个侧面了解美国人是怎么看待中国军队的……
《德国与中华民国》读后感(三):《德国与中华民国》的读书笔记
过年,没带几本书回家,不知是过年鞭炮的气氛,还是寒冷的天气,鞭炮的热闹和电视里的喧闹,让人变得浮躁起来,看不下书,或许这就是过年,尽管自从长大似乎就不怎么向往和憧憬过年了,热情已然不在,很多时候像是在应付。
书翻阅着看,其中还看了电影《末代皇帝》,书中再次提到,对于1911年在清王朝崩溃的基础上,中国不可避免地要卷入国际激流的漩涡,是一种危险与希望同在的现实。中国人引入外国模式的一种方法是将其作为“主义”,即作为普遍适用的政治或哲学框架而引进的。立宪主义、共和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20世纪30年代某些国民党领袖的眼里,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动员和寻到民众的好方法(新生活运动)。
19世纪60年代,大英帝国在华拥有垄断的地位;20世纪的最初十年中,日本能够轻易地使中国找到一个可供借鉴的模式,它提供了易于接触西方技术与思想的机会,日本短期内的进步,已经从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一跃而成一个强国;1928年-1938年国民党统治中国的十年,这是德国影响中国的十年,中国为重整军备的德国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和战略原材料(特种金属钨),在军事和工业方面频繁交流;40年代,美国成为了自由中国的头号伙伴,它们有着共同的目标——抗日战争;1950年代苏联在中国具有压倒性的影响力,其中的确包括一个具体的“苏联模式”的经济发展计划。中苏意识形态。
军事现代化,自清代起,按西方模式组建中国的武装力量已经成了国家生存的先决条件,在解除了苏联顾问后,对身为军人的蒋介石来说,没有什么能比转向德国这个世界上主要的武器出口国和传统的军事科技强国更自然的了。中央军,主要问题,人数太多,精锐太少,蒋介石想用将军队之舟与水相分离的方法,避免“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危险。而蒋所需要一支既能统一国家、又能抗击日本侵略的军队,然而穿上德式军服并不能给这支军队带来威望和声誉,声望是要靠战场上赢得的。而且蒋介石多年经营的新式的军队(先进的德式装备)在1937年遭受到了毁灭性打击。军事现代化更大的困难是资金,资金只能通过原材料的出口换回。
中国对德国出口的产品依然是她所独有的未经加工的原料。在1932年以前,满洲的大豆和豆制品在对德出口中占有统治地位,但日本占据东北后。为了补偿这一损失,1934-1937年中国芝麻、花生以及其他油料对德出口成倍地增长。然而,最引人注目地改变还是金属矿方面的出口。
锑和钨是两种最重要的战略出口金属,锑的一个重要用途在于使用于制造弹药的特种铅合金变得坚硬。对于钨的全球性抢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它首次被德国人用于切削工具并使军火生产大大增长。钨于“一夜之间成为所有战时金属中最重要的”。在已知的所有金属中,钨的熔点最高。钨铁的首次制造,以及克虏伯公司在20年代生产出碳化钨,并取得了这种“军事金刚石”的专利。它被进一步用来制造生产装甲、穿甲弹、枪管和飞机所需的坚硬、抗高温的钢材,它也可以用来制造电话机、灯丝和钟表零件。
中国有丰富的钨矿藏,1933年,中国生产的钨占世界产量的一半,气候和经济方面的条件也有利于中国的钨矿开采:钨矿地区温暖、潮湿的气候致使沉重的石头风化侵蚀,钨矿砂终年暴露在外,大部分能由廉价的手工劳动来开采。
(最主要的是钨)钨矿业,1934年后,黑钨矿开始向北方出口,国家逐步开始统制,江西大余县西北约10公里,离广东边境约20公里的西华山,有一块世界上最大的钨矿床,在政府统制之前,矿区被划分许多小块,每一块独立经营,漫山遍野充斥着杂乱无章的露天矿区和浅矿道。像采矿业本身一样,矿砂的备制过程以中国特有的手工劳动方式来进行。用锤子将含矿的石头敲成小块,然后将矿砂到进漆黑的竹底篮子,放进一个大水箱里使劲摇晃、颠动。这个过程重复几次,矿砂便从石头里分离出来,沉到水箱底部,看上去更像黑砂。(听说至今我们老家还有人在延续这种古老的纯手工方式开采钨矿,用着生命和体力换取大米和食物)。这时矿砂的氧化钨(WO3)含量50%。然后将矿砂卖给政府加工厂,工厂里通过一个简单的磁性分离器提取锡,再把矿砂放到一个特制的炉子里熔炼,去掉砷(砒霜)并将之作为副产品加以回收。
书总是能带给你,令人赞叹的知识和崭新的视野,所以
摘抄写书中的知识点,记下来。
《德国与中华民国》读后感(四):蒋介石、德国与现代中国
本书是现任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柯伟林(William C. Kirby)的博士论文,也是他的成名作《德国与中华民国》(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柯伟林是汉学家费正清的关门弟子,也是前任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而这本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的书也有很强的费正清学派色彩。
这本书共分八章,英文版的绪论很精彩,而出中文版时柯伟林又加了两版序言,一版写于九十年代,第二版写于大概十年前。第二版中文版序言提出,自从80年代成书以来,中德双边关系的研究已有了更多进展,而他这本书放在当下的意义,已不是中德外交,而是从中德关系来看中国的现代化与国际化进程。他更进一步地提出对中国的国际化研究的两个议题,也即世界如何影响中国,中国又如何改变世界?于是在这篇很短的序言中,他做了三件类似于“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事:一是将自己的这本书放到一个更广泛的视野中做一个聚焦;二是再次为其师费正清及其用国际化视角研究中国的治学方式正名;三是再提中国迅速增长的国际地位以及中国国际化研究的影响。从这个角度审视此书,德中关系史就成了中国在外交、工业、军事和政治的现代化和国际化的过程史。
这本书研究的时间点是从1928年到1938年,这不仅是德国与中华民国的关系最为密切的十年,也是南京政府的黄金十年,这其中的含义也就不言而喻了。第一章讲述1914年之前德国在中国的活动。这一段时间点又被分成了1897年前后。1897年以前,对于以自强为口号的中国官员,德国迅速统一并且经济扩张的先例是一个鼓舞,而这种仰慕又具体表现在军事领域。这一幕将在未来蒋介石与纳粹德国的合作中再次上演。这个时期的德国并未对中国构成最大的威胁,清廷甚至有利用德国在华利益抗衡英国势力的意向。1898年之后,德国取得了山东胶州湾为期99年的租借权。镇压义和团和索赔标志着德国对中国的侵略到达了顶点。1902年之后,德国的强权政策有所收敛,据柯伟林分析,这是因为德国在亚洲的外交陷于孤立,不管是英日同盟还是俄法英三国协约,都将德国孤立在外。德国试图将中国列为“维护远东力量平衡”的伙伴,并且再拉上美国(是不是和亚太力量再平衡有些相似),虽然这一计划最终并未成功。
应当注意的是这段时间美国也是首次直接参与到中国地区事务中来。参照邹谠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开篇:“1899 年 9 月,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向德国、俄国、英国、日本、意大利、 法国发送了关于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声明……维护中国的领土与主权的完整,为保护一切由条约和国际法所授予友好各国的权利。”对于德国,即使与中国的关系并非其首要考虑,但因为牵扯了其欧洲的主要对手,它也必须重新调整对华政策;对于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其实是其门罗主义政策的延续,其目的是阻止列强持续瓜分中国,以保证利益均沾,扩大美国在华影响力。这一策略延续到了二战后期的中美苏关系:美国对华政策的考量,背后是美苏两国在中国的角逐,而当时的共产党与国民党,必须将其国内战略与美苏两国关系联系起来,为之后的内战蓄势,就如同当时的清廷被迫斡旋于德国与英国之间以求生存一样。
及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同年11月7日,日本抢占了青岛,1917年中国对德宣战,德国在中国的地位遭到严重打击,经济利益也损失殆尽。1918年德国战败,凡尔赛条约后面临巨额赔款。而1920年代的中国,军阀混战,对武器和其他军备物资有庞大需求。战后的德国则致力于军事复兴与扩张,重新建立所需的国际联系,加之德国本来就在武器研发生产和军事工业技术等方面享有盛誉,这就为德国重返中国市场提供了机遇,也就是第二章的关注点。这一时期的中德军备贸易中,德国官方甚少插手,但运到中国的武器占到全部外国武器的一半以上,多数是一战期间制造的,这一过程因为要躲避盟国的收缴,充斥着走私与欺骗。德国方面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与中国方面的军阀混战给德国的冒险家们提供了一个高风险高收益的灰色地带。
此时的孙中山正在其职业生涯的低点,护法运动失败,西方外援的冷漠,他所能求助的只剩下苏联和德国。在这一时期的《实业计划》一书中,他非常有前瞻意味地提出,中国将在战后为解决全球经济问题提供出路,尤其因为中国是一个永不枯竭的市场,并且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做后盾。孙中山也为未来中国的发展做了规划,尤其是发展重工业与积累社会资本。柯伟林指出,在孙中山规划中国未来并提出民生主义时,他可能是以德国本身为“理想国”的。他曾经数次访问德国,并相信德国最具有活力,而其政府最具竞争力,俾斯麦不但用武力统一了各州,而且还增加了社会福利。凡尔赛条约虽然剥夺了德国在华利益,却使德国和中国变得“平等”,甚至给了他们统一战线的契机,如孙中山对德国官员所说,“你们德国人已经被解除了武装。现在你们必须武装中国,这可能是你们唯一的自救方式。”
即使在得到了苏联的援助之后,他想要和德国建立联系的愿望依旧,也许是出于想要用德国制衡苏联的考虑。然而当时孙中山自身地位不稳,致使德国军方并未能给与其重视,他所提出的中德俄三国联盟也没能实现,但他的努力为蒋介石在30年代继续与德国合作并模仿其发展道路埋下了伏笔。
可惜鲍尔并没能看到考察团到来。他的公开活动挑起了有关凡尔赛条约的争端,因条约禁止德国公民以其军事才能受雇于外国政府。他与德国国防部的关系也日趋疏远。1929年,鲍尔病死于中国,但此时德国军方开始与在南京的军事顾问团建立直接联系。
德国考察团的访问所带来的乐观不久就因一系列发生在两国的政治经济危机打了折扣:欧洲银行业危机,德国提款和清偿恐慌(panic of recalls and liquidations),长江洪水泛滥,日本入侵东北,国民党的内耗,蒋介石于1931年12月被迫下野。第四章着重描写了在1931到1933年之间国民党自身在工业、教育、经济方面的探索。这一章可能和全书的主题联系的不那么紧密,但是也是必要的背景介绍。
第五章是全书比较重要的章节,即蒋介石与纳粹德国于1933-1936年之间的合作。1933年之后,德国开始公开加速其重整军备的进程,在最开始,增长的军工产品不能被快速消耗,而对原材料的需求又大幅度上升。 再加上因为希特勒将苏联列为其要最终一战的国家,所以与苏联的合作已不可能。这时,如孙中山所预料的,中国作为巨大的市场和战略原料产地的位置就被凸显出来。尤其是战略金属,钨和锑的出口量很大。前者因为熔点高,所以是制造坚硬、抗高温钢材必不可少的材料;后者可用来制造特种铅合金,也就是各种弹片和弹头。
中国方面,日本占领满洲之后,中华民国需要快速实现现代化以自卫和准备对日抗战,于是,共同的利益将中德两国联系在一起。1933年5月,汉斯·冯·塞克特将军到达上海,担任蒋介石的顾问。在其《致蒋介石元帅的备忘录》(Denkschrift für Marschall)中,他就中国的政治制度,工业和军事改革给了详细建议。塞克特的军事思想强调军队应保持小规模、快速、机动、灵活、装备精良、补给充分。考虑到此时的法国正在花费大量人力物力修建最后没什么用的马奇诺防线,而戴高乐的运动战主张却不被法国政府采纳,也许可以说法国在二战中的迅速败北在三十年代初期已有端倪。
和鲍尔一样,塞克特希望搬来德国军队模式,在中国组建一支只听命于蒋介石一人的精兵,并且挑选一个严密的军官团。同时,塞克特也游说蒋介石购买外国新式武器,以履行他为德国军火商做广告的职能。塞克特的建议得到蒋介石的高度重视,亦成为中国军队重建的蓝本。在华期间,塞克特与蒋介石讨论了具体的应对日本和共产党的方针,制定了具体的国防规划,并参与制定了中德合步楼条约。
但此时德国军备的发展影响到其对油的需求,而他们找到的替代物是满洲生产的大豆,于是德国-满洲国-日本三方于1936年结成了贸易体系。德国的亚洲政策因牵涉到与日本、满洲、中国在经济、军事和能源领域的多方博弈而变得充满矛盾,预示着日后德国必须在中国和日本之间有所选择。
书的前五章都在按时间顺序论述中德在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合作,第六章则是探讨了整个三十年代德国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对中国的影响,尤其是法西斯主义、蓝衣社以及新生活运动。如前所述,从孙中山起,中国知识分子就对德国的快速统一和振兴称羡不已,到了三十年代,知识界普遍认为德国的历史和国家形象树立可以给中国提供借鉴。一大批知识分子开始拥护集权政府以及专家型独裁。这一讨论伴随着蒋介石改组国民党的尝试。国民党内派系林立,而其中以黄埔系为蒋的中坚力量。从1932年起,为了增强对军队和国民党的控制,蒋介石开始发展蓝衣社——需要注意的是这也是蒋介石在塞克特的建议下改组军队的时间。1933年,蓝衣社的刊物《前途》发表了多篇称颂希特勒的文章,以支持他们希望在中国进行的激进改革。1934年,蓝衣社以及其他组织开始呼吁授予蒋介石独裁权,国民党内各元老也竭力拥护蒋成为“中国的希特勒”。我们现在重看这段历史,会发现问题并不是蒋介石是否是独裁者,而是在实际操作中,他如何获取权力,积累政治资本;而同时他的权力又因国民党的内耗而被削弱,这直接导致他不可能像俾斯麦或希特勒那样使自己的意志得到彻底贯彻。这一“权力的流动”过程可以从蓝衣社的兴起和1937年的解散找到实例。
1934年,蒋发起新生活运动,其模板也是德国。在比较中德历史经验时,蒋说,德国也曾丧失军事地位,承受不平等条约和赔款,但它依然能快速振兴的原因,在于其“精神”。蒋希望新生活运动能实行中国传统道德规范并结合德国的民族主义观,以重塑中国人的人格和精神。这种兼收中西的精神贯穿于蒋介石本人的生活和行事中,可惜这样一套礼仪规范并不能对人民大众产生感召力,后来也就不可避免地失败了。
在大致读完这本书的重要章节之后,我们可以有哪些收获呢?首先,作为研究德国与中华民国外交关系的著作,成书30年后,其主要结论,用柯伟林自己的话就是,依然“岿然不动”。这当然因为此书的材料非常详实,尤其是考虑到成书时间是八十年代,很多档案并不容易获取。而且细微处的考虑很周到。举一例,在讨论德国从中国进口锑时,他考虑到了锑和钨在中国的生产量,矿石的质量和纯度,更重要的是产地。因当时中国的混乱,而锑和钨主要出产于国民政府控制的湖南省,且可以由廉价手工劳动开采,这一系列条件的满足才使得出口成为可能。
其次,这也是一本讲述国家间关系的范本式著作,里面探讨的很多问题基本都属于“母题”,如果我们拿一本中美关系的书,甚至就是《左传》来对照,会发现很多主题都是重复出现的,比如列强在中国的角力,中国作为弱国被迫斡旋,德国最终因日本可以牵制苏联而放弃与中国的关系等。可以看出,民国外交的一大主题即是各国不同势力借助两国外交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除了塞克特之外,还有一批德国人与当时在广州的国民党人秘密合作,虽然最后被蒋介石阻止。与之相似的是,二战期间美国战争部与国务院,尤其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与战略情报局(CIA的前身)在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上分歧严重,最终导致对国务院一批中国通的打压,风波一直持续到冷战。任何的国家间关系都会与国内态势形成一个dynamic,并且互相影响,中德关系也不例外。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第三,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国民党与苏联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最初苏联给予了国民党很多支持,但渐渐地苏联就成了悬在蒋介石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1938年德国为了能和日本联手对付苏联还是放弃了中国。蒋能与德国在三十年代关系密切的一个原因是意识形态的相似,而苏联与CCP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蒋的大患。随着抗日战争的进行,蒋在中国北方的控制日益薄弱,斯大林与罗斯福交好,最终导致苏联出兵满洲和内蒙古,以及外蒙古的独立。
第四,中国现代民族主义起源近年来也是学界讨论热点,而本书从一个侧面给出了德国对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甚至是法西斯主义的影响。这个过程既是当时知识分子自发的,又是蒋介石为了巩固自身政权着力引导的。关于是否要专政的讨论可以说是糅杂了当时知识分子对中国近现代的耻辱、对德国崛起的羡慕嫉妒恨,对中国国民素质的不满,对中日将有一战的恐惧等诸多考虑。现在看人们歌颂希特勒的文章不免觉得魔幻现实主义,但是在当时的蓝衣社看来,法西斯主义却是可以救中国的正义事业。
第五,关于蒋介石的思想资源以及他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没有无本之木,柯伟林证明了蒋介石对德国的仰慕直接继承了孙中山,这不仅促使他与德国合作,而且也的确深刻影响了蒋介石对军队、政府和党务的改革与管理。虽然Chung Dooeum在Elitist Fascism一书中探讨了蒋介石更受日本的影响,但我是觉得这是个很难给出确切结论的问题。Jay Taylor于2009年出了一本《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但在蒋如何推进了现代化这个问题上,柯伟林这本书有更独到的回答。
第六,国民党内部的组织形态,尤其是蒋介石之外的别的高级官员,如孙科、宋子文、汪精卫、孔祥熙等人如何利用与德国的关系巩固自己的位置。还有一个重点就是黄埔系、政学系、蓝衣社、CC系的关系。这一点是全书比较薄弱的地方,当然情有可原是因为资料的确比较少。我之前猜测蓝衣社可能与上海青帮有关系,Chung Dooeum的书也证实了这一猜测,但是这些派别到底怎么运作的还是不清晰。当然了,我怀疑蒋介石本人可能都未必非常清楚。正是因为这种loose ends太多,导致蒋很难贯彻实施他的想法。
第七,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它让我们重新审视两次世界大战与全球化进程之间的关系。二十世纪初,虽然中国对于德国人而言依然有神秘色彩,但是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增进了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了解和影响。想象一下,希特勒想要一统欧洲的愿望,与在南中国的深山老林里贩卖廉价劳力的矿工之间,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政治交易被联系在了一起,而最终它使得中国的军工业得到发展,并在对日作战时能有一定的防御能力。我在想,究竟是世界大战促进了全球化,还是全球化为战争的准备提供了便利?
柯伟林在序言的结尾处说,“这段历史提醒我们,不是什么非人力的因素,而正是人类自身往往由于不完整的信息、太多的目标,并且时常带着无法改变的意识形态的眼罩影响着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这基本概括了人类历史上一切战争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