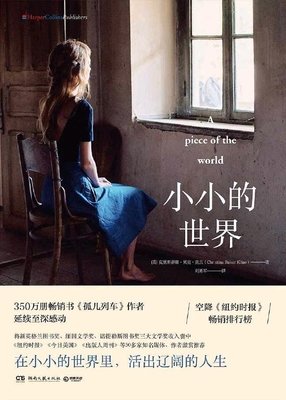
《腹地》精选点评:
●抗战的中间面孔
●从哪个角度来说都不算是艺术上的上乘之作,辛大刚个人形象的充满了私欲和鄙夷使得党所赋予他的英雄形象也并不如其他红色小说一样光辉,革命政党与乡村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并没有通过人物情节这些细节得以更加完满的呈现。所以整本小说都显得稍流于一种泄愤的控诉,一个归乡且残疾的战争英雄在沉默不变的乡土世界中丧失尊严之后通过证明党对抗日的合法领导权而得以恢复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可能是这本书的命运里所蕴含的文学史意义,权力的沉浮反复带来作家想要练就经典的困难。
●有别于其他五六十年代公开发行的其他抗战革命小说,本书节奏并不快,舒缓展开的风情画卷,讲述了冀中腹地村庄的恋爱、派系斗争、小生意人,党员们的小情小爱小算盘小恩怨小矛盾,甚至面对敌人的畏缩,然而在最后迅速转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I247.52/1149 康健 浦分
●党是各色人等组成的,本身有其复杂性。可以肯定的是:有求于民众的党,才是伟大的党!
●主线是伤退军人辛大刚的重新寻找个人价值,副线是辛大刚、白玉萼和范世荣三人的爱情纠葛。辛大刚既有普通人的虚荣和慕艾之心,又能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小说塑造了辛大刚的英雄形象,并以革命赋予的卡里斯马式魅力俘获玉萼芳心,却未能解决小说前半部分提出的问题:伤退军人如何安置?基层组织的有效性和公正性如何保证?
●前面一半写得不错,后面一半太烂了——有种看人民日报的感觉
●值得再看
●禁书,哈哈
●85版细读了,这个原版迅速扫了一遍。书本身不错,作者的身世经历与这本书几版的命运更具学术、历史价值。
●发现历史的本来面貌
《腹地》读后感(一):真实的抗战和小说
抗战题材最真实的小说,也许根本就不是小说。
不是作者主观的想象、抒情、议论,没有矫情和煽动。
是老百姓身上滴落的泥水和鲜血写成的。
我的老家就在“百里自在王”滹沱河北岸,
与小说故事发生的地点很近。
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
我知道那种来自底层的力量有多大。
也知道在微观上,是多么杂色。
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
那是草根,也是脊梁
《腹地》读后感(二):1946年的声音
“在小说《腹地》中,抗日战争在一个具体的村子里,党的领导实际上是被否定了的,党的作用是看不见的,党内的斗争充满了无原则的纠纷“
”对于我们矢志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作者,是值得十二分警惕,应该千百次去思索的。”
《腹地》读后感(三):揭秘新中国第一部遭禁的小说《腹地》被批过程
2011年05月30日 09:22 来源:中国新闻网 参与互动(5) 【字体:↑大 ↓小】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新中国第一部遭禁的小说《腹地》
本刊记者/杨时旸
1954年元旦下午,作家王林到吴砚农家做客。吴砚农是天津市委宣传部部长兼统战部部长。
晚饭后,吴砚农劝导王林,对小说被禁一事,就不必再追究了。王林有些火:“这问题比我的生命还重要,我死了也要写遗嘱要求解决这问题!”
吴砚农劝道:“历史自有公论,何必再追究?”
两人不欢而散。回家后,王林把这些记在了日记里。
王林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就是他的小说《腹地》。这部以1942年日军对冀中抗日革命根据地的“五一大扫荡”为背景、被著名作家孙犁称为留下了“一幅完整的民族苦难图和民族苦战图”的小说,1950年遭禁,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遭到批判的长篇小说。
没想到,王林“死了都要求要解决”的气愤之语,竟一语成谶。
“没有爱护党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
其实,早在《腹地》出版前,争议就开始了。
这部30万字的长篇小说,主人公叫辛大刚,是一位因伤致残回到村中的八路军战士。他参加了剧团,并跟剧团主演、一位美丽的姑娘白玉萼相爱。村支书范世荣是破落地主后代,丧妻后想将白玉萼续弦,于是在村中开反淫乱斗争会批判辛大刚。此时,日军开始了残酷的五一大扫荡,村支书躲到了亲戚家,村政权陷入瘫痪。危急之时,辛大刚毅然担负起军人的职责,带领村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斗争。
小说用细致的笔法,描述了村民在战时的生活和中共基层组织的状况,真实地描写了人物的处境和内心:支部书记也有私心杂念;主人公也有对现实的不满、对当地领导的怀疑和对恋爱的渴望。
王林对《腹地》异常看重,因为这部小说可以说是他拿命换来的。
1946年,王林将《腹地》手稿本拿给文艺界的朋友们看,征求意见。曾在延安鲁艺任戏剧系主任的张庚提意见说:“第一节到第六节气魄大,但辛大刚到剧团中搞恋爱去了……这村前后两支书皆坏蛋,令人不知光明何在?”另一位作家沙可夫却来信鼓励他:“张庚同志他们给的意见,不一定就是说这篇文章完全要不得,用不着藏之名山。”
这是一次尖锐的警告,但是王林忽略了。他以一个作家的固执,拿着原稿四处奔走。
彼时,国共战事正紧,一部小说的命运不足挂齿。直到战争胜利前夕,《腹地》的出版才又重新提上日程。
1949年,王林随部队进入天津,后历任天津总工会文教部部长、文联党组副书记等职。6月,周扬致信王林。虽然他并没有读完整部作品,但肯定地表示:“抗日史诗是需要写和印的。”
此时,针对这部小说仍有各种各样的建议,比如“能否将支书换成副支书”,让王林觉得自己的神经“实在经不住这些老爷们的奚落啦”。
最终,在周扬的支持下,1949年8月20日,《腹地》在天津开始排印。就在开国大典的前一天,王林拿到了第一本《腹地》。他像捧着自己的孩子一样,把它送到爱人刘燕瑾手中。
这位1931年加入中共、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并亲历西安事变的老党员不会想到,在躲过了日军的扫荡和国民党的枪炮之后,他却会因为一本小说,倒在自己同志的批判之下。
《腹地》实际成为禁书
在1950年的第27、28期《文艺报》上,时任该报副主编的陈企霞发表了署名文章《评王林的长篇小说〈腹地〉》。
经历过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洗礼的陈企霞以无产阶级文艺的典型视角,对《腹地》作了一次文本细读。
文章徐徐展开,历数了小说的种种问题:主人公被作者描述为孤僻、村民被小丑化、党员有私心杂念、村支部书记不够正面……然后直指“问题核心”:“在小说《腹地》中,抗日战争在一个具体的村子里,党的领导实际上是被否定了的,党的作用是看不见的,党内的斗争充满了无原则的纠纷。”在文章末尾,作者提出警告:“对于我们矢志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作者,是值得十二分警惕,应该千百次去思索的。”
1950年的《文艺报》,几乎直接代表着中共对文艺思想的态度和看法。这篇两万三千字的重磅文章,将《腹地》定性为“否定党的领导”,实际上已经宣判了这部小说的死刑。
王林后来写道:“因为陈企霞同志的批评,《腹地》实际上成了禁书。”
“也没有具体的禁止发行这本书的文件。就是这篇文章一出,新华书店就都买不到这本书了,很快就全部下架。”王林的儿子王端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陈企霞的批判文章发表后,当时的一位作家孙峻青曾特地去书店寻找这本小说,但无法买到,后来他偶然在废纸堆里发现了一本扯去封皮的《腹地》。
王林感到气愤。根据作家、《小兵张嘎》作者徐光耀的回忆,王林曾专门去找周扬:“我这是在日本鬼子的炮楼下写的小说,你看了没有?”但于事无补。
“她哈哈大笑,我浑身打冷战”
这次名为批评实为批判的事件,是王林命运的拐点。此后,他因为这部小说一共写过8次检查。
这篇写于1952年3月27日的检查,无意间道出了小说被批判的根源。
但王林并不认为自己的这部小说“暴露黑暗”。因为,无论从主题抑或内容上,这都是一部“光明战胜黑暗”的作品。
王林一直关注着形势的发展。1952年,先后任天津地委书记的刘青山、张子善因贪污罪被执行死刑。“刘青山、张子善一抓,我父亲就觉得这实际生活中比我小说写的还黑暗啊,这都可以说,我的小说就可以没问题了啊。他就要给中央写信啊等等。”王端阳回忆。
王林1953年3月的日记中写道:“刘青山从12岁当长工,参加了党……抗日后一贯英勇坚定……因党内民主生活不足使这些好干部走上了可耻道路,我不能不感到异常沉痛!同时我又觉得《腹地》所被动反映出来的这个问题,长期被误认为‘暴露黑暗’而感到异常沉痛!”
三个月后,王林终于等来了一封中宣部的回信。信中写道:“这种问题完全可以在作家中间进行公开讨论。经我们提议,全国文协创作委员会准备在最近召集专门的座谈会谈论你的小说《腹地》,我们并提议届时请你本人参加讨论。”
很快,文协内刊《创作通讯》上刊登了准备召开《腹地》讨论会的消息。王林“喜出望外”,天天盼着这个座谈会。
但再无下文。后来王林才得知,所谓中宣部的回信,只是“一个秘书看了看就回了信”。
丁玲告诉王林:“企霞同志那篇文章发表的时候,我虽在《文艺报》当主编,但是我没看过《腹地》。”王林惊讶地问原因。丁玲说:“我听说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我怕卷入漩涡!”接着哈哈大笑起来。
后来,王林在文章中回忆:“她开心地大笑,我却浑身打冷战。”
1954年,感觉到“呼天不灵,入地无门”的王林终于低头,写了一份《我的检讨》。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创作上无一件成功。抗战期间写的《腹地》又严遭打击和批评……所以我的情绪是‘自馁’‘自惭形秽’……我初步认识到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危险性,希望同志们帮助挖掘和监督改正。”
改稿30年
放弃抗争的王林开始修改《腹地》。没想到,这一改就改了30年。
除了这些,就是无休无止地修改《腹地》“一有想法就写个《腹地》修改提纲,前后我都没数,有好多次。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脑子完全混乱了。”
让王端阳感到痛心的是,王林越来越陷入自我怀疑。“改革开放之后,他也从没想过是不是可以把最初版的重新出,他就认为必须得修改。按照《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的精神修改。”王端阳说。
此时,王端阳已经成为作家,他的弟弟王克平成为“星星美展”的发起人之一。王林对两个儿子叛逆的作品极为反感。“你们以后就是卖国!”老人有时这样说道。
偶尔,王林也会让子女帮自己誊抄《腹地》修改稿。“我从来不管。我说你改那个干什么?现在有谁看那样的小说?你知道那么多事,你写个回忆录多好!”王端阳说,“我父亲对我很失望。”
此前一年,王林病逝。他至死也没能看到缠绕自己几十年、代表自己思想改造成果的新版《腹地》。
2007年,王端阳自费将49年版《腹地》再版。
“我本来一直认为我父亲就是个二三流作家。直到看到了1949年版的手稿才改变了想法,觉得越看越好。”王端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
1950年代初的王林。
《腹地》1949年版、1985年版及2007年版。
在49版《腹地》中,王林手抄了郑板桥的诗句:“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
《腹地》读后感(四):腹地,被忽视的现实一种
表现人类永恒主题的文艺作品常被我们视为经典。不同时代对文艺作品的价值内涵,是有不同标准的。“十七年文学”中,一些作品的的创作,也许正因为欠缺艺术上的推敲与打磨,才使那种真切的情绪、 精神有着难以替代的历史价值。《腹地》是解放区文学中最早表现抗战的长篇小说,以1942年的“五一大扫荡”为背景,以返乡的伤残军人 辛大刚的故事为主线,描写了冀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人 们保家卫国、英勇抗战的事迹。 它对冀中革命根据地 “ 原生态 ” 历史的想象和展示,使其不仅具有了文学与历史的双重功能,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发显现出真正的价值和文学史的意义。习惯于从建国以后革命“正史”中获得历史知识的今人,在读到《腹地》所展现的这一段抗战历史的日常细节时,不能不感到陌生和新鲜。
王林的《腹地》写作于四十年代初期,它塑造了日常化的具有普通人性的英雄形象,保留了时代与乡村的原生风貌,。今天, 当我们重新阅读《腹地》和相关的批评文本时,可以看到小说和新意识形态话语之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断裂”。深入考察这饶有意味的距离和裂缝,剖析批评文本的论述方式,可以看到在批评的意旨所向和批评家貌似强大的批评逻辑中,折射出的是浓烈的民族国家想象和意识形态色彩。
一、为了深入生活到了不要命的地步
王林向组织申请时是这样说的:“ 作为一个文艺写作者,我有责任描写这一段斗争历史,我不能等时过境迁,再回来根据访问和推想来写。 我要做历史的一个见证人和战斗员,来表现这段惊心动魄的民族战争史。”30多万字的纪实性长篇小说完成得并不容易,“因为敌人的点碉如林,汽车路、 封锁沟密如蜘蛛网,随时随地都可能与敌人相遇。我虽坚信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华民族,但并不敢幻想自己能够在战火中幸存。 我就这样,像准备遗嘱一样,蹲在堡垒户的地道口上,开始了《 腹地》 的写作。 …… 写完一叠稿纸,就封闭在地道里。 ” 应该说,王林是一位真正的战地作家。呈现的,大致是最接近历史本然的抗战游击生活。
沈从文评价王林说:“中国倘如需要所谓用农村为背景 的国民文学,我以为可注意的就是这种少壮有为的作家 。 这个人不独对于农村的语言生活知识十分渊博,且钱庄 、 军营以及牢狱 、逃亡,皆无不在他生命中占去一部分日子 。 他那勇于在社会生活方面寻找教训的精神,尤为稀有少见的精神 。“
二、依靠真实的力量打动人
《腹地》作为战争小说,记录了作者所亲历的冀中反扫荡生活,但并没有大规模的战争场面,这正是小说忠实于史实的地方。在《腹地》中,王林通过日常化的叙事方式来处理辛大刚的返乡之旅和战斗生活,让英雄返回“日常”,还原了英雄的“人性”。小说将辛大刚置于貌似恬静实则充满矛盾和冲突的乡村生活之中,通过他的种种遭遇展现了“英雄”的痛苦和迷茫,致力于让“英雄”与周围的环境之间形成有机的联系,以建立一种“现实主义”叙事。《腹 地》的感觉是与真实的生活没有距离。“如芙蓉出水般真实而又美妙地表达思想情感的艺术精神。”使这部小说从结构到语言,都更接近原生态。
孙犁发表文章评论《腹地》说:“这是一幅伟大的民族苦难图,民族苦战图,作者王林自始至终亲身经历了这个事变 。写‘反扫荡’是本书最拿手最成功的地方 。 当然,本书最精彩的地方还是真正写出了地道的冀中人民的生活的战斗的情绪。因为作者写的不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苦难,也不是单纯以故事传奇动人的英雄故事。这是一幅严峻的甚至残酷的现实图画 …… 这里沒有传奇,沒有编造,沒有粉饰.”在王林看来,按照自己在冀中敌后真实的生活感受来写作,让文学呈现敌后抗战的“ 原生态”是自然而然的审美选择。然而,这种选择不符合《 讲话》关于怎么写的要求。《讲话》的精神,要求文艺工作者在创作之前,先从党的立场出发,明确什么可以写,什么不能写。这位1931年加入中共、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并亲历西安事变的老党员不会想到,在躲过了日军的扫荡和国民党的枪炮之后,他最终因为一本小说,倒在自己同志的批判之下。
三、文化单一化是巨大的悲剧
革命文学中不仅是《腹地》的命运如此。从《我们夫妇之间》 、《洼地上的战役》 、《关连长》, 一直到“ 文革” 后期的《 三上桃峰》 、《园 丁之歌》 、《创 业》 , 可以列出一个太长的名单。一路批下来, 人家一拿到《 文艺报》 手都哆嗦:又批谁了?《文艺报》主编陈企霞晚年不愿意写回忆录,儿女们不明就里得到了他这样的回答:“ 我拿棍子打了别人。 有什么价值?”
四、《腹地》实际成为禁书
在日常生活的叙事逻辑里,“感情”是一个很重要的叙事维度。在“十七年”,情爱叙事成为禁忌并非指完全不能描写情爱,而是应当以经过“净化”的世俗快感强化英雄的革命激情,“以爱情如何服从革命的需要来叙述革命的爱情 。在解放区的文学作品里,情爱叙事就不再是个人追求幸福的现代性表征,而是新思想新观念与封建思想斗争的武器,是边区政府实施新政功能的有力表现,如《小二黑结婚》等。 这种叙事禁忌导致“十七年”的许多作品都将伦理叙事纳入了政治叙事的轨道, 在“十七年”的革命历史小说中,这种超尘脱俗的“新英雄”往往通过弃绝儿女情长和俗念肉欲以获得纯粹清洁的革命精神,从而成为芸芸众生的模仿对象和理想范型。
现实主义艺术之所以能够满足现代人对历史感和思想深度的要求,首先就在于它可以确保生活现象的客观真实,这也是认识论美学进入近代后被历史赋予的全新的原则和要求。当情感与偏见,这些通常被认为是个人主观的因素遭到贬斥的时候,现实主义的客观性便无不矛盾的拔高了主体的地位(作为一个独立不羁的观察者)。在司汤达著名的《红与黑》中,小说被比作“道路上移动的镜子”,良莠不分地映射着路上的一切。 从《腹地》上面的描写来看,王林的确没做那样的处理 :把人物本质的边界清晰化 ;没有按照一种惩恶扬善的戏剧程式,对人物进行脸谱化归类,从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小说遵循的是人物在现实中变化的逻辑,而不是一种观念或写作程式的逻辑。在现实主义真实性诉求当中,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它假定了作品直接产生对生活的描摹,而非源于其他作品。
从政治观念出发而导致的文艺灾难并非肇始于“文革”;就所受打击的严重程度而言,陈企霞50年代初始的批判并不亚于六七十年代 “文革”对文艺的破坏。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现代哲学思维方式,本身就不是一个封闭的终极结构,特别是它对文艺思想解放的意义,甚至超过了作品本身。但同时《腹地》面临着无以为继的局面。20世纪以来举步维艰的中国现实主义美学,在40年代末期就完全中断了,对中国文艺来说,现实主义至今还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挫折。
参考文献:
[1]安敏成:现实主义的限制,江苏人民出版社
[2]王端阳.王林和他的 〈腹地 〉.新文学史料
[3]邢小群.“《腹地》事件”引起的思考——从新中国成立后被批判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谈起[J].南方文坛. 2009(06)
[4]钱少武.现代文学批评中的自然观 [J]. 求索. 2016(04)
[5]杨联芬 红色经典为什么不能炼成以王林腹地为个案的研究
[6]邹华 :关于腹地文本命运的美学思考_
[7]曹霞 :论十七年文学批评的主题与意识省略约从王林的腹地及其批评说起
[8]徐玉松 :从自然主义到革命历史传奇论省略兼及十七年文学批评的规范功能
[9]董之林 :旁生枝节对写实小说观念的补正以腹地再版为关注点
[10]马芳 :腹地新中国第一部遭禁的长篇小说
[11]闫立飞 :腹地历史的原生态想象与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