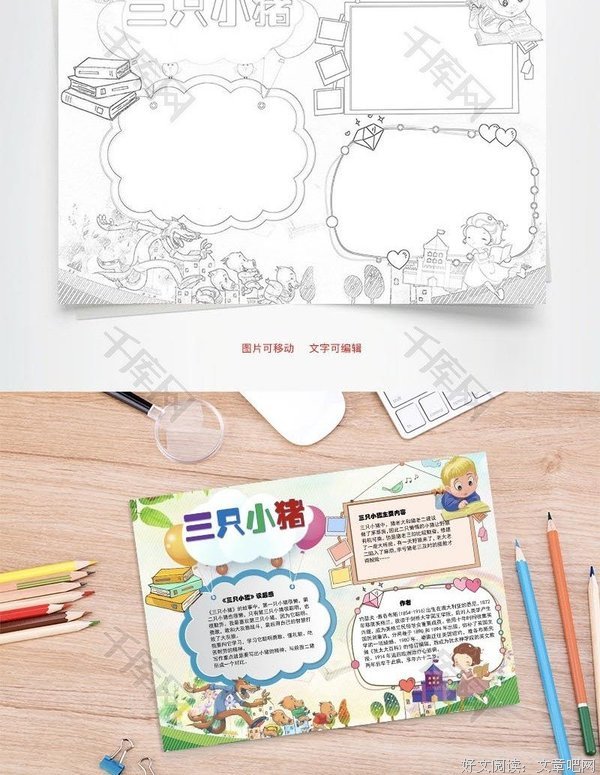
《何以为家》是一本由【美】胡其瑜著作,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3.00元,页数:25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何以为家》精选点评:
●之前很少接触关于北美南美洲华人的书,比较快的阅览了一遍。改变了之前的一些看法,海外的华人似乎总认为是内聚性的,封闭保守,乡缘浓厚,但在异国他乡他们也有积极融入本地社会的一面,为生存所迫,因此华人既然有着融入本土社群的倾向。
●个人认为这本书还是很值得一读的 ,九篇论文从不同方面讲述近代十九世纪的华人在美洲地区的离散与播迁。有关于黄色贸易的全球史分析,华工在墨西哥和加勒比地区的生活遭遇与社会矛盾,唐人街与边境地区中体现出华人的适应策略等等。还通过这些史料分析,看全球化时期,这群被学界研究忽略的加勒比地区华人群体如何适应与生存,也有移民研究中的常规讨论,如种族,排华,民族主义,华商,组织等等。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对于奴隶制和华工契约的探讨。
●论文集。中国移民在拉美。前后内容重复略多,看前面几篇挺好,再看下去发现,只需要看三四篇就够了,后面跟前面视角和意思都大致相同。
●写的相当无趣资料堆叠却干巴巴,没洞见也没趣味。费劲巴拉,而且不如写成排华历史更贴切,浪费了一个很好的切点。
●论文集就不连贯,而且会反复讲同一个话题。第一次正视黄色贸易,南方诸越真是自古以来吃苦耐劳逆来顺受。会将自己的同类作为产品来贸易,说明还没进化好,黑人是,黄色猪仔们也是。当这个世界呈现出新的面貌,会发现不是所有人也都一起同步进化好了的。
●大致是本论文集,有部分有趣的细节,也有不少冗余。
●从黑奴解放之后作为劳力输出到如今的海外务工,因太拼而被排挤,这一百多年来中国移民的特点变化似乎并没有太大。
●胡其瑜從Diaspora離散社群入手分析拉美加勒比華人的遷移狀況,部分研究領域和視角補充了原有華僑史的不足。 另外,18年胡來廈大開會時的名牌是我寫的。
●比较学术化的论文集,观点不多,证据比较充分。本来想看看全球华人飘零史,结果本书专注于北美和加勒比海华人历史。
●内容很多重复,还可以的个案研究。
《何以为家》读后感(一):摘要
古巴及秘鲁蔗糖种植园苦力:自认为契约劳工,法律意义上外国定居者,经济意义上取代黑奴劳力,实质上处于奴隶向自由劳力过渡时期的准奴隶。随1880s种植园衰败而消失,少有女性,老死他国 。
墨西哥北部索诺拉州小商人:平均本金额小,主要经营杂货,从业人口70%,家族化地依附于北美华资网络,为美资开拓市场,受美资支持与庇护,在民族主义浪潮中被驱逐。
墨西哥墨西卡利河谷棉花佃农:租种美国大地主名下土地,可能雇佣当地人,16人可耕种1000英亩,棉花经济低迷以及排华运动阻止了进一步移民(似乎在排华运动受损较小,是否因为实际并不富有?)。
《何以为家》读后感(二):华人移民的“身份”之殇
美国布朗大学教授胡其瑜,多年任职民族与族群研究中心主任,她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发现,学界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华侨移民史多有疏忽,《何以为家:全球化时期华人的流散与播迁》正是她关于本项研究的近十年论著结集。
该书主要展现19世纪古巴和秘鲁平原的中国契约劳工群体。与开拓美国西部的华工群体相比,他们不仅在时间上更早,而且也呈现出迥然有别的社群发展历程。劳工制度的出现,最初是为了填补奴隶制被废除后的劳动力空白,廉价的中国苦力立刻成为了那些大种植园最可靠最经济的劳动力来源。
胡其瑜对大批劳动契约进行了再发掘与比较分析,契约的中文标题叫做“雇工合同”,文本内容强调工作和劳务输出,不涉及“移民”或“定居”,对于报酬、工时、假期,双方的权利和义务都有明确的规定。我们有理由推断,这些受募的中国人出洋的目的仅是为了工作,而不是到陌生的国度永久定居。后来的事实是,雇工合同从来没有被真正履行,工人们在恶劣的环境里超负荷劳动,只能拥有最低限度的生存保障,即使八年劳动期满,他们也被排斥在当地主流社群之外,买不起回家的船票,又没法融入社会生活的中国劳工,只能和原雇主续签,一年年地继续劳作。
翻读这些泛黄的契约,胡其瑜发现,这些劳动力的买家通常被称为“货主”或“业主”,这其实就是奴隶制时期“主人”一词的更具专断色彩的表达。从实际的劳作与生活实态来看,中国契约劳工与奴隶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异。尽管如此,这个仅存在了25年的中国契约劳工体系并非是奴隶制的再版,而更像是奴隶制度向自由劳动制度过渡的中间环节。大多数华工对此都有深刻的清醒与绝望,他们不断地提起诉讼,同时对诉讼结果又少有幻想,华工争取到了最大的、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胜利——肉体惩戒被废止。
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胡其瑜没有忽视华人本身的弱点。关于华工对鸦片的依赖,她的描述同样令人深感痛惜。她关于排华运动的研究和原因剖析尤其有价值。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给华人移民造成了深重灾难,但仅此是不够的。胡其瑜提醒读者,必须注意不同文明的交流与冲突,华人到哪都抱成一团的习性,既是群体发展的优势,也是让自身隔离于当地文明之外的谬误做法,而中国商人爱贪小便宜、以次充好、以假乱真,忽视商业伦理的种种做法,往往是激发当地人反感的导火索。
全球化时代,地域空间不断被打破,移民流动必然会打破原有的秩序,激发土著居民自我保护的倾向,历史上,许多移民好几代都保持着母国的民族文化,新的族群认同一定是在不断碰撞、反复斗争中逐渐形成。胡其瑜以“离散社群”的概念贯穿全书,虽是历史论著,始终洋溢着人文情怀,全球化时期华人的流散与播迁,可以说是早期华人移民身份丢失去重建的过程,这个过程通常伴随着失根之痛与身份之殇。
如需转载请豆邮联系本人,谢谢。
《何以为家》读后感(三):让我的子民走
近代的西属美洲极其类似亚历山大东征后的希腊化世界,希腊人(西班牙人)攻城略地、修整文教,和当地的波斯、埃及(印第安)的贵族联姻交通,华人则处于犹太人的境地,颠沛流离,在各民族大熔炉里煎熬。
漂浮的地狱
19世纪中叶,西方人揣着洋枪洋炮,半威胁半利诱,带走了100多万青年少壮。为了吸引华工,劳务公司欺骗道:美洲的年份相当于中国的一半,签订一个8年的劳动契约,其实是4年,事实上根本不存在所谓“半年”历法。还有一些年轻人不知道古巴、墨西哥在哪儿,以为目的地是宗亲常去的越南、泰国。踏上运输船的甲板后,华人子弟便卷入了全球贸易,成为其中一条环节。
任何一本讲述美洲拓殖开发的书,都不会漏掉大西洋“三角贸易”。很少有人知道,地球另一边隐藏着范围更广的“三角贸易”:欧洲商人带着枪炮、钢铁和纺织品,绕过好望角来到亚洲。他们在福建、广东的通商口岸,卸下货物后,装上了移民,横穿太平洋,运到南美洲;最后装载加勒比的蔗糖、咖啡,运回伦敦的大宗商品市场。(第六章《黄色贸易与大西洋中央航线》)
19世纪中叶正好赶上造船业升级,蒸汽动力船取代古老的风帆桨板,航船载重最多可达1000吨。可运输的时候,吨位总是嫌不够,超载是常有之事,原本客载名额300的,实际装400多人。一名乘客占1吨货物的空间(2吨货物占1.3平方米,大约是一口棺材尺寸,1吨的空间可想而知),人们把运输船“漂浮的地狱”。
华人在船上缺的是粮食,多的是疾病,卫生设施形同虚设,洗漱、寝具、衣物晾晒全挤在一块。前往秘鲁的运输船曾在三年内保持30.4%的高死亡率,去古巴的稍微人道点,死亡率大约是10%,最高的死亡率是一艘叫“蒙塔古女士号”创造的——66.6%,一个在汉语里代表吉祥的数字。漂泊海上的日子仅仅是苦难的开始,到了陆地后,迎接华人的不是解放,而是种植园,19世纪自杀率最高的地方。
种植园·失乐园
单纯看劳务契约,华人的待遇似乎不错,合同把苦力称作“亚裔定居者”(Colonos asiaticos),把新型奴役称为“工业性拘留”(industrial residence),但所有人都知道这些法律术语的真实含义是什么,华人的处境就是奴隶,广东人把劳务公司的经理称为“猪仔头”,把苦力住的地方叫做“猪仔馆”。
由于19世纪英国带头取消奴隶制,南美无法从非洲获取黑奴,便引入中国、印度劳动力。古巴种植园主Pedro Diago回忆1847年第一船中国苦力上岸时,激动地说道:“这些移民将成为我们的手臂,取代那些日益匮乏的黑奴。”华人曾经是秘鲁种植园的唯一劳动力,一度占古巴人口的3%(1877年五万三千八百一十一人)。
从凌晨四点半点名开始,中国苦力持续工作12个小时,晚上睡在肮脏的简易木板房,没有双休日,没有法定假期,监工用皮鞭、棍棒维持庄园的统治。1849年秘鲁移民条令甚至规定了私刑合法,雇主可以体罚“逃跑”和“不服从”的捣蛋分子,异族统治下的华人失去自由、尊严,甚至结婚也需要主人的批准。一开始体罚还有个规矩:当有黑奴在场的时候,白人监工不可鞭打华工。取缔奴隶制后,那些刚获得解放的黑奴当上监工,管起种植园的事务。华人沦为最底层的族群,就像巴比伦之囚的犹太人。
在恶劣的生存的条件下,很多人丧失活下去的信念,轻生上吊、投井。美洲有一种甜蜜而又残酷的自尽方式:大部分种植园用甘蔗炼糖,自杀者跳入炼糖的容器,溺糖而死。讽刺的是,一些种植园在管理本上把自杀列入犯罪事项,因为按照天主教的观点,自杀是为罪孽。(第四章《自由劳动力抑或新型奴隶制——19世纪古巴和秘鲁的中国苦力》)
各种死亡当中,吸过量鸦片慢性自杀很常见。在契约八年的为奴岁月里,华人百无聊赖,只能用鸦片来排解忧愁,这反过来又恶化了华人的形象。秘鲁首都利马的报纸,鸦片广告是专门用中文写的。鸦片和辫子是华人的标志,成为外国人最厌恶的两样事物,甚至黑人在华人面前有了道德优越感(黑人很少抽鸦片,但是酗酒较多)。
华人喜欢鸦片,种植园主也喜欢鸦片,因为它能麻痹人的斗志。一个古巴历史学家统计华人犯罪时,发现18年间,只有12起武装叛乱,许多种植园容许乃至纵容劳工抽鸦片,甚至拿鸦片来付工资。(第五章《鸦片与社会控制》)
排华就是爱国
华夏也曾有过被异族奴役的时刻,在蒙元、满清的统治下,华夏失去了权柄、国度,但保持了宗族、团练、帮会等自治团体。然而这一次不同,华夏面对的不是匈奴、鲜卑、西南夷,而是欧洲文明,论繁荣程度西班牙仅仅是它的二级梯队,但这个次级文明结出的果实仍可媲美华夏: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比中国功夫更实用、审美的巴西柔术,还有圣保罗的耶稣像。
就像《圣经》年代的犹太人面对先进发达的希腊人,失去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中国人向西方文明臣服:皈依天主,放弃祖先印迹,改用西班牙姓氏、基督教的教名,娶本地女子,在圭亚那华人结成不少天主教社区。下南洋的华人离母邦较近,还能保持精神上、组织上的联系,南美华人则一无所有,只能依靠经商的天赋挽回局面。
19世纪末种植园主削减华工,转而招募高原山区的土著;再加之社会改革,大型种植业分散化,华人逐渐告别种植园,有点小本事的靠手艺吃饭,当厨师、司机,工匠开作坊,小本经营,华人中产阶级逐渐形成。尤其是自然环境不适合种植园的墨西哥,华侨发展尤为迅速,在这个国家的大城市里,总会有一两家华人的贸易公司,西北部的一个省份(索诺拉州,对面就是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华人企业共有572家,墨西哥本地企业只及其一半,华人垄断了零售业。美墨边境城市墨西卡利,80%的棉花由中国人种植。(第二章《移民与发展中的社会——墨西哥北部的华人》)
一向繁华的加勒比海地区也有了中国人的立足之地,19世纪五六十年代,特里尼达岛的中国商店遍地开花。1925年牙买加30%的零售业执照在华侨手里,在当地人的语言里,中国人和商店老板是同义词。没有华侨的贸易网,香蕉、可可、咖啡豆只能烂在地里。
美洲人有时候也会拿犹太人和华人相提并论,但这并不是什么好话,他们眼中的华人形象,如同反犹主义塑造的犹太人:自私狡猾、放高利贷,通过压榨他族的血汗过着富足的生活。种植园主仅仅把华人当做“手臂”,可现在这只手臂挣脱了,而且还抓住了钱袋子。当华人做苦力的的时候,美洲人讥笑蔑视;当华人有了物力财力后,美洲人恐惧、痛恨。他们攻击华侨,烧抢店铺。
联共(布)史观说闹事的只是一小撮流氓无赖,事实上排华是有广大群众基础的:底层抱怨华工抢饭碗,商人想抢占华商的市场,牧师要捍卫本地妇女的贞操。每一个民族主义政党都会把排华写入党纲,激进者提出了“排华就是爱国”的口号,政府法规禁止中国人拥有地产,警察对群众排华袖手旁观,最残酷的暴行发生在墨西哥的托雷翁城,300多名华侨在一天之内全部毙命。(第七章《假想敌还是替罪羊?——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排华运动的检视(1870-1930)》)
昭昭天命
多年前学界兴起了航海热,谈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郑和的某支船队去了澳大利亚、哥伦布是拿着中国地图发现新大陆等。奢谈蓝海强国的“大中华费拉民族主义者”,不会想“娜拉出走后”的问题。即使大明宝船真的跨过了太平洋,也无法把美洲变成华夏子民的应许之地。假如郑和真到了秘鲁,情况恐怕和南洋相同,赐予印加国王财货,当成朝贡体系的美洲分部,或许留下一个叫三宝港的地名,除了增添明王朝的荣耀外,别无他用。
即使学者考证出郑和比哥伦布先到了美洲,建立世界新秩序仍然是日耳曼—拉丁民族,中国只能在后面亦步亦趋地跟从。西班牙人开创大航海时代,华人被卷入西方体系;英国废除奴役制度,华人成为奴隶的替代品;欧美三十年代大萧条,华人做了替罪羊。
流落异乡的中国人,品尝到了犹太人那种深刻的苦楚。但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争取的自由机会,华人反抗统治者,兴兵起事(在古巴十年战争中对抗西班牙当局),结交外国(秘鲁华人在南美太平洋战争中协助智利军队)。古巴成功获得独立后,迪哥沙达将军赞叹:“在古巴独立战争中,没有一个华人当叛徒,没有一个华人当逃兵。”
华人翻身为主的机遇到了,在古巴,中国裔领袖Jose Bu被奉为开国元勋,地位和总司令马克西莫·戈麦斯等同。祖籍广东大埔县的客家人钟亚瑟,在圭亚那共和国独立后,被推选为首任总统(1970年3月17日至1980年10月6日在任),他也是首位亚洲以外国家的华裔总统。
刊登于《新京报》 题目改为拉美华人的血与泪
《何以为家》读后感(四):全球资本主义运作之下的劳工制度审视
在古巴首都哈瓦那总统大道街心花园里树立着一座古巴华人纪念碑,纪念碑的铜牌上镌刻着古巴民族英雄贡萨洛·德格萨达·阿罗斯达特吉的一句名言:“没有一个古巴华人是逃兵,没有一个古巴华人是叛徒。”这座纪念碑建于1931年10月,旨在纪念在长达30年古巴独立战争中牺牲的中华英烈。贡萨洛·德格萨达·阿罗斯达特吉还就华工、华商在古巴革命里所做的贡献撰写了一本书《中国人与古巴革命》,书中高度评价了华人在古巴革命中的杰出贡献,碑刻铜牌上的话语便出自于这本书。由这本书我们自然会产生疑问:古巴地区的华人什么时候来到古巴的?又是如何与古巴革命产生联系的?作为外来人身份的华人是如何在当地生存的?循着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追溯19世纪跨越半个地球的劳工制度体系,以便厘清“华工”这一群体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身份与境遇问题。
美国布朗大学历史学胡其瑜教授的专著《何以为家:全球化时期华人的流散与播迁》,通过到古巴、秘鲁的档案馆查阅一手史料,披露了19世纪中后期长期遭受忽略的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中国华人问题,尤其是这一地区历史上引人注目的中国劳工问题。这本书汇集了作者不同时期的论文,这些论文就劳工制度的性质问题,墨西哥北部华人的发展演变,排华运动,唐人街与边境地区华人发展境遇的演变问题做了详细论述。从这些论述中,我们通过历史文献的解读,将对华工当时的境遇有更为深刻的体会,也将促使我们思考奴隶贸易瓦解之后的劳工制度究竟是标榜人权还是“旧瓶装新酒”的美好幻象。当然这一研究显露出来的人文关怀也将促使我们思考当下此起彼伏的排华问题,国际难民,种族歧视等问题,历史的真实面貌从来不会被掩埋。
通向自由劳动制度的荆棘之路
黑暗的非洲奴隶贸易经历漫长的黑暗期终于在19世纪中叶迎来终结,1867年随着最后一艘贩卖黑人奴隶的船横渡大西洋抵达古巴,奴隶贸易自此消失。面对国际上对奴隶贸易的广泛谴责,制定出符合人道主义的自由劳动制度成为重中之重。这项自由劳动制度必须同时具备两项主要内容:其一,保证劳动力的自由与维护其人权,避免遭受诟病;其二,符合资本主义运作的需求,赚取大量资本。这两项因素使得从海外引进廉价劳动力变得尤为重要,于是契约劳工制应运而生,它成为一种新型劳动力制度,用来解决因奴隶贸易造成的劳动力匮乏问题。而中国由于当时复杂的社会环境成为其中一个廉价劳动力出口国(这一点将在后文论及),这些“被出口”的人群有一个特定的名字——华工。
契约劳动制通过一纸契约将劳动力与雇主连接起来,契约规定工人的工作内容与年限。“这类契约通常都由中文和西班牙文对照写成,签订时一式两份。其中一份由苦力自己保管,另一份则由中介机构暂时代管,待交易成功后转交给买家。”(2015:88)表面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份公平的契约,同时这也像极了传统中国签订契约的形式,契约的形式迷惑性诱使大量东南沿海中国人签订契约,成为“华工”。根据作者对契约劳动制的研究,这项契约具有很大程度的欺骗性,契约对于工作时长,社会保障,惩罚措施等方面苛刻的条文泯灭了契约劳动力与奴隶的界限。长期遭受奴隶制影响的秘鲁与古巴地区显然无法在一开始就接受奴隶贸易到契约劳工制的巨大转换,依旧尽其所能压榨劳工,所变化的部分必定以其他部分的压榨来补足(如想方设法延长工作年限),这种“旧瓶装新酒”的把戏因为一纸契约的形式迷惑性欺骗了诸多劳工,也以制度上的合法性确立下来继续作威作福。
然而,随着部分经历千难万险成功完成契约年限的华工成为自由人,种植园雇主面临新的问题:如何让他们的劳动力继续维持下去,继续压榨劳动力。作者通过历史研究指出,为解决这一问题,雇主们一方面通过政府颁布各种严苛的法令想方设法延长工作年限;另一方面,通过培养华工吸食鸦片的习惯对华工进行社会控制。严苛的法令规定华工若因拖欠工作内容或拖欠雇主资金可通过劳动力来补偿,直接结果就是续签不平等契约。而鸦片的社会控制手段使得大量华工不得不通过延长工作年限的方法来偿还购买鸦片的钱。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对华工的压迫。不仅如此,吸食鸦片还成为之后排华运动的一项重要原因。
1874年秘鲁和古巴宣布取消苦力贸易,但是苦力遭受的压迫依旧经历漫长的过程才结束。考虑到华工生存的恶劣环境,作者在对比了华工与奴隶的生存状况后认为契约劳工制更像是奴隶制度向自由劳动制度过渡的中间环节。为什么不是奴隶制度的翻版呢?这涉及华工在契约劳工制中的个体能动性。拿到一纸契约的华工在种植园从事工作的时候,已经自动把自己划分为区别于黑人奴隶的存在,奴隶贸易已经成为了过去,他们是以契约工作的人,年限达到就可自由回家。同时的确黑人奴隶与华工受到的待遇有所区分,尽管不怎么显著。另外,华工到自由人的演变使得他们拥有更多权利,尤其是华工在工作年限期间还拥有不同程度的议价能力,成为自由人的华工还开办商业。从议价能力到独立经营的转变,我们看到的是华工在契约劳动制度下的个人能动性,他们已经形成了在契约劳动制下的生存模式,这套生存模式不是完全被动的,也包含了华工的抵抗。在通往真正意义上自由劳动制度的过程中,华工经历了压迫与剥削,最终终于看到了微弱的自由之光。
“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的华人刻板印象
“他们任劳任怨、技能娴熟,无疑是最好的剥削对象。而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心甘情愿地被剥削。只要能够得到不低于50%的利润,他们能够忍受任何程度的艰苦劳作。”(2015:55)美国Boyle领事曾这样评价在加利福尼亚工作的中国人。无独有偶,在主管墨西卡利棉花种植的美国大地主眼中,中国人人也被视为承担繁重劳动力的苦力代表,“平整、改良土地需要付出极其艰难、繁重的劳动,只有中国人能够在骄阳烈日下承担这样的工作。”(2015:51)作者在对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华人研究过程中,不论是论及美国人,还是秘鲁,古巴地区的种植园主,都提到这些人眼中的中国人人品质。在他们眼中,中国人勤劳节俭、吃苦耐劳、任劳任怨,能够承担一切艰难的劳动,哪怕是让无数奴隶丧生的秘鲁鸟粪经济,在吃苦耐劳的中国人努力下也能完成。久而久之,人们似乎觉得中国人天生就是如此般,这一印象也使得跨越太平洋的“黄色贸易”愈发兴盛。
尽管“勤劳节俭、吃苦耐劳、任劳任怨”这些词汇放在汉语乃至别的国家语境里都是属于品格称赞的词汇,中国也以此来概括中国人的民族气质。但这些词汇置于契约劳工体系下还拥有同样的意义吗?这种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难道不正是造成华工遭受压榨的原因吗?作者在文中并没有对这一问题作出明确回应,在这里我想尝试提出一些关于这一问题的想法,试图分析当时对华工的这一刻板印象是如何形成的。
想要谈及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先明确华工这一群体在没出国之前是何身份。历史学家经过确认,1847年中国第一批华工到达古巴哈瓦那,开始漫长的契约劳动。1847年正值鸦片战争爆发后几年,中国于1842年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在这一不平等条约之中规定清朝政府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同时赔款2100万两白银。紧接着也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繁重的赔款数额通过清政府直接下达到民众身上,民众成为了赔款的直接牺牲者。除此之外,孔飞力在《他者中的华人》一书中在论及这一时期移民构成时提到,土地资源的短缺也使得农民开始向海外谋求生存空间。国内局势动乱,民众遭受清政府愈发严重的压迫,征收高额赋税,再加之闵粤两地土地资源缺乏,人们开始向外迁徙。在这些迁徙的人中,有商人,他们大多集中在东南亚地区,还有农民与流民,后者成为华工的主要群体构成。
传统中国的经济制度是封建小农经济,在长期的小农经济制度下,中国的农民与土地之间形成了割不断的联系。几千年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练就了农民顽强的生命力,以及在恶劣的环境下生存的能力,无论是天灾还是开荒,都成为农民世代流传下来的生存技能。在这世代的与大自然共生的经验里,勤劳节俭、吃苦耐劳的品格特征形成。但是农民面对的不仅有地理环境的严酷挑战,还有封建帝国的压迫。长达千年的的赋税制度尽管有时苛刻无比,但因封建力量的强大也不能完全引起农民的反抗,中国古代历史上虽然爆发过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但收效甚微。长期的起义失败与谋求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得农民养成任劳任怨的品格特征,埋头苦干,只求谋生。这些特征保留了下来,使得这一群体在成为“华工“的时候也按封建主义压迫之下的生存模式生存,更何况殖民地政府也不会以人道的方式对待他们。
再者,我们不能忽略种植园主、大地主对华工的压迫,压迫加深了勤劳节俭、吃苦耐劳、任劳任怨所谓民族品格的程度,或者说这些品质某种程度上是被制造出来的,对华工的刻板印象只不过是对丑恶压迫的辩白。当“黄色贸易”成为一个跨洋贸易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从“猪仔”的招募,到将他们软禁起来,期间再经历长达三四个月的海上航行,这些劳工已经经历了被驯服与恐吓的过程。作者在文中描述了航行过程中华工的生存状态,他们被严格限制在下层船舱,生活环境恶劣,也遭受体罚,和奴隶无异,有人死去,有人活下来。他们在到达之前已经经历“驯服”过程,而到达后严苛的工作规定只会更胜一筹,作者在书中花大量篇幅论述此处不再赘述。面对严苛的契约劳工制度,回家的渴望使得他们迫切想要完成工作年限拿到契约,大多数人自然便形成任劳任怨的品格特征。对华人的刻板印象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压迫者不能以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来为自己的压迫辩白。
除却以上两项内容,作者还在书中讨论了国家在华工、华商管理体系过程中的参与,展现了国家基于政治利益对于华人的庇护(如美国),跨国公司的参与,同时还注意到“唐人街”与边境地区华人的发展演变,从历史中汲取研究养分将有益于我们未来的研究。
(匆匆结尾,还有些议题没有详细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