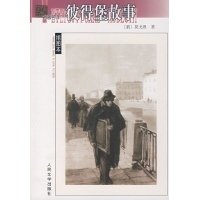
《彼得堡故事》是一本由果戈理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4.00元,页数:23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彼得堡故事》精选点评:
●「脑子是被一阵风从里海那边吹来的」
●涅瓦大街探讨了一个主题 世界为什么是错位的
●很遗憾,短篇小说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在加速被遗忘。故事行云流水的怪才果戈理,其讽刺和幽默早被夸烂,更吸引我的是那充满灵气的怪诞。狂人日记、外套、鼻子,都有对后继文人大有影响的开创;肖像则谈到了艺术、宗教和灵性,这种关于艺术家的故事总让我十分着迷。
●相比《狄康卡近乡夜话》,这本在叙事策略上显得更加成熟,或许因为是都市故事,鲜艳、活泼的东西少了不少——另外,的确可以看出,鲁迅的小说受果戈理的影响非常深。
●读果戈理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所以这些故事的情节都已忘得差不多,再读的时候就有了一些新的体会,最重要的还是自己亲自去了趟圣彼得堡,对故事的场景有了直观的感受。全书第一篇涅瓦大街,是我淋过暴雨,也曾后半夜暴走的核心街道,但果戈理却将它形容成了谎言的渊薮。鼻子和外套都非常典型地反映了都市小职员的悲剧,前者更是荒诞得离奇。狂人日记因鲁迅后来的同名小说而备受中国学界重视,但这个故事更近妄想狂,较之鲁迅的悲愤交加,作者像在鉴赏笔下人物的笑料似的超然。肖像充满鬼魅色彩,让读者脊背发凉。马车则只是特点最不鲜明的一个讽刺笑话罢了。
●《鼻子》!!!《罗马》和《外套》也都不错。这个魔幻现实、精灵古怪的果戈理,是不符合我们的预期的。
●毛子行前功课#1
●我的天哪,可以多分点段落吗?长句已经看得累人了,而且还不怎么分段,实在是太考验我了。不过现实主义的故事还是挺可看的…
●罗马
《彼得堡故事》读后感(一):好书
起初看果戈理的《死魂灵》时,不是很有感觉,中途甚至还停止过阅读放在书架上,过了好久才接着看完,才明白了那本书的伟大之处,最近看了这本中短篇小说集依然非常喜爱,尤其是《外套》让我几次差点落泪,一生遭遇坎坷的果戈理用唐吉诃德似的幽默和深具洞察力的叙述嘲笑和剖析他所处的那个阴暗的社会,在我对其贫穷困苦的一生产生命运不公的感慨时也在我的心底向其敬以崇高的尊敬。
《彼得堡故事》读后感(二):哦,涅瓦大街
1,看果戈理的书,还是要看满涛翻译的。
2,果戈理的文章好学,就是观察、观察、观察,然后记录、记录、记录,然后修改、修改、修改。
3,涅瓦大街读到会背,文章写出来就不差了。我们的文风是欧化的,看左传其实对当下写文章意义是不大的。
4,果戈理改文章也好,可以去看新世纪万有文库里面的《果戈理是怎么写作的》一书,会改才有提高,看别人怎么改自己的文章更是事半功倍的事情。
5,其实,当下的我不是很适应这种文风,所有只能敬仰一下了。
6,我翻看过了。
《彼得堡故事》读后感(三):别老盯着那件“外套”,一点不好笑
虽然俄国大文豪都说“我们都是从果戈理的《外套》里走出来的”,但就个人而言,从中获得的阅读乐趣远要低于《彼得堡故事》中的其他篇目。果戈里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外套》却似乎因为其故事过于“现实”,使得这种对现实的批判过多地沉湎于读者对小人物的同情当中。
相比之下,《鼻子》、《肖像》和《狂人日记》是我比较喜欢的篇目。故事的中的各种荒诞可笑,却被果戈里写得一本正经,好像这才是“现实”。在我看来,当中的想象力和艺术效果是要超过《外套》的。
《鼻子》和《狂人日记》都多少有点像现代主义小说。《狂人日记》是一篇第一人称的呓语,尽管离奇,却也有真实存在感。《鼻子》则走得更远,故事荒诞,以至于果戈里在小说的结尾要费一些笔墨说来说服读者,“人世间总有这类事情,——不很多,可是免不了”。译者满涛在前言中建议读者不要纠结于这篇小说的一些无逻辑的细节,毕竟这不是警察查案,个人非常认同这种阅读策略。从文学的角度解看,“鼻子”可以有很多象征意义。但囿于教科书中心思想的定型,八等文官经历的怪事也只能算是俄国封建体制下畸形社会的必然后果了。先不管果戈里写作的最初意图,小说中所反映的诸如报社广告、政治联姻等等的社会百态,在今天读来,也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多少陌生感。反倒是借着寻找鼻子这条故事主线所带来的陌生化效果,小说才得以超越了某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作为读者,我们或许总能在其中找到一些“耐人寻味的东西”。
《肖像》和《涅瓦大街》都是关于艺术家的故事,小说结构也有相似之处。只是《涅瓦大街》通过正反两个故事给读者呈现了大街的明暗面——艺术家的高尚和官僚的堕落。果戈里对涅瓦大街从清晨到深夜的精彩描写是小说的亮点,给人以置身其中之感。但是,小说以对比手法呈现主题的形式——至少对我而言——没有带来多少新鲜感。《肖像》同样由两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将讲述了艺术家“财迷心窍”的“堕落”故事,第二部分以大段人物独白补充了故事的来龙去脉。要不是小说结尾的神来之笔,也许《肖像》就会和《涅瓦大街》并列成为现实主义批判小说的范文。小说以一句话结束了沉闷的情节交代,开启了一个意犹未尽的循环,所达到的批判效果远超出了《涅瓦大街》黑白分明的叙事。
《彼得堡故事》读后感(四):彼得堡的挽歌
早在1928年,曼德尔施塔姆就在他的《埃及邮票》中写道,“一想到我们的生活不是一个有情节,有英雄的故事,而是一个由忧伤,由玻璃制品,由不停息的到处蔓延的狂热的嘈杂声,以及由彼得堡流感引发的谵妄呓语所构成的传说,就让人毛骨悚然。”彼得堡之所以使对其爱恨交加的曼德尔施塔姆如此形容,其实正好体现了彼得堡不同于俄罗斯其它城市的独特气质。据说彼得一世一开始就想让彼得堡代替莫斯科成为俄罗斯帝国的首都,1703年,彼得堡在彼得大帝的雄心下在沼泽地上拔地而起,作为俄国现代化改革的重要进程,彼得一世满怀期许的想让彼得堡成为向欧洲打开的一扇窗口进而取代莫斯科几个世纪以来的宗教传统。
然而在沼泽地上打造彼得大帝的乌托邦的结果是,大量的劳工死亡,亡魂无数。这使彼得堡在建成伊始就被打上了一股阴郁的调子。彼得堡宏伟宫殿的窗户玻璃与消逝的暮光交相辉映,但除了一片火红的景象之外总还有点颓败和忧伤的模样。1835年,一个神色奇诡,有点神经质的年轻人开始徜徉在彼得堡的涅瓦大街上展开了对这座城市和人的全部想象,就好像里斯本的佩索阿或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博尔赫斯或伊斯坦布尔的帕慕克,彼得堡将会因为果戈理的到来而变得更加完整,彼得堡的身后开始有了个幽灵般的偷窥和沉思者。虽然十七年后,果戈理仍然抵挡不住他应该已经司空见惯的现代化的侵袭——很难断定他是否真的热爱那座为现代化而生的城市——就像在《涅瓦大街》中他所写到的一样,“为了把斗篷更紧的裹在身上,”他有步骤的将自己饿死。那时,我们才发现原来果戈理想要更紧的裹住自己的东西原来是死亡。
果戈理好像并没有赫尔岑或奥加莱夫信誓旦旦的决心和燃烧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激情。当十二月革命党人疯狂的迎着风浪,冲向彼得堡的青铜骑士广场寻找着普希金和伟大的俄罗斯精神的时候,果戈理正平静的在大街上溜达。《彼得堡故事》中的人物和事件需要他每天闲逛在涅瓦大街上的神秘想象。我们宁可这么想,也许果戈理眼中这见鬼的现实一无是处,但他依旧不可避免的要与工厂机器,酒精,路灯还有沿街的商店遭遇,即使他的眼光无比犀利,很快的讥讽“你都来不及看一眼就消逝在你面前的幽灵”,但他还是愿意停顿,在他的关于彼得堡的故事里,事实证明,他对眼前如幻像一样的真实生活兴趣盎然。
有些人愿意把果戈理的故事往“含泪的笑”上面理解,其实那可能低估了果戈理对待哭泣看法。在《外套》中,果戈理把恐惧和屁滚尿流丢给了老是扒别人外套的人,那个趾高气昂的将军最终看到的是一只大得出奇的拳头。马歇尔·伯曼说过,《外套》可能是果戈理关于彼得堡最好的小说,因为阿卡塞耶维奇在穿上了新外套之后的确美好的融入了一阵彼得堡的幻象中去了,看见了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亮的灯光,衣着华丽的可爱的女士还有对他看似善意的玩笑。但这一切的结局却是,广阔天地中的微光和“看上去好像站在了世界的尽头,”就在阿卡塞耶维奇仿佛走在旷野中的一瞬,果戈理阴沉的站在他身后要向我们说明什么呢?在哭泣中微笑么?我们能看到的是最低限度的尊严的剥夺,但到死甚至死之后,果戈理也没用含泪的笑使他自己和读者释然,有的只是孤寂的亡灵四处的游荡。
对我们来说,果戈理的意义也许就在他狡猾的挑明了一种潜在的事实,他漫不经心的暴露了彼得堡或者现代主义的吊诡经验,虽然“彼得堡们”同样的狡诈,果戈理最后还是输了这场战争,但他向散发出时代光源的镜子有预谋的打碎的举动,令我们或多或少的清醒一些。他最终也只留下了甘心变成亡灵的侧影,在其消失的一刻,我们还是看见了一丝暧昧的光亮,那光亮正是果戈理想要提醒自己和世人的,它令我们疯狂,也令我们惋惜。
《彼得堡故事》读后感(五):飞奔呀,马,带我离开这世界
果戈理展示的景观是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彼得堡。这是古老俄罗斯为向现代转型而建立的城市,一个灰暗喧嚣的城市。这个灰暗喧嚣的城市里最灰暗喧嚣的地方是涅瓦大街,如果你来到涅瓦大街,必须带上一万卢布,好在入夜后狂歌纵饮。上等马车飞奔而过,燕尾服贵族们昂首缓步,鲜艳华服在身的小姐太太满目兴奋,准备在即将到来的舞会上大放光芒。暮色苍茫,街灯点起,一种美妙的游荡的气氛笼罩着整条大街。海獭皮领子,英国式女帽,如轻烟的舞鞋,晶莹的宝石戒指,希腊式鼻子,勾魂的眼睛,雪白的臂膀……你不由得要去观望,你忍不住要去追逐。如果你没有钱,你是多么痛苦。这里就走来了一位买不起冬衣的小公务员,他畏畏缩缩,他佝偻而行,看着缤纷世界与自己无关。他走回那个阴暗狭窄的小黑屋,躺在床上让自己早早睡去好让夜晚容易过去。
这就是果戈理的彼得堡。果戈理的彼得堡是真实的也是虚幻的。这个短篇集有七个美妙的故事,七个美妙的故事创造了一个看似光彩夺目实则平庸乏味的世界。这个世界的核心是“庸俗”,用心认真的人在这里获得失败与痛苦,无耻虚伪的人如鱼得水,自在大笑。人类世界永恒的一面就是这种庸俗乏味,你在什么时代,总是能听到这种得意的大笑,大笑泛滥之处,意义消解。果戈理听不惯,他要的笑是带泪的,是悲悯,他写的是一个个微小的生命如何在这样没有意义的世界里被吞没。
《涅瓦大街》开启大幕,这个包含了一切的大街上一日的景象与在其中游荡的人们。这是彼得堡的舞台,是人类舞台,是整本书故事的背景。两个在街上追逐女伴的青年,一个在寻找美丽,最终发现堕落,无法接受而自杀;一个随便玩玩,闹剧一般调戏女人,最终挨了一顿打,打就打了,他气了一顿饭的功夫,一杯酒的功夫,就忘记了,再到街上追逐。一切如同幻影,一切都是欺骗。
《鼻子》是写官员的,一个一心往上爬的八等文官一早醒来,发现自己的鼻子丢了。他恐惧,恐惧是因为这样有碍于前途,有碍于找到有财产的未婚妻。他的鼻子在哪里呢,正身穿燕尾服,乘坐上好马车,在街上闲逛,鼻子是一副五等文官的样子,他哀求自己的鼻子回去,最后一番追逐后,鼻子回去了。他可以继续去相亲了。去高升了。去活着,去死去。在这个故事里,“鼻子”是什么?是欲望,野心?还是我们活着的可怜目的?
最经典的是《外套》,是《狂人日记》,都在讲任何时代任何一个人可怜的存在真相。
《外套》讲一个小公务员发奋得到一件梦想的外套与失去外套后痛苦而死的故事。在这篇里,果戈理真是大师手艺,一点点扎实推进,把小公务员阿卡基推到了绝望的地步。阿卡基是文书抄写员,白天抄写文书,晚上抄写文书,从不注意街景,从不到任何地方,“他于抄抄写写之中似乎看到了一个多彩而舒心的世界”,“他尽情地抄写够了,就躺下睡觉,一想到明天就暗自微笑:老天爷明天又会赐给他什么东西抄写呢?”他做好外套后,几年来第一次出门做客。他走在街上,夜景出现,通过阿卡基的目光,果戈理的彼得堡夜晚闪现出来:
“路上人来人往的,时而可见衣着华丽的淑女和身披海狸皮领子的男子,赶着装有木栅栏和钉着镀金铜钉的雪橇的载货马车夫倒不多见,——相反,头戴深红色的天鹅绒帽子、驾着上了漆的铺着熊皮褥子的雪橇的神气的车夫却不时地迎面而来,还有装饰一新的轿式马车的轮子轧轧地辗着雪地,疾迅地掠过街道。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望着这一切都挺新奇。他已有好多年晚上足不出户了。他好奇地站在一家商店灯火通明的窗前,望着一幅美人图:那美人脱下鞋子,露出一只好看的纤足,而她的身后则有一位长着络腮胡子和唇下短尖小胡子的男子探头张望”
这幅夜景曾经与阿卡基没有任何关系,但凭着新”外套“,他第一次看见了这个城市。好悲悯的细节啊。
“在他的生命行将结束之前,外套这个光明的使者曾倏然一现,使他的可怜的生命瞬间活跃起来”。每个人都有一件自己想得到的“外套”,但有时目光升起,这一切变得可悲而狭隘。
《狂人日记》里肆意奇绝的语言真是精彩。这个也是讲小公务员,因出路无望而发疯,把自己可恶的现实处境变形为一个更加荒诞的世界,小说便是叙述这个变形过程,真实的世界与梦幻的世界互相映射:一个疯狂的世界。
纳博科夫对《彼得堡故事》的评价多好啊,“一个四处漂泊的读者……一个人在破败寒伧、月影班驳的旅馆里醒来,在又一次沉入昏睡之前,听到单墙的另一边传来低沉的喃喃声,起初仿佛静静的欢快的众鸟啁啾:一些无意义却又非常重要的句子,奇怪、破碎的声音的混合,谈着人类的生存,一会儿是展翅时发出的歇斯底里的劈啪声,一会儿是焦急的深夜呢喃。我觉得,那些彼得堡故事不灭的魔力和永恒的意义就存在于它与相邻世界的联系中。”
果戈理的彼得堡,你应该来转转。也许你根本无须来,而是一直生活其中,谁说不是呢,看看周遭的世界吧,果戈理的彼得堡也许就是你的上海,你的北京。它们“同毁灭处于同一纬度”,你需要的兴许是“一辆快得像旋风一样的雪橇”, “开车呀,我的驭者!响起来呀,我的铃铎!飞奔呀,马,带我离开这世界!再远些,再远些,我什么都不要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