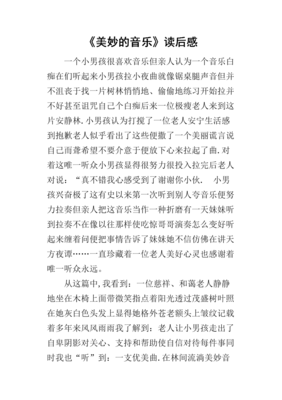
《小夜曲》是一本由[美] 詹姆斯·M·凯恩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29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小夜曲》精选点评:
●前半段的铺垫在于节奏一直压着,很多的线索是围绕声乐来说的,没有这方面基础的读者自然一脸懵逼,很多人前半段看不下去也大概是这样的原因,可这些都是为了后半段的加速服务,有许多WTF桥段,还有一个黑色小说式浪漫的结局,拿斗牛的桥段如何设悬念来说,真的非常棒。
●开头倒是简洁凝练
●我还挺喜欢这首B面曲,当然,凯恩克制到冷的笔依旧是太迷人了,我可能是喜欢凯恩所有但唯一不喜欢《邮差》的人
●胡安娜对神明的敬畏,可爱又浓重的鼻音,让我知道她是个好女孩。她把乳头塞到他的嘴里,吃吧,像个母亲和姐姐一样安慰他,诚实结实的好姑娘。
●这是我觉得最棒的凯恩的作品,其中对于胡安娜、墨西哥和好莱坞的评论我不能赞同更多。
●终于下定决心KO了这本,(伦家短篇你下什么鬼的决心!)囫囵吞枣,理解靠后记啊。不过我总觉得为什么说是社会毁了他俩?命运不是因为自己的选择而改航的吗?另我再也不会说我懂音乐了…
●一个明星和妓女的故事
●在今天来看,明显的政治不正确,但故事的节奏,编织没说的,相当好看。
●断断续续读了将近一周。翻译别致可爱。
●在我心上用力地开一枪,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
《小夜曲》读后感(一):闷骚凯恩也救不了糟糕翻译
对白完全没有人物特点,只有胡安娜因为口音被区分开了。
这个锅必须译者来背了吧,毕竟《邮差》的译本行文是不差的,虽然一贯冷峻克制臭脸感。不至于入口即化,但也绝不至于难读。
话说回来,从个人喜好上,这个故事本身也不如他其他作品来得好看,密密麻麻的歌剧圈的知识点,报复性地堆砌。更像是凯恩夹带私货的个人趣味,我假设他是放开了写着玩玩儿?(人家做不成歌剧演员还能当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在我现在这个年龄再过六年都写出了《飘》,而我还在这里挑凯恩的刺)
是不是对社会的控诉姑且放在一边,两个人走向毁灭的结局更像性格使然。价值观与性格都楚河汉界,却偏偏相互疯狂痴迷、执拗纠缠。
一碗鬣蜥汤还是一个知心人?
答案恐怕永远消失在亵渎神明的那个雷电之夜了。
两个人真实生活后潜意识里互相怨怼的那一段,写实到喉咙发紧。啊,男人的幼稚和女人的天真相遇,注定是个美好但殊途同归的故事。
旅行路上断断续续看,回来的飞机上读完。全篇读到最后一个句号后,又翻回到开篇第一句——当时我正在图皮南巴,吃一份烤饼配咖啡,这妞进来了。
恍如隔世。
全文停不下来的对墨西哥碎碎念似的吐槽还蛮带劲的,凯恩这个人真是闷骚又毒舌啊,很巨蟹。
《小夜曲》读后感(二):执拗
书里写如果夏普没有接那通电话(温斯顿的电话),他们的生活将是另外一副模样,可我觉得错误在逃离墨西哥已经显现。
爱情在某种程度上追求对等,夏普其实同温斯顿是同一类人,跟胡安娜却差之甚远,夏普说温斯顿只看钱,而自己又何尝不是呢?胡安娜在乎的只是自己开不开心,从来不在乎其他人的眼光。好莱坞女明星的话刺痛不了胡安娜,但能切实的扎痛夏普的虚荣。
金庸说温斯顿代表的是“社会黑暗”,其实我觉得这种说法相对有些夸大。温斯顿一系列的做法难道真的有错吗?他爱夏普所以想要得到他,从巴黎追到墨西哥再回纽约,他的内心如同一个小孩子,喜欢就得占有,就得不择手段的占有。也有着单纯的执拗。
夏普。在墨西哥瞧不起墨西哥的一切,却想尽办法的让自己“生活下去”;觉得只要回到美国,一切都好办,可置身于好莱坞却身不由己。他其实一直在逃离,想逃出墨西哥,又想逃出美国。这个人物身上的无所适从很像现在的一类人,在哪儿都不对,在哪儿都差点什么。
我很喜欢很喜欢这个故事,喜欢这种不顾一切的执拗。啊如果要重拍电影,Sofía Vergara演胡安娜就好了。
《小夜曲》读后感(三):金庸:《相思曲》与小说
你或许是我写的《书剑恩仇录》或《碧血剑》的读者,你或许也看过了正在皇后与平安戏院上映的影片《相思曲》(Serenade)。这部影片是讲一位美国歌唱家的故事,和我们的武侠小说没有任何共通的地方,但我们这个专栏却是上天下地无所不谈的,所以今天我谈的是一部电影。也许,百剑堂主明天竣的是广东鱼翅,而梁羽生谈的是变态心理。
这一切相互之间似乎完全没有联系,作为一个随笔与散文的专栏,越是没有拘束的漫淡,或许越是轻松可喜。但《相思曲》据说是从美国作家詹姆斯·凯恩(James M. Cain)一部同名的小说改编的,我在三四年前看过这部小说,现在想来,不觉得小说与电影之同有什么关系,后来拿小说来重翻一遍,仍旧不觉得有什么关系。
你看了电影之后,一定会觉得这是一个普通的俗套故事,不知道有多少美国影片曾用过这个故事:一个艺木家受到一个贵妇人的提拔而成了名,两人相爱了,后来那贵妇抛弃了他,使他大受打击,但另一件真城的爱情挽救了他。然而小说的故事却不是这样的,完全不是。
凯恩的作风与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很相像,他们两人再加上司各特·菲兹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和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这几位美国第一流的作家对欧洲近代小说发生了相当大的影晌。凯恩有点模仿海明威,不论题材和风格都有点相似。这部《相思曲》的小说,造句筒短有力,描写激烈的感情、粗鲁的火热的性格,在性的方面肆无忌惮,都很像海明威)但社合意义却胜过了海明威大多数的作品。
单是这两个例子,你就会想到,电影与小说的风格是截然相反的。是不是电影的文雅比较好些呢?我以为一点也不是。
小说中有一段话(小说是用第一人你写的),表示了作者对好莱坞的看法,也说明了好莱坞为什么要用现在的方式来摧毁这部文学作品,书中这祥说:“我不喜欢好莱坞。我所以不喜欢它,一部分是由于他们对待一个歌唱家的方式,一部分是由于他们对她的方式。对于他们,歌唱只是你所买的东西,你必须付钱的东西,演技、剧本的编写、音乐以及其他所有一切他们所使用的东西都是这样。这些东西本身可能自有其份值、这种念头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他们认为本身自有其价值的,那只有制片家,他决不知道勃位姆斯与艾荣·柏林之间有什么分别,他不会知道歌唱家与哼时代曲的人有什么分别,直到有一天晚上,二万多人高声大叫要听那唱时代曲的人唱歌,他才懂得两者的不同,除了遍剧部替他写好的故事大纲之外,他不合读书,他甚至不合说英语,但他自以为是精通音乐、歌唱、文学、对话以及摄影的专家,只因为有人把奇勒·基宝借给他拍一部影片,于是他成功了。”
小说家凯恩对于好莱坞一点也不尊敬,于是他们对他的小说也使用了暴行,不过不是在教堂里,是在摄影场上。
黄夏/文
美国作家詹姆斯•M•凯恩一生著述颇丰,有趣的是,他最好的几本小说,如《邮差总按两遍铃》(1934)、《双重赔偿》(1936)、《幻世浮生》(1941)等,都是在其创作最初十年内写成的。日后评论家将凯恩归入“硬汉派”(Hard-Boiled)小说家之列,其实他笔下的主人公都是些意志不坚的软蛋,且多作奸犯科的亡命徒。真正让读者产生冷硬感受的,是凯恩凌厉简洁的文笔,和如抽丝剥茧般层层展现小说内在精神的结构。凯恩发表于1937年的《小夜曲》虽不似上述几本小说有名,但它无疑属于最能体现其创作特色的作品。
也就是说,直到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夏普的心结,我们也知道康纳斯的那段话,并不是要警告夏普注意胡安娜作为女性的毁灭性,而是要提醒他,胡安娜可能会识破他的真面目。换言之,夏普知道的事情,康纳斯也知道,而我们是只有在胡安娜起疑并且质问夏普的当儿,才知道这件事情。
这种声东击西的手法堪称石破天惊。在凯恩以往的小说中,我们总是紧跟着男主人公的足迹,去探寻女主人公(通常是些诱人、神秘和危险的美女)的秘密。一言以蔽之,我们天然地信任叙述人的忠诚和可靠,但在《小夜曲》中,这种忠诚和可靠崩溃了。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内心装着深不见底的“永恒和无限”,其叙述的合法性、自洽性,皆因胡安娜的存在而渐渐丧失,也迫使我们回过头去重新检视那些曾引起我们怀疑、却因惰性或者成见而宁愿觉得不无道理,以至帮着自圆其说、让其再度具备合法性的细节。读者发现小说读到这个地步,被作者狠狠揶揄了一把,气恼之余,除了重读,又有何法?凯恩文笔的简洁只是表象,其内里的丰富性是十分骇人的。
凯恩的创作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几乎与海明威和福克纳同期。把这三个作家摆在一块儿似有点不伦不类,一个是写“类型文学”的,另两个是写“严肃文学”的,怎么看都不搭调。但凯恩文字刀劈斧砍般的简洁有力和丰富意蕴,和对不可靠叙述声部近乎邪门的运用,还是让我们不禁想到后两位作家,因是同时期,谁影响谁自然无从谈起。因而,如果取消“类型”和“严肃”的界限,把这三位作家放在美国文学的大背景中来审视,我们自会发现,他们都敏锐地触摸到了20世纪文学发展和变革的脉搏,其创作应当是有着内在的隐蔽联系在其中的。
《小夜曲》(Serenade,1937)自然不是詹姆斯•M•凯恩最知名的小说。同《邮差总按两遍铃》、《双重赔偿》和《幻世浮生》三部作品的熠熠盛名相比,她更像是一首精彩绝伦的B面歌曲。同那三部名作一样,《小夜曲》也被改编成了电影上映(1956),可尽管有马里奥•兰扎(Mario Lanza)的精湛演唱与琼•芳登(Joan Fontaine)的倾国美貌,此片还是几近湮没无闻了。这次失败的改编或许伤害了小说本身的流传。说“失败”,倒不全是后见之明。金庸大侠早年同梁羽生、百剑堂主合写专栏“三剑楼随笔”时,曾发表过一篇《<相思曲>与小说》,说的正是凯恩的这部作品及其电影版本。金大侠以为:
说得不错。撇开两大巨星的演绎不论,电影版的叙事框架,哪怕在当年看来也是够俗套的。而原作小说,恰如金大侠所言,是个关于毁灭的故事。至于是否仅仅意在“控诉恶劣的社会”,可就没那么简单了。
一、
当时我正在图皮南巴,吃一份烤饼配咖啡,这妞进来了。
这样冷峻的开头,我们已在《邮差总按两遍铃》里见识过了(“约在中午时分,我被人从运干草的卡车上扔了下来”)。开篇第一句,作者就让两位主人公全部登场。故事的源头也已交待大半:“这妞”闯进了“我”庸常的生活。读者心知肚明,不用等太久,“我”就没闲工夫在墨西哥的小酒馆里吃烤饼喝咖啡了——凯恩的演奏会可不需要暖场嘉宾。
约翰•霍华德•夏普原是个著名歌唱家,可出于神秘的原因,他猝然失了声,流落到墨西哥。他在酒馆里对胡安娜一见倾心,可跟她回家后才发现自己的心上人竟是个“三比索一晚的妓女”。这并没有破坏夏普对她的好感,他为她唱小夜曲——一切甜蜜在此时戛然而止。胡安娜从歌声里听出了一些东西,夏普不愿面对的东西。
夏普带着胡安娜回到美国,在电影与歌剧上都大获成功,终于重振声誉。他把高额报酬作为给她的“惊喜”,却只换来淡淡一句“是的,非常棒”;他演唱《卡门》博得满堂彩,问她:“你为我骄傲吗?”她却答道:“我干吗要骄傲呢?我又不唱歌。”夏普渐渐明白,胡安娜要的不是财富与荣耀,而是忠于本心的生活;现代文明的繁华,合同、协约的束缚,全然撼动不了她那句“我喜欢”。在夏普眼里,好莱坞的佳丽名媛,在人前光鲜亮丽,私下则是一众下流货色,都及不上胡安娜可爱。
其实从一开始,夏普看到的就不是真正的胡安娜,而是想象之灯在他心上的投影。夏普要追求艺术的境界与世俗的成功,胡安娜关心的却是一日三餐与自己的心情,她最大的理想,也不过是开家妓院。可她那种热腾腾,近乎原始的活力是夏普所缺乏的。虽然他在教堂里强奸了胡安娜,可他始终是这段关系中受支配的那方——夏普蒙在鼓里,读者可看得清楚。温斯顿的电话来了,夏普终于从幻梦中眯开一只眼睛,可大祸也将临头。
二、
从温斯顿出场起,整个故事开始不可避免地滑向悲剧。就如同现代版的俄狄浦斯,众目睽睽下,只有夏普本人尚不自知命运的无可挽回。他与胡安娜正行驶于一条单行道上,错过转弯口,等待他们的只有万丈深渊。温斯顿可比雷暴雨、陡峭的山路和鬣蜥要可怕上千万倍。是他指导了夏普舞台的技艺,成就了他的事业,可也正是他“唤醒”了夏普的“心魔”,“每个男人的身体里,都有百分之五的那个,要是他刚巧遇对了人,那部分就会被激发出来。我的就被激发了,就这么回事儿”。
在最终的冲突爆发前,有一幕,胡安娜将乳头塞进夏普嘴里,夏普说:“现在我知道了,我整个的生命来自那里。”可他并没有超脱出来。他没有勇气去冲破业障。他选择逃避。直到看见左手拿披风,右手持剑的胡安娜俯视着口吐血沫的温斯顿,夏普这才承认,“我正目睹平生见过的最为壮观的景象”——曾经透过灯影瞥见她身上的那些特质,不过是自己的一厢情愿。此时的胡安娜,不禁令人想起尤金•奥尼尔剧作《大神布朗》(The Great God Brown)中的西比尔,也成了地母(Mother Earth)的化身:
她是个结实、安静、肉感的金发姑娘,约摸二十岁光景,皮肤滋润、健康,乳房丰满,屁股肥大,她的动作慢腾腾、懒洋洋而踏实,像野兽的动作,她的大眼睛像做梦似的恍惚,反映出深沉、本能的激动。她嚼着橡皮糖,像一条圣牛,怀着永恒的目的,忘掉了时间。(《奥尼尔文集》卷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128页)
三、
夏普痛恨墨西哥人,认为他们一无是处,胡安娜不过是特例。当他还沉沦在自建的迷梦里时,康纳斯已看清胡安娜“是典型的墨西哥人”,可“她身上存在美”,这种美恰恰源于她流淌着阿兹特克人的血液。他也不忘提醒夏普,“真正的美包含恐怖”,“那个小妞身上也有恐怖,但愿你在同她交往时一刻也不要忘记”。
••••••永远••••••永远••••••都不再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