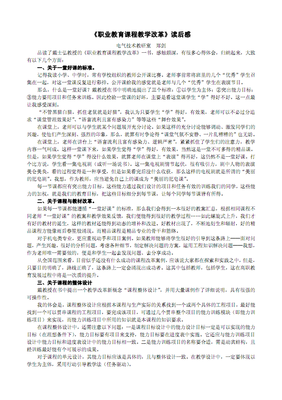
《课程》是一本由约翰•富兰克林• 博比特(John Franklin Bobbi著作,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元,页数:26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以培养现代公民为目标来确定课程,无关、低效的内容全部舍弃,逐步实现社会的进步。
●保守主义者写的马基雅维利教育手册。以历史时间轴来看,其远见与创建令人敬佩。"行业专业化与行业道德建立在组织上必须分开。专业化过程中,为了道德与专业发展,代理人意识必须明确。"这是什么?明显是自由原则与代议制民主经验的结合啊。本书的表达务必在教育建设本身和教育内容上贯彻这两点。道德原则出发点所在,硅○学的来?
●读过的第一本专业相关书籍。非常开脑袋。 很有必要常常回看!
●我有一个做人民教育家的梦。 我也有一颗(如天空中的太阳一般黑里透红)的黑心!
●跟杜威的进步主义相随(芝加哥大学),第一次将「课程」作为专业学科来建设。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作者提倡的教育取向,大多数放到今天看,也是一种回潮,例如强调要把教学的场景不限于学校、提倡实践车间中的行动学习
●自己翻译的又一部书,历时四年多,终于出来了。二十世纪是个伟大的世纪,美国跃升为一个超级大国,美国教育开始展现她独特的魅力,美国教育研究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部书,就是这样一部奠基性的作品,它标志着现代课程理论的建立。今天几乎全世界,包括中国,所有学校的课程规划都受到这部著作或显或隐的影响。认识他者,也是为了认识自我。
●现代课程理论的开山之作。书名平实,但内容相当丰富有启发,对中国社会如今普遍焦虑的许多教育问题均仍有现实意义,课程设计其实并不只是一个教育学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社会要培养什么样的成员(现代公民)的问题。
●博比特有他那个时代进步主义者中很普遍的乐观精神、科学精神,相信教育对社会的优化更新作用。联系今天的教育现实,书中很多理念依然有被重视的必要。以及,刘幸师兄的译笔非常流畅,读来十分舒服!
●百年前的经典,观点仍未过时。也是一本极佳的教育指南。课程编制在于坚守原则而并非执迷于各种方法与所谓流行模式,社会经验为教育的原料库,教育的理想主义是先在的,至美至善是最为阔远的追求。教育所培育的理想的社会参与者,必拥有健康的同理心和严肃的思想。
●从太平洋西岸遥遥回望百年前大洋东岸的美国教育,有多少日用而不知。却难言这种“无知”是福是祸。
《课程》读后感(一):课程:学习的过程以及顺序
既然天下的父母都是能看到《皇帝的新装》那样得高度“称职”。――我想他们没有什么“课程”的必要了。
这是2018年02月03日《人民教育》微公号有奖征答【每周一问:你读完会忍不住分享的一本书是什么?】活动的幸运赠书。
我的回答是:我想推荐北师大版的《人格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拥有这两本书五年有余了,之后了解的心理学通俗作品、的内涵都不超过这两本书。――对于学生来说,我推荐一些有哲理性地书籍供参考:《小王子》《亚当夏娃日记》《苏菲的世界》…这些书籍在讲述情感和思想方面有独到之处,希望学生们喜欢。
岁月蹉跎,一年多后才加强阅读进度,于今天刚刚读完。――翻译是精良的,只是少量句式明显非汉语言风格;也许是“直译”,以体现翻译事业的文本忠诚度。
虽然终身学习观已经提出好多年;虽然男女杂交的敝人等已经明显把【性关系口头语】这种传统语言能力退化了很多;但是,在市县边区的昨天,我某个无性繁殖的奶奶还在(无耻地)为和我姥娘睡觉的语言实践找逻辑基础。――这些纯种中国遗民,倚老卖老的架势,还想“我死我有理”三十年!
用鲁迅的疯话:这都是他们娘老子教的!――“(传统)从来如此,便对么?”――“我不同你讲这些(现代科学大)道理,总之你不该说(我,我怎么说也是个长辈),你说便是你错!”
这些倚老卖老[不时玩玩封建迷信、三纲五常]的行尸走肉,把儿子没有教育好的耻辱全都忘完了,继续正大光明的毁人不倦地改造留守于家的孙子们!――这些孙子很快都有了自己的《兵法》,准备实践在广阔的犯罪舞台上!
我怀着鲁迅不敢假设的险恶居心,冷冷地看着这群无耻地反对几何公理的叫驴们!
《课程》读后感(二):博比特《课程》:百年后的重逢——与《课程》中文版译者刘幸对谈
(本文刊登于《中国教育报》3月20日第9版,发表时有删节。)
1918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教育管理学教授约翰·富兰克林·博比特(John Franklin Bobbitt)出版了一本新书《课程》(The Curriculum),由此诞生了“课程论”这一教育学的分支学科。作为课程论的开山之作,本书的出版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上半叶美国的课程改革运动。但是,这本经典著作在中国却芳踪难觅,仅有少量民国时期的节译本存世。青年学者刘幸有感于访书之难,于是历数年之功,潜心钻研,重新翻译了《课程》,收入教育科学出版社“世界教育思想文库”,终于让它在百年诞辰之际,与中国读者重逢。为使读者进一步熟悉《课程》的写作背景、博比特及其身后的课程理论发展脉络,本书责任编辑对译者刘幸做了一次访谈,全文辑录如下。
问:你最早接触到博比特,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境下?对他最初的认识是什么样的?后来为什么会萌生翻译《课程》的想法?
刘幸:我个人第一次接触到博比特,是2012年,当时我进入北师大教育学部,攻读“课程与教学论”方向的硕士。郭华教授为我们开了一门必修课“课程理论”。在介绍了中外的一些传统课程之后,当郭老师正式介绍现代课程理论时,她开宗明义:博比特以及他在1918年出版的《课程》一书,为整个现代课程理论奠定了基础。那堂课带有入门性质,因此郭老师只是大致地介绍了他的理论,比如,博比特开始思考如何用科学的理论指导课程的编制,而不再是基于个体教师的感性经验;另外,教育要实现效率化,就需要将课程编排得紧凑、细致、精确,不再用一些笼统的概念来涵盖一切。这些思路都贯彻到了他的学生,日后享有盛誉的拉尔夫·泰勒的课程理论中。我现在都还清晰记得,郭老师的课是在第二教学楼上的,那栋楼出门走几步就是书店。下课后,我想把博比特的原书找来读读,就溜达到了书店,结果却找不到任何一种汉译本,事实上,当时市面上也确实没有博比特的译本。之后回北师大图书馆检索,我才看到,民国时期有两本博比特的书被译为汉语,分别是《课程》和《课程编制》,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但当时师大图书馆只有一个书目,民国版的原书已经佚失了。我没有料想到这个过程竟是如此一波三折,这一方面让我意识到,我们今天在经典学术著作的翻译和推广方面还有很多沧海遗珠,另一方面也更激发了我想要了解博比特的兴趣。
《课程》读后感(三):课程的读书笔记
什么是课程?
课程,指的是孩子和年轻人以提升自己能力的方式来完成和经历的一系列事情,它有两种意义:1.整个旨在拓展个体能力的经验,包括有指导和无指导的经验。
2.一整套有意识的指导下展开的训练经验。
教育经验获取的两个阶段
谈到人如何获得教育经验,作者将获得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游戏经验和工作经验
游戏活动和工作活动与教育之间的关系*这里的工作指的是指一个人的职业以及要负责的各项活动。
游戏经验和工作经验的比较
游戏经验和工作经验的不同点师生对工作所得成果的看法差异
教师:注重学生施展个人能力完成工作的发展成效,比如对某学科知识点的进一步思考和感受
学生:先注重学习成果,比如作品的完成和考试的分数,其次再关注发展成效。
学生应当参与教育流程的预演阶段
预演
预演阶段是执行任务前设置任务目标和对应计划的阶段。
教育流程
预演-执行-优化
该流程出现的常见问题
学生只执行老师设置好的设计方案,没有自己的计划,导致责任感缺失。
老师只教与实际工作无关的知识,导致学生获取的工作培训匮乏。
预演完成后,执行阶段未完成,导致没有成果,教育毫无意义。
执行的完成有利于提升个体的操作技巧,理解力和鉴赏力,但不利于提升智力视野宽度。
作者主张学生参与预演,培养提升自身的责任感以及公民意识。
如何制定课程?
课程,是针对用普遍的,无指导的训练无法解决的错误而设置的一系列有指导的经验,是个体无法通过无指导的教育和经验习得的专业学科知识。
课程设置者需着眼于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从工作世界的缺陷(工人效率低下、管理者在组织操作和指导工作方面效率低下等)中挖掘对有指导的职业训练的需求,提供解决缺陷的一系列课程,以完成提升社会职业发展和教育下一代的教学使命。
当受教育者将课程上学过的知识运用到控制自身行为和培养习惯的层面上时,教育才算是完成了。
其他零碎知识点
作者主张通过休闲活动锻炼体能以及提升阅读能力。
职业教育的目的是通过普遍启蒙消除戕害人的工作环境。
职业的社会伦理是由接受对应服务的人完成的。
作者主张生产领域的职业低效和消费者判断的低效应当被克服。
将职业活动转向学校和鼓励学生参加校外实践成为解决学校教育脱离实际生产的主流方案。
在集体工作的大环境下,作者主张,每一个成员都要了解整个组织的工作流程和各个部分,精通自己负责的部分即可。
作者主张公民树立服务所在团体的对内道德和抨击敌人组织的对外道德。
《课程》读后感(四):构成「好生活」的种种活动
(一)三面透视镜
西元前400多年,孔子就奔走于齐鲁大地传业授道,但现代课程的历史中鲜有来自东方的注脚。教育是一项悠久的人类活动,而课程作为「科学」只有短短一百年的历史。当人们试图超越个体经验,当人们开始思考为什么而教、为什么教这个而不是教哪样、该怎么教、如何教才有效,并企图总结出一套心法时,现代课程科学/理论就诞生了。第一个做这项工作的是美国人博比特(John Franklin Bobbitt)。19世纪20年代,美国占领菲律宾后,旋即着手将美国的现代化制度引入当地。博比特作为七人委员会之一员,自1902年起负责为岛内所有小学编制新课程。在驻扎菲律宾的五年里,博比特意识到美国学程在菲律宾水土不服。课程不能仅仅是对学科知识的直接挪用,而「必须基于某些原理,针对不同的社会背景进行调整」。
1918年,在参与美国多地的学校调研之后,博比特出版《课程》(The Curriculum),立下现代课程研究的第一块里程碑。
简单来讲,在《课程》这本小书里,博比特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学校可以教什么?(What the Schools Teach and Might Teach,1916)
我们把这个问题往前走多两步。如果你是博比特,要破解这个问题,必然绕不开这几个问题:
1. 眼下学校正在教什么? 2.(我认为)什么值得教? 3. 判断「值得不值得」的标准是什么?即:我对第2题的观点是从何而来?
这三个问题,即便放在当前、即便你是以课程消费者的角色去考察各个学校、某套教材、某个课程,都是可以拿出来用的透视镜。
(二)学校教什么
显然,眼下的学校所教的东西并不能令博比特满意。在此之前的课程形态是古典的,是以继承文明精粹为任的博雅、道德、修身,是孔子的六艺、柏拉图的七艺。孔子一生鞠躬尽瘁也只能教出三千门徒、七十二贤,博比特则是生活在追求「时间就是金钱」的时代,大城市、大企业在美国土地上拔起林立,工业企业福特汽车的车间亟需批量的流水线工人、更高效的生产率。与此同时,进步主义知识分子号召平民和劳工,要从保守的精英阶层手中争取议事的权利。
这种进步主义的社会气氛,加上在菲律宾的五年、在美国本土多校调研的经历,让博比特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社会:今日的学童,未来将在社会中开展什么活动?除了生产能力,一个公民的活动能力需要具备哪些?一个人要做些什么,才是「漂亮地完成成人生活的事务」?为了此目的,课程所要传递给学生的,是什么?
博比特给出的答案是:经验。
这一想法或许还可追溯到务实的斯宾塞(Herbert Spencer)那里:教育的功能就是要为未来的完美生活做准备。课程,是有意识地提供各种经验的发生。
年纪尚幼的游戏阶段(play-level),经验是不去考虑实际用途,带着兴兴头头的劲儿去观看人类大戏、游览盛会就好;接着,人则逐步步入工作阶段(work-level)——历史、科学、数学、哲学,摈弃感官的高层次智力游戏。体育锻炼、肌肉训练带来身体的效率、能量、活力,提升工作的愉悦。文学是用来体验的,阅读是一种具备理智特点的休闲活动。团体、宗教、道德教育,则是在预演如何成为一位合格的公民。
博比特勾勒出,一个理想的成年人该从事些什么活动、以何面貌过一种Ideal 的生活。从这些事务倒推回来,便得出学生应当在学校里开展何种实践、获得何种的经验。
(三)游戏:是目的,也是过程
串接起这一系列经验的内在线索是什么?假如去除那些束缚人的「套子」(生存的压力、严肃的职业、家庭的责任),一个人独立的生活状态、充满活力的面貌,是由什么力量驱动的?
富有意涵的是,《课程》开篇以「游戏经验」发端。并不仅仅因为那是生命中无知懵懂的初期,而是博比特深信,如果一个人能积攒将「游戏精神注入工作之中」的经验、并拥有此番能力,工作就能变成一种审美的的活动。
一个人这样获得自己的自由。感觉自己就是工作的主人,而非工作的奴仆,那么他就把工作转化为一种广阔的休闲娱乐的经验。 ——《课程》,教育科学出版社,2017年3月,p173喝酒、抽烟、享受冬日暖阳;田径、足球、交际舞、运动大会;棋牌、文学、歌剧;科学、哲学、宗教——这些被观察到的自由的良好的人类活动,被格鲁斯(Karl Groos)排布进一个游戏的层次阵列中,从引发最简单的感官愉悦到高级的智力活动,最高序列的是到严肃的、理智特点的休闲活动。
博比特在书中引述席勒的话:
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这个道理看起来有点似是而非,不过如果把它运用到义务和命运这双重的严肃上去……将承担起审美艺术以及更为艰难的生活艺术的整个大厦。 ——《审美教育书简》游戏(请不要从当下的字面意义来理解这个词汇,我这里所指的是席勒、格鲁斯、赫伊津哈所阐释的「游戏」)——不单单是开箱吃鸡,它要求你明智地选择、平衡,往往还需要「加以充分而严肃的努力」。特别是到工作阶段(work-level),一个人面对的更多是艰难的生活艺术,比如挣脱自己所在的「套子」、比如议事、比如参与社会事务、比如理解、比如爱。
写到这里我似乎已离题「课程」太远了。但读这本薄薄的小书、这本尚未形成严密编制方法的小书,我读到更多的确实是博比特对于「好的生活」理解、对一个「大写的人」的描绘。他比哲学家们所谈论的「Good Being」要来得具体:他所谈论的是构成「好生活」的种种活动。
未来,不管我们谈到卢梭杜威泰勒还是威金斯(Grant P. Wiggins)和麦克泰格(Jay McTighe),不管我们考察任一课程模式、设计模式,任何一套线上还是线下课程的概述或广告词,都需要自觉地抓起那三面透视镜,因为它们无法抽离一层哲学意味的底色:在What 和 How-to面前,Why 是不可逃避的。
而在「 How-to」这个问题上,博比特的学生拉尔夫 · 泰勒(Ralph W. Tyler)接过了接力棒。
20190312 Create by Doujiang《课程》读后感(五):《课程》译后记
译后记
最早接触到博比特,是在北师大教育学部念硕士期间,上郭华教授的课。郭老师为我们讲授课程理论史,明确地将博比特以及他于1918年出版的《课程》一书定为现代课程理论的起点,也介绍了博比特的“活动分析法”“效率主义”等基本概念。之后在别的老师的课上,“博比特”这个名字也反复出现过,这引起了我的兴趣,让我想读读他的原作。然而,我在逛书店时才发现,市面上根本就买不到任何一本博比特著作的汉译本。到北师大图书馆进行专业检索,我才发现,博比特的书在民国时候其实有过两个译本。1928年,张师竹先生译的《课程》在商务印书馆出版;1943年,熊子容先生译的《课程编制》(How to Make A Curriculum)也同样交由了商务印书馆出版。可惜北师大图书馆只存一个书目,所藏的民国书原版已经佚失。我辗转去了国家图书馆,见到了前一本;后来,又在北师大丁道勇老师那里见到了后一本。
博比特原书的英文版在网上不难见到,我比照着英文版,将两个民国的译本读过一遍。两位译者都是饱学之士,对原书的理解并无大的偏差,但时代的巨大差异决定了这两个译本对我们今天的读者而言,是不敷应用的。一来,两位译者所用的文辞夹杂着大量文言——毫无疑问,这是那个时代的普遍风貌——这对今天的一些读者而言,不啻一道理解上的鸿沟;二来,当日的翻译毕竟没有今天这样严格的标准,译者自出机杼,删改原文的情况时有发生;最后,一些零星的误译也不难见到。更何况,这两个民国译本的存世量还是太少,我为了见到这两本书就不知费了多少心血。一般的读者朋友如果只是想把博比特的书找来了解一下美国教育史的大体情况;教育专业的学生如果像我一样,只是单纯地想看看博比特的原作究竟谈了些什么,恐怕大多数都会因为访书之难而打消了这个念头吧。但我在阅读博比特的著作时,其实很有些被他的文字所吸引。他的书写得平实,论证也不复杂,但有一种洞若观火的透彻,而且远远比教科书里总结的那几个理论要点复杂得多。我打心眼里觉得,如果只是因为访书之难就让很多潜在的读者和这本世界教育发展进程上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失之交臂,未免太可惜了。有鉴于此,我有心想为博比特的《课程》一书重新译出一个中文本。这个想法得到了导师郑国民教授和教育科学出版社刘明堂主任的大力支持,我的翻译工作由此得以顺利展开。
本次翻译所用的底本是波士顿Houghton Mifflin出版公司1918年出版的《The Curriculum》初版本。2013年6月,我开始着手翻译,历时大约一年后提交初稿。责任编辑翁绮睿女士秉持着高度的职业素养,向我反馈了一份细致的修订意见。这个时候,我刚刚获得日本广岛大学的博士入学资格,于是带着一沓厚厚的翻译初稿,坐上了前往日本的飞机。我一边进行博士课题的研究,一边进行修订译稿的工作。广岛大学丰富的英文和日文藏书让我加深了对博比特的理解,我的导师丸山恭司教授也常常和我聊起他在美国求学时的点滴回忆,让我多了一些感性的认识。日本的大学里没有宿舍,我每天骑着自行车,沿着一条长长的黑濑川,往返于学校和住所之间。这段漫长的车程,就成为了我在口头一遍遍打磨译稿的最佳时刻。有时候,确实要把一些长句子念出来,才能察觉到当中可能存在的疏漏之处。今天回想起来,这条黑濑川听我念叨了快两年的博比特,如果按日本古代“万物有灵”的说法,可能也该修炼成世界上最懂课程论的一条河流了吧。
修订稿提交后,翁编辑又与我进行了多次来回往返的审稿工作,力求将译文打磨得更精准一些。在合计历时三年多之后,《课程》一书终于能以现在的面目问世,我的心里满是激动。两任导师郑国民教授、丸山恭司教授给予了我充分的信任,也给我留出了学术自由的空间,这是最令我感动的。郑老师也花费了相当大的精力,赐下一篇精彩的序言。我相信,这会对读者朋友们理解博比特,起到很好的作用。在翻译过程中,我曾向北京师范大学的郭华教授、张斌贤教授、石中英教授、王本陆教授、王晨教授、李家永副教授、丁道勇副教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曹卫东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的张心科副教授和东北师范大学的徐鹏副教授等多次请教相关问题;广岛大学的坂越正树教授、山田浩之教授和安田女子大学的内田诚一副教授也对我关照有加;美国佐治亚大学的William G. Wraga教授和Peter Hlebowitsh教授、北佛罗里达大学的Jon Wiles教授曾对我研究博比特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学友王慧敏博士、蒋佳博士和孙雅望研究员曾在美国为我找到许多博比特相关资料。教育科学出版社的刘明堂主任和翁绮睿编辑尤其为此书的出版付出了巨大的辛劳。
最后,我想借这个机会感谢已经永远离开我们的教育学大家黄济先生。黄先生曾告诉我,他早年念书的时候就读过博比特的民国译本,因此非常关心我这个新译本,还兴致盎然地为这本书题签。当日的情景,我还历历在目。现在,因为这本书有幸被收入“世界教育思想文库”,黄先生的题签就不方便单独使用了。但更令我感到遗憾的是,在我求学东瀛的第一年里,就传来了黄先生因病辞世的消息。如今书出来了,我却没法履约为黄先生寄去一本,这让我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遗憾。
有人讲,翻译注定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因为完美无缺的翻译从来都不存在。我的译作亦是如此,如果译本中有任何疏漏之处,还请各位读者朋友多多批评指正。
刘幸
2016年10月18日
于日本广岛大学
黄济先生题签,虽然最终没有印在书的封面上,却印在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