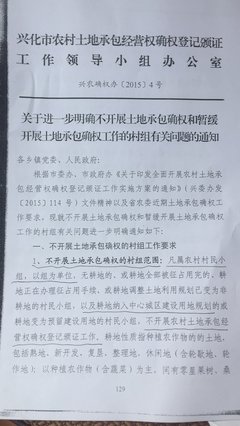
有一年,我度假回家省亲,久住了一段时间。
“哎呦哟,你看看,你还没咋见到太阳就已湿成这样,这可咋办?”
我看母亲有疼爱之色便打起哈哈笑道
母亲实属见不曩昔,默不作声径自便向中堂走去。
停稀有刻,母亲便仓促端出一盘整齐的西瓜送进我屋。
我见罢,急速动身接过笑道
“咋还亲身上阵了呢?”
母亲见我如小时般狡猾便摆出一副冰脸说道
“越大越不正经和小时候咋还多出这般狡猾话?吃点西瓜堵堵嘴!”
我看着母亲说出这般言语,便也笑了笑,拿起西瓜便咬了一口。
母亲见我写作便也没有怎样打扰,看了看便离去了我的“书房”……
午过三时左右,太阳正值热腾时期。
我久坐不安便抱怨起这般如火的气候,写写停停不时想不出如下体裁。
久罢,倾听家饲普犬有吠鸣之声,紧接着便听母亲从中堂走出来的动静,刚一出门便听母亲如春雷般的动静叫道
“哟,这不是他二婶吗?大中午的您咋过了来?”
只听回复动静细如蚊翅喏喏应道
“这不是出了档子事,串串门、散散心!”
此刻我已无心写作便推开门走了出去,我端视眼前妇人有三十左右,一米六三的个子,步入中年却不见得怎样发福,白脂的皮肤,细长的大腿、鹅蛋脸,如不是出在我家院子又怎能瞧出这是村庄的人?
白丝衫的蝙蝠装修搭配在两肩,米黑色长裤紧紧包含她那圆实凸翘的臀部。
妇人见我走出了房门便客套的讲道
“这是你家二份吧?长得真俊!还没有成家吧?”
我听罢早已羞涩两颊,时问也不见得啥词能推脱曩昔。
这时母亲笑道
“可不?刚来,上学纯属了傻子,这媳妇也不见得怎样上心?他二婶来,屋里凉爽,啥事进屋再说!”
妇人听后客套的讲道
“你家二份这么好,还怕娶不到媳妇咋地?”
说完整个脚步已迈进了中堂,目睹妇人此般言语,整个身心显得愈加炎热千般,在门口站了站又回了去“书房”。
所谓的“书房”只不过是西侧的一间偏房,我故称“书房”全因整间舍间都是我从入学到结业的书本罢了,满满的书本硬硬的塞满了各个死角。在我书桌墙体的一 侧就是中堂,仅一墙之差,隔音作用不见得怎样良好。起耳初听就是母亲操忙之声,杂乱无序。妇人也许见母亲忙合不来便开口道
“嫂子,别忙了。我坐坐便回去了,不必这般服侍,我又不是啥外人?”
母亲便笑笑显得分外动静
“他二婶虽说不是外人,来一次也不容易,至少喝点水、吃点西瓜聊聊天。”
妇人笑笑便没有作声。
停稀有刻母亲也安静了下来,嘤嘤就是母亲和妇人的对话
“他二婶这中午咋来了?是不是有啥事?”
妇人支支吾吾半天才开口道
“这…这不是家里出了点事,头几天俺当家的外出遭了事故,整个下小腿全折了去。现在还躺在医院不省人事。”
母亲听罢好久才轻轻叹出一气道
“哎呦哟,瞧瞧这是啥子事?咋还摊上这事了呢?”
“可不!这事真让人头疼,现在都不知道咋办好了?”
“瞧瞧这事闹的,那他二叔在医院几天了?”
只听妇人叹了一口气无奈的说道
“都五天了,光是医疗费现在都十多万了,再这样下来可咋办?”
说完便隐约听到妇人隐泣的动静,母亲听罢也不见得表啥心情,劝了劝几句就是母亲在房间里走动的动静。稍后就是母亲的动静
“他二婶谁家都有点难出,俗话说天灾、人祸咱顶不过,已然工作出来了也没啥好办法?这院咱还得住,俺家您也知道啥状况?这三千元您先拿去,不行?您在来届时侯我让华他爸在帮您借点!”
妇人听后更是激动的讲不出啥,只听隐约的哭声之外就是结巴的言词
“这…这…嫂子,这……”
“好啦,你就别说啥了。俺知道这点钱也帮不了啥忙,您先拿着!”
妇人嘤嘤哭诉起来。
听罢,过了好久妇人才稳定下来心情便向母亲苦诉这悲苦、茶凉的人生,母亲依坐一旁也仅仅唏嘘叹气,帮衬着烘托这悲愤般人情油滑。大约在四点左右妇人才慢慢走出中堂,母亲跟从其后把妇人送出了门外……
母亲一回家便向我屋走来,絮唠叨叨讲诉了许多这人生无常、冷暖茶凉的悲情油滑,要点仍是替妇人抱抱不平。
我听罢母亲言语之间已无言笑之说,便也安安静静听诉母亲的这番人生哲理。
听母亲说来这妇人仍是一个命苦的主儿,妇人是二次入门,入门不过三个年初就摊上这事。母亲唏嘘叹气之间便也讲不出个啥,临行还说了一句
“这命,哎……”
晚上,天色已尽星斗,父亲才从村部回来。饭间,母亲便把此事与父亲讲了一番,父亲听罢甚是惊奇急速问道
“咱家还有多少积储?你给了三千能做啥?人家顶晒跑来咱家,陌生人若不是转的久了,也不会来咱家?你再拿点,我给她送去就是!”
母亲诺诺不语,久罢才应和附道
“咱家你不是不清楚,老大双子接户口用去两万多,您这二小刚结业您又打理关系用去了三万多,就您在村上的那点钱,积储还存了啥?一大家子的生活还要过吧?这钱……”
父亲听后显得反常消沉,猛地喝了一口酒便没有说话,吃了几口菜便站了起来。母亲见状急速问道
“您这是做啥?”
父亲瞪了母亲一眼
“去找徐老三……”
说完父亲便夺门而去,母亲忙起看着父亲的背影紧紧地“哎”了两声,随后就是母亲唠叨的动静
“你爸就是这样,一辈子的操心命…”
说完叹了一口气,坐了下来……
父亲几时回来我便不知晓事,因为气候炎热、无心写作便也早早睡去。
清晨朦出,院子吠犬之声喧嚷甚急。
“哎,老徐你咋来了?”
徐书记不急不躁慢慢的说道
“我找你参议点事。”
父亲应和道
“来,来!啥事屋里说。”
我听罢羞于见人便缩到了内屋。
犬吠声此刻叫的甚欢,父亲吼了两声,此刻犬吠之声才逐渐小了许多。
稍后就是火机冲击的动静,之后徐书记慢慢的讲道
“昨日你讲的那件事我想了一晚,身为村委干部本应是该多多协助,但是你又不是不知道?前天乡长来,光是吃饭就花去了三千多,临行咱们又悄悄塞了两万多,现在村里这点公费剩下的也是屈指可数,要是再从村委开销我怕…”
父亲接过
“怕啥?有啥怕的?现在救人要紧!”
“哎,这事我也理解,眼看县长又要来了,届时…”
父亲一听县长忍不住叹了一口气深重的讲道
“老徐照你说咋办?”
徐书记停稀有秒说道
“这…这…我也不知道哎!要不这样届时咱们给村里的小队开个例会让村上按人头捐点?”
父亲想了一会回道
“我看使不得,咱村是有啥人你不是不清楚?发钱还好,你要是一提拿钱不巴结,村上的某些人还不在背面骂死咱们?”
徐书记叹了一口气
“要不你说咋办?”
父亲听后便没有说话,徐书记见状也使不得啥法子嘤嘤几句便推塞了曩昔。
此事便也不再参议。
之后满是评“村庄四五”的工作参议起来。
我见此事甚是无聊便在床头,取来一本书看了起来……
后来接连几天也不见得此事有什么解决方法?逐渐我也忘了,直至记不起来。
度假期限到了,我便买了去济南的车票。
临行我又听母亲唠叨说什么妇人也去了济南,传闻是老公病得凶猛就转了曩昔。
济南医院甚多,坐车简直百米便可见得一处医院,看着这般许多的医院也不晓得妇人住了哪家医院,想寻也可贵寻去…
也许真应允了一句惯例俗话:说天大,不大也大,说天小不小也小。
来济南几十日,因为气候改变毫无惯例,我呢不甚染上了一丝风寒,甚是难过。
便趁临休之时去了**医院,暂时挂单之时便见的了妇人,妇人看去瘦了许多,皮肤渐近蜡黄,眼带黑而浮肿,看去也知妇人最近吃的不少苦处。
我走去叫道
“二婶!”
妇人回头看了我一番惊道
“哟!这不是姜家老二吗?你这是咋了?”
我笑笑便把伤风之事讲了一番,妇人听罢也是破旧了一阵便叮咛我身体保养之类的言语。
偶见妇人在说话之间总是时不时向验血科瞄上一瞄看样子恰似有急事一般。
我便开口说道
“二婶,二叔也在这家医院吗?”
妇人笑笑说道
“不,他在历城**医院,我今来有点事便转了来看看!”
我哦了一声便也不再诘问。
这时在验血科门口一位护理喊道
“26号”
妇人听后摊开手中现已揉成一团的机打印数字昂首又看了看我抱歉的说道
“不好意思,我先去去。”
我看着妇人嗯了一声,妇人便与我擦身过了去。
过了好久,我才听到我的号码,我跟从护理走过了去。
走廊内,我经不起猎奇的问道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刚刚那验血科是啥意思?”
护理看了我一眼
“验血和卖血呗!”
我听后脑袋“嗡”的一响不经意的自语道
“卖血?!”
护理白了我一眼
“卖血咋了?这不是很正常吗?!”
我得知失了态便紧张的应说道
“没…没事!”
说完便跟从护理而去……
从医院出来,心里分外沉重。
脑海中满是妇人憔悴的面孔,想想心里很是难过,昂首看了看天色叹了一口气。怪恨自己也帮上啥忙,想想便也作罢。跟着时间推移此事便也逐渐放了下来。
临年公司年休,我便又回家搁置。
期间除了写作便也无事。
年二七我又见得了妇人,妇人看似漂亮了许多,尼格棕色风衣,一头褐色波浪似的发髻,白脂脸蛋看似上了一些淡粉,看去年青、神韵不少。
走曩昔便唠嗑了几句,话间听的口气变得自傲不少,笑脸也不见得那么愁容。
随意聊聊我便回到家中。
唠嗑之时我便向母亲提起了此事,语罢,看去母亲不是怎样高兴,板着脸一副冷态。我问起原因,谁知母亲哼了一声
“提她做啥?”
“为什么?”
我疑问的看着母亲,母亲看了我一眼冷冷的抛下一句
“小孩子问这么多做啥?”
说罢便不再理我,径自朝中堂走去……
一次,我与朋友聚餐之时偶然提起此事,谁知期间都中止了下来,不再说话。
我见其友都不是多愿提起这妇人,便也无心再提此事,便转了论题。
后来我才逐渐知晓
自从前次济南**医院离别今后,妇人已无心再去接受这般高额的医疗费。
某日午夜,妇人服侍完老公便下去转了转。
忧心、忧虑烦闷妇人想想此般境况便也逐渐饮泣起来,就在哭泣之时从一家理发店里走出一位年约四十左右的老妇拉住了妇人。
老妇热心的把妇人让进了店里,唠嗑之余老妇得知了妇人之事。
怜惜之间老妇便也撮合起妇人做一些不正当的生意。
妇人初听便想起步离去,甚是愤恨。
就在愤恨之余便见老妇随身掏出三万元猛地排在了桌子上,好言相引,说长说短。
妇人见那红红的纸币登时也起了贪心,加以老妇的蛊惑。
妇人抵抗不了引诱便也赞同了此事。
一连几个月,妇人把老公服侍结束,便在午夜之前来到店里上班。
逐渐生意好了,口袋里也逐渐敦实起来。
老公问其原因,妇人总是笑笑推塞曩昔,说什么在一家午夜餐厅上班,待遇甚好。
逐渐其夫也不再多问。
后来有人进城便在暗处见得了妇人,妇人不晓此事便过了去。
此人回村今后便四略讲起了此事。
起初谁也不怎样信,久经言传多了、此事便也成了真。
此事不甚被徐书记听了去,徐书记本是老封建一个,一听此事这还了得,连夜便去了济南。
时之不运,妇人被逮了一个正着,传闻妇人躺在三尺板床上叫的正欢呢?
妇人见得夺门而入的徐书记当时脸都吓的绿了,连跪带哭的徐书记才肯罢休而去。
临走徐书记还说了一句
“你仅仅做啥?真是作践、造孽!”
妇人哭哭啼啼便也答应下来,不在做这档子生意,此事便也压了下来。
事后妇人也没有再去上班,但时隔多日妇人不知为啥又去了那里?
此去风声不知又是谁传使出来。
传闻徐书记为了此事也去过几次。
恰似妇人皮脂厚了不少,见得徐书记也不再逃避、哭泣,时而略带有豪放,竟当着徐书记的面儿做起了那事。
徐书记气不过来便仰头回了来,再也没有问津此事……
妇人此事传了起来,但见妇人对此并无羞涩之心。
时不时穿戴花枝招摇街头,活的甚是快活。
此般作态更是让人作呕,逐渐便无人传颂此妇,只要提起此妇便讨厌极致,甚至烦恶……
还有一事更是荒诞。
前次县长来访,不甚见得了妇人,说甚也让妇人坐来陪酒,其间还大肆赞扬此妇先明、敞开、21世纪的女人模范、村庄的前驱。
酒国三巡,传闻妇人还随县长去了,做了啥?便也无人知晓。
但听徐书记说什么县长拉去妇人,代表村委前去开了一个例会。
此话骗傻子一般,常人谁不知做了甚?碍于徐书记的体面不便揭穿就是……
一春节我便坐车回到了济南,期间偶然我又遇到了妇人,随意聊聊几句便不再言词,一直顶达济南车站。
大约三年前,我听母亲说道妇人得了一种怪病,浑身起了很多的浮水小泡,看样是奇痒难忍,不时起有的血泡都被扯起了皮,白森森的脓疱顺着皮郛印染了一地,时不时还伴有血沥从干咳中带出,医院看罢也是无处上心。
此病一出三个月人便独自离了去,其夫还为此痛哭了几天。
前丑恶事便向人相同逐渐从村里散了去,再也无人提起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