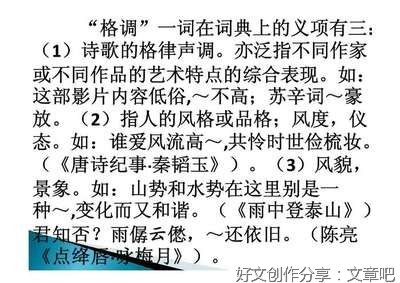
爷爷喜欢侍弄花草,尤爱文竹,那小小的一盆青绿,旁逸斜出,在被埋没在姹紫嫣红中,平静而又坚忍。
爷爷退休后没有什么事做,不会抽烟也不会喝酒,会打点麻将,也会下下象棋,每天下午四点准时去街上围观别人博弈,六点乐呵呵地回来,手里拿着两袋子菜,奶奶发怒他也不生气,麻利地把菜做好,然后平静地扯开晚餐的话题。
我知道爷爷不是本地人,还在我没上幼儿园的时候,他会跟我聊许多有意思的事情,像小时候上山砍柴抓到一窝野鸡,回家放到炕上,居然全都跑了;外出的时候遇到狼,心惊胆战,那狼竟跟着前面一个挑担子的走了。半夜里路过坟地,看到鬼火跟着自己跑。我屡屡冒出想上山砍柴的想法,爷爷总是笑着说:“你可不知道那有多累啊。”我是没有砍过柴,只是听爷爷说的,一脸轻松,我便也当它是件轻松愉快的事了。
我也好奇,远在北方的爷爷怎么会到这里来,爷爷也只是笑而不语:“有些事情小孩子不知道的好。”然后给我讲些部队里的故事,打狍子,炸鱼,作报告。我问他:“部队好吗?”爷爷总是一脸肯定:“那当然好,我们的部队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然后絮絮叨叨地讲一些或是惊险或是平淡的部队故事,有时会唱一首朝鲜民歌,悠扬又凄凉,据说内容是表现朝鲜人民找到野菜时的欣喜。一次看电视时看到了有人在唱这首歌,画着浓妆,载歌载舞,一样的曲调,似乎少了些什么。
有时候爷爷不在家,我奶奶和我一起聊天,奶奶偶尔会提及那些往事:“要是你爷爷那时候不说错话,不那么犟……但那样我也见不到他了。”我逐渐长大,也懂得了一些历史,我的语言充斥着批判,我不明白爷爷为什么要以那样一种心境去回顾那段历史,我有时候很愤怒,但爷爷只是安静地侍弄花草,阳光斑斑驳驳,撒在花草上,撒在爷爷的身上。
有次看到爷爷坐在阳台上不知写点什么,我好奇,于是缠着爷爷去给我做蛋饼,爷爷一离身去厨房,我就悄悄打开那个本子,随手翻到中间,这本子看来有些年头了,红面子,铅印的字体,里面还有几张港台的风景照片,我随手翻到一页,似乎是在讲爷爷被开除党籍后的愤怒与哀伤,右边是一页香港的照片,城市的绮丽风光,好不迷人,又翻过这页,看到爷爷在背面写着:共产主义是我永远的信仰。
我不禁抬头看桌上的那盆文竹,它无花无果,无论那百花斗艳,它都坚守绿这一种颜色;它平静而又坚忍,一如爷爷生命的格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