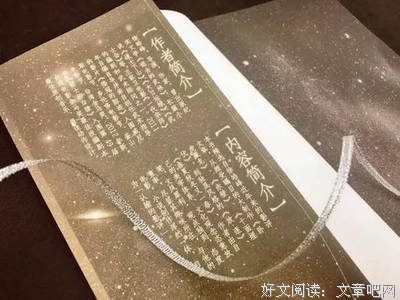
《玩笑》是一部由亚罗米尔·伊雷什执导,约瑟夫·索姆尔 / Jana Dítetová / Ludek Munzar主演的一部剧情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影评,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玩笑》影评(一):玩笑
因为看过kundera的同名小说,所以才很容易看懂这个叙述的方式不一般化的电影。影片在摩拉维亚传统庆典的欢乐中,插叙ludvik早年饱受政治运动折磨的生活。在那种情形下,生命不过是对自身开的一个玩笑。
这是最近看过的最喜欢的电影。共产主义毒害了整个世界。无辜者成为这个政党合法的玩笑。有些人至死抱着对党的忠诚与信念,可在党眼里,他连条狗也不如。有些混蛋,利用体制混到如鱼得水。害了别人觉得是理所当然,没有丝毫忏悔之心。把别人的生命和青春当作一个廉价的卑微又凄掺的玩笑。
《玩笑》影评(三):“玩笑”的影像表达
1969年,经昆德拉亲自改编,由捷克新浪潮导演亚罗米尔·伊雷什执导,电影《玩笑》最终上映。二十多年后,米兰·昆德拉在给1991年版《玩笑》所作序言中表示:“我仍然认为那是一部出色的影片,没有过时感。”
“玩笑”透露了米兰·昆德拉对人性、社会与历史不确定性的认知。而这种深彻的不确定最终构造了如“玩笑”般荒诞而又尖刻的现实。人永远被抛掷于如此的现实之中,“玩笑”因而颇具幽暗的宿命意味。
《玩笑》影评(四):无望的复仇
“乐观主义是人民的精神鸦片,精神健康是冒傻气”,这是卢德维克写给玛盖达的信中的玩笑话语。而玛盖达这个“正能量”,“单纯”,“听话”,一心跟着党走的漂亮女孩却将这个玩笑反弹给了卢德维克,并且毁掉了卢德维克的人生。在玛盖达眼里,这是正义,这是身处天堂需要遵守的准则,是替天行道,大义灭亲之举,是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天赋权利,举报揭发一切心术不正的害群之马,抹除一切邪恶思想,让空气中飘荡正能量鸡汤的味道……这里不得不提到库斯图里卡的经典之作《爸爸出差去》,《爸爸出差去》里的父亲因为情人将自己对领导人的玩笑话告诉了身为警察的小舅子,从而导致了自己被流放和迫害的人生。而本片中的卢德维克同样受到了制裁和迫害,就像某国的某某大革命一样,接受批斗,面对法庭审判,恋人变成了给自己定罪的证人,遭到迫害,强制服役,面对军营里的暴力和强制洗脑,消解个性,同化思想,被无情的加工成符合国家机器运转的零部件。一切都是这么似曾相识,又无能为力,就连最后的复仇都绵软而无望。失去的人生无法弥补,这是唯一的悲剧。
《玩笑》影评(五):历史总是喜欢开怀大笑的
受到乌托邦声音的迷惑,他们拚命挤进天堂的大门,但当大门在身后砰然关上时,他们却发现自己是在地狱里。这样的时刻使我感到,历史总是喜欢开怀大笑的。 ——米兰·昆德拉 这一次,我发现自己也跌落在同一个“历史的玩笑”之中的时候,已经可以开怀大笑了,十分庆幸——1979 年,中国官方否定文革。感恩那些打开地狱之门的人。
米兰·昆德拉同名小说改编的捷克电影《玩笑》,说的是“捷克版文革”中的平常事。亲历过文革或对文革有一定了解的人,对这样的故事绝不会感到陌生,不了解文革的人,如有兴趣了解,最好的方式是尽快去一趟朝鲜游。
公元 1969 年,电影《玩笑》在捷克推出,人家已经开始对乌托邦进行反思了,而我们却正在牵起乌托邦的新高潮。好在 10 年之后,我们突然惊醒。只可惜乌托邦的阴魂未能散尽,今年初的重庆事件若非意外曝光,我们是否再“玩”或者“被玩”一次可就难说了。
东望“三金”领导下的朝鲜人民,却难笑得起来。但愿他们很快也能看到《玩笑》这部电影。
2012.7.25 http://william-ho.lofter.com/post/6c3aa_12bced74d
《玩笑》影评(六):多么冷、多么寒、多么静、多么孤独的未遂的复仇
电影和小说之间的差别,在此不是要讨论的问题。小说的文体和语言的风格,其实对于中译本来说总是隔靴搔痒地在被谈论。我们可以关注的最应该是故事和人物,在大时代思想意识形态下被牺牲的个体。
我想应该从电影的角度谈论这部电影。
它最惹人瞩目的地方是:交叉行进的回忆和现实,天衣无缝地将命运中的转折点(痛苦、悲凉、无法抵抗。。。)和现实状态下的幸福生活(同样还有幸福中的荒谬、同样无法抵抗)接在一起。剪辑做得精练而优雅,寓意丰富但又不那么教条。我个人非常喜欢,尤其在音乐和主人公惆怅的表情、军营生活的片断相交进行的时候,你恍如站在了人物的内心,看到命运如何一幕一幕地剥开来,人生中的配角倚仗着庞大的政治舞台而将你自己(这个人生和命运的主角)消灭了,随之奉送而来的只是无理由的折磨、你变成了和国家机器打交道的无名螺丝。
这种剪辑手法当然很多电影都有用过。但这部电影里,年轻时代的回忆片断却采用了主观镜头的手法,人物在镜头背后说话,令一切“回忆”更加逼真。欣赏。
我在网上找到如下的评论——
按照好莱坞的电影叙事法,《玩笑》是再好也不过的一个“复仇”故事。一个被明信片上的玩笑话毁灭全部生活的人,在经历了漫长的15年等待之后,开始了他的的复仇。故事充满了传奇,性与暴力。而按照苏联老大哥的蒙太奇电影叙事理论,电影应该赋予深刻的教育意义,其中蕴涵着铁定的真理和强烈的爱憎,不可逾越地道德,它不仅仅影响着同时代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电影面貌,也在试图塑造捷克电影的形象和面貌。不过,这个时刻,至少在1968年春天的布拉格,捷克电影却在孕育着自己的“新浪潮”。
但事实上,我觉得即便故事结构是复仇式的,但电影本身更要从这简单的“复仇”心理出发,到达一种无奈。正如电影最后一句所言,“我要打的并不是你”,复仇的对象和途径最终被证明是徒劳的。这比15年的迫害更让卢德维克无从适应。
电影本身的画面感也很精辟。和我们当今所信奉的小资旅游胜地的“捷克”和“布拉格”是完全不同的映象。
电影一开头所展现的静物,传统,死板,有趣,机械,实体。犹如电车到达后的那个场景:广场的地砖细密而整洁,但留白太多,会让人无来由地感到冷漠。遥远。
中国也有很多批判文化革命的电影。但从温情的角度说,都有过于煽情的嫌疑,尤其与这部《玩笑》相比。这是一种多么冷、多么寒、多么静、多么孤独的未遂的复仇啊。(可笑的是,网上还有文章说,这部电影里容纳了暴力和性和政治,真是让人受不了。)
:以下是一些相关的网文摘录。
--捷克电影的新浪潮当中,涌现了米洛斯-福尔曼、伊日-门泽尔、贾洛米尔-吉里斯等一大批直面捷克现实的青年导演(其中门泽尔的《紧密监视的列车》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这部影片是根据捷克的另一位杰出的作家赫拉把尔的小说改编),昆德拉既是他们的导师,也是他们的合作者。米洛斯-福尔曼后来到了美国之后拍摄了《飞越疯人院》,这部影片对专制与暴力的表现震动了整个世界。当然,这个时候的米洛斯-福尔曼已经不仅仅是要呈现捷克人民的心灵创伤了,他要表达的是对以任何形式出现的暴力的抵制。
--从一九六二年起,昆德拉着手创作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玩笑》。它给我们描述了卢德维克这样一位富有朝气的大学生,他极有思想和个性,只是平时爱开玩笑。玛盖达则是个热情活泼但事事较真的女孩,这使她与时代精神天然地吻合。卢德维克在寄给玛盖达的一张明信片上写了几句玩笑话,竟引发出一连串的灾难,完全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正因为这些灾难来自机制,来自社会和时代,个人毫无抵抗的能力,甚至连复仇都会走向它的反面。因此,笑背后的含义就达到了恐怖的程度。
《玩笑》出版后,引起了巨大反响,连出三版,印数惊人,达到几十万册,仍很快被抢购一空。
不久之后,《玩笑》还被拍成了电影。几乎在一夜间,昆德拉成为了捷克最走红的作家。他在捷克文坛上的重要地位也从此确定。人们认为,小说说出了许多人想说而不敢说的真实。不仅如此,《玩笑》很快便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注意,被译成了法语、英语、日语等几十种语言,为昆德拉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
一九六八年八月,苏联军队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玩笑》被列为禁书,立即从书店和图书馆消失。在东欧国家,除去波兰和南斯拉夫,它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全部匈牙利版的《玩笑》还没进入书店,就被捣成了纸浆。
然而,著名的法国作家路易·阿拉贡为该小说的法文版写了前言。他称《玩笑》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小说之一。
对于昆德拉而言,阿拉贡的赞美到最后又成为一种尴尬。原因就在于阿拉贡本人。昆德拉清楚地记得,一九六八年秋天,他在巴黎逗留期间,曾去拜访过阿拉贡。当时,这位法国大作家正在接待两个来自莫斯科的客人。他们竭力劝说他继续保持同苏联的关系。阿拉贡对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断然告诉他们,他再也不会踏上俄国的土地了。“即使我本人想去,我的双腿也不会同意的。”阿拉贡说。在场的昆德拉对他极为敬佩。没想到,四年后,阿拉贡就去莫斯科接受了勃列日涅夫颁发的勋章。这仿佛又是一个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