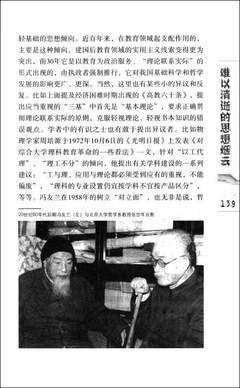
《中国哲学史》是一本由冯友兰著作,古吴轩出版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38.00,页数:84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哲学史》读后感(一):东哲西哲,道术未裂 我读《中国哲学史》
本书第一部与其说名为《中国哲学史》,不如改为《轴心时代哲学史》为佳,因为每一提到中国轴心时代某一哲学家总会用比较文学的方法与西方轴心时代的哲学家进行对比。比如《列子》篇时,冯先生会以西方轴心时代的伊壁鸠鲁为例,说明其相似之处及相异之处,认为二者以同一前提得同一断案,这涉及到比较哲学的范围了。所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是也。
冯先生的哲学之方法,乃是比较新鲜的,学者普遍认为哲学是逻辑与理性的,而冯先生却认为哲学是直觉与反理智的,而科学才是逻辑与理智的。其中大有道理,他指的是用直觉与反理智的方法得来的道理,用理性而严刻的理智态度表达出来才是哲学,比如佛家的最高境界是不可说的,然而在“不可说”的时候仍然不是哲学,须得在得到神秘体验后,用判断与证明成立一个道理之后,哲学方才产生,而得出真理的方法与科学不同,表达方法则是相似的。而这也是哲学家与普通人的区别所在,普通人凭直觉得出的道理放在心里,不会诉诸文字,变成理论,而哲学家得来的道理是必以论证证明其成立以后,方才成为一种学说或理论传之后世。
冯先生这本书的写作方法,从后文进一步看出是一种比较哲学的方法,他在第一章第五部分进一步论证了与西洋哲学相比,中国哲学的弱点在于其功利性,从未有为了哲学而哲学,为了知识而知识的哲学家,都是为了某种目的,比如为了幸福,故而中国人不重视著书立说,中国哲学家讲的多是内圣外王之道,是为了立德和立功的目的,而视著书立说为不得已而为之之事,这也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遗憾,哲学史中精心结撰的哲学书比较少,多以语录体出现,成书也随便,孔子甚至不立言,这当然也与写书用的工具过于笨重有关系,但西方古时代也存在纸张的问题,然而古希腊轴心时代的著述已远超中国,冯先生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哲学家重人事,不重天马行空的宇宙之研究,而西方哲学于宇宙之学皆极发达,与中国哲学家注重“内圣”的修养方法有关,“道”应当如老庄所说在言说之外,然而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却必在语言文字之中,否则即不是哲学,这就把哲学的思维方法与研究方法说得很透彻了。
冯先生认为哲学缺少系统性是中西的共性,然而只指的是形式上的系统性,西方苏格拉底也不立言,而柏拉图的哲学也是以对话体写就,但并不能说形式上不成系统的哲学就不是系统的哲学,西哲到了亚里士多德就有了形式上的系统性,但中西方哲学仍然有着实质上的系统性,故冯先生写此哲学史的宗旨就在于从形式上无系统的哲学中找出实质的系统。
后文在论证董仲舒与王阳明的学说时,冯先生仍然不时插入亚里士多德的言论,认为潜能与现实之间是有着重要的区别的,其深意在于说明王阳明与董仲舒不过是拾人牙慧而已,其理论其时在轴心时代的儒家已经基本说尽,他们就只是引申和发挥而已。有了这个前提,后面自然以轴心时代(冯老称之为子学时代)为重心来讲述中国哲学了。并说明为何会在这个时代有这样发达的哲学的原因,引用了胡适的论证,即“政治那样黑暗,社会那样纷乱,贫富那样不均,民生那样困苦。有了这种形势,自然会生出种种思想的反动”。而冯先生称这样一个时代为大解放之时代,并从政治经济社会等角度分析了那样一个时代,比如商鞅变法,春秋大变动,到汉之中叶完成变革的数百年,中国社会进化的大过渡时期,旧制度礼崩乐坏,守旧者认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而主张复古守旧,孔子为拥护旧制度而给予理论上的依据,才有了儒家学说的“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然而根本原因在于当时思想言论之自由使其成为一大解放时代,一大过渡时代。此后的学术发展也因为秦的迅速灭亡而得以继续,由董仲舒终结了一个子学时代,开启了一个“独尊儒术”的经学时代。
《中国哲学史》读后感(二):三史释今古
冯友兰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史家和哲学家。“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是冯先生对他一生重要著述的归纳。所谓“三史”就是指他的《中国哲学史》(二卷本)、《中国哲学简史》(1946年至1947年间,冯先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其英文讲稿经整理出版而成《中国哲学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本)。“六书”是他在抗战期间的六部专著,《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和《新知言》,合称“贞元六书”,标志其“新理学”体系的确立。
他在20世纪三十年代所写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是第一部完整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在当时就被翻译成多国文字,成为世界多所大学的通用教材。因此,被时人誉为“当代中国哲学第一人”。
中国哲学史(全二册)典藏版|古吴轩出版社,2021冯友兰1915年考入北大,听胡适讲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听梁漱溟讲东方哲学。1919年考取了官派留学生资格,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导师杜威在给他的奖学金推荐信上写道:“这是一个真正学者的材料。”1923年,冯友兰完成了博士论文《天人损益论》,顺利毕业。回国后,接受了时任校长罗家伦的邀请,来到清华。
《中国哲学史》就是冯友兰先生于1928年到清华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期间所写。该书没有采取“信古”或“疑古”的态度,而是以“释古”的角度来写中国哲学史,把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两大阶段。冯友兰先生所著的《中国哲学史》不仅得到了当时陈寅恪、金岳霖这两位审阅人的高度评价,时至今日仍然备受赞赏。当代哲学家张世英就说:“《中国哲学史》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史论结合、有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的第一部哲学史著作……把史论结合得那么紧密,把中国哲学史讲得那么有条理、那么清晰,而且贯穿着自己的观点,不人云亦云,到现在还无人能及。”
形容一个人学问大,常说其“学贯中西”。但是,真正学贯中西的人并不多见。“现在经常说西化和传统文化,但能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对西方文化有透彻的理解,并把这二者融合起来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的人,在当代实在很少,冯先生是其中的佼佼者。”资中筠先生如是说。
记得周有光先生曾说,要从世界看中国。我想,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就是一部从世界哲学史看中国哲学史的例子。正因为有这样的视角,有这样的眼界,他写出来的东西才不一样。
比如,他对于中国人不大关心宗教是这么解释的:“对超乎现世的追求是人类先天的欲望之一,中国人并不是这条规律的例外。他们不大关心宗教,是因为他们极其关心哲学。他们不是宗教的,因为他们都是哲学的。他们在哲学里满足了他们对超乎现世的追求。”
冯先生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
学哲学的目的,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今天,我读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读的还不仅仅是他的观点,更主要的是领略他的视野。
读书的间隙,我突然想起一篇小波的文章《花剌子模信使问题》,“假设有真的学术和艺术存在的话,在人变得滑头时它会离人世远去,等到过了那一阵子,人们又可以把它召唤回来——此种事件叫做‘文艺复兴’。”
《中国哲学史》读后感(三):中国哲学,依然是学术的顶端与文明的肇始
1919年于中国文学史而言,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间节点,“新文化运动”成为文学的里程碑,而在哲学上,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这部书的价值自不必说,但只有上半部,却让当时的哲学史有了断层。之后的风起云涌让哲学史的这个断层迟迟没有接续上来,直到1934年冯友兰先生承前启后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出版,现代化的哲学研究方法才成功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这也奠定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基本框架,冯友兰版的《中国哲学史》在史料搜寻上更加详尽,在史证方法上也更系统,这一切成就了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在中国哲学史学上的奠基作用,即使如今已经出版近百年依然是读者了解中国哲学史最经典的著作,加之后续的《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成就为当时大家一致推崇,即便是陈寅恪、金岳霖、张东荪也对此书推崇备至。
读书的时候读的是《中国哲学简史》,那时候的冯友兰先生是帆,引领的是小舟远航,只是“简”之一字鼓荡起小舟远行,却还是无法乘风破浪,今天与这本足本的《中国哲学史》相遇,那就成了长风激荡,扬帆起航,让人对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虽然纵观全书,其实对于哲学,依然无法尽善尽美,但是已经让人有了开山取铜的美好感受了。当时与这套书相遇的时候,其实是被装潢吸引的,封面相当朴实,真正的白纸黑字俨然在目,宋体的中国哲学史五个大字非常醒目,匠心所在,其实在于设计,比如黑白二色的交错,如果你翻到侧面,就可以看到了,上下卷各自用黑白两色来对比,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在上下两册的内容里,还以黑白两种不同的颜色围绕成了一个太极的图形,“上”“下”两个字各自呈现出出黑白两种颜色交错其间。这样的设计极其富有中国风,十分古典且优雅,内容与表达上也显得特别精致,“太极”的两极圆环和旋转十分自然,看起来就是典型的中国风格。毫无疑问,深刻的书籍,配上深邃的图案,的确读来就让人深有感触。
读书的时候,恰逢窗外的小雨淅淅沥沥,春日的清凉和静谧的确适合以这样书籍来阅读,《中国哲学史》其实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一体,比如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所言,“如果我们以‘真理是永恒的‘为出发点,则真理就不会落到变化无常的范围,也就不会有历史。但是如果哲学有一个历史,而且这历史只是一系列过去了的知识形态的陈述,那末这历史里就不能够发现真理,因为真理并不是消逝了的东西。”我们应该要如何界定这个时期,那么仔细考量中国的文学、哲学和历史,你会发现一个很独特的问题,就像封面的内容设计一样——哲学还是历史?所以冯友兰先生做了一个全新的分析,以“子学”和“经学”来做分析,这样的时代其实是“子学历史时期的哲学”和“经学历史时期的哲学”的辨析,在中国子学时代的历史和文化中,孔子是所有文学之肇始,《淮南鸿烈》将子学时代做了一个完整的归纳;经学时代则是以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起点,最终在廖平地“经学五变”有了一个终点。所以冯友兰先生对哲学史的划分就非常具有中国特色,不再以“上古、中古、近古”的历史方式来划分,也不同于中国哲学“无近古”的划分,而是让中国的哲学研究因“其精神面目,实有卓绝显著的差异”,呈现为“皆装于古代哲学——大部分为经学——之旧瓶内”,历史与文学在这里交错,而且在时代意义上,切换了三百余年的“子学时代”,将历经千年的“经学时代”进一步细化而出,中国哲学的变化就在科学革命的驱动下,有了一个全新的定义。这样的切换,无疑是一个创举。
然而,中国哲学其实依然被“国之之器”的框架所约束,纵然时代已经让我们知道,地球确实是围绕着太阳转,也让我们知道,所有的哲学和思维其实很多时候需要屈从于科学,但是“显学”的思维和思考“头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准则”在《中国哲学史》的呈现依然非常明显,中国哲学史里对子学和经学的脉络划分,其实也正是以这样的思维来推动的。
那么,这本《中国哲学史》这种独特的划分方式为何成就了百年来最出色的哲学史书,也让同时代的哲学大家都为之倾倒呢?个人认为,首先被认可的其实是对历史规律和历史趋向的准确把握,纵观中国文化哲学的繁衍,我们可以看得出“统一”与“分立”的历史规律依然顺应在哲学领域中,几乎每一个哲学高峰时期都必然是一个历史“合流”的时期,冯友兰先生准确抓住了这一点,从战国末年的“道术一统”,到经学家活跃在历史时期的“百家合流”,子学与经学的第一次汇总,再到宋明以降的“三教合一”,朱熹与程颐程颢最终的“理学”,“合”与“分”在哲学支流中呈现得很清晰,所以承袭旧制来合乎时宜,选择一个“核心价值观”来通纳所有流派与学术分歧,这是高明之处。其次是与时俱进的时代思想,从论医者的“手足瘘痹为不仁”,奏乐者“靡靡然”的时代和“严肃”“端庄”“雅乐”的哲理时代,到避虚就实的“儒释道”三教的角力和理念的分歧,“ 外无内有,事皆唯识”,这种思想无疑是每一个时期都符合,但是又对时代进行准确扣合的切分方式,再如理学与心学之争,张轼说法,陆九渊、朱熹布道,“吾心即是真理”“个个都是圣人”在哲学时期的感悟,已经佛学的信仰和传入的理念延续,这些其实到最后都是期待,尤其是当下,民国时期对传统哲学的推翻和重建,冯友兰先生都存有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我们应该以怎样的哲理思维来面对当局,“贞下起元”为当下时局启端,“元亨利贞”般如环无端,循环往复才是常态,中国文化绵延五千年亦未断绝的根本因子,在这里的概括和叙述,相当让人信服。
当然,完美的书籍是不存在的,冯友兰先生学贯中西,尤其是对时局和新思想的衍射,很是让人赞赏其博文广识,而由此带来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西方哲学与东方哲学之间的天然界限被模糊了,西方哲人的思维来解释东方学说,毕竟彼此之间有着不同,而冯友兰总是套用西方哲学的思想来对比中国哲学,这样就难免有点不伦不类,即使用中国化的语言,依然显得有些别扭。再如冯友兰引经据典自然是毫无疑问,但是大段大段的原文加上个人的注解,甚至以个人评价来做一种汇总,大量的阅读原典自然是正道,只是掺杂在哲学史中,就很明显需要读者有一定句读、训诂、音韵基础,小学解读大经,哲学与思想就显得被掩盖了,这样其实更多的是学术著作,而少了一些人文气息了。当然,瑕不掩瑜,作为一本哲学基础书,依然值得当代人继续品读。
《中国哲学史》读后感(四):从中国哲学角度看国人的文化自觉
《中国哲学史》大概是我目前为止看过的书里面,最难啃的一本,无论是它长达八百页的厚度,还是它关于哲学的内涵,都决定了这本书读起来不会很容易。
再加上冯友兰先生在完成这本书时,旁征博引,将大量的史料原文直接呈现在书里,这对于我们读者而言,绝对算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同时如此大的信息量也让我们对先生的哲学储备叹为观止,要知道这本书不仅关于哲学,而且它还是“史”,是“中国哲学史”。这样一个玄妙而又全新的课题,到底能带给我们怎样的启发呢?
01.古代中国有哲学吗?
要想阐述中国哲学史,首先有一个问题不得不明,那就是中国有哲学吗?
哲学这个词当然是一个舶来品,起源于外国。那是不是意味着哲学也是外国所特有的呢?既然冯友兰先生能洋洋洒洒完成一本《中国哲学史》,那这本书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最好回答,古代中国当然是有哲学的。准确地说,早在哲学一词诞生之前,古代中国的先哲们就已经开始思考这一问题了。
这种情况并不罕见,文学也是如此,早在文字诞生之前,文学就已经产生了,无论是文字还是哲学,都只是一个人造的名词,而非思想的滥觞。
证实了古代中国是有哲学的,这本《中国哲学史》也算是师出有名了。但紧接着又有一个问题来了,那就是该怎么编写中国哲学史呢?古代先哲的哲学论调固然有之,然而那些历史史料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这给今人解读古代哲学增添了很大的难度,更遑论编写哲学史了。
抛开史料之外,还有一个难题困扰着企图编写中国哲学史的人们。那就是西学东渐的趋势。哲学一词起源于西方,而在近百年的时间里,西方哲学也一直被视为是哲学的中心。
因此在编写中国哲学史时,很容易会受到西方哲学的干扰,这样一来,所编写的未必就是客观的中国哲学史,很有可能就成了西方哲学之东方映射。
如果是这样,拿西方哲学思想在古代中国先哲思想中按图索骥的话,得到的结论恐怕会让中国哲学沦为西方哲学的附庸……
由此可见,想编写中国哲学史,实在困难重重。然而冯友兰先生的这本《中国哲学史》自出版以来就被奉为经典,至今依旧无可超越。因此即便它难懂,可只要得其皮毛,对于我们读者而言就已经受益匪浅了。
02.中国哲学史
既为中国哲学史,那显然不仅要紧扣哲学这一主题,同时还要以史的形式呈现出来。
《中国哲学史》基本按照中国古代社会的时间更迭顺序为轴,以此论述了各个时间节点,古代先哲(或称哲学家)们的哲学思想。
在本书的开头,冯友兰先生先以哲学这一西洋名词切入,阐述了哲学研究方法以及各种性质。同时还开门见山地指出了中国哲学的缺点:中国哲学家之哲学,在其论证及说明方面,比西洋及印度哲学家之哲学,大有逊色。但同时冯友兰先生也指出,此点亦由于中国哲学家之不为,非尽由于中国哲学家之不能。
在本书中,中国哲学史自孔子讲起,这并不是说在孔子以前,古代中国就没有哲学,而是孔子率先将哲学变成了一种有系统的思想。
自孔子始,诸位先秦思想家均有各自的哲学学说,因此均可以称之为哲学家。百家争鸣的局面见证了先秦文化之繁荣,同时也见证了先秦哲学之繁荣。
同时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也基本为之后历朝历代的哲学思想奠定了基调,此后的哲学家们即便有新的哲学学说,大多也都由先秦学说阐发而来。
或许我们也可以说,先秦时期是中国哲学史的开始,同时也是中国哲学史的高潮。为什么会导致这种局面呢?为什么之后历朝历代的哲学发展,都再也无法达到先秦时期那般发达呢?书里面给出的理由是“上古时代思想言论之自由”。自秦朝建立以后,历朝历代的哲学家们再也得不到像先秦那般思想言论自由的氛围了。
先秦时期,中国哲学史最为灿烂,儒家、道家、墨家、法家以及其他学派的学说中都包含有哲学的成分,它们与西方哲学有一些相似之处。比如孟子哲学中曾有关于人与宇宙关系的论述,透漏出神秘主义的倾向。
秦汉时期,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哲学史上的主流,这一时期中国哲学中的宇宙论开始有较完整的规模,《易传》及《淮南鸿烈》中所说是也。
秦汉之后,佛学以及道学的兴起将中国哲学带入了新的时代,八卦方位、阴阳之数、象数之学这些全新的概念也随之出现。这些在当今看来或许有迷信之嫌,然而很多科学就是在这些迷信中产生的。
南北朝之玄学,隋唐之佛学,宋明之道学以及明代之心学、清代之汉学,这些是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哲学史的多种表现形式。这些思想无论有无新见,均需依傍古代哲学家之名。
中国哲学史以清代作结,新时代的中国哲学还处于形成和创造之中,尚无卓然能自成一系统者,因此这本书以经学时代(董仲舒之后至清朝)之结束终焉。
03.国人的文化自觉
无论能不能具体看懂中国哲学史各个时期的哲学理论,读完《中国哲学史》之后,最起码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中国哲学思想的脉络和发展,而不是迷失在西学东渐的思想风暴之中。
诚然,即便我们明白中国哲学古已有之,思想文化并不逊色于西方哲学。但在当下,西方中心论依旧是多数人的共识,无论是在哲学领域还是在其他领域。对于这一问题,刘擎老师在新作《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中有详细的论述。
所谓西方中心论,指的是一种思想偏见,将西方历史视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高级阶段或标准模式,将西方的观念、理论以及价值看作优越和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知识。
这一论调是随着西方国家的崛起而兴起的,但同样随着中国的崛起,西方中心论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判,甚至这种批判在上世纪70年代就逐渐居于主流。
然而这种对于西方中心论的批判以及“中学西渐”的文化趋势容易让我们国人走入另一个误区,那就是“东方中心论”。
正如刘擎教授所说,“西方中心论”的谬误不在于“西方”,而在于“中心”,我们需要反对和批判的是一切形式的族群中心主义,从而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建立平等、尊重和相互学习的关系。
要想实现这一点,我们需要的是“文化自觉”精神。文化自觉的理论由费孝通先生提出: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它化。
费孝通先生认为,只有具备文化自觉的精神,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
冯友兰先生所著的《中国哲学史》就可以帮助我们国人进行一次哲学角度的文化自觉,借这本书,我们能明白中国哲学的来历、形成过程以及它发展的趋势。了解这些并非是复兴古代哲学,而是让我们正确地看待中国哲学以及西方哲学,从而摒弃中心论,能以一种平等、尊重的姿态接受不同的文化。
这一点适用于哲学方面,同样也适用于任何其他形式的文化和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