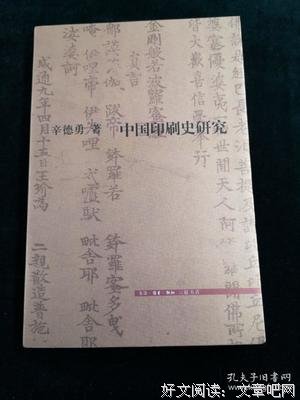
《中国印刷史研究》是一本由辛德勇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54.00,页数:39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印刷史研究》读后感(一):《河汾燕闲录》
重点关注辛神对明朝陆深《河汾燕闲录》中的这段话:“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此印书之始,又在冯瀛王先矣”。 曾经偶然听到过韩琦的讲座,在场的听众提到这段话时,他并没正面回答,只肯定了后半句,冯道用雕板刻书是无争议的。 潘吉星在其著作中有一句话:至迟在隋未唐初即世纪至7世纪之交(590-640)印刷术己在中国处于实用阶段。
《中国印刷史研究》读后感(二):一一垂“辩驳”
上篇从印刷术起源诸说中,一一整理厘清(吐槽)。 集中对唐贞观说、高宗说、武周说、玄宗开元说展开辨析与论述。爬梳古今中外文章著作,进行细致考据和合理推测。比如对《妙法莲华经》的断代、《阿毗达摩阿毗婆娑论》的译作时间与刻本真伪,以及韩国庆州佛国寺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的分析与推测等等,都可以说得上细致严谨。 中篇对于元白诗“模勒”一词进行解读,其应为摹写勾勒之意。更辨析了捺印技术与雕版印刷的本质区别,结合功利性的科举环境,推其无市场环境,十分合理到位。 下篇对于铜活字印刷的驳论,结合文献典籍、社会背景以及铜的物理属性与价值,作出了明代及以前无铜活字印书的推论。应大多以木活字为主,最多是“范铜为版,镂锡为字”的锡活字。 整体而言,对各个问题进行抽丝剥茧,论述有据。不少地方也显得有点啰嗦和颠三倒四,有越拉越长之感。(对潘、张、李的冷嘲热讽尤多哈哈哈)
《中国印刷史研究》读后感(三):吐槽的吐槽
页36 至于公元330年前后这个发明雕版印刷的时间,则很有可能是公元303年的误植,因为330年这个年份,没有任何标志性意义。 从前面论述所看,德拉克伯里所用文献到底是什么,作者也只是推测,然后他根据他的推测接着推测德拉克伯里提到的330年是303年的误植,简直没什么说服力。即使前面的推测都是对的,也不能因为无法解释330年就说其为303年之误。330和303混淆的可能性并不大。 页256 因为若是已经应用比这种捺印高明得多的雕版印刷,王玄策就没有必要不远千里从印度带回“佛印”了。 印度菩提寺主戒龙将四枚佛印作为礼物赠送给王玄策,不带回来难道扔了???“不远万里带回”和有没有雕版印刷不存在逻辑上的关联。页157提到“制作使用印章是婆罗门必备的几项技能之一”,可见佛印是印度佛教很典型的一种事物,所以拿来做礼物赠送给外国使者。 页284 雕版印经,可谓多快好省。 考虑人力、物力、财力么……普通百姓干不来啊……乐于和能于是两回事啊……而且真的不考虑宗教信仰问题么……结论太草率
《中国印刷史研究》读后感(四):小疑惑与小商榷
26,所引日文原文,汉字字体是楷体,日文字体是方正书版中的默认字体,完全不搭调嘛;三联底蕴那么厚,请教一下日本相关书籍编辑室的同事,完全可以选用一个日文字体的。
88,倒数第3行,“潘吉星的质疑初不足以动摇这一合理的认识”,“初不足以”这个短语,我才疏学浅,理解起来有点困难,不知道“初”字放在这里有何特别意义?
关于长孙皇后引文的括号注释,P118为“及(长孙皇后)大渐”,P133为“(长孙皇后)及大渐”,是否可以统一?还是说来源文献语境不同,括号注释的位置必须不同?
146,引文第7行末第8行始,“纸用写经故张,字样集字写经旧字”,说的是日人西村赝造中国古代刻本采用的具体手段,前一句是纸张选择,后一句是字形选择,看来看去,“字样集字”是否为“字样集自”之误?
151,第4行,引用李书华的说法,“此项记载曾于公元一九三〇年为中山久所引用”。对照上文,可知“中山久”是“中山久四郎”的缩略,李书华可能是想以姓指代全名,可是对日本人的姓名不熟悉,错将名字中的“久”字当成了姓。查维基百科“中山久四郎”词条(https://ja.wikipedia.org/wiki/%E4%B8%AD%E5%B1%B1%E4%B9%85%E5%9B%9B%E9%83%8E),日语发音为“なかやま きゅうしろう”,清楚显示“中山”为姓,“久四郎”为名。而且词条著录的中山氏著书中,与人合著一项有《世界印刷通史》,也不是李书华及本书所引“《世界印刷史》”。
152,第8行,“足已勘正清代中期自杭世骏以来的误读误判”,足已?足以?
192,第8行,提到日本孝谦天皇,因所叙史料发生于孝谦天皇“重祚”(即再即位)改称“称德天皇”的时期,因此行文中以“称德天皇”为主要主体。但是文中第一次出现“称德天皇”时配的括号内注释,可能不太妥当。原文如下:“称德女天皇(即所谓‘宝字称德孝谦皇帝’,又称孝谦天皇)”。商榷如下:(1)按日本习惯,正式文书中是不写明“女天皇”的,直接以“天皇”称之,最多称“女帝”。(2)在提及孝谦天皇时,以“孝谦天皇”为主体的时候居多,每提及“称德天皇”,多说明为“孝谦重祚”,文中“又称孝谦天皇”,“又称”二字相当不妥,给人感觉“孝谦天皇”是一个比“宝字称德孝谦皇帝”更不常用的别名,不如直接注释为“为孝谦天皇重祚”。另外,称德天皇驾崩,是在神护景云四年八月,而非文中所称神护景云四年四月。
311,提到韩国庆州佛国寺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及对其刊印年代的推测(704—751年),但前文中对这一内容进行了深入分析,作者并不认同这个结论。由于这部分内容所在的论文,其撰写早于前文的内容,可以认为是作者对该问题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但还是在此处做一些注释为好,以提醒读者注意本书前后对同一问题的不同态度。
《中国印刷史研究》读后感(五):怎么像辛先生一样写本印刷史
关于印刷起源的研究,前人依据的材料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是传世文献中可能涉及到“印刷“行为的记载。另一方面则是韩国、日本、中国三地近代以来发现的疑似唐开元之前印刷品材料。辛先生这本书三分之二的内容可视为对前人印刷史研究的“纠谬”。因此,对于第一方面传世文献的记载,辛先生纠谬的手法大概可归为三板斧: 1,史料学手法。这一步也就是先打一招虚的,即通过后代人对该书的评价说明该书史料价值有问题、或是通过作者的序言说明该书有民族主义或者经世致用等情结,由此证明其有关印刷记载的论断不足为资。也就是从史料本身的形成上把史料给彻底揭底。具体操作,辛先生主要是取用清代学者乃至现代学者对其批判史料记载书籍的看法,或者是征引这本书的序言、作者墓志铭、后人编的自传,总之,就是一切有关作者身处行事的材料。因为除非是清代考据学者,一般没人会去在这种地方论证其人写作如何严谨仔细,而都是偏向于颂扬该人如何经世致用,因为古代评价良史的标准都是以二司马乃至孔子修春秋作为标准,这自然是不符合现代实证主义的,所以越是搜集这样的材料,辛先生就越能说明这本书不以严谨考据为主,有删削的可能,不足为征也就成立了。比如在批判唐太宗时期已经有印刷,前人证据之一是有关清代郑机《师竹斋》转引《宏简录》记载唐太宗把长孙皇后撰的《女则》十篇“令梓行之”的这条史料,辛先生先不去说材料内容的问题,先打他的史料学,分析这个清代三流学者郑机的生平,说他并没有考据学养,只是三家村塾师,水平很次,而且有改书的前科,再加上前人对其评点,就先把这个史料陷入一种伪证的境地。这种论证的内涵,反倒有点像刑事犯罪审查前,往往先流出贪腐者的艳照,形象先抹黑,营造一种氛围。 2,史源学手法。在评点一个说法谬误时,辛先生不是直接列出这儿方法本身的问题。而是先列出一个说法的比较晚的记载,再不断逆向呈现传抄过程。比如同样是上面那份唐太宗把长孙皇后撰的《女则》“令梓行之”的这条史料,其实按照研究生博士生的做法,绝对不会去绕,很直接,因为这份材料是清人记载的,书没名气,一看就是转引,因此经训练的学生第一时间便知道要去查它的史源,直接在数据库搜“女则十篇”四个字,搜出来的结果很简单,一共就22条,前两条就是《贞观政要》和《新唐书》,直接对比就能看出显然郑机损益的痕迹。然而,辛先生在讨论这个案子却不是如此,他从117页切入这个事儿,直到p133页才引到这个核心环节。总共整整十六页就是绕弯子,他明白知道《弘简录》的史源是《新唐书·后妃传》,本来就是黑这种说法,却非把后来误信这种说法的人也拉出来,甚至把一些《华中师院学报》、《宁夏图书馆通讯》、上海新四君历史研究会印刷分会编的书,这种级别期刊的文章也拉出来骂一骂,就因为这些不知名的学者也引用过他反对的张秀民的说法。这似乎就有点琐碎了。而在其他案件中,更很明显可以猜想,他是把凡征引过某条错误史料的所有文献都辨析一遍,在数据库时代,这并不难做到,故此显然是玩心太重。(在评论区发现也有很多同样的观感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6916135/comments/)其他类似的赘述的考证也很多,比如p21“刊、刑”误笔其实充分可以解决问题了,他非推倒重来,论述一遍自己的说法。p35德拉克伯里,不过是三流汉学家,既据类书《御览》且汉文差劲,这种论文本直接指明史源即可,但辛先生非逐条驳正一遍。p58镂版一事不过将王祯语插入,他却费笔墨论述。p65页墓碑刻反正文,这种宗教性的文本具有特殊形式本不足为奇,早在殷代甲骨对贞之时便正反文字对写,刻意对照,显然是有意地形成一种文字空间排布格局,但文中却搜寻大量材料予以论证。
其实,想来蛮奇怪,读辛先生文章的趣味在于对历史学者而言可以揣摩史料方法,不知怎么这却成为了显学,由此便使得全书似乎有刻意炫技之嫌。但在辛先生这里,其实这反而是件好事,这成为了一种方法论的教学,你可以不管辛先生书讨论什么主题,都可以让本科生去读他的书,因为史料学方法,其实就是现代学术的一种基本规范,史料学本就应成为文史哲专业的通识教育,辨别叙述的真伪。这本书无异于手把手教您史料学和史源学的运用。
《中国印刷史研究》读后感(六):陈晓珊 | 三千世界,万般因果:雕版印刷术的诞生
原载于《中华读书报》(2019年10月09日10版)
金风玉露不相逢
在历史长空中,人们的智慧之光常如星辰闪现。其中一些灿若恒星,辉映万载,另一些则如流星划破夜空,灵光瞬现后又重归寂灭。还有一些如草蛇灰线,明灭千年,终于在某一天如惊雷震破长夜,盛放出漫天绚烂的星光,引世间万姓仰首赞叹。
雕版印刷术的产生,正是这样漫长而曲折的故事。在人们的印象中,这种被称为刊书的技术,是将柔软纸页覆上刷有油墨的刻字木板,印出一篇篇文字,装订成册,流传人间。然而在这种场景正式出现之前,似曾相识却又全然不同的画面,早已出现了上千年。
远古的人们用木条和石器在陶罐和树皮布上压出花纹,帝国的工匠们用模具在砖瓦上烧制出祈福文字,公文和封泥上留下印鉴的痕迹,石碑上的铭文供人们拓印求索,道士的桃木印章上刻着驱邪文字……这些看起来似乎都是雕版印刷的预演,只要将它们覆纸印册,刊书便水到渠成。
然而这一切却迟迟没有发生。文书上的玺印只代表着一时一事的信用,不需要印出千纸万页,书生们摹写拓片,也只在师友和同好之间观摩。砖瓦上的祈愿词很快会被砌入建筑,随身佩带的枣木大印只为辟邪。类似的印章、印陶和印花布出现在世界许多地方,但这些零散印记的目的并不是用来传播,它们不会变成连续的书章,更不会走进普通人家的书斋案头。
倘若光阴一直这样徐徐流过,纵然千百年之后,人们依旧只能一字一句地手抄经典,绢布上印染的凤凰牡丹,终究不会变成读书人手中的经史子集。印板与书籍之间似乎只隔一步之遥,但却如同两条平行的河流,各自安好,永不相逢。
这破局的机缘,究竟要出现在何时何处?
开元盛世的佛迹传说
时光进入唐代,丝路与海路上隐隐传来天外梵音。据说在遥远的天竺,只要制出千百万张佛塔图像,就可以看到神灵真身显现,于是人们将木板雕成凹凸的佛像,在沙土与绢纸上压出痕迹,放置野外,任万千佛影飘散于天地之间,修成无上功德。
这风潮也传到东土大唐,求法的僧人与远征的将军带回天竺的佛印,在长安印纸分发。此时的佛印仍未脱开印章的特质,莲台上的法师们也依然讲述着佛陀修行与降魔的传奇,隔着一层人间烟火,与世事悲欢遥遥相望。人们聆听教诲,却未曾想过要让佛像和经咒充盈自己的生活空间。千秋功业,还需一瞬点化的机缘。
时光终于流到开元年间,梵音从千山万水外动地而来,被后人称为开元三大士的高僧们从异域带来新的密教经典。他们讲述着极乐世界的千般安好,地狱的百种轮回,告诉芸芸众生如何趋善避害,将今生的愁怨修成来世的福祉。
深经奥义从未像此时这样,与每个普通人的命运紧密相连。盛世的荣光里依然有疾病的苦痛与生死的恐惧,朱门红墙下也难免藏着求不得的遗憾与别离的忧伤。人间万苦终要寻一个出口,超脱的法门似乎就在重重佛像与经咒之间。然而未曾专习画工的双手绘不出佛的模样,写惯了行楷的笔端描不出梵语文字,只能期冀画师与刻工们雕出印版,重现繁难的异域图文。
于是大唐的诸多印版应运而生,人们捺出千万张佛像与经咒,将它们奉在家中,携在身旁,藏在随葬的衣物里,相信着无论生前逝后,这字纸总能引领自己前往极乐净土。人们的祈愿与日俱增,纸上的图像与文字也日渐繁复,小型印版已不能再满足人们的渴求,它们被排列成四幅一体,组成如卍字或回字般旋转的图案,很快又被合刻为一体。当整片大幅木版刷墨覆纸,印出千百页图文流传天下时,终于开启了刊书的序章,金风玉露从此相逢,电光石火般盛放光华万丈。
然而这只是一个开端。人们顿悟出触类旁通的商机,让新生的刊书技术蔓延到生活的每个细节。从经书到历书,到占梦与相宅手册,又有家用针灸方和初学教材,一种种新付梓的书籍承载着或深或浅的知识,如同延绵的灯火,在暗夜中点亮辽远的丝路,从天际直到长安。
芸芸众生与智慧之门
回望这段传奇,会看到雕版印刷术的产生,实际来自一种意外的机缘。刊书的受众本应是读书人,但密教流行而引发的印经之风,却让达官贵人与贩夫走卒都卷入其中,竞逐不已。无论是否识得文字,都期待着神明赐福,这使得初生的技术瞬间拥有了最广阔的市场,自下而上席卷式的需求,远远超出了刊书事业本应有的消费体量。在传统农业社会里,读书人本属小众群体,他们对阅读的需求,千年来已被手抄书卷满足和限制。然而开元年间的这场风潮却贯通了三教九流,让无限商机促成无尽灵感,反向培养出各种需求,而在中晚唐新衍生出的历书灸方等印品,也无不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在此前漫长的岁月里,或许也曾有人想象过与后世刊书相似的工艺,但在成本与收益的衡量下,只能如萤火消逝于长夜,无法照亮更远的路程。从创意初生到流布天下,中间难以逾越却又终究无法忽略的,永远是期盼着岁月安好的芸芸众生。人们的悲欢与祈愿催生了技术的初生与流传,他们对幸福生活无孔不入的期待,促成了工艺的完善与扩展。
而在遥远的天竺,虽然早已有佛印,但在这片没有造纸传统的土地上,人们常常只能用贝叶抄写经书。坚硬平滑的叶面无法印出清晰的图文,初生在恒河的种子未能在当地发芽,它飘向遥远的丝路,在东土落地生根,绽放出盛世莲华。
雕版印刷术终于诞生在大唐,而在这一天正式降临之前,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早已在冥冥之中准备了千百年。那些柔软的纸张,坚实的木板,灵巧的刻工,华彩的文字,千头万绪终于交汇,尽数融入新生的刊书技术中。那些拥有悠久刻碑印布传统的城市,也将成为名扬天下的出版业中心。三千世界,万般因果,明灭的星光终获永恒的生命,并将在两百年后的神州大放异彩。刊书事业会伴随诸多赵宋年号流行中土,它让原本无缘读书的孩童接触到平价书本,激发出对学业的好奇,让渴求知识的学人阅读到更多经典,一代代积累出高远的成就,让无数匠人商贩在新兴的行业里谋求生机,让更广阔的天地山水变得富庶安康。来生的轮回毕竟太渺远,这一页页字纸才是现世生活中,真正的普渡众生之门。
《中国印刷史研究》中重现的,正是这样一段探寻历史脉络的故事。人间事千回百转,每一件都自有其水到渠成的生命源流,并因此出现在时空坐标系的某个特定位置。开元盛世的丝路上,来自异域的风潮与本土的古老传统终于相会,在存留至今的敦煌文书里,依然能看到当年印沙佛会的盛景。一盏盏明灯燃起,照亮茫茫夜空,梵铃与诵经声里,祈福的人们在新春的河沙岸上印下层层佛迹,它们终将变成千般文字登临纸面,承载着文明与希望,飞向万户千家。一人的低喃终于汇合成千万人的齐声吟唱,天门豁然洞开,仙乐声起,佛陀露出安然的微笑,凝望着漫天花雨飘向人间每一个角落——
从此,便是万世光明。
《中国印刷史研究》读后感(七):作为批评的考证
考证,常被视为文史研究中寻获真相的最基本方法,不过运用得当的话,它有时也可以成为有力的批评,借以让人反思旧有的方法和观念。读完辛德勇先生所著《中国印刷史研究》,给我印象更深的,与其说是他以狮子搏兔之力考证得出的结论,倒不如说是他在考证过程中展现出的对旧有学说及其方法论的犀利批评。就此而言,本书不应被仅仅视为“对中国印刷史的研究”,倒不如看作是对中国历史研究方法的批评,只不过选择了中国印刷史作为切入口。
对中国印刷史的研究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仅仅是对这种科学技术发明或其社会传播过程的客观论述,因为长久以来,“中国是印刷术的故乡”一直是我们民族自豪感的一部分。无人敢于质疑这一神主牌,相反,正如在其它诸多科技发明的论述中时常见到的那样,国内学者通常会习惯性地加上一句“比西方早了若干年”这一短语来增强我们一度受损的自信心。在这种政治气氛的笼罩下,中国史学中存在一种弥漫的“目的论史学”(teleological history),即为了将当下所需要的结论合法化,而去寻找历史“证据”的倒推方式。
由于结论已经预设好,因此人们常常无暇去仔细推敲每个细节证据,稍有一点能和预设结论相联的资料,都被迫不及待地拿来作为支撑那个庞大架构的材料。这在心理学上称之为“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即当你相信一个事物之后,就会主动寻找能够增强这一信念的信息。这有时还会导致一种奇怪的现象,就像在西方学者质疑“马可·波罗究竟是否到过中国”(更多是为了通过这一设问来展开相关问题的讨论)时,为这位信口开河的意大利探险家竭力辩护的却是中国人,原因恐怕或多或少是因为他已被视为“中西文化交流先驱”,那他就非到过中国不可。印刷术研究也不例外,一如书中所言,“在研究印刷术起源问题时,有相当一批人都是以捍卫中国人的发明权作为研究目的”。
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吴鲁旺(Dennis H. Wrong)曾说的,脱离了问题,答案是没有意义的。但在中国的历史研究中,人们往往太过注重“答案”而很少去想“问题”本身究竟是什么,至于论证的过程也是走过场,因为他心里已经有答案了。这在学术研究中造成了一系列遗留至今的问题,诸如:先入为主的预判或“定调”;想当然的设想、推导,而忽略逻辑论证;乐于采信符合自己预期的薄弱证据乃至错误论证,但忽视或淡化对自己结论不利的证据;采纳不够可信的第二手、第三手文献,甚至将明知已被证伪的材料仍用作论据,只因这些有利于推导出自己的结论;只看孤证,而不顾及深远的历史驱动力及其逻辑性;急于自树新见,而缺乏与学术共同体的对话,甚至在遭遇质疑后仍各执己见……凡此等等,在中国印刷史研究中都可找到。辛德勇先生在书中多次强调受“正规文史训练”的重要性,但这些问题的根源或许更可能是思维定式,以及国内文史训练注重解读材料而偏废纯理性的逻辑思辨。有些人读完本书后或许觉得卑之无甚高论,似乎并未考证出多少惊人的结论,因为某些观点早有人提出——这同样是一种过于注重“答案”和“结论”的思维定势,然而对学术研究而言,设问、论证和逻辑推导过程的价值至少并不低于结论。
书中关于铜活字的考证在这方面可谓典范。辛氏以扎实的文史功底,证明所谓明代铜活字印书,其实根本没有任何可靠记载,“事实上根本无法认证它的存在”,而我们理应承认朝鲜在活字印刷上比中国先进。在此,他详细辨析了古籍中“活字铜板”、“铜板活字”和“铜板”等记载,主张这只能解读为是“活字印本在印制时采用了铜质版片来承放字钉,而根本没有涉及字钉的材质;据此推定的所谓明铜活字印本,当然完全不能成立”。在此,考证在摧破旧说的过程中,是一种不可替代的批评方法。
在以往对这类发明权的研究中,还存在一个不自觉的倾向,即“越早越好”。尽管这有时也是与学者们对材料的不同解读所致,但恐怕也是这种心态才促使人们去相信一些不可靠的孤证。在《中国印刷史研究》中,辛德勇反复强调“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一种预设的研究结论,或是某种一定要达成的目标,往往会对客观分析史料,合理审视历史事实,造成严重伤害”(p.170)、“历史的发展,是有正常伦次的。文献记载若是严重背戾这样的伦次,就要反过来审视这一文献本身是否存在问题,或者是我们的解释出现了差误”(p.8),同时,他秉持一种严格的实证主义方法,摒弃那些“想当然的猜想”。这样,他通过对文献材料的缜密考证和推断,证明早期的石刻拓印技术、隋代的所谓“摸书”、张秀民主张的唐代贞观年间即发明雕版印刷的观点,以及一些学者将唐代元稹文章中提到的“模勒”视为雕版印刷的看法,都是孤立而不可信的。
这背后的逻辑是无懈可击的:任何重大发明都不是凭空掉下来的,它在生成的过程中会留下许多“痕迹”。正如《现代欧洲史》在第一卷开头就说到的,“我们对印刷术起源相对不了解也确有好处,这样我们就不会错误地把一项复杂的科技发明归功于某一个人,这种不了解也让我们认识到,在任何情况下,一项发明都不像一首诗或一幅画那样是由一个人创造出来的,它是一种社会产物。”印刷术不是“一项”技术,而是在许多项技术的基础上,通过“旧元素的新组合”才得以演化出来的。这其中至少包括:木石或金属材料上雕刻文字、供印刷用的纸张或绢布、印泥(墨),但最重要的,则是发明这一技术的那个社会的内在驱动力,简言之,人们为什么要发明它?
这无疑是个重大问题,但也同样引起了持续不断的争论。对那些试图捍卫中国对印刷术发明权的学者们来说,常惯于将钤盖印章和制作碑石拓片视为印刷术的“先驱”。在1949年后的很长时间里,很多学者还因受政治环境影响,而将印刷术的起源归为“劳动人民的伟大发明”,强调这是由庶民需求的通俗文学或日常生产生活实用印刷品推动产生的。但辛德勇认为,这都是难以成立的,因为用印玺“印纸”与用雕版来“印刷”,看似接近,却不是一回事,因为中国的印信是用作信用凭证而非出于广泛流布的目的制作的材料;相反,他认为只有佛教密宗信仰那种“大量制作经文来念诵供养,以获得功德福报”的观念,才是雕版印刷产生的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驱动力。值得补充的是,初期的雕版印刷耗资巨大,因而只有宗教或国家机构等才能组织起这样的人力与财力。不仅如此,他进而认为,“中国的印刷术,是在印度捺印佛像技术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换句话来说,即印刷术源出于印度”,这其中,最关键的是印度在约7世纪中叶出现的捺印方法。
在此,他赞同藤田丰八、向达等前辈学人的观点,不仅强调印刷术的大规模应用起源于佛教徒的宗教需求,而且认为其方法源自印度——最初可能是用模具制作小塔和经文后印刷在绢或纸上。但问题在于,印度在雕版印刷出现于中国数百年后,仍极少用纸,“而在其广泛用于书写的贝叶上面,却不适宜捺印钤盖佛印或塔印”。结论是:“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中国普遍使用的纸张,为其提供了实际可能和新的发展条件”。
这样看来,印刷术仅仅是在输入中国之后遇到了更适合的社会土壤而获得大发展,但本身并非产生于中国社会,一如活字印刷源于中国而在西欧发扬光大。不过,在此需要讨论的一点是:“印刷术”的界定到底是什么?在迄今未曾见到印度有早期印刷品出土的情况下,印度那样捺印于沙或绢纸是否可算作是成形的印刷术?打个或许不恰当的比方,汽车的发明者一般公认是德国人卡尔·本茨,但组成汽车的关键部件如轮子、轮胎等根本就不是德国人发明的,在他之前也有英法等国科学家的实验和设想,甚至内燃机和四冲程工作循环原理也都别人发明或提出的,本茨只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创制出第一台二冲程试验性发动机,最后将一辆三轮机动车申请专利而被视为汽车的发明者。甚至被视为西方印刷术发明者的古腾堡,现代学者也发现他仅是把原有熟悉的技术转化为一套新程序,并首先将之做成一项产业而已。在这一意义上,说“中国是印刷术的故乡”也不为过。
事实是,由于印度长期不能自行造纸,印刷术从未在古代印度盛行过。在此我们可以补充东南亚地区和藏区的状况:在东南亚的小乘佛教地区,古代使用的是不适合印刷而只能手抄的贝叶经;而藏区虽盛行密宗,但强调的是师徒口传而非印经的传统,加之缺少木材等原料,藏区的印刷术(如德格印经院)是很迟才由汉地输入的。更进一步说,印刷术所需要的广泛读写能力,恐怕本身是与印度这样森严的等级社会不相容的。凡此均可证明印刷术难以、或竟不可能在当地社会条件下自发产生并扎根发展。
或许可以说,这些意味着,辛德勇先生在设想中仍假定了有单一的真相存在并可去探究。正因此,他最终将发明权归于印度,至于由这单一起源中心向外扩散的传播,他大胆推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王玄策和义净将其传入中国的”。然而麻烦之处在于,这一传播路径的推测没有任何文献可资证明;同时,也与他引证的季羡林观点矛盾,季氏确认:直至王玄策和义净入印,当地都只是从域外输入纸张,无法普遍使用纸张作为书写载体,“从而也就无法在印度当地引发印刷技术”。或许更可取的方法是:既然这一技术的发明是一个社会过程,我们不如反过来去讨论促使它得以诞生的那些最适合社会条件——当然,由此我们也可以反思中国为何虽然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但却始终未能发展它。
顺便说一句,辛德勇先生在书中不仅考证缜密,且持论辛辣犀利无比,批评前人治学之失时绝不留情面,而以“求真”为唯一目标。他多次强调“即使是天大的权威,也不会屈从”,也无人能“代表这个国家的所有学者和公民”为学术研究下定论。有时似不无反应过激之嫌。不过无论如何,对国内学界而言,这样的狮子吼恐怕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已刊2017-4-24《经济观察报》书评版 ------------------------------------------------------------------------------- 勘误: p.113:吐鲁番县吐浴沟:浴=峪 p.130:《四库提要》亦谓此书系“删掇诸史”而成:疑为“删缀” p.136:[张秀民提到]“唐代自高宗至哀帝七帝发行的钞币数量,多至不可估计”:疑原文有误,唐代至高宗至哀帝,即便不算武则天,也有多达十八位皇帝 p.139:当时士大夫晏集皆为之:同页倒数第二段引文作“宴集”,是 p.205:永离地域恶鬼畜生:地域=地狱? p.277:西安西郊丰滈路:“滈”古亦通“镐”,但作为今西安地名则只能作“丰镐路” p.284:台北,稻香出版社:稻香=稻乡 p.323:注1提到“徐寅”多处,在前文均作“徐夤”,是 p.332:后归阮文达公小琅环仙馆:阮文达即阮元,彼有“小琅嬛仙馆”,此处“环”字误 p.348:潘天祯就曾经:同页注2则作“潘天桢”,误。下文p.359-367等页,亦多处误作“桢”,且多在正文中 p.350:蒙古马乃真后统治时期:“马乃真”当作“乃马真”,这位后妃出自乃蛮部,其姓“乃马真”即蒙古语“乃蛮人”之意 p.350:名儒姚枢,在家乡辉县隐居:姚枢为柳城人,辉县是其四十岁后才隐居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