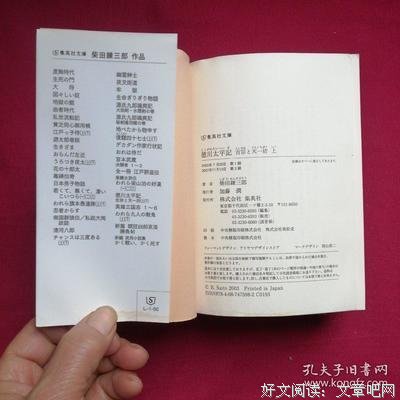
《太平记》是一部由真田广之 / 泽口靖子 / 赤井英和执导,剧情 / 历史主演的一部日本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影评,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太平记》影评(一):尊氏的有心无力
剧内大部分战争场面因为大河剧传统艺能缩减到几乎没有,所以很难体现他一直被打败的惨状(比如多次想zs之类的)。他每一次奋起,说实话是足利的统领这个身份作用更大,各国武家,需要一个人代表他们去夺取权益,就像明治的西乡一般,同时,朝廷也必需要干烂武家的统领。在土豪恶党崛起的世代下,有心无力的他无法平定武家的不满,只能成为朝敌,开幕后无法平定一门和外戚的矛盾,被迫南北横跳,与弟弟和自己私生子作者。他理想的太平盛世,也因为自己的无能不断的被自己所推翻,到最后估计也是疲惫而死(室町的宿命啊)。感觉就是从小见到朽木神佛的执念,让高氏变得非常不懂人心,从这点来看,他和后醍醐帝真是同一类人,也难怪他对上皇的执念了。
《太平记》影评(二):太平记
剧集表现的是以足利尊氏建立幕府前后的日本历史,相对于其推翻的镰仓幕府和其后的德川幕府,足利建立的室町幕府是相对软弱的政府,各封建割据势力力量大增,也为足利室町幕府末期的日本战国时代提供了土壤。而一般人所熟知的关于室町幕府应该就是金阁寺和一休和尚了。
我想其力量较弱的原因应该是处于封建制度增长时期,镰仓时日本可能还未完全建立封建势力,公卿贵族势力强大,武士只能团结一心才能够掌握权力,这也就是其能够战胜蒙古人的原因。而德川时已经进入封建鼎盛时期,统治手法已经相对熟练。
从剧中可以看出,大量的战争反复,这点与战国时代类似,所以作品也采用希望一统天下建立和平为主要思想,不过感觉这永远是个梦想,才建立幕府不久,尊氏就与其弟开始急权夺利,真是永无止境。
《太平记》影评(三):被深深触动的片段
高氏在得宗的命令下被迫牵狗
北条高时要求人质、拒绝足利家治丧时近乎疯癫的可怕
北条一门滅亡,在东胜寺集体切腹。曾经傲慢的长崎家族、时而可怜无比时而心机重重的高时、沉重的赤桥执权,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高时的亡国之舞,让我看的比平氏一门坛石浦投海还要壮烈心疼。
北条一族滅亡后,尊氏举家庆祝,而右马介却被纷乱的世道所冷却心灰意冷时
楠木一族凑川合战大败后,在破旧的寺庙中共沐阳光,笑谈“七生报国”之时
年轻的北畠显家感叹十箭之中必有一箭不中,神佛不再庇佑与战死时,以及其父亲房终于流露出悲伤之情时(让我想到平清盛中的恶左府之父)
尊氏与高师直最后一段对话
旅途结束,尊氏和佐佐木道誉坐在庭前樱花处,唏嘘居然相互陪伴走到最后之时
《太平记》影评(四):一些感触
后醍醐帝的理想,足利尊氏的善变,楠木正成的忠义,北畠父子的无悔牺牲……足利一派尽是些尔虞我诈的小人,甚至连跟随足利尊氏30年的高师直都产生过弑杀将军取而代之的念头,足利尊氏本人也是靠着利益诱惑才聚拢这些人,以利益聚拢的人必定为利益争斗。当初足利尊氏在京城大败,逃亡九州,旗本精锐尽失,只是依靠九州武家土豪的援助才得以东山再起,所以足利本身的实力很弱,身边尽是些投机客,后来与足利直义的战争其实是清理不太安分老实的投机客。
小人打败君子,一来是接地气,重视平民的利益诉求;二来是善于用小恩小惠收买人心。比如第38集尊氏与后醍醐帝讨论不成,碰到阿野廉子,便将计就计,说动用阿野廉子的儿子继承皇位,居然将阿野廉子弄的感激涕零。不得不说女人好骗,或者说阿野廉子也是胸无大志的人。如果换成后醍醐帝,他甘心做一个有名无实的皇帝吗?尊氏的小把戏骗骗胸无大志的人也就罢了,只能拉拢一些比他弱的人,真正的君子如楠木正成(足利曾经为了拉拢他许诺赏赐十一国)不过一笑了之。
个人感觉真田广之是想把尊氏塑造成正义的王者,可是他越想这样演,却演成一个大奸似忠,城府极深的奸雄,无法评价。
《太平记》影评(五):太平记24~34
我承认北条氏举族自尽之后是一度兴味索然的。不过既然放不下就还是捡起来了。
24、25很是沉闷(除了显家着红裳起舞惊艳了一下),但26甚为绝妙~~远离理想和道义的鼓吹,把实实在在的利害得失摆上台面才更有诚意啊。足利尊氏的确是长进了。26 与亲房的对谈,28与佐佐木的对谈,简洁且切中要害。后者甚而有些可畏——相当出色的情报网呢。然而拒绝三位局的交易一场,尽管之后在后醍醐面前直陈胸臆,言辞慷慨、不乏巧妙之处,还是隐隐露着主角威能的光轮。自26之后他对后醍醐所说之言简直句句伪善,只是这一次主角越是伪善我却越开心。
这边厢猿石讨要领地的经历也是值得赞赏的安排,既给了“日野留书”这一埋下N久的伏线一个交待,又暴露了恩赏争端、假纶旨等社会问题,顺便也为藤夜叉母子与足利兄弟的几度邂逅创造条件,可谓一石三鸟。之后的藤夜叉之死,如此的矜持甚而让我惊了——几个当事人居然统统未掉一滴泪……但该传达的情感都传达到了,也不违背各自的身份。藤夜叉遭逢不测之前,偶遇猿乐艺人而忆起作为白拍子时的旧事,手法很不新鲜,却也妥当合宜。至此,在足利尊氏心目中作为诗意化的“京都”而存在的她,其退场也预兆着尊氏与被辜负的政治理想决裂的未来吧。
猿石与藤夜叉、不知哉丸(当他还没有成为足利直冬的时候)、花夜叉一座,只有这一次对虚构人物有了好感和敬意。他们有自己独立和完整的人生轨迹,虽和主角时有交叉,却绝非为了衬托主角的伟大而存在的。他们是实实在在的另一个视角、另一条线索、另一种立场。
登子对不知哉丸的态度,意料之中,合情合理。
忍不住又去搜了剧透。并没有点进去细看,但观标题即可知后半部的死亡会相当密集吧。已经上路的有护良亲王,虽不甚喜欢但死得不错,后醍醐可算是自作孽。之后……楠木兄弟、显家、新田义贞、高氏兄弟、直义。直义是我期待的重头戏无疑。而自从演员换上根津甚八,对新田义贞好感也日增。和勾当内侍的交情是打算开辟新的恋爱线么……不过义贞出征前,内侍那番“心中已有思念之人”的话似又暗示这情节并不简单,究竟如何还是看后续吧。目前为止还是很欣赏高师直,依然是自身利益集团忠实、诚实和现实的维护者。这一点上北畠亲房也是一样——倒有点萌了他对镜画眉的样子。
但是再没有哪个能像当初守时的死一般让我挂心了。偏偏唯有他的死,一个镜头也没有给。或许这样也好。
看了这么多集唯一想吐槽的地方:为何持明院统的公卿都如此猥琐,日本人究竟还记不记得这一支才是如今皇室的先祖?当然到后半部大觉寺统的公卿也一样猥琐了。看演员表发现四条隆资=井上伦宏,这是Code Geass里修奈的声优啊orz
34集尊氏遁入空门倒不认为是装孙子,看起来是真的事情闹大而吃不准后果。所以后来得知后醍醐要将自己赶尽杀绝后立刻就横下心了。至于那纶旨,被佐佐木随手撕掉,莫不是假的^^最后披散头发横刀跃马的pose很威啊,要说真心喜欢主角的话,也是从这一刻开始吧。
《太平记》影评(六):持续增加中-绪形拳大赞!
一直看了绪形拳很多剑豪片武打片,其中大量是烂片,以为他在《蝉时雨》中算是终于“改过自新”,哪里知道在《太平记》中早已大赞!
所以,任何时候没有看过海之深沉,不要轻易用斗去衡量。
绪形拳在《太平记》中的演出,甚至让我想起了司马懿之为人和当初小心翼翼侍奉曹魏的状态来了,笑。
我总以为司马懿比较喜欢曹丕曹叡父子时代,到曹叡死时托孤,“他所喜欢的皇帝都死了,他仍不得不多活一代人的时间!”曾写了这么一句,不要以为我是同人女之心发作,其实不过是最世俗的男人心的预料(啥?):在谁手下干得爽气,在哪个BOSS手下干得有前途当然也就卖力,干得卖力当然也就晋升得快,晋升得高了自然野心也就大了,现在来了一个曹爽和一个来路不明的小皇子,干得憋气又有性命之虞,当然要干掉曹爽了!当然……手段很是阴鸷凶狠,那要另外开篇才行。倒是说司马懿二十八岁时一被曹操点名就知道自己将来七八十岁要当宣皇帝,这是小说家的笔触了。
=======================================================
真田广之,最初几集强扮少年郎实在是为难了。
虽说这部太平记,我是为了看真田广之而看的,不过一开始,视线就完全被绪形拳夺走了,到真田广之出来的时,“呃”了一下,当初《魔界转生》或是《柳生家族的阴谋》中那是真的水嫩美少年,现在眼袋都出来了还要强作少年郎,真的难为你了。囧。连配他的赤桥夫人,也是有眼袋的= =为表现两人一见钟情,还给两人极其多的面部特写,真是眼袋见眼袋,十分心爱爱。何止是赤桥夫人,每碰到一个生命中重要的人,比如后醍醐天皇,藏人头日野俊基,少年时的对头新田义贞之类的,就会彼此含情脉脉地对望一番,我……真的要怒了,这难道不是耽美片咩?足利义满的祖先,你怎可这样?!
=======================================================
2008.09.28
#10-11集
足利贞氏(绪形拳)的戏份结束了。果然很赞!现在想起“阴鸷坚忍”这样的词就会想起绪形拳的表情和语调来。
以前喜欢魏宗万的司马懿,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可能是多了一点诙谐,而少了一点大儒世家的风范感。不过“大儒”这种词,大概都是看了一些电视剧或者长袍马褂的照片而产生的空泛感觉,三国汉魏时的大儒未必不能诙谐有趣。
而绪形拳的足利贞氏给人的感觉就是:这人家教很好,很讲道理,做事很有尺度,能忍人所不忍,其实是肚皮里一心想着“反出城去打天下”的阴谋家,甚至是让人赞叹的阴谋家=_=|||不过相比司马懿,他还是退却居多,没有功绩可以相提并论。
现在想一想汉魏末期,世族大家对曹魏的袖手旁观,一边是司马氏的阴狠,一边是司马氏所推行的事情必定是对他们有利,而曹魏严格的行事未必是使人感觉幸福。正因为司马氏借世族大家的默认上位,后来司马炎放不开手脚进行革新,只能一味讨好世族门阀,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
楠木正成出场了。
我很喜欢这样市井化的楠木正成,很有“英雄不问出处”的豪杰之感:打扮也不是特别注重,看起来就像一个慢性子的商行老板,性情平稳,态度温和,总戴一顶不甚美观的帽子。
估计很多浪漫派的观众不会喜欢这样的演绎,哈哈。
以前我也总觉得“大角色”之类的,一定是一边展示胸大肌一边做POSE一边战无不胜的,不过,现在,更喜欢这种“隐藏在平常人中间的大角色”。
《太平记》影评(七):原本以为美丽的事物,最后都消失了
拖了四五年才看完,以致于在讨伐北条以前的心态和持重都不太记得清楚。偶尔看到伏线一收,才想起幼年的尊氏在山洞里看到一块丑陋的木头被供奉为神佛,而养成了“原本以为美丽的事物,最后都消失了“这一执念了。
九十年代真是了不得的历史”虚无主义“,每个人物都塑造的那么可爱,并且安守于自己的立场。重要的是没有人物呈现出自我意识过剩,头疼脑热地推动历史事件的状态。想必是到了那种地步,反而对自身、对世道的拿捏已经很有分寸了。毕竟有永原庆二作为历史顾问,可以感受到那种公武之分,以及将土地、庄园和日本国制联系起来的叙事框架。虽然后醍醐天皇刚出场时犹如神明(镜头太美),即使后来失脚或者自称为人,也没有过于神话天皇这一角色。演员选得有器量,面庞威严眉眼宽厚,大笑起来的时候威风堂堂。也难怪尊氏一直记挂着这一位曾经”像神佛一样美丽的人物“。
然而这些人后都死了。最初让尊氏开眼的新田义贞,同为源氏,在疾风般攻下镰仓灭亡北条氏之后,成了整日阴沉着脸念叨着”你们想去(打仗)就自己去”的忠犬。不知是不是从小是清贫的乡下武士的关系,器量上永远不可能追到足利成为武家统领的高度。大概真的是命运使然,没有势的人只好武运不济。而尊氏虽然总讲“迫不得已”,在众人的推动和期待下恰到好处地走上了自己该走的路。这一点大塔宫就看得很清楚,“倘若武家希望如此的话,你便会与公家一战”。于是尊氏只好念了两句诗“苟利国家生死以,不以祸福避趋之。”(快别闹→_→)
其实我还真的挺喜欢大塔宫护良亲王的。夏天去镰仓的时候本来已规划好去走《太平记》的路线,因为差点被热死就作罢。镰仓真的好小,沿着若宫大路很快就能攻打到东寺,也就是北条灭亡之地。隔一条马路就是护良亲王之墓,再往北走一小段,便能看到源赖朝公之墓。而足利家的护国寺,也不过在东寺往南不远处。作为沿途散策不需要很久。就像镰仓还存留这五山制度下的寺院一样,在一个狭小的舞台上施展政治,每个人必须像所规定好的角色,完成自己命运所交付的事情。
所以说《太平记》与其是一部讲历史的片子,不如说是一部讲政治的片子。从灭亡北条开始,到杀掉自己的弟弟扶持起好像没那么基磐坚实的室町幕府结束,每一场争斗、辩解和交锋都那样合情合理。楠木正成作为一个土豪为天皇器重,从此提拔于云上,他的“忠义”是出于报恩。新田是为了和争一口同为源氏为什么你可以我不可以的气。还有诸国武家,投靠谁跟从谁,全然乃是为了作为武士的自身的命运。没有人摆出一副为了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事物去牺牲性命,正如北条高时讲“为什么要信没有人见过的佛祖呢”。相反地尊氏和后醍醐却抱有一种超然的态度,尊氏对“美好世道”的追求,后醍醐对“公家一统”的执念。也可以算作身为那样的人所应有的理想。
还有就是佐佐木这个人,也不尽如他所说是为了永远投靠胜利的一方而倒戈。他的情报功能和信息交换的作用,在最后高师直五万人马围困御馆的时候体现了。如果没有他带来的意味深长的威胁,想必事后无论尊氏还是高师直都惊出了一身冷汗吧。有这样一个互相通气的人物存在,往往也能制止些由互相误解和一时错觉带来的不可收拾的战事。在谋略上,很多不输于此的战役都使本片显得真实而矜持。
最后讲讲藤夜叉还有一座。有种想哭却又哭不出来的情绪。藤夜叉和赤桥登子的演员都很美,那种窄额小口面庞丰腴的古典美。和足利的会面也不是那么突兀。虽说要断念无缘,独自将孩子抚养成人,然而对于尊氏来讲,藤夜叉既是他对“美好世道”这一抽象理想的具象体现,也同时保留着对遥远的爱恋、美好事物的诗意想象。坐在台下观赏她的舞,带着白拍子来到海边,说着要去“都城”,从那时起,尊氏就将“都城”看做创建美好世道的必经之路了。上洛,夺取天下,只是时间问题,而他自己彼时却还意识不到。
还有那么多露水一样消失的人。千种忠显在哪一集死的我都没注意。而北畠親房和顯家父子,既是一代学匠又能为武将,的确在公家身上嗅到一统的可能性。毕竟光靠雅行是赢不了战事的,公家也是依赖忠于自己的武家来剿灭朝敌,一旦丧失了武力根基,权力和政事就会旁落。放在任何一个层面,足利家面对自身的下克上,都是一样的道理。
它很想传递一种不可抗力,叫命运使然也好,叫实力决定历史也好。都让人不免产生一种期待,期待出现一位人物,能在这乱世里开辟和建立一个美好的世道。而被赋予这一力量的婆娑罗,也几乎无暇顾及作为一个人所背负的过于沉重的负担,只好用沾满鲜血、见神杀神的双手,乃为万世开太平。
《太平记》影评(八):乱世之中,求取太平
深深的悲哀里总是包含着些许的滑稽,命运的捉弄诠释着滑稽的无情。
足利尊氏的一生,可谓诠释了“波澜万丈”这个词的含义。从最初的忍辱负重、苟安一时,到在被镰仓幕府调派进攻千早城楠木正成时,与后醍醐天皇一派内通,于三河国携足利一门众举起反旗,攻下六波罗探题,待新田义贞攻陷镰仓,灭门内管领长崎圆喜、高资父子为代表的北条氏镰仓幕府;倒幕成功、后醍醐天皇公家一统的建武新政开始后,诸位倒幕功臣陷于新的权力斗争,尊氏捕获试图消灭足利家的征夷大将军•大塔宫护良亲王,而后于违旨奔赴镰仓清除北条残党之时,与后醍醐天皇决裂,由镰仓攻上京都,又因与公家众战败逃奔九州,再于西国集结兵力,由西而东直扑京都,在凑川决战中阵斩楠木正成,之后陆续袭杀北畠显家、新田义贞等旧识再临京都,终于在北朝光严上皇的支持下,创立室町幕府亲身就任征夷大将军,制建武式目,委政事于弟•足利直义,其间后醍醐天皇出逃至吉野建立南朝朝廷,南北两方争斗不休;此后却又因兄弟二人政见分歧日益加深、围绕二人身边的党派权力斗争势同水火,再加之执事高师直、高师泰与直义之间长期的矛盾,尊氏、直义兄弟阋墙,尊氏、直冬父子相残,先由高师直高师泰弟兄二人包围将军御馆而使直义派失脚,后因尊氏放走直义,而又使直义派趁尊氏、高师直等出兵西国与足利直冬对阵时,攻占京都、大败将军,谋杀高师直、高师泰;最终,以讨伐反逆佐佐木道誉、赤松则佑等友军为名,尊氏、义诠父子分赴京都东西两侧成总角之势,成功地再度统御京师,并由越前北陆追击直义派至镰仓,捕获直义,将军决断毒杀其弟,而后与亲子•足利直冬对阵,经一色右马助劝说,直冬放弃战争,此乃将军•足利尊氏终战之阵。
“美丽高尚的人,是无法战胜长崎殿下的。”不想弄脏自己的双手,想要创立一个美丽的世道,可是每一次优柔寡断的政治决策只能带给自己、带给己方所有同袍更深的伤害。
“将军在对自己的弟弟下手之时,已经将自己的性命斩断了。”旧日主君、内兄、朋友、弟弟、儿子,战胜了所有敌人,却不过白首一声叹息。
这场长达三十余年、遍及六十六国的漫无止境的战争,究竟带给人们什么?我们能用一句“黎明前的黑暗”,就理所当然似的接受那些战争带来的生灵涂炭、人伦不存么?乱世之中,求取太平,是为《太平记》。所谓太平之世,便是没有战争;而倘若人人所求之世便是太平,又何须战乱?之所以有战争,就是因为,世间所求并非仅有太平,人心思定,乃是饱尝战争之苦——人不到一无所有的地步是不会后悔的。人性中既有思求安定的一面,也有渴望纷争的一面。美丽的太平之世,我想,终归是一曲田园牧歌。乱极思定,盛极將倾,让我们承认吧,人类内心深处潜伏着一只野兽,它渴望着鲜血和毁灭,它呼号着杀戮与战争,“斗争乃万物之父”,赫拉克利特们早就如此断言。确实,没有一次又一次的斗争,也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上每一次文明的迈进,都伴随着流血与牺牲。新的取代旧的,或者一方压倒另一方,战争,是最简单粗暴,却也最直接有效的方法。
只是代价太大了。牺牲太多了。无谓的死亡太愚蠢了。所以让人怀疑,战争这种方法,究竟值不值得?自幼朝夕相处数十年的亲兄弟互相残杀,父亲和儿子于战场上对阵,赢得了战争,留下了痛苦。随之而来的,便是权力者的寂寞,生命的空虚。所以让人怀疑,战争这种方法,究竟值不值得?“人宁可追求虚无,也不愿无所追求。”尼采的话总是刺耳,可又露骨的真实。可是,人生的意义在于人生的虚无,作为人而言,是不是也太可悲了呢!所以让人怀疑,战争这种方法,究竟值不值得?“而当他们发明了地狱时,就等于找到了天堂。”难道“太平之世”就如查拉图斯特拉如是所言,是名为天国的炼狱?
想到一个关于太平之世的描述:“你不需要坚强。让软弱的自己痛苦才是最重要的。人类本来就是软弱的生物,但是,因为想要脱离痛苦,所以才希望变得坚强。变强就等于变得迟钝,痛觉变得迟钝。对自己的痛苦迟钝之后,对别人的痛苦也迟钝了。误解自己是强者的人就会攻击别人,对痛苦变得迟钝也就失去善良之心。没关系的,让自己继续当个弱者,面对自己的软弱。人啊,保持他的软弱,这就行了。弱者们手牵手,所构成的社会才最精彩。”——太过牧歌了,是不是?
对自己的痛苦保持敏感的同时,也就可能感受到他人的痛苦,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正视自己的痛苦,为理解、宽容别人的痛苦提供了可能性,从而就有可能不会去给他人制造自己也不愿承受的痛苦,不是去抹杀、逃避痛苦,而是直视痛苦,面对痛苦微笑,其实这才是真正的坚强。将自己无处排解的痛苦、不愿面对的痛苦发泄到他人身上,不是去审视自己的灵魂而是迫不及待地毁灭他人的灵魂并毁损自我的灵魂,我认为,这便是所谓“虚无的追求”。申言之,太平之世并非不允许一切纷争存在的极乐净土,水至清则无鱼,而是一个实现了合理性竞争的社会,一个建立了合理竞争机制的社会。太平之世不是一个没有任何痛苦的西方世界,太平之世终究也是一个对于现实社会的期许,也唯因太平之世可能成为现实社会,它才值得人们为之奋斗。所以这样的社会中,不应该存在战争。因为,战争从来不是一种合理性竞争机制,恰恰相反,战争是人类非理性行为中最为有力的代言人。诚然,今天的我们不应也无法低估战争的作用及其历史意义,那也是人类局限性的一种标志;然而,这完全不能成为我们现在否定战争价值性的一个借口。正因为在不断的战争和伤害中实现了所谓人类文明之进步,已经进步了的人类,难道还要采取与石器时代的野蛮人一样的方法——战争,作为解决重大问题的根本手段吗?假如回答是肯定的,那我只能说,“人类的本质,从石器时代以来就没有过一丁点儿的进步。”只是战争的方法更先进了,从火与剑到精确制导导弹和信息战争,如果我们把残害自己人类同胞花样的不断翻新作为某种进步性的根据,那还真是可喜可贺至极啊!
“互相伤害,逐渐习惯此事的世界,我们也在此出生、长大。”习惯了伤痛,麻痹了痛苦,对于伤害别人这种事情也就无所谓了。我们都说人是自私的,为了自己不受伤害,可以伤害别人,这正是因为这种自私是非理性的。实际上,其可以成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手段,只是这种解决必定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虽可成为一时之计,然则却是以矛盾的积累而非化解为代价。在这个意义上,自私总是与愚蠢、短见相结合的。比如本剧中的桃井直常,就是那个时代利欲熏心、极端自私的武家众的代表。假如说足利尊氏、直义兄弟之争是对于幕府施政方针、对于实现他们心中的太平之世而产生的歧见之权力斗争的话,桃井直常自始至终的目的就是个人权势。为了能够成为室町幕府的实权者,他不惜挑拨足利兄弟之间的关系,不惜发动战争,作为一个有力的政治家,他没有任何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悬壶济世的政治理想,而是完全成为一个权力的追逐者,成为自身权力欲望的奴隶,虽然这种权力意志是可以理解的,但却不能成为他的行为正当化的理由。因为他是一个有力的政治家,因为“位高则任重”。当然,毫不客气地讲,历史上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掌握实权者,大抵都不配称为一位称职的政治家,而人民群众早就看穿了这一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说到底,这些当权者只是比一般人民更容易实现和扩大自己的欲望罢了,也不过就是自私自利的权力意志的仆人罢了,这也是独裁专制和世袭制度的一个必然结果。但这正是人。这正是人性。人是欲望的综合体和人性中的自律性,光明的、黑暗的都有,这才是人,这才是人性。其实人性无善无恶,只是我们更愿意去看那我们认为光明或者黑暗的一面罢了。“这个世界上从来也没有什么道德现象,有的只是对于现象的道德解释。”
大河剧一贯有洗白主角的传统,本作也不例外。可能,可能历史上的足利尊氏并没有本作描写中那样美丽的太平之愿,那一系列的战争是北条方与反北条方、公家众与武家众、足利家中党争的诸多私利私欲权力斗争的集合,皆为无义之战、非关正义,更无所谓美丽的太平之世,也许这就是残酷又丑陋的历史真实。可是,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应忘记,“美是真的光辉”。我们没有必要因为这种历史真实而绝望,而回过头去不敢面对真实。NO ONE IS PERFECT,人因为人的不完美性才是人,重要的是,人可以在审美中创造灵魂,人可以在不完美的一切真实中创造完美。虚假的材质只能做出虚假的形式,所有的真和美,归根到底根据于人所真正感受、思考和相信的一切。事实常常是残酷无情的丑陋,然而美却是真的光辉,因为人可以审美。就比如本作中那命运的无奈与悲哀,却让观剧的我们随之心潮起伏,为之欢笑,为之叹息,这种复杂的心情也是我们真实的感受,在那沉痛历史物语的尽头有我们的审美,也正因为受这种实感的驱使,作为笔者的我才会写下这篇拙文,正是因为感受到了美,才会想要用纸笔留住这份美丽,尽管是徒然。在观看中我感受、思考着可能作为事实的现象,在我所相信的真实中进行审美,并用这篇文章为载体,创造着我所希望的美。这样就足够了。
不管处于怎样的黑暗中,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有权期待一个光明美好的未来将会到来。但是,“世界上没有那种伦理能够回避一个事实:在无数的情况下,获得‘善’的结果就必然会采用道德上可疑的、或至少是有风险的手段,还要面对可能出现、甚至是极可能出现的罪恶的副效应。当什么时候、在多大程度上,道德上为善的目的可以使道德上有害的手段和副产品‘圣洁化’,对于这个问题,世界上的任何伦理都无法得出结论。”(马克思•韦伯,《以政治为业》)太平之世亦然。为了太平之世的“善”所采取的的所有手段,包括战争在内,其道德与否在何种程度上是“可以接受的”,这是一个关乎人类前程和良心的问题——除了战争以外,为什么人类没有更加合理的、更有可能倾向于道德上的善的手段呢?或者是,虽然人类从不缺乏这种手段,只是因为那种伴随合理性机制而生的复杂关系,比不上战争的直接有效?我们不应忘记,“任何企图用一场战争结束所有战争的博爱主义者,其结果不过是为一场新的战争的出现而作准备。”以战止战,徒生战乱。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仍然是一种“武装的和平”,就如伊藤博文百年前所言一般。“乱世之中,求取太平”,相信仍然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家们,和所有热爱和平的人们提出的一个从未过时的命题。
:文学价值大于史学价值的脚本《私本太平记》、古典太平记和NHK大河剧的一贯洗白主角的传统改编,还请考据党放过。不是只有还原历史才能欣赏艺术,历史剧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形式。
《太平记》影评(九):从镰仓到南北朝到室町的乱世哀歌
1.1 关于《太平记》
7-8月份将91年的NHK大河剧《太平记》49回看完。该剧改编自吉川英治历史小说《私本太平记》,吉川原著又是依托于14世纪日本中世的军记物语古典《太平记》。曾见有同学将军记物语《太平记》与《私本太平记》的关系比拟为我国的《三国志》和《三国演义》,其实军记物语也是一种文学体裁,并不等于严格意义上的史著。《太平记》的文学价值也重于它的史学价值。不过水户藩主德川光圀(1628-1700)编撰纪传体史书《大日本史》对《太平记》参引颇多。
《太平记》约成书于1371年,作者佚名,描写50年间的南北朝内乱,共40卷。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从后醍醐天皇的讨幕计划到镰仓幕府的覆灭。第二部分,建武新政的产生及其内部对立,足利尊氏背叛新政,拥立持明院统成立北朝,压制新田氏、楠木氏,开创足利(室町)幕府,南北朝纷争肇始。第三部分,南北朝的持续对抗,不绝的骚乱,直至细川赖之就任执事后天下平静。这段历史横向对照过来,我国正处于元朝末期。《太平记》顾名思义,自为乱世之中求取太平之祈愿。
大河剧版《太平记》由真田广之(足利尊氏)、绪形拳(足利贞氏)、高岛政伸(足利直义)、柄本明(高师直)、泽口靖子(赤桥登子)、阵内孝则(京极道誉)、片岡孝夫(后醍醐天皇)、榎木孝明(日野俊基)等主演,为颇受推崇的大河剧经典之作。
本剧的时间线大致为:霜月之乱-尊氏出生-后醍醐讨幕-楠木、新田、足利相继举兵-六波罗落花、北条氏覆亡-建武新政-足利反叛-楠木、新田、北畠显家之死-足利幕府开创-观应扰乱-尊氏之死。
1.2 北条氏与足利氏
HK91《太平记》从镰仓幕府灭亡前奏到南北朝并立混战到室町幕府初创,讲述了约五十年间的历史,以主人公室町幕府开创者足利尊氏的生平为主线来展开这段波澜壮阔同时也苦难深重的岁月。足利尊氏享年五十四岁,二十岁后至辞世的三十年间是他一生中荣耀与阴影并存、从繁盛走向衰败的过程。他既是历史的参与者、缔造者,同时又是痛苦的见证者。三十年前他还是个方及弱冠、心存彷徨的青年,在偶然的一次上京途中,命运的轮辙开始转动。
时值镰仓幕府统治末期,身为执权的得宗北条高时疏懒于政务,幕府权力实际上为内管领长崎円喜、高资父子把持。镰仓幕府的开创者源赖朝的正室就是著名的北条政子,出身伊豆贵族的北条氏原系平氏支族,因协助源氏灭平氏而功勋特出,后任镰仓幕府执权。源赖朝殁后,第二代执权北条义时杀害了源氏血脉,彻底篡取了幕府实权,将执权之位世袭,将军沦为傀儡。在此状况下,据德川氏《史》(德川光圀《大日本史》,以下简称德川氏《史》)记载,尊氏的祖父家時和父亲贞氏“以源氏胄胤,忿为北条氏所裁制,每有灭之之计,而终不果”,足利一门作为源氏嫡系(“其先出自源义家。义家生义国,义国长子义重为新田氏,次义康为足利氏”)的有势力的御家人,自然遭到北条氏的忌惮和压制,被迫依靠世代联姻来保全家族。“义康子义兼娶北条時政女生义氏。义氏生泰氏,泰氏生治部大辅赖氏,亦皆北条氏之出也。赖氏生式部丞家時,家時生讚岐守贞氏。贞氏亦北条氏外孙,即尊氏父也。”轮到尊氏这一辈时,又娶了北条氏女,赤桥的北条守时之妹登子。因此足利与北条实有千丝万缕之联系,足利尊氏及其后嗣身上亦兼有源氏与平氏之血。
2.1 赤桥守时
进退之间不失据
义勇坚贞赞守时
赤桥守时,嘉历中,代北条高時执权、为相模守。以妹妻足利尊氏。元弘三年,新田义贞攻镰仓,守時将兵六万,出拒于巨福呂坂。战数十合,士卒死亡略尽,谓余众曰:“军固有百败而一胜者。今我军虽败,北条氏之命,岂必穷於此乎。然我尊氏姻戚,恐相州疑我。义当速死,以示无貳心。”乃自杀,从死九十余人。
——德川氏《史》卷之二百三·列传第一百三十·将军家臣十三
正如我在题头所写,“进退之间不失据,义勇坚贞赞守时”,在北条氏的镰仓濒临覆灭前夕,赤桥守时的位置是尴尬的。德川《史》说他是受尊氏的牵累而死,虽不中亦不远矣。他本是北条氏贵族,镰仓幕府的衰败他是清醒看在眼里的,但当时的北条氏在他看来已无能从内部自救,只能依靠外部的力量,尊氏便是他的救亡良方。然而这正是赤桥守时的可悲之处。因为他竟把希望寄托在了足利这个北条氏的天然仇敌身上。他对牵连进后醍醐倒幕一事而身陷囹圄的尊氏伸以援手,又将亲妹妹登子嫁给尊氏,以图为暮气沉沉的北条注入新鲜的生机。可这正是北条走向覆灭尽头的丧钟。
我以为以守时的明智不会没有担忧到这种变数。那么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做?是孤注一掷还是无可奈何?为何要将自己陷身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作为北条氏族人,同时又作为足利氏姻戚,必然在两边都不可能得到彻底信任。不管他是出于什么考虑这样做了,我们看到他在任执权期间所尽的一切试图延缓危机的努力,一切避免开战的努力,都不得见用。主事的是长崎氏。作为执权的守时亦是傀儡和担当罪责的幌子。尊氏举兵之际,守时放归留在他府邸监守的登子母子,宁愿独力承担幕府的问罪。他对尊氏可谓仁至义尽,对北条氏也尽忠职守。进退之间,他并没有失去立场。他的立场始终在北条氏这一边。作为亲人和朋友,他愿意帮助尊氏,体谅尊氏的背叛。作为兄长,他不能亏待妹妹。作为一个好人,他不愿意伤害他人。作为北条氏一员,他宁肯战死也不接受尊氏派来的右马介的救助。最后他在战场上战至“箭尽刃折”,毅然自刎赴义。北条氏一族在燃起的熊熊烈焰中集体自戕,为其覆亡之曲谱写了悲壮的尾音,而赤桥守时正是这其中最令人感动唏嘘的一个音符。
或许这是大河剧式的“慈悲”,不把与主人公对立阵营的人物全部作为反面角色来刻画,即使是对立阵营,他们也有各自的思想和苦衷,各自的喜怒哀愁,各自的不能承受之重。甚至也能这样消亡得令人叹息,令人肃然起敬。人之将死,或能露其真实本相,或能奋发一搏,显其人性中最可贵之光彩。尽管只是一刹。在北条高时切腹之前,我已对其深深同情。在长崎父子自尽之际,所有的过往也霎时泯灭,惟余叹息。人,倘若不能生得高贵,那么,且无妨死得高贵。
2.2 日野俊基
“古来一句,无死无生。万里云尽,长江水清。”
日野是一名公卿。《太平记》里公卿如魑魅魍魉,群相并不美好,大觉寺统然,持明院统亦然。日野,却是特殊。
初见他是山伏相,游方僧式样的打扮,披散头发,手执行杖。一点也不美。一点也没有公卿样。在镰仓的街市上他出手救助为僧尼打抱不平的尊氏,仗义救仗义,惺惺相惜。听到尊氏对镰仓的厌烦之语后,他指点尊氏前往京都一行。尊氏去了,从困顿的镰仓自我放逐,途经伊势,转上京都,京都果然是个截然不同,光风霁月之地。京都的风物优美旖旎,文采斐丽,连街市上都飘荡着醉人的香。初入京都的关东武士尊氏和右马介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什么都新奇。也就在这里,在树影葱茏的后醍醐寺,他见到了后来影响他一生的后醍醐天皇,还有恢复公卿样的日野俊基。宽大的狩衣,银灰的底,灰蓝的团花纹,迤邐而来。
松枝挂剑,清雪藏樽,梅花煎茶,桐竹作歌。总以为这该是适合他的生活,藏人右少辨,天子宠眷的心腹近臣,出身儒学世家,才学优长的翩翩尚书郎。只宜做学问,宜风雅,云上之人,图谋倒幕这种刀光剑影的事实在违和。即便要干大事,也最好是高高在上地不沾血腥,不陷险境,只运筹帷幄。然而狭小斗室里的一席交谈,图谋昭然自揭。他不是只会清谈逗趣轻挥桧扇,捧着圭板束带姿俨然从里内迴廊上行过的公卿众,他是实干家。他是后醍醐讨幕的事实筹画者。一个书生,做这样事。一个书生,从他身后那群蝇营狗苟,胆小如鼠的公卿众里排闼而出。
他联络自树一帜的楠木家族,联络困窘欲振的新田家族,联络近江的统领者京极道誉,也笼络武家中拥有首领威望的足利氏的公子。他与尊氏的相逢看似不经意,未尝不有预谋。他指点尊氏上京,对相交不深的尊氏和盘托出计划,推心置腹,是真正判断清楚了这个青年,还是以此搏取尊氏的信任,然后为朝廷争取到又一股强大的支持力量?一个谋算者,一个实干家,是不可能天真的。日野却仍然是个天真的理想者。他的理想指导了他的行事,最终只能蹴向失败。这其间并无错处。他受儒家王政复古,尊王一统思想的熏陶,要推倒幕府统治,为天皇争回施政实权,这不是不能行,但他迷信新政,以为凭借以天子为中心的朝廷之力,以为集合公武两家之力,在当时就真能实现天下治平的理想,这就超越了,过于理想化了。他对阿石所描述的那个不会有人失去家园失去幸福的好世道,终究如他在京都斗室中对尊氏所说那样,“你就把它当作痴人说梦吧。”
幸而他死了。和风丽日,葛原岡,尊严、漂亮地死去。一袭白衣,恬静、安详地死去。一幅绝笔,禅意、诗意地死去。设若他活着,活到了建武新政,活到亲眼目睹又一场崩毁,活到再次跟随后醍醐流亡,活到眼睁睁看着南北朝动荡战火,也像尊氏那样目睹一个个曾经志同道合的人纷纷死去,他是不是会幻灭呢?是不是会觉得,所谓理想,也不过如此而已?
理想未曾实现,它就始终是美的,因为它还没有实现。它还存在梦境中。能为理想而献生,觉得自己死得其所,是多么幸福的事。
日野死了。他就永远以这样一副姿态停留在了尊氏的记忆里,作为京都最繁盛美好时代的象征,作为那许多曾经美好的人最美好时代的缩影,作为未曾实现的理想的化身。日野的死,打碎了尊氏对理想的幻梦,却将理想本身完好地保留在了尊氏的心底。
“他们都曾经活过这世间。”人生即将走到尽头的尊氏喃喃自语。在他送鸩酒给直义时,兄弟促膝相对,言及幼小时事,欢笑渐作苦笑,直义装作不知地喝下鸩酒,尊氏说,“我小时候去窥探岩神真面目,那时以为它不过是一块腐朽的破木头,面貌丑陋,现在想起来,觉得丑陋也无妨,或许那就是岩神的真面目,纵然丑陋腐朽,那毕竟也是神啊。我总是会毫无缘由地这样想,倘若不这样想的话,倘若不这样想的话……”声调平静,却字字如泣血。这样的体悟,又是经历了多少的痛苦割舍、骨肉厮杀而来。倘若不愿意相信人的本相是丑陋的,因而宽恕接纳这种丑陋,那么所做的一切,根本是无以为继,也无法自我宽恕的吧。
所以,宁愿日野就一直这样天真着,理想着,直到干净地死去。
2.3 众生相
作为历史剧的《太平记》是部群像戏,即便是主人公足利尊氏,在前期也并不耀眼,并不格外突出。尊氏的演员是演出过《黄昏清兵卫》的真田広之,彼时的真田広之方当三十盛年,面目尚且温润,他的表演以我来看颇富层次感,于少年、青年、中老年各个阶段有细致入微的变化呈现,其转换又如鱼水交融,过渡自然。因此在剧情逐渐走入衰败的后半段,特别是后期痛苦疲惫的尊氏面临内外交煎、难以转圜的困境,被迫手足相残父子相杀时,作为观众的我也逐渐被带入了他的内心,从他的视角,站在他的立场,来理解他所做的一切事。即使是权谋者的道路,也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不是能够承受,而是不得不承受。
后醍醐,日史上百折不扰,意志坚忍无比、雄心壮志的一位天皇,不过命运相当曲折悲剧,数度流亡。到死也没能完成他的所想。这个人物在剧中似乎并不太受观众喜爱,有野心的上位者总是难以塑造得讨喜,不过片岡孝夫真是极好的演员,大概也就他,能够举手投足,帝王气自然流溢。后醍醐对尊氏一生的影响都极为深刻,尊氏曾把他当作神人来崇拜景仰,响应他的讨贼诏灭了镰仓的京都镇守六波罗探题,推翻了北条氏统治,及至日后举兵反叛,亦数度不愿正面与他为敌,总试图达成妥协。双方的矛盾在于公武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导火线是建武新政的弊政。后醍醐一心想政归官家,但对武士的过度贬抑,恩赏不行乃至剥夺旧领,都激起了武家怨声载道,足利家族作为武家统领,处于万众所目之地,自身对政治利益同样也有需求,再加上剿灭北条的独大功劳,不惟自骄亦易震主,足利反后醍醐,实乃时势之必然。
尊氏的父亲贞氏,因为其父家时的前车之鉴,一生忍辱负重,一位非常好的父亲。他到死的时候,大约终于认识到自己委屈求全的做法已不能保全家族,也就鼓励尊氏以他的方式去抗争。他的死为尊氏日后的举兵打开了枷锁。
北条高时,镰仓幕府的执权,反面阵营的头。虽然是“反派”的头,高时的命运也很令人同情,他多少非出本心地坐上了执权之位,实际上却并不喜欢政事,却又被勉强去担当幕府责任。这就是在其位者的苦恼吧。而且当时的幕府已经积重难返,内外矛盾根深蒂固,无法消除,他看得很清楚,却也无能为力,于是就早早放弃了,过上了疏懒玩乐的生活。他和赤桥守时是对照的两个人物,是北条氏人面对灭顶忧患时所做的两种反应,守时是明知不可为依然为之,他则是明知不可为便放弃之。结果作为与不作为殊途同归。高时最后是率领族人切腹而亡,死得甚为悲壮哀感。
楠木正成,河内独树一帜的武士大名,是个银英里红茶杨一样的人物,性情恬淡,不爱战事,在田间耕种整日也不厌其烦。而这样的人,后来却响应天子号召,去勤王了,以河内孤军吸引镰仓军倾巢出动,为尊氏在京都、新田义贞在镰仓的举兵创造了空档,终又与尊氏从倡义时志同道合的战友,转变为两个对立阵营的敌人。最后,战败举家自刎。尊氏想招降他,被拒绝。这又是一个尊氏不愿杀,却也死在他手里的人。在战场之外,他们是惺惺相惜的朋友。如果战事不起,他们本可以成为一生挚友。楠木有一句名言,为自己宝贵之事物而战,虽不成亦不为败。
新田义贞,是关东的另一支源氏嫡系后裔。其祖上应该说和足利系出同门。这个人在日史里记载和尊氏关系并不好。但在本剧里,他也是尊氏曾经的同志之一。同样惺惺相惜,不过,最后分道扬镳,彼此开战。直到新田中伏而亡。新田和尊氏的道路颇为类似,如果是他击败了尊氏,那么他可能成为另一个尊氏,开创另一个幕府。不过总觉得这人的格局不如尊氏。
京极道誉,近江的武家统领。在剧中更常被叫作佐佐木判官。这是一个绝对无法让人不注意到的人,他的出场就极其噱头,服饰花哨,爱好风雅,喜立花之艺。是京都的婆娑罗大名(婆娑罗,大意指离经叛道,不遵循旧权威)。这个人最著名的特点就是他朝秦暮楚,视倒戈叛变如家常便饭。这样的人按道理不可能为大家所喜欢。不过京极道誉是个中极品,他虽然倒戈叛变如家常便饭,但每回倒戈,都是最后又倒回尊氏这边来。而且尊氏一不在阵中,他就倒戈去别人家,尊氏一回足利阵中,他不管身处何人旗帜下,又会立刻倒戈回尊氏麾下,这种囧囧有神的剧情安排,不知是史实如此,还是小说家言,还是编剧故意安排。你以为他是墙头草顺风倒,他偏偏又屡次不曾舍弃尊氏于危难中。故而三十年后,尊氏垂垂老矣,行将就木,亲朋故旧死的死,老的老,离散的离散,惟有他还陪伴在侧。两个半老人两鬓星霜,闲话樱花院落,也只有他,还能倾听尊氏说心里话吧。尊氏把义诠和幕府托付给他,他仍然是打着那副花腔,笑说,我可是不能够依靠的哦。尊氏回道,三十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你,就觉得你是我的朋友了。朋友这两个字,也能令京极道誉这样的人,回避过脸,掩盖住热泪吧。
“看来,义满殿下定能成为一个比义诠殿下更有成就的人吧。”
尊氏笑而不答。
“那么,我就从义诠殿下麾下倒戈到义满殿下那里去了吧?”
尊氏一怔,禁不住骂:“卑鄙小人。”
两人相顾大笑。
多么温暖。
还有直义。
直义死后,尊氏甚至对着右马介说,我实在活得太久了。我想,不是活得太久了,而是活得足够悲痛了吧,以至于觉得生命很负累了。洗白主角是大河剧的传统,历史上的尊氏未必这么感性,不过历史谁也不知道,谁也无从揣测生活在消逝时代里的人的喜怒哀愁。尊氏一生的道路,有一半是被直义给拗曲折了。他可能原本就有野心,但在多次关键决定的时刻,是直义代他或促使他下了决定,比如反叛幕府,又如后来反叛天皇。杀护良亲王、伪造纶旨种种事件,都逼尊氏走上了无法转圜之路。在后醍醐下诏着新田义贞和北畠显家讨伐尊氏时,依照足利族人《梅松论》的说法,尊氏还曾怀着“义与直义同生死”之念毅然对抗后醍醐(兄弟多么和谐),《太平记》则记载了上杉重能和直义伪造纶旨断尊氏退路一事。所以作为足利幕府开创者的尊氏,身上也有直义的影子。手足间的矛盾激化,也跟足利幕府的权力和对公武之政的看法分歧有关。如果说后醍醐的失败在于无法消解公武矛盾,那么直义的失败则在于态度过度倒向公家,丧失了幕府的独立性,引致幕府内部分裂。同时还有一个致命的缺陷,他并没有重视也就无从处理武家名门和出身不高,但在历次战争中崛起壮大,掌握了实力的豪族之间的矛盾。
还有对足利氏世代忠诚、司职执事的高家的高师直,一直跟在尊氏身边出谋划策,是军师也是管家,一直坚定、诚实,也现实地捍卫着己方集团的利益。最后与直义起争端,造成尊氏两头为难。高师直这个人物并不是个始终如一的单面人,他有恶的一面,有婆娑罗的一面,有惟利是图、胡作妄为的一面,也有心生背主之念的一刻,但这仍旧是个颇有可爱之处的人物,他聪明,绝大多数时间里稳妥可靠,善谋算,战功赫赫,绝大多数时间里对尊氏忠贞不贰。并且毕竟到最后,他也没有背叛尊氏,反而在尊氏战败于直义之手时,要尊氏割下自己的人头去和直义谈判。高师直的结局是在回京途中被直义派暗杀。他有个兄长高师泰,在剧中笔墨并不突显,跟他同时被暗杀。剧中两处情节表现出尊氏对他的极端信任,一处是在众目睽睽下用扇子痛打他,另一处是命他部署五万军士围困自己的将军御馆,以迫使直义与自己面对面谈判。前者,尊氏竟没有忌他心生怨恨,后者,让一个大将以五万兵围困自己的住所,是极端危险之举,没有绝对信任,是不可能如此的。大约那时,他如不信任高师直,也再无可信任凭藉之人了吧。不信任高师直,也就是不信任自己(的御下之能)了吧。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