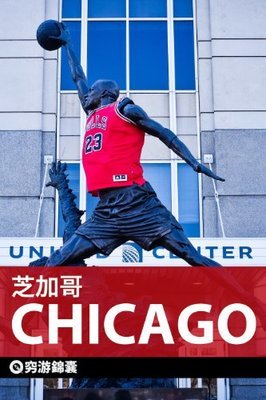
《朝圣者的碗钵》是一本由菲利普.雅各泰著作,纸上造物|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9,页数:9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朝圣者的碗钵》精选点评:
●被莫兰迪的画吸引,却很难找到一个准确的词形容。看这本书我才意识到,这些画是一种抵抗涣散的静默的力,我们喜爱它们,是因为可以专注地照见自己。
●说了这么多,却一言不中;这些化作在你面前,谜如青草。
●雅各泰是我冬天的阳光
●精美的艺术评论小册。莫兰迪最爱的作家:帕斯卡,莱奥帕蒂。
●新年的第一本,献给这本小而美的书。以诗人的眼与心来论画,所带来的是异于常人的敏锐与精妙。有的时候,觉得他说得非常地贴切,于最深处有了那幽微的发现,又有的时候,因为一种自己对于艺术的生疏和模糊,而感到迷茫难解。但最能打动人的还是莫兰迪的画,这是否就像作者所说的,“这要比我之前写下的一切,……都更简洁,更有力”?翻译文字很好。
●最近和帕斯卡很有缘呀,又看到了。不到100页的艺术评论,一幅画配上一段思考,有几段写的很妙,将画作的静物比作纪念碑式的符号;撇开主观观点去看,我觉得还是对于创作背景还是存在主观臆想,在观看方式上这样的引导反而会局限自己和读者(观者)的思考;艺术评论真的难写,即要避开赘述大家都能看到的视觉信息,又要转述作者本人所意图传递的信息,且引导观者去思考作品属于自己的文字表达。作者提到莫兰迪的画会让他想到巴赫,那于我我会想到萨蒂。装帧设计很用心了,再放几年看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吧。
●莫兰迪的专注带有神性,建立在背对世间、弃绝所谓正常生活的基础上,日复一日地画他的瓶瓶罐罐,就像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于简单的重复中臻于永恒的寂静。
●抒太多情了吧。
●之前看过诗人斯特兰德评论画家霍普的那本《寂静的深度》。相比前者,诗人雅各泰评论画家莫兰迪,写得更加轻盈,更加诗意。书中引述了帕斯卡,莱奥帕尔迪,但丁等人,都是雅各泰尝试进入莫兰迪以及他作品的尝试。无论如何主观,看起来真的很享受。莫兰迪那迷人的画,依旧是个迷,而这正是艺术的特质之一。另:书中的插图是真好。
●用“忍耐”这个词语谈莫兰迪,但忍耐中又有一种舒展。
《朝圣者的碗钵》读后感(一):多事的评论家
没几个字,薄薄的一本书。作者从出发点就错了。作者全书总是东拉西扯,一会把贾科梅蒂拉过来,一会把帕斯卡拉过来,一会有讲述几何对世界的意义等等吧。错了,一开始就错了。莫兰迪是艺术史上一个单独的个案。没有流派,没有传承。他孤零零的就出现了。强行承上启下或许在别的大师身上都好用,但是放在莫兰迪身上一点意义都没有。
拿莫兰迪和贾科梅蒂做对比更是毫无意义。他对比的也稀碎。评论家是喜欢讲出一些文学性的东西或者哲学性的东西附加在艺术家作品之上。如果说萨特当时对贾科梅蒂加上存在主义的头衔是一个至少看似完满的自圆其说,那这本书真的是又碰到了一个雷区。莫兰迪的作品,他本身视觉上的魅力就足以征服人,在这种情况下硬憋出他有多少文学性,要么作者水平不够,不如萨特那帮人能憋的自圆其说,要么就别瞎逼逼了。
无论是诗人还是画家,都在于对现实世界一个形而上的提炼,只不过艺术家选取的表达媒介不相同。评论家可以主观的理解艺术家,但是如果要在艺术家头上再戴一顶文学或者哲学的帽子,这个帽子就一定要有张力,至少能盖得住莫兰迪的长度和宽度。不然就是给莫兰迪穿了个不合身的紧身衣,无论你怎么强行解释都事倍功半。
读评论家的书,并不是因为读者看不懂画。而是想看看别人心中的哈姆雷特是否比自己心中的更有趣。你把读者当傻子,自然只能得到一群傻子的捧场。
《朝圣者的碗钵》读后感(二):摘录
-贾科梅蒂与莫兰迪两人在作品上独具特色的专注,恰可以在其构图中寻到一一总是正视图,在贾科梅蒂那里,聚焦在面部、在模特的眼睛上;在莫兰迪这里,不断趋向于将物向着画布中心聚集,那些物早已被画得像是在一条横饰带上一般。 可以看到,在两位艺术家这里,一切,绝然是一切——人生以及作品——皆奋力地在抵抗着涣散。
-“有时当我去思考人类的种种纷乱,我发现一切人类的不幸均来自一个原因:他们不知道如何安静地在家中休憩…”尽管帕斯卡后来言之凿凿地认为人没有玩乐是切不幸之中最大的不幸,但他明白,所有玩乐皆是虚妄,能够在沉默与孤独中,只专注于必要之事的人,方是唯可以栖居在真实中的人。无论如何,这是莫兰迪从帕斯卡那里所学得的一课。他一直都在照此去做。
-关于此,我曾在一些静物画中注意到他描绘的白色碗钵它们令我想到日本的诗僧。我很欣喜地在让·克里斯托夫·贝利( Jean Christophe Bailly)为马格纳尼·罗卡基金会创作的一幕“场景”中看到这样一段话一场景是为展现基金会的藏品而做的,而这段话是根据莫兰迪的全部画作藏品而写的 仿佛绘画变成了一种茶道,不过乃是眼目的茶道——将感官的叶片浸入超然之水的种艺术。 不细思的话,是可以这么做比的。
-又会想到柏拉图在《会饮篇》中对我们所做的邀约,一种更加古老的飞升。然而,这种向着纯粹理念的飞升在艺术里,是否导向的是蒙德里安晚期作品所呈现的那种几何学家的天堂呢?一个令人室息的天堂,一个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空间。而莫兰迪的画作,哪怕色彩淡化至极,哪怕形相消失殆尽,依旧是有气息在——仿佛我们在此能听到将死之人唇间嗫嚅着的临终遗言。 我在莫兰迪最后那些静物油画中看到的纪念碑式的造型,在水彩画这里,变成了无形的石碑一般的东西。
-在一个盒子、一个罐子 个瓶子近旁的,这个近白的碗钵一一它是不是比任何其他的碗钵都更适合朝圣者带在自己的行囊里,并且在停歇处,在“看顾我的永生者之井”处汲水解渴呢?哪怕是一个如如不动的朝圣者一一当他的双脚不再领引他,而最终唯有在自己的思绪中行进的朝圣者一一亦可如此吗?
《朝圣者的碗钵》读后感(三):任时代的波涛拍打他的门垣
“纸上造物”系列读过三本,《寂静的深度:霍珀画谈》《观看王维的十九种方式》,以及这本莫兰迪。这些书虽然轻薄,但却需要花一定的时间思索吸收。信息量大且需要反复揣摩,并不是轻松的读物。
莫兰迪和他的画这两年确实“火”了,火的更多的是一种色调和风格。至于有多少人真的驻足了解画家和画作本身,恐怕属于少数。
作者以诗文短篇的方式去解读他理解的莫兰迪。译者光哲则保持着一贯简洁优雅而精确的翻译水准。确保了阅读体验的愉快和流畅。
这本书适合向往安静,习惯于独处沉思的人阅读。不言不语都是好风景,只有暂别喧嚣,回归寂静,我们才能有机会走近莫兰迪,通过观察他笔下的光影、灰尘、朴素的静物,排除周遭的纷繁复杂,得以观照灵魂。
“真是疯狂,只要想想,想想自己的一生,日日如此。但莫兰迪一点不疯狂;相反,他的眼睛是明亮的,心也是静得出奇;他坚持,毫不懈怠,是因为他一定相信,这三四个主题的这些无穷无尽的变奏,无论多么细微,都不会是徒劳的,哪怕是在维苏威火山的威胁下;相信一个人可以堂堂正正地,将自己的一生囿于这非同寻常的志业中去,任时代的波涛怎么拍打他的门垣,他都不在意。仿佛依旧是有一些事情值得付出一试,哪怕是在这漫漫历史的尽头。我们并未完全失却一切,还可以另有所为,而不是因为恐惧而尖叫、嗫嚅,或更糟糕地闭口不言。”
“有时,颜色尤其简素,仿佛是冬日,是木头与雪的颜色。它们再一次地,让你马上想到“忍耐”这个词,想到老农,想到灰衣僧人——与雪中,与空房间里粉白墙壁之间的那种寂静同等。这种忍耐,意味着生活、操劳,意味着“挺住”:谦卑,忍耐,而非反叛、漠然,以及绝望;仿佛有人仍期盼因这忍耐而得富足,乃至相信,可以默默地沉浸在那重要的唯一的光中。”
——《朝圣者的碗钵:莫兰迪画作诗思录》([法]菲利普·雅各泰 著,光哲 译,商务印书馆)
《朝圣者的碗钵》读后感(四):没有标题
一个经常性的无常之问:画到底诞生在诗之前还是诗之后?是有形邀约了无形,还是无形诞下了有形?
独自探索这些是无趣的,诗人菲利普·雅戈泰在这条道路上摸到了他的旅伴——莫兰迪的画。和许多人相同,也和许多人不同。在寂静的房子里,最适合的是色彩充沛的巨幅画作与华彩雕塑;而在庆典庆典和醇酒之后,给倦眼垂怜一吻的应当是莫兰迪的静物。
这本书里没有高声赞美。浪漫的词句就像五月节捧在花冠女郎手中的干麦穗,拂过春夏交际的溪水,牧童的歌,还有恋人的心房。有趣的是,莫兰迪是一位静室画家,雅戈泰也是一位静室诗人。这书也是一本小小的书,文字也是隽永的短篇。却不给人一定要“读出个什么来”的束缚。它的精美,是那么的不经心,正因此才惬意。假如我有一些小动物,我会在动物们枕在肩头时一只手翻动它。
怎么能够不去往博洛尼亚就结识莫兰迪呢?去看这本书吧,读出声来,你会找回青少年时期的语调来。过去的你依然在场,过去的四季依然在场,莫兰迪本人也在场,就坐在你的小桌子前看着照亮你的灯光。
莫兰迪的色彩是一种无法过时的“反色彩”主张。它不是个主义,还没被用到那一步,这个主张在莫兰迪身上有初学者的活泼与自在。画面低沉,但不沉重,是同时有自然光、灯光与炉火的二十世纪居室产物。在那之前,宫廷画与宗教画派生的绘画学派,对颜色有严格的定位。有伦勃朗那样的人打破规矩,就有莫兰迪这样的人绕开。
他是一个坐在高脚凳画画的人,人和摆放景物的桌子同等高度。有的时候他会画一整天摆放,观看,来达到一种不经意的现实与内心的重合,好让他喜爱的色彩组合更自由地显现出来。他对自己的苛刻恰好是通向技能自由的踏脚石,这样一来,每一段时间在他身上都有了确实的意义。如果他的手不在作画,内心也在。他的全身都活在不会中断的艺术之中。
还有一种可以辨识的“无性别”主张,是莫兰迪被广大研究者归为“画僧”的特点。他深居简出,把社交成本压到最低。除了一些自画像,他极少展示自己,甚至系统性的艺术专著也没留下。在他的自画像里,我们能看到的是一个极不希望引起注意的人。和他的画作是统一的,画面里没有人,包括街道上,也没有人。那些田野,街道,房子,景物,既不带有男性特征,也不带有女性特征。所有东西都是“被给”的,存在于此,十分自由,因为不必向“被给”的人或物来介绍自己出现在此的缘由。在观看他的画作时,你的境遇也是“被给”的。所以他的作品也没有男性话语体系里的那些负累,离教廷更远。他把物还给物,也就是把人还给人。
布罗格之类的宗教画大师用圆润无骨的手腕和鼓鼓的线条来表达“正值童贞的年纪”,进而表达童贞。女子不是女性符号,男子依然,是老道学高深莫测的按天象与神示摆放的教具。莫兰迪则是另一种更接近心灵的童贞之愿,而非出于伦理的“安排”。
他对艺术的爱并非“超人之爱”,是凡人之爱,但更让他具有神思。
莫兰迪对绘画与绘画研究的影响,至少在下一个一百年内不会结束。他与中国艺术的缘分,也不会止与译介和传播。
巴尔蒂斯如是评价:“莫兰迪无疑是最接近中国绘画的欧洲画家了,他把笔墨俭省到极点!他的绘画别有境界,在观念上同中国艺术一致。他不满足表现看到的世界,而是‘借题发挥’,抒发自己的感情。”
莫兰迪本人所言:“我本质上只是那种画静物的画家,只不过传出一点宁静和隐秘的气息而已。”
《朝圣者的碗钵》读后感(五):朝圣的路 以及 诗人献给画家的一章水仙辞
朝圣的路
以及
诗人献给画家的一章水仙辞
作为里尔克谈塞尚那些书信的法文译者,雅各泰以为,那部诗人谈画家的经典之作,实是细描了一个诗人如何尝试趋近一个画家,就像塞尚趋近圣克多山,走的俱为一条朝圣的路。 而他自己,在面对莫兰迪,在心生震动时,所做的也正是也是一个趋近,趋近一个谜。
这谜: 这位画家用一生,反反复复,来来去去,只是那么几朵花、一点点风景、一些瓶瓶罐罐,然而,这有限的形里,却仿佛有无尽相。这谜乃至让人起疑。 便有点像斯特兰德在霍珀画前的感觉,有某种熟悉,却是道不清说不明的。斯特兰德写霍珀, 没有任何理论的切入,没有任何意义的脚手架,只是一种原始的观看。近乎天真的观看(这倒与里尔克在1907年的秋天遇到塞尚又是一样的)。斯特兰德那里,不过“如是,如是”的指指点点,白描。而雅各泰却有不同。
若说斯特兰德是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行走,那么雅各泰便是在空中飞翔。他讲莫兰迪,却分明见里尔克、但丁、帕斯卡、莱奥帕迪、巴赫、维米尔、贾科梅蒂……这些诗人、哲人、画师、乐手,在召唤中,纷至沓来,自相映发:或者并置来,看形相的差异,看构图与光色;或者远溯而去,拓印彼此的思想图谱;或者比对,演绎他的巴赫式的变奏手法。他以他们为观照,照见其画作里数学与几何的精魂。照见画作背后的黑暗深渊,以及其上“振奋的灵魂,少年的灵魂,燃着纯粹的火焰”。照见他画作惊人的平静与同等的激越。
雅各泰说但丁诗句能给我们飞升或狂喜,并以为这是诗人的必要,倘若无,便有所不及。而莫兰迪显然是有的。的确, 雅各泰在那些静物、花朵、水彩前每每的耽思、寻觅、偶然兴得,总是会感味到“圣母升天”、“主显圣容”、“圣谈”、“临终圣餐”等圣经里的奇迹,超凡入圣的奇迹,云门宗所言的“ 拄杖子化作龙,吞却乾坤”的奇迹。这也是一种炼金术的原理,含有某种物理的转化、某种精神上的变幻。这便是莫兰迪的秘密所在。他画作里相与无相之间的幻化之谜所在。当然,也许这都不相干,因为莫兰迪走的或许是另外的路——想想牧溪——我对他的喜欢,永远都要在对莫兰迪的喜欢分值上另加三分——想想他的那幅《六柿图》——那永恒的六个柿子。而那幅画,它自身仿佛已成了绘画的第一义。相与无相俱在。在此说什么擢升不擢升的, 都只觉得是落于下乘。
我又想,雅各泰为何要选择莫兰迪呢?这其实是要想一想的,因为如他自己宣称的,他之前从不谈画—— 他本是很有资质的:与他偕隐且一生挚爱的妻子即是专业画家,他家里无数当代画作收藏,自己又曾专门钻研过16到19世纪的绘画——而最终因为莫兰迪食言。这样的破例,这样的郑重,而我们——起码作为译者的我——不问这个,简直是有点轻浮了。
而对此,第一个想到的,是他们的人生。他说莫兰迪如僧侣,背对世间以及世间的日月。说莫兰迪对两位思想先驱的心仪,其中之一便是共有的隐逸心。而他自己也正是如此,1925年出生的他在28岁结婚的当年即离开巴黎,在法国南部乡村隐居,直到今天。
然后是他们的作品。他屡屡提及画作里弥漫的专注与耐心,以为莫兰的人生与作品皆分明地在抵抗着涣散。而这个也正是雅各泰的写作品格。这里只讲一点,就是对光的辨认。莫兰迪画作里有光么?当然有的,然而是几不可见的,是一个almost invisible . 但雅各泰却能看到——暗哑的光,永恒的光,宁静的光——且看得明晰:他能分辨出晨光还是暮光,是迟落在地平线上的遥远的星子的光还是黎明日出之前那一瞬的光。他说画家对光的追逐、等待、心心念念,永无厌倦。而这恰好就是雅各泰自己啊。他自己正是一个捕捉微光的人。他是被称为“黎明诗人”的。诗人冷霜翻译了他不过十首诗,就已经敏锐地感受到他“似乎倾力于书写昼夜更替之际光影变化的无穷奥妙”,“醉心于捕捉事物的黎明状态”。所以,他们是同类。即使笔调这么减省,但其实与里尔克遇见塞尚的那种烈燃与迷醉,有着同样的强度。那么,其实这乃是诗人为画家献上的一章水仙辞。
“你终于闪耀着了么?我旅途的终点。”
是梵高,他有一幅自画像,一个背着画具的画家阔步走在一条大道上,去往塔拉斯孔,那是他作画的地方。画家走在路上,阔步走着,背后是金色的麦田,脚下的路明亮。五光十色,梦幻一般。而画家的脸看不清,暗暗地,与地面拖着的影子有着同样深度的黑,灼烧后所留的黑。 黑得惊心,像痛苦。
光哲
2019年7月, 北京,良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