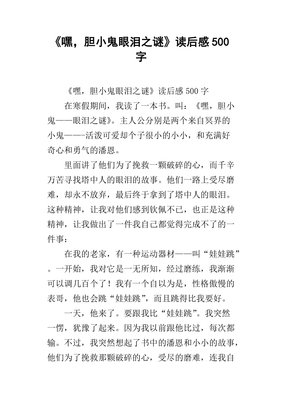
《日本权力结构之谜》是一本由[荷] 卡瑞尔·范·沃尔夫伦著作,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18.00元,页数:73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日本权力结构之谜》读后感(一):日本为什么失去了三十年?
文/徐谌辉
我觉得这不是一本结构日本的书,也不是介绍日本的书,准确的说,我认为这是一本批判日本的书。
虽然作者来自西方,在日本生活了二三十年,口口声声表达着对于日本的爱,但是,从他的字里行间,意识形态,对比中,始终存在着,只要与英语世界不一样的就不够好的潜意识。也就是说,作者在这本书了,其实大部分做的是美日意识形态比较,从而推断出日本现在的问题。而我认为,这种做法很不客观,也不够严谨。
当然,这本书虽然不一定够细,但是作为对于日本这个社会了解之书,足够全面,用了多个角度的阐述日本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从这点考虑,此书倒值得一读。
不过,这本书是三十多年前写的书。所以,那时候日本还是荣耀时刻,傲视全球。作者在批判中眼里都是他们成功的原因。当然,现在看来,这也是他们失去的十年、二十年、乃至三十年的原因。
一个系统,效率越高,越整齐,在当时是极大的优势,然而,时过境迁,船大再难掉头。
《日本权力结构之谜》读后感(二):西方的主观思想质询日本“系统”
一切直抒胸臆理性地批驳都是对当事者最为触动的良剂,《日本权力结构之谜》在糅合西方主观理论思想揭示日本现况以严谨逻辑的例举与针砭时弊的阐释其“混乱”的体系,“系统”的“自发且失控”行径背离西方社会在西太平洋中“理想”的日本国定位与作用。作者用诸多工具(政治体制的矛盾、社会的问题与假象、经济的不稳定与衰退、文化被钳制,宗教信仰的缺失、国民的顺从与麻木、民族主义的驱使等)敲打着脆弱的日本,犀利且准确的铺展了日本自战败后的复苏、繁盛、低迷、没落背后的内部谜团。也渐渐张开了日本权利的大网。
作者在日生活25年,深谙日本政治之道。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吸收大量西方先进思想与制度体系,然而在固有的基础上,日本人总会把其“改进”成为自己所能接纳的样子,所以在现今看似三权分立的资本制度的外衣下,实质是半自制团体的权力制衡,官僚、政客各自心有盘算,掌握大权的中央机构并不能行使权利,所以可以看到日本首相并不能制定国家政策,这在与西方国家的外交事务中总会有模棱两可的答案与缺少责任与信任。这种形式与本质的差异被制度化,成为日本官员政客的各种说辞理由与精巧伪装。
以此书诸多视角中结合两个最近的例子来阐述。
责任假象
在2020年2月26日新冠疫情期间,北海道知事铃木直道在记者会宣布全道1600多所小学次日将全部停课,这要比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全国停课令”要早了整整一天。铃木说道:“或被批评反应过度,所有责任都将由自己负责。”这样史无前例的事件引起广泛讨论,期间铃木在民调中的支持率上升到88%,紧急事态支持率95%,紧急事态的发出及让北海道成为模版并非出自中央政府授意,而完全是其个人的想法。
这一事件证明政府官员应有的基本责任在日本社会看来是需要巨大勇气来承担后果的,这似乎成为共识。早在丸山真男的《日本的思想》中提到过日本的无责任体系——有自由、独立判断的个体,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承担起责任的意识的缺失,在制度中的全体主义下的无限责任体系里。这就好比把国家的责任均分给每一个国民,看似都承担着责任,然而每个人的责任也近乎为零。
无限责就是无责任,这种诡辩在日本近现代史中屡见不鲜,在远东军事法庭,日本战犯将罪行的主体责任开脱的令人吃惊;而日本民众也仅仅对于侵华战争表示“陆军”所为而非日本所意。这样吊诡的推责体现了国民整体责任感的缺失而不自知。
文化即政策
“Cool Japan”是日本文化国策的代表,它旨意把“产品输出”变为“文化输出”,以此来促进日本经济的发展。然而日本文化的输出实则被看作是一种亚文化的存在形式(不会成为主流而被必须),它个性与表达在年轻的群体中成为了独立的标签,或调剂原有的文化。但之于经济政策就变得复杂、脱离且被钳制了。
安倍内阁为“Cool Japan”设立了战略担当大臣,投入大量配套资源,成立政府背景的投资基金,只为推动其产业化,但在僵化的体制与内向化的产业传统中,大多只有国民在心甘情愿的买单,把非市场、非盈利化的日本文化作为“软实力”输出的经济效益,让文化政策也走入了不知所谓的泥潭之中。
这本书的内容信息量很大且复杂(日本权力的错综复杂),有很多个人理论与思辨,需要很多时间来消化。其中西方的视角是浓重的,虽然在理性的分析事实的真相,但透露着优越意识主导、督促的忧虑感。如今看来,西方世界统治(武力或思想)的可能在变弱,所谓民主国家的制度社会在塌陷,以一种自恋的形态在崩坏(美国国会大厦被占领)。我们看到日本“系统”也在摸爬滚打,是时候放平心态的来面对彼此的关系与未来,总觉得2020年启迪着什么,希望能让人类共同命运走的更坚实长远。
《日本权力结构之谜》读后感(三):译者后记
(本文为即将上架《日本权力结构之谜》一书的译者后记)
中信的王雪老师最早和我联系这本书的翻译时,我有一个很大的疑问:中信一向以出版“昨天写完”、甚至是“明天写完”的书出名,为什么想到翻译出版一本写在30多年前的关于日本的书呢?
翻译完全书后,我对这个问题似乎有了自己的答案。
世界是复杂的,也是简单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无非那么几条。通过回顾历史,从中归纳、总结出对现时仍有用的内容,对进一步向前具有重要的意义。
与之前的翻译不同,翻译本书对我来说有额外的两个挑战。一个是2001年日本对各省(相当于中国的国家级部)进行了重大改组,一些老省变成了新省(如“大藏省”成为了“财务省”,“通商产业省”成为了“经济产业省”等)。译者在翻译时为尊重历史,需要用书成当年或者出现该名词的背景当年的历史名称。
另一个挑战就更大。本书中出现的大量日文名词以及专有名词,是作者根据日文转译到相应英文发音后给出。一些著名的人名(天皇、首相、大臣等)、地名和专有名词还好办,但有一些人名和法律名字却很难找到对应的日文汉字。
在互联网上搜索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文档,是件很困难的事情。译者不是日语专业,更是增加了难度。
在此,我要感谢多年的同事和好友叶毅德先生(Mr Yap Tong Teck)。他是新加坡人,早年在日本留学,精通中文、英文和日文。叶先生和他太太碇知子(Ikari Tomoko)根据英文原文以及上下文帮助我搜索原始档案,找到了大量名词的原文,为译文的准确性做出了巨大而独一无二的贡献。如果没有他夫妇俩的帮助,本书中文版的准确性和学术性一定会大打折扣。
由此,译者对这些名词的处理方式是,专有名词(包括但不限于人名、组织名、地名、文件法律法规名)的翻译在不影响理解的情况下一般只在给出日文平假名、片假名和英文拼写,而不做解释。这么做,是因为译者相信,直接给出日文写法可以体现某个名词在日本语境中特有的微妙含义(比如“天下り”、“地上げ屋”等)。只有当日文平假名和片假名不利于中文理解,才会进行简短解释。不过译者仍然建议有兴趣的读者根据这些信息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另外感谢好友李勋(Lee Hoon)对书中出现的几个韩语人名的翻译提供了帮助。
我还要感谢对我翻译初稿进行阅读的几位朋友。他们忍受着我译文的佶屈聱牙,做出了批注和修订建议。他们分别是(排名不分先后):吴闻杰,郭瑞卿,叶毅德,蒋文敏。他们可以说是我的“一字之师”。
但不论如何,应该由我对最终译文以及其中不可避免会出现的错误负责。
感谢中信出版社、特别是王雪老师和孙未末老师的信任,将这一本“大书”交到了我的手中。我希望交出了一本合格的作品。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太太Gloria和儿子Peter。翻译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也不是很赚钱的事),是他们的支持和理解给了我动力和信心。
让我用一段之前翻译的小诗来结束我的后记:
书已终章
但求尚佳
唯有一事
尚需交代
谬误归吾
赞誉归汝
任颂华,于任氏有无轩,苏州
2018年10月
《日本权力结构之谜》读后感(四):日本社会的全面政治体检
《日本权力结构之谜》读后感(五):这本书印证了我对日本的一些政治印象
日本和中国真的很不一样,在日本没有人可以说自己说了算。
1.日本推行的是在半自治团体之间分享权力,以此维系这些团体间的平衡。如今,最有权势的团体包括某些政府官员、某些政治派系以及一群官僚商人,还有不少相对小一点的团体,如农业合作社、警察、新闻媒体以及黑帮。所有这些我们都可以称之为“系统”的组成部分,我们用“系统”这个术语是为了将它与政府区分,理由将在后面讨论。没有人最终负责。那些半自治的组织都被赋予有损国家权威的自由决策权,而掌握大权的中央机构却不行使这些权力。
2.日本的相对封闭的岛国形态,让他可以对来自中国或者西方的思想文化和技术进行挑挑拣拣,从中选出那些最能巩固他们地位的技术和看法。
3.日本对权力的委派并未止于幕府这一等级。在13世纪形成了这么一种情况,如历史学家乔治·桑松(George Sansom)所描写的:“政府一个令人称奇的现象是,政府顶层是一位只有虚衔的天皇,他那些残缺不全的职能被一位退位的天皇篡夺,而真正的权力则在名义上委派给一位世袭军阀,但最终运用权力的却是这位军阀的世袭幕僚。”最后这句话说的是北条氏家族,这个家族控制了将军,就像早些时候有权势的家族控制了天皇那样。
这样的安排显然很符合那些有权势之人的想法。几个世纪以来,他们控制着日本。他们中没有人曾认真地试图为自己夺取皇位。考虑到中国存在篡位这种惊人的模式,其中造反成功的将军们不断建立起新的王朝的话,那么这一点就更加引人注目了。但是,权力的向下委派带来的好处似乎总能弥补形式上荣耀的缺失。藤原氏建立起这种统治类型的范式,似乎并没有迫切地要去摧毁这么一个除了名分之外,能为后人提供统治者的所有权力的体制。这种传统对真正的掌权者来说确实有一个明显的好处。如果一个人要让别人拥有名分,而自己拥有与名分匹配的实权,那么此人便不那么容易被打倒。如果真正的权力源头不明,那么如何打击权力也就因此不明。
4.日本从来没有形成中国式的中央集权统治,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都没有实现这个目标。
5.20世纪初开始出现了中央政治权力涣散,到20世纪30年代,因日本不受任何人控制,权力涣散达到顶点,这让一些狂热的中层陆军官员有机会去“劫持”国家。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进攻驻守奉天(今沈阳)的中国军队,开始了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这一赤裸裸的举动并未受到东京政府的谴责,日本陆军于是便认识到可以走自己的路,而且按着自己的想法建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接着激进的官员做出更惊人的举动,他们将日本带向珍珠港,最后又带向广岛。进攻一个比本国工业规模大上十倍的国家,这一举动肯定会被认为是自杀行为,而且一个统一的领导层是不大可能同意这种行为的。实际上,我们可以这样说,陆军和海军之间的争斗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那次突袭珍珠港,此举将美国拉入第二次世界大战。陆军把日本往战争的道路上引,而且想当然地认为海军会管好防务,会抵抗美国的力量;而海军却希望保持自己的权力和作为一个爱国军队的公信力,克制自己不直接表达自己的信条,也就是战争无法获胜——而这个信条在其各级官员中都是被普遍接受的。战争本身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并没有将国内的政治团体团结在一起。但它毫无疑问地加强了官僚的权力,不过,这样的权力没有集中在一个人或者一个机构的手中。
6.明治时期的人们被迫优先处理外交政策,他们一直有着这样的观念,就是有必要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统治机构来与别的国家打交道。
但从1945年开始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根本没必要担心它到底有没有一个政府,因为人们几乎从来就不会要求日本作为一个政治实体而采取行动。人们感觉不到需要外交政策。日本战后第一位重要的首相是吉田茂,他有一个重要的政治发现,就是日本没有必要在传统意义上为国家安全尽力,因为美国会随时准备处理这个问题。后来日本又意识到,政府要为外界所知并得到认可而采取的其他行动,同样可以让美国作为代理人。
日本变得完全依赖美国,不光是为了国防,而且最终也是为了外交。事实上,美国提供了一个外交屏障,让日本可以躲在后面,并在新重商主义贸易实践的帮助下,建立起日本战后强大的经济机器。在中曾根康弘成为首相以前,日本一直对外推行所谓全方位的外交,把这看作意识形态上的创新,实际上只是想对所有购买日本产品、为日本提供原材料的国家表现出八面玲珑的形象。只有在美国容忍日本这么做时,日本才能维持这种姿态。因此,日本与美国非同一般的关系中,包含的远远不止外交帮助、双边贸易以及承诺的军事保护。这让日本在和其他国家的交往时完全优先考虑经济,而很少去考虑政治后果。
7.日本一直都是自民党一党专政,那些反对党只是在假装反对,只是在演戏给外界看。工会运动,农会组织也是一样,都只是被驯服了的反对派。
8.在所有的后援会中,田中的“越山会”具有独一无二的名声,它成为众多其他后援会的典范。它在新潟这一处地方就有92000名成员,维护着一个巨大的分支网络。它除了进行许多别的活动之外,还仔细跟踪葬礼和婚礼在何时进行。直到1975年,新婚夫妇和80岁以上庆生的老人,都会收到由田中亲笔签名的祝贺。这一做法被禁之后,他们会收到电报。而在每个葬礼之上,都会燃烧一支粗大的蜡烛,上面饰以用毛笔写上的田中的名字。越山会安排了许多联姻,至少帮助1万人找到工作。这些得到好处的家庭和亲属对田中都感恩终生,感到欠了他的情。在东京,田中主持工作,每天上午接待数十个到数百个上访者。安排联姻、安顿工作、为老年公民安排周末旅行、帮助访客、解决当地的争端……这些是如今大部分自民党政客日常事务的一部分,但田中完善了大规模执行这些事务的方法。
《日本权力结构之谜》读后感(六):我的读后感
承蒙中信孙未末老师的努力和辛劳,我最新的译作《日本权力结构之谜》终于付印。
这本书应该说是比较被期待的,在豆瓣相关页面标记了“想看”的人达到了1172人。我想,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很多人看过了《菊与刀》——一本受到极度好评的书。但可惜的是,《菊与刀》成书太早(虽然《日本权力结构之谜》成书也不算新),观察的对象有限,对日本投降后的观察只能说是不够的。
那么,《日本权力结构之谜》一书的特点也就呼之欲出了:
成书时间相对较新。作者成稿时间约在1988年底,同时特别应邀为此次中文版增写了第17章《改变与困难的平成30年》。观察对象多、时间非常长。沃尔夫伦在日本待了25年。身为特派记者+外国人的他,显然享有一些“特权”,可以接触各方面的人,更不乏与高层人物的接触,从而可以听到在几杯清酒之后才能吐露的真话。独到的视角和分析。我个人愿意信任作为记者的作者的视角和分析能力。在我翻译和请朋友帮忙进行试读时,我请他们就此发表意见。他们从事不同的工作,更不乏在日本工作生活多年的人。他们的反馈,我可以总结成三点: 过去不知道的事情,看完后知道了;过去/现在不理解的事情,看完后理解了;对未来的日本发展,有了全新的看待方式。我想,一本书如果能做到上述三点中的任何一点,已经可以被称为一本“有用”的书了,更何况本书做到了如上三点。
作为译者,前后全文通读了本书不下4遍,在实体书到手后,又马不停蹄地看了一遍。我不敢说就此对日本的理解有了什么本质上的突破,但我觉得如下几点是我的深刻体会。
首先,一个组织(小到一个作坊,大到一个国家——以下定义同)必须要有一个目标才能建立、生存、发展、壮大、存续。
对于日本来说,这个“目标”就是维持“日本人性”。
说实话,我对一个组织能以一个如此抽象的东西作为目标,是很意外的。不过,日本历代的政府显然找到了比较“完美”的落地方案:将“日本人性”具体化,用“和(wa)”作为最终的追求,从而训练出一批对此忠诚并不遗余力地加以宣传、贯彻、实施的官僚和政客,再将他们紧紧地与与之相关的实践、利益绑在了一起。从而最终达成在没有任何“终极真理”、没有任何“终极命令官”的条件下,国家机器被调动被激发起来,在经济上得以全面发展、扩张、侵入的结果。
在西方政体中,我们很容易找到这样的“终极真理”和“终极命令者”。但作者明确并一再指出,在日本不存在这样的东西。
一个自然的问题是:那么到底是什么维系了日本政府,同时赋予政府以“正当性”?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跳出去一下。讨论在极端混沌情况下,高度组织的结构产生的问题以及这样的结构的一些特性。
在宇宙这样的大尺度下,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常见的——否则我们就看不到银河系、太阳系、我们的地球以及众多的生物。这是在极端混沌前提下,高度组织能够自发出现的极好例子。
很早之前我看过一本《混沌——开创新科学》,一直以来有这样的想法:这样的情形应该可以出现在非自然科学领域——自然也包括政治领域。
日本也许正是这么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表明的是,在没有“终极真理”(没有规则)、没有终极命令官(不存在外部干预)的情况下,一个政府是可以形成的。
以上从一些我觉得我能掌握的原理出发,解释了这样一个政体存在的可能性——如果谈不上必然性的话。
让我们回到之前的问题:到底是什么维系了日本政府,同时赋予政府以“正当性”?
一个常规的政府,其合法性来自于超越政体的法律体系、人民做出的选择、超越性的“信念”(如宗教)。作者尖锐地指出,在日本这三样东西都不存在:没有法律体系(或者说法律无法被实施)、人民没得选择、也没有一个宗教。所以,其实我们可以说,日本政府很脆弱、几乎没有“正当性”。
可是这个政府已经存在那么多年,为什么?
我觉得,一个原因是这个政府在二战后很大程度上是由外力建立起来的。而正如作者指出,日本民族对强于它的势力,一直有着敬畏。这种敬畏转为变成对其“创造”出来的一切东西有一种崇拜。
另一个原因,在于二战后共产主义的蓬勃涌现,使得美国调整了整个西太平洋战略(以及对日战略),从遏制军国主义+重建民主变成遏制军国主义+遏制共产主义。日本战前和战时政府中的众多顶级官员战犯(其中就有前几天刚创造日本首相任职最长记录的安倍晋三的外公岸信介)被刻意安排无罪释放并进入了战后的新机构重新执政。
在我看来,这样的刻意安排也许在事实上给日本政府制造了一种因连续性而带来的正当性。而普通日本人民也可能因为这样的连续性而认可了其稳定性、一贯性:既然一切照旧,那么自然一切OK。
这样的情形是有类比的。比如,我另外一本还没出版的译作(初定译名《帝国与蛮族》)中讲到,欧洲的很多新兴国家就要通过追溯其历史而确立对某一块领土的合法占有性。惟其如此,这些国家的人民才能心安理得地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并接受统治阶级的领导,并捍卫自己和国家的利益。
==========
说几句题外话。
这本书到底是不是如豆瓣某书评所言,是一本“批判日本的书”,而不是一本“解构日本”的书?
我个人对这本书的判定正好与上述相反。
首先,这本书进行了很详细的所谓政权结构分析,甚至涉及到了很底层的政府机构和黑社会,并分析了这些“组织”间的关联关系。以作者25年在日经历作为背景,这样的分析我相信是到位的、精准的。
其次,如果我们从“批判”最广义的定义出发,自然这本书可以称为“批判”;如果从“批判”比较狭义的定义出发,那么我觉得将这本书认为是“批判”可能略微过了一点。毕竟,讲出事实和自己的判定,离真正狭义上的“批判”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
那么,请允许我冒昧地总结一下:
日本,因战争而屈服,并接受了外来势力以日本历史为参照而实施的相应改造,调整了日本的“优先级”。日本和外来势力由此构筑起相应的初始组织。之后,通过系统性的(虽然是没有中心的)剥夺选择、固化思想、可能无意识但利益一致的协同,完成了一个类似自组织那样由上到下、由大到小、由宏观到微观的精密自相似结构。我能想到的一个合适的形容词就是“混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