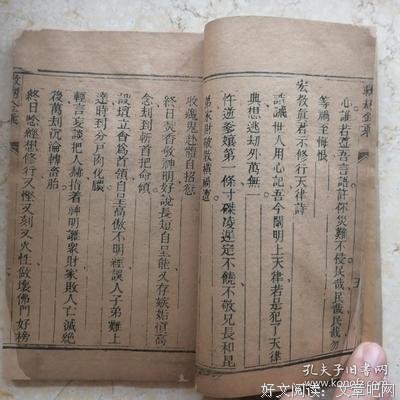
《救劫》是一本由陈进国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98.00元,页数:43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救劫》精选点评:
●题材难得,资料丰富,术语堆叠,“内卷”不妥。
●材料丰富,田野考察的部分读起来并不晦涩。作者试图为旁门正名,全书导论起码占了三分之一,调门起的很高,但可惜后面许多关键处作者又有些草草,罗教复兴一段着实精彩,后半部分侧重点在东南亚。不过若从旁门的角度看福建真的是个极其诡异的存在,有太多欲说还休的“不能言”。
●材料很好,但充满野心的导论和其中的理论建构显然是不成功的。
●认真而有新意的著作
●为道门正名的诚意之作。导论130页,将近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一。章节结构和内容处理需要进一步调整。同时太中华文化本位化,引赵汀阳也让人觉得很怪异。其实可沿着杜赞奇、宗树人、王大为等人开创的路子接着讨论。
●晚近新兴宗教如何发生、与社会-政治相调适,这一点有趣;不过引出民族-国家的话题,似乎有些鸡肋。其中可能也有作者自身的意识形态立场吧…另外,全书都把「范纯武」写作「范存武」了0.0
●导论视野开阔,使后面的案例分析具有了共通的更宏观视野
●这种书我为什么要买来看。。(全书最精彩在那个黑洞的比喻。三星半吧。
《救劫》读后感(一):民间教派的人类学视角
晚清以来席卷中国的民间教派宗教一直是本土学界未能充分展开讨论的一个话题,一方面有其意识形态上的约束,比如民间教派长期被称为“会道门”、秘密教派、秘密结社等,另一方面也有是否可以视其为宗教以及用何种方法来研究的纠结。虽然意识形态的偏见尚未完全廓清,但至少一道窄缝已经慢慢开启,陈进国的《救劫:当代济度宗教的田野研究》(以下简称《救劫》)一书的出版就是证明之一。至于民间教派是否可以称为宗教,自从杨庆堃提出“制度性宗教”与“弥散性宗教”的分类后,大体上也已经解决了,不同的研究者可以在从“制度性”到“弥散性”的连续光谱上各自寻找其定位,如欧大年(D.Overmyer)常常把民间教派归为弥散性(民间信仰)的一端,而陈进国就视其为制度性的一端,或正在向制度化演进。而在以什么视角来讨论民间教派的层面上,欧大年是研究中国民间教派最绕不开的人物之一,他在比较国际学界对欧洲民间教派和中国民间教派的研究时,委婉地批评了“以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为背景”的研究取径,认为这样的研究是把宗教运动简单化约为社会运动,把宗教视为教派领袖为实现政治目的而利用的一种手段,没有承认宗教信仰本身具有塑造事物的力量。换言之,研究民间教派,应该意识到这是人类在追求一种神圣现实,对民间教派的研究应该让它回归到宗教自身的脉络中来(欧大年:《中国民间宗教教派研究》,刘心勇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欧大年持这一观点,一方面固然因为他是个宗教学者;但另一方面,是为了替中国历史上的民问教派运动去污名化,他认为历史上的民间教派实际上大多是和平、非秘密结社、没有明确社会政治纲领的宗教运动本身。
同为宗教学者,同样抱着为民间教派运动正名的目的,陈进国却选择了被欧大年批评过的这个方向,只是更准确地说他选择的是宗教人类学的进路。表面上看,宗教人类学和宗教社会学的具体旨趣、研究方式、理论关怀虽然不一样,但究其本质是一致的,两者关心的不是信仰内容和宗教体验本身,而是信仰实践、宗教体系如何镶嵌在社会中,受到社会的建构,又反作用于社会,也就是它们在社会中可见的“生与死”。更进一步说,宗教人类学研究宗教,实质是把宗教视为一个趁手的研究对象或范畴,真正目的是借此透视宗教所由生成的那个社会和文化。在这个意义上,作者的方法会奏效吗?一方面,宗教学者的人类学探索究竟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洞见,让我们同情式地理解这些历史上“危险”的教派团体在当代生活中的命运?另一方面,他历十数年之功搜集到的这些不同地区的民间教派个案,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有效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历史及变迁?
二
《救劫》的结构相当清晰,除了篇幅巨大的“导论”以及相对简约的“结论”外,主体内容是五章,分别讨论了闽西客家地区的罗祖教、闽东的儒教道坛、香港金兰观新道教、台湾一贯道以及南洋空道教这五个当代民间教派。五个案例又各有侧重:罗祖教集中考察了民问教派与地域崇拜体系的相互嵌入关系,发现民间教派借助于地方社会庙宇网络(后者属于民间信仰)的中介作用,实现地理扩张以及加强自身的综摄主义(syncretism)色彩。儒教道坛关注“神启权威”在民间教派的当代进程中所起的核心作用,但“卡里斯玛”式的权威必须与本地乃至遥远的知识及科层制精英合作才能让民间教派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金兰观重点讨论民间教派的神道设教功能,神道设教包括两个面向,一是通过神启,二是自我修行。金兰观虽然位于香港,但其在宗教及政治认同层面的正统化追求却相当突出,这也是道堂基于实践理性的神道设教的自然结果。一贯道主要分析民间教派与“位育”教育的关系,一贯道通过进阶学制,充分结合宗教性和日常性的修行生活,不断培养信徒的道德人格和灵性生命,从而完成正统文明重建。空道教则侧重于探讨民间教派在传播过程中如何建立起跨国、跨境性的区域网络世界,其早期兴盛得益于以“戒烟(即鸦片)治病”为核心的本土文化复振追求,晚期则陷入内部教名、教权及经济纷争,乃至陷入更为深重的合法性危机之中。《救劫》将民间教派还原到社会文化中来讨论的做法颇为纯熟,而且踏勘田野、收集材料的功夫,对不同教派之分析的针对性,以及对华人民间教派的区域性视野和整体性把握,都達到了一定的高度。例如,目前南洋新、马、泰三国尚存空道教道坛一百二十余所,作者竟一一到访并详加记录,其用心用力之勤,令人叹服。
作者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框架集中地反映在导论部分。我们来讨论其中一些最为核心的概念范畴,包括:一、何为指向救劫的济度宗教?二、作为本土文化复振运动的教派宗教;三、宗教内卷化。
济度宗教与救劫。作者使用“济度宗教”来统称近代民间教派宗教,“济度”二字有其中文语义学上的思考,以此来替代既有文献所使用的救世、救赎等概念。作者认为“救世”一词偏于“立外功”以及社会性的一面,“救赎”一词偏于“修内果”以及个体性外在超越的一面,而“济度”一词则可以兼及普遍救世(济)与个体救赎(度)两个方面,甚至还包括以气功团体为代表的身体修炼功能。济度宗教普遍以释、道、儒三教合一为立教主体,因此具有综摄主义的特征。按照杨庆望的看法,民间教派主要混合佛教的神学理论、道教和其他传统宗教的法术仪式,以及从儒家得来的伦理系统(杨庆望:《中国社会中的宗教》,范丽珠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二00六年版)。欧大年也指出民间教派调和各种信仰,其中佛教因素的影响是压倒性的。在民间教派形成之初起到核心推动作用的,正是佛教的劫期观念。“劫”既是一种循环创世的时间范畴,如过去、现在和未来即称为“三劫”,后来很大程度上又从字面上被广泛理解为灾变劫难。“救劫”正是绝大部分济度宗教之根基性的创世神话的中心母题,也就是在末劫阶段,天上众神下凡应世救劫或化身为创教者或教派领袖代天宣化。但本书中“济度”所对应的英文概念是Salvationism或Soteriology,仍然不脱西方宗教中超乎世界的全能神之终极救赎的含义。尽管如此,陈进国对“济度宗教”概念的提炼以及对“济度”与“救劫”两个核心关键词的互文式用法,仍然较具开创性,显示了欲以精当的本土化概念来解释中国民间教派宗教运动的追求。
教派宗教是本土文化复振吗?晚清民国恰逢“千年变局”,民间教派兴起是为了因应西来文化冲击和现代民族国家新式意识形态的规训,加之主要从传统的儒、释、道三个源流中吸取资源,因而把民间教派宗教理解为一种本土文化复兴运动似乎顺理成章。作者区分了外来文化主导型、传统文化主导型两种形式,其下又各有灵性型、理性型、混合型三种,合共六种本土运动的形式。这种“理想型”之范畴区分,简直包罗万象,甚至拜上帝教、五四新文化运动、基督教灵恩派等都可以分别被界定为以外来文化为主导的灵性型、理性型和混合型的本土宗教运动。这一定位是否妥当,当然是一件见仁见智的事。至于清末民国以来的民间教派宗教,则大体都可归入以传统文化为主导的形式。作者认为,这种文化保守主义力量支配下的教派宗教,虽然也呈现某种包容性和开放性,但由于缺乏自我否定和批判精神,会走向衰微一途。但教派宗教的创建本身,表达了一种追求正统化、文明化的诉求,强化了中国宗教谱系的边界,并且参与培育了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意识,成为与近世西方文明对话的主体,这在港台地区及东南亚的教派宗教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民间教派宗教走向衰微的另一个原因是其自身的内卷化困境。内卷化概念被运用于宗教领域分析,这是一个颇为难得的灵感。大致而言,宗教内卷化指的是,在信徒数量、教派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宗教信仰质量却没有相应提升甚至边际效益逐渐下降,宗教团体越来越僵化芜杂、缺乏可持续发展机制乃至陷入合法性危机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作者从教典教义、仪轨实践、神明体系、组织形态、社会功能、宗教传播等方面分析了宗教内卷化的成因及过程,并且借用台湾一贯道的案例,指出教派宗教走出内卷化困境的核心途径是实现权威转型,即从教派领袖的卡里斯玛权威向传统权威、法理型权威或后两者结合型权威的转变。
换言之,在这里我们注意到了作者观念上的多种内在纠结:既把民间教派宗教目为复兴中华文明的本土文化运动,又认为其未来在于韦伯式的理性化、制度化的现代转型;既忧心于内卷化困境导致的教派宗教的危机,又欢欣于民间教派宗教内在的增长极限可以缓解政权对其的挤压。但通过上述讨论,作者成功论证了近代以来的教派宗教有其和平化的宗教诉求和自身的生命周期。
三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华人的民间教派宗教,而所容纳的个案又涉及大陆、港台和东南亚这样的跨地区、跨国网络,我们面对的核心问题是:从教派宗教这个维度呈现出来的中国性(Chinese-ness)在当代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也即什么构成了中国社会文化的一体性?
赵汀阳曾经提出以“逐鹿中原”为中心的“旋涡模式”来描述中国大一统政治文明之生成的动力学;同时他把秦至清代的中国政治体系描述为一个“内含天下的中国”,意即大一统政治体系之内仍容纳了以多元文化、族群、政治生活为特征的天下观念;最后他还主张“作为方法论的中国”(当然,沟口雄三更早也提出过“作为方法的中国”),意思就是说,理解中国文明的存在方法论,就是要把中国视为一个在天命之下的持久的“以变而在”(being in becoming,赵汀阳:《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中信出版社二。一六年版)。
陈进国巧妙地挪借或化用了赵汀阳的思想资源。一方面,他把大陆地区民间教派的发展历程描述为一种“救劫旋涡”模式。近世以来为数众多的民间教派都是基于“救劫”这个中心母题创生及展开的,而所谓的“劫”,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文明之“道统”在晚清民国以来所遭遇的危机。而由民间挺身而出来拯救道统,实际上也是这个危机本身的一个历史后果,即道统的承载者已经从“君相”下移到“师儒”,再进一步下移到“庶民”。这个救劫旋涡的持续吸引力,使得民间教派在历史上此起彼伏,始终处于一个不断生成、逸出、消亡以及再生的动态过程。在此他把教派宗教置于作为整体的中国文明或社会背景之中来讨论,并逻辑自洽地解决了教派宗教的发生学和动力学问题。另一方面,陈进国把教派宗教的跨地区、跨国传播,归结为一种“外延中国的天下”模式。虽然“外延中国的天下”对“内含天下的中国”的化用本身甚显生硬,但仍然可以理解作者的用意。这里指的是,随着华南汉人迁居海外,教派宗教也随之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边界之外开枝散叶。境外的教派团体通过“分灵、割香、进香、谒祖”等形式与中国祖庭的教派宗教维持联系,更由于其所遭遇的政经环境与大陆不同而有不同的发展历程,最后成为大陆教派宗教的一面镜子乃至一颗火种,从而使海外华人地区成为中华信仰版图的一部分及其历史性的来源之一。换言之,教派宗教的生成动力,在中心是旋涡模式,在周边是迁流模式,但共同构成了整体性的“信仰中国”。
毫无疑问,陈进国在这里触及了历史中国的一体性问题。这个问题指向的是,如何理解他归纳出来的教派宗教的“家族相似性”现象(需要指出的是,在本书中他关于家族相似性的理解并不完全准确,因为这个概念本身指的是各要素之间部分交叉、重叠的关系,可以表达为AB、BC、CD、DE……但并不存在所有要素共同的特征),也即民间教派如此一致地以“救劫”为母题,以儒、释、道三教合一为源流,必然与其所由生成的中国文明的一体性相关。但在《救劫》中,作者只是粗泛地论及晚清以降的外来文明冲击及国内的意识形态变革,以此作为展开个案的总体背景,而且全书提供的五个个案,只有表面上的地域差异性与理念一致性,而未触及从表征多样性中挖掘出与结构一体性的深层关联,尤其是没有从民间教派宗教实践的细节来入手。换言之,《救劫》并没有呈现出足够细致的民族志“深描”,显得没他自己所声称的那么“人类学”。就如何认识中国社会的一体性,汉学人类学和历史人类学已有不少出色的田野观察的示范。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弥散性的民间信仰方面,而民间信仰往往被认为更碎片化。
弗里德曼(M.Freedman)第一个提出了涵括精英宗教和民间宗教的“统一的中国教”的論断,他的理据主要落在中国教的观念基础上,即基于“天命”的“阴阳五行”学说,其中天命是道德秩序来源,阴阳五行是天命的运行和呈现。各地的神祗谱系和仪式实践尽管多样,但都服从于这个根本原则。桑高仁(P.Sangren)为弗里德曼的根本原则找到具体可见的证据,他在同意“阴阳说”是中国宗教普遍深层结构的基础上,指出是“朝圣”(进香)把文化的大小传统联系起来,“在中国,朝圣是一体化的重要进程,它在连接基本的宇宙观和文化定义上的社会一体性之间扮演了重要的仪式角色”。而华琛(J.Warson)的讨论更为别出机杼,他曾经从两个角度出发来讨论民间信仰的一致性问题:一是从各地丧礼中发现共通的步骤和程序;二是帝国有一套册封地方民问神祗并且确立仪式标准化的做法。比如士农工商乃至妇女、海盗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来拜妈祖,不管他们信仰的内容有多不同,只要祭祀的外在形式合规就行了。也即官方首要强调的是正统实践而非正统信仰。在这里,丧礼的程序和祭祀的外在形式都是从田野观察中得来并对其展开历史分析的。
对田野材料的历史分析是科大卫(D.Faure)等人的拿手好戏。华琛的观点影响甚巨,但遭到的反思也很多,主要集中在对标准化效果的质疑上。科大卫与刘志伟为华琛做了很多深刻的辩解,认为华琛并没有否认民间传统的差异性与延续性;他们认为地方多大程度上接受包括国家在内的外来标准化,必定有其自身的能动性在;而且,华琛讨论的是村民自己观念中认为的是否符合正统,而非客观上是否符合正统。在这里,他们延伸了一个来自华德英(B.Ward)的重要观点,那就是,乡民的“意识模型”分为多个层次,其中包括“对自我的认知”与“对大一统的认知”,尽管乡民都会努力拉近“对自我的认知”与“对大一统的认知”之间的距离,来实现正统化的追求,但由于不同地方、不同历史时期用来定义大一统的标签(label)往往不一致,导致正统化的呈现效果并不一致。比如在珠江三角洲表达正统性的标签是宗族,而在莆田则更多表现为地方神崇拜,这与两个地方真正纳入“化内”的历史阶段不同有关。因此对标准化/正统化的理解和分析,不能抽离具体的历史时空(科大卫、刘志伟:《“标准化”还是“正统化”:从民间信仰与礼仪看中国文化的大一统》,载《历史人类学学刊》,第六卷第一、二期合刊)。按照科大卫的经验,这些具体历史时空中的“礼仪标签”之重叠,在今天的田野调查中都可以观察到,比如建筑特征、文字传统、神祗故事、乡村仪式。最精彩的例子包括,科大卫注意到福建惠安女进庙时要在腰部戴上围裙,由此推测历史上惠安女的穿衣习惯可能是露出腰部。衣着的习惯改变后,礼仪的要求仍在,于是围裙和衣服就重叠了。又比如,香港新界的打醮仪式中,道士拜“三清”,呈现出一种有体系的正统性;村民们只关心他们相信的地方神祗,但认为道士的举动对于社区净化也有帮助。这两套仪式在同一个时空中举行,祭拜者也都认为他们是在进行同一个宗教活动(刘泳斯:《理解民间宗教:乡土中国的内生逻辑》,载《文化纵横》二0一六年第二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随处可见的“礼仪标签”重叠,正是民间宗教纳入社会一体性的绝佳例证。
讨论至此,我们或许可以进一步反思“救劫旋涡”对于分析汉人民间教派运动的合用性。赵汀阳的“旋涡模式”所针对的是历史上围绕中原中心、不同文化及族群问的互动,虽有融合,亦有析出,互动的框架始终不易;而当我们面对已经充分认同为汉的群体的内部宗教行为时,事实上,我们所见的是在同一套体系内,不同区域、不同阶段的人群依其地方或时代特征,各自选取趁手的“标签”,比如民问庙宇网络、神启权威、神道设教、位育教育以及戒烟治病等,来共同实现救劫的目标。究竟是旋涡,抑或平行,殊难定论。
尽管存在着宗教学进路和人类学进路的宗教人类学之间的微妙分野,黄剑波认为中国的宗教人类学无疑应当同时是宗教研究、中国研究,也是人类学研究。以此衡之,陈进国已经做出了值得肯定的探索:顺着赵汀阳的思路,他将“济度宗教作为方法”,让我们看到了民间宗教本身的生存与困境,据此反思已有對中国宗教谱系的认识;并以此为维度,反思了中国的历史和文明在当代的复兴方向;就人类学的层面而言,《救劫》一方面已经展示了其理论雄心和创见,另一方面,对于民间教派与中国社会一体性的关联,则尚待真正意义上的“深描”并进一步展开精细的历史分析。总而言之,当我们讨论不同地区的民间教派,实际上是在花样翻新地一再回眸“何为中国”的古老话题。
《救劫》读后感(二):转载丨魏乐博、庄孔韶、林美容评《救劫》
Preface Ⅰ Robert P.Weller : Significance of Salvationistreligions
Professor Chen Jinguo’s book on salvationist religions comes at an important time.Such religions began growing rapidly in China roughly a century ago.Even though they lost much ground on the mainland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y continued in Taiwan, Hong Kong, and among overseas Chinese, especially in Southeast Asia.Today they are once again growing significantly.If we take the term “salvationist religion” very broadly, as a concern with curing the ills of the present and creating the possibility of a kind of heaven on earth, the phenomen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certain kinds of Christianity and to the rapid rise of humanistic Buddhism.That is, it constitutes one of the most creative and rapidly growing cultural developments in modern Chinese life—something that is important for all of us to understand more clearly.It has been a long time since we have had any sophisticated broad overview of these groups, and much has changed in the years since the pioneering work of Daniel Overmyer and others.In addition, we have never had a general study of general range of Chinese salvationist groups based on the kind of ethnographic depth that Professor Chen offers here.This book thus offers a very welcome and important addition to our literature.Of the many significant insights that this book offers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salvationist religion, there are three that I would particularly highlight here.First, although the rise and success of these groups cannot be understood apart from China’s contact with global forces, all of them are fundamentally indigenous.That is, they developed in Chinese societies, at the hands of Chinese people, in part as ways of bringing Chinese thought into dialogue with broader global events.It is thus no surprise that we see a constant dialogue of Confucian, Buddhist, and Daoist ideas as they are reworked to face new problems.The frequent use of spirit mediums in many of these groups further encouraged rapid change and experimentation with new ideas, because such direct communication with spiritual powers carries enough charisma to make change possible.We can look even more broadly—extending the set of “family resemblances” that Professor Chen uses to identify these groups—to see some of the same indigenizing forces at work in some Chinese Christian movements of the Republican Period, in Kang Youwei’s hope for a 孔教会, or in the humanistic Buddhist hope, beginning at around the same time, to create a “Pure Land” on earth. China was thus not simply a victim of globalization and imperialist ambition, but an active player in the attempt to create a new spiritual world.Second, these groups are completely modern.Such a claim may seem odd given how these groups recall ancient systems of religious thought, and how they make use of mechanisms like spirit possession or other forms of divine revelation.In spite of this, their modernity consists in just those traits that Max Weber and others consider the hallmarks of modernity: placing the idea of an autonomous individual as the basic unit of action, seeing the world as subject to universal principles rather than communal ones, creating broad bureaucratic structures, and striving to foster rationalized and orderly forms of knowledge.They bear a certain amount of resemblance to what the philosopher Erik Voegelin called “modern Gnosticism,” by which he meant movements based around the idea of a direct access to truth, the important role of a privileged spiritual elite, and the possibility of creating a perfected realm on earth.Even though the term recalls a far earlier Christian movement, Voegelin saw these movements as absolutely modern, and indeed as having influenced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global movement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In this sense too, these salvationist groups offer a uniquely Chinese response to a global conversation.Finally, I find Professor Chen’s idea of religious “involution” (内卷化) extremely useful.It helps to explain why, with so many of these groups, we see the development of ever more elaborate spiritual systems of meditation and cosmology, the emphasis on secret knowledge, and the clear demarcations of membership (in contrast to more traditional Chinese forms of religiosity). He has identified a phenomenon that occurs across a wide range of salvationist group and allowed us to see it as a sensible adaptation.Many of th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world-wide anthropology of religion have concerned Christianity outside the West—a topic that had previously been much neglected by the field.With Professor Chen’s book we have a widening of perspective beyond Christianity, which offers us a greatly enhanced view of how religion can adapt itself to modern times without simply giving up its indigenous roots.序二-庄孔韶:济度宗教的过化现象与类家族主义形态
为了深入了解作为民间教派的精神传统,进国君行走闽粤赣、港澳台,以及更大范围的东南亚华人地区做田野工作,侧重于诸种教门“济世度人”的主导理念,使读者把握了一个巨大地理范围的华人民间信仰实况与特征。这在学术上已经颇具建树。单纯从信仰本身而言,人类学的基本出发点是相信民间信众精神需求与布道的真诚,随后才会有对教门与信众的长久传统的理解。尤其是在基层社会,民间信奉大体无权所依,他们的内心却真挚如一。我们看到近年来为数不少的人类学著作,总是无限扩充“权力”原本范畴的外延,把“权力”看作无所不能和无所不包。然而,当我们换一个视角,就不得不思考人类精神、情感、意义与信仰的感染性的动力源泉,并不是仅仅一个“权力”使然。我在几年前阅读了早期儒学的一些文献,思考尚在弱势时期的儒学重在“自我教化”与“为仁由己”,导致了非强力推进型的、如墨渍弥散式的“过化”现象。当时,从国学中抽取“过化”一词推陈出新,原是为了和文化过程中常见的“濡化”“教化”“德化”以及“涵化”等术语及其含义进行比较。其中,早期圣贤儒者“过化”之所以感人而获得认同,还关乎他们出使布扬和讲学的态度、德行和内容。这些方式还借助文字刻印交互传布,而最终成为中原儒学得到大面积认同与成功“过化”的主要特点。从《孟子?尽心》提炼出的成语“过化存神”便是参与者被由衷感化的整体性动力。如果我们从公安派袁氏三兄弟提出的“性灵”、“真”和“趣”之关联含义进一步思考,无论是文学、诗歌、音乐和宗教,都连接着由衷感染和被感染的“过化”佳境。当我捧读进国君的这本用心之作时,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于是,我们讨论了各种教门同样呈现的如墨渍般洇开的“过化”与“信仰感染”现象,并尽可能在宗教内外加以比对。我们在电话里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华人教门的组织人类学观察视角。进国君著作中的海内外多种教门组织,实际上展示了“作为文化的组织”的存在特征与意义。台湾学者早年提及的“泛家族主义”和笔者团队十余年前做流动人口和公共卫生项目中涉及的汉人社会多类“类家族主义”的组织惯习,甚至可以推及历史上的捻军、四川的袍哥、中原的红灯区,直至今日进城打工的民工组合,等等,都显示了大体意义上的华人社会习惯采纳的“家族主义”模拟框架。进国君告诉我,他的下一本宗教人类学专著,就准备扩充本书第五章的南洋真空教研究专题,以其布道环境、组织、信条、理念与实践过程,展示民间教门的信仰意义、“类家族主义”形态与现代变迁,以及“心所存主之处”何以“神妙莫测”之原委解说,或许是宗教学与人类学相结合最为期待的产品,尽管我们已经从这本书中预见了某些端倪。进国君这本大书中的诸多教门信仰、组织与实践框架的类同性与多样性,文化的惯性与现代性影响,也许是当今信仰“过化”过程的变通与转换现象。然而在这其间,书中的善男信女既完成了个体对日常生活世界的意义与价值追求,也实现了整合外在社会秩序的夙愿。 庄孔韶 2016年6月17日北京景山住家
序三 林美容:万水归宗,普济群黎
陈进国博士的这本新书,有幸先睹为快,不禁赞叹。其实这本有关教派宗教的著作,并非我的专长领域所能擅自美言,不过因为我做过台湾斋教的研究,也写过高雄县的教派宗教,勉强算是沾得上边。过去有关教派宗教研究的多是历史学者,人类学者David Jordan(焦大卫)跟宗教学者Daniel L.Overmyer(欧大年)合作,写过有关台湾的鸾堂的研究。陈进国博士有关教派宗教的研究师承马西沙,自然在教派宗教的研究上是名门正宗。而他这本书,广泛地调查了福建、广东、江西、香港、澳门、台湾,以及东南亚华人的教派宗教,这本书主要便是他的有关教派田野的呈现。对于教派宗教这样某种程度具有秘密性,跟民间信仰相对照,有许多不公开的仪轨、神圣空间等,也背负着许多历史的原罪或阴影,教派宗教的调查并不容易。但是,陈进国博士的书引领我们了解了客家长汀的罗祖教、闽东的儒教道坛、香港金兰观新道教、台湾一贯道和南洋的真空教,特别是在东南亚有关真空教的踏查,戮力于珍贵的基础资料的搜集,极为难得。如果宗教人类学旨在对宗教人与宗教场所的田野考察,本书呈现的田野幅度之广,堪称一绝。本书的特色是以“济度宗教”的概念来统整所调查的诸教派宗教。教派宗教自来有“三期末劫”的思想,“三曹普度”,济度众生,以“济度宗教”来综摄之,自不为过。不过我个人浅见,救赎或是济度几乎是所有宗教必然有,也是共通的思想,不仅教派宗教为然。佛教的“自度度人”,道教的“拔度”,民间信仰的“救世”,基督宗教的“救赎”,可说任何宗教都有它的救赎观。何以要用“济度宗教”名之,似无法凸显教派宗教的特性。所幸书名主标“救劫”,点睛式地化解了读者这样的疑问。 陈进国博士的文笔精湛有创意,常发新词,不仅能创词(“济度宗教”一词可见一斑),而且能把人们记忆中的过去惯用名词,不管是庶民的或是学术的,均能朗朗上口,添增不少历史感。我特别在阅读导论的时候,感受到他描绘的田野场景,历历在目,看来他记忆力好,田野笔记记得细,田野的功夫了得。即便如此,书中对学术典籍文献的充分利用与掌握,也是不可多得的。一般而言,长于田野的,常常拙于文献。或许是历史学专业的背景训练,以及他本身阅读广泛,帮助匪浅。 当今的教派宗教,自明代罗祖以来,迭经变化,主张“三教合一”,唱言“三教同源”,甚至也产生了“五教合一”的说词。无论如何,民间教派有浓厚的中华思想,万法归一,一归于中,也因此产生了许多创新性的思想。在这点意义上,如同书中所言,是一种本土运动或是本土复振运动,并不为过。我个人觉得,这种创新性的思想是中华文化的活水灵脉,却因为过去的历史而无端背负了“秘密宗教”或“秘密结社”的色彩,在发展过程中屡遭跌宕。我在读本书的导论时,感受到作者以中国为中心,走访教派祖庭,横跨海峡两岸,纵横港澳与东南亚,踏查教派道场,从各个面向探讨民间教派的相关课题,莫非一念至诚,中国本土理当是中华思想最能存续的所在。所以他思量再三,勇振文毫,大有再兴教派祖庭文化之气慨。 林美容 2016年5月写于台湾花莲
《救劫》读后感(三):魏乐博、庄孔韶、林美容序言三篇
Preface Ⅰ Robert P.Weller : Significance of Salvationistreligions
Professor Chen Jinguo’s book on salvationist religions comes at an important time.Such religions began growing rapidly in China roughly a century ago.Even though they lost much ground on the mainland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y continued in Taiwan, Hong Kong, and among overseas Chinese, especially in Southeast Asia.Today they are once again growing significantly.If we take the term “salvationist religion” very broadly, as a concern with curing the ills of the present and creating the possibility of a kind of heaven on earth, the phenomen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certain kinds of Christianity and to the rapid rise of humanistic Buddhism.That is, it constitutes one of the most creative and rapidly growing cultural developments in modern Chinese life—something that is important for all of us to understand more clearly.It has been a long time since we have had any sophisticated broad overview of these groups, and much has changed in the years since the pioneering work of Daniel Overmyer and others.In addition, we have never had a general study of general range of Chinese salvationist groups based on the kind of ethnographic depth that Professor Chen offers here.This book thus offers a very welcome and important addition to our literature.
Of the many significant insights that this book offers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salvationist religion, there are three that I would particularly highlight here.
First, although the rise and success of these groups cannot be understood apart from China’s contact with global forces, all of them are fundamentally indigenous.That is, they developed in Chinese societies, at the hands of Chinese people, in part as ways of bringing Chinese thought into dialogue with broader global events.It is thus no surprise that we see a constant dialogue of Confucian, Buddhist, and Daoist ideas as they are reworked to face new problems.The frequent use of spirit mediums in many of these groups further encouraged rapid change and experimentation with new ideas, because such direct communication with spiritual powers carries enough charisma to make change possible.We can look even more broadly—extending the set of “family resemblances” that Professor Chen uses to identify these groups—to see some of the same indigenizing forces at work in some Chinese Christian movements of the Republican Period, in Kang Youwei’s hope for a 孔教会, or in the humanistic Buddhist hope, beginning at around the same time, to create a “Pure Land” on earth. China was thus not simply a victim of globalization and imperialist ambition, but an active player in the attempt to create a new spiritual world.
econd, these groups are completely modern.Such a claim may seem odd given how these groups recall ancient systems of religious thought, and how they make use of mechanisms like spirit possession or other forms of divine revelation.In spite of this, their modernity consists in just those traits that Max Weber and others consider the hallmarks of modernity: placing the idea of an autonomous individual as the basic unit of action, seeing the world as subject to universal principles rather than communal ones, creating broad bureaucratic structures, and striving to foster rationalized and orderly forms of knowledge.They bear a certain amount of resemblance to what the philosopher Erik Voegelin called “modern Gnosticism,” by which he meant movements based around the idea of a direct access to truth, the important role of a privileged spiritual elite, and the possibility of creating a perfected realm on earth.Even though the term recalls a far earlier Christian movement, Voegelin saw these movements as absolutely modern, and indeed as having influenced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global movement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In this sense too, these salvationist groups offer a uniquely Chinese response to a global conversation.
Finally, I find Professor Chen’s idea of religious “involution” (内卷化) extremely useful.It helps to explain why, with so many of these groups, we see the development of ever more elaborate spiritual systems of meditation and cosmology, the emphasis on secret knowledge, and the clear demarcations of membership (in contrast to more traditional Chinese forms of religiosity). He has identified a phenomenon that occurs across a wide range of salvationist group and allowed us to see it as a sensible adaptation.
Many of th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world-wide anthropology of religion have concerned Christianity outside the West—a topic that had previously been much neglected by the field.With Professor Chen’s book we have a widening of perspective beyond Christianity, which offers us a greatly enhanced view of how religion can adapt itself to modern times without simply giving up its indigenous roots.
序二-庄孔韶:济度宗教的过化现象与类家族主义形态
为了深入了解作为民间教派的精神传统,进国君行走闽粤赣、港澳台,以及更大范围的东南亚华人地区做田野工作,侧重于诸种教门“济世度人”的主导理念,使读者把握了一个巨大地理范围的华人民间信仰实况与特征。这在学术上已经颇具建树。
单纯从信仰本身而言,人类学的基本出发点是相信民间信众精神需求与布道的真诚,随后才会有对教门与信众的长久传统的理解。尤其是在基层社会,民间信奉大体无权所依,他们的内心却真挚如一。我们看到近年来为数不少的人类学著作,总是无限扩充“权力”原本范畴的外延,把“权力”看作无所不能和无所不包。然而,当我们换一个视角,就不得不思考人类精神、情感、意义与信仰的感染性的动力源泉,并不是仅仅一个“权力”使然。
我在几年前阅读了早期儒学的一些文献,思考尚在弱势时期的儒学重在“自我教化”与“为仁由己”,导致了非强力推进型的、如墨渍弥散式的“过化”现象。当时,从国学中抽取“过化”一词推陈出新,原是为了和文化过程中常见的“濡化”“教化”“德化”以及“涵化”等术语及其含义进行比较。其中,早期圣贤儒者“过化”之所以感人而获得认同,还关乎他们出使布扬和讲学的态度、德行和内容。这些方式还借助文字刻印交互传布,而最终成为中原儒学得到大面积认同与成功“过化”的主要特点。从《孟子?尽心》提炼出的成语“过化存神”便是参与者被由衷感化的整体性动力。如果我们从公安派袁氏三兄弟提出的“性灵”、“真”和“趣”之关联含义进一步思考,无论是文学、诗歌、音乐和宗教,都连接着由衷感染和被感染的“过化”佳境。
当我捧读进国君的这本用心之作时,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于是,我们讨论了各种教门同样呈现的如墨渍般洇开的“过化”与“信仰感染”现象,并尽可能在宗教内外加以比对。
我们在电话里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华人教门的组织人类学观察视角。进国君著作中的海内外多种教门组织,实际上展示了“作为文化的组织”的存在特征与意义。台湾学者早年提及的“泛家族主义”和笔者团队十余年前做流动人口和公共卫生项目中涉及的汉人社会多类“类家族主义”的组织惯习,甚至可以推及历史上的捻军、四川的袍哥、中原的红灯区,直至今日进城打工的民工组合,等等,都显示了大体意义上的华人社会习惯采纳的“家族主义”模拟框架。
进国君告诉我,他的下一本宗教人类学专著,就准备扩充本书第五章的南洋真空教研究专题,以其布道环境、组织、信条、理念与实践过程,展示民间教门的信仰意义、“类家族主义”形态与现代变迁,以及“心所存主之处”何以“神妙莫测”之原委解说,或许是宗教学与人类学相结合最为期待的产品,尽管我们已经从这本书中预见了某些端倪。
进国君这本大书中的诸多教门信仰、组织与实践框架的类同性与多样性,文化的惯性与现代性影响,也许是当今信仰“过化”过程的变通与转换现象。然而在这其间,书中的善男信女既完成了个体对日常生活世界的意义与价值追求,也实现了整合外在社会秩序的夙愿。
庄孔韶 2016年6月17日北京景山住家
序三 林美容:万水归宗,普济群黎
陈进国博士的这本新书,有幸先睹为快,不禁赞叹。其实这本有关教派宗教的著作,并非我的专长领域所能擅自美言,不过因为我做过台湾斋教的研究,也写过高雄县的教派宗教,勉强算是沾得上边。过去有关教派宗教研究的多是历史学者,人类学者David Jordan(焦大卫)跟宗教学者Daniel L.Overmyer(欧大年)合作,写过有关台湾的鸾堂的研究。陈进国博士有关教派宗教的研究师承马西沙,自然在教派宗教的研究上是名门正宗。
而他这本书,广泛地调查了福建、广东、江西、香港、澳门、台湾,以及东南亚华人的教派宗教,这本书主要便是他的有关教派田野的呈现。对于教派宗教这样某种程度具有秘密性,跟民间信仰相对照,有许多不公开的仪轨、神圣空间等,也背负着许多历史的原罪或阴影,教派宗教的调查并不容易。但是,陈进国博士的书引领我们了解了客家长汀的罗祖教、闽东的儒教道坛、香港金兰观新道教、台湾一贯道和南洋的真空教,特别是在东南亚有关真空教的踏查,戮力于珍贵的基础资料的搜集,极为难得。如果宗教人类学旨在对宗教人与宗教场所的田野考察,本书呈现的田野幅度之广,堪称一绝。
本书的特色是以“济度宗教”的概念来统整所调查的诸教派宗教。教派宗教自来有“三期末劫”的思想,“三曹普度”,济度众生,以“济度宗教”来综摄之,自不为过。不过我个人浅见,救赎或是济度几乎是所有宗教必然有,也是共通的思想,不仅教派宗教为然。佛教的“自度度人”,道教的“拔度”,民间信仰的“救世”,基督宗教的“救赎”,可说任何宗教都有它的救赎观。何以要用“济度宗教”名之,似无法凸显教派宗教的特性。所幸书名主标“救劫”,点睛式地化解了读者这样的疑问。
陈进国博士的文笔精湛有创意,常发新词,不仅能创词(“济度宗教”一词可见一斑),而且能把人们记忆中的过去惯用名词,不管是庶民的或是学术的,均能朗朗上口,添增不少历史感。我特别在阅读导论的时候,感受到他描绘的田野场景,历历在目,看来他记忆力好,田野笔记记得细,田野的功夫了得。即便如此,书中对学术典籍文献的充分利用与掌握,也是不可多得的。一般而言,长于田野的,常常拙于文献。或许是历史学专业的背景训练,以及他本身阅读广泛,帮助匪浅。
当今的教派宗教,自明代罗祖以来,迭经变化,主张“三教合一”,唱言“三教同源”,甚至也产生了“五教合一”的说词。无论如何,民间教派有浓厚的中华思想,万法归一,一归于中,也因此产生了许多创新性的思想。在这点意义上,如同书中所言,是一种本土运动或是本土复振运动,并不为过。我个人觉得,这种创新性的思想是中华文化的活水灵脉,却因为过去的历史而无端背负了“秘密宗教”或“秘密结社”的色彩,在发展过程中屡遭跌宕。
我在读本书的导论时,感受到作者以中国为中心,走访教派祖庭,横跨海峡两岸,纵横港澳与东南亚,踏查教派道场,从各个面向探讨民间教派的相关课题,莫非一念至诚,中国本土理当是中华思想最能存续的所在。所以他思量再三,勇振文毫,大有再兴教派祖庭文化之气慨。
林美容 2016年5月写于台湾花莲
《救劫》读后感(四):【黄建兴】中国民间宗教的近当代转型——《救劫:当代济度宗教的田野研究》述评
由于历史与意识形态的原因,世人对中国民间宗教(教派)一直存在着刻板的印象,“反动会道门”、“秘密结社”、“封建迷信”已然成为了它们的“代名词”。国内学界相关民间宗教的研究除了政治上的批判之外,大多被局限于历史学范畴的客观陈述及宝卷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其代表作为马西沙与韩秉方的《中国民间宗教史》。[1]二人在此领域的成就至今仍然无人超越。国外学界的研究路径则相对多样,民间宗教成为汉学家观察中国文化与社会的切入点,期间出现了不少优秀的作品,如杨庆堃(C.K.Yang)[2]、焦大卫(David Jordan)与欧大年(DanielOvermyer)[3]、丁荷生(Dean Kenneth)[4]、宗树人(David A.Palmer)[5]、志贺市子[6]等学者都有相关的论著。这些作品代表了中国民间宗教研究范式的转移,研究方法从历史学和宗教学拓展至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内容从历史延伸至当代,其中亦不乏新理论和新观点的呈现,但是他们对于近当代民间宗教的研究多为区域和个案探讨,或是散见于中国宗教中的简述,也即中国近当代民间宗教研究至今仍然缺乏一部宏观的综合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当代宗教研究室主任陈进国先生的新书《救劫:当代济度宗教的田野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大胆地挑战了这一缺憾,无疑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救劫:当代济度宗教的田野研究》(以下简称为《济度宗教》)一书的思路清晰,全书包括“导论”与“余论”在内共七章。“导论”对该书的主要概念、理论、观点和方法作了概览性的梳理。作者创新性地提出了“济度宗教”的概念,用来统括近世以来那些借助“应世救劫”为中心母题进行创教演教的各类教派宗教运动。(页33)“应世救劫”是近世中国及其周边地区道(教)门的内在精神气质,亦是其持续存在的动力结构。各地的道(教)门明显具有“泛家族主义”的特征,既宣扬至上神创世的神话,又具有“统摄主义”的色彩,主张三教合一或者实质上的四教合一(儒释道巫);既崇拜教派创世的至上神,又膜拜区域性的救世神明和教派“卡理斯玛”(箭垛式权威)型的领袖;既注重个体德性与灵性的修行(修内果),又强调社会集体的救世(立外功)使命。在此基础上,作者还借助“宗教本土运动”理论深入地分析了济度宗教生成的社会背景,借助“宗教内卷化”理论,精彩讨论了济度宗教的传播限度和发展前景。
主体五个章节分别为五个不同的个案,详细描述了五个不同区域的教派,包括闽西客家罗祖教、闽东儒教道坛、香港金兰观、台湾一贯道和南洋空道教。每个章节的论述并非平铺直叙,而是各有侧重点,分别从济度宗教与地域崇拜、济度宗教与神启权威、济度宗教与神道设教(修行实践)、济度宗教与位育教育、济度宗教与区域网络不同的面向着手,这实为“导论”的延伸,进一步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近当代济度宗教之所以能够不断生成和发展的内外因素,同时也展现了不同时空和社会文化背景下济度宗教的多元面貌,及它们在近当代的生存实况、发展困境及未来发展趋势。“余论”强调了济度宗教的文化价值和文明意义:“重思济度宗教运动,也是重思历史中国何以持续,重思中国文明何以持续”。而将济度宗教作为态度和方法,则有助于我们还原济度宗教的真实面貌,从而实现去“神话化”和“污名化”的可能,并进而反思中国宗教谱系自身内在的发生机制、运行逻辑和发展模式。
深刻的理论分析及长时段、宽幅度的民族志深描清楚地展示了一幅精彩而逼真的近当代济度宗教运动图景,有效地化解了我们长期累积的对于济度宗教的“刻板印象”。
从其发生学上看,近当代各地轰轰烈烈、影响深远的济度宗教运动实质上是民间宗教徒在面对民族殖民危机的一场救亡图存、保存民族传统宗教文化的运动。从这一点上看,济度宗教是进步的,而非反动的。
从其创教机制上看,各地济度宗教的“统摄主义”、主张三教或四教合一的传统虽然有弱化其教典教义神圣性的一面,但是也使得其能够兼容并蓄,成为各教信仰的“拼盘”,甚至吸收和模仿外来基督教的组织形式和传教模式。即便如神秘性的“神灵附体”和“扶鸾降神”的教派神启机制也同样具有创造性,使其能够适时地引进新的教义思想。济度宗教的创教机制可以是传统的,但是教派的内容却是不断更新的,“旧瓶装新酒”,这的确是“立足于传统根基上的返本开新”。(页92)从这一点上看,济度宗教是一个开放的的系统,而非封闭的旧式教派。
从其传播方式上看,各地济度宗教具有灵活多样、与时俱进和因地制宜的传教策略。空道教之所以能够在晚清和民国年间在南洋广泛传播,构建其信仰的区域网络,与它针对当地时弊而开展的“戒烟(鸦片)治病”运动是分不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济度宗教在中国大陆的传播被阻,但它却能够远渡重洋,在台湾及东南亚社会“开花结果”,实现跨境、跨国的传播,这与济度宗教“以商弘道”“以道化商”的新式发展机制是息息相关的。从这一点上看,济度宗教不是一个停滞不前的保守派,而是一个不断革新、开放进取的、具有社会担当意识和时代精神的新式教派。
从其修行传统上看,济度宗教既保存传统的“静坐无为法”(空道教)修练方式,也发展新式的修行方式,如香港金兰观的“保健”“修身”和“修真”课程,一贯道的进修班学制和人格位育之道。这些修行方式不仅有利于信徒的身心健康,也有利于他们德性和灵性的培养。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济度宗教延续了中国古老的“神道设教”传统,其“存神过化”的修行既重视个体的精神性关怀,也具有深深的济世情怀,意在创建一个内在与外在秩序和谐的“善世”。济度宗教在社会上公开推行新式教育、设立医院、开展慈善活动等公益事业,这些无疑都具有社会整合和教化的功能。从这一点上看,济度宗教又不是消极出世的,而是积极入世的、具有现代性的教派团体。
济度宗教本是中国近当代社会因应时局而产生的宗教组织团体,如果硬要说它的“反叛性”品格和“封建迷信”的落后属性,那么只在于济度宗教“救世”的野心、传统的创世神话、旧式的组织形式和修行方式,以及间或被某些政治和利益团体所利用而被卷入到社会政治运动的漩涡之中。由此看来,我们对于民间宗教的刻板印象来自于强势话语的灌输,《济度宗教》一书成功地顛覆了我们以往对于民间宗教片面认识和“想当然”。
马西沙与韩秉方曾为历史上的民间宗教“正名”,陈进国通过在各地的田野研究为近当代的济度宗教“正名”。作为一名宗教人类学者,他不仅深入调查研究济度宗教,而且关心济度宗教在近当代的生存和发展前景。借用美国人类学家亚历山大·戈登威泽(Alexander Coldenweise)的“内卷化”理论,他创造发展出了“宗教内卷化”(Religious Involution)理论,从济度宗教的教典教义、仪轨实践、神明体系、组织形态、社会功能、宗教传播剖析了济度宗教的传播限度和发展困境,并指出了新兴济度宗教要向制度化宗教转型发展的方向。站在民间济度宗教的立场,为其发声、“献计献策”,这是一名宗教人类学者的社会担当和使命,本书也因此具有了现实意义和政治意义。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济度宗教》也不乏学术价值和意义。书中作者所提出的研究理论、所采取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不仅有利于我们深入认识近当代济度宗教运动的实质与变迁,而且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宗教,甚至是中国社会和历史文化也无不具有启发意义。
在探讨济度宗教与宗教本土运动的关系时,作者指出它是中国当代本土(复兴)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类以‘道门’、‘教门’自称的济度宗教团体,是一种以复兴或传承传统文化为主导、以‘应世救劫’中心母题为创教共相、并努力适应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本土运动。同时这场济度宗教也是中国宗教谱系主动谋求‘近代化’转型并自觉开展中西宗教对话的新尝试。当代中国及周边地区复兴的济度宗教,仍然是这场本土运动的存续和发展。”(页121)这一观点不仅是对近当代各类济度宗教运动性质的深刻洞察,更是将其置于中国近当代社会转型的宏观叙事当中。
在这一理论视角下,这场原本为人所忽视的济度宗教运动即刻突显出了它那非凡的社会文化意义,使得其能与近代著名的“新文化运动”“人间佛教运动”相提并论。不同的是,“新文化运动”是以外来文化为主导的理性型本土运动,“人间佛教运动”是以传统文化为主导的灵性型本土运动,而各类济度宗教(包括同善社、一贯道、德教会、真空教等)是以传统文化为主导的、兼具理性与灵性的混合型本土运动。济度宗教的这一属性使它天然地被赋予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的使命。晚清民间的大陆济度宗教在面对列强入侵和外来基督教的挑战时,发出了“保国”“保教”和“保种”的呐喊。台湾一贯道在战后日本文化殖民下,提出“去日本化”“复兴中华文化”的口号,得到了台湾民众的强有力支持,获得了快速的发展。香港道堂运动在面对异质文明与资本主义文化时,有着强烈的“正统化”诉求。东南亚各国的济度宗教战后的复兴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应对当地政府对华人少数族群的种族歧视和文化同化,济度宗教在东南亚起到凝聚华人群体、保存中华传统文化的作用。
规模浩大的本土宗教运动影响深远,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中国民间宗教的近当代转型。济度宗教对于历史上的教派既有传承亦有创新,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又是一场中国宗教内部的自我革新运动,在教派思想、组织形式、修炼方法、传播方式等上都有所体现。各地济度宗教在其形成之初多带有较强的佛道巫色彩。民间刻经和灵媒是闽西客家罗祖教复兴的强有力动力之一;闽东儒教道坛兴起之初依靠的是当地道(仙)师的治病救劫和神启权威;香港金兰观与台湾和东南亚一贯道的基础是民间扶鸾降神的道坛;南洋空道教在其形成之初的信仰基调也偏向佛道色彩。
然而,随着济度宗教运动的向前推动,各个教派内部的佛道巫灵性文化不断衰减,而代表理性的儒家文化却不断增长,甚至越来越居主导地位,所谓的“以儒为宗”。这其实是儒家文化不断向地方社会和基层民众渗透的结果,要将其放在“儒学运动”的历史脉落之中加以审视。引用济度宗教归根道的话说:“三代以前,道在君相,以君道而兼师道也;三代以后,道在师儒,以师儒而兼君道也;至下元末劫,则君相儒儒,皆失其道,而道落庶民,名为火宅开道。”(页64)济度宗教的这场运动属于“道落(降)庶民”的阶段,从宋代就已经初露端倪,一直延续至今。
当儒学普及到为民间宗教信徒所信奉和解释的时候,这说明它已经深深地扎根于基层社会了。“当官方儒教作为一种正统的圣教被蜕变为神怪化的‘道门’、‘教门’时,‘道在师儒’的解释权也开始旁落民间了”。(页67)不止济度宗教有此转变,中国宗教作为整体包括民间信仰也有着相似的发展趋势。引用汉学家劳格文(John Lagerwey)的话说,“这是一个不断内在化(Internalization)和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的过程”。[7]宗教学者的这一观点与当前思想史学界与历史人类学界的研究结论不谋而合,相互印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宗教也是解读中国社会与历史的一个良好切入点。
《济度宗教》的不凡之处还在于它推动了宗教人类学一块崭新的研究领域——“修行人类学”。诚如庄孔韶在其序中所强调的:“我们看到近年来为数不少的人类学著作,总是无限扩充‘权力’原本范畴的外延,把‘权力’看作无所不能和无所不包。然而,当我们换一个视角,就不得不思考人类精神、情感、意义与信仰的感染性的动力源泉,并不是仅仅一个‘权力’使然。”(“序二”,页1)其实不止人类学,宗教研究范畴下的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及历史人类学领域同样存在着相似的问题。例如,当前民间信仰的人类学著作不少,但其研究旨趣大多指向民间信仰背后的社会文化秩序、权力结构及其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也即学者仅仅只是把宗教作为研究的切入点,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其背后深层的社会文化。这诚然是宗教人类学研究的一个传统和重点,无可厚非,但是他们却忽视了宗教内在丰富的情感和精神世界——“宗教的本质和最为核心的层面”。
陈进国敏锐地察觉到了宗教人类学研究的这一不足。《济度宗教》从“导论”到“余论”,每一个章节都有相关济度宗教修行实践的细致讨论。从中我们看到了济度宗教内部多样化的修行传统,既有非常原初的身体化的、属于民间信仰和巫术层面的修行传统,也有道教内丹的“性命双修”、佛教的“打坐冥想”和“素食主义”,儒家的读经与内省,及具有现代性的各类研修课程和人格位育之道;既有宗教徒追寻“超凡入圣”和“即凡即圣”、兼顾灵性和德性的修行之道,又有普通信众纯日常的、侧重于德性的实践方式;既有宗教徒个人神秘的修炼,也有集体的公开修行。
不仅如此,作者还借用“存神过化”一词来统括济度宗教多元修行传统的内涵,并且很好地阐释了“存神”与“过化”两者之间的关系。其中“存神”是济度宗教的宇宙观和本体论,“过化”是它的社会教化。“存神过化”的有机结合就是“知行合一”的修行境界。济度宗教丰富的修行传统是济度宗教广泛传播的内在动力之一,也让我们看到了民间宗教徒对个体生命内在精神的追求和对外在社会的关怀。近年来作者与宗教人类学界黄剑波、杨德睿等一起积极推动修行人类学的研究,举办了三届相关的研讨会。[8]修行人类学是一个集宗教学、人类学、社会学、精神学、心理学于一体的新领域,促进了宗教人类学由外向内的研究转移,进一步拓宽了该学科的研究范畴和空间。
济度宗教持续的时间长,横跨的幅度宽,主要潜藏于广大的民间社会,各地教派内容不一,形态复杂,加上它在当代大陆还是一个较为敏感的议题,在有些地区甚至还被列为调查研究的“禁区”,在此情况下,要对济度宗教做通论式的综合研究是很难的。作者果断地放弃了做通史和断代史的传统研究,而是别出心裁地采取不同个案的来呈现不同区域的济度宗教形态和特征。由于大陆地区的济度宗教发展受限,多数已经衰落凋零,无法有效地开展田野调查,作者又采取“礼失求诸野”的方法,大胆地走出去,进行跨境、跨国的田野调查,足迹遍及中国港澳台和东南亚各国。不仅“以中国为中心”,从中国看周边地区,亦从周边看中国。这一方法视角亦有其理论依据,港澳台与大陆的紧密相依自不必说,东南亚地区原本亦属“外延中国的天下”。
书中五个个案不是随意选取,而是精心挑选。其中有客家罗祖教和儒家道坛来自于民间宗教信仰发达且较为开放的福建地区;金兰观和一贯道来自于境外边缘的香港和台湾;空道教来自于“下南洋”的东南亚。五个个案当中来自境外的就占了三个,加上境外济度宗教“老水返潮”式的影响,这实属“墙内开花墙外香”。济度宗教的研究离不开境外教派的深入调查。五个个案之间有机互补,既显示了各地济度宗教的共通之处,又让我们领略了它们的独特性。跨区域的比较研究和历史与当代的交叉论述,这种宏观的视角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全景式的中国济度宗教图景,精彩而生动。
当然本书也有一些观点和论述值得进一步商榷。
其一,济度宗教“应世救劫”的母题和“劫”的概念最早都来源于佛教,尽管后来的道教与民间宗教也对其作了创造与发展,但是佛教与济度宗教之间的天然关系是其他宗教所无法撼动的。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佛教的传入为中国宗教注入了新鲜血液。它那以“教”为中心的“教缘”组织迥然异于中国本土宗教以“血缘”、“地缘”或“神缘”为主的组织形式,与基督教一样具有传教的主动性和扩张性。济度宗教延续了佛教的这一传统,从一开始就具有积极在异地主动传教的精神,这也就是书中所称的“陌生人气质”。济度宗教的这种精神气质是与生俱来的,而并非是后来受基督教影响所致,或是传到异邦之后受资本主义商业精神才发展出来的。
其二,闽西客家罗祖教与闽东儒家道坛的复兴时间与背景与一贯道、金兰观和空道教有所不同。虽然它们都是以传统文化为主导的本土宗教运动,但是后者是为了应对近代的外族入侵和殖民危机兴起的,而前者是在当代改革开放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背景下开展的。两者虽不是质的区别且相互联系,但也不能一概而论,而应该作细致的比较研究,以观其不同的特征和意义。
《救劫:当代济度宗教的田野研究》不仅是一部优秀的宗教人类学著作,也是一部跨学科交叉研究的经典之作,值得大力推荐。
注释:
[1]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2]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Religion and Ritual inChinese Society of contemporary Social Functions of Religion and Some of theirHistory factors),范丽珠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3]David Jordan andDaniel Overmyer ed.The Flying Phoenix:Aspects of Chinese Sectarianism in Taiwa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
[4]Dean,Kenneth.Lord of theThree in One:the Spread of a Cult in Southeast China,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98.
[5]David A.Palmer:"Chinese Redemptive Societiesand Salvationist Religion:Historical Phenomenon or SociologicalCategory",载《救世团体与现代中国的新兴宗教运动专辑》,《民俗曲艺》,2011年第172期。
[6](日)志贺市子:《香港道教与扶乩信仰:历史与认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
[7]John Lagerwey.China:A Religious State.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Press,2010.
[8]陈进国主编:《宗教人类学》(第七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