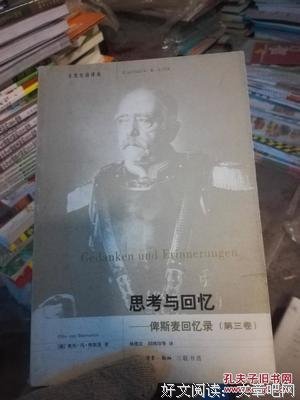
《思考与回忆》是一本由[德]奥托·冯·俾斯麦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1070图书,本书定价:59.80,页数:2006-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思考与回忆》精选点评:
●小麦的嘴也是很贫的,很有微博控的潜质。。。
●这书的注释居然是每本的最后,让我这个只对普丹战争到普法战争略有了解的人读起来有点迷茫,不清楚每章历史背景,也就没法体会透彻俾斯麦在吐槽什么……
●俾斯麦把自己描述得很"伟光正";不了解欧洲历史及其宗教文化,很难理解这部回忆录中的很多内容。翻译不太行!
●读起来好累...
●时间总是在回忆过去与思考未来中流逝。
●俾斯麦给德国攒了一手好牌,玩法都写成“说明书”了,还是被威廉二世玩的稀碎。
●有点晦涩
●终于有时间看这类书了
●大学时初读,年底准备重温。与其说民族主义者,不如说法家式国家主义者。普鲁士与拿破仑民法典基于普遍地权的自下而上恰恰相反,是条顿森林的游牧军国遗物,安危皆系于吏。难怪俾斯麦在信中痛诋拿破仑。寡头英国介于法德之间,欧洲楚项。
●翻译还可以改进
《思考与回忆》读后感(一):回忆录挺考验耐心的,不过也挺好看
这类回忆录不能从第一页开始看,否则会很无聊很崩溃。随意打开一页,前后读开去,才有了乐趣。读这本传记,还要基本了解德意志近代历史,否则真的很浆糊。于是又配了一本韦勒的德意志帝国。其实那本书比较好看。
《思考与回忆》读后感(二):翻译很糟糕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无意间看到过此书的1985年初版,很是心仪。身为首相的FANS,不免拜读多遍。只不过这翻译……
这本就是当年初版的再版罢了。精力所限,实在无法对应着研究其中的差别。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翻译依然很糟糕,不推荐狂热者以外的人。不过由于注释的比较详尽,又适合初心者……好矛盾……
《思考与回忆》读后感(三):“政治家的自传”
《思考与回忆》读后感(四):幽默的俾斯麦先生
之一
最近在看《思考与回忆》,俾斯麦的回忆录。退职后写的,厚厚三大册。看来退休后的老人还真有空。而说起读书这事,进入最难。坚持了几天,总算是进了大门。而且我发现这位老人家很幽默。随手翻了翻,举几个例子,大家看看,俾斯麦先生是不是很好玩?
1。他们对于政治一无所知,仅仅由于熟悉法语便得到了高官;即使他们的报告中,谈的也只是他们能够用法语谈得畅通的事情。(外语真的很重要)
2。为了表决而不得不把他从假寐中唤醒时,他总是说:“我赞同我的同事泰佩尔霍夫的意见”,有时甚至不得不提醒他,泰佩尔霍夫先生并不在场。(泰佩尔霍夫真惨,看来要抓不开会的人,他是第一个,因为他有一个如此坚贞的同盟。)
3。对于一位警察总监来说,由于一次叛乱而获得声望是不自然的。(这有什么关系,英雄不问出身嘛。)
4。我在这里附带述及,我从青年时期起签名就不写“冯”,现在写始于对1848年取消贵族这些提案的抗议。(俄国人在注解中说了,俾斯麦先生此处的说法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因为他年青时几乎每封信都写“冯”。 )
5。如果我们三个人在这里看到窗外街上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那么议长先生会借机发表一通我们缺乏信仰和我们机构不完善等等的机智的想法;而将军呢,就会准确的说出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方法能够帮上忙,可是仍然坐着不动;只有我才会到街上去或找人来帮忙。(看来俾斯麦先生不会吹胡子瞪眼,连责备人都这么委婉,或许因为当时他的官没有另两位大? )
6。“奥地利在波希米亚有两万八千二百五十四名士兵和七千一百三十二匹战马”,他话里提出的千位以上的数字,是我偶然记住的,而其余的数字是我随意加上的,只是为了突出将军提供的情报的极端准确性。(真够准确的,这等骗人的魄力果然非常人所能拥有。不过千位已经是这些数字中的最高位,俾斯麦先生的千位以上如果没有包括千位本身,那么整个数字全为杜撰,我只能说:佩服,佩服。 )
7。桌子上排列着许多他应得的,起初是在战场上因功荣获的勋章。这些勋章在他胸前构成的习惯的排列被一颗刚授予的新的金星勋章打乱了。寒暄之后,他和我谈的不是关于奥地利和普鲁士的什么事,而是要我判断,从艺术鉴赏的观点看,应该把这颗勋章插在什么地方。从儿童时代起我就对这位建立大功的将军怀有尊敬的情感,这使得我十分认真的考虑了这个问题,只是在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才谈公务。(我由衷地佩服俾斯麦先生的做好一个合格的粉丝的精神。)
8。剩下我一个人,不知如何是好,又不知道宫中房间的配置情况,只记得国王说过,三个门中有一个通往患麻疹而卧床的王后的寝室。(俾斯麦先生真八卦。 )
9。我们就为这种信函制定了一种类似密码的东西,用我们熟悉的村庄的名称来代表国家,用莎士比亚的主人公代表任务,这不无幽默之感吧。(神啊,救救我吧,冷死了。 )
10。一个注释:废物:旧时化学术语,表示蒸馏时余下的不挥发的,稳定的沉淀物(“死脑袋”)。(写这个解释的俄国人真是死脑袋。 )
不举了,不是因为没有了,而是有太多,举不完。原来一个叱咤风云的外交人物的生活是如此的好玩,有时侯想想我们学的那些理论,到底是我们玩理论,还是理论玩我们?现实和本本的差别岂只天壤?面对社会,我们都要从头学起。
幽默的俾斯麦先生说要让此书有教益于未来,我想有一条应该就是,注重现实,尊重实际吧。政治其实也是幽默随性的艺术,别学究化了才好。
之二
之所以又写一篇关于本书的札记,实在是因为这本书太有意思了。
自然是上网搜。没看见俾斯麦,倒是见了朱可夫。仔细一查,原来把书名输错了。俾先生写的是《思考与回忆》,我给打成了《回忆与思考》,那是朱先生的书名。于是开始想一个问题——回忆和思考谁先谁后呢。半天得出了个结论:应该边思考边回忆。可是一想也不对。这思考和回忆毕竟是两个东西,夹杂会出乱子的。就像俾先生,我总觉得他有些避重就轻,或者说驾轻就熟?想忘的就忘了,不愿写的就不写了,觉着谁不顺眼可以花好几页的篇幅来批。功勋卓著的老人家,这么做倒也是符合人之常情。
看到一篇书评,有如下一段文字——
如果俾斯麦地下有知,中国人是如此重视他的回忆录,他会感动的,或许也会感到脸红。因为“1890年去职后倾全力撰写”已经是溢美之词。在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恩斯特·恩格尔伯格的《俾斯麦》传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幅展现俾斯麦创作回忆录的素描:俾斯麦正散漫地躺在沙发上审阅初稿,旁边躺的是他的爱犬,一桌之隔坐着他的满脸无奈的助手洛塔尔·布赫尔。回忆录的口授大概是在这种场合下进行的,恩格尔伯格写道,口授时俾斯麦并不是很合作,他常常打不起精神,回忆起来又不按时间顺序,喜欢东拉西扯,把历史回忆与时事评论搅和一起。他更关心的是时事,因为他刚刚被威廉二世赶下台,心里忿忿不平,对政治也是兴犹未尽。回忆录的口授至1892年布赫尔去世基本停止,随后只是修改与添补工作。
凉了半截。果真是老人家。但是转念一想,正是老人家。散漫没什么不好,至少真实些。
想起当时看卡森的传记,很惊讶于她身体残疾还到处跑,记得某位作家写过一篇专门介绍卡森的文,具体文字记不请了。大意是这样的:卡森残着身体,坐在南方的家里,写着东西,云云。这和实际情况如此的不同!很多事情,其实都很随性,没那么壮美,如果有,大都是“人云”的结果。再加上“亦云”,话早就变了形,人也就失了真。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俾先生的写作态度尽管自我的甚至没有什么责任感,可是在我看来,还是很好的。
扯了这么多,也不知道在写些什么。老老实实地抄录一段俾先生损人的话,也免的通篇游离在《幽默的俾斯麦先生》这个标题下本应该表述的内容之外——
他谈及感到疲倦并想退休,这时他说:“只要我没有在欧洲主持过哪怕一次微不足道的会议,我就不能上天去见圣彼得。”随即我(俾斯麦)请他主持当时正在举行的一次外交会议,不过这次会议只是半官方性质的,他便前往主持。听着他那作为主席所做的冗长演说,我感到百无聊赖,便用铅笔写道:夸夸其谈,夸夸其,夸夸,夸。坐在我旁边的奥多罗素勋爵,从我手中抽出了这张纸,收藏起来。
《思考与回忆》读后感(五):斗争与摇摆:属于俾斯麦的胜利时刻
“唯有一场胜仗能及这场败仗一半悲壮”
1870年9月1日的下午,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收到了一封信。信件的书写者表示愿“愿将他的佩剑交到陛下的手中”。
隔天,拿破仑三世率8万士兵向普军投降。隔年1月,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正式加冕,成为德意志帝国的首位皇帝,德国完成统一,成为欧洲大陆第一强国。
普法战争以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失败而告终,法国人将这场战争称为“1870年法德战争”。经此一战,法军损失12万人,普军仅损9000。
唯有一场胜仗能及这场败仗一半悲壮。
55年前,拿破仑战败于滑铁卢,而55年后的拿破仑三世,使法国遭遇了更为崩塌的失败。这一次,横亘在拿破仑三世和法国面前的,不是一座比利时的小镇,而是一个人。
巧合的是,普法战争结束的这一年,俾斯麦55岁。
“诚实经纪人”的第四次胜利
1871年,刚刚完成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像一台巨大的国家机器,俾斯麦是德意志帝国的首相兼外交大臣,这台国家机器的中枢神经。
过去的8年中,普鲁士已经在他的主导下打了三场胜仗,分别是普丹战争、普奥战争、普法战争,而过去的大半生中,他做过律师、书记和行政人员,曾经短暂参军入伍,还在1839--1846年间经营了家族的农庄生意,整整照顾了七年。
俾斯麦现在的这份差事,是从1847年参选州议会的议员才开始的,在1851--1859年间,俾斯麦一直担任着议会发言人,当时的普鲁士国王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在威廉四世的时代里,俾斯麦一直不被重用。军队曾举荐俾斯麦担任首相,但威廉四世的评价是:
“此人只有在刺刀横行无忌时才可任用。”直到威廉四世病逝后,摄政的亲王威廉一世即位,1862年,俾斯麦成为了普鲁士王国首相,一个时代过去了。
对外的三场王朝战争结束后,如今的俾斯麦已经是这座帝国的发言人,现在是他的时代。他正在筹备的,是面向国内的第四场胜仗。
战场已经变换,对手戏有了新的主角。
1871--1877年间,俾斯麦在“文化斗争”中与罗马教廷分庭抗礼,于1878年起开始“围剿左派”,打压社会民主党,与此同时制定了很多保障工人的措施,德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拥有劳工立法的国家。
解决了天主教和左派劳工的问题后,俾斯麦再一次转向国外的战场。
这一次,俾斯麦觉得,自己可以试着做一个“诚实经纪人”。
基辛格在《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上对俾斯麦做出过如下评价:
俾斯麦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的对手“仍陷在18世纪的观念之中,认为国际体系就像一只有着复杂部件的钟表:牛顿的科学。俾斯麦预见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各种相互作用的力量之间的平衡一直在变化,这些力量也处于变动之中,就像后来的原子物理学。与它相宜的哲人是达尔文而非笛卡儿,不是我思故我在,而是适者生存”。如何在国际问题中做一个“中介”?俾斯麦找到了一种回答。
1873年的俾斯麦已经不再希望德国迎接战争,他认为:
“任何曾在战场上凝视过濒死士兵双眼的人在开战前都会三思”。但是,他不能对普法战争后的法国掉以轻心。为此,他与奥匈帝国、俄罗斯缔结了“三帝同盟”,孤立法国。
1877年,俄国大败土耳其,双方签订《圣斯提法诺条约》。柏林会议上,俾斯麦的态度有些微妙。
俾斯麦表面中立,实则偏袒奥匈帝国,导致俄国成为输家,两国关系恶化,俄国退出了“三帝同盟”。重新签约后的俾斯麦与奥国,成为了“德奥同盟”。
但这个保险力度还不足以让俾斯麦放心。
1882年,俾斯麦与意大利、奥匈帝国签订了新的“三国同盟”;1887年,法国仍然是悬在俾斯麦心头的隐患,于是俾斯麦与俄国签订了“再保险条约”。
这些问题一直陪伴俾斯麦直至晚年。
但在他政治生涯的前一部分里,俾斯麦拥有另一个著名的标签。
人生中的第17322天
1862年9月26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召开了一次会议。
当时的德意志四分五裂、诸侯林立,在近百年间一直处于封建割据状态,而普鲁士是境内的30多个政权中最为强大的一个。
与会者里,有20多位议会预算委员会的委员们,他们首先对1863年拨款的决议草案进行了讨论,而俾斯麦则代表政府与议会共同解决问题。
会议的议程进展还算顺利,直到话题的焦点转向普鲁士,涉及到德意志的统一。威廉一世看向自己的内阁大臣和议员们,群臣们已经争论许久,意见难以一致。直到俾斯麦站了起来,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他对解决德意志问题的基本见解:
“普鲁士必须积聚自己的力量并将它掌握在手里以待有利时机。”“这种时机已被错过好几次。《维也纳条约》所规定的普鲁士国界是不利于健全的国家生活的。”“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与多数议决所能解决的——这正是1848年和1849年所犯的错误——,而是要用铁血来解决。”这一天是俾斯麦人生中的第17322天,也是他出任普鲁士首相后的第4天,第一个上任周。
会议一周后的10月5日,威廉一世从巴登返回柏林,跟俾斯麦见了一面。
威廉一世表示:
“我完全可以预见这一切将会如何终场。”“在歌剧院广场前,我的窗子下,他们将会砍下你的头颅,过些时候再砍下我的头。”威廉一世的悲观是显而易见的,他想到了英国的托马斯·温特沃思·斯特拉福伯爵和查理一世。但俾斯麦在回应中展示出了无与伦比的信念,俾斯麦表示:
“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只好奋斗。”“我们能不能死得更体面一些?”“我是在为我的国王的事业和陛下奋斗。”此后,俾斯麦原本的临时任命终于得到了正式确认,他与威廉一世之间形成了十分牢固而特殊的关系。俾斯麦真正成为了普鲁士的首相。
“铁血政策”是俾斯麦的利器,俾斯麦是德意志的利器。
“铁血演说”后的9年里,俾斯麦在数次对外战争中取得胜利,帮助威廉一世于在位期间实现了德意志的统一,威廉一世加冕为帝国的皇帝,俾斯麦从普鲁士的首相走向德意志帝国的宰相和亲王。
政治遗嘱的未尽之处
20多年的首相生涯里,俾斯麦不属于任何党派,威廉一世是他唯一的权力来源。
1888年威廉一世去世,他的继位者只做了“百日皇帝”就罹患重症,皇位的新主人是威廉二世。29岁的威廉二世与俾斯麦时常产生分歧,俾斯麦开始大权旁落,于1890年3月18日请辞,结束了将近30年的执政期。
下野之后,俾斯麦着手将人生往事写进了自己的回忆录——《思考与回忆》。
他生来是一个容克贵族,性格里的复杂与两面天然存在。
父亲是一个是传统容克地主和退休军官,传统且保守,母亲拥有资产阶级的家庭背景,相对先进和开明。学生时代,俾斯麦的同学们多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作为一个容克之子,他的童年阴影里除了家庭问题,还有在校园生活里遭受的排挤。
叛逆和恶习往往属于这一时期。
入读哥廷根大学时,俾斯麦未满17岁,曾在9个月内与同学们决斗27次,仅有一次负伤。在校期间,俾斯麦经常佩剑,并牵着一只大狼狗,某种意义上,算是对斯巴达式教育的一种叛出。
在后来的人生中,这些叛逆的特质陆续变成了一些新的定义,有时是失败和胜利,有时是胜利之后的摇摆,有时是摇摆之后的铁血,有时是周旋于欧洲事务之时的那位“诚实中介人”......俾斯麦逐渐找到了对极度和平衡的感觉,成为一个理性主义者。
16岁那年,俾斯麦成为一个“泛神论者”,28岁时,俾斯麦加入了一个信奉新式路德教的圈子;统领德意志帝国的20余年中,俾斯麦偶尔会联合社会主义者,但也曾制定《反社会主义非常法》;1873年,他与奥匈帝国、俄罗斯缔结了“三帝同盟”;1882年,他与意大利、奥匈帝国签订了新的“三国同盟”;从政之初,俾斯麦选入新的普鲁士州议会,他当时的政治立场是反对德意志统一;后来,俾斯麦成为了德意志完成统一的最大功臣......
回溯至幼年之时,父母对俾斯麦寄予过不同厚望。父亲希望俾斯麦未来成为一个军人,母亲则希望他做一个政客。晚年的时候,俾斯麦对统一后的德国也寄予厚望,他的期望是德国能够避免军国主义。
起点和终点在命运的暗处产生连接。
1898年7月30日,德意志帝国永久失去了俾斯麦。墓碑上只有一句简短的墓志铭:
“皇帝威廉一世的忠诚的德国仆人”。威廉一世却曾经感叹:
“做俾斯麦的国王实非易事。”俾斯麦离世后,其政治遗嘱被完全抛弃,德国不可避免的走向了军国主义,于1914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百年后,在德国电视二台于2005年展开的“最伟大的德国人”票选活动中,俾斯麦名列第九。
而对于当年那场大败了拿破仑三世的普法战争,卡尔·马克思的评价是: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喜剧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