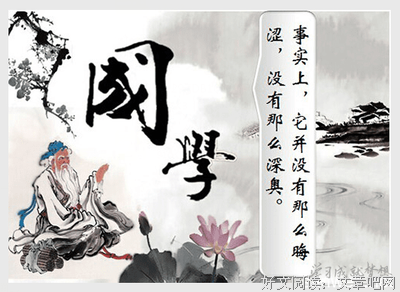
《无需法律的秩序》是一本由〔美〕罗伯特·C·埃里克森(Robert.C.Ellickson著作,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图书,本书定价:26.00元,页数:37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无需法律的秩序》精选点评:
●难读…… 内容不如标题精彩。 苏力老师的翻译真绝了……
●呃,博弈論一段不知道是翻譯的原因還是我自己的原因看得云里霧里的。
●徐昕当年推荐我读的。
●法经济学和法社会学的结合,标题就是作者致力证明的问题,至少证明野心不大的弱版本。
●这是很好的人类学研究教科书啊。第一部分,先从牧民的生活环境开始讲起,牧区的情况,当地发生纠纷的类型,纠纷类型化,纠纷解决的具体方式。第二部分是对现有的学说进行批判和理论建构,第三部分对话了科斯。
●博弈论、交易费用、自重损失、福利最大化的经济学进路,搭配对选择规则的规则和选择控制者的规则的注意。但还是太啰嗦了……苏力的翻译正如这个本不必要这么长的句子一样在任何程度上都是一场灾难……
●涉及博弈论那里看得有点头疼,不过大体上,用E师的话,就是讲科斯和霍布斯的媾和;然而,这个也仅仅限于私法领域之下,至于涉及到公法上的问题,包括自由、权利等,就没有什么帮助了。
●第二遍没读。。。
●不错研究路径,只是当时没有太读懂
●收藏。
《无需法律的秩序》读后感(一):法律之中与法律之外
无论是法律人,抑或是法律之外的人,都应当充分认识到:法律对于社会调整来说,仅仅是一个十分有限的手段。法律可能会致力于创造一种优良的社会环境,但是,在整个社会秩序的形成过程中,其只能扮演当中的一个角色,切忌法律的盲目自大,合理认识到法律作用的有限性,才能更好地理解其他的社会调整方式的益处。
《无需法律的秩序》正好诠释了这一点,法律在一个社会中究竟能够起到多大作用,究竟能够从什么样的方面,以什么样的方式追求社会秩序的优化,法律与其他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如何整合融通,是一个值得一直思考的话题。
《无需法律的秩序》读后感(二):摘要
[美]罗伯特·埃里克森:《无需法律的秩序》,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1991年初版的书,最早由苏力于2003年迻译,可以想见本书对中国的法律社会学和法律经济学产生了不小的推动,苏力个人的研究风格甚至论说风格或许也受此书影响。一个重要的启发是:社会控制的方式是极为弥散的,法律中心主义和经济学后果主义都极为片面。
本书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夏斯塔县,展示了一个极为规范的法律社会学研究:埃里克森找到了一个完美的田野,一个主要依靠非正式社会规范维系的牧民社会。表明科斯所谓的“高交易成本下由法律界定权利”在真实世界中未必为真。说坏话、心中记账、“扯平”……这些充满乡土风格的社会规范非常苏力。
第二部分,一种规范理论。埃里克森试图从夏斯塔的故事出发提炼出一个具有一般性的规范理论。他提出的总体假设为,在关系紧密的社群的日常生活中,非正式的社会规范将以这样的原则产生:最大化客观福利,或者减小交易成本和无谓损失(deadweight loss)。他将这一假设运用到五种规范的检验之中:实体规范,救济规范,程序规范,构成规范,控制着选择规范,以简洁的经济学分析和丰富的常识论证了上述假设的成立。
第三部分,规范的未来。对作者提出的规范理论进行了“预测”。作者最后总结:“法律的制定者如果对促成非正式合作的社会条件取法眼力,他们就可能早就一个法律更多但秩序更少的世界”。【304】
《无需法律的秩序》读后感(三):内生与外生秩序的互动张力
看到最后才明白这文跟科斯什么关系。
“科斯说,不存在交易费用也许会使法律无关紧要(交易费用为零时,责任规则的改变不影响资源配置);然而,在夏斯塔县,正是存在交易费用导致了人们在许多情况下有意不理睬法律。”...乍看根本没逻辑,实际上中间少了一步:科斯言外之意是交易费用不可能为零,所以法律很重要。但是此文作者想证明:有交易费用,法律也可能不重要。
总的来说,这种非正式控制体系还是建立在熟人社会基础上的。而现代社会虽然从某种程度上不可能脱离差序格局,但是这种格局已经较为松散,以致需要法律作为最终的强制力后盾。
但是这不意味着法律和非正式控制体系是不相容的。实际上,可以以法律来强化非正式控制。“一些法律政策本身就影响着非正式社会控制系统的活力。要想不用法律而成就秩序,人们必须具有持续的关系,有关于昔日行为的可靠信息以及有有效的抵抗力量”。
几个例子
1、土地租赁的基本规则可能对土地纠纷中所涉及的当事人数量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影响到人们关系的紧密程度;
2、一些根本性的法律可以延长一个人对时间跨度的理解-从而影响博弈时间长短;
3、还影响人们获得非正式社会控制所必须之信息的难易-法律制定者在考虑对收集和传播真实的、可公开获得的有关昔日行为的信息施加新的规制性负担时,应当牢记这一点(因为会影响博弈前的信息搜寻)。
当效用是最高考虑因素时,对解决一个群体之内发生的日常纠纷感兴趣的法律制定者不可能改进该群体的习惯规则。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法律体系的比较适当的做法是依从一个群体的非正式做法。这一结论支持了——比如说——普通法法官普遍具有的冲动,即重视习惯,也支持了卢埃林将商业习惯纳入《统一商法典》的努力。(我应该在去西藏调查之前看到这书的TT)
不明白的是1.2的矛盾
1、法律和非正式控制体系相容,应当在法律系统内加深对非法律控制的理解和运用。
2、混合二者又可能产生资源浪费,结果是要么法律很强,要么法律很弱。
总之,法律制定者如果对那些促进非正式合作的社会条件缺乏眼力,他们就可能造就一个法律更多但秩序更少的世界。
书里面举了个有趣的例子:那些法学院的老师一般都是法律中心主义者,但是在学术复印时却无法无天,完全无视版权法而在教育圈子里自采一套非正式控制系统(虽然这样对学术圈来说是效用最大化的)。
遗憾的是,这书没有告诉我们法律系统与非法律控制系统(实际上是社会控制的五大系统:个人伦理、合约、规范、组织规则、法律)具体是如何互动的(作者说这个学界还搞不清楚)。
我就是意识流一下,这文没逻辑。
《无需法律的秩序》读后感(四):《无需法律的秩序》提要
本书的问题意识来自科斯定理——科斯以一个农民/牧主寓言为例说明,当交易费用为零时,责任规则的改变并不影响资源配置。由于类似的冲突经常发生,夏斯塔县为检验科斯定理提供了一个理想环境。作者意识到自霍布斯以降,包括科斯在内的理论家所秉持的法律中心主义观念,因此试图通过对夏斯塔县的分析表明,很多时候秩序并不产生自法律。在理论资源上,作者未遵循法律与社会科学内部的楚河汉界,而是同时借鉴重视经验的“法律与社会”和长于理论的法律经济学——这也是本书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地方,它在法律社会学与法律经济学领域都成为了经典。
开篇首先以描述性的手法带领读者进入夏斯塔县的纠纷世界。在这个畜牧业发达的地区,牲畜越界的事情并不罕见,甚至造成围绕开封牧区/封闭牧区的激烈政治冲突。牲畜越界主要引发三种争议:(1)牲畜走散,给邻人的财产造成损害;(2)邻人之间修建共同的防止牲畜越界的边界栅栏;(3)牲畜与公路上的汽车相撞。颇为吊诡的是,虽然在夏斯塔县围绕法律规则产生了政治骚动,但实际的纠纷解决却与法律没有相关性,牧人们对作为法律的封闭令充满了误解。
以夏斯塔县的经验为基础,作者尝试构建了一个有关社会控制的规范理论:
1. 人类的行为可以区分为有利社会的行为、普通的行为与反社会的行为,从而对应奖赏的规则与制裁的规则。
2. 根据控制者为第一方、第二方还是第三方,可以区分出五种不同的规则,即个人伦理、合约、规范、组织规则与法律。
3.每个规则体系又应该包含五种不同的规则类型,分别为实体规则、救济规则、程序规则、构成规则与选择控制者规则。
4. 目前的法律经济学理论与法律与社会理论都存在缺陷:前者错误地坚持了法律中心主义的观点,不恰当地假定行动者知道且信守法律;后者虽然注意到规范的意义,却将规范作为给定的外生变量,避开了对规范内容的讨论。
5. 借助博弈论的框架,可以解释社会规范何时会导向合作结果:突破囚徒困境的关键,在于重复博弈,由于可以预见一个持续的未来,博弈者会采取针锋相对的战略。
6. 由此作者提出福利最大化规范假说:在关系紧密之社会群体中,成员们会非正式地鼓励有关日常事务的合作性行为。在关系紧密的群体中,尤为关键的是未来实施制裁的权力与足够的信息供给。
7.在夏斯塔县以及其他的个案中,福利最大化规范假说获得了有力的解释:
(1)实体性规范:例如在牲畜越界问题上,当规范制定者可以确定其中一方为最小费用者,要求该方承担严格责任,可能是符合福利最大化的。
(2)救济性规范:救济性规范包含对未履行日常工作的惩罚和对完成不寻常工作的奖励。告知、议论乃至强力破坏与扣押的不同救济措施,遵循逐步升级的格局展开,以实现费用的最小化。在关系紧密的群体内,扯平成为一种比针锋相对更具效率的战略。
(3)程序性规范、构成性规范:依据福利最大化的假说,程序性规范会要求,只要信息交流的价值有可能超过信息传播的费用,就要传播信息。构成性规范则通过成员规则、团结仪式与对利他的第三方的奖励,增进群体的凝聚力。
(4)选择控制者规范:由于不同的社会控制都有实现福利最大化的潜在可能,选择控制者规范可能导向非正式体系与法律体系的混合。
作者的野心显然不止步于对夏斯塔县经验的解释,本书遵循的是从经验中归纳出理论,再将理论进一步验证于经验的结构。因此在最后的部分,上述规范理论被应用于对更具挑战性的个例的解读乃至预测。在作者看来,他的理论不仅无惧于人类学家提出的有关个别社会的落后规范,而且将可以解释相邻业主之间、土地共同业主之间以及房东与租户之间的关系——福利最大化的非正式规范会在这些关系紧密的群体身上得到应验。
回到本书的起点科斯定理,作者指出科斯及其追随者的缺失在于,误以为人们可以轻易地知悉并实施法律,无视了法律本身具有的高昂费用。由此也需要进一步反思法律与非正式的社会控制之间的关系:因为非正式规范具有效用的优势,对法律而言,更明智的策略不是去改变它,而是去依从它;与此同时,有的法律政策可以为非正式社会控制的实现提供基础性条件。无论如何,如本书标题所提示的,法律与秩序之间的联系,远比一而二、二而一更为复杂,“法律制定者如果对那些促进非正式合作的社会条件缺乏眼力,他们就可能造就一个法律更多但秩序更少的世界”。
《无需法律的秩序》读后感(五):我教郎咸平讲良心
上海塌楼事件,一位日本网民点评道:“梦中才有的事情,却总在现实中发生,中国真是个童话般的国家。”太精彩了,我在梦里想起这句话,都会笑醒过来。一个童话王国, 自然少不了很傻很天真的臣民。我闭着眼睛都能猜到,这个事件的发生,就像之前的豆腐渣校舍、大桥折断、地铁塌陷等事件一样,唯一被总结出来的教训是:要讲良心,要加强监管。每次我看到网民成群结队地疾呼“良心与监管”,还煞有介事当成解决体制痼疾之道,我就笑到口吐白沫、嘴角抽搐。这不就是郎咸平嘛!我有些弄不明白,既然他们自己就是郎咸平,为什么还需要一个讲坛上的郎咸平?还有一个问题:既然这个国家到处都是郎咸平,“良心”如此普及,为什么童话般的故事却愈演愈烈?
在中国,爱讲良心的太多了。很多知识分子,问题讲不清楚,就推到“良心”上面。郎咸平也是这一派的,但他很高明,说的是“信托责任”,有时指法律,有时指良心。不过,模棱两可的手段固然“高明”,却让我想起一个笑话。一位寡妇生活苦闷,就去请教情感专家。专家沉吟半响说,爱情是良药。寡妇一听就叹息了,唉,现在要找一个如意郎君太难了。专家频频摇头,答道:你理解太片面了,我说的“爱情”是,你先去找个男人,找不到,就买个振荡器。郎咸平的“信托责任”其实就是这回事,它既可以是男人,也可以是振荡器。这个答案荒诞不经,却大行其道,只能说明一点,这个国家苦闷的人实在太多了。
必须强调,我反对郎咸平,并不是反对“信托责任”,而是反对他的相关解释。我也不反对“良心”,我知道很多情况下,良心是人唯一的行动准则。我甚至承认良心是社会秩序最基本的来源,它先于法律。正如齐美尔所言,“通过良心,个人付给自己的是自己的正直,否则的话,就必须以其他方式通过法律或习俗才能保证他正直”。我反对的是郎咸平混淆概念,将“良心”和“法律”随意调换,不加区别。我还反对他把“良心”当成口号,用来煽动群众和自我表彰。但我并不反对有人尝试建立以“良心”为基础的学说,讲述“良心”的生成,它在社会中赖以存活的条件,以及围绕它而形成的某种社会秩序。简单说来,我不反对把“讲良心”当成职业,但我反对郎咸平的执业资格。
如果郎咸平真想无愧于“良心经济学家”的称号,我建议他回炉重造,尽快提高业务水平。我还可以为他推荐教材,例如这一本,罗伯特.C.埃里克森的名作《无需法律的秩序》。该书是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通过对夏斯塔县畜牧业的田野研究,展现了一个“无需法律”的真实世界。这个世界井然有序、运作自如,但可能和许多法律经济学家想象的不一样,这里“社会生活有很大部分都位于法律的影响之外,不受法律影响”,“人们常常以合作的方式化解他们的纠纷,而根本不关心适用于这些纠纷的法律”。用通俗的话来说,该书证明了,在现实之中,良心之治可能比法律之治更普遍,良心的秩序有时比法律的秩序更适宜。
埃里克森首先挑战的是著名的科斯定理。科斯通过一个牧人和农夫的寓言说明,当出现牲畜侵扰造成的冲突时,双方会依据法定的权利讨价还价,达成“对双方有利的协调。”埃里克森发现,科斯的结论在现实中检验是对的,市场化的力量会令交易成本内化,根本“无需政府的监督”,或者“其他科层机构的协调”;但有一个环节科斯却错了,现实中牧人和农夫解决纠纷并不依据法律,而是依据邻居间的规范。对于他们,搜索法律知识,并寻求法律救济的成本还是太高了。无论是修建边界栅栏,还是车畜相撞纠纷,他们都倾向于“私了”,把相关法律撇在一旁。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凭良心”,或者说“将心比心”。有时候,受损一方知道法律上的规定可以帮助自己,却不愿去做,因为不愿破坏邻里关系。这里面也有一本帐,只不过是人情账簿。
看样子这个无视法律的世界运转良好,那它依靠的“良心”从何而来呢?如果要让郎咸平回答,答案一定是政府监管或者严刑峻法。埃里克森的发现却相反,恰恰是因为完全没有外力,在所谓“丛林状态”中,才形成了这样一套“你好我好”、“你活我活”的规范。埃里克森从博弈论的角度作出了解释,实际上无政府也会形成好秩序,“当两位关心自我的个体处于一种高度特定的并因此保证了持续相遇的情境下,通过简单的针锋相对战略,他们常常能使他们的关系进入一种合作模式。”埃里克森举了很多实例说明这一点,这里的人更讲良心,并不是因为他们受到了良好教育,或者害怕法律制裁,而是因为他们怕招致对方的报复。他们愿意与人为善,也不是因为信奉“吃亏是福”的哲学,而是觉得对方也会同样地回报自己。而这种良心秩序的前提条件是,这里甚少有公权力插手,也没有什么守法的强制性要求。例如有一个农夫,自己的园地屡遭邻居的公牛越界而造成损失,他有一次就把一头公牛阉割了。这是当地法律不允许的,但邻居并没有兴讼,而是得到了教训之后,更注意去管束自己的牲畜。由此可见,良心是人与人博弈的结果,不来自政府的管制,也不来自法律的恐吓。
不过,尽管埃里克森强调法律之外的秩序,却并没有要用“良心”取代“法律”的意思。他承认“良心”的局限性,因为这种规范往往只出现在相对封闭的地方,人际关系较简单,不是邻居就是熟人。如果是陌生人之间的纠纷,就很难用“将心比心”的方式去协调。从这个角度来看,埃里克森虽然反对“法律至上”的观点,却例证了法律经济学领域里的许多重要论断的真确性,例如哈耶克的“自发秩序”,还有德姆塞茨和波斯纳所认为的“在初民社会产权就演化出来了,并没有一个可见的主权者介入。”他只是进一步证明了,人完全可以自我执法、自我救助,即使在强制执行明确的合约过程中,也根本无需“国家的一臂之力”。埃里克森并不否认法治,只是揭示出了法律的起源,这就是塔西佗说的,“没有道德,法律又是什么呢?”而道德的基础是自由,人是自愿地接受某种规范,而不是被强制着听从某种律令。埃里克森最后提出严正的警告:“法律制定者如果对那些促进非正式合作的社会条件缺乏眼力,他们就可能造就一个法律更多但秩序更少的世界。”
有人或许会问了,埃里克森的观点是否适用于中国国情呢?答案是肯定的。埃里克森认为产权不一定要法律界定,也无需国家的科层机构来干涉。中国的现实里有太多反面教材证明他是对的,例如小产权房这一畸形产物。这类房产的产权是自发而完整的,但通过国家“法定产权”的界定,却变得不能在市场上买卖。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这类房产在国家认为是“非法的”的情况下交易,无端端引发了许多纠纷。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国家不仅在产权界定上不帮忙,只会添乱。像郎咸平那样主张“政府必须更加着重权利,更要中央集权”,无疑是痴汉说春梦。这不是有无良心的问题,而是良心大大的坏。
或许,还有人会为郎咸平辩护,说他的良心不表现在他的经济学观点上,而是表现在他的某些作为上。比如什么“郎顾之争”,什么社保基金案之类。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无法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但我可以提示一下,当皇上把和珅的家产没收充公,那些欢欣鼓舞的民众自己有没有获益呢?没有,当然没有。那些被挽救的国有资产,只是从和珅的口袋,挪回到了皇上的口袋。国是富了,民却依然穷。如果说郎咸平有良心,那也不是站在人民一边的良心。他始终站在国家这一边,而这个国家的现实就是,杀了一个和珅,就有千千万万的和珅站出来。真有良心,就该直面体制之恶,呼吁“还权利予人民”,学性感的我,而不是学郎咸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