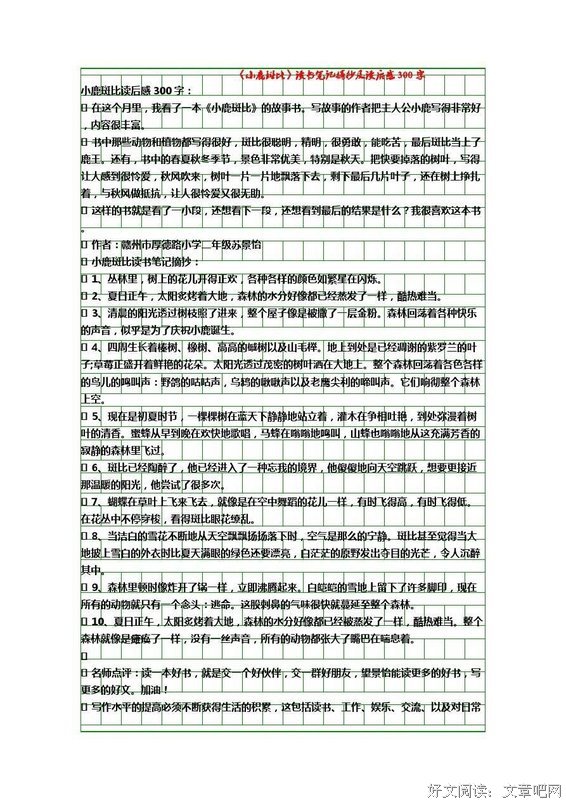
《五月之诗》是一本由(美)W.S.默温鲁刚著作,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简裝本图书,本书定价:18.00元,页数:13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五月之诗》精选点评:
●我得承认其实我没看得下去~
●被参差复原的音节旋律重建着这些弧形入口,旋转楼梯,浅浮雕门廊.直到写定之日,拱顶石将完美无瑕架在神庙圆柱之上,一切都将各就各位...
●真正的普罗旺斯在默温的笔底波澜中是不存在的。因为本初便无一个真实在,所谓的记叙自然在创造一种真实的等价物。由诗的身份而来的投入的自觉和深度,及诗人的身份而来的温和,五月之诗实在是为达到诗与诗人之乡的统筹和各各直观。
●2009年读过
●希望看到原文。
●May
●最受益的是其中关于中世纪行吟诗人的介绍。【多年前读过的东西了,最近突然想了起来】
《五月之诗》读后感(一):望书哀叹,放下便是
看了两天,实在坚持不了看完。
偶尔发现这本书时还惊喜来着。默温的散文,再加上写中世纪行吟诗人,肯定是很好看的。
可惜,译文太无吸引力了。
没有看到原文,只有谴责译文咯。
翻来翻去,看到很多可能精彩的段落死气沉沉,只能望书哀叹了。
里面提到但丁对行吟诗人传统的熟悉和引用。提到一些有吸引力的观点或八卦,可惜都被翻译弄得没兴致了。
默温遵循庞德的教导,然后开始了他的追寻之旅。
我也不再抱怨了,放下便是。
《五月之诗》读后感(二):“阅读种子而非嫩枝”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找了六位世界知名作家写命题作文——“我心中最美的地方”,美国诗人默温写了《五月之诗》,回忆他二十多岁时在法国普罗旺斯地区的经历,或者说是“在欧洲的经历”:默温研究法国中世纪游吟诗人,并在一个叫凯尔西的地方买得一处房产住了几年,冬天去伦敦或纽约。离开十二年后,默温又回来继续研究游吟诗人。
这都拜“卓越的匠人”庞德所赐,战后默温深受庞德影响,正是后者建议他如果想成为诗人,应该积累素材,而“法国的普罗旺斯文学是最好的源泉”。此书第二、三、四章尤其好看,但总体来说译文缺乏默温的风格气质,书的装帧也缺乏创意。或许默温的两本中译(《默温诗集》,董继平译)正应了当年庞德告诫他的,“阅读种子而非嫩枝”,还好,这句译得上口。
《五月之诗》读后感(三):有一种旅行叫安居
《五月之诗》【美】W S 默温 著 鲁刚 译
有两种旅行的方式在我看来是土鳖到极点的:一种是我父亲他们单位经常组织的那种,一个单位的老老少少,每人脖子上都挂着一架傻瓜相机,跟在一个始终吐沫横飞的导游屁股后面,忠实于已经设定好的路线,在各类标志性建筑前摆POSS、说茄子,留念。另一种更时髦些,也小资的多,这些个人以我们敬爱的于丹老师为代表,言必称大理丽江,马尔代夫,仿佛只有在那些地方,咖啡才是咖啡,阳光才是阳光,时光也才真正是时光一样。
这两种方式,一种是在走马观花的猎奇,而另一种是在装佯,这些人在乎的其实只有他们自己,至于时间与地点,仅仅是一种所谓心情的背景罢了。真正的旅行,其实不光需要钱,还需要很多其它的东西:如果你想像徐霞客老师那样靠双腿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没有一副好身板肯定是不行的;而如果你想效法切·格瓦拉老师骑摩托车横贯美洲大陆,那么不光需要勇气与毅力,维护摩托车的技术也是必备的;至于你想像凯鲁亚克老师那样不花几文钱,就在美国东西部之间来回溜达,那难度就更大了,你不但要永远在路上,而且还要“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这几种旅行的方式风格似乎都过于粗犷,流动性过大,且性质更接近“探险”而非旅行。那么有没有危险指数不那么高,也不俗套的旅行方式呢?答案是肯定的,比如默温老师这种方式。默温老师这本书带有游记的性质,写的是他在法国普罗旺斯度过的一段时光。一提到普罗旺斯,估计又会有一大批小资们开始激动,脑子里立刻开始浮现五彩斑斓的田园风光。不过对不起,默温老师让你们失望了,默温老师不但要写诗、教书还要忙着研究欧洲中世纪的抒情诗,所以他可没那么多闲功夫,到普罗旺斯去边喝咖啡边看风景。他去那里是事出有因的,普罗旺斯是欧洲吟游诗人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而当年一大批吟游诗人正是用普罗旺斯语来吟诵他们献给王公以及他们漂亮妻子的优美抒情诗的。在接受庞德老师的建议开始研究、翻译欧洲中世纪抒情诗之后,随着研究的深入,默温老师从中所获得的快乐和遇到的困惑同步增长,于是,他决定要亲自去那些地方看一看,走一走,从阳光、雨露、泥土、农民们的面容与他们过去以及现在的生活中而不仅仅是白纸黑字间去体味这些诗歌所意味着和代表着的东西。
于是,他徜徉在母鸡和土狗出没的乡村土路上,驻足在一间间已经荒废多年,被荆棘、燕子与睡鼠所接管的房子前,他沿着绵羊与山羊们道路去寻找一座座城堡的废墟,望着那些曾被认为和现在依旧被认为是永恒象征的石头的废墟,他慨叹:“那些石头像是从来就在那里一样,而且将永远矗立在那里。我们的时间流逝感使我们无从意识到那些石头也会像雪花或分子一样地运动,在我们看来,这些石头似乎一动也不动,是永恒的象征,就像维纳斯女神雕像从来就没有胳膊似的,而这片废墟似乎也从一开始就是这座城堡的真相所在。”他决定留下来,他购买了一间没有水槽也没有煤气的农民的房子,并在那里住了下来,和挥动锄头、采摘葡萄的普通农民们成为邻居、朋友——和他所研究的那些在各个乡村、城堡之间四处游荡,和村名们打成一片的吟游诗人们一样。
但这本游记并非仅仅到此为止,这里,此时此地,正在被整齐划一的现代社会一点点吞没的普罗旺斯,不,这里并非是默温真正的安居之所,并非是他旅行的目的地。与这现实的旅行同步的,是他的记忆,是倒退着回到青年时代与伟大诗人庞德的一次改变自己一生的会面,是回到童年,在一处破败的乡间别墅里度过的快乐的童年时光;也是他对由吟游诗人肇始,一直到伟大诗人但丁所终结的中世纪欧洲文学传统的追忆。三条方向、所处时空都不相同的旅行最终在这本游记中合并到了一起,他让他最内在的自己,像一滴水那样靠近、走近并最终汇入了他所研究着的欧洲中世纪文学传统,让自己在同一片土地上,再一次的,感受到那些曾激动着先辈们的事物。这是他旅行的终点,也是他生命的安居之地。
旅行,有时也可以是一种安居,不是为了远离自己所熟悉的,而是为了更加贴近他们,同时也贴近自己。或者是完全忘记自己,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像一滴水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