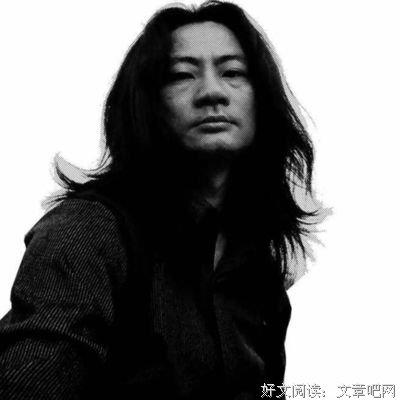
《我们家在康乐里——反对市府推土机运动文件》是一部由黃孙权执导,台湾主演的一部1998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观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我们家在康乐里——反对市府推土机运动文件》精选点评:
●原来台湾有些建筑师不只是做建筑,还在想怎么改造社区,关注点还是具体的人。好开眼的片,从头到尾的干货。台北抗拆第一线!好劲!原来拆不动都是直接放火的!导演跟伙伴做的民谣“大爷吃早餐”原来是个悲伤的爱情故事。。。
●看完会感动,特别是那个二十年前的青年一同样一种姿态站在你面前的时候
●如果想象力能夺权,那我们要想象些什么?
●黄孙权这个人真有意思,第一次在成都看到此等人物,却还是个台湾人。
●守卫家园,维护尊严,从来都是与政治息息相关。
●结尾强拆开始防火烧屋的时候,我就在想,丧尽天良!道德沦丧!有悖人伦!
●震撼。想再看一遍。
●
●映后见面会收获好大,听导演讲话好像在听杨德昌电影里的台词,“反正你们不要相信他们就对啦”
●今年看过最好的纪录片。
《我们家在康乐里——反对市府推土机运动文件》观后感(一):诸众之貌
10.22在深圳看了这场放映,之后是导演黄孙权的讲座。他说这部片子是他在台大城乡所读研究所一二年级的时候,一群学建筑、学都市计划的学生的作品。
他们的初衷是,若是被抓走了,可以在法庭上把这些片子播出来作为证据。“拍纪录片是很残忍的事情,差不多在这个片子拍完之后的三年里,我都经常去参加葬礼,因为很多伯伯搬走之后没多久就过世了”。
纪录片是他们参与群体活动的一种方式,目前导演和他在大陆、港台的学生、合作团队一起做了叫做“诸众之貌”的program,希望记录下来亚洲群体事件中,每个参与者的面庞,从更细致的角度去理解群体活动的过程,而非仅仅记得一两个所谓的英雄人物。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诸众之貌”的网站看看,上面有非常丰富的影像资料,也常年需要愿意帮忙的义工。
《我们家在康乐里——反对市府推土机运动文件》观后感(二):昨夜映后谈
上海影视文献中心 2016.12.10 晚6:30
黄孙权映后谈,阿花主持。
那时搞运动都会有主题曲-就像竞选曲一样
黄孙权经常自己作词
如本片中《穷人的坟场》一曲即由他作词,彭扬凯作曲,改编自陈水扁竞选台北市市长歌曲《台北新故乡》
更让人记得的是《大爷吃早餐了》这首曲子,黄孙权作词,杨友仁作曲。这首歌曲与片中最让人一致安静下来的事件有关。拆迁前四天,一位本省大妈天天早上去看望并给他送早餐的一位“违规”住在康乐里的退伍老兵大爷没有开门,门被锁起,与平日不同。待到大伙儿破门而入,他已经过世,以半蹲上吊的姿势显示他的决心。
片子剪完后,每隔一段时间黄就会去参加一次从康乐里被动迁的老人的葬礼。
片子曾在台北市府对面广场上召集原来住在康乐里的居民观看放映。
拆迁当天康乐里约有4处着火点,放火的人是谁?公权部门没有追究。
这两处为了动迁而搬出来的所谓“公园用地”是在台北市人口才30万的时候当时执政的日本政府划定的,而今台北市超过百万人口,原来被划定的公园用地还有一半没有被使用,这都是连年GDP在8~9%增长的代价。
最为支持康乐里拆迁的人群是住在附近高楼广厦里的中产新富。然而中产又一个好处,当他们意识到在制度的框架底下没有那么多利益好捞的时候,可能会唤起原本的良知来关心弱势人群,但是如果法律本身,制度本身就在告诉他们有利益可以往自己身上倾斜,如何能够要求他们来放弃这些?
黄老师目前执教于高雄师范以及中国美院。他说纪录片、展览都是他做社区工作的副产品。想知道黄老师在大陆也一边教书一边带着学生做社区工作吗?是怎样的社区工作?是与建筑有关的吗?和城市更新一定有关……
《我们家在康乐里——反对市府推土机运动文件》观后感(三):这部将反拆迁运动的电影,为何如此触动人心
曾住在康乐里的老人们在讲这部影片之前,要先说说康乐里和台湾1997年的“反对市府推土机”运动。
康乐里:台北市现第十四、十五号公园所在的地块,亦即中山区林森北路与南京东路的交界。日据时期这里是日本公墓,1949年国民党战败后,从山东和江苏等地撤退的士兵及其家属经由海南岛来到台北,在无住所分配和新工作的情况下,他们自谋生计,在此搭起简陋棚寨聚居,后来慢慢吸纳从台湾其它地区来的移民而发展成一个社区,称康乐里。
被拆前的康乐里在被拆前,康乐里的建筑均为低矮的自建房,以砖木结构加塑料板为主,居住着约3000多人,1000多户,其中超过三分之一户为老兵(台湾称为“荣民”)、残障者、临时工、低收入户和贫困家庭。
反对市府推土机运动:1956年,台北市按日据时期的城市规划把这里编为公园用地,但多年来因为住户争议及预算方案的多次反复,公园计划一直未能实施。1994年,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曾深入康乐里,发动居民参与讨论,提出了“就地整建、社区重建”的设计方案并获得了台北第一届 “市民参与都市设计奖”。1995年陈水扁就任台北市长后继续维持公园计划,但承诺先建后拆,妥善处理拆迁户的补偿和安置,后在1997年1月又推翻这一原则,决定在3月4日执行强行清拆。在康乐里居民到市议会抗议无效之后,台大城乡所联同超过100多个知识界知名人士及民间机构在2月1日签名发起“反对市府推土机”运动。
以下文字涉及中度剧透,如有顾虑可避开~
拆迁
面对不公平的待遇,康乐里的居民在里长的带领下,来市议会大楼找阿扁对峙。面对不信守承诺的指责,阿扁早已想好了说辞,狡辩称“先建后拆”就是拿到建照后便拆。这一典型的政客行径,激起了学界的反感,台大城乡所的教授与学生发起了“反对市府推土机”的声明并举办论坛邀请社会各界人士,试图与政府对话,讨论合理方案,暂缓拆迁。
政府并没有做出什么积极回应,还是在按部就班地执行拆迁计划。很快,康乐里的居民接到了正式的拆迁通知,被拆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康乐里的住户决定珍惜时间,多联络联络感情,为后面的事情做准备。
死亡
就在学界努力谈判,居民联合签名陈情时,一件事的发生使所有的沟通都失效了。
退伍老兵翟所祥先生在自己家中上吊自杀,导演黄孙权是第一批赶到的那群人。据他所说,因为翟大爷的房间十分低矮,想要上吊自杀,必须要半蹲着抱着膝盖才可以。其痛苦的死亡过程,让人难以想象。
翟大爷痛苦的死亡引起众怒面对突发的事件和愤怒的民众,政府首先做的是回避,康乐里里长带领居民再次包围了议会大楼。
随着矛盾的激化,越来越多的问题被揭露:社会局答应给拆迁住户分配的安置房,被指出根本没有位置;社工说“没问题,已经安排好了”,可是居民却收到没有位置的回复。
负责人声称在努力安置遭到反驳,“本来就没有做,是学者提出来之后你们才做”。
老人的自杀,将政府和居民的沟通渠道彻底切断,也暴露出政府根本不在乎这些低收入者的死活。
希望
拆迁进入最后倒计时,各界动用一切力量做最后的抗争。晚会在一片悲伤的气氛中开始,几十张桌子上冒着热腾腾的饭菜,几百人围着桌子心凉到冰点。
当自创歌曲《我们家在康乐里》唱起时,所有人哭成一片。这场坚守家园的晚会,最终变成了哀悼会。
政界、学界等各界人士纷纷上台讲话,时任行政院政务委员的马英九承诺拆迁当日会到现场一起坚守,原住民音乐人胡德夫也来到现场用歌声表达支持……
随后,居民在路边竖起《穷人的坟场》石碑,点起蜡烛,焚烧遗物,为翟大爷哀悼,也为康乐里哀悼。随即,许多市民也自发地加入此次坚守家园的运动中。
拆迁当晚,抗议人群堵满了整条街道,这是他们最后的希望,也是最后的坚守。
拆迁开始时,政府派出1200名警员维持秩序,各种大型工程车也随之开到,当晚康乐里发生了六场大火,火光映红了半边天。一晚上的焚烧与拆除,康乐里社区就此消失……
我在看这部片子时,泣不成声,一方面觉得不甘,而更多的是无力。
导演采访的老住户中,有好几位都是山东人,那纯正的山东方言,在一众台湾腔中显得那么格格不入,却倍感亲切。
因为口音问题,采访时下面配的字幕都是残缺不全的,没人知道他们嘟囔的到底是什么。
他们是一群被社会和历史遗忘的人,一群付出了一辈子,却始终活在最底层的人。
战争时被迫离乡,漂泊到海峡另一边挣扎求生,在一片坟墓上盖起了房子,却在迟暮之年被强拆……
导演在采访时很少提到“强拆”,不得已提到时,老人没说几句便哽咽起来。八十多岁的老人,自打退伍就住在此地,如今只剩自己一人孤苦伶仃。人越老越想家,他却再也回不去了。
政府的强拆相当于加快了这些老人的死亡速度,将他们流放到残酷而陌生的环境中折磨至死。
双目失明的老太,在邻里的帮助下可以正常生活。生病有人来照顾,行动不便有人帮忙买菜,电器坏了有人会维修……
这是个关系紧密的社区,是几千人最后的庇护所。
可政客和商人关注的永远是利益,是价值、发展和政绩。有价值的是这片建筑下的土地,不是这片建筑里的人民。
这种把康乐里指认为贫民窟、认为它有碍城市观瞻的长官论调,其实是一个司空见惯的拆迁借口,与之相随的是把康乐里的弱势人群视同废物的潜意识。
他的同僚在与运动人士的谈判中,就曾口气强硬地指出,“老人不搬也会死”。
面对强拆,我们所能做的选择只有两个——妥协或抗争。但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两种选择最后的结果只是殊途同归罢了。
导演黄孙权是参与反拆迁运动的总召,在后来的采访中,他说自己拍摄这部片子的初衷带着点鱼死网破的意味:若是被抓走了,可以在法庭上把这些片子播出来作为证据。
“拍纪录片是很残忍的事情,差不多在这个片子拍完之后的三年里,我都经常去参加葬礼,因为很多伯伯搬走之后没多久就过世了”。
——资料引自豆瓣、欧宁《城市更新及其对抗》与机器人马文原创文章《没有什么是强拆解决不了的,如果有,不存在如果》。
原文发表于公众号“呆丸星球”
https://mp.weixin.qq.com/s/tcobdjHeFq95qYFbOt-0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