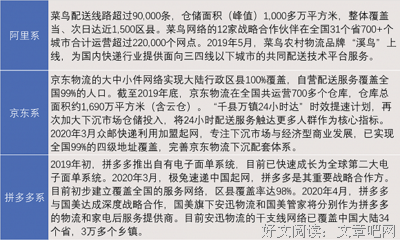
《反对有理》是一本由马克·图什内特著作,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6.00元,页数:21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反对有理》精选点评:
●宪政简史
●我所见过最糟糕的翻译之一
●看得我挺开心的...在案例里见到dissent的时候可惜的发现碰上的不是这种历史意义的反对,虽说也有理~
●杜若姐送的... ...就是京东的质量,太烂了,像盗版
●有一部分翻译得不太好!
●异议的影响终将被时间稀释——这是种非常虚无的感觉。
●每个公民都有提出异议的权利!
●I DISSENT 直译成 我反对! 更有力量.
●看了前几个案列,很晦涩难懂...... 而且都是跟宪政有关的,貌似读起来有点距离。
《反对有理》读后感(一):异议的勇气
此书未看完,不过我想说的是提出异议总是需要勇气的,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都需要提出异议的勇气。
书里冗长的人名和历史事件,令我觉得自己的知识很贫瘠,我不得不边看书边搜集相关资料。
五十字够未?
五十字够未?
五十字够未?
五十字够未?
《反对有理》读后感(二):翻译的很晦涩
《反对有理》读后感(三):异议与权威
刊于《法治周末》2010年12月17日
按照一般的认识,参与案件审理的法官对案件得出相同的结论,形成全体一致的判决,可以体现出判决的权威性、立法的准确性。面对全体一致的判决,胜诉一方自然欢喜,败诉一方也无话可说。根据法律要求权威性的共同特点,美国的法院按理也应该消除异议,采用统一的法院裁判意见才是。可是作为美国司法分支的最高机构,美国最高法院至今仍坚持法院意见和异议同时对外公布的做法。这不禁让人疑惑:异议与权威,是否真的截然对立?
和美国最高法院众多带有异议的判决一样,上面这个问题并没有全体一致且恒久适用的答案。
全体一致的权威
美国建国之前及建国初期,法院沿用英国司法传统,由各法官单独发表裁判意见。待到约翰·马歇尔担任首席大法官后,最高法院改变规则,采用全体一致或多数意见作为法律意见的方式。马歇尔对全体一致意见情有独钟,任内常采用“饭桌讨论”等方式协调其他大法官的意见,争取使最高法院对外用同一种声音说话。马歇尔是一位优秀的领导者,他在这方面做得非常成功。终其任内,最高法院的异议判决书都十分少见。
二十世纪中期沃伦法院期间,州长出身的首席大法官沃伦也偏好全体一致判决。在影响巨大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中,为了劝持不同意见的大法官改变立场,沃伦迟迟不作出判决,以留下充分的时间让持反对观点及立场摇摆的大法官们改变立场。为了争取保守的里德大法官最后一票,沃伦甚至不惜在判决书中暂时去除救济措施部分。
马歇尔和沃伦对全体一致意见的热衷有其特定的背景。在美国建国初期,相对于国会和总统,最高法院力量羸弱、地位低下。另外,作为一位积极支持扩大扩大联邦权力的联邦党人,马歇尔需要利用最高法院来平衡当时仍处于强势的各州。要实现这些目的,最高法院需要提高其权威。作为一位政治家型大法官,马歇尔深知全体一致意见对于提高最高法院权威的重要性。所以,马歇尔用他天才的领导才能尽量统一大法官们的意见,使得最高法院在面对强势的国会、总统及各州时显得团结坚定,判决不容置疑。
沃伦所处的时代,正是美国民权运动高潮时期,整个美国社会处于一场大变革的关头。摆在沃伦法院面前的,是一场近一百年前南北双方六十万士兵用生命都没有解决的政治难题。现在,或许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弥补自己没有做成总统的缺憾,沃伦选择通过最高法院的判决来解决黑人民权问题。沃伦所面对形势之复杂,同他的前辈马歇尔所处环境不相上下。正因为此,沃伦也选择了同马歇尔一样的方式,极力促成全体一致判决,为判决增加权威性,以免给南方留下反驳的余地。
然而,即使是在强势的马歇尔时代,作为传统的异议仍然存在。在1804年的Simms & Wise v. Slacum一案中,威廉·帕特森大法官表示了自己的异议,这应是目前所知的最高法院实行法庭意见制度之后最早的一份异议。
只有胜负,没有对错
自从最高法院可以自由决定挑选需要审理的案件后,大法官们有意挑选那些涉及原则性问题的案件进行审理。案件审理数量的下降也使得大法官们有更多的精力详细阐述自己对法律问题的看法,最高法院的反对意见及协同意见的数量也因此迅速上升。
但异议的增加并不意味着美国最高法院判决权威的下降。
在过去一个世纪的背景环境下,最高法院异议的增加是必然的。盖因进步主义思潮后,最高法院向能动主义方向的转变,大法官们更多地主动参与到社会变革之中,有意无意的成为重大社会问题的立法者,而不再是传统的那个“最小危险部门”。而且作为宪政一极,最高法院本身也是一个政治机构,它的定位决定其所审理的案件具有更多的政治属性。政治关乎民意,民意不可能全体一致,于是就要妥协与共生。也正因为此,现在最高法院的许多的判决“只有胜败,难分对错”。
譬如事关妇女堕胎权的罗伊诉韦德案,原告一方以隐私权和身体自由选择权为法律依据,反对一方以胎儿生命不可侵犯为法律依据。权衡双方论据,一方是怀孕妇女的身心健康,一方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二者孰轻孰重?对于这个问题,中立裁判的大法官们和社会旁观者们谁都不能绝对确信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在该案判决三十年后,原告罗伊改变了立场,成为反对堕胎的代表人物。这一巨大转变也为最高法院的异议的存在和增加的合理性提供了绝佳的支持例证。
异议也维护权威
《反对有理》读后感(四):为什么异议?
为什么异议?
马克•图什内特
这是一种令人欣慰的说法,但事实是,异议者一直不乏其人,我们却完全不知道历史会认可谁、抛弃谁。一旦我们意识到,也一定会意识到,有些异议者在表达不同意见时就错了,以后仍然是错的,这样一来,关于异议的叙述、以及历史如何决定谁赢谁输,就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了。
一、异议真的有用吗?
我们习惯于认为,你应该、或者至少可以发表异议,解释你与同事意见不一的理由。然而,怀疑者可能会认为,发表异议难道不是自我放任吗?基本上毫无意义,很可能适得其反。毕竟,你和同事都看的是同样的材料,凭什么你就认为自己对法律的理解比同事们的看法更合适?当然,如果你认为他们能力不如你,或者不如你对待工作尽职尽责,你大可以反驳他们的结论,但是,这样一来,你是不是有点妄自尊大吗?
你可能会觉得,发表异议表明自己曾尽力争取,但最终失败了。所有的这些只意味着,你自己的感觉可能会好那么一点点,可以向你希望得到支持的那些人表示,你和他们是一起的。总之,即便原告的结局更糟,你也会感觉更好一些。忽视真正输掉案子的人的感受,把异议看作是用一种不引人注意的方法,来安抚自己的良心,这是可以理解的。当然,有时候你会认为,肯定地附和多数大法官的判决,等同于与恶魔合作。这正说明了一个现象:“某某大法官不同意”,但没有发表完整的异议意见。(当然,今天的法律助手不会让大法官如此简单地脱身,让法律助手起草一份异议很容易。)
当法院需要政府官员与普通民众的支持,以保证法院的判决真正得到实施时,发表异议可能会削弱法治的担心就更重了。典型的例子就是学校隔离案。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及其同事们的法律分析结论是,种族隔离违宪,但他们担心,异议会向判决的反对者——他们知道有很多反对者——提供炮弹,指责法院的行为不合法。当异议意见本身就时常提出这种指责时,这方面的担心就更甚了,这些指责,有时是暗藏在自身的法律分析中,有时是通过毫不掩饰的陈述:多数意见的判决不是法律分析的结果,而是多数大法官个人偏见的产物。
当然,你还可以继续认为,以这种方式削弱法治是件好事。毕竟,你认为多数大法官的判决,作为一种法律是错的,有可能甚至错得很离谱。依你看,你当然希望这样的判决不要“持久”。也许是这样。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法官仅仅只是解释法律,并不是在实施他们偏好的政策,当争议并不是那么大时,异议意见的危害,可能会超出你从解释自己为何对、同事为何错中所得到的自我满足。(比如说,法官为何发表长篇大论的异议,解释联邦税法或养老金法含糊其辞的条款,就很让人费解。)
赞同你异议的人,可能不会发表那些完全一样的、给他人带来麻烦的言论,律师也会说,他们批评政府的言论,与你同事认为应该受惩罚的言论,还是有区别的。你的异议可能会促使检察官与低级法院法官重新考虑,是否将法院判决“扩展”到新的情况。
所有的这些构成了一个复杂、并很可能错误的“理论”:一个案件如何成为其他案件的先例。我们继续来看这个例子:去年,你的同事判决批评政府者有罪,你发表异议。今年,另一个案子到了最高法院,涉案言论很相似,但稍有不同。结果可能会怎样?
你同事认为,去年判决有罪时所使用的原则,今年同样适用。你的异议对判决结果不起任何作用。
你同事认为,去年的原则不能涵盖今年的言论,允许发表这样的言论。同样,你的异议还是不起作用。
你该怎么办?
你仍然认为去年的判决是错的,并坚持己见。你并不在意今年的言论是否与去年不同。
至此,你在第一个案件中的异议对第二个案件不起任何作用。当然,还有其他多种可能。
你去年的异议可能触动了你同事的态度,其中一些人改变了看法,站到你这边来,同意推翻他们去年作出的判决。这是可能的,并且会发生。但并不会经常发生,这也没什么奇怪的,毕竟,你去年提出的理由当时并没有说服他们,除非发生新情况(这是重要条件),否则很难想象,为什么同样的理由今年就突然打动了他们。
你也许会对自己说,你有责任适用完整的法律,应该考虑去年的先例,然后你这么做了,将最高法院的(错误)原则用在今年的案件上。这样一来,你也赞同将发表这种言论的人送进监狱。这样的事也会发生,但是很少,原因很明显:你认为,如果同事们去年正确适用法律,被告就应该获得自由,但是由于他们去年弄错了,被告进了监狱。这不是你希望作出的合理判决,只要有可能将今年的案子与去年的案子区别开,你会非常倾向于认为,即便依据同事们提出原则,这两件案子也是不同类的。
所有这些得出一个结论:在短期内,你的异议不会对结果造成太大影响,无法阻止你的同事延续他们的错误判决,当然,他们可能会依据自己的理由,不再在新的案件中重复自己的逻辑。
二、异议如何起作用?
这是常规情形,当然也并不总是如此。偶尔,总统候选人也会发现,批评最高法院也对竞选战略有帮助。理查德•尼克松就是这么干的,他在竞选总统时提倡“法律与秩序”,说他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将推翻沃伦法院在刑事程序问题上的开明判决先例。这样的总统候选人可能会利用最高法院内的异议,来充实自己的政治演说。但是,即便在这类总统竞选中,候选人的胜败也很少依赖最高法院争议的问题:1990年以后,民主党人一再极力警告支持堕胎的选民,不要投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票,因为这些人一旦当选,就会任命大法官推翻罗伊诉韦德案,但这种警告并不起作用。
异议起作用的途径如此间接,也促使我们自然而然地提出一个关于异议的疑问:如果异议占上风,我们的世界会如何不同?在某种意义上,答案通常会很简单:“不会有多大不同”。无论最高法院如何判决德雷德•斯科特案,几乎肯定还会有内战;无论最高法院如何判决民权案与普莱西诉弗格森案,南方的非洲裔美国人也几乎一定会受到实质性歧视。这个世界不会有太大不同,原因也很简单。我们世界的呈现方式,更多的是由经济、社会变迁、人口统计等因素决定的,而不是最高法院的判决决定的。走完我所说的间接影响路径,需要很长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很多事情都会改变。当证明异议是正确时,我们是该解释说这个判决从一开始就是对的?还是要提出,在写作异议与异议成为法律这段时间里,发生了其他事情?
异议有作用,但几乎总是间接性的,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形成我们对最近异议的看法。异议的时间越近,就越难判定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将来发展,是会将异议弃之不顾,还是使其越来越重要。
三、其他需要讨论的问题
异议的修辞。司法意见书的写作风格一直在改变,早期的司法意见书比最近的司法意见书用词更华丽。约翰•马歇尔•哈伦大法官的意见书极其冗长,即使经过编辑,很多地方仍是空话连篇,没有提出任何清楚的论据。罗伯特•杰克逊大法官的写作更加洗练,在言简意赅方面是位大师,不过,他有时候也很难从头至尾坚持连贯的论证。在当今的最高法院,安东宁•斯卡利亚大法官娴熟地运用“以意见书为攻击炮弹”的手法,为报刊评论的作者提供可供直接引用的批评语句,后者可以原封不动地照搬到的自己的评论中。路易斯•布兰代斯在惠特尼诉弗吉尼亚案中的异议,无疑是典雅的散文篇章——它出自我们认为具有会计师灵魂的布兰代斯大法官,多少有些让人称奇。
作为先例的法律原则。就像我们必须解释多数意见一样,我们也必须解释异议,才能弄清其含义。还有,正如多数意见一样,异议的含义不仅取决于作者的表述,同样还取决于我们选择如何来理解。先例——这里我们讨论的是作为先例的异议——可以向多个方向延伸,其词句通常不只是为未来提供一种含义。本书中最生动的例子是约翰•马歇尔•哈伦大法官在普莱西诉弗格森案中的异议。这份写于十九世纪末的异议,在二十一世纪既用来解释为什么说肯定性行动违宪、还用来解释为什么说肯定性行动完全合宪。重要的是,双方都没有“误用”这份异议。无论是赞同肯定性行动还是反对肯定性行动的主题,都可以公平地在这份异议中找到,哈伦大法官并不需要作出选择。两个主题都要求他推翻普莱西案所提及的种族隔离法,他没理由操心将近一百年后才会出现的肯定性行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