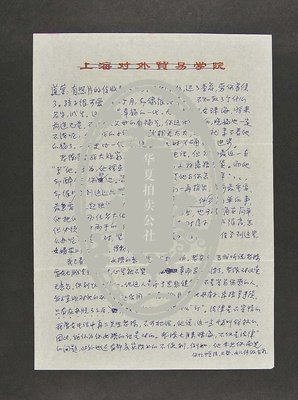
在散文《儿女》一篇中,当丰子恺把“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从上海的租寓,送回乡间,他的内心充满虚空。把小孩子们穿得破旧的鞋子整齐地摆在自己的床下,看着它们,内心便感到“一种无名的愉悦”。
每次返回乡下的家中,他的生活便充溢着生的欢喜。夏日的傍晚,他领着四个孩子,在小院中的槐树荫下吃西瓜,看三岁的孩子笑嘻嘻的摇摆身体,口中发出花猫偷食的喵呜声;听五岁的孩子发表他的诗歌,欣赏七岁和九岁的孩子饶有兴味的散文和数学,内容不外乎“瞻瞻吃西瓜,宝姐姐吃西瓜,软软吃西瓜,阿韦吃西瓜”,“四个人吃四块西瓜”之类的童言稚语。等孩子们尽情表演完后,他再颇为认真地评判他们的作品。在丰子恺看来,“天地间最健全者的心眼,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世间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能最明确、最完全地看到。我比起他们来,真的心眼已经被世智尘劳所蒙蔽,所断丧,是一个可怜的残废者了。”
小院平屋的南窗下暂设一张小桌子,上面秩序井然地布置着笔墨纸砚,是丰子恺独有的空间。丰子恺平常对此总是谨慎,细心,端详,斯文,不喜欢别人任意移动。然而孩子们一爬上来,乱挥水笔,泼洒墨水,把笔尖蘸在浆糊瓶,撞翻茶壶,打碎壶盖……把个秩序井然的桌案搞得一塌糊涂,惹得他这个父亲不免不耐烦地哼喝着,去夺取孩子们手里的笔墨,然而这时,丰子恺往往又会转瞬即悔:“哼喝之后立刻继之以笑,夺了之后立刻加倍奉还,批颊的手在中途软却,终于变批为抚。”且立刻自悟其非:我要求孩子们的举止同我自己一样,何其乖谬!
在丰子恺的画集序文《给我的孩子们》中,对小儿瞻瞻尤其佩服,称赞他是“身心全部公开的真人”,“甚么事体都像拼命地用全副精力去对付”。对外婆普陀烧香买回来的泥人“鞠躬尽瘁地抱他,喂他”,被自己失手打破后,嚎哭地比大人的破产、失恋、全军覆没的悲哀都要真切;每次父亲剃了头,他真心地怀疑父亲变成了和尚,好几时不让父亲抱;发见父亲腋下的长毛,当作黄鼠狼,立刻爬下,瞪眼端详,继而大失所望地伤心号哭,如同对判了死罪的亲友一样;弱小的身体却创造强盛,要把皮球停在壁上,要拉住火车尾巴,要月亮出来,要天停止下雨。看到父亲把从书店买来的新出版的毛边《音乐入门》用小刀将书页一张张裁开。自己也得意地在书架上拿了一本连史纸印的中国装《楚辞》,裁破了十几页,还欢喜地向父亲夸耀自己得意的作品!结果是,被父亲惊骇的表情吓哭。
在丰子恺的心里,儿童即是尘世的天使和神明,孩子们的一切都是自然天籁,都是值得敬畏与怜惜的。一如作者在文末所言:“这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是在人世间与我因缘最深的儿童,他们在我心中占有与神明、星辰、艺术同等的地位。”
读这两篇文章,我很自然便想到周国平的《妞妞》。同样的溺子深情,同样对自然生命的尊重与热爱。由此我想:一个人,越是知识广博、思想深刻,越是懂得如何善待生命,如何欣赏和赞美一切本真的情感与行动;越是知识浅陋、思想狭隘、精神懦弱的人,越是容易去苛责和压制别人天性的纯真与奔放的自由:因为他们自己的精神世界也是残缺而扭曲的。
继而想到我们今天的教育对儿童天性的压抑:下课除了上厕所,不允许下位走动,更不要说跑跑跳跳,说说笑笑;体育课除了跑步、跳绳和偶尔的篮球运动,其他一切含有安全隐患的体育项目早已全部取消;自习课检查要“零抬头”;服装、发型要整齐划一;除了上课和考试,一切实践活动皆为“纸上谈兵”;甚至于读课外书也被某些人认为是 看“无用的闲书”。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培养出来的人会是怎样呢?当一个人活泼泼的自然天性被压制和囚禁,剩下的恐怕唯有病态的社会性,踽踽独行。呜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