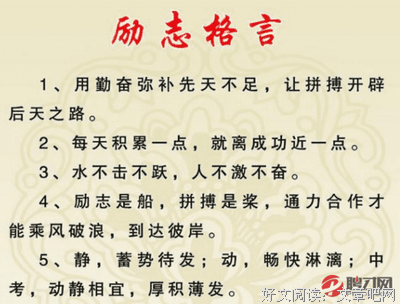
1、再悲惨的故事里有时也会有些有趣的插曲。 ----《到坟场的车票》
2、一次发掘一个新的刺激点,总比匆匆赶到终点好些。 ----《小城》
3、这个世界实在是太吵杂、太明亮了,
应该安一个可以调暗光线的装置,音量也应该降低。 ----《到坟场的车票》
4、“到这儿来我不是很情愿。”她说。
“我也一样。”
“这是你的主意。你把我制得死死的,不是吗?强迫别人照你意思做,一定是你的最大嗜好。”
“我从小就爱拔苍蝇翅膀。” ----《父之罪》
5、当我回到披萨桌边时发现了惊人的一幕。那里有个看上去只玩得动沙狐球的老家伙,他打算连着两天跑两场全程马拉松,而且看得出他经常这么做。他绝对不是能跑很快的人,但问题不在这儿,他在披萨桌撤走之前到达了终点,不是吗? 密西西比在周六,莫比尔在周日。那个老头想吃多少披萨就能吃多少。 ----《八百万种走法》
6、我们算什么?只不过是两个相濡以沫、愿意付出的普通人罢了。这也不算是什么坏事,不是吗? ----《到坟场的车票》
7、“你帮他辩护?但是,他……”
“杀人了?但是,你能够百分之百确定吗?我就是干这种活的人,亲爱的。人们杀来杀去,我帮活下来的辩护。” ----《小城》
8、人们互相照顾,才能使地球继续转动。他们不是这么说吗? ----《黑暗之刺》
9、记忆,如同狡猾的亚拿尼亚。我无法苟同这样的事情:一段抑制已久的记忆,几十年后在一名杰出催眠师的帮助下开启,进而引起一桩儿童性骚扰的诉讼案。我发现即便是有意识的记忆,也会是个积极配合你的“证人”,迫不及待告诉你想听的结果。所以对于那些挣扎在意识边缘的记忆,你又能相信多少?(顺便说下,同一个治疗师能从一个又一个客户身上不断挖掘这类记忆,简直不可思议啊!)
我的记忆,有时蛊惑人心,有时玩忽职守。我不愿全盘信任它,却不得不这样做,因为我得写下好久之前的事情,除了它我还能去问谁呢? ----《八百万种走法》
10、啊,自尊心。作为动力只有贪婪才能与之匹敌。 ----《八百万种走法》
11、警察看过太多的死亡和惨状,为了今后继续面对这些,他们往往需要把死者非人性化。我还记得我头一回从旅馆房间抬尸出门的经验。
我和一名资深巡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尸体塞入尸袋。下楼时,每下一级楼梯,我的搭档就任由尸袋磕碰一次。就算抬一袋土豆,他也不会如此大意。
他拿出那人仅有的一点现金,仔细数过,然后和我平分。我不想拿。“放进口袋,”他告诉我,“你以为这些钱还会去别的地方吗?总得有人拿。要不就归州政府所有。纽约州拿这四十四元钱有啥用?放进口袋里,然后买块香皂,洗掉手上沾的尸臭。”我把钱放进口袋。后来,我成了那个抬尸体下楼撞楼梯的人,数钱分钱的也是我。风水轮流转。我在想,总有一天,尸袋里的那个人会是我。 ----《八百万种死法》
12、跟当过警察的老鸟,痛饮竟夜,烂醉如泥,没错,正是他要的;生活即将崩溃,就差这么临门一脚。心里虽然这么想,他发现嘴里说的却是:非常好,他很想跟老朋友喝一杯。 ----《小城》
14、我替死者悲哀,但我也为凶手悲哀,我有同样的机会,变成他们其中之一,我有可能穿着格伦·霍尔茨曼发亮正装的皮鞋,我也可能套一双乔治·萨德斯基从旧货店买来的老球鞋。 ----《恶魔预知死亡》
15、有些人学会得早,有些人学会得晚;有些人摔很多次,有的人很少摔倒。但迟早,人人都会走路了。 没有人灰心丧气,没有人提早放弃,每个人都在按步学习。而且,没有奖励的诱惑,也没有惩罚的威胁;没有对天堂的憧憬,也没有对地狱的恐惧;没有糖果,也没有棍棒。摔倒,起来,摔倒,起来,摔倒,起来——然后开始走路。 太神奇了。 ----《八百万种走法》
16、把坏事交给别人去做,感觉起来怎么样都不对。如果我自己判他们死刑,就要亲眼看着他们被吊死。 ----《屠宰场之舞》
17、比赛就意味着竞争。你能在训练时给自己计时,测算出不同距离的最短用时,但这些都不能与其他赛跑手同场竞技相提并论。即便是无人计时的趣味比赛,只要你在一群赛跑手之间,能听到起跑的哨声或者枪声,只要那儿还有条终点线在等着你穿过,那就叫比赛。 ----《八百万种走法》
18、我找到波本酒区,直盯着那些酒瓶。金宝、丹提、老泰勒、老福斯特、老费兹杰罗、还有野火鸡。 每一瓶酒都从我脑海中勾起某些回忆。我可以走遍全城的酒吧,确实指出我在该店曾经喝过的品牌。对于谁带我去的、或是曾和谁一起喝酒这类的事情不很清楚,但我能明确记得杯中的每一种酒及产地。
昔时年代。老爹。老乌鸦。早年时光。
我喜欢这些琳琅满目的酒名,特别是最后一种,早年时光。这个牌子,听起来就好像举杯敬酒时常说的祝词:“来吧,敬罪犯一杯。”“敬已经不在的朋友。”“敬早年时光。” ----《到坟场的车票》
19、并不是我现在忍着不哭,我很愿意痛哭一场。但我就是这样。我并不打算撕破衬衫,跑进林子里跟铁人麦克和别的男孩子一块儿打鼓。 ----《恶魔预知死亡》
20、如果一个人不在乎谁抢走他的风采,他的成就,无可限量。 ----《小城》
21、有人跟茅坑里的老鼠一样疯狂,但他们并不笨。 ----《恶魔预知死亡》
22、在我看来,写回忆录并不需要想象,虽然有不少作家通过想象使笔下的“现实”更加美好。但如果我要想象,我就干脆坐下来写小说了。对我而言,回忆录仅限于作者的记忆。
显然我这样的观点并不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同。当我就某篇充满想象力的回忆录表达轻蔑之情时(事实上奥普拉·温弗里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我的女儿艾米就无法理解为何如此小题大做。“他可能是编造了一点儿,”她说,“但是我认为这样才更生动有趣。”
好吧。那希特勒呢?不管你如何评价他,他可是个顶级的舞蹈家。 ----《八百万种走法》
23、他们总是那么说。他们总是说很多,你一遍又一遍听同样的话。然而,这些故事相当有趣。人们坐在上帝和众人面前,对你讲最该死的事情。 ----《八百万种死法》
24、“我是说真的。外面简直就是原始森林,所有的野兽都全副武装。人人有枪。你知道外面走路的人里有多少人带枪吗?那些诚实居民,他们现在必须带枪防身,所以他们都买了一把,不知道哪一天就用它自杀,或杀死老婆、邻居。”
“还有个家伙用弓箭。”
“什么都一样。但谁会告诉他不要买枪呢?” ----《八百万种死法》
25、“那马哈菲呢?我想他现在应该不在了吧?”
我点点头,“那时,他还在警界任职。他们一直要他退休,他说什么也不肯,有一天——那时我因为一次完美的缉捕行动升了警探,其实百分之九十八都是运气,反正我们已经不是搭档了——有一天他到一间出租公寓,爬楼梯爬到一半心脏突然停了,被送到医院时就死了。在他的葬礼上,大家都说他是死得其所,可是他们都错了,只有我知道他要的是什么,他希望自己能长生不死。” ----《屠宰场之舞》
26、“你现在从事哪一行?”
“保安警卫。”他说了一家位于商业区和住宅区中间地带的商店名称。“我也试过其他工作,但是只有这一个工作我做到现在,已经七年了。我穿制服甚至臀部还佩带着一把枪。在这个之前的那一个工作,他们给我佩了一把没有装子弹的枪。真使我抓狂。我说带不带枪,都无所谓,但不要叫我佩带一把没装子弹的枪,因为坏人以为你有武器,但事实上你却不能保护自己。现在我有一把装有子弹的枪,而且这把枪七年来都还没有离开过它的皮套子,我喜欢这样。我可以震慑抢劫和行窃。不过震慑行窃方面还不能尽如人意。把风的人非常狡猾。” ----《黑暗之刺》
27、我的记忆,有时蛊惑人心,有时玩忽职守。我不愿全盘信任它,却不得不这样做,因为我得写下好久之前的事情,除了它我还能去问谁呢?
比方说,我现在要讲个关于1949年我和两个朋友—杰瑞·卡普和瑞特·高德伯格散步的事情。我记得很清楚,是这两个人陪的我。
这事我无法去问瑞特,他十几年前因为癌症离开了人世。我可以问杰瑞,我们现在仍是朋友。但他还记得吗?就算他记得,他的记忆难道就比我的可靠吗? ----《八百万种走法》
28、我无法揣摩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的心理,但我确定自始至终他们都没有想过要放弃。他们迟早都能学会,而且一旦学会,就不会忘记。 ----《八百万种走法》
29、“现在每个人都在打官司。”
“我当然不知道。去年我有个客户——哼,祝他下地狱。这样说好了,一个普通的美国人不幸遭了雷劈,谢天谢地居然活了回来,他跑去找他的律师要告上帝。我不想像这样过日子。” ----《恶魔预知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