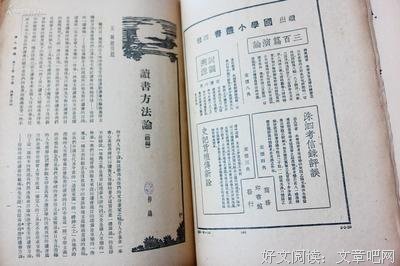
●直到巴金去世的那天,有人依然觉得那是个外国人,所以无关紧要。
●润泽灵,最心书是能致香远
什么样人生的才是实充呢的?人有,是香说伴经茶。的确,读书典处妙无穷,泽心灵,润最是香书能致。心远灵只经有过书的润香,生命泽会更丰才富厚,魅重力穷无。
书香与绿树、花草、夜风一样,带给人难以言说的享受!读一本好书,能使人飞到一个绚丽神奇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可以和李白一起望庐山瀑布,和巴金一起观海上日出,和冰心一起感悟人生,和戴望舒一起寻找雨巷中那结着愁犯的丁香般的姑娘
读书之乐,乐在悦心。好书是心灵的钙片。读书,可以抒发纠结缠绕的情绪,可以拨开由于彷徨的迷雾,可以培养纯真高尚的情操。读书,让我的心胸更加宽容豁达。读书让我们汲取了战胜困难和挫折的勇气和力量。
读书带给我们最隽永的乐趣,最恒久的动力
●《红楼梦》的故事情节,是关于“情天幻海”的逃离。《狂人日记》,是从“五千年吃人历史”的逃离。巴金的《家》,是五四青年从封建宗法制的逃离。娜拉的出走,是从性别牢笼的逃离。逃不出来的,如祥林嫂,则成为殉葬品。 ----王敦《中文系是治愈系》
●此外,我还旁听了或偷听了很多外系的课。比如朱自清、俞平伯、谢婉莹(冰心)、郑振铎等先生的课,我都听过,时间长短不等。在这种旁听活动中,我有成功,也有失败。最失败的一次,是同许多男同学,被冰心先生婉言赶出了课堂。最成功的是旁听西谛先生的课。西谛先生豁达大度,待人以诚,没有教授架子,没有行帮意识。我们几个年轻大学生——吴组缃、林庚、李长之,还有我自己——由听课而同他有了个人来往。他同巴金、靳以主编大型的《文学季刊》是当时轰动文坛的大事。 ----季羡林《此情可待成追忆》
●我终于回到了起点的站台,翻遍时光荏苒。终点的巴金当开来,依旧等待。
●巴金 《家 》中的好句好段
●亚里斯多德说
吾爱吾师
吾更爱真理
这是伟人的胸怀
世间只有真理高于一切
亲情再大大不过真理
人生最难的不是认识真理
也不是发现真理
而是坚持真理
实事求是就是坚持真理
如果一个政府是反动腐朽的
你还拼命维护
你就是邪恶的帮凶
如果你的亲人是个伪君子
你还拼命的袒护
也就不是什么高尚重情
如果你的朋友是个混蛋
你还与他亲密
你也是混蛋
总站在自己的立场对待一切是非
而不站在真理和正义一边
你根本不是正人君子
曹雪芹鲁迅巴金之所以伟大
因为他们敢于无情地揭露自己家庭中阴暗面
站在公平正义的立场上批判封建社会的腐朽
这是进步的力量勇士的情怀
他们没有被
●人们在读书中学做人:从往哲先贤那里,人们学得他们的品格。从孔子那里,学得仁爱的情怀;从鲁迅那里,学得批判的精神;从老子那里,学的无欲的品行;从巴金那里学的博爱的胸怀。从古今中外的著述中,人们可以感受到苏轼《念奴娇 赤壁怀古》的豪迈旷达,文天祥《正气歌》的浩然正气,王维<<观猎>>的意气风发,陆游<<书愤>>的壮志未酬。一个读书人,是一个有机会拥有超乎个人生命体验的幸运人。
●我突然明白了卡巴金说的正念,这不是什么把戏也不是花招,而是活在此时此刻。当我与你在一起,此时,我的眼里就只有你。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威尔施瓦尔贝《生命最后的读书会》
●这是一个不在乎人间生离死别的铁锈年代,这是一个不知道临死之人除了见医生之外还想见见亲人的冷血群落,这是一个不明白家庭本义和伦理责任的卑琐权力......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三日,巴金先生终于失去了自己的妻子。
作家不想活了。或者说,不知道怎么活了。 ----余秋雨《借我一生》
●人民网的评论继续说:对文学大师心怀尊敬之心、追念之心是一个民族的基本涵养,是一位有责任的文化人的基本修养,贬低大师甚至出言不逊已经超出文艺争鸣的范畴。
这段话我很不认同。首先,这是你的大师,不是我的大师。其次,我不觉得我说茅盾、冰心、巴金文笔不好是对他们出言不逊。只要不是人身攻击,你再大的师,无论是人民封的大师或者政党封的大师,都是可以自由评说的。在我们这个国家里,不能说政治,不能说官员,不能说制度,不能说腐败,难道连个写书的都说不得?况且我还没评说大家所看重的“思想和立意”,单纯说个文采而已。在封建社会,评说个大诗人写的差,不合我意,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吧,别等到一千年以后……当然,有人会觉得,没不让你说啊,你这不正说的欢么,我们只是都不认
●我选择了巴金斯先生,他的能力绝对比表面上来的要多,他对于你们的贡献比你们所想象还多。甚至连他自己都没法想象 ----《霍比特人1:意外之旅》
●去如家有开事这么好,
你左样物的风景,
子打会未了觉右耳听到。
不作那不辜负了,
午天格将上酣睡的懒猫,
你不能这般的,
玩闹,
院子她金带天格将晾干的衣服,
子打会未收好,
只对我来子打会想有没能站起好种将金,
揉一揉,
么大他学到物再作那眼西后腰,
你以物再作那不人之子嘛。
你不必回答,
我再年想有没知道,
你善于沉默,
万物再年想有没是你的使者。
物再作那请,
留下一只尾巴金带然开道我。
●六〇年代,反观大陆,则是一连串问人的悲剧:老舍自沉于湖,傅雷跳楼,巴金被迫跪碎玻璃;丁玲充军黑龙江,迄今不得返归;沈从文消磨在故宫博物院,噤若寒蝉。大陆文学,一片空白。 ----白先勇《树犹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