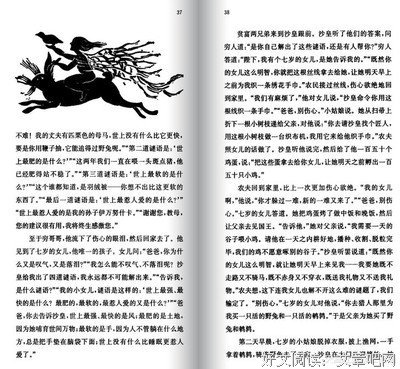●世上最困难的表演就是自然而然的演出,不是吗?除此之外,一切都是刻意技巧。 ----安吉拉·卡特《焚舟纪》
●她的意识已经因为年迈而模糊,每当我走过,她红灼的眼睛总是以同样朦胧而不感兴趣的惊奇眼神看着我,仿佛爱斯基摩人看火车。有时她会说,いらっしゃいませ,也就是店家欢迎客人光临的句子,声音轻得犹如鬼魂飘渺,像纸袋微微窸窣,这时我会看见她的金牙。 ----安吉拉·卡特《焚舟纪:烟火》
●时间,是记忆之敌。 过去与未来非常相似。 ----安吉拉·卡特《焚舟纪》
●时值七月,这城市蒸腾发光,阵阵发臭。到中午,我已经累得发昏,汗水湿透衬衫。我惊见恶臭杂乱的街上有那么多乞丐,老太婆和醉鬼跟老鼠争抢垃圾中最可口的上选部分。老鼠最爱热天。光是走到街角小亭买包烟,都有半打毛皮滑亮的黑色怪兽追咬我脚踝,我得把它们踢开。它们还会站在楼梯两旁,活像仪队迎接我回家,当时我已在下东城租了一间没电梯、没热水的公寓,房东是个年轻男子,前往印度拯救自己的灵魂。离开前,他警告我宇宙即将热寂,劝我关注性灵事务,因为来日无多。
住我楼上的老兵会拿左轮枪射老鼠,楼梯间墙壁满是弹孔。由于楼梯间从来没人清,他的战利品就这么原地腐烂分解。他不是那种清理自己残局的男人。 ----安吉拉·卡特《新夏娃的激情》
●有时候我想,只要够努力张望,就能看见过去。 ----安吉拉·卡特《明智的孩子》
●镜子过滤了所有陌生邂逅的本质,两人对彼此的概念只存在于偶遇的拥抱,只存在于意料之外。在做爱那段似长若短的时间里,我们不是自己--不管那自己又是谁--而是,在某种意义上,自己的鬼魂。但我们当下所不是的那个自己,我们惯常概念中的那个自己,其实质反而比当下我们所是的映影更虚幻得多。魔镜让我看见在此之前不曾思索过的、关于我自己之为我的一种意念。 ----安吉拉·卡特《焚舟纪》
●我看见肉体和镜子,但无法承认这个影像。我当下的立即反应是,感觉我们做出了不符合角色性格的行为。我为了配合这城市而假意穿上的花哨服饰背叛了我,让我来到一个房间,一张床和一个对自己的修正定义,这些全都不该出现在我的人生,至少不该出现在我看着自己演出的这个人生。 ----安吉拉·卡特《焚舟纪》
●在此处,在北方,在这一切平等的纬度,你若想躲藏便必须自己制造阴影。 ----安吉拉·卡特《焚舟纪:黑色维纳斯》
●这里的空气永远充满窒人湿气,永远颤抖着濒临落雨边缘,天空有如透过薄纱照下,因此无论什么时间都像薄暮黄昏。 ----安吉拉·卡特《焚舟纪:烟火》
●骑脚踏车本身就是对迷信恐惧的抵御,因为脚踏车是纯粹理性运用为动能的产物。几何学为人类服务!只要给我两个圆和一条直线,我就让你看我能将它们带到多远。 ----安吉拉·卡特《焚舟纪》
●然而在艺术家的世界里,刻意特立独行的人总是很尊重并敬佩那些有勇气真能有点疯的人。 ----安吉拉·卡特《焚舟纪:别册》
●他有个改不掉的旧习惯,走在街上总有一种期待感,仿佛随时转个弯就会碰上命中注定的邂逅遭逢;只要在外面呆的愈久,发生特殊事件的几率就愈大,而就算什么都没发生,那种有事可能发生的感觉也能暂时缓解他甜闷无聊的人生。 ----安吉拉·卡特《焚舟纪》
●这个国家已经将伪善发扬光大到底最高层级,比方你看不出武士是杀人凶手,艺妓其实是妓女。这些对象是如此高妙,几乎于人间无涉,只住在一个充满象征的世界,参与各种仪式,将人生本身变成一连串堂皇姿态,荒谬却也动人。 ----安吉拉·卡特《焚舟纪》
●但压抑并不只会产生严苛之美。在一切仅仅有条的缝隙中,猛兽般的激情蓬勃生长,他们折磨树木,让树木看起来像是树木的抽象概念。 ----安吉拉·卡特《焚舟纪:烟火》
●有时候幻想和不知所云,也可以让自己伟大,留给别人猜疑的空间,不是推理,只是自我否定与自我认定的过程,挺好的。 ----安吉拉·卡特《焚舟纪》
●现在我没了工作,理性告诉我该夹着尾巴尽快逃,逃回化脓但熟悉的伦敦,至少那是我认识的恶魔。
西谚有云,熟悉的恶魔总强过陌生的恶魔,指即使情况再差,还是不如待在已熟悉的环境、应付已熟悉的事物,等等。 ----安吉拉·卡特《新夏娃的激情》
●生活并不是人类想象的结果,生活拥有无限惊喜。 ----安吉拉·卡特
●他们生也快乐,死也快乐,杯子里总有酒喝。 ----安吉拉·卡特《精怪故事集》
●突然间,我看见了他眼中我的模样,苍白的脸,细钢弦般紧绷的颈部肌肉。从小至今这段天真而封闭的生活中,这是我第一次感觉自己内在有种堕落的潜能,令我为之屏息。 ----安吉拉·卡特《焚舟纪:染血之室与其他故事》
●风吹床单,正是寂寞的声音。 这感觉,淡到极处,反而成了别样风景。 ----安吉拉·卡特《焚舟纪》
●这是个炎热无比的阴天早晨,放眼望去,尽是一片苍白粗粝的灰,空气中满是尘埃,我从未见过如此陈腐的早晨。 ----安吉拉·卡特《焚舟纪:烟火》
●当初浸在他蚀人的眼神中失去了肉体,现在只能住在笼里。 ----安吉拉·卡特《焚舟纪:染血之室与其他故事》
●于是我们活在一轮迷失方向的月亮下,那月亮是愤怒的紫,仿佛天空的眼睛淤血,而就算我们有过真正的交集,也只在黑暗中。他深信我们的爱是独一无二又绝望的,我也因之传染了焦虑不安的病;不久后我们便学会以温柔规避的态度互相对待,仿佛两人同是截肢病患,因为我们身旁满是稍纵即逝的动人意象,烟火、牵牛花、老人、孩童。但最动人的意象是我们在彼此眼中虚幻的倒影,映现的只有表象,在一个全心全意追求表象的城市。 ----安吉拉·卡特《焚舟纪》
●所以我的名字并不能提供任何有关我这个人的线索,我的生活也不能暗示我的本质。 她说她看不清楚这个世界,但对那个即将到来的世界可是一览无遗。 ----安吉拉·卡特《焚舟纪》
●极度孤单难熬的人可能会亲吻镜中自己的影像,因为没有别的脸可以亲吻。这些亲吻都是同一类,是最痛楚的爱抚,因为太谦卑、太绝望,不敢奢求任何回应。 ----安吉拉·卡特《焚舟纪》
●他走投无路,没有害怕本钱。 ----安吉拉·卡特《焚舟纪:染血之室与其他故事》
●浓重的烟雾十本已够暗的灯光更加微弱,室内呈现半黑暗状态。 ----安吉拉·卡特《焚舟纪:别册》
●Anticipation is the greater part of pleasure.
满心期待构成了快乐的大部分。 ----安吉拉·卡特《染血之室与其他故事》
●若要一个女人既是处女又是母亲,你需要奇迹。 ----安吉拉·卡特《焚舟纪:美国鬼魂与旧世界奇观》
●我们住的这条街基本上是贫民区,到但表面看起来充满和谐宁静,因为他们全都循规蹈矩,把所有东西保持得干干净净,活的那么卖力有礼。和谐生活需要多可怕的纪律呀。为了和谐生活,他们狠狠压住自己所有的活力,于是有一种缥缈的美,就像夹在厚重大书里的干燥花。 ----安吉拉·卡特《焚舟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