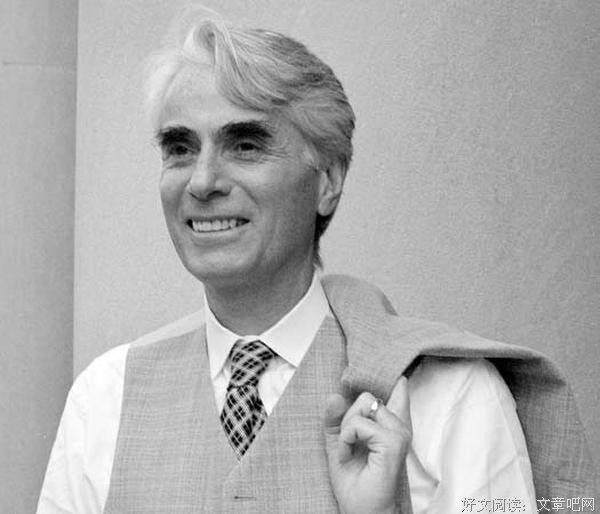●【教室中的中央计划制度】还要进一步补充说明一点。(未来)从事文字工作的知识分子作为正式的、官方的校园社会中的成功者,奖赏则是由作为中心权威的老师分配的。而在教室、在走廊、在学校操场上还有另一个非正式的社会群体,在这些场合,奖赏则不是由某个指导中心分配的,而是由同学们一时兴致和好恶进行分配,而恰在此处,知识分子表现得却并不怎么样。因此,毫不奇怪,那种由一个中央控制的分配机制分配物品和酬劳的制度,会令知识分子砰然心动,相反,对市场的“无政府和混乱”却是避之惟恐不及。实行中央计划体制的社会主义社会之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对立,恰相当于由教师主导的分配与操场上和走廊内的分配之对立。 ----罗伯特·诺齐克《知识分子为何拒斥资本主义?》
●怡悦我,激发我的,是去思考新的问题,提出新的看法,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 ----罗伯特·诺齐克《苏格拉底的困惑》
●为什么当代的知识分子觉得社会应该给予他们最高的待遇,而不能如愿时就心怀怨恨?知识分子觉得他们是最有价值的人,也具有最高贵的美德,社会理应根据他们的价值和美德给予相应的待遇。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不是实行“按照美德或价值分配”的原则。在一个自由社会中,除了个人才能,祖上的传承、运气都能使一个人成功,市场只会青睐那些能捕捉到并满足他人需求的人,至于获利有多少,则取决于需求有多大,竞争的供应者有多少。所以失败了的商人和工人并不会像人文知识分子那样怨恨资本主义。唯有优越感不被社会接受,特殊的权利不被社会承认,才会在知识分子心中产生愤恨。 ----罗伯特·诺齐克《知识分子为何拒斥资本主义?》
●他不知道什么是虔诚,什么是勇敢,什么是正义。对于任何问题,他缺乏一个完全充分的真信念。对于任何观念,他缺乏一个正确的充要条件。对于这些概念之间的联系,他更缺乏一个正确的理解。因此,当苏格拉底说他不知道答案时,他并不是反讽。他不知。他自知不知。 ----罗伯特·诺齐克《苏格拉底的困惑》
●苏格拉底展现了更丰富的一面:即那种不懈的探索所塑造的人格。苏格拉底教导我们的,不纯然是探索真理的方法,更是他身上体现出来的方法(及引导他的那些信条)。我们看到,苏格拉底活在他的探索中,活在他与别人的探索交往中。我们看到,探索的方式如何塑造了苏格拉底,渗透了他的生,他的死。苏格拉底是以身传教的,一如佛陀与耶稣。在哲学家中,只有苏格拉底如此实践哲学。 ----罗伯特·诺齐克《苏格拉底的困惑》
●我们有关「国家」的主要结论是:一种「最小限度的国家」(a minimalstate)——即一种仅限于防止暴力、偷窃、欺骗和强制履行契约等有限功能的国家——是被证明为正当的(justified);而任何功能更多的国家(extensive state)都将因其侵犯到个人权利(不能被强迫去做某些事)而被证明为不正当。由此并可以得到两个值得注意的启示:国家不得使用其具强制力的机构来迫使一些公民帮助另一些公民;亦不得以同样方式禁止人们追求自身的利益或自我保护。(前言) ----罗伯特·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
●我想,哲学家对他们在自己的观点中认知到的弱点保持沉默,并不只是一个哲学上的诚实或正直的问题——虽然在自觉上,它的确是、或至少会变成这种问题。这种缄默跟哲学家形成其观点的目的有关。为什么他们力图把一切事物都纳入一个固定的范畴呢?为什么不用另一个范畴,或更基本地说,让那些事实保持其本来面目呢?把一切事物都纳入一个范畴对我们有什么帮助?我们为何会想这样做?(我们要用它保护什么?)我希望自己在将来的著作中,仍然对这些深刻(和令人震撼)的问题保持关注。 ----罗伯特·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
●约翰?杜威说过,真理的探索因困惑而生。相信自己的大多数看法是真理的人不大可能投入对这些问题的探索 ----罗伯特·诺齐克《苏格拉底的困惑》
●知识分子期望整个社会就始终像学校一样,期望着在这个环境中他们照样最出色,也照样得到赏识。学校里的奖赏标准与社会上的标准如此不同,则从学校出来的拔尖者未来进入社会后通常都要经历一种心理挫折感。那些在校园等级制度中处于顶端的学生,会觉得他们不仅在校园这样的小社会中,也在更大范围社会中有资格也处于顶端,然而进入了社会,他们如果得不到如他们所期待的地位,他们就心生怨恨。因此,是学校教育制度在知识分子中间制造出了反资本主义的情绪,当然更多的是在人文知识分子中间制造出了反资本主义情绪。为什么从事跟数码打交道的知识分子没有产生同样的情绪呢?我推想是这样的:这些在数字方面有天赋的的孩子,虽也能在他感兴趣的科目中考得高分,也能得到老师的赏识,但与在人文学科方面 ----罗伯特·诺齐克《知识分子为何拒斥资本主义?》
●那些亲聆苏格拉底说他自己不知道答案的人认为他的意思是他不知道“真理”,而欧文与伏拉斯托斯将苏格拉底的话理解为他不“知道”真理。 ----罗伯特·诺齐克《苏格拉底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