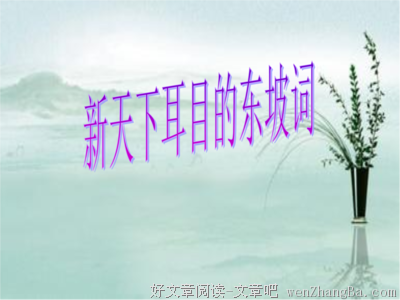●唐以前的几千年,北方一直是中国的文化中心,是主流文化的基地。五代时期,南北文化分向发展,然后文化中心转移到南方。五代之前,中国的人才多出自北方;五代之后,中国的人才多出自南方。唐代的文学家基本上都是北方人,如王勃、卢照邻、骆宾王、孟浩然、王维、岑参、王昌龄、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刘禹锡、李商隐、杜牧等,都是北方人。五代之后到了宋代,诗文的名人又几乎都是南方人了,如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王安石、曾孔、苏洵、苏轼、苏辙、陈师道、秦观、范仲淹,刘永等。唐代和宋代之间隔了一个五代,变化就如此之大。最明显的例子,“唐宋八大家”,唐二家全是北方人,宋六家全是南方人。 ----陈传席《西山论道集》
●晚辈高声朗读经典,老辈倚床而听,抑扬顿挫清脆悦耳的声音,老辈认为是人生的一大乐事。这样,父亲可以校正儿子读音的错误,因初学者读经典,自然有好多困难。就好像欧阳修和后来苏东坡都那样倚床听儿子读书,现在苏洵也同样倚床听他两个儿子的悦耳读书声,他的两眼注视着天花板,其心情大概正如一个猎人射了最后一箭而未能将鹿射中,仿佛搭上新箭,令儿子再射一样。孩子的目光和朗朗之声使父亲相信他们猎取功名必然成功,父亲因而恢复了希望。 ----林语堂《苏东坡传》
●明于大而暗于小。 ----苏洵《高祖》
●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行于左;而目不瞬。 ----苏洵《心术》
●教化之本,出于学校 ----苏洵
●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 ----苏洵《六国论》
●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 ----苏洵《心术》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 ----苏洵《心术》
●嘉佑三年北宋帝国文人眼中的王安石,调侃归调侃,后面更多的是几分神秘和敬慕,像三苏中的老苏洵那样在仁宗时期就给王介甫打上奸逆标签的,恐少之又少,他们更愿意把他看成是自己队伍中的一员,虽然有些独行特例和神秘感,但他们把他归类于有魏晋遗风很不愿的在为五斗米而折腰的的文学愤青一类。
他们没有想到十年后,不拘小节的文艺青年摇身一变成为了大无畏的革命者,站到了大部分北宋精英文人们的对立面。进行着这个帝国最后的救赎和折腾。
嘉佑三年后的第六十九年,北宋帝国在金人的铁骑袭击下轰然崩塌,南渡的文人们痛定思痛眼光朝北,突然想起了王安石在嘉佑三年的进京和他的《言事书》。 ----夜狼啸西风《一个帝国的生与死》
●事必有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 ----苏洵
●内外同心,家宝以宁 ----苏洵
●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至于颠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此言得之。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
悲夫!有如此之势,而为秦人积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趋于亡。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
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 ----苏洵《六国论》
●洎牧以谗诛,邯郸为郡。 ----苏洵《六国论》
●一忍可以制百勇,一静可以制百动。 ----苏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