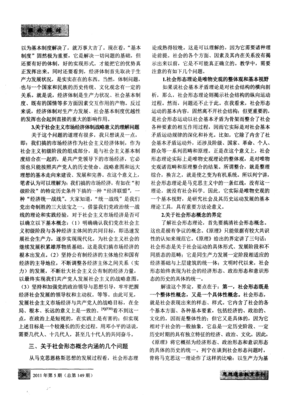
●“加入我们发现,在我们的历史观中,总是能够聪明地发现别人的种种恶行,同时又总是对应出自己的种种光荣事迹,而很少能在历史的镜子里,看到自己曾经和别人一样有过的那张清晰而丑陋的猿脸,甚至那条猿尾巴的时候,我们大概就可以怀疑自己的聪明是否过了头了。在这样的历史观下,很难有什么本质的进步,因为一切可能取得的历史教训都被我们排斥了。”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正是歌德和他这一代人环视四周的外国民族情况的一个重大发现。而德国人对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在心理与情感上的亲切感又反过来促成了世界文学的概念的形成。人们终于明白,人类在根本的人性上是相通的,文学从根底上是人类的,由此而酝酿着一种考察文学的新的眼光与方法:“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心理上探索更深刻的文学运动,并指出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流动的质料怎样凝聚起来,结晶成一种或另一种明晰易解的典型。” ----钱理群《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
●接到梵澄先生复信,其中言道:
我是唯物史观的,也略略探究印度之所谓“精神道”,勘以印度社会情况,觉得寒心,几乎纯粹是其“精神道”所害的,那将来的展望,科学地说,是灭亡。
来信说《五十奥义书》中有不解处,我相信其文字是明白的。这不是一览无余的书,遇不解处,毋妨存疑,待自己的心思更虚更静,知觉性潜滋暗长(脑中灰色质上增多了施纹或生长了新细胞),理解力增强了,再看,又恍然明白,没有什么疑难了。古人说“静则生明”——“明”是生长着的。及至没有什么疑难之后,便可离弃这书,处在高境而下看这些道理,那时提起放下,皆无不可。这于《奥义书》如此,于《人生论》亦然。 ----扬之水《读书十年》
●这事真正荒唐!是史观察不是,虽未可知,然创此议之人,却也不是坏心,並无一毫为己私见在内;只因但会读书,不谙事故,举手投足便错。孟子所以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岂但河工为然,天下大事,坏于奸臣十之三四。坏于不通事故之君子者,倒有十之六七也。 ----刘鹗《老残游记》
●民族史观容易将世界的交流局限于自己所在的出身与立场。 ----杨奎松
●在当前世界性事件的影响下,历史学家所要达到的理想是建立一种新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认为,世界上每个地区的每个民族和各个文明都处在平等的地位上,都有权利要求对自己进行同等的思考和考察,不允许将任何民族和文明的经历只当做边缘的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排斥。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
●写文章的史观,各自不同,有人似不需要什么史观,文字后面自有心灵境界,这如掘井或修花园,又似现代的储蓄,天性有些基础,自年轻起读书、观察、对人生持肯定态度,自然有话可说。 ----陈丹青《我们这个时代的怕和爱》
●眼中印象的我任你怎么说,恨者可以恨,惑者继续惑,这一切不就正是历史吗?(反问句)
人们总说要辩证多方位衡观纵观看历史,看不懂的人可以抨击继续对我困惑抱怨。而小心一步步走路的我对未来没有平反昭雪那么憧憬的希望。但我相信,如果你学历史观察历史的水平足够牛逼,那么!不管怎样看待都不会对我产生困惑。
●古印度与希腊、罗马、中国不同,它没有历史观念。时间是梵天的一场大梦。那是mayas,一种幻象。因此印度的社会制度起源与模式,不似希腊或中国般在于古代。种姓制度不是由一个像皇帝那般的神话英雄,或像莱克加斯般的传奇性立法者所创立的。它是自行孕生的,虽然是经由神、宇宙的旨意,出自于社会的土壤与底土,有如植物。种姓是jati,而jati是物种。种姓就某方面而言,是自然的产物。它的模型就是孕育天地万物的自然秩序。 ----奥克塔维奥·帕斯《印度札记》
●我曾经冥思:我曾经来到一个我可以看到我前世的点,而那就足够证明了。这是我的知晓、我的经验;它和印度的传统、信仰或任何事情无关。我是以我自己的权威来说的。我是以一个智性的人开始----不只是在这一世而是在很多世。在许多世我的整个工作都是关注于聪明才智----提炼聪明才智、磨利聪明才智。
【自说自话,自证自明,自圆其说,除了自己、上帝或全知者,无人可以验证,不论是证实还是证伪。但这是从人本和科学的角度而论的。若是从神话史观来看,既然你原本就是神灵的化身,那么不论你怎样想象、先验、创作或虚构,其实都是无限、永恒、整体或神话的体现或组成部分,因为本来是无所不有,无所不无的,而神灵是无限自由,无所不能的。......】 ----奥修《奥修传》
●“一个民族的自大和自卑都源于对于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无知,只有了解自己的过去,才能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产生深层的民族自尊” ----梁思成
●这种历史观为孔子当时的核心问题提供了舞台:贤良者如何在乱世生活得更好些?因为如果普遍存在的天地和谐关系缺失,正如明摆着的事实,那么一个智者该如何办呢? ----威廉·麦克尼尔《世界史》
●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这个世界的历史观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
●生产力。这个概念在《费尔巴哈》章中没有解释,但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作者当时对这一概念主要是从物质生产力即广义生产工具或生产资料的含义去理解,并相应地把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主要理解为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例如手稿第Ⅳ部分在结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讲唯物史观时,一上来就是讲“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指耕地、河流等)和“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指人工制造的工具)。作者正是通过比较这两种“生产工具”在生产发展中的作用,来揭示地产和资本的对立以及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区别。 ----李零《何枝可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