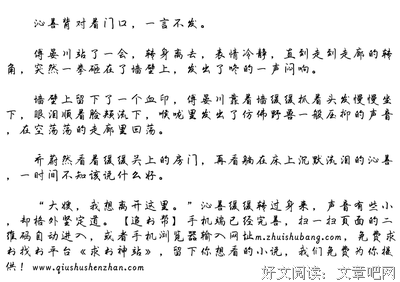一。
这两天有两篇文章不断以各种姿态出现在我的朋友圈里,分别是:《通勤,正在“杀死”1000万北京青年》和已被删除的《未来一年,请做好失业的准备》。
前者说的是:“数据显示,北京是全国最先醒来的城市。清晨五点,人们已经在为通勤奔波。”
后者的开头则是:“最近发生了两件事,很多人都没怎么注意,但这两件事导致的结果,很可能会影响我们未来几年甚至十几年的人生。”
然后围绕着之前出台的一个税收政策讨论,为什么这一代年轻人将会面对一波失业潮。
这两篇文章之间看似没什么关系,但两位作者,都不约而同地拿了同一个城市的就业者作为观察的标本:
“北京青年。”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北京青年”意味着“全国各行各业最顶尖的年轻人”。
而且上知乎一搜,发现坐拥全国最好资源的“北京青年”的回复都含有一种“不是我针对谁,只是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的表情包既视感。
但我知道他们当然不是故意的,人家只是有一说一,有“才”说“才”而已。
只是看回我朋友圈里的那些“北京青年”们,他们从来不炫耀机会跟饭局,反而上镜率最高的,是那些深不见底的北京黑夜。
但无论是哪一种“黑夜照”,配出来的文字都渗出了一种藏不住的疲惫感。
所以当我看完开头提到的那篇《通勤,正在“杀死”1000万北京青年》时,我一度以为他们的疲惫来自于“平均单程需要56分钟的通勤”。
直到我问起一位在综艺节目制作团队工作的朋友,她告诉我:“其实北京的上班时间都比较晚的,没有文章里那么夸张。”
我才意识,真正让他们成为“最疲惫的年轻人”的,并不是通勤和熬夜,
而是选择了“北京”这个副本的他们身上流传着的焦虑的血液和不认命的骨头。
二。
在刚刚过去的八月份,如果没有滴滴跟“反杀龙哥”的事件的话,“北京房租疯长”一定会成为最多人讨论的话题。
然后这个帖子就像一个闷弹被抛到了湖里一样,它爆的时候没有太大声响,但泛起的涟漪波及到了湖里的每个人。
我那些北京朋友,开始相继在社交平台里发一些房东涨房租的聊天记录。
有的房东直接粗暴;
有的房东会说“你再想想”;
也有的房东也不忍心,但还是说出了那句“我也没办法”。
反正无论如何, 北京的房租是一定要涨的,只是“今天涨还是明天再涨”的问题而已。
忘了在哪里看到一个聊天记录,房东对租客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也知道最近的北京租金...”。
然后没等租客回复,房东就又补了一句:“我就不涨你房租了,但从现在起,你按季度交房租吧。”
面对这个“一点都不无理”的要求,这位租客连忙把原本打好的祈求话语都删掉,然后马上回复“好的好的”,生怕房东将消息撤回。
不知道这个八月份过去之后,多少个“北京青年”的记账本上的存款又要被全部划掉。
然后又有多少人,因为迫于无奈,只好再次问家里伸手要钱。
当然,有的“青年”自尊心较强,同时他们对自己的职业生涯还存有一丝自信,所以他们的策略是:“宁愿问软件借,也不要问家里拿。”
但在交完房租后的某个深夜,当他们想起前不久那个下定决心前往北京的夜晚时,他们会不会记起来,
自己来北京的目的不是为了挣一份只安身不立命的房租。
三。
他告诉我:“我也不想承认,但‘厉害’的概率的确比我们这边高一些。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北京的作者会更加‘专业’,不用教,他们都知道情绪是用来写作的,而不是用来工作的。”
他笑了起来,说:“但是那边的工资和租金都很贵啊。”
我问他贵多少。
他看了一眼左上方,然后告诉我:“单说租金吧,同样的地理位置和条件,北京至少翻个两倍吧。”
听完后我拿起水杯灌了自己一口,然后就转到其他话题上了。
不过机缘巧合之下,杂乱也招了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北京作者,陆亦非。
因为亦非是个很神奇的人,平时写稿从来都不问稿费,甚至有时候,她会给远在广州上班的我们点寿司外卖。
问她为什么,她只会告诉我们:“因为我当你们是朋友,所以你们开心就好。”
同事在群里骂我,说我作为老板都不会主动请吃饭,还要人家一个大学生来给我们点外卖。
亦非出来帮我解围,说:“其实是因为,在北京,多这两百块也没什么用啦。”
我问亦非“是真的吗”。
她告诉我,我现在的学校在三环边上,如果要真要租,没有一个应届生受得了。
我想了好多勉励她的话,但打出来,就只剩三个字:“辛苦了。”
她说:“这很讽刺,因为只有像我这种‘暂时路过’的学生,才有资格在北京三环边上安然入睡。”
“那你之后打算去哪发展?”我问。
“要么上海,要么广州。我家在上海,所以难度会降低很多,广州也不错,因为那边生活成本低很多。”
四。
从一年前的那篇《两千万人在北京假装生活》,到如今被推上风口浪尖的北京青年,我不经开始思考一个问题。
为什么当人们提到就业,提起通勤,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北京青年”们?
是因为北京是我们的中心吗,还是因为北京既能提供创造奇迹的机会,也能保证最大程度的公平?
所以一旦连北京的青年们都“沦陷”了的话,意味着其他城市的青年们也会跟着“沦陷”。
就拿杂乱来说,我们公司之前开在东莞,今年年初才搬来的广州。
没错,租金是比起之前要贵上一倍,但说实话,也没有“北上深”一半那么夸张。
我住在离CBD只要十五分钟车程的地方,但跟几位伙伴摊下来,也就是三千块出头,楼下还有游泳池。
所以每次当我看到那些被冠上“北京青年”的朋友们诉苦时,我都想跟他们说:“不如回广州吧,条件差不多,但不至于被压力压垮。”
只是话到嘴边,又一次次被我吞了回去,因为我不敢亵渎他们的决心和努力,我隐隐觉得,这群连“清晨五点的通勤”,“按季度交的房租”,以及“习以为常的加班文化”都熬过去了的北京青年。
他们之所以选择北京,就是冲着那一句“不是我针对谁,只是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去的。
五。
但是就在前几天,我那位当初一心要扎根北京的大学舍友在微信群上说,他准备离开北京,回南方的家里找工作了。
理由是:“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自己先放弃,也许这样还能体面地说句再见。”
回家前,他拖着行李来广州找我吃了顿饭,他眼里没有那股“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的狠劲,大概是没能修成正果的缘故,反倒是看到我后,他有些羡慕。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羡慕你从一开始就没动过去北京的念头。因为一旦动了,不管在哪,北京都会永远在你心里扎下根。而你抓不住北京,北京却早已牢牢地抓住了你。”
只是留恋又如何呢,他能做的,
也只有在逃离的时候选择火车这个交通工具,让自己离开北京的速度慢一点,再慢一点而已。
音乐 | A portrait - Spangle call Lillli line
作 者 介 绍
张荆棘
“嘿,长按*,跟我们一起有趣”
我们想给你一个理由 继续面对这烂生活
信箱:
这里收集了很多不愿意迎合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