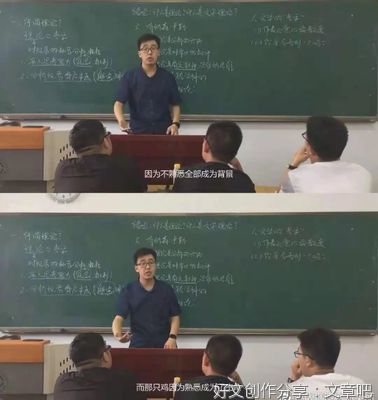
《十三邀 番外篇:许知远对话刘擎》是一部由朱凌卿执导,刘擎 / 许知远主演的一部脱口秀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影评,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十三邀 番外篇:许知远对话刘擎》影评(一):刘擎语录 多看多思考,冷静看世事
孤单逼迫你适应安静,长时间的安静,独自的劳作和思考。然后迫使你爱上这种状态。因为它还是有对你的奖赏——智性上的发展,新的洞见。这是一个塑造。年轻的时候太容易浅尝辄止,不喜欢就退回来了;但有些事情要经过挺长时间才能尝试出自己喜不喜欢。有时候要经历不是那么自愿的阶段。
我觉得年轻的激情有的时候是特别浪费的,没有目的的燃烧。成年需要阅历,早慧代替不了阅历。
我爱人是一个对秩序有洁癖的人,要不然会很不安。但这样的生活方式容错率太低了,最后会很焦虑。如果把这作为一个非常强烈的要求期待和标准的话,你会永远惶恐不安。你要承认人的无知,和理性的局限性,要对世界有一个容错的能力。
现在,在任何意义上,在所规范,所命名,所区分的那个世界完全消失了。现在对任何物品、感受都有了过于详尽的打分评级,即便最私密的领域也无处可逃,它是全面的社会规约和机制的绑定。正如双城记所说,这是一个特别自由的时代,又是一个特别被禁锢的时代。惊讶、惊喜、从试错、从偶然的事物中诞生新可能性的窗口都被一个个封死、关闭了。
把自己和一个更大的背景,甚至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并没有特别明显的直接的作用。但自己作为一个更充分意义上的人在生活。
——刘擎
《十三邀 番外篇:许知远对话刘擎》影评(二):“美美与共”“各美其美” 斗则两伤 合则两利
1. 新世界主义是如何出现的?
刘教授:只有生物的基因,是可以无条件地传承下来,在文化上是没有基因的,任何文化的基因,需要经过制度实践,它不能自然的遗传下来,要becoming。其实建构是在关心当中的,只有我们发现彼此,我们彼此碰撞,你才能够建构,它需要克服的,就是本文明中心主义。
2. 如何看待过去十多年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愈演愈烈?
不是说fan中国,但它是背离中国一个文明传统的,“美美与共”、“各美其美”...相信社会达尔文主义,相信弱肉强食,这个想法是非常西方的,是已经过时了的西方,西方当然现在还会有,这样一个东西,至少在学界、文化界,这个东西是被非常鄙夷、批判的东西。因为这是对达尔文的一个误解,达尔文是说,有一个适应性,是适者生存,不是强者生存。不是那个power/strength,如果你是中国人,那中国文明当中最理想、最高的那个美好的东西,你就放弃了。你最后赢,你可能变成了一个反而是西方十九世纪野蛮的一种文明的再登场,这是中华民族的复兴吗?我不认为是如此。就完全那种残酷竞争的逻辑,它可能在一段时间是特别管用的,在现在不起作用了,在现在这个时代至少局部的不起作用了。
“斗则两伤 合则两利”这个道理,它正在成为世界的现实,它越来越成为一个现实的规范逻辑,而不是空中楼阁。用罗尔斯的话说,我们提的这个想象,叫现实主义的乌托邦,它是有实践可行性的,要不然我们在做梦吗?虽然“悲观的人(显得)比较深刻”(--福山),悲观的那个证据很多,小证据很多。但我不知道,这里面知识和信念的因素都有,我们确实不能从过去推断未来,但是你从未来猜测未来,你是更不可靠的,所以现在我们就处在这个时代。
施密特(相信那个冲撞存在于敌我之间)当然深刻,但是有时候我会说,我们明明知道人性有这么复杂,特别有这么多阴暗面,尽管如此,你相信人类会斗争会厮杀,难道比相信人类可以共存,和平相处,更深刻吗?
《十三邀 番外篇:许知远对话刘擎》影评(三):价值根基/现代性/艺术和理性
本文虽然是一篇观后感,但我以节目为引子,尝试探讨一些比较深层次的问题。本文并不像哲学文章般严谨,只是一篇随笔。
时光飞逝,我从法教义学逃离到政治哲学领域已经有大半年。(由于我觉得政治哲学和法哲学、道德哲学、实践哲学存在一种非常暧昧且难以区分的关系,所以本文使用的“政治哲学”一词粗略地指称上述哲学的共同部分。关于这几类哲学的关系可以参阅Finnis的论文。)经过大半年,虽然可能我还没摸到哲学之门,但这段时光好像是我真正在上大学的时光,在做一些自己真正相信的、走近生命的学问。《十三邀》番外篇的嘉宾是一位在公共领域中活跃的政治哲学家——刘擎老师,我感觉刘擎老师和我接触或了解的其他政治哲学学者都有一种相似的气质,这种气质让我共鸣,因此我想写一篇观后感,并夹杂抒发自己的理解。
我将重构本期节目的内容并加上自己的理解,本文分成三个部分。
1. 价值根基
在我学习哲学的过程中,我深刻感受到,对于道德和价值的根本看法是整套政治哲学的根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自认为是“理想主义者”,但这种自诩是在对其对立概念“现实主义者”的叛离中产生的。我会把自己的非理性情感认为是“理想主义”的,而当我进行理性分析时,我便仍会持一种“现实主义”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用哲学术语表达即“虚无主义”,即认为并不存在客观的道德上的真和善,不存在适用于每个人的道德准则。例如,我之前会认为法律以及价值领域是“统治阶级的强权体现”,认为并不存在可以仅靠理性辩护的规范性(或者说,义务)。
然而,经过哲学反思后,我的想法改变了。以下我将对虚无主义进行一个并不强势的最低限度的反驳。我发现,至少,如果认为哲学反思是为了让我过得更好,政治哲学是为了让我们作为共同体在一起过得更好,虚无主义就是错的,因为虚无主义并不符合我对好的生活的理解。其实,虽然我看过很多对虚无主义的强势攻击,对道德客观主义(虚无主义的对立观点)的辩护,但我认为是否认同虚无主义可能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而非必然的要求。面临这个选择,不妨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究竟相信什么?”例如,我愿意相信法律是强权和统治者意志的控制,还是愿意相信法律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正义的体现,这是一个人对内在世界塑造的选择。(联想到了Ruth Chang的关于on a par情境的理论,虽然可能并不恰当,但我想类比虚无主义和道德客观主义是一种on a par的关系,对于一边的选择会塑造我这个人)
我认为这是一个诉诸内心直觉的判断。我选择相信道德客观主义,因为我相信平等、自由、尊重等美好的价值,一个公正而美好的世界是可被追求的。这些美好价值的内部可能会起冲突,比如说自由可能会被秩序所限制,正义可能会压制秩序。但至少,我相信美好价值和“好的生活”的存在。
我的这种对美好价值的相信是不是又是一种用来聊以自慰的“理想主义”的一厢情愿?我是不是仅仅是试图让自己更加心安理得,而把自己装进幻想的箱子里?《理想国》中,色叙拉马霍斯就这样质疑,他认为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理性论辩在拳头前并没有用。我要承认,这个反驳非常有利。刘擎老师在本期最后的彩蛋中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他父亲小时候经常打他,打完之后还要问他:“你知道你错在哪里没?”。但是有一次他对父亲说:“你打我就是心情不好,我昨天犯了一个比今天还大的错误,你兴高采烈地回来就没打我,今天你不开心就打我。”于是,他父亲再也没打他。刘擎老师说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话语的力量。
正如同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所说,讲道理是重要的,打只是讲道理的手段。理性虽然是有局限的,但是理性是可以被相信的。的确,这个世界上不讲道理的情况很多,但是每当这个时候我会问自己经典一问:“从来如此,便对吗?”事实是如何和我应当是如何是两个问题,这类休谟原则已经成为了共识。或许论证到这里,我可能陷入了循环论证,但是我会用我之前提到的直觉判断来结束我的论证,“你究竟相信什么?”
除了虚无主义,对道德客观主义还存在一种相对主义的反驳。相对主义者认为只有自己相信的道德准则才是真的,这些准则只能适用于自身,无法用来要求他人。这种相对主义也可以推广到不同国家或社会的道德准则是相对的,不存在能够达成一致的标准。
相对主义是可能的。比如在元宇宙中,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独立且互不干扰地生活。或者如同谭嗣同曾经的想象,如果我们每个人单独占据一个天上的星星,我们的价值冲突就不会存在了。又或者如同有人提出的对美国社会撕裂的解决方案,将美国分裂成两个国家,两党人分别生活,井水不犯河水。
但是,我真的可以当一座孤岛吗?我认为很难。我们总是要在一起生活的,我们不仅要和意见相同的人生活在一起,也要和意见相左的人一起生活。况且即使是再相似的人也总会有意见不一致。更进一步,要和他人一起生活也并非无奈的现状,而是个人的需要。至少从我的经验来看,固然独处可以让我获得智性的提升,但是和他人在一起会带给我慰藉和快乐,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固然需要距离,但却是分不开的。我们可能会在公共生活中不理性,比如爱国主义就是一种包含偏爱的不理性的情感。这种情况下的理性就体现在,承认对自己也会对某些事情存在偏爱,并且理解对方不理性的偏爱。
如果我们可以承认有共同价值的存在,那么我们如何获取或认知这种共同价值呢?或许我们可以观察我们的信念共同的部分,这些共同的信念组成了我们的重叠共识(罗尔斯语: Overlapping Consensus)。但这还不够,从外部观察公共生活是不够的,我们要深入到公共生活去,从实践的具体角色出发。以法律举例,我们不能只停留在从外部观察原告的诉请可能满足几项要件,而要站在原告的立场上体会此时自己的内心会认为什么规则、原则或道德信念会支持自己的诉请。从外部观察社会的共同价值可能是从来不可行的,我们最终都要回到自己对于某种道德信念的确信上来。
(由于我并不十分了解罗尔斯,上一段对于罗尔斯观点的介绍可能有误。我仅仅是在这里借用刘擎老师的叙述。)
对于美好价值的相信也可以用来应对当今的意义匮乏。至少美好的价值就是一种看起来可以相信的意义。
2. 现代性
我觉得对于社会现象的反思离不开一个对于价值的根本看法。承继上文,如果我们基于道德客观主义反思现代性我们会得到什么?
刘擎老师提出的新世界主义主张世界的各个文化共同生存,美美与共。这种“和谐社会”可能看起来并没有对世界进行悲观理解那样深刻。但,真的相信施密特那种人类之间的厮杀会比相信人类和平共处更深刻吗?我认为这一问根植于我上面的那一问:“你究竟相信什么?强权还是正义?”
对于美好价值的信念是内在反思的,并非外在定义的,这在现代尤其重要。刘擎老师认为我们的时代是自由和禁锢并存的。这体现在,我们有很多想象力和技术突破,但同时又特别单向化,我们会把任何事情都类型化并且用一套标准进行打分评级。我们被技术规训到了极致,这套系统外的自由野蛮生长的空间在变少。
追求一种内在反思而生的价值,而非外在给定的标准,可能是跳出这套系统的一种方法。但我承认这是有局限性的,这样的做法可能只会获得一种通过将这套系统强行客体化而获得的虚假的主体性感觉,而并非获得一套解决方案。
该怎么办?我不知道。或许理性是有局限的吧。但是我现在至少相信这种虚假的主体性感觉会让我获得一种内心的安宁。本集中,刘擎老师说:“未经反省的人生不值得过,过度反省的人生过不下去。”这后半句话我不想承认,但越来越感觉不得不承认。
3. 艺术和理性
在许知远和刘擎交谈的酒吧,吧台的对面挂着一整墙的哲学家肖像。调酒师说的一句话特别好:“哲学解决不了的,让酒解决;酒解决不了的,让哲学解决。”
哲学教给我理性探究,如何用概念和逻辑探求真理。刚学哲学的时候我有一种自大,会认为这个世界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用哲学解决,只有理性才是唯一值得追求的。但我们真的是时刻理性的动物吗?概念固然可以包含洞见,但真的是足够精确而非是用来终结讨论的吗?
当我沉醉在戏剧、音乐、画和文学的世界里时,我觉得哲学并不重要。我能感受到艺术实实在在地洗涤我的生命。和刘擎老师一样,我也在艺术和学术间彷徨、徘徊、激动、焦虑、迷茫。
对于在艺术面前的那种心灵触动,再多的文字描述可能都是多余的。写到这里,或许我该结束了。我只想请求各位读者,当你对理性十分确信的时候,不妨感受一下艺术,内心的感觉会给你最直接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