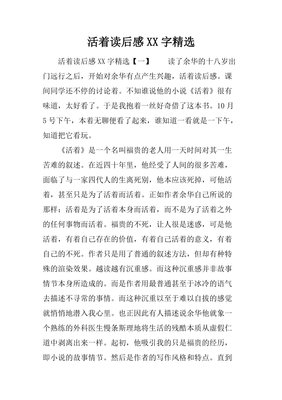
《是与时》是一本由[德]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著作,http://vdisk.weibo.com/s/zmD2mvoTNzspt(PDF版)出版的图书,本书定价:413,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是与时》精选点评:
●我反而觉得把“存在”翻译成“是”更好理解了。。。
●熊林老师!
●开篇生起而结尾仍显现为未被充分地提出的,乃是是之意义问题,它发自我们向来活动于其中的是之理解,故对问题的拟定先要求澄清追问者在是态学上的情状;"意义"犹言目的,是一物可被理解或筹划的条件或根据,故探索之法必须是实际性的解释学.经由清理此是在现象上的结构,得出蕴含于操心中的生存论规定;操心的三重结构之整体性奠基于时间性,确切地说,它们以后者绽出为三维的统一性为前提,故时间性显露为此是之是的意义与是之理解的视域;此结论是通过界定此是本真的能整体是(先行着的决心)――以获取其完整的是之规定――而得到的.生存本质上是将来的,故只有在决心中面对源自将来的曾是,才能"瞬间地"是;本真的历史性奠基于其上.最后未回答的是:总在我"之外"的世界之内的是者之超越性以及我与它们的照面究竟是如何可能的?
●终于读完了,诗有诗眼,书亦当如是吧。不管是未读《存在与时间》,还是已读《存在与时间》都希望牢牢记住下面这一段话,“只有下面这种是者才能在把继承下来的可能性承传给它自己本身之际接纳本己的被抛性,并面对“其时间”而瞬间地是:它本质上就其是而言就是将来的,以至于它因自由地面对它自己的死亡而撞碎在它那儿之际,让它自己被反抛到它那实际的在此之上,也就是说,它作为将来的是者同等源始地就是曾是的。只有本真的时间性——它同时又是有终结的,才使得命运这样的东西成为可能,即使得本真的历史性成为可能。”等到你可以清晰明了地用自己的话论证,阐释这段话时,大致就可以跟别人说,“我读过了一遍《存在与时间》”。
●之前读熊林译的布伦塔诺时就已经感受到这种别扭了,sein还是译成“存在”吧,译成“是”,真的没法在汉语阅读中流通,而且那种“存在的阴影感”好像被“是”的光照意味覆盖掉了。另外,Dasein译成“此在”已经十分费解了,译成“此是”,更加不知所云了。
●woc!太棒! 这个版本不为众人所知,自然是所谓“版权”问题背后的话语权问题。略 虽然存在的译法流行很久,已经成为了国人哲学思维方式的重要建构元素,但在阅读导论时,明显感觉“存在”一词对理解提问方式本身有限制,这种限制甚至感觉就是一个语法问题。而改为是之后,可以深入语境中。这确实不符合汉语习惯,但这种异质化的翻译方式不正适于理解思维之思维的架构吗?而且“是”更加源始性的纯粹,对于思维来说的纯粹。 相较于“是”,存在一词更偏向于人类学向度,所以在阅读第一编“在世之中”与“在之中”时,存在的译法对于理解这本就很人本主义的诠释很有帮助,但这确实使我们沉浸在【人】的在中,无法进一步深入到那贴近语法(不是逻辑)的希腊智者的提问中。
●这个版本确实好读多了,但多少有些矫枉过正了
●Sein und Zeit 的这一份译稿像个幽灵。学界有它的传说,它却没有公开出现过。但见过它的人,特指认真阅读过的人,想必会认真告诉另外的人:这才是Sein und Zeit 的真身。
●重读用了这个版本,没什么好说的,还是滚去学德语吧
《是与时》读后感(一):对sein理解的随笔短记
(接短评)
不得不说,在古典语言及其内在逻辑(这词太差了)、思想翻译成现代语言的过程中,用是这个不合现代汉语语法的词可以揭示出另一部分无法用存在不加解释的理解到位的sein的意思,当然,是也并非是完美的表达,我只是隐隐感觉,是的翻译会是一个不错的补充,对于理解作者的意思或者说现象学本身,有更好的启发作用。
(持续补充)
《是与时》读后感(二):【转】丁耘:是与有——从译名之争看中国思想的哲学化与现代化
【作者简介】丁耘,1969年生,哲学博士,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任《思想史研究》、《思想与社会》、《开放时代》编辑委员。主要研究兴趣为中西思想史、德国哲学、古希腊哲学与中西比较哲学。已出版专著《道体学引论》(2019)、《中道之国》(2015)、《儒家与启蒙》(2011)、《十七世纪形而上学》(合著,2005)等。译有马丁·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2008初版、2018修订版)等。主编《思想史是什么》(2006年)、《五四运动与现代中国》(2009年)等。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20余篇,另有译文多种。
《是与时》读后感(三):转载:熊林教授讲解《是与时》
http://philosophy.whu.edu.cn/info/1037/13074.htm
四川大学熊林教授来我院讲学
点击次数:319更新时间:2020-11-24本网讯(通讯员 汪虹宇)11月21日,四川大学哲学系系主任熊林(浦林)教授做客我院名家讲座第8讲。上午9时30分至11时30分,熊林教授在哲学学院B214做了一场题为“对自由之形而上学的一种奠基——海德格尔Sein und Zeit的核心问题及方法”的精彩讲座。此次讲座是哲学学院名家讲座第8讲,同时也是外国哲学学科“经典与问题——诠释与方法的变奏系列讲座”第2讲和“珞珈德国哲学讲坛”第9讲。讲座由外国哲学教研室杨云飞副教授主持。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外国哲学教研室苏德超教授、王咏诗副研究员及院内硕博研究生30余人参加了此次讲座。
杨云飞副教授代表哲学学院对熊林教授的到来表示欢迎。熊林教授对海德格尔哲学、中世纪哲学与古希腊哲学都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目前正在从事希腊文-汉语对照版的柏拉图全集翻译工作,近期将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
讲座伊始,熊林教授指出正是《是与时》(《存在与时间》)奠定了海德格尔在哲学史上的伟大哲学家地位。《是与时》不是通常所认为的人生哲学、哲学心理学、哲学社会学或哲学人类学作品;其核心内容实际上延续了德国哲学尤其是康德哲学传统,是“对自由之形而上学的一种奠基”。
熊林教授从海德格尔《是与时》的核心问题与方法两个方面展开自己的阐释,重点聚焦于《是与时》扉页以及第1节、第2节的文本内容。
熊林教授首先回顾了是态学(存在论)问题的提出。前苏格拉底哲学的发问方式是宇宙论的(cosmological),即“世界的本原是什么?”。苏格拉底第一个提出是态学的(ontological)问题,“这是什么?”(What is it ?),这奠定了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基础。这种关于“是者作为是者”的学说,后来在中世纪与近代被系统化为形而上学,分为一般形而上学(是态学、第一哲学)与特殊形而上学(宇宙论、心理学与自然神学)。
在核心问题上,海德格尔《是与时》的开篇点出“诸神与巨人之间关于所是的战争”,显示了其核心问题正是“是之问题”。“所是”即ousia,不是通常所理解的“实体”(substance/Substanz),而是“本质”(essence/Wesen),是对“这是什么?”问题的回答。例如当我们追问人是什么,我们其实是在追问人的本质。
在《是与时》的第1节中,海德格尔批判了有关是之问题的三个教条。
第一,“是”是最普遍的概念。是并不是种属意义上的普遍,而是超越者,是一种“类比的统一”。在亚里士多德的范畴学说中,范畴是我们打量世界的基本发问方式:我们会问“这是什么?”(所是、本是),“是如何?”(质),“是多少?”(量),“是在何时?”(时间),“是在何处?”(地点)等等,一般对象正是在范畴之网中得以对象化。范畴是言说“是”的方式。(1)范畴统摄种的方式是“同名同义”,下位分有上位的名,同时分有上位的logos;(2)是统摄范畴的方式则是“同名异义”,范畴分有是的名(范畴是“是”之方式),但不分有是的logos,因为每个范畴有其不可还原、不可通约的意义。因此,“是”是一种超越者,是类比的统一。
第二,“是”是不可定义的概念。这一点同样不能通过范畴、种属的概念性来理解。是之不可定义性,在于所有的定义都已经预设了对是的某种先行理解,所有的定义都开始于“这是……”。
第三,“是”是自明的概念。但自明性并没有取消是之问题,因为恰恰是自明的东西才构成哲学家的工作课题。
在方法上,《是与时》的扉页已给出提示,“具体地拟定出‘是’之意义这个问题,乃是下面这部论文的目的。对作为任何一种一般是之理解的可能视域的时间进行阐释是该论文的临时目标。”换言之,正是为了追问是之问题,海德格尔才追问作为是之理解的可能视域的时间;而为了追问时间,海德格尔才追问能崭露时间性视域的是者,即此是。所以海德格尔的方法思路为:
此是→ 时间 → 是
在这里,海德格尔批判了康德“人是什么?”的问题。康德在致司徒林的信中以及《逻辑学讲义》中总结了四个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以及“人是什么?”。海德格尔认为康德的问题并没有深入到人的本质,因为人的本质不是作为“理性的动物”的人,而是此是(Dasein)。海德格尔虽然与康德都赞同“人是自由的”,但并没有止步于追问“人是什么?”,而是更深入地追问——“人是自由的”中的“是”是如何“是起来”的?这就是“此是是什么?”的问题。
此是的“本质”在于生存。此是从来不是一个现成的东西,可以用诸范畴来概念性地规定。人自己是什么以及如何是都是由自己“是出来”的,即所谓“存在先于本质”。此是是一种对是有所领会并且能够追问是的是者。对于人的此是而言,可能性永远高于现实性,人总是一种“尚未”的是者,同时总是可以“本不是那样”。对于此是而言,是什么以及如何是,是一种重担,需要存在的勇气或去是的勇气。
在《是与时》第2节中,海德格尔区分了一般问题的形式结构。任何问题都具有三重结构:被问者,被询问者以及被问得者。熊林教授以问“武汉大学在哪里?”为例,被问者就是武汉大学,被询问者就知道武汉大学在哪里的信息源(武大师生或信息数据),被问得者就是武汉大学的位置。具体到是之问题上:被问者就是“是”,被问得者就是“是之意义”,而被询问者正是“此是”。因为此是是唯一能够领会并追问是的是者。
所以《是与时》中的此是之生存论分析(无论是人们、沉沦、本己、非本己、死亡、良知等“概念”)不是人生哲学,而是为了回答“此是是什么?”的问题,都是此是之是的一般规定。在《是与时》中,海德格尔最终将“此是是什么?”的问题收摄为源始时间性的样式,是此是之生存的曾经、当下与将来。此是的是之规定,被总结为“已经抛入一个世界之中-依寓于世界-而先行于自己向着将来筹划”的绽出时间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的《是与时》是“对自由之形而上学的一种奠基”。
在提问环节,熊林教授与杨云飞副教授、王咏诗副教授以及现场师生就此是在是态学中具有的范本优先性,柏拉图的事物本身(auto)与亚里士多德的诸是(onto)之间的关联,是态学与认识论之间的关系以及意志自由与海德格尔式自由的关系问题展开了进一步的讨论。
最后,杨云飞副教授代表哲学学院师生对熊林教授精彩而深刻的讲座表达了感谢。本次讲座在现场师生们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
(编辑:邓莉萍 审稿:严璨)
《是与时》读后感(四):【转】溥林:否定形而上学,延展形而上学?——对《是与时》核心思想的一种理解
溥林[1](四川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 成都 610064)
摘要:本文认为,形而上学的核心是“是态学”,是态学的核心是范畴理论,而范畴无非就是对“是者”的一般“是之规定”。海德格尔《是与时》一书基于对“此是”的生存论分析所给出的各种“生存论规定”,同适用于非此是式的“是者”的范畴一道都是对“是者”的一般“是之规定”,它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一种延展。
关键词:形而上学,是态学,是之规定,范畴,生存论规定
《是与时》(Sein und Zeit)是可以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以及黑格尔的《逻辑学》相比肩的一部严格意义的哲学著作。只有将之置于西方“形而上学”(Metaphysik)发展史的整个背景中,置于作为对形而上学核心内容的“是态学”(Ontologie)的探索中,该著作方才不至于降格为一部“人生哲学”作品;它所进行的探索,才不至于如作者所担心的那样,成为“哲学人类学”、“哲学心理学”等意义上的探索。本文试图从上面这一角度出发,对《是与时》的基本思路进行一种理解。
(一)
传统形而上学(第一哲学)的核心理论是“是态学”(die Ontologie)。柏拉图说,在人的灵魂中有着哲学的因素。这种哲学的因素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试图用“一”来统摄“多”,即对统一性甚至最高统一性的某种追求。在希腊哲学那儿,它经历了从“宇宙学”(die Kosmologie)到“是态学”(die Ontologie)的转变。前者所思考的,乃是纷纭复杂的现象背后是否有着某种统一的东西,其基本的发问方式可以规定为“它是由什么构成的?”或“它是从哪儿来的?”,它追问万物产生于它又复归于它的某种或某些 “基质”、“本原”或“元素”。而后者打量世界的基本发问方式是“它是什么?”以及与之相关的“它是怎样?”,核心的是追问万物的“所是”或“本质”。后者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即“第一哲学”所要思考的东西。
“它是什么?”(Was ist das?)这一打量世界的基本发问方式不仅催生了逻辑学和科学,更是导致了形而上学的产生。柏拉图的理念论以及亚里士多德的范畴学说,都可以视为对这一问题的某种回应,都是对现象的某种拯救(σῴζειν τὰ φαινόμενα)。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一书中明确将“第一哲学”(ἡ πρώτη φιλοσοφία)[2]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是者作为是者”或“作为是者的是者”(τὸ ὂν ᾗ ὄν),它也是“第一哲学家”(ὁ πρῶτος φιλόσοφος,《论灵魂》403b.16.)所要加以探究的东西。他在该书的第四卷(Γ卷)、第六卷(Ε卷)和第十一卷(Κ卷)中反复指出,第一哲学的对象乃“是者作为是者”(τὸ ὂν ᾗ ὄν,pl. τὰ ὄντα ᾗ ὄντα),它研究“是者作为是者”(περὶ τοῦ ὄντος ᾗ ὂν,pl. περὶ τῶν ὄντων ᾗ ὄντα)。例如:
有一门科学,它研究是者作为是者以及那些就其自身就属于它的东西。它不同于任何的特殊科学,因为其他那些科学中的任何一门都不普遍地思考是者作为是者,而是切取它的某个部分并研究该部分的属性[3]。因此,显然有一门科学研究是者作为是者以及那些位于是者作为是者之中的东西;这同一门科学不仅研究各种所是而且研究那些属于所是的东西,既研究前面所述的那些东西,也研究在先和在后、属和种、整体和部分以及其他类似的东西[4]。
哲学家的科学普遍地的探究是者作为是者,而不是探究它的部分;而“是者”在多重方式上而不是在一重方式上被言说[5]。
这种学说在古代被称为“关于是者的理论”(ἡ περὶτῶν ὄντων θεωρία)[6],研究“是者作为是者”乃是形而上学即第一哲学的任务[7]。对它的理解是把握形而上学和是态学的关键。关于这一点,亚里士多德本人也曾指出: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那总是被追问和总是让人困惑的问题就是:“是者”是什么[8]。基于形而上学打量世界的基本发问方式,凡是可以用“是”(Sein)加以发问和回答的,都是“是者”(dasSeiende)。也正因为如此,亚里士多德才会说,“因此,我们也说不是者是不是者。”(διὸ καὶτὸ μὴ ὂν εἶναι μὴ ὄν φαμεν. 《形而上学》1003b.10.)
我们认为,在传统形而上学中(至少在亚里士多德那儿),并未如海德格尔那样严格区分“是”(das Sein)和“是者”(das Seiende),也即是说,并未将τὸ εἶναι和τὸ ὄν加以严格区分。ὄν是动词εἶναι的现在分词的中性单数,前面加上中性冠词τό,就可以成为一个名词。这一名词既可在动词的意义上进行理解(是、是着),也可以在名词的意义上理解(是着的东西、是者)。亚里士多德本人似乎并未严格区分“是”和“是者”;他在 “是”和“是者”这两个意义上使用这一语词,这既给后世的理解带来极大的麻烦,也为一种新的哲学理解提供了可能[9]。
当τὸ ὄν作物质名词“是者”理解时,有复数形式τὰ ὄντα;当τὸ ὄν作动词“是”或“是着”理解时,亚里士多德有时使用替代表达τὸ εἶναι。τὸ ὄν的否定形式是τὸ μὴ ὄν,它也既可在动词的意义上理解,也可在名词的意义上理解。作动词理解,则有替代形式τὸ μὴ εἶναι(不是,不是着);作物质名词理解,则有复数形式τὰ μὴ ὄντα(不是者,非是者)。我们这儿选取《形而上学》第五卷(Δ卷)第七章中的一段话作为例证:
“是者”(τὸ ὄν),有的被称作根据偶然而来的“是者”,而有的则被称作根据自身而来的“是者”。……根据自身而来的“是”(εἶναι)如范畴表所表示的那么多;能说出多少范畴,“是”(τὸ εἶναι)就有多少意指。在诸谓词中,有的意指“是什么”,有的意指“质”,有的意指“量”,有的意指“相对物”,有的意指“行动”或“遭受”,有的意指“地点”,有的意指“时间”;“是”(τὸ εἶναι)就意指着它们当中的某一个。因为人正在康复和人康复之间并无区别,人正在走或人正在切同人走或人切之间也无区别,就其他的情形而言也同样如此。……此外,“是”(τὸ εἶναι)和“它是”(τὸ ἔστιν)意指着是真的,而“不是”(τὸ μὴ εἶναι)意指着不是真的而是假的,就肯定和否定而言同样如此。……此外,在前述“是”(τὸ εἶναι)和“是者”(τὸ ὄν)中,有的意指潜能上的“是者”,有的意指现实上的“是者”[10]。亚里士多德不止一次用τὸ εἶναι替代τὸ ὄν。例如,亚里士多德经常说“‘是者’被以多重方式加以言说”(τὸ ὂν λέγεται πολλαχῶς),但有时他也会说:
τὸ γὰρ ἓν καὶ τὸ εἶναι ἐπεὶ πλεοναχῶς λέγεται.(“一”和“是”被以多重的方式加以言说。—《论灵魂》,412b.8.)ἀλλ᾽ ἐπεὶ πολλαχῶς τὸ εἶναι.(“是”具有多重含义。—《物理学》,206a.21.)ἔτι τὸ εἶναι πλεοναχῶς λέγεται.(“是”被以多重的方式加以言说。—《物理学》,206a.29.)ἐπεὶ δὲ τὸ εἶναι πολλαχῶς, πρῶτον μὲν τὸ ὑποκείμενον πρότερον, διὸ ἡ οὐσίαπρότερον.(“是”具有多重含义,载体是在先的,故“所是”是在先的。—《形而上学》,1019a.4.)关于这一点,海德格尔在《是与时》[11]的一个边注中也指出,τὸ ὄν在传统形而上学中具有两重含义,一重含义指“是(着)”(dasSeiend),另一重含义指“是者”(das Seiende)。此外,根据海德格尔在《是与时》(德文页3)中所引用的希腊文,也可以看出这一点:»Sein« umgrenzt nicht die oberste Region des Seienden,sofern dieses nach Gattung und Art begrifflich artikuliert ist: οὔτε τὸ ὄν γένος. (如果“是者”乃根据属和种被概念性地表达,那么,“是”并非限定着是者之最高领域:οὔτε τὸ ὂν γένος. [是不是一种属]。)根据他对das Sein和das Seiende的区分,这里他显然是用das Sein而不是用das Seiende来理解τὸ ὄν。
在亚里士多德那儿,“是者”的种类是由“是”的样式或样态(modus)决定的。我们后面会看见,亚里士多德之所以提出“是者作为是者”(τὸ ὂν ᾗὄν)这一表达,那就是因为“是(者)”(τὸ ὂν)不是比诸范畴(每一范畴都是最高、最普遍的“是者”)更高的、统摄它们的属。这也是我们主张将Ontologie翻译为“是态学”的一种理由。
(二)
是态学(die Ontologie)的核心内容是“范畴论”(die Kategorienlehre)。海德格尔在《是与时》第1节“明确地重提‘是之问题’(die Frage nach dem Sein)的必要性”时,列举了传统形而上学关于“是”(das Sein)的三个偏见。其中,对后两个偏见的理解都较为容易:
偏见2:“是(das Sein)这个概念是不可定义的。”关于这一偏见,除了海德格尔所指出的那些理由外,最直接的就是他在脚注中所引的帕斯卡的那段话:“一个人无法在试图定义是时而不陷入这样一种荒谬之中:无论通过直接的解释还是暗示,人们要定义一个词都必须以‘这是……’来开始。因此,要定义‘是’,就必须说‘它是……’,人们已经使用了这个要在其定义中被定义的词。”(德文页4) 偏见3:“‘是’(das Sein)是自明的概念。在所有的认识活动和陈述中,在对‘是者’(Seiendes)的每一关联中,在所有对—自己—本身的—关联中,都得使用‘是’(Sein);并且这种表达在此是‘轻而易举地’可理解的。每个人都理解‘天是蓝的’,‘我是快乐的’,等等。”(德文页4)关键是对偏见1的理解(甚至第二个偏见在某种意义上直接就来自第一个偏见),这也是海德格尔论述最多的一个偏见:“‘是’(das Sein)是‘最普遍’的概念。……‘是’(Sein)的‘普遍性’不是属的普遍性。如果‘是者’(das Seiende)乃根据属和种被概念性地表达,那么,‘是’(Sein)并非限定着是者(das Seiende)之最高领域:οὔτε τὸ ὂν γένος. [是不是一种属]。是(das Sein)的‘普遍性’‘超乎’一切属上的普遍性。依照中世纪是态学的刻画,‘是’(Sein)是一种‘transcendens [超越者]’。亚里士多德已经认识到这种超越的‘普遍’之统一性与含有实事的最高属概念的多样性截然不同,他将之称为类比的统一性。”(德文页3)
要能理解海德格尔在这儿所说的,还是只能回到亚里士多德那儿;事实上,海德格尔的许多秘密都在亚里士多德那儿。
亚里士多德在不同的地方反复指出“是者”具有多重含义(τὸ ὂν λέγεται πολλαχῶς)。根据前面所述,总体来说,“是者”(τὸ ὄν)主要地具有四重含义:(1)偶然意义上的是者(是偶然的),(2)在其自身意义上的是者(是在其自身的),(3)真假意义上的是者(是真的或是假的),(4)潜能和现实意义上的是者(是潜能的或是现实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1)和(3)意义上的“是”及“是者”不是第一哲学(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因为我们不会具有关于前者的知识,而后者的处所在判断或命题中,它不能离开人的心灵和理解而独立存在。(2)和(4)意义上的“是”和“是者”乃第一哲学的研究对象,但(4)意义上的“是者”又体现在(2)意义上的“是者”之中;而“在其自身意义上的是者”就是“范畴意义上的是者”,范畴有多少,在其自身是的“是者”就有多少。
从逻辑学的角度看,亚里士多德的范畴乃是简单语词或词项;从形而上学或是态学的角度看,则是对“是者”(τὰ ὄντα)的最大分类。“范畴”(Kategorien)体现着“逻辑学”(Logik)和“是态学”(Ontologie)的统一。简而言之,如古代评注者所说,它是:“那些简单的、最初的语词,这些语词通过简单、最初的概念指称着最初的、最高属上的是者。[12]”诸范畴是对“是者”进行在属上的“最大可能的分类”(μεγίστη διαίρεσις),即将“是者”在属上分为十种;正是基于这一点,在古代一些人甚至主张《范畴篇》一书的真正名称应是《论是者的属》(Περὶ τῶν γενῶν τοῦ ὄντος)或《论十个属》(Περὶ τῶν δέκα γενῶν)[13]。
既然在“是者”(τὸ ὄν)的四重含义中,只有范畴意义上的“是者”和潜能、现实意义上的“是者”属于第一哲学的研究对象,而后者又体现在前者当中,因此,范畴理论就构成了第一哲学(形而上学)或是态学的核心内容,而在诸范畴中,“所是”(ἡ οὐσία)范畴最为重要,对它的讨论又进一步成为了第一哲学的核心所在:
正如我们在前面关于一个语词有多重含义那儿所指出的,“是者”具有多重含义。因为它或者意指“是什么”即“这个”,或者意指“质”,或者意指“量”,或者意指这类谓词中的其他某个。尽管“是者”有如此多的含义,但显然其中首要的“是者”乃“是什么”,因为它揭示的乃“所是”(当我们问这个东西具有怎样的质时,我们说它或者是善的,或者是恶的,而不说它是三肘长或是人。但当我们问它是什么时,我们不会说白的、热的、三肘长的,而说人或神。),而其他的之所以被称为是者,乃是因为要么是这种是者的“量”,要么是它的“质”,要么是它的某些情状,要么是它的其他某种东西[14]。“首要的”具有多重含义,但“所是”在各方面都是“首要的”,无论是在逻各斯上,还是在认识和时间上。其他的范畴都不能独立存在,唯有它能够独立存在。在逻各斯上它是首要的(因为在每一范畴的逻各斯中必然存在着“所是”的逻各斯)。当我们知道人是什么,或者火是什么,而不是知道它们的“质”、“量”、“地点”等时,我们认为我们最为充分地知道了它们;而且我们要知道这些东西中的每一个,也只有当我们认识到“量”或“质”是什么时才行。事实上,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总是被寻求并总是让人感到困惑的东西,就是“是者”是什么,即“所是”是什么(因为一些人说它是“一”,一些人则说它不只是“一”,而是“多”;一些人说它是有限的,一些人则说它是无限的);因此,对于我们来说,最根本的、首要的和唯一的问题就是考察这样“是着”的东西是什么[15]。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诸范畴是不能彼此归约的诸最高的属。如果范畴之间的差异是最高属上的差异,那位于每一范畴之下的属、种也是不同的,它们彼此之间没有隶属关系。既然诸范畴都是最高的属,那么,它们除了不能彼此归约外,也不能归约到某一更高属之下。对此,亚里士多德给予了非常清楚的表达:
那些原初载体不同的东西,被称作是在属上不同的东西,它们不能彼此归约,也不能将两者归入到同一东西中;例如……以及那些归入是者的不同范畴中的东西(因为一些是者意指‘是什么’,一些意指‘质’,有些意指前面所划分出来的其他范畴)。它们不能彼此归约,也不能一起归入到某种“一”中[16]。那么,有无比作为最高是者的范畴更高、更普遍、统摄它们的东西呢?有!那就是“是(者)”(τὸ ὄν /τὸ εἶναι ,das Seiende / das Sein)。根据前面所讲,诸范畴也就是在其自身“是着”(τὸ ὄν)的诸方式;“是(者)”虽然比它们的普遍性更高,但“是(者)”本身不是一种属,即不是比诸范畴更高的、统摄它们的属。也正因为如此,它不“同名同义地”(συνωνύμως)谓述诸范畴;而根据亚里士多德,范畴作为属,“同名同义地”谓述位于其下的种直至个体:
属和种都是同名同义者。(συνώνυμον γὰρτὸ γένος καὶ τὸ εἶδος. 《论题篇》123a.28-29.)属同名同义地谓述一切种。(κατὰ πάντων γὰρτῶν εἰδῶν συνωνύμως τὸ γένος κατηγορεῖται. 《论题篇》127b.6-7.)“是(者)”(τὸ ὄν/τὸ εἶναι)是最普遍的,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讲就是它最为述说所有的东西。这又该作何理解呢?因为即使在古希腊语中,我们也发现,该词除了大量出现在系表结构中外(当然也可以省略),还有大量的句子不会使用它。要理解这一点,还是只能回到亚里士多德那儿。在我们前面所引的《形而上学》第五卷(Δ卷)第七章中的那段话中,亚里士多德说到:“‘是’(τὸ εἶναι)就意指着它们当中的某一个。因为人正在康复和人康复之间并无区别,人正在走或人正在切同人走或人切之间也无区别,就其他的情形而言也同样如此。”历代注家面对这句话,都做出了相应的解释,而托马斯·阿奎那在其《<形而上学>注释》(In XII libros Metaphysicorum AristotelisExpositio)中的解释最为清楚明白:
但是,由于有些进行谓述的语词在其中显然并未使用动词“是”——例如我们说人走路,为了避免有人以为这些谓词与“是”这个谓词没有关系,于是他接下来就排除了这种情况,他说:在所有这样的谓词中都有着某个东西意指着“是”。因为每一动词都可归为动词“是”加分词。因为说“人正在康复”和“人康复”并无区别,其他情形也同样如此。因此,显然谓词有多少种样式,“是者”就有多少种含义[17]。
“是(者)”(τὸ ὄν / τὸ εἶναι)虽是最普遍的,但却不是统摄诸范畴的属。亚里士多德本人不止一次讲到这一点:
“是”不是任何东西的所是,因为“是”不是属。(τὸ δ᾽ εἶναι οὐκ οὐσία οὐδενί· οὐ γὰρ γένος τὸ ὄν.《后分析篇》,92b.13.)“是”和“一”都不可能是诸是者的一个属。(οὐχ οἷόντε δὲ τῶν ὄντων ἓν εἶναι γένος οὔτε τὸ ἓν οὔτε τὸ ὄν.《形而上学》, 998b22.)对此亚里士多德的理由主要有两点:(1)一方面,无论是属、种还是种差,都可以用“是”加以谓述,因为“是”谓述所有的“是者”;另一方面,就属、种和种差之间的关系而言,属在本质上不能谓述种差,因为种差是外在于属的,正是通过它将属划分为种。因此,“是”不是属。(2)如果“是”是属,那么,就可以通过在它之外的种差将之划分为种,但“是”的最高普遍性不同于范畴的最高普遍性,因为在它之外就是“无”,故“是”不是属[18]。因而它不“同名同义地”(συνωνύμως)谓述所有的是者(当然包括诸范畴),而是“同名异义地”(ὁμωνύμως)谓述它们。关于这一点,珀尔菲琉斯(Porphyrius)在其《导论》(Isagoge)中也曾加以指出: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是(者)”并不是所有东西的一个共同的属,所有的东西也不会因一个最高的属而是同属的。但是,正如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中所做的那样,十个最高的属要被确定出来,它们就像十个最高的本原一样。他说,即使有人将所有的东西都称作“是(者)”,那他也是在同名异义的意义上而不是在同名同义的意义上那样称它们[19]。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在“同名同义地”和“同名异义地”之外,进一步提出“类比地”(κατ᾽ ἀναλογίαν)这一观点,明确指出,“是(者)”的最高统一性乃是类比的统一性,而类比的统一性是最高的统一性。
此外,一些东西在“数目”上是“一”,一些东西在“种”上是“一”,一些东西在“属”上是“一”,一些东西在“类比”上是“一”。那些在“数目”上是“一”的,其质料是“一”;那些在“种”上是“一”的,其定义是“一”;那些在“属”上是“一”的,指的是同一范畴形态适用它们;那些在“类比”上是“一”的,指的是具有如比例相同的那样的关系。后面的情形总是跟随着前面的情形。例如:凡在“数目”上是“一”的,在“种”上也是“一”;但在“种”上是“一”的,并不全都在“数目”上是“一”。凡在“种”上是“一”的,在“属”上也全都是“一”;但在“属”上是“一”的,并不全都在“种”上是“一”,而是在“类比”上是“一”。凡在“类比”上是“一”的,并不全都在“属”上是“一”[20]。
由于作为最普遍者的“是”(ὄν)所具有的统一性是类比的统一性,故亚里士多德将它标示为一种无规定的东西,这种无规定的东西通过诸范畴方才获得规定,而诸范畴自身也就是“是之规定”(Seinsbestimmungen)。根据亚里士多德,一方面我们的全部思维对象最终都会落入诸范畴之中;另一方面,也正是通过范畴,我们方能进行表象活动,放才能有思维的对象,各门具体的科学方才可能有自己的“基础概念”,并基于这些基础概念展开自己的活动。对范畴的思考属于形而上学(第一哲学)的任务,它属于对“是者”(ὄν)的一般思考,即归属在对“是者作为是者”(τὸ ὂν ᾗ ὄν)的思考中。因此,亚里士多德才会说:“有一门科学,它研究是者作为是者以及那些就其自身就属于它的东西。它不同于任何的特殊科学,因为其他那些科学中的任何一门都不普遍地思考是者作为是者,而是切取它的某个部分并研究该部分的属性。”[21]而海德格尔在《是与时》第3节“是之问题在是态学上的优先性”中的那段话则是亚里士多德这段话的最好注脚:
诸基本概念是这样一些规定,在这些规定中,那为一门科学的所有专题对象给予奠基的专业领域得到了在先的、并且引导着所有实证探索的理解。因此,只有在对专业领域自身进行一番相应的先行考察中,那些基本概念方才获得其真正的显示和“确立”。然而,只要每一个这样的领域都是从是者本身的畿域中赢得的,那么,这样一种在先的、创造诸基本概念的研究就只能意味着就是者之是的基本情状对是者进行解释。这种研究必须走到实证科学的前面;它也能够这样做。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工作就是其明证。对诸科学的这种奠基从根本上有别于跟在后面跛行的“逻辑”——逻辑不过是根据一门科学的“方法”来探索这门科学的某种偶然情况而已。对诸科学的奠基在下述意义上是生产性的逻辑:它仿佛先行跳进某一特定的是之领域,首先就这一领域的是之情状将该领域展开出来,并让赢得的诸结构作为对追问的各种透彻指示供诸实证科学使用。例如,在哲学上的首要东西既不是某种关于历史学之概念构造的理论,也不是关于历史学上的认识的理论,也不是关于作为历史学之对象的历史的理论,而是就真正历史的是者之历史性对真正历史的是者进行阐释。同样,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之积极成果在于着手清理出那属于一般的自然的东西,而不在于得出了某种关于认识的“理论”。他的先验逻辑是关于是之领域-自然的先天实事逻辑。(德文页10-11)
(三)
无论是范畴(dieKategorien)还是“生存论规定”(die Existenzialien),都是“是之规定”(Seinsbestimmungen),它们都是在是态学上(ontologisch)对“是者”的一般规定。只不过前者适用于非此是式的是者,而后者乃是对“此是”(Dasein)这种独特是者的规定。根据海德格尔的思路,《是与时》一书的最终目的是要拟定出“是之意义”(der Sinn von Sein),而临时目标则是对作为进行是之理解的视域的“时间”(Zeit)进行阐释。而这一视域是从一种独特的是者,即“此是”(Dasein)那儿显现出来的。
因此,一方面,所有“是态学”(Ontologie)所追问的都是“是者”(das Seiende)之“是”(Sein),而“是”自身不是某种“是者”(海德格尔语),“是”具有多重含义(亚里士多德语),因此,对于它只能拟定出它的“意义”(Sinn),从而生出“基础是态学”(Fundamentalontologie)。另一方面,既然“时间”是进行“是之理解”的视域,而它又是从“此是”(Dasein)这种是者那儿给出的,故需要对这种是者进行是态学上的分析,从而生起“此是之分析学”(Daseinsanalytik / Analytik des Daseins)。于是,“基础是态学”和“此是之分析学”具有了一种内在的关联,对此,海德格尔曾反复加以指出:
因此,所有其他的是态学所源出的基础是态学,必须在生存论上的此是之分析学中去寻找。(德文页13)现在已经显明:一般此是的是态学上的分析学本身就构成了基础是态学,因而此是所起的作用就在于,它就是那要在原则上事先就其是而加以询问的是者。(德文页14)因此,对作为是的是(Sein als solches)进行阐释这一基础是态学的任务就包含有对是之时态性进行清理。是之意义问题的具体答案只有在对时态性的整个问题的阐述中给出。(德文页19)就实事而言,现象学就是关于是者之是的科学——是态学。在前面已经给出了的关于是态学之任务的说明中,生起了某种基础是态学之必要性,它将是态学-是态上的独特是者,即此是作为课题,从而将自己带到了主要问题即一般的是之意义问题的面前。(德文页37)那直逼操心现象的关于此是的分析学,应准备好基础是态学的整个问题,即一般的是之意义问题。(德文页183)在继续探索这个问题之前,需要对迄今为了一般的是之意义这一基础是态学问题所进行的阐释进行一种回顾性的、细致的占有。(德文页196)传统形而上学所给出的范畴就是对是者的一般的“是之规定”,它们也适用于“此是”吗?显然不行!传统形而上学中的范畴只能适用于非此是式的是者(das nicht daseinsmäßige Seiende),它们无法规定“此是”。而海德格尔在《是与时》中首先要从事的,恰恰是要对“此是”进行是态学上的一般规定——他将之命名为“生存论规定”(Existenzial / pl. Existenzialien),这些一般规定蕴含在“操心结构”(Sorgestruktur)中,而操心结构的源始统一性在于时间性。“时间性在每一种绽出中都整体地将自己时间化,也就是说,生存、实际性和沉沦之结构整体的整体性——即操心结构的统一性,奠基在时间性之每一当前完整的时间化那绽出的统一性之上。”(德文页350)当然,即使这样,也并未完成该论文所设定的目的:“时间性将被展示出来,作为我们称为此是的那种是者的是之意义。这一证明必须在对那暂时展示出来的作为时间性的诸样式的此是之诸结构的重新阐释中得到检验。然而,将此是解释为时间性,那关于一般的是之意义这一主导问题的答案,并未随之就已经给出。但是,赢得该答案的地基或许已经被准备好了。”(德文页17)
无论是诸范畴(Kategorien)还是诸“生存论规定”(Existenzialien),都是“是之规定”(Seinsbestimmtheit),都只能放在整个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中来把握。康德将他的三个著名问题归于“人是什么?”(Wasist der Mensch?)这一问题之下,并将对该问题的回答视为其哲学的顶峰;而在海德格尔看来,这一基于传统形而上学而来的发问本身就是成问题的,所有的范畴都是规定不住作为“此是”(Dasein)的“人”的,因为对于他怎么能以“是什么”的方式加以追问呢,因为这种是者的“本质”(Wesen)在于它的“去-是”(Zu-sein)和“能是”(Seinkönnen)。因此,海德格尔说:
由关于此是的分析学而来的所有阐明,都着眼于其生存结构而赢得。因为那些阐明都从生存论性那里得到规定,所以,我们将此是的是之性质称为生存论规定。它们严格地同非此是式的是者的是之规定相区分——我们将非此是式的是者的是之规定称为范畴。在此,我们是在其原初是态学上的含义上选取和坚持这个表达的。古代是态学将在世界内照面的是者拿来作为其是之解释的范本性基础。而νοεῖν [认识]或λόγος [逻各斯]则被当作通达这种是者的方法。是者就在其中来照面。然而,这种是者的是必须在一种独特的λέγειν(让某种东西被看)中才成为可把握的,以至于这种是作为它所是的和在每一是者中已经是的,预先就变成可理解的了。那在对是者的谈论(λόγος)中向来已经在先的对是的谈及就是κατηγορεῖσθαι [述谓]。它首先意味着:公开地考问,当着所有人的面就某件事责问某人。这个术语在是态学上加以使用时,意味着:仿佛在责问是者,责问它作为是者向来已经是什么,也就是说,让所有人就其是来看是者。在这种看中那些被看到的和可以看到的就是κατηγορίαι [诸范畴]。范畴囊括了那在λόγος [逻各斯]中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可谈及和谈论的是者的各种先天规定。生存论规定和范畴是是之性质的两种基本可能性。与之相应的是者所要求那种原初的询问方式向来就各不相同:是者是谁(生存)或是者是什么(最广义上的现成性)。只有从是之问题那业已澄清了的视域出发才可能讨论是之性质的这两种样式之间的联系。(德文页44-45)
在《是与时》中,海德格尔所给出的关于“此是”(Dasein)的“生存论规定”(即一般的是之规定)主要有:在-世界-中-是(In-der-Welt-sein),世界性的(Weltlichkeit),自身(Selbst),在之中-是(In-Sein),依寓……而是(Sein-bei…),操劳(Besorgen),去远(Entfernen),定向(Ausrichten),设置空间(Einräumen),操神(Fürsorge),共同是(Mitsein),常人(Man),展开性(Erschlossenheit),处身性(Befindlichkeit),实际性(Faktizität),可能性(Möglichkeit),理解(Verstehen),言谈(Rede),沉沦(Verfallen),两可(Zweideutigkeit),好奇(Neugier),闲谈(Gerede),畏(Angst),筹划(Entwurf),缄默(Verschwiegenheit),意义(Sinn),真(Wahrheit),操心(Sorge)……。“此是”即“在-世界-中-是”,其余的那些生存论规定都是对这一基本整体结构中的诸要素的具体化,都是“在-世界-中-是”的“是之方式”,都是对此是这种独特是者的一般“是之规定”。
康德通过划界指出范畴只能适用于现象界,没有直观所提供的内容就是空,在现象界之外的运用只能导致各种幻象。海德格尔则指出传统形而上学中的范畴根本不能用在此是(人)这种是者身上的,对于这种是者的是之规定只能是生存论规定。因此,我们认为海德格尔在其未完成的《是与时》中的部分工作,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内容,它并不是对形而上学的拒斥,而是对它的延展;故他在该书的开篇就讲:“尽管我们的时代因重新肯定了‘形而上学’而视自己为一种进步,但这里所提及的问题如今已经被人遗忘了。”(德文页2)
The reject ofMetaphysics, or the extension of metaphysics?
——Anunderstanding concerning the ideas of Being and Time
u lin,PhilosophyDepartment Sichuan University
Abstractio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central idea ofmetaphysics is ontology, and the core of ontology is the theory of categories.The categories is the determinations of being for beings in general. Heidegger’s Being and Time gives the Existentials based on the existential analysisof Dasein. Both the categories and the Existentials are the determinations ofbeing for beings. the former applies to those beings unlike Dasein; the latterapplies to Dasein, and it is an extension of traditional metaphysics.
Keywords: metaphysics, ontology,the determinations of being, categories, the Existentials
主要参考文献:
1. Aristoteles, Kategorien, Übersetzt und Erläutert vonKlaus Oehler, Akademie Verlag Berlin, 2006.
2. Aristoteles, Metaphysik,Neubearbeitung der Übersetzung von Hermann Bontiz, 4. Auflage, Felix MeinerVerlag Hamburg, 2009.
3. Brentano Franz, Von der mannigfachenBedeutung des Seienden nach Aristoteles.Freiburg im Bresgau: Herder 1862.
4.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MaxNiemeyer Verlag Tübingen, 2006.
[1] 溥林(1970—),男,成都人,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教授。
[2] 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了“第一哲学”(ἡ πρώτη φιλοσοφία)这个概念,就现有文本来看,主要出现在《物理学》、《论天》、《论动物的运动》以及《形而上学》中(凡未注明出处的,所有亚里士多德原文均为作者翻译,并仅注明贝克尔标准页码)。例如:
περὶ δὲ τῆς κατὰ τὸ εἶδος ἀρχῆς, πότερον μία ἢ πολλαὶ καὶ τίς ἢ τίνες εἰσίν,δι᾽ ἀκριβείας τῆς πρώτης φιλοσοφίας ἔργον ἐστὶν διορίσαι.(准确地确定形式方面的本原——是一还是多以及它是什么还是它们是什么,此乃第一哲学的任务。—《物理学》192a.34.)
πῶςδ᾽ ἔχει τὸ χωριστὸν καὶ τί ἐστι, φιλοσοφίας ἔργον διορίσαι τῆς πρώτης.(确定可分离的东西是怎样的和是什么,此乃第一哲学的任务。—《物理学》194b.14.)
Ἔτι δὲ καὶ διὰ τῶν ἐκ τῆς πρώτης φιλοσοφίας λόγωνδειχθείη ἄν, καὶ ἐκ τῆς κύκλῳ κινήσεως, ἣν ἀναγκαῖον ἀΐδιον ὁμοίως ἐνταῦθά τ᾽ εἶναικαὶ ἐν τοῖς ἄλλοις κόσμοις.(这也能被由第一哲学而来的那些讨论和由圆周运动(无论是在这儿还是在其他世界,它都同样是永恒的)而来的那些讨论所证明。—《论天》277b.9.)
Περὶ μὲν οὖν ψυχῆς, εἴτεκινεῖται εἴτε μή, καὶ εἰ κινεῖται, πῶς κινεῖται, πρότερον εἴρηται ἐν τοῖςδιωρισμένοις περὶ αὐτῆς. ἐπεὶ δὲ τὰ ἄψυχα πάντα κινεῖται ὑφ᾽ ἑτέρου, περὶ δὲ τοῦπρώτου κινουμένου καὶ ἀεὶ κινουμένου, τίνα τρόπον κινεῖται, καὶ πῶς κινεῖ τὸ πρῶτονκινοῦν, διώρισται πρότερον ἐν τοῖς περὶ τῆς πρώτης φιλοσοφίας, λοιπόν ἐστι θεωρῆσαιπῶς ἡ ψυχὴ κινεῖ τὸ σῶμα, καὶ τίς ἡ ἀρχὴ τῆς τοῦ ζῴου κινήσεως. (关于灵魂——它是否被推动,如果它被推动那又是如何被推动的,我们已经先行在其他论著中探讨过了。既然所有无生命的东西都被其他东西所推动,而关于最初的被推动者和永远的被推动者是以何种方式被推动的,第一推动者又是如何进行推动的,这些问题已经在关于第一哲学的那些论著中被先行确定了,那么,剩下需要探究的就是灵魂如何推动身体,以及动物运动的本原是什么。《论动物的运动》700b.4.)
[3] Ἔστιν ἐπιστήμη τις ἣ θεωρεῖ τὸ ὂν ᾗ ὂν καὶ τὰ τούτῳ ὑπάρχοντακαθ᾽ αὑτό. αὕτη δ᾽ ἐστὶν οὐδεμιᾷ τῶν ἐν μέρει λεγομένων ἡ αὐτή· οὐδεμία γὰρ τῶνἄλλων ἐπισκοπεῖ καθόλου περὶ τοῦ ὄντος ᾗ ὄν, ἀλλὰ μέρος αὐτοῦ τι ἀποτεμόμεναιπερὶ τούτου θεωροῦσι τὸ συμβεβηκός, οἷον αἱ μαθηματικαὶ τῶν ἐπιστημῶν.《形而上学》1003a.21.
[4] ὅτι μὲν οὖν μιᾶς ἐπιστήμηςτὸ ὂν ᾗ ὂν θεωρῆσαι καὶ τὰ ὑπάρχοντα αὐτῷ ᾗ ὄν, δῆλον, καὶ ὅτι οὐ μόνον τῶν οὐσιῶνἀλλὰ καὶ τῶν ὑπαρχόντων ἡ αὐτὴ θεωρητική, τῶν τε εἰρημένων καὶ περὶ προτέρου καὶὑστέρου, καὶ γένους καὶ εἴδους, καὶ ὅλου καὶ μέρους καὶ τῶν ἄλλων τῶν τοιούτων.《形而上学》1005a.13.
[5] Ἐπεὶδ᾽ ἐστὶν ἡ τοῦ φιλοσόφου ἐπιστήμη τοῦ ὄντος ᾗ ὂν καθόλου καὶ οὐ κατὰ μέρος, τὸδ᾽ ὂν πολλαχῶς καὶ οὐ καθ᾽ ἕνα λέγεται τρόπον.《形而上学》1060b.31.
[6] ἡ περὶ τῶν ὄντωνθεωρία这一表达后来在拉丁语中被概念化为ontologia。现在一般认为ontologia一词最早是由德国哲学家雅各布·洛哈德(Jacobus Lorhardus, 1561-1609)在《八艺》(Ogdoas Scholastica)一书中提出来的,他将它视为形而上学的同义词。在该书中,他讨论了八门学科:拉丁语法(Grammatices Latinae)、希腊语法(Grammatices Graecae)、逻辑学(Logices)、修辞学(Rhetorices)、天文学(Astronomices)、伦理学(Ethices)、物理学(Physices)、形而上学或是态学(Metaphysices, seu Ontolgia)。
[7] περὶδὲ τῶν ὄντων ᾗ ὄντα ἐστὶν τὴν μετὰ τὰ φυσικὰ καὶ ὅλως τὴν πρώτην πραγματεύεσθαιφιλοσοφίαν. Simplicius,In Aristotelis Categorias Commentarium, 9.29-30.
[8] καὶ δὴ καὶ τὸ πάλαιτε καὶ νῦν καὶ ἀεὶ ζητούμενον καὶ ἀεὶ ἀπορούμενον, τί τὸ ὄν.《形而上学》1028b.2.
[9] 后来海德格尔就严格区分了“是”(das Sein)和“是者”(das Seiende),并将之称为一种“是态学上的差异”(die ontologische Differenz)。
[10] Τὸ ὂν λέγεται τὸ μὲν κατὰσυμβεβηκὸς τὸ δὲ καθ᾽ αὑτό, …καθ᾽ αὑτὰ δὲ εἶναι λέγεται ὅσαπερ σημαίνει τὰ σχήματατῆς κατηγορίας· ὁσαχῶς γὰρ λέγεται, τοσαυταχῶς τὸ εἶναι σημαίνει. ἐπεὶ οὖν τῶνκατηγορουμένων τὰ μὲν τί ἐστι σημαίνει, τὰ δὲ ποιόν, τὰ δὲ ποσόν, τὰ δὲ πρόςτι, τὰ δὲ ποιεῖν ἢ πάσχειν, τὰ δὲ πού, τὰ δὲ ποτέ, ἑκάστῳ τούτων τὸ εἶναι ταὐτὸσημαίνει· οὐθὲν γὰρ διαφέρει τὸ ἄνθρωπος ὑγιαίνων ἐστὶν ἢ τὸ ἄνθρωπος ὑγιαίνει,οὐδὲ τὸ ἄνθρωπος βαδίζων ἐστὶν ἢ τέμνων τοῦ ἄνθρωπος βαδίζει ἢ τέμνει, ὁμοίως δὲκαὶ ἐπὶ τῶν ἄλλων. …ἔτι τὸ εἶναι σημαίνει καὶ τὸ ἔστιν ὅτι ἀληθές, τὸ δὲ μὴ εἶναιὅτι οὐκ ἀληθὲς ἀλλὰ ψεῦδος, ὁμοίως ἐπὶ καταφάσεως καὶ ἀποφάσεως, …ἔτι τὸ εἶναισημαίνει καὶ τὸ ὂν τὸ μὲν δυνάμει ῥητὸν τὸ δ᾽ ἐντελεχείᾳ τῶν εἰρημένων τούτων.《形而上学》1017a.7.
[11] Heidegger, Sein undZeit, Max Niemeyer Verlag Tübingen, 2006, p.442. 为了便于行文,以后凡是出于该书的引用,均在正文中直接注明“德文页……”。
[12] περὶ τῶν ἁπλῶν ἐστι φωνῶν τῶν πρώτων καὶ τὰ πρῶτα καὶ γενικώτατα τῶν ὄντωνσημαινουσῶν διὰ μέσων τῶν ἁπλῶν καὶ πρώτων νοημάτων. Simplicius,In Aristotelis CategoriasCommentarium,13.19-21.
[13] 参见Simplicius, In AristotelisCategorias Commentarium, 15.27-30.
[14] Τὸὂν λέγεται πολλαχῶς, καθάπερ διειλόμεθα πρότερον ἐν τοῖς περὶ τοῦ ποσαχῶς· σημαίνειγὰρ τὸ μὲν τί ἐστι καὶ τόδε τι, τὸ δὲ ποιὸν ἢ ποσὸν ἢ τῶν ἄλλων ἕκαστον τῶν οὕτωκατηγορουμένων. τοσαυταχῶς δὲ λεγομένου τοῦ ὄντος φανερὸν ὅτι τούτων πρῶτον ὂντὸ τί ἐστιν, ὅπερ σημαίνει τὴν οὐσίαν (ὅταν μὲν γὰρ εἴπωμεν ποῖόν τι τόδε, ἢ ἀγαθὸνλέγομεν ἢ κακόν, ἀλλ᾽ οὐ τρίπηχυ ἢ ἄνθρωπον· ὅταν δὲ τί ἐστιν, οὐ λευκὸν οὐδὲθερμὸν οὐδὲ τρίπηχυ, ἀλλὰ ἄνθρωπον ἢ θεόν), τὰ δ᾽ ἄλλα λέγεται ὄντα τῷ τοῦ οὕτωςὄντος τὰ μὲν ποσότητες εἶναι, τὰ δὲ ποιότητες, τὰ δὲ πάθη, τὰ δὲ ἄλλο τι. 《形而上学》,1028a.10.
[15] πολλαχῶςμὲν οὖν λέγεται τὸ πρῶτον· ὅμως δὲ πάντως ἡ οὐσία πρῶτον, καὶ λόγῳ καὶ γνώσεικαὶ χρόνῳ. τῶν μὲν γὰρ ἄλλων κατηγορημάτων οὐθὲν χωριστόν, αὕτη δὲ μόνη· καὶ τῷλόγῳ δὲ τοῦτο πρῶτον (ἀνάγκη γὰρ ἐν τῷ ἑκάστου λόγῳ τὸν τῆς οὐσίας ἐνυπάρχειν)·καὶ εἰδέναι δὲ τότ᾽ οἰόμεθα ἕκαστον μάλιστα, ὅταν τί ἐστιν ὁ ἄνθρωπος γνῶμεν ἢτὸ πῦρ, μᾶλλον ἢ τὸ ποιὸν ἢ τὸ ποσὸν ἢ τὸ πού, ἐπεὶ καὶ αὐτῶν τούτων τότε ἕκαστονἴσμεν, ὅταν τί ἐστι τὸ ποσὸν ἢ τὸ ποιὸν γνῶμεν. καὶ δὴ καὶ τὸ πάλαι τε καὶ νῦνκαὶ ἀεὶ ζητούμενον καὶ ἀεὶ ἀπορούμενον, τί τὸ ὄν, τοῦτό ἐστι τίς ἡ οὐσία (τοῦτογὰρ οἱ μὲν ἓν εἶναί φασιν οἱ δὲ πλείω ἢ ἕν, καὶ οἱ μὲν πεπερασμένα οἱ δὲ ἄπειρα),διὸ καὶ ἡμῖν καὶ μάλιστα καὶ πρῶτον καὶ μόνον ὡς εἰπεῖν περὶ τοῦ οὕτως ὄντοςθεωρητέον τί ἐστιν. 《形而上学》,1028a.31.
[16] ἕτερα δὲ τῷ γένει λέγεται ὧν ἕτερον τὸ πρῶτον ὑποκείμενονκαὶ μὴ ἀναλύεται θάτερον εἰς θάτερον μηδ᾽ ἄμφω εἰς ταὐτόν, οἷον….ὅσα καθ᾽ ἕτερονσχῆμα κατηγορίας τοῦ ὄντος λέγεται (τὰ μὲν γὰρ τί ἐστι σημαίνει τῶν ὄντων τὰ δὲποιόν τι τὰ δ᾽ ὡς διῄρηται πρότερον)· οὐδὲ γὰρ ταῦτα ἀναλύεται οὔτ᾽ εἰς ἄλληλαοὔτ᾽ εἰς ἕν τι. 《形而上学》,1024b.9.
[17] Quia vero quaedam praedicantur, in quibus manifeste non apponiturhoc verbum est, ne credatur quod illae praedicationes non pertineant adpraedicationem entis, ut cum dicitur, homo ambulat, ideo consequenter hocremovet, dicens quod in omnibus huiusmodi praedicationibus significatur aliquidesse. Verbum enim quodlibet resolvitur in hoc verbum est, et participium. Nihilenim differt dicere, homo convalescens est, et homo convalescit, et sic dealiis. Unde patet quod quot modis praedicatio fit, tot modis ens dicitur.Thomas Aquinas, InXII libros Metaphysicorum Aristotelis Expositio, 893.
[18] 参见《论题篇》,144a.31;《形而上学》,998b.14。
[19] οὐ γάρ ἐστι κοινὸν ἓν γένοςπάντων τὸ ὂν οὐδὲ πάντα ὁμογενῆ καθ᾽ ἓν τὸ ἀνωτάτω γένος, ὥς φησιν ὁ Ἀριστοτέλης.ἀλλὰ κείσθω, ὥσπερ ἐν ταῖς Κατηγορίαις, τὰ πρῶτα δέκα γένη οἷον ἀρχαὶ δέκα πρῶται·κἂν δὴ πάντα τις ὄντα καλῇ, ὁμωνύμως, φησί, καλέσει, ἀλλ᾽ οὐ συνωνύμως. Porphyrius, Isagoge sive quinque voces, 4,1.6.5-9.
[20] ἔτι δὲ τὰ μὲν κατ᾽ ἀριθμόν ἐστιν ἕν, τὰ δὲ κατ᾽ εἶδος, τὰ δὲ κατὰ γένος, τὰδὲ κατ᾽ ἀναλογίαν, ἀριθμῷ μὲν ὧν ἡ ὕλη μία, εἴδει δ᾽ ὧν ὁ λόγος εἷς, γένει δ᾽ ὧντὸ αὐτὸ σχῆμα τῆς κατηγορίας, κατ᾽ ἀναλογίαν δὲ ὅσα ἔχει ὡς ἄλλο πρὸς ἄλλο. ἀεὶδὲ τὰ ὕστερα τοῖς ἔμπροσθεν ἀκολουθεῖ, οἷον ὅσα ἀριθμῷ καὶ εἴδει ἕν, ὅσα δ᾽ εἴδειοὐ πάντα ἀριθμῷ· ἀλλὰ γένει πάντα ἓν ὅσαπερ καὶ εἴδει, ὅσα δὲ γένει οὐ πάντα εἴδειἀλλ᾽ ἀναλογίᾳ· ὅσα δὲ ἀνολογίᾳ οὐ πάντα γένει. 《形而上学》,1016b.31-1017a.3.
[21]《形而上学》1003a.21.
原载于《同济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