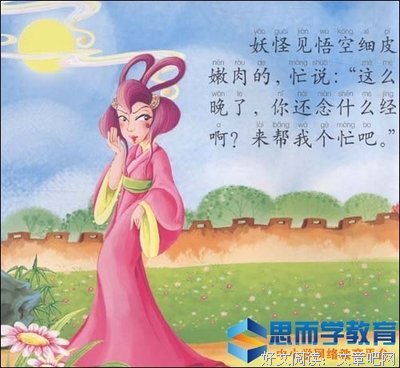
《永恒的敌人》是一本由[波兰]亚当·扎加耶夫斯基著作,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6.00,页数:21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永恒的敌人》读后感(一):我们需要诗歌
为你自己而读,为你的灵感,为你灵巧头脑中甜美的骚动。 可也要为对抗你自己而读,为疑惑和无力,为绝望和博学。 因为唯有如此你才能成长,越过你自己,进而成为你自己。 ——亚当·扎加耶夫斯基“我们需要诗歌,正如我们需要美。”这也是扎加耶夫斯基诗歌中的一句。如今,我们似乎已经远离了需要诗歌或者富产诗歌与诗人的年代,但我们就不需要诗歌了吗?其实不然,我们可以在其他艺术中也可以看到诗歌,比如电影,《路边野餐》、《长江图》、《在码头》等等,仍旧会发现诗人与诗歌的踪迹,只不过我们已经很少静下心来读诗歌了。
这次看扎加耶夫斯基新的两册诗集,他的经历与部分诗作会让我想到前两天读了的北岛的几册散文与杂文,是一位在平淡中的叙述者,用简单朴实的语言却能够直至读者的内心,美和丑、善和恶总并存于同一场域,从不加以褒贬。《无形之手》与《永恒的敌人》封面设计就会有一种“回旋往复”之感,其中诗作则也是如此,主要分为三种主题的诗歌:译者所说的“纪游诗”、“人物诗”以及对于诗歌探讨的作品“诗之诗”。
“纪游诗”:从诗人流浪到回归故乡
扎加耶夫斯基受到广泛注意,是近几年来的事。他流亡但又不那么流亡,这应该是他“纪游诗”最大的特点。每篇“纪游诗”中场景、人物、情感都异常丰满,更像是一场对于流亡生活的“漫游”。
后来,回到了故乡,他开始写现在的家乡、阿兹海默症的父亲与逝去的母亲,写谨小慎微的日常与旧人旧事。随着时间的流逝,年纪日渐衰老,正如宣传所说,这些诗“更属于世界文化,而不是政治”,而且“开始带有更多的哲学思辨,融入了更多现代手法,变得更成熟”。
“人物诗”:从书籍人物到作家旧友
在扎加耶夫斯基看来,写作的任务就是积极地寻找新的道路和新的生命。在阅读米沃什时,在怀念逝去的母亲和旧人旧事时,我们都可以看到人物在其诗歌中生命的延续。诗人终究不能被一首诗或者文章限定,他会捕捉到角色或人物细微的情感表露及意象,所以我们会看到他对于不同事物的反馈与表达的不同。
不论是诗歌还是其中的人物,都在“试着赞美这遭损毁的世界”。在这之前,他内含反叛,在一次采访中他说到:
“在我很年轻的时候,我没想过赞美。我认为我们必须哀悼或者反叛,而许久之后,我看到反叛是很短视的反应,因为如今没有太多敌人值得做出如此重大的反叛。同时,阅读我们的大师,我发现,赞美是诗歌主要的调子。”。“诗之诗”:从质问反讽到幽默和解
因为经历所以质问,因为时间所以和解,因为诗歌所以浪漫。他说:“诗是隐藏绝望的欢乐。但在绝望下面——有更多的欢乐。”当诗歌抛去了晦涩的隐喻,那它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子?简约、直入核心、别有含意。在去自我、去神秘,而逐渐物质的当下,诗歌似乎也正如扎加耶夫斯所说“我们将不断从灵感的柏拉图转到明智的亚里斯多德”。
在经济舱上,在威力电影院,在婚礼现场,我们都可以在其诗歌中找到平淡而又悠长的情感与诗句,寻找到那令人惊喜的诗歌,他似乎已经逐渐回归生活,少了之前对于社会和事件的质问,但又多了许多深邃,历史和情感总是结合在一起的。当然,我们捧起他的诗歌,还会发现其所做的质问与反讽都是我们当下所需要质疑的,它永远也不过时,陪伴着不同的文学介质,我们都能看到其中的内含。
就像《生活不是一个梦》的结尾所说,“而生活继续,不可避免的生活,那样怀疑,那样谨慎,它又坚定地回到了我们中间 以至于有一天我们感到寻常的失败,落到我们唇边的寻常悲剧的味道,它也是某种胜利。”
“我们生活于深渊,在暗淡的水域,在明亮里。”因此
我们,不能停止读诗。
我们,需要诗歌。
《永恒的敌人》读后感(二):诗的(不)可能性:扎加耶夫斯基的晚期诗歌
《无形之手》和《永恒的敌人》这一套两册扎加耶夫斯基诗集给人的舒适感是直接的——小开本、不到二百页、没有冗长的头尾,将最多的注意力投注到诗本身。译者的说明放在末尾,读者打开书就直面诗人——诗集理想的物理状态。正如这些诗本身:直接、不故弄玄虚、温厚如老友。
对于熟练的诗歌读者而言,扎加耶夫斯基不是陌生的名字。他甚至已经和波兰同乡米沃什、辛波斯卡、兹比格涅夫·赫贝特一同进入了大师行列。这个名单不仅有时空上的关联,也有明显的精神连带。读上几首扎加耶夫斯基的诗就会明白——对诗艺的追求与现实感的把握趋于平衡;对读者的邀请胜过筛选;力量潜伏于自然流露的哲思和节制的抒情中;常常严肃,又带着幽默感——这还是我们熟悉的波兰风格。
特别的是,扎加耶夫斯基在这两本诗集中展现了少有人书写的老年状态。这批作品在他将近七十岁时完成。主题上,父母、朋友、故乡占据了大量份额;风格上,在回忆和死亡的包裹下,伤感、疲倦的气氛让平和更为沉稳,但不是“沉郁”,因为时不时还带出一些严峻的幽默,构成奇妙的混合。另一个令人赞叹的特征是他更胜以往的放松——例如在纪游诗中看似信笔写就的句子,乍一看诗意淡薄,但松弛的即兴状态和对“金句”的隐隐对抗(扎加耶夫斯基其实很善于写精巧句子)达到了近乎天真自然的程度。
死亡固然是诗歌永远的主题,但老年不是。年轻诗人也可以谈论死亡,但他们没有老过。老年经验难以言说,也缺乏言说。这份困难正是留给诗人的任务。在献给米沃什的这首《伟大的诗人已经离去》中,扎加耶夫斯基写到:
“我们突然会感到无语,现在,我们必须为自己发言,没有人为我们发言了——因为伟大的诗人已经离去。”在“说”与“说不出”之间,扎加耶夫斯基开辟了一块不可思议的诗学空间。又如他献给母亲的这首《关于我的母亲》结尾一句:
“而我如何记得,如何从休斯顿飞往她的葬礼,却什么话也说不出直到现在。”这是关于“说不出”的言说。语言在关于自身的悖论中消解,同时完成。诗句中的虚无、伤感、无语凝噎又在诗的尝试中得到纾解和安慰。
再来看这首《奥斯维辛的燕子》:
“在营房的阒寂里,在夏日的星期天的无声里,燕子刺耳地尖叫。是否这就是人类的话语所剩下的一切?”这首诗几乎达到了诗的(不)可能性的极限。面对集/中/营*和大屠杀,“诗的野蛮”似乎成了一种难以挣脱的原罪,但诗仍然可能。在历史巨大的恐怖和罪恶之后,对人类(及其话语)的失望、虚无笼罩了几代人。扎加耶夫斯基承认了这种感受,同时写下了它。写作本身成为一种不可思议的精神行动。它是对虚无的反讽,也是对写诗本身的反讽。自反中又包含了无比苦涩的幽默感。诗在这些轻盈的句子里完成了沉重的自我证明。
在那些更个人化的写作中,扎加耶夫斯基以日常的词语、以呈现的方式完成了对记忆的追索和老年状态的言说。那些诗恐怕不是摘句式的评论足以介绍的,读者通读之后自然会感到这位诗人的魅力。
————
*这个词是豆瓣敏感词,测试时间:2021年3月9日
《永恒的敌人》读后感(三):扎加耶夫斯基诗集 设计手记
[删除]这是一个被迫营业。[/删除]
无形之手9.1[波兰]亚当·扎加耶夫斯基 / 2020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永恒的敌人8.8[波兰]亚当·扎加耶夫斯基 / 2020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一开始能确定的就是要做成窄小细长的开本,诗歌的体裁相对短小,感觉可以让人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阅读。原计划是两本打套一起出版的,后来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最终被拆分成了两本。所以一开始《永恒的敌人》连词条都没有。说着一段大概是为了强行解释为何两本要做成如此紧密相连的视觉体系吧(笑)。
初稿的时候还有一个版本的方案是只用黑白二色,因为觉得东欧诗歌是冷峻严肃的色彩。后来摒弃的原因也是这一个,心里想着难道冷峻严肃只能用黑白来表现了吗?最后决定反其道而行,用了比较鲜艳的色彩。回看文本本身,扎加的诗歌有兼具沉重的历史感和生活的日常感,说不好冷色调的紫色和绿色有更切题。
选择的封面图其实有和书名有一些隐性相关。《无形之手》的外封是被风吹动的树,内封是独自伫立在沙滩上的树;《永恒的敌人》外封是拿着弹弓和自己影子对峙的人,内封则是凝视着傀儡的人。有点像诗歌给人的感觉,隐约觉得和主题相扣,但文本表面却没有相关明显字眼。
外封上做了打孔,可以透过孔洞一窥内封的一些画面,像阅读诗句时感受表层意象同时隐约窥见作者文字下的隐晦映射。
豆瓣读者 珍妮的肖像 说:
随意散点开了五个圆洞,或者就是弹孔的意象,射向低语的诗歌,和我们缺席不了的知觉肤浅生活感觉有更贴近设计理念的解说呢,豆瓣的读者个个都是人才,说话又好听~
封面图可以左右拼接。长春三联书店的展台实体书到手后很多读者都发现了,这两本的封面图做了一点点小小的诡计,左右可以无限拼接在一起(看第一张效果图会更明显)。所以有书店一口气接连在展台展出六本相接,让我觉得挺开心的,有种诡计被人洞识的成就感。这样做大概是为了让大家 all in 吧,买一本的趣味性会减少哦(xd)。
内页的辑封页背面做了关于诗歌的句子设计。这套虽然是做了双封设计,但外封是不分离的,在路上阅读时也可以不必苦恼剥落下来的外封该放在哪里,也不会把外封随手丢掉后就找不到。
其实初稿方案在年前的时候已经出来了,定稿也是在年前。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我一度以为今年也许什么多做不成。2月份的时候打样直接寄到我家,我和编辑在小区的院子里碰头,商讨封面图片的噪点大小多少等细节,选纸,说起无法打套等事情。いろいろあったけど(虽然发生了很多事情),最终在初夏的时候这套小小的诗集得以面世,我觉得时间上恰到好处。还有什么时间比夏日和诗歌更般配呢。希望这两本沉重着轻松的诗集,能够和更多人一起度过风中的夏夜,驱除暑气。
作为一个一直一言不发丢设计稿的人来讲,讲这么一大篇废话纯属不易,奖励自己一朵小红花。
以上。
汐和
2020年6月30日
(6月的最后一日,有着一种无意义的充满意义。)
《永恒的敌人》读后感(四):扎加耶夫斯基:必须保卫诗歌
首发于深港书评:https://mp.weixin.qq.com/s/XZs5ZN5WZeWqFxiD1I5w7g
1933年,克罗齐在牛津大学发表了题为《为诗一辩》的演讲,这是锡德尼在1583年,雪莱在1821年之后最重要的一次“为诗辩护”。这次,他所反驳的还有雪莱,他指出雪莱的“诗人是立法者”割裂了人类精神中各个范畴的联系,将诗歌塑造为空幻的海市蜃楼。 克罗齐是对的,就像大部分现代主义者以及之后的我们所确认的那样。一个困难是“为诗辩护”常常低估常识和理性的力量,另一个困难是“在文章里为诗辩护的人忽略了正在写作中的诗歌”,扎加耶夫斯基如此说。
在当下的中国,扎加耶夫斯基的诗歌是在潮流之外的存在,而事实则刚好相反。当下的我们如此信仰着诗歌作为现代性、作为无限度、作为生活等等的责任,就像雪莱们所想象的那样。对于我们的谬想,扎加耶夫斯基是一剂良药。对于扎加耶夫斯基来说,诗歌寄存在某种整体之中,寄存在有限性的、破碎的整体之中,诗歌“来源于对世界、对可见与不可见的一切最深刻的欣赏”……“整体性?……整体只存在于部分之中,受到服务于宇宙的各种微小生物巨大的支持……我们时代的阿特拉斯,只是一头小牛……”
在去神秘、自我主体、理性遍在的当下,诗歌的存在是尴尬的,但也不那么尴尬。我们还没有适合高效的、辉煌的、野蛮的现代生活的一种诗歌,起码在中文世界是如此。我们还无法完全将诗歌用作我们即刻审思和吐露的语言的一部分,即便在文艺人士群体中也是如此。我们还无法在这个或者宏大或者卑微的现场书写一种确凿的诗歌,而未来不必然还是如此。它没有现成的道路,而我们时代的大诗人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回到一种最普世、最现实的立场之上,正如扎加耶夫斯所说“我们将不断从灵感的柏拉图转到明智的亚里斯多德”,他们和我们最终会走向哪里?
扎加耶夫斯基的诗歌似乎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轨迹和演变,类似于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两者都只是随着时间有了老态),但与后者不同的是,扎加耶夫斯基甚至连主题都没有变更过:世界、入门/敞开、生活的崇高。唯一变化的或许是晚期的他更眷恋着生活了,“我们的生活是平凡的/……/平凡的生活欲求着。”整体而言,扎加耶夫斯基的诗歌蛮像是一个熟透了的果实,这是现代主义之后的征兆,但更重要的是,它几乎代表了我们时代的诗歌的基本特征:它是饱满的,又是即将腐烂的。它饱满到没有善恶,它腐烂到只有新生。
扎加耶夫斯让自己的诗歌成为一种微不足道的存在,他的书写开始于在生活中醒来,又结束于在生活中沉睡。在经济舱上,他“蜷缩如胎儿”,享受一首诗歌诞生;在威力电影院,他在映后沉默许久,仿佛上帝就在身边;在阅读米沃什时,他懂得米沃什富有但孤零零,而诗歌之外还有城市的喧嚣;在婚礼现场,他写诗祝福情人们,“爱与时间/这永恒的敌人,会师一处”。诗歌的发生也不过是生活的缓慢加速和缓慢减速而已,它几乎没有了我们预想中的诗歌的加速度。可想而知,扎加耶夫斯基的诗歌预定的读者既不是对诗歌孜孜以求的作者们,也不是冷漠的没有准备好的消暇者们,它与之共舞的是开放的心灵,他们都很丑陋,也因此这支舞蹈是奇迹的。就像《生活不是一个梦》的结尾所说,“而生活继续,不可避免的生活,/那样怀疑,那样谨慎,/它又坚定地回到了我们中间/以至于有一天我们感到寻常的失败,/落到我们唇边的寻常悲剧的味道,/它也是某种胜利。”
真实状况和我们所想的仍然相差甚远。考虑到扎加耶夫斯基所经受的现代主义洗礼和全面的反讽训练,他所选择的恰恰是一个普罗米修斯式的传统,类似于米沃什,但更当下。在米沃什的世界里,诗歌是大灵魂的造物,诗歌的主宰作用从司铎祭祷、史诗、悲剧、基督教神学、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一直延续到神秘的又社会化的浪漫主义。在这份诗歌想象的中心便是普罗米修斯,在西方他是奥维德,在东方他是鲁米。扎加耶夫斯基不止一次向米沃什献诗,在《伟大的诗人已经离去》中,他一边哀悼,一边强调“现在,我们必须为自己发言……”他们共享了太多东西:克拉科夫(米沃什晚年定居于此)、真诚或者反“凯特曼”(米沃什:“文学产生于对于真实的渴望”)、世界(《世界(一首天真的诗)》:“我们和鲜花把影子投在地上。/那些没有影子的事物没有活下去的力量。”)、抵抗潮流(“这个世界的事物应该被沉思,而不是被解剖”)……
只不过,相比于米沃什,扎加耶夫斯基传达给我们的是一个简化的思想,他甚至连阿奎纳的思想都选择性地忽略了,还有弗洛伊德(他极力反对弗洛伊德,他在大学研究的是“内省”)……甚至可以说,单单看他的诗行,我们会认为这是幼稚而僵硬的物质。他在世界文学中的成名作《试着赞美这遭损毁的世界》不就是这样的吗?在这首诗里,扎加耶夫斯基显露了几个他的典型特征:平和而壮丽的几乎是反殉道式的爱、不断涌现的“形容词”(不是修辞学的形容词,而是博尔赫斯意义上的形容词,“轻轻附着在事物或人身上”)、多样性的有序(像植物有机状态一样)。或者几乎同样发生了的《神秘主义者入门》。或者像《世界的散文》的笨拙的结尾,“生命的散文在我们周围展开,/而诗蜷伏在一间心灵的小室。”
扎加耶夫斯的诗歌是新古典音乐式的新古典诗歌:简约、直入核心、别有含意。在《雨燕风暴般聚集在圣凯瑟琳教堂上空》里,扎加耶夫斯基让词语和意义或者符号和神话交织演绎成轻妙的音乐,它所呈现的并非反讽,而是澄明,错杂而寂静的澄明。《雨中的天线》更是如此,它没有一个中心的意义,它的每一诗行都缺少显然的联系,维系它的是心灵的元素,是Periagoge,是诗歌里面的说话和寂静。新古典诗歌遵循简单而杂粹的规则,它表面的冷静理性之下是广阔有灵的世界。单就扎加耶夫斯基而言,这是不是他所钟爱的爵士乐、交响乐所赐予他的礼物呢?简言之,扎加耶夫斯基将艾略特、卡瓦菲斯拖曳到了二十一世纪,需要平静多过于一切的二十一世纪。
扎加耶夫斯基于1945年6月21日生于波兰老城利沃夫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是整个贵族世界的一部分,他寄身在被规训的单一的世界里,他的记忆又充满了坚不可摧的绿色。不久后,一家人就携带着仅剩的银和画作迁徙到西里西亚省格里威策,像贵族一样落魄地生活着。扎加耶夫斯基沉浸在侦察、足球、收音机、爵士乐和藏书的世界里,11岁做童子军的经历让他懂得如何在巨兽的掌心做冒险活动,而不是游击活动,他对摄影深有领悟,“在黑色的点之间,物体被编织出来,边沿反射着白线条似的光”。在这里,他还会见了赫伯特,他教给他什么是诗歌,或者如何才能抵达诗歌,这是要永恒地去抵达的路,很巧的是他被指导到了这里。在一生所爱的城市克拉科夫,他就读于雅盖沃大学学习哲学和心理学,并一劳永逸地发现了那个想象力的世界,“可触、可见、芳香的世界”,他开始大量阅读,持续地为贡布罗维奇和舒尔茨激动不已,同时他也开始真正写诗,在狂喜的瞬间、在凯木丛中、在爱情故事里、在记忆中、在文学宣言里,写一首诗。1968年前后,他随心做了一段愤怒的青年,参与巷战,被抓进警察局待了一小时,不过他没有停留在这里,他只是像多数人一样从一个时代移入另一个时代。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人结成了“现在”运动,在一个残酷的和变革的时期,源于荷尔蒙和野心,诗歌注定是艰难的。扎加耶夫斯基的诗歌从树上落下来,新嫩无比,像“失去外壳的栗子”,“像创伤一样红润”。他不会将自己认同为“新浪潮”的一部分,他对于“新浪潮”只有漠然,他认为“新浪潮”利用了集体性的情感,不过他们这波人用演讲、激情和攻击达成了对于未来的协定。他游走在集体主义和创造世界的野心之间的地带,相信政治和社会,相信它们赠予他的灵感和源泉,正是否就像奥维德的相信呢,但更关键的是,他没有放弃“一种根植于文学的贫瘠空洞的文化”,就像奥古斯丁一样。
不像苏联诗人不得不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土壤中靠着小圈子和个人的力量野蛮地生长,波兰诗人似乎有一种集体性的共识,这或许要归功于他们文学的启蒙紧跟着欧陆主体的潮流,或许要归功于波兰的地缘政治和历史契机。扎加耶夫斯基的诗歌所表现的阵痛相较于米沃什已经大为减少,相较于密茨凯维奇更是如此, 但这并不妨碍他有着机敏的嗅觉,并不妨碍他写道,“在营房的阒寂里,/在夏日的星期天的无声里,/燕子刺耳地尖叫。//是否这就是/人类的话语所剩下的一切?”战后的波兰先是涌现了一波对于传统文学的清算,它们的基调是现实主义的,但如今看来是以现代主义为基础的现实主义。在波兰推广几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很久就受到作家们的批评,在1956年的“十月转折”后,作家的真诚和美学得到了巨大的释放,清算文学再一次涌现,它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达到高潮,而这就是扎加耶夫斯基登场的时期。在阿·桑达韦尔的波兰现代主义诗人版图中,赫伯特和辛波斯卡被视为是第四代诗人,那么显然地扎加耶夫斯基就是第五代。在二十世纪,从青年波兰,到《新文化》,再到《当代》,最后到后来的新浪潮,波兰诗歌共享了一种超越政治的国族想象,它是正义的,是伦理学的,更是诗学的。同样地,很显然,存在一种显而易见的波兰因素,它弥散在赫伯特、辛波斯卡,甚至更早的密茨凯维奇的诗篇里:它是机警的,是人直接和世界相遇的,是回避双重性的,最终它是赞美诗式的……对于他们而言,诗歌不在这里,它“来自于另一个世界”,隐藏在被邀请之中。
作为波兰最好的文论家英伽登的学徒,扎加耶夫斯基并未沾染观念/意识形态、反讽/幻灭、虚无/秩序,他选择了古老的立场,在这里,(世界的、生活的)历史和情感总是结合在一起的。比如在《暴风雨》中,“我们穿过暴风雨宛如一道真正的河谷。/你驾驶;我怀着爱注视着你。”虽然这是私人生活的书写,但是它带领我们进入了神秘的沟谷之中,在那里,诗歌成为激荡、不确定的、神秘的存在。总是这样,一边是其他,一边是生活,“吟唱格奥尔格·特拉克尔的诗,/而我们需要梦想和生活。”(《雨滴》)他总是提醒我们,我们在具体和超验之间滑动,在两者之间,居间存在,“我们持续的运动,总是以某种方式暴露出另一边。”他是那么简单,他会胜利的。
扎加耶夫斯基是流亡的但也不那么流亡的奥维德,他不咆哮,也不呻吟——原谅他写得没有那么出色,原谅他不曾为诗辩护,原谅他总是寻求着光芒。在今天还有什么没有继续延伸下去吗?还有什么不是有限的但渴望面对无限呢?还有什么不是在现代性、全球化的废墟之后新了那么一点?还有什么是不属于诗歌?不属于一片云的呢?还有什么宏大而庄严的论题没有留在这一小片地方呢?从现在开始,走进诗人为我们建起的家吧。在这些哀悼、祈祷、苦涩、血里,就这样生活、回忆吧。你将知道,这些伟大的事物“一旦成熟,接近它们的本质,它们就变得坚固、真实、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