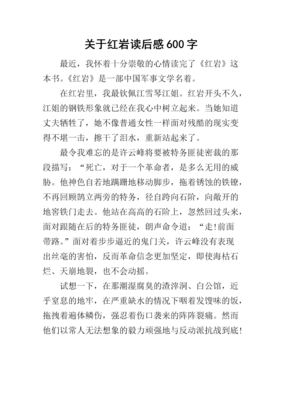
《“自然”之辩》是一本由杨治宜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2018-1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自然”之辩》精选点评:
●很喜欢作者对苏轼诗文细读与阐释。
●写得很好,可以再细致些
●好题目。
●22岁的第一天结束了眉山之行,孜孜以寻的,最终成为了我本身。
●还可以嘛,主要是问题提得很清楚。把“自然”当做一种被设定出来的状态,它有其内在的时间性,而人只能通过对其终极性、完满性的否定达到真正的畅达和自我解脱,人和诗都永远处于生成之中。读的过程中感到有不少能够和当代思想产生对话的地方,我认为作者对苏轼的理解是符合情理的,并且打开了更加深远的阐释空间。
●三星半。
●诗与人生,美学与哲学。 回到自身。
●我法不然,非千非一。如百千灯,共照一室。虽各遍满,不相杂坏。
●此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苏轼研究专著,毋宁说是以苏轼为媒介,对“自然”这一命题进行了美学和伦理学的精彩阐绎。阅读过程中,时有思想的闪光点,胜在行文流畅,以及糅合中西方理论而造成的陌生化的表达效果。(杭州,利奇马台风过境次日傍晚)
●视角偏奇。不朽诗人之有限,不知诗人自己作何想?
《“自然”之辩》读后感(一):《“自然”之辩》——杨治宜
本书的核心观点就一个——苏轼所说的“艺术即修行”,而所谓“自然之辩”是指苏轼在实际生活中用行动在这个观点上的三种辩论: 1.苏轼与王安石之辩:(1)关于科举考试,王安石建议取消诗赋科而改考时务科,但苏轼认为教育改革是系统问题,只改考试科目收效甚微;(2)关于艺术,程灏认为唯有读圣贤书才能获得真理,但苏轼认为诗词歌赋和琴棋书画一样是学习方法;(3)关于佛学,禅宗认为立地成佛不应该受艺术干扰,但苏轼认为写诗不仅能成佛并且还是很有效的方式。 2.中国文化面貌之辩:苏轼用“艺术即修行”的观点和行动影响着中国文化面貌:(1)打破写词道德禁忌——“所有文化力量都为己所用”;(2)开创文人画传统——“各种艺术载体都为己表达”;(3)用艺术重释人石关系——“各种审美对象都为意义载体”。 3.《形影神》一书之辩:晚年苏轼可谓穷困潦倒,但是他依然乐观豁达,并借用《形影神》一书的分饰三角来思考人生,并用艺术处理痛苦。 最后,个人是很崇拜苏轼的,不管是文学艺术成就,还是人生和生活态度,正如“艺术即修行”所说去,人生何尝又不是一场修行呢?
《“自然”之辩》读后感(二):苏东坡的自然与逍遥
文王绍贝
作为一个“东坡粉”,我最喜爱阅读苏轼作品时所感受到的“坦荡之怀,任天而动”(郑文焯),那种放任自然、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简直就是一种无上的“心灵鸡汤”。他被贬谪到蛮荒之地,却依然乐观、旷达,我们倾向于认为他的文章就是他天性的自然流露,但苏轼的“自然”境界真是彻底的“天性”,没有“人为”的因素?他的“自然”是如何达到的?杨治宜的《“自然”之辩》一书,通过细读苏轼文本,对苏轼的文艺审美思想作了精彩的论述,为我们阅读苏轼提供了诸多启发。
面对“人为”与“自然”之间的鸿沟,批评者们用“天才”概念来解释艺术品超越其物质性、仿佛能够沟通天人的力量。天才总是带有前瞻性的,因此多数艺术天才都只能留待后人发现。———譬如凡·高生前穷困潦倒,死后作品却价值连城。苏轼却是少有的在生前便被时人认定的天才。他本人也把自己的创作过程描述为“道法自然”的自由流露,从而印证了他在旁人眼中的“天才”形象。苏轼把自己的文法比喻为流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符合自然而然(古代“自然”一词的意思不是物理世界,而是指顺应自然而然的规律和法则行事)的特点,那么苏轼在创作上是排斥技巧的吗?否!否!
苏轼在《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一文中强调了技巧的重要性,艺术的自然创造力乃是基于学与习之上,所以在得意、得法之上,还需要勤奋练习才能心手相应。文艺创作必须“学”,而且有“法”,他还用“道”与“技”的关系来阐述审美规律,“道”与“技”之间存在一种辩证关系和张力,他的审美理论每每引用《庄子》的典故,暗示自然创造力乃是灌注了“道”的“技”。
苏轼深受佛学思想的影响,宋代佛学“渐修”与“顿悟”“文字禅”等等非常流行,苏轼经常借用这些理论来阐释艺术创作中“人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宋代“自然”一词主要是指艺术家心灵的无意向性的表达,佛学也是塑造这种人格典范的思想资源之一。“悟”是一种从束缚中解放出来,进入完全自由的澄明之境的状态。然而在“悟”之前,修行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从有限跃入无限,一切修行手段都是方便。“渐修”是偏重于技巧的,而“顿悟”则是达到“自然”的必要飞跃。自然的审美表面不但需要有心、持续、刻苦的练习,也需要在创作的那一刻引导自己进入物我两忘之境。
苏轼的“自然之艺”指的是经过长期集中、有意的训练,高度掌握了一系列模式化的技法、动作或者思维方式之后,向一种不再需要反思的直接状态的回归。一旦“自然”成为艺术的最高理想,最好的艺术品就必然是个人化的了。可以说,对“自然”理念的强调恰恰契合了北宋主要文人艺术种类里大胆的个人主义潮流。
通过高度个人化的形式,艺术作品不仅保存了作者,也保存了他的个性和生活经历。苏轼去世后,黄庭坚曾被人请去鉴定一幅书法是不是苏轼的真迹。经过仔细检查,黄庭坚宣布这是伪作。他的理由是:“东坡先生晚年书尤豪壮,挟海上风涛之气,尤非他人所到也。”作者的“自然”风格最终保证他的作品成为自我的替身,因此一位“知音”便能从作品认出作者,并像承接绵延不绝的流水那样,把作者的生命记忆保存在自己的生命里。这样,作者便实现了不朽———并非与天地共生的绝对不朽,而是与他的读者共存、对他的作品的审美体验共存的有限的不朽。
放逐岭海期间,苏轼创造性地运用“追和”古人作品这种形式,实现自身创作与人格塑造的另一种飞跃。“追和”陶渊明的全部作品的“和陶诗”表明了文化传统对他自我意识的影响。“自然”是艺术家不断向其“回归”的目标,但这一目标是不可企及的,因为它仅仅作为“人为”的否定面存在,所以任何向它回归的努力都只能导致它的不断退隐。与“自然”相联系的是“平淡”一词,“平淡”是宋代美学的基本理念,有宋以前多为贬义,指无味无趣者,而宋代以来则开始代表简单表面下隐藏的不简单、丰富和韵味。苏轼定义的“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平淡的审美表面需要最高的艺术技巧来造就,这是一种臻于极致后学会自我约束、作减法的技巧。苏轼认为“平淡”的美学风格乃是掌握最高的文学技巧之后的返璞归真。通过晚年有意效法陶潜,效法陶潜即“回归陶潜”,一位能够达到极度铺张繁复的作者有意回归的风格极简主义。苏轼把陶渊明的形象提升成了崇拜和神话,而通过戴上他所建构的这个陶渊明的面具,他对自己的命运行使了一种想象的权力。作为结果,他向内心的自然的回归也同时成为从客观自然的撤退,撤入逍遥的内在乌托邦之中。
刊于 南方都市报 2019年05月19日 A15版
http://epaper.oeeee.com/epaper/A/html/2019-05/19/content_16966.htm#article
《“自然”之辩》读后感(三):作者跋
作者跋
根据《圣经·创世纪》的神话,亚当和夏娃在偷食知识之果前是没有自我意识和羞耻感的,他们就像野兽一样裸身,天真游荡。而当他们获得自我意识的刹那,也就是真正成为“人”之始祖的刹那,就被永恒地从伊甸放逐了。作为“人”的人不能生活在伊甸园里,但伊甸这一纯真之地却成了普遍的理想,是我们试图“回归”的地方,因为在那里我们终于可以放下自我意识这一沉重的负担,与无合一。思维有一种超越纯粹物质存在的内在需要。自然的理想因此具备了某种乌托邦的性格,是永恒否定、永恒不满的。但终极的否定乃是否定思维本身。这样一种最高层次的反思重新肯定了物质存在,把人类主体性丧失的状态高举为理想国——一个人类从中放逐了自身的理国。“道”既是目标、也是道路。在通往绝对自然的道路上,一旦当人意识到最终目的地并不存在、而旅途本身就是真理,人或许也就能分享伊甸的至福。 本书中,“自然”的概念是通过否定和辩证的方式得以定义的。绝对的自然只能存在于被丧失的或不可企及的状态。矛盾的是,当一个人努力超越自己、同时又清楚意识到自己限度的时候,他却忽然可能获得一种暂时的、有条件的逍遥自然。这恰是苏轼“快乐天才”的源泉。它是一种仁慈的天才,和蔼可亲又令人振发。尽管他时时流露出超迈的理想──要化身“万斛泉源”、如天工造物一般创造艺术作品,或者要作罗浮山上的谪仙人,与宇宙万象往来──他也嘲笑自己作为凡人的有限性。他必然要妥协,因为束缚的力量过于强大,不论是人性的弱点还是政治的威权,命运抑或死亡,他都无法反抗。但如果这样的洞见与现代存在主义不无类似的话,那么他的乐观精神则让他与众不同。他眼中看见的世界不是一个荒谬无意义的无情宇宙,而是无穷无尽的自我完善的可能;而假如“自我完善”假定了一个完美的终点,他也悬置了这一终点是否存在、存在何方的问题。因此,他的“自然”拥抱了自身的反面,包括中介性、物质性、文化典范和仪式的规定性。此外,他还常常以幽默的方式把这套逻辑用作修辞技巧,以达到各种现实的目的,譬如自我说服、自我辩护、社交的客套和巧计等等。他诗中所暴露的这些“弱点”恰恰让后世读者倍感亲近,允许他们把苏轼的诗歌想象成忠实的明镜,映射出作者真实的人格。某种意义上,尽管作为学者的我在阐释学上有意拉开距离,但我的读解也同样延续了这一神话。苏轼的这面镜子里,映出的是我作为现代、跨文化读者的面孔。 不过,读者不断把自己的经历带进对作者的阐释之中,这或许不是什么坏事。戴维·洛奇[David Lodge]的《小世界》[Small World]虚构了一位英国文学专家莫里斯·乍浦[Morris Zapp]教授,他雄心勃勃地想要写一本关于简·奥斯丁的集大成之作,给整个“奥斯丁研究”领域划上一个句号、一个终止符。幸运的是,中国文学的学生不会有这样的雄心。自苏轼身后,近千年间已经有无数对苏轼的读解,每一种都试图发现他的真面目,而这一努力至今不息,使得他的作品真正成为“经典”。就像歌德所说,经典是永远阐释不尽的;或者如卡尔维诺所说,它永远说不完它要说的话。每一代读者都发现新的进入苏轼的途径,使他成为他笔下的庐山: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如果通过他作品的接受史,苏轼已成匡卢,那么我的读解也是历史的一部分,为这座山又贡献了一张现代的素描。 这本书也是我个人经历的一部分。我自幼就喜欢苏轼,读研究生的时候有幸在张鸣先生的课上比较系统性地读了他的作品,并最终在博士期间决定写一本关于苏轼的书。这也许是因为东海岸的普林斯顿离我江西的老家之间恰隔着一个大洋和美洲大陆的距离。苏轼的黄州寒食诗每每让我想起刚到美国的窘境: 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 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 刚到普大的那几天,学期还没开始,我未知的室友还没有抵达,学校安排的公寓周边环境又富于地广人稀的荒野之趣。周末没有巴士。公寓是白木墙壁、塑胶地板、单栋单排的军营样式。除了床垫和电脑,四壁皆空,我既没有电话,又没有熟人,更没有交通工具。东海岸的九月,绵密的细雨封锁了天空,室外的绿草开始转黄,只需要一个足印,便会浆汁崩裂、摧折腐朽──但是并没有人行来打破它们低头静默的生存。就连邻居的狗,也不堪孤寂在苦雨中哀鸣。然而度过这个周末,周一的世界忽然又充满阳光,青草重新振作,我的室友到来,我去系里报道,并认识了一群极度聪明、友善的新朋友。但六年的温暖美好时光并不能驱散开端的孤寂;又或者那孤寂其实是与我相侔的,吸引着我的回忆。我后来想,就像林语堂一样,我们都是在文化的“流散地”[diaspora]找到了苏轼,得到慰藉和心灵的向导。 我的个人之旅是不随着一部博士论文便结束的。2013年夏,我终于来到四川盆地中部的眉山,一座潮湿多雨的小镇。“三苏祠”如今是当地的旅游名胜,每天都有中国各地的游客络绎不绝地来此朝圣。导游说,门内的两株大银杏树是苏轼、苏辙神童时代手植的。尽管是年春天的雅安地震毁坏了花园里的部分花木和建筑,银杏树却依然无恙。如果导游所言不虚,那么这两棵浸润过苏氏兄弟手中汗水的树,就是我们离天才最近的物理证据了。但其实故事真假并不重要。阴湿狭窄的亚热带花园里处处都回荡着大宋帝国的遗音。虽然苏氏后人都没有生活在眉山,但两位少年在广阔天地里的成就与光荣,都在他们留在身后的空壳里被吟咏、纪念。至今,既没有见过苏氏子孙、也没有见过那片天地的家乡人民,依然以他们为荣。我去眉山是为了开一个苏轼的研讨会,与会者自然都是苏轼专家。祠堂的每个细节都引发他们无穷无尽的苏轼学讨论。我们随口摘引苏轼的作品,会心一笑,彼此默契。通过苏轼,我们被联结在了一起。我们流动的窃窃私语把这座残破的花园转化成微型的宇宙,其中充满了历史、地理、诗人的生命瞬间和鲜活的文化记忆。我忽然有一种错觉,仿佛苏轼还活着,他走在我们中间,和善地点头微笑,参与着我们的对话,透过我们的身体长存。多年来,与他的对话是我灵感的源泉。我因此写下这个故事:我如何通过这些对话,抵达自身。
杨治宜
《“自然”之辩》读后感(四):杨治宜对谈丨内心的乌托邦:苏轼的自然美学
晚上好,终于见面了!之前的线上读书会,我都是充当撰稿人和画外音的角色。这次上镜的原因,是为了这一期的嘉宾。 这一期雅昌艺术读书会,请到了一位重量级嘉宾。我的好朋友,杨治宜教授。 杨教授目前执教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汉学系。她的导师、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主任柯马丁先生(Martin Kern),也是西方汉学界的泰斗。杨教授常年生活在德国,这次为了雅昌艺术读书会讲座首次破例,一下子奉献给雅昌的观众两个“第一次”,第一次线上对谈的方式讲课,第一次跟普通观众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所以我也必须要出镜支持,这也是我的“第一次”。这次读书会,采用隔空视频对谈的形式,也是读书会的“第一次”。这四个“第一次”,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请多多给我们留言反馈。 之所以会请到杨教授,是因为之前鄙人在讲“当绘画成为奇迹”第三讲,受到她的一本书的启发。就是这本《“自然”之辩:苏轼的有限与不朽》。 这本书很神奇,原本是2015年以英文版写成并出版,2018年受到三联的邀请,又用中文改写了一遍,增加了“名花的挑战”一章。她在里面提出的“自然之辩”:苏轼的自然美学观念,还有“无用之用”,包括苏轼作为传统文人,他的“奇石癖”,对于枯木怪石的喜爱,都有被我借用到我的讲义中。 艺术和文学从来不分家,我们可以举出很多艺术家与诗人、作家过从甚密,也有很多艺术风格受到文学流派的影响。所以这一次是关于文学和诗歌的对谈,我们双方都认为,PPT太多,会影响对谈节奏,所以大家就听我们聊就行,静静的体会诗歌、文学的魅力和趣味。对谈中涉及的苏轼诗歌,我会打在屏幕上,请大家注意看。下面我们有请杨教授。
(以下简称“陈”,“杨”)
陈:杨老师,您好,给雅昌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杨:观众朋友,大家好,很荣幸有这次机会和大家见面。我现在德国法兰克福,在家里,因为这个新冠疫情吧,所以在家里也是属于禁闭状态。 陈:您那边现在几点,是有时差吧?杨:对,下午两点一刻,跟中国差六个小时。 陈:那边疫情怎么样?杨:德国其实还好,暂时属于不可防,但是可控的状态。就是说这个(感染)人数还是在上升,但是这个曲线已经比较平缓,新增的人数没有到一个指数状态。第二就是死亡人数,暂时还不算太多,相对于感染人数而言。然后就是医院的医疗资源还没有被挤兑,还有大量足够的重症病床。 陈:好的,杨老师把自己在疫情期间的工作和生活记录了下来,被发表在今天(Uarts)官微的第二篇,有兴趣可以看。这里就不多聊,我们正式进入对谈。
〔 一 〕
艺术与自然:关于自然(Spontaneity)的美学概念
陈:刚才我们已经开始聊到这本书了。枯木怪石意象、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大家都听得很有趣。但这只是表象,怪石也好,“名花”也好,再深入,就是苏轼和老庄哲学之间的关系,也是艺术创作,不管它是诗歌、文学还是绘画,与自然美学、哲学之间有一定关系。而且这个关系呢,尤其在中国的传统的文人、传统的艺术,文人画影响深远。这本书也是杨老师通过对苏轼研究,探讨了自然美学的概念。所以可否请杨老师先给大家聊一聊,关于自然的美学观念。 杨:好的,这个问题当然比较复杂,不是三言两语可以完全讲清楚的。因为艺术跟自然的关系,应该说在中国的古典艺术,美学传统也好,在西方的古典美学传统也好,都是一个不断挑战着我们去思考的一对概念。所以在这本书里,我简单介绍一下英文题目叫Dialectics of Spontaneity,就是自然辩证法,所以这个英文词,Spontaneity,对应的是,在中国,所谓道家哲学的自然,尤其是庄子哲学的自然,不是现代中文意义上的大自然,就是不是Nature,而是Spontaneity。然后我们会看到“自然”这个词,它的构词法很有意思,是“自”,自己,加上一个“然”,就是这样,如此,对吧。所以自然的这个含义就是即强调不凭借外力、只凭借自身的性质或能力而形成的状态,就是如此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个外观。 所以在我的书里会说,Spontaneity这个词,当然主要对应的是“自然”,但它并不完全只对应这个词。事实上,在中国,传统的艺术批评美学这个话语里面有大量的词都跟Spontaneity这个词相关。譬如说天然、天才、神钧、神思、无心、无为等,对吧。所以你仔细看一下这几个词的构词法都很有意思。天然、天才、神钧、神思都是强调一个超越性的主体:“天”或者是“神”作为施动的主体,然后达到的结果就是,“然”(“这样”),“才”(“才能”),或者是“钧”(就是制作),然后“思”(就是思考)。所以就说它们强调的是一个超越性的主体带来的结果。或者是像无心也好,无为也好,它是强调一个施动主体的缺席,没有主体、没有心、没有为(就是无作为)形成的这个境界。所以我觉得它就很有意思,它其实强调的是作为个人的一个意向性,或者是个人主动性的一个缺席。 所以我们看到,像这样的批评话语,其实苏轼本人也多次非常非常熟练的运用,他的自评文称“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我的文章就像一万斛泉水一样,不去挑选它出来的那个地方。创造力一喷薄,它就出来了,就是强调自己创作的无意识状态,仿佛创造力的流露,第一是不经人力干涉,甚至不经过他本人的意向干涉;第二就是不经过他的创作媒介,包括选择用某个文体来表达,选择哪些词汇来表达等等,都是没有经过选择,它是自然而然出来的。然后很多苏轼的评论者,都是强调这一点,书里都引用了,就不具体讲了。 所以后世评论家会强调说,因为苏轼天才嘛,所以说读者如果真正会心的话呢,对他作品的接受,就像是流水一样,从作者的心灵已流入到读者的心灵,有点禅宗的讲法了。所以像这种探讨中,诗歌作品本身的语言习惯、技巧、成规,作者本身的这个意向性的干涉,仿佛都可以忽略掉。所以,在我们中国的艺术批评里,对于Spontaneity或是“自然”这种状态的通常的一种诠释。 但是为什么这本书叫做辩证的“自然”(《“自然”之辩》),因为我要强调的是: 第一点,我们所谓的美学都必然是接受者的美学,历史上的人物苏轼也好,梵高也好,哪怕他们是天才,但不管怎么样,他们都消失了。事实上,读者只有通过作品来想象作者,对吧,所以作者是我们读者所建构起来的一个对历史人物的想象。所以事实上,虽然苏轼的自评文称“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好像是说他的这个流露是一个直接的状态,从他的那个心灵里面直接流出来,可以直接抵达读者的心灵。 但事实上,南宋也有人说,他在苏轼的后人家里,看到苏轼的手稿,上面其实是涂涂改改的,就是全是涂改的痕迹。所以我强调说,事实上,作者是否在创作时,处于这样一种自然自发的状态,并不重要,关键是他的作品,让读者产生这样的感觉。好像我们就真的在跟作者毫无障碍对话一样。或者是你看到梵高的作品会说,哎呀,我知道他在那一刻处于什么样的心灵状态,这个才是作者的天才所在。 陈:我这里打断一下,你把这个苏轼和梵高来类比,但他们俩实际上是有不一样的。梵高在世时并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苏轼实际上,在他去世之前就已经有盛名,诗歌有盛名,一个得到大家公认的天才级的诗人。那你觉得他们俩之间的这个差异性在哪里呢? 杨:这个问题就大了。其实,苏轼在整个中国古代的诗歌史上是都很少见的现象:生前就被认为是大天才。我想李白可能是唯一可以类比,李白也是生前就被认为是天才。其他的诗人都是在死后才重新因为种种原因(被认知),因为诗歌接受史的原因,因为他们作品的前瞻性,对于后代形成了一种典范性的力量。所以这个我觉得在艺术史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就是诗人、诗歌在生前或者艺术家在生前是否能够得到欣赏。 海德格尔有一篇文章很有意思,谈的是艺术品的“物”的性质。因为我们经常强调艺术品,简直就是充满天才,充满魔幻力量的。海德格尔就提出一个问题,说假如梵高他的画在身后,没有被人欣赏,躺在地下室里面,跟土豆放在一起,那么他的一幅画,跟土豆有什么区别呢?或者是贝多芬的一个奏鸣曲(Sonata),从来没有被演奏过,就躺在那里,那么它跟纸有什么区别呢?艺术品,它必然是“物”,它有很强的“物”的属性。 当然,这里面的诗歌跟画还是有很大的不一样,因为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嘛,所以苏轼会谈到艺术传达的“艺术的力量”,艺术的感发力量,跟它的媒介之间的关系。画的话,还是可以直接让观众来看,音乐要通过演奏者才能够跟听众发生关系。那么诗歌呢,给人感觉就是说,似乎连印在上面的纸,都可能不是那么重要。因为古代的诗歌,包括《诗经》也好,主要是通过口头传诵的。苏轼也有这样的想法,他有谈到“诗、书、画”的关系,其实诗的话,跟读者发生的关系仿佛更加直接,因为语言是我们存在的一个空间,任何一个人群,一个民族,它跟自己的母语的关系,类似于婴儿和母亲的关系。没有这样一个母语,我们不会有我们的想法,我们自己行动的方式,我们对自己的认知,都是通过母语发生的。所以语言跟“人之为人”的属性,是非常相关,非常重要的。 我们谈了第一点:从艺术批评史来说,什么叫做“自然的美学”。第二点,就是说,在我看来,自然美学,跟读者、听众、观众的一个关系。第三点就从创作主体来说,虽然苏轼,他好几次都半开玩笑的说,说自己从来不练习什么的。但其实苏轼他并不否认,刻意的有心的练习非常非常重要。包括黄庭坚也说,其实苏轼经常临摹前人书法,包括他不欣赏的那些书法家,他也经常临摹,而且他在《文与可画竹记》里面也说,其实要经过大量的练习才能做到心口相应,胸有成竹。而且通过练习,才能够不仅得其意,即创作的原则,而且得其法,即创作的方法。 所以就一种美学的创作原则而论,“自然”始终是辩证的自然,即在经过大量练习之后,在创作的一刹那让自己陷入遗忘的状态,任凭作者那一刻的不完美的真实通过艺术媒介流露出來。所以它是一个动态的辩证的平衡,就是在有心和无心、记忆和遗忘、完美和不完美之间,所以艺术是一个求道的过程。可能艺术家,他永远达不到那个“道”,但他始终在求道,他始终在朝向完美的不完美之中。但这个最终的完美,我强调是一个“否认”的状态,它不存在。它只有在我们说它不存在那一刻而存在。 陈:无限接近但永不达到。 〔二〕关于诗歌内心的乌托邦:从苏轼“和陶诗”到想象的自由 陈:你也提到了苏轼。实际上,诗、书、画三者都俱佳。而且是在生前就已经得到世人的认可。那我们来聊聊苏轼的诗歌吧。其实他的诗人的名声还是远远超过了他的画家的名望。因为诗歌都是口耳相传,苏轼的画,到现在为止,其实存世的肯定就三幅半,(可能,对,而且是“可能”是真迹,或者说“可能”存世。)嗯,这个对这个流传也是一个问题。 下面这一个话题呢,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诗歌,内心的乌托邦,因为苏轼,他谪贬好几次,他在谪贬的期间,或者是在他不顺利不顺心的日子,怎么样在自己内心建立起一个乌托邦?或者说怎么样达到这种想象的自由? 杨:苏轼遭到贬谪,平生被贬官三次,“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他的贬谪是他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第一次被贬黄州,是因为他跟王安石变法的对立。大家都知道,北宋中期最重要的政治事件,王安石变法。苏轼的(政治主张)其实我们如果用现代的话来说,应该是保守派里面的温和派。他基本上反对很多变法的措施,但是也同意其中的一部分,他同意变法的目的是强国强兵。所以他跟王安石其实最早的时候,并没有特别绝对的对立,他还参与了变法初期的一些工作,在京城。但是很快,王安石他这个人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很急于求成,然后对于意见跟他不同的人,马上大发雷霆。所以苏轼在京城待着待着就发现他跟变法派的那个裂痕越来越大,然后就被迫出京了。 出京之后他去了杭州,在杭州,他最早接触了禅宗。因为苏轼是四川人,他虽然家族信佛,但信奉的是比较老派的佛教,就是以念经啊,做法事为主,以修行为主。他到了杭州之后,才跟当时新兴的禅宗、禅僧发生了更多的交集。所以出京的这段时间,对于苏轼后来的诗歌风格、美学理想有非常大的影响。 后来就经过密州、徐州等等,突然就被别人密报说他的诗“讥议今上”,用西方的话来说就是lèse-majesté,这是非常大的一个罪名,可以杀头的。所以有了“乌台诗案”,乌台诗案审来审去,最后也没审出什么来,包括就连皇太后都说苏轼没有“讥议今上”。所以苏轼捡了一条命,被流放到黄州去了。 他在黄州确实是非常的穷困潦倒。因为其实宋代大多数的贬官,他都有一个地方的职位,包括苏轼的弟弟苏辙被贬到筠州,就现在江西宜春我的老家。他(苏辙)在筠州,是收盐酒税,市场上的税,所以是一个小吏的职位,是有一点薪俸。但苏轼可能确实是朝廷比较记恨他,所以苏轼连一点薪俸都没有,所以他当时非常穷困,开始开辟一个荒坡,东坡,而且(写作)《东坡八首》的时候,就已经有流露出对陶潜(陶渊明)诗歌的一个接受。 但是苏轼他以前的诗歌,和陶渊明诗歌是非常不相像的,所以苏轼的诗歌,分为前半段和后半段:开始学陶之后,跟学陶之前。包括苏轼的批评家里面,也有两派不同的意见,一派认为苏轼前期的这种才气奔放的诗是好的,另一派认为苏轼后期学陶风格走向平淡的,这个是好的。 陈:对,杨教授(能否)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唱和诗?什么是“和陶诗”?可能要简单的给我们普及普及。 杨:唱和诗从六朝开始兴起,但早期跟后期的形式不完全一样。在六朝的时候,可能大家诗人在一起,就是一起喝酒。然后某个王子写了一首诗。然后他也写一首酬唱的诗,把他(前面人)的意思用不同的语言再重新讲一遍,到结尾再添上几句,就是发表了自己的观点,然后唱和的意思就是你唱我和,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是好朋友,所以唱和(诗)是一种社交的诗歌写作的形式。 到了唐代开始,特别是从那个白居易和元稹开始,开始有步韵唱和,白居易和元稹是好朋友,他们在不同的地方任职期间,还继续把自己的诗寄给对方,然后对方拿到诗之后又用同样的韵脚重新再写一首诗再寄回去,然后收到的人可能再用同样的韵脚(和诗)。所以一套韵脚可能在这种酬唱的过程中,可以写上百十首的也是有的,后来酬唱就慢慢成了一种风气,就是所谓的步韵唱和。唱和是朋友之间写的一种诗歌形式。唐代有没有“和”古人的作品呢?可能有,但是并不常见,也没有成为风气。 后来苏轼是在贬谪结束之后,任扬州太守期间,他有一天忽然喝酒的时候有心得,说想写和陶饮酒二十首。其实大家知道苏轼的酒量是非常不好的。 陈:我知道苏轼特别喜欢酿酒。而且据当时的笔记小说,说他酿的酒特别难喝,而且他自己酒量特别小,又特别爱醉。他这个酒当时是怎么个酿法,你知道吗? 杨:他酿酒是去惠州以后,在扬州的时候还是喝别人酿的酒。他确实酒量特别小,“空杯亦常持”,他觉得很好,我不用喝多少酒,我就喝醉了。苏轼在扬州的时候,写了《和陶饮酒二十首》,但那只是一次性的事件,并没有升华到要把陶诗都和一遍的地步。 后来再贬。变法派重新上台,然后守旧派又重新被贬谪,苏轼被贬到了惠州(就是现在广东惠州)的时候,有一天他去白水山瀑布下面洗澡,然后忽然在半醉半醒之间,(可能是)在午睡,听到儿子苏过——因为苏轼其实有几个儿子,但是跟他去岭南的只有儿子苏过还有侍妾朝云,朝云在惠州因为瘴气死掉了——然后他(苏轼)在沐浴和午睡之后,听到儿子苏过在那边朗诵陶潜的《归园田居》,非常有感触,忽然就是下决心要“尽和陶诗”,把陶潜的每一首诗都拿过来用同样的韵脚再重新写一遍。 这个在苏轼是个非常大的事件。我前面说过,刚刚说过就是苏轼的诗歌风格,以前跟陶诗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清朝的纪晓岚,说苏轼是“敛才就陶”,把他很大的才华,非常非常雄瞻的风格,非常丰富的词藻收缩起来,开始写类似于陶潜的非常清浅的平淡的五言小诗。但是苏氏虽然是“敛才就陶”,也时时“露其本色”。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在书里谈到的,苏轼跟朱熹对于“平淡”的不同的见解。 苏轼开始“尽和陶诗”,这个在中国诗歌史上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事件。在文学接受史上。我们如果用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的《影响的焦虑》的讲法,那么陶潜(陶渊明)就是苏轼的literary precursor,苏轼认为他和一个前代诗人,能够通过文字建立一个类似于投胎转化的关系。所以这个苏轼和陶,有重要的文学史的意义。
然后这个(和陶)对陶渊明变成一个经典的诗人,也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像苏轼这样一个当时名满天下的天才,认为自己是陶渊明的后身,而陶渊明在当时还不是被大家认为是最最第一流的诗人,包括苏轼年轻的时候也认为陶渊明还不是第一流的诗人。但是通过他老年的这样一个忧患的转换,把陶渊明变成一个经典的诗人。在苏轼之后,很多人都写了“和陶(诗)”,也是受苏轼的启发。 陈:我按照你的理解,就是说,其实和陶诗,是苏轼被贬谪之后,对真实处境、不是特别好的处境的一个转化。在这个处境下,苏轼建立了一个内心的乌托邦,把不自由转化成自由的形式。 杨教授,其实乌托邦呢,是一个挺西方的一个观念,或者一个词语,你是怎么在书里头,把“桃花源”和“乌托邦”两者对应上的呢? 杨:我应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乌托邦”。
乌托邦,用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话来说,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这本书——这本书写的非常好,也不是很难。希望大家有机会看一下——意识形态Ideology有广义跟狭义(之分)。广义就包括所有我们思想建构起来的这套体系,狭义的就是Ideology,跟Utopia乌托邦是对立的,那么狭义的意识形态是维持现有体制的,而乌托邦则是对现实秩序的否认,甚至是反抗和对抗。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为什么说我们说苏轼把不自由转化为自由,因为贬谪是不自由的,贬谪的一个官僚,依然是这个帝国的官僚。陶潜(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挂冠而去,就是到乡里去耕田,对吧,他其实是自由,其实是一个选择的权力,而苏轼当时并没有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权力,他是个囚徒,只不过他的囚笼是惠州,是儋州。所以苏轼通过和陶,把他当下的这个不自由转化为一个自由,而且也是对他当下处境的一个反抗。 我在这个论述里面,有三点,我想请你放下这个PPT。 *以下诗歌文本解读,可在完整版视频观看
1.
苏轼对岭海蛮荒的文化想象:《和陶·归园田居》
《和陶·归园田居》这首诗。第一点,就是说他和陶诗里面,对于岭海这样一个蛮荒之地,进行了一个文化的想象和转换。譬如说:
第一句,环州多白水,际海皆苍山。它其实是把自然界的这些意象,建立一个文学的对仗。大自然是不对偶的,大自然没有说水一定是白的,山一定是黑的,对吧。其实水既不是白的,山也不是黑的。大自然并不对偶。然后,苏轼是把大自然这个意象,用语言的方式把它组织在一起,让大自然的这种无序,让没有经过驯化的惠州这个蛮荒,变成一个秩序井然的大自然的印象。而且它不仅是有秩序的印象,而且是环州际海,是环绕着人类建立起来的一个小小的社会。所以大自然是有仁慈的,保护人类事业的一个力量。
以彼无尽景,寓我有限年。又是对偶。当然,陶渊明的诗本身是对偶的,所以他是对陶诗的一个借鉴,也是通过无限的时光,超过人类的生命之外的。在我们人类生命、我们有限的生命之外,(无限)这个时光其实是跟我们发生着关系,这个(关系)本身是通过想象而发生的。那么苏轼说“以彼无尽景”,用无尽的风景,既是包括时间意义上的,也是空间意义上的这样一个风景,来寓我,暂时的寄宿我有限的年华。那么人的生命,跟这个无限的自然无限的时间也发生了一个关系。而且这个关系我要强调是仁慈的,大自然、历史对人的生命起一个保护的作用。
东家著孔丘,西家著颜渊。这个是类似于笑话了,就是他的左邻右舍都是儒家的圣人了。惠州是什么地方,当时是中华文明的边界,对吧。苏轼在其他诗里有写到,当地人是“践蛇及茹蛊”,地上走一步就会踩到蛇,吃的东西可能都是很多昆虫。但他会说我的左邻右舍都是儒家的圣人。
市为不二价,农为不争田。包括普通老百姓可能不识字的老百姓,都是非常非常道德纯良的。就把惠州这样一个中国文化的边缘地带,甚至是蛮荒地带,转化成在中国经典里面所描写的最好的最好的这样一个地方。所以我会说,它是通过文字对他所处的现实处境的转化。
那么这个转化有什么意义呢?大家要知道,当时像我说,苏轼经过不断的贬谪,他一辈子在这个官僚系统里面,他和这个系统有什么样的关系。我在书里面会写到一个主题就是“咏三良”。
其实苏轼年轻的时候,他第一个工作就在凤翔县,所以他经过了秦穆公的墓。在《左传》里面,秦穆公算是一个有为的贤君,他死了之后呢,让他国家里面最好的三个年轻人,为他(秦穆公)殉葬。殉葬是自愿的吗?其实,这是不是说这个秦穆公也是一个暴君、昏君?为什么年轻人要为你殉葬?反正不管怎么样,《左传》是说“国人哀之”,大家都觉得他们死的实在是很可怜。所以后来的这个评论家有很多的讲法,他们到底为什么殉葬。其中有一个讲法,就是说他们因为是之前就承诺过秦穆公,要跟他一起赴死,所以他们是自愿的。
所以说是他在年轻的时候,他是说我们现在都没有这样好的风气了,所以我们才会怀疑古人会不会因为一个简单的承诺,而付出自己的生命。
那么大家会看到,其实到了惠州之后,他选择《和陶咏三良》就有非常大的变化。
他写到:此生太山重,忽作鸿毛遗。生命是很重的,你怎么能够把它像大雁的羽毛一样丢弃。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就算他们真的做过承诺,那么为之而死的这个原因也是非常非常微小的。
贤哉晏平仲,事君不以私。这个就突然有意思了。他突然把晏婴的故事引进来,是什么故事呢?晏婴的国君是因为偷情被杀了,所以晏婴有去吊唁,但是别人问他要不要去殉葬,他说我不,因为我的国君不是为了公事而死,他是为了私事,因为偷情被杀的,所以我不能够成为他的牛马一样,我为什么要为他殉葬。
所以苏轼接下来说: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我难道是君主的一条狗、一匹马吗?我需要他放在我头上这个华盖吗?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我不是不能死,但是要为一个大节就是重要的一个道德原则而死。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如果这个我的国君为了社稷而死,那么我可以去殉葬。
顾命有治乱,臣子得从违。魏颗真孝爱,三良安足希!魏颗的故事是说魏颗的父亲(去世前要魏颗)把自己最心爱的侍妾杀了殉葬。魏颗当时说好,但是父亲死了之后,并没有这样做,别人问为什么。他说我父亲死前,头脑是不清楚的,所以要我做出这样的事情。如果我父亲头脑清楚的话,他绝对不会让我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宁可要保全我父亲的名节,也不要因为他临终之前的这个乱名而坏了他的清名。所以苏轼在这里说,魏颗的忠,和对父亲的孝(孝和忠两面一体的),他这个孝才是真正的忠。三良安足希!三良没有什么值得钦慕的。
仕宦岂不荣,做官难道不好吗?有时缠忧悲,但是你会有各种各样的忧患和悲哀。像苏轼这样被贬到惠州那样的地方。所以靖节翁,服此黔娄衣。所以陶靖节(潜)要像黔娄一样,宁可忍受穷困,也要挂冠归隐,不在这个系统里做了。
所以我觉得苏轼这首诗其实非常有力量的,表达他当时政治思想的一个作品。而苏轼对自己的处境是非常清醒的。他知道他不是陶渊明,他的出处不同。
在苏轼写完了和陶一百零八首诗,从儋州从海南回来以后出版的时候,他的弟弟苏辙在前言里面也写到说,就是他们的外迹是非常不同的:陶渊明挂冠归隐,而苏轼被贬了三次,还老老实实地在这个系统里面,是不是他这样就不合适。苏辙说他们的心境是一样的。心境,就是说他们内心其实都是自由的,他们之所以一个要归隐,一个被贬谪,都是因为他们内心的自由所导致。其实写“和陶诗”是我的书的第五章。第五章其实就是关于自由和勇气的。
也就是说,不论是归隐也好,还是贬谪,还是没有出仕(仕途),但是他们的内心有一种殊途同归的感觉。不论你在哪里也好,你只要把自己安顿好了,你就能达到一个自由的状态。
苏轼他有一句话说的很妙。他说有些话如果闷在心里,会伤我自己,吐出来会伤人,那我觉得伤我自己不如伤别人,我就吐出来好了。所以他这个是强调不管他的外在境遇如何,不管后果如何,我们要诚实,我们要有勇气,说我们真正应该说的话。
在一定的成分上,苏轼在归隐期间所想象的“乌托邦”,它既有政治的也有哲学的,也有道家的养生方面的想法。因为苏轼其实后期,这个毋庸讳言,在岭海期间,他做了很多养生修行的练习。所以大家知道中国的所谓的“乌托邦”,经常有对应着一个词“桃花源”。
因为陶渊明的桃花源则是“逃秦”,因为不堪秦人的暴政而逃走的一批人,躲到山里面,一群农民。他们建了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跟外在世界不再发生关联,“秋熟靡王税”,到秋天有了收获,我也不用交税。外在于这个政治秩序之外,但是并不外在于社会习俗,并不外在于人类社会之外。它同样是一个老少有序的,热情好客的这样一个社会。就是它外在于政治秩序,但并不外在于社会习俗。
2.
内心的乌托邦:《和陶桃花源并引》
我们所谓的文本历史就是 Contexts,没有一个文本是凭空产生的。因为苏轼写《和陶桃花源》的时候,他面对着六朝和唐代大量对桃花源的述说。其实六朝和唐代对于桃花源可以说是“滥用”的一个状态,我就不细讲。所以苏轼他开头第一句话,就是说“世传桃源事,多过其实。”因为他们经常把桃花源认为是仙人住的地方,其实并不是。
考渊明所记,止言先世避秦乱來此,则渔人所见,似是其子孙,非秦人不死者也。所以就是他们不是仙人。然后他接下去说,其实各种各样长寿的村庄啊,然后(人)活的很长的一些地方都挺多的。
桃源盖此比也欤。使武陵太守得而至焉,则已化为争夺之场久矣。如果有一个当官的来这边,开始制定法律啊,收税啊等等,那么它这个地方就变成了勾心斗角的地方。所以他会说:尝意天壤之间,若此者甚众,不独桃源。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桃源可以说是无政府主义的一个理想的乌托邦。这是他写《和陶桃花源》的引子,他对桃花源的一个看法。
那么接下去,写的就是凡圣无异居,清浊共此世。桃花源跟其他地方,并不是在物理空间上隔开的。就是凡人跟圣人,并不住在不同的物理空间,有道德的人和有没道德的人也都共享同样一个居住的物理空间。这是人和人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避免。
心闲偶自見,念起忽已逝。在我心处于闲适状态的时候,桃花源就自己出现了。但是我一旦有个念想,意念的波动,一旦有意去寻找它的话,它就突然消失了。
所以这第二句话就已经很明显的,把桃花源变成内在的一个状态,就是人处于完全的Spontaneity,处于完全的自然自发状态的时候,就会自动进入的内心的这样一个境界。下面(诗)用了很多道教和道家的术语,我就暂时跳过。我想讲下结尾。
梦往从之游,神交发吾蔽。还是强调一个梦跟神交的一个状态,精神状态。桃花满庭下,流水在戶外。是对桃花源的描写。卻笑逃秦人,有畏非真契。他反而会说,你如果有意逃避这个秦朝暴政的话,还是有所畏惧,有畏惧的话,就不是我的真的知己了。所以我觉得这句话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对这样一个外在的暴政的系统处于畏惧状态的话,你不是桃源的合格居民。
*以上诗歌文本解读,可在完整版视频观看
3.
回归自然的老庄哲学:《和陶·归去来兮辞》
《和陶·归去來》呢,是苏轼到海南以后写的。苏轼在惠州其实慢慢经营起来,慢慢觉得日子过得也不错。他后来在白鹤峰,还建了一个新居。白鹤峰是那个六朝的道士葛洪炼丹的地方。他认为自己可以开始练道教的长生之术了,可以成仙了。结果新居刚刚落成,他写了一首诗:“尽(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先生已经睡得很好了在春天,请外面的道人敲钟时候打得轻一点,表达他当时这种闲适自足的状态。当时的宰相,王安石的弟子,章惇读到这首诗,据说是勃然大怒,说苏轼过得这么舒服,我们把他贬得再远一点吧,就把他贬到海南岛去了。 大家如果今天去海南的话,会看到很多椰子树啊,应该说今天是很好的地方,但当时你说从海口到儋州,我们等于可能到了巴布亚新几内亚那样,在蛮荒部族中生活,对吧。当地人带着椰子做的冠,穿着草织的衣服。所以他这样一个名满天下的苏轼,被贬到儋州去,跟当地人生活在一起,必然是非常苦楚的。他在信件里说,慢慢觉得自己已经不是人,就是人的定义,就是文化的人。我们已经不是人了。 但是呢,他在他的诗歌作品里,就努力强调说我随便到了什么地方,都已经回到了我的家里,因为我的家是我的内心,这样一种自然的状态。所以我引用了这个《和陶·归去来》: 子瞻谪居昌化,追和渊明《归去来辞》,盖以无何有之乡为家,虽在海外,未尝不归云尔。他的家在“无何有之乡”,就是《庄子》里面写的那个大樗树,百无一用的大樗树,种在什么都没有的“乌有之乡”。
〔三 〕
关于自我
我的诗人苏轼
陈:我想,虽在海外,未尝不归云尔。这句话可能对于杨教授来说,会有一些感慨吧。杨教授常年在海外生活,虽在海外,未尝不归云尔。“你的诗人苏轼”是这本书的缘起。苏轼和你之间的关联,是怎样的呢? 杨:这个问题我感觉怎么有点私人啊!是这样的,其实我在书的一开始,就有跟林语堂作对。但其实书的末尾会写到,我跟林语堂写苏轼的缘起是类似的。林语堂当时也是跑到美国,然后自己的行囊里面装不了几本书,但他把苏轼全集带上了。通过阅读苏轼,他也是获得一个(乌托邦吧)。也可以说,苏轼读陶渊明,林语堂读苏轼,或者我在海外读苏轼都是类似,就是寻找自己真正的根源,跟力量勇气吧。嗯,我确实是非常喜欢苏轼。
陈:后记里面写道:“就像林语堂一样,我们都是在文化的‘流散地’找到了苏轼,得到了慰藉和心灵的向导。” 杨:对,是这样,因为流散地,就是所谓的Diaspora。你跟你的这个文化的母体、文化的这个根源切断了联系之后,怎样重新定义自己的文化身份,对吧。 我想这是当时苏轼在岭海遇到的一个问题,也是我后来去美国读博士的时候,给自己提的一个问题。所以对苏轼的这样一个探讨,它不完全是外在的,它也是内在的,是我跟我内心的一个对话。“我的苏轼”不是一个外在的历史的诗人,他是我内心存在的一个文化典范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也可以说写苏轼,是让我“虽在海外,未尝不归云尔”的。 陈:其实你做了一个很大胆的尝试。我想这也是你的导师柯马丁先生说的“这是一部勇气和雄心的著作”有关系。虽然只是一本小书,但你试图架构起了一个你自己的,呃,或者说是文化流散地的乌托邦,而且采用的是一种大家都能够认知和能够接受的方式。我觉得非常的了不起。 杨:谢谢,谢谢。大家要知道,我跟陈俊是多年的好朋友,我们认识的时候,你十五我十六岁对吧,已经很多年了。你能够这样评价我,我也非常的荣幸。 陈:我现在跟十五(岁)也没什么区别,也没什么长进。杨:嗯,我也没什么长进。 陈:其实引用很多的学术著作、引用很多的观点,把书写的非常的难懂艰深,其实我们做学问都知道,它是一个很容易做到的事情。用很多的学术术语来堆积,引用很多的学术文献。而把这些所有你看过的(刚才我在前面介绍你们进来时,我也说了)中国的文献、还有西方的文献、日本的文献之间游刃有余的引用,但是你的书上却很少会出现各种各样引文、引述,整个书的行文是很干净的。 所以怎么把这些文献化成自己的东西,然后用一种“大家小书”的方式来写,颇有一些民国的趣味,和民国文人的风采遗留了下来。我是非常喜欢这部作品的。 杨老师现在还在研究苏轼吗?现在应该不算“文化的流散地”了吧?已经在国外生活那么多年。 杨:应该也还是属于“流散地”。我跟中国文化的关系始终是母亲跟她的Diaspora流散在外的子女的关系。对我来说,可能很多的研究课题都是在重新思索我作为一个现代中国人的身份的起源,这样一个的问题。所以在美国的时候写苏轼。现在在德国,可能也因为受到德国历史的启发,我会经常思考,我们今天是怎样发生的?我们的中国古典传统,在现代还有什么样的意义?所以我这几年在做的研究是二十世纪的古典诗歌,就是讨论古典诗歌跟新文化,然后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之间的关系。
陈:今天杨老师也讲了非常精彩和丰富的内容。如果大家对杨老师今天讲的内容感兴趣,也想细细地去品味一下苏轼这些精妙的文本之间的内涵,可以点击下方的图片来购买这本书,也可以通过公众号菜单栏加入我们的雅昌艺术读书会书友群,我们会每月有一次,跟大家以书为友来分享关于艺术和图书的一些事情。今天谢谢杨老师。
杨:谢谢陈俊,谢谢雅昌给我这次机会和大家见面。当然也要谢谢三联为我出版这本书的中文版,可以有机会跟各位读者见面。
好的。杨老师再见!
转载自公众号 Uar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