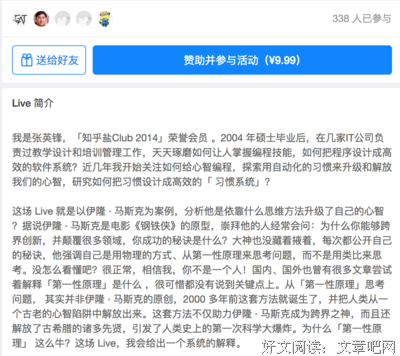
《成神》是一本由〔美〕普鸣(Michael Puett)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51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成神》精选点评:
●感觉前半部分在读“吉德炜上古史研究”的导读,后部分在读中国哲学。全然在纠结中国文化思维模式。最能对话的其实是劳悦强的博士论文,不过普鸣没提。
●普鸣把自己的工作放置在韦伯到吉德炜的延长线上,所以我更愿意将该书视作对中西比较的边界以及可能性的思考。从梳理海外汉学围绕“超越问题的讨论来看,它确实做了很好的反思,对“比较的陷阱”以及“西方文化中心主义”都有十分自觉的意识。但就对具体的文本分析来说,又是比较平庸的——这也展现了海外汉学长于范畴建构短于文献分析的一贯特征。对“天人之间连续性”的质疑在我看来并没有太多理论的必要,因为内向超越本身已经预设了“旧瓶装新酒”的思维,普鸣的新说并没有给出更好的解答。此外,对卜辞的运用过于简单,对张光直的批评也没有系统展开,对一些关键性的人类学/社会学概念也缺乏必要的解释。
●第一時間購得此書閱之,纔發覺三代哲學思想遠“玄”於魏晉玄學……
●和以往的西方学者们常常从关联性宇宙思维、萨满通灵理论来解释早期中国的思想特质相比,作者另辟新径,认为早期中国的宇宙论与王权更强调“自我神化”这一拟神性的思维途径去呈现。视角新颖、论述得体。不过,作者对神、仙、灵等重要概念的文本理解似乎还有待深入挖掘与考辩。
●理论分析与文献解读相结合,构成了一个逻辑清晰的叙述框架,非常难得
《成神》读后感(一):读了一半还没完
外国研究中国古典学和历史的著作,总能让国人看到那些被忽视已久、简单的认为是不言自明的东西。似乎“天人合一”的这种和谐关系,我们都将其视为是从中国文化诞生初期便天然存在的,存在一种天人之间连续性得预设。古人崇敬天,服从天,侍奉天,将天视为万物存在的根源和一切人类活动准则与道德的依据所在。但通过普鸣的研究,古人在如何看待“天”与人的关系上,出现过如此多种不同的立场。并且通过确立人与天交流方式的合法性和对技术的垄断,进而将俗世权力加以巩固,这也成为了反对派诞生的根本原因:看似是在质疑你的祭祀方式,实则是否定你祭祀权力和地位的合法性。
庄子和孟子的一章,阅读收获不少,帮我将一直以来模糊、不成体系的认识梳理个明白,摆脱了从文字反求先贤思想而难以理解的困境。孟子代表了自然道德性的一面,它们来自上天,人必须无条件接受它们,或者说除了尽可能去在个人身上实现它们之外,人没有什么其他的事可做。归根结底,孟子还是想为俗世王权的统治寻求一个坚实不可动摇的基础;而庄子则代表了无关道德的一面,它们全然出自人类,不应该用道德来规范和批评上天。人应该以合乎天然存在于世间的、代表着大道的“文理”的方式去修身,摆脱对自然秩序的被动接受状态而是自发的去接受,这样便能获得真正的“天人和谐”。庄子不如他前人的那种所设想的那样,希望通过对天地大道的理解与掌握,进而变为神,或者成为近似神的存在。他所希望的是人能摆脱对人为之事的依赖,不再按照人为的标准来纠正事物。而所谓神人,也不是成了神的人,他只是充分修养了自己的神,不系于物,自由徜徉,能够使得万物充分实现自然禀赋的人。
庄孟二者实际上都拥有了一种“超越”的概念,这也使得他们抛弃了预设一个和谐宇宙的认知方法。
《成神》读后感(二):从人类学做跳板,能完全跳出去就完美了!
普鸣的这本书非常棒,作者把一个历史现象问题还原成了历史“过程”问题。
中西方的对比建立在一种对现象差异的认知上,强调中国的“自然一元论”在作者看来是把一个结果(目标)说成了原因(预设)。古典时期的希腊和中国其实面临的一样的关于人神关系的问题,并且都面临着一样的阻力:隔绝。
希腊神话强调人与神的区别,《国语.楚语》里也有著名的“绝地天通”。人神之间的隔离将外在的不确定性与内在的不完美性进行了“对照”。神因此是“强大却难以揣度的”,与文明兴起后对“家国”概念的确定性需求有矛盾,所以在处理方法上,不管东西都有“分离”的趋势。
巫者是在这种分离中进行“调和”的专家阶层。他们想尽办法的要“贿赂”、“诱惑”、“说服”乃至“欺骗”神灵,目的就是让外在的不确定却强大的未知,成为社会化人类组织可以“沟通”(驾驭)的力量。普鸣很聪明的在这里用了萨林斯等人类学家的视野,将狩猎采集文化中人类与神沟通的田野调查的结论,用到了思想史的研究中,把文字脱离语境的问题给补上了。所以,商周时期,通过祖先来与“帝—天—神”这类完全不在祖先祭祀之内,却很可能是神性(力)真正来源的神灵“讨价还价”的历史情境被“模拟”了出来。
因为有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支撑”,所以当普鸣开始着手处理史料的时候,可信度与逻辑路径都变得清晰了很多。
以这样一个理解为背景,“大戏”即开场了。春秋战国的一系列过去被学者认为是“人文化”证据的史料,却在“我—文化”渴望获得神力的趋势中,最终在“秦皇汉武”那里汇聚成了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拟神”的神权帝国现象。管子、老子、庄子、孟子、孔子……作者将这些人的见解一一展开,只想说明一件事:为了打破祭祀阶层对“天——力量”的垄断,士是如何将外在的、不可揣度的神灵,重新内化成了遵循某种规律就可以顺从(庄子)或者应和(孟子)的神性。
外在的人格神在这种思潮中被内化成了“圣人”、“真人”、“神人”。于是一个连续的“自然一元论”的宇宙观据此形成了。所以,普鸣一再强调:中国神与人的“天人合一”的关系,不是一种悠久的“历史渊源”,而是从公元前四世纪开始的一场“神学大改造”。
书的立意非常好,切入点也很棒。东西文化的对比在方法上从简单的围绕史料的历史现象对照,加入了人类学的洞见,又能如此严谨的运用,难能可贵。但我觉得可惜的是,如果放大一些,将“成神”的历史看作一部人类认知史,我们是否还应该引入更多的、其他学科的见解与方法呢?
其实,这本书在处理一些歧义见解的时候,令人遗憾的又走回了简单的单一学科的评判标准里去了。
比如对伊利亚德和张光直的质疑,在我看来就有些“歪”了。
说商文化与萨满教有关联,如果仅仅是从传播学派的观点,声称是西伯利亚萨满文化的“流觞”,确实乏善可陈。生硬的将这种地域文化塞入古希腊的历史谱系中,也缺乏证据。但如果我们已经将人类学对早期文化的研究成果引入历史考据,为什么不能仔细的思考,萨满教所体现的“通灵”、“入迷”、对感觉体验的极端依赖,是否在人类认知演化中,有其历史性的存在位置?
伊利亚德对萨满的研究,在我看来其重大价值,不是体现在“萨满作为一个文化现象在历史中的位置”,而是萨满所蕴含的“认知阶段”是否在人类的历史演进中,占据了不可跨越的位置?这个时候,就像人类学可以用来扩充历史研究的语境,认知科学(具身认知和基于环境耦合的自创生理论)的研究结果,也可以成为考证萨满文化历史位置的,极为强力的工具。
从这样一个考证路径上来看,就我现在对认知科学的了解,强调萨满文化所代表的的主客过渡式的、带有连续性的二元自我——世界认知的模型,在人类演进中与早期城邦文化有历史延续性,是一个解释性很强的见解。
神话学上大量的“故事”,从“认知在体验阶段的历史记录”这个角度予以研究,就会发现它极为可信的历史价值。伊利亚德的世俗与神圣的理论,有价值的就在这里。实际上如果将伊利亚的理论和普鸣的见解进行结合,强调萨满体验与拟神需求在认知史上的连贯性,在我看来,我们会得到更多有益的启迪。
很可惜的是,学术圈有自己的“规矩”,其实如果我们在考证思想史的时候,多注意一下书写者的“语境”,就能很容易的发现这些“尴尬”。张光直是一流的学者,他自然懂得学术的规矩,如果想要强调“萨满文化”在早期中国文化历史中的价值,按照史学内部的逻辑,它们必须有符合史学语境的关联。也就是说张光直必须找到历史学术形式里的“硬连接”,才能把它对萨满文化在学术认可的前提下,融入历史的感悟。
这其实有些让人觉得非常遗憾。
依靠单一学术体系的结构,真的很难将别地学科——尤其是跨度比较大的学科,比如认知科学——引入如此古典的人文研究之中。
所以也难为了普鸣。只不过我还是忍不住感慨:如果我们能引入“形式逻辑——派生语义——认知语用”这三个领域的知识,其实我们就可以轻易的找到为什么“士”花费如此大的精力去拒绝“绝地天通”。
仅仅从社会组织学说来看待这个问题,太窄了……。
说到这里让我想起前几天读的马苏米的《虚拟的寓言》,某种程度上来说,先不说她的见解,但就是将拓扑学引入感觉的运动理论,将“定位”(空间认知)彻底虚拟化的“技术手段”,确实有用“思想镁光灯亮瞎了我的脑灰质”的感觉。
在这方面来说,古典研究领域的条条框框可能还是太多了吧?
不管怎么样,这是一本开卷有益的书。只是作者太针对一些观点了,反而浪费了诠释自己见解的页面。如果能集中精力继续挖掘,从人类学的跳板上,引入更多的跨学科成果,那就不是好,而是简直可以说完美了吧?
《成神》读后感(三):“天人合一”还是“神人有别”?
“天人合一”还是“神人有别”?
——读普鸣《成神》的一些想法
注:括号内为中译本页码。
《成神:早期中国的宇宙论、祭祀与自我神化》一书,翻译自普鸣2002年出版的英文作品,原书名为 To become a god: Cosmology, Sacrifice and Self-Divinization in Early China.。据三联出版编辑的介绍,此书“用融合哲学、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全新文化比较模式,揭示早期中国‘天人合一’思想的成型历程。”
英文版的书名看过此书的人就会知道,这个介绍并不完全准确。从表述上来讲,“哲学、历史学和人类学”前都应添加“西方”二字;从内容上讲,普鸣要揭示的是“天人本不合一”如何走向“天人合一”的思想历程,而且前者的那种“不合一”属于相当紧张、对抗的状态。简单而言,普鸣反对将“天人合一”作为早期中国甚至是整个中国的基本思维方式和命题预设。
不过,还需要指出的是,中译本的封面和版权页都将god大写,在我的设想中,它极有可能会引起中国读者的严重误会,因为普鸣讨论的并不是早期的中国人如何成为基督教意义上的“上帝”。god一词大写还是小写,在西方语境中本有相当严格的语形规则。
当然,这并不仅仅是英文的书写规范问题,更重要的在于:当把become a god理解为“成神”意味着什么?中译本亦将become a spirit译为“成神”,为什么“神”既可以是god又可以是spirit?而且中译本中还出现有“拟神的(theomorphic)”和“自我神化(self-divinization)”等表达,虽然它们都在翻译后与中文“神”字有关,但是theology和divine不首先和基督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吗?这些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翻译问题。我猜测,《成神》这个书名也很切中普鸣心怀。然而——就在我们自己的中国语境中(尤其是早期中国),“神”究竟该如何理解?
要理解普鸣此书,最关键的就在于,普鸣如何在早期中国构建了一种关于“神”的叙述。我在之前已经略谈过《作与不作》的理解问题,见《读普鸣<作与不作>的一点思考》。这里的理解不仅包括普鸣本人对中国思想文本的理解,还包括我们在译介西学(也可以说是“汉学”)时的“再理解”。那些西方学者是怎样理解中国的,我们又该如何理解他们视域中的“中国”。我的基本看法是,普鸣从西方文化的基本误解中成功地塑造了一种新的“误解”。而普鸣自己也说,《成神》与《作与不作》“这两部书实际上是彼此相关的”(《致谢》),因此在我看来,《成神》所可能潜藏的弊病与不足与《作与不作》如出一辙,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王正原博士生已经对全书做了极为精彩的概述和评论,见《天人与“成神”》,《读书》2020年第5期。我十分同意文中所指出的普鸣解读文本方式的种种“遗憾”,该文谦逊而委婉,但我希望再多作一点更“露骨”的补充。
从导论一开始,普鸣别有用心,用宇宙的起源作引子来质疑一种“自生自发的宇宙论”。《淮南子》的“有二神混生,经天营地”成为普鸣的重要根据,因为此句既可以确定宇宙之前的“神”的存在,还暗示了“神”对于宇宙的决定性作用即“经营”,而“经营”一词又非常明显代表了一种关乎人的筹划性活动。这样的开头,值得我们联想《圣经》中上帝在创世活动中的安排。普鸣接下来进一步预告,《淮南子》还“讨论了那使修道者得以成神的修身步骤”,“神首先经营宇宙,然后人也能成为神,并掌控宇宙”,“这些主张认为人有自我神化并进而获得控制自然现象的力量”。(第3页)
仅仅是这几句话,已经足够看到普鸣对“神”的基本理解。无论“神”是人格化的神灵还是理性化后的某种自然力量,在普鸣看来,“神”是宇宙创生和运行的根据,“神力”就是掌控宇宙的力量,所谓的“成神”就是人通过某些特殊手段攫取神力、代替神的地位以影响并控制宇宙。书名中的几个关键词也就能顺而理解:“宇宙论”是为了彰显“神”本身的存在和作用,“祭祀”是表现人与“神”沟通甚至“交易”的尝试,“自我神化”从根本上是“成神”的基本模式。因此,三个关键词其实恰好呈现了人神关系中的“拔河”,而拔河的结果可理解为“神”的下落和人的升格。
普鸣在导论中勾勒了西方世界在20世纪中国思想研究中的两种极端立场以及各自的人物谱系。(第14页起)普鸣分别称之为“进化论模式”和“文化本质主义”,前者的主要代表有冯友兰及雅思贝尔斯、史华兹和罗哲海等,而后者的代表有葛兰言及李约瑟、牟复礼、张光直、葛瑞汉、郝大维和安乐哲等。双方代表中也有不小差异,但总的说来,“进化论模式”更突出(早期)中国与西方世界全局的同步性,而“文化本质主义”更强调(早期)中国在西方世界全局中的特殊性。普鸣认为,这两种框架都存在各自的问题而建议摒弃,并“尝试提供一种关于从青铜时代到汉代初年的人、神与宇宙之间关系的完全历史的研究方式(第35页)。
第一章对普鸣来说非常关键,因为这里所建立的基本结论引导了之后的系列想法。普鸣首先质疑“商代的占卜和祭祀活动显示了一个人神和谐的预设”(第56页),并根据大量商代甲骨卜辞提出了一个商代祭祀的权能结构,这个结构本身就是对人神和谐的最大冲击。这里的“权能”指的是作为神灵介入人间事务的能力。简单来说,普鸣认为商代的神灵喜怒无常,无端介入人间事务,祭祀和占卜作为对神的回应,既是一种是对神意的试探,又是对神力的反作用(58、63-64)。普鸣极度依赖吉德炜“制造祖先”观念,他认为商代正是通过祭祀祖先,即把祖先当做是人神沟通的中介,按照一条神灵的权能链条来处理人神之间的实际冲突。这个想法有三个要点:
①祖先之间有权能的等级结构。
②祖先的权能之间存在一种效应递减原则。“越老的祖先权能越大。”(第66页)
③祭祀是为了寻求祖先的权能发挥以至于最高神(“帝”)的权能发挥。
权能大小实际上决定了神灵渗透人间在世生活的深度和神灵处理人间事务的类型。中国俗语常说,请神容易送神难;普鸣却还想说,请小神容易请大神难,不过,祭祀正好可以请小神(如祖先)去请大神(如自然神灵以至于“帝”)(第72页)。既然小神管小事儿,大神管大事儿,一旦真的请动了大神,那么大神便会替代小神更有力地改变人事。祭祀就像打通关游戏一样,不断挑战更高级别的boss,只不过对于boss 的态度不是消灭,而是请求他们的帮助。
必须指出的是,普鸣的这个理解,用他自己的话说,既是一种“最合理的假设”(第71页),也是“合理得出”的结论(第73页)。在普鸣看来,“商代祖先崇拜代表了将自然神和死者之灵融合到一个单一、统一体系中的尝试”(第76页),这种尝试的根本做法就是“将死者变成合适的祖先,让祖先出面引导自然神灵和帝”(第77、305页)。在一个神灵弥漫的商代,商人出于自己生存和生活的需要,希求神灵改善自己的生存处境,希求的途径正是祭祀。但普鸣并不关注占卜和祭祀的社会文化史意义,他只需要借助卜辞中所推演出的商代祭祀结构,来说明人神关系在商代的不和谐。普鸣隐晦地表达,尽管“神灵并不倾向于为生者的利益服务,而且卜辞记录表明商人认为祭祀不起作用”(第77页),但是祖先被“制造”出来的目的就是希望他们能为人所服务。看起来好像是人祭祀神灵而人卑神尊,但人神关系又反过来表现为被服务者与服务者的关系。商人对于“祖先”的理解是否仅在于其工具性,这是值得追问的问题,不过,译者和校者指出,普鸣对卜辞的理解已经有足够多的错误。
那么,商、周之间又是否存在人神关系的断裂或根本性转变?普鸣的回答仍然是否定的。(第82页)普鸣曾在校注指出:“天是周的至上之神,就像帝是商的至上之神一样。”(第78页)在普鸣看来,商周之别只是表面的不一致,周人类似于商人,仍然处于一种“人-祖先-天”的三方博弈中。假若说作为最高神的帝或者天,其地位不变,商周两代的不同就落在了人和祖先的关系上,或者说后代与祖先的关系上(第85页)。
普鸣的意思在对《大雅·文王》的解读中表现得最直接。文王作为周人(当然其实只是周天子)的祖先,常在天帝左右侍奉,“维系帝对周的支持”(第91页)。这种维系既体现了周人祖先的特殊权能,同时也意味着周人祖先对于后代的义务,这是普鸣称他们为“称职的祖先”的最主要原因。天命这个概念本来意味着天对于周人的存续享有最高决定权,但是由于文王与天的这种“亲近”,反而使得文王间接掌控着天命。也正是由于这种间接性,此时摆在周人面前的,不是像商人情况那样首先面对自然神与帝的“无常”,而是作为祖先的文王以及一连串的先王谱系。周人首先要处理的就是自己和祖先的关系,实际上,赢得祖先的支持就是赢得天的支持,也就能享有天命。这进一步意味着祖先的地位从商代到周代的提升,迫使周人后代密切关注祖先的动态而表现出对祖先无比追随的样态,祖先对后代的意义也就从“可以服务”变成了“应当服从”。因此,就人神关系而言,商、周只具有程度上的差别,而不具有本质上的断裂。“西周对于和谐的预设并没有比商代更多。”(第94页)
《生民》是上述理论的另一个例证。普鸣还专门拿了《生民》一诗与和赫西俄德的《神谱》比较,二者当然有诸多差异(第105页),但普鸣却从中发现了共通之处,二者在人神关系上所体现的一致性不妨用两个词概括:人神有别,各有其分。最重要的是,恰恰是祭祀承担了沟通人、神的根本的而且是唯一的功能,祭祀一方面意味着人、神本有的分离,另一方面又代表了人、神关系之间的妥协。普鸣之所以觉得“两者对转化性祭祀活动的描述”是“令人惊讶的”(第106页),这是因为无论是后稷还是普罗米修斯都作为人、神之间的中间角色,将本来只应属于“神”的力量带向人间。普鸣认为祭祀活动归纳为转化而不是献礼,这是因为祭祀的转化性就在于“神力”的循环,而献礼则不存在对神的回馈。虽然普鸣明确强调了祭祀行为的代价和收获,但这种转化性祭祀是否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人神“交易”,普鸣并没有直说。
稍作小结,普鸣把以商周为代表的青铜时代认定是人神不合一的,而他的重要证据就来自于商周祭祀活动的创造性转化,这种转化即是即是一种“秩序化”的努力(第109页)。商周人都努力尝试把人、祖先、神以及天分配到合适的位置,而形成相对稳定而动态的博弈结构。尽管普鸣也没有明说周人的祭祀理念是否比商人更具效力,但商周的祭祀理念都体现了“人神之间根本断裂与和谐缺失”(第110页),这个结论是普鸣始终要达成并奠定的。现在的问题是,既然商周已经开启了人向神的靠拢或“僭越”,那么人对“神”的需求还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吗?这就是第二章以后的问题。
公元前4世纪大致相当于中国的战国前期,普鸣认为此时发展了一种不同于往前的新宇宙论,人神关系也因此得到了大幅调整。普鸣先是花了相当篇幅来介绍早期中国的萨满观点和古希腊的神人问题,进而提出用萨满观点来观察早期中国是不合的,反倒是古希腊(尤其是恩培多克勒)和早期中国有相当可比性。如普鸣所说:“在中国和希腊,一元论观念都是与自我神化主张——认为人拥有变得如神的能力——同时出现的,而这种学说的出现是为了反对当时的祭仪专家。”(第133页)。这里的一元论指的是宇宙自身就有其统一性,而神也在这统一性之中。也就是说,战国前期才和之前的商周宇宙论具有根本不同,也就打破了原来“人-祖先-神”结构。普鸣分别解读了《论语》、《墨子》部分、《国语·楚语下》以及《管子·内业下》,普鸣自己的简述可见第153、163-165页,我自己概括为四个要点:
①孔子对天无比尊崇而无意以祭祀影响神灵。(第141页)
②墨子根据宇宙的伦理化进而主张祭祀“有利可图”。(第144页)
③《楚语下》主张人神之间的“仪式性分离”或说“象征性分别”(第153页)
④《内业》在“气”的世界中主张人通过自身修炼就可如神灵一般。(第160页)
这四个要点当然各自不同,但从不同分组来看:前二者都暗含了天或者神的正当性,后二者又都凸显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合理性;前三者都对祭祀行为有所保留,最后一者却完全可以抛弃祭祀而“独与神往来”。这四个要点层层递进,最终走向了人神合一。和之前商周的人神关系相比,这些学说都指出“人能够以比当时的祭仪活动更加直接的方式来获取神力”(第168页)。其实,到此为止,普鸣关于人神关系的叙述基本上已告完结。之后的篇幅很大程度上都没有逃脱出《内业》的基本思路,要么偏离、要么回归,只不过普鸣还要继续讲述这些偏离或回归的历史效应。
第三章论庄子和孟子,其实二者在天人关系上的差异很简单,普鸣绕了一大堆无非想说:庄子主张以天统人,孟子承认人难统天。二者都承认人的有限性,只不过庄子认为这种有限性可以克服,而孟子延续孔子的天命观而不得不接受而已。
第四章重新勾勒人神关系在战国晚期调整后的宇宙论框架。普鸣花了大量篇幅提供了他的讨论背景,一方面是为不熟悉相关领域的读者方便,但也是为了他自己的方便——便于。普鸣明确说自己否认“中国是一元生成论”(第216页),而认为“关联性宇宙论并不是战国时代的一种预设,而是一种批判性的修辞”(第280页),并依次讨论了《太一生水》、《老子》《黄帝四经》中的《十六经》、《管子·心术》、《吕氏春秋》、《荀子》和《易》的《系辞传》。其中,《太一生水》《老子》《十六经》可看成一组,这三个文本都表明了“存在物都是从一个单一祖先那里产生的”,尽管对这么一个“祖先”表述各不同,“太一”或“道”或者“一”,但是这个宇宙论已经扭转了之前的祭祀模型(第237页)。这个想法的要害在于,既然所有的存在物都作为这个最高存在者的后代,那么人也已经以“血统”的方式和自然、天、神直接联系在了一起。“血统”不断,这种类型的“天人合一”也就不会终结。《吕氏春秋》更是这一联系的“复杂改写”(第253),《管子·心术》也主张“对‘一’的把握使得圣人能够统治万物”(第239页)。
《荀子》最与众不同,因为他“支持祭祀与占卜,并且反对那种认为人可以控制或理解自然进程的主张”(第262页)。普鸣构建了荀子和《系辞传》在“文”与“神”上的对立,他认为,荀子所理解的“神”指的是“将万物带入其合宜秩序的东西”(第260页),而“文”的重要内容就是祭祀和占卜,所以,虽然荀子延续孔子的主张保留了祭祀和占卜,但从普鸣的表述来看,荀子或只是象征性地在延续传统意义上在意它们,更关键的是荀子仍然“完全接受神化的学说,他也认为人在为宇宙赋予秩序方面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第262页)。普鸣反复强调荀子的神化理论和之前不同,因为荀子的成神或者神化所指向的不过是人为宇宙和自身带来秩序的建立,与之前的神化理论相比是一个“剧烈的改动”。《系辞传》的意味在于,《易》这个文本蕴含了宇宙运行的无穷变化,所以《易》本身就是“神”的代表。我个人认为,普鸣关于《荀子》和《系辞传》的说法是全书中最匪夷所思的部分,他对这两个文本的解读和思想重构令人百思不解。
第五章开始,全书思路走向另一个方向即“登天”。之所以要讨论登天,因为登天是成神或者自我神化的一种极端模式,与“将神化视为赋予力量的手段”的另一种模式截然不同(第391页)。普鸣先在第五章分别解读了马王堆帛书中的《十问》、《庄子》外篇中的《在宥》和《楚辞·远游》。这三个文本的思想尤其与青铜时代的人神关系相比,“每一个文本都在教导凡人如何才能摒弃形体,融于天地,在宇宙中遨游并实现永生。”(第308页)。换句话说,之前的“成神”还停留在依靠“神力”来改变人间事务,到了这里,人间事务反而是一种对“成神”的拖累而应该断离。
第六、七、八章都是对“登天”主张的历史实现。从第六章开始,普鸣勾勒了皇帝(如秦皇汉武)、有识之臣(如陆贾、董仲舒、司马迁)和方士(包括公孙卿)三方在“登天”路上的博弈与皇帝祭祀体系的转变。对熟悉秦汉史的读者而言,普鸣本可以在“礼崩乐坏”和“重整礼乐”的观点下理解皇帝祭祀的意义,但普鸣主旨却是从秦汉的文本中透视出人神关系和宇宙论的变迁。不管怎么复杂,普鸣最终是要告诉我们:“在早期中国并不能找到人神之间和谐连续或人神之间没有张力的预设。”(第436页)
以上我对《成神》第一、二章做了尽可能的概述,因为这两章确实是该书的重中之重。值得提示的是,《作与不作》的译者曾“呼吁”我们要“重新思考‘天人合一’问题的复杂性”,然而,普鸣的这一本《成神》其实只是间接提出了他对“天人合一”的看法。因为,通观全书,即便是到全书末尾的点题,普鸣始终关心的是“神人之间的连续性问题”(第432页)。实际上我们应当有意识的提醒自己看待《成神》的方式,抛开出版编辑的介绍或者部分学者的误导,讨论“天人合一”不完全等同于讨论“神人合一”,而《成神》的核心论域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从普鸣的回答来看:在“神人是否合一”这个问题下,“天”至少是被附带讨论的。不管人通过何种方式与神沟通甚至成为“神”,“天”始终是属于“神”的领域。青铜时代的祭祀结构中,祖先需要上升到“天”去侍奉最高存在者“帝”;战国以来,通过修炼身心达到的一种“神”的境界,至少被设想为与天的秩序齐平;更不用说极端化后的“登天”,本身就是“成神”的重要途径而让秦皇汉武着魔。如果我曾经的理解无误,《作与不作》中所谈论的“天人合一”实际上讨论的是自然(天然)与文化(人为)的关系问题,但《成神》所提出的“神人合一”,需要考虑的是人与神明或超自然力量之间是否和谐以及如何处理两方冲突的问题。即便两者确实相当类似而有共通之处,但也不是说可以混为一谈,讨论其中一个“合一”不一定要捎带另一个“合一”。这也就是说,两个“合一”要求不同方向的回答。
然而,中国语境中“神”该如何理解,比“神人合一”该如何理解更重要也更根本。从普鸣的叙述来看,“神”主要被理解为一种人格化的神明、神灵(如第一章),又被理解为一种修炼身心后所获得的一种力量(如第二章),还在讨论《系辞传》时被理解为宇宙运转过程中的一种变化(第264页)。其中,第一种意义上的“神”与第二种意义上的神“紧密相关”,神明的力量就是操控宇宙、把握天地秩序的力量。我国的哲学史家张岱年先生除了有与本次话题相关的《天人五论》,其实也曾在《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中极为简明扼要地梳理了“神”的三种意义:
①“‘神’的原义指原始宗教的所崇拜的神灵。”
②“战国时期的著作中开始以‘神’与‘形’对举,所谓神指人的精神作用。”
③“在先秦哲学中,‘神’除了指神灵和精神作用之外,还有另一个意义,指微妙的变化。这一意义的神往往与化相连并提,合成神化。”
其实普鸣的理解和张先生的梳理是大致合得上的,最有解释空间的是“神”的第二个意义。普鸣也说过:“神这个语词并没有意味着‘人之精神性’又意味着‘神性’。‘神’这个语词在青铜时代是专门用来指涉神灵的。直到战国时期,这一语词才被用来指称人体内的实体。”(第32页)
我的看法是:就个人身心上来说的“神”,究竟是理解为一种类似于控制自然、掌握吉凶的力量,还是仅仅当做刻画一种特殊的心智状态的修辞,恐取决于如何看待和解读早期中国关于修炼身心的文本。像庄子中的“神人”可以呼风唤雨、腾云驾雾、无坚不摧,对普鸣来说就是获取神力的最佳例证,但是对中国读者和研究者而言则不会像普鸣那样如此当真。普鸣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祭祀过程中的“神”与修炼身心后所达成的“神”是完全同一的吗?普鸣认为是的,因为他并不考虑文本的修辞。
总的说来,普鸣对文本的解读是大胆而粗疏的。普鸣对文本的理解简单而粗暴:文本即史料,亦即反映相应时代的信息载体而已。普鸣对文本的理解中,断代是一个根本基础。某个文本在什么时期成型,它就代表了什么时期的思想。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比如《论语》,普鸣认为《论语》要放到战国初期来讨论而不是春秋晚期,因为《论语》是孔门弟子的集结,不能代表春秋晚期的思想。甚至在《作与不作》中明确说,《论语》不值得全部相信。普鸣的心态基本上是现代史学的,但是他对史料的解读和处理是极其肤浅的。 诚如之前提到,普鸣综合运用了历史学的方法,普鸣对史料的理解和运用都须大打问号。
和《作与不作》一样,普鸣保持了避免对文本首先进行学派上的分类(第273页),但是这种从无前见出发的解读多数都是语词与概念上的联想。尽管普鸣一直说他要把思想观念放到历史情境中去,但是普鸣对中国历史情境的了解和把握都令人汗颜,尤其比如关于“南面”的理解(第251、299页)。我们可以发现,普鸣对于二手文献的梳理更上手,他非常善于抓住二手文献之间的观点的对立与缝隙,来突破固有结论,然后用他自己所理解的文本加以证明。普鸣对现代学者观点的熟悉与引用,远远超过了对文本的忠实解读。校者和译者都指出了普鸣关于卜辞理解的基本错误。当然,出土文献本来就会面临解读的多种可能,但普鸣的有些错误是相当幼稚的、有失水准的、不可容忍的。
我不知道是否人类学领域能接受他的整套想法,但对中国思想界而言,普鸣的写作方式与中国固有的研究范式格格不入。如何合理获取关于“中国”的文本信息,以及如何组装“中国”,都会导致“中国”的图景大不一样。直面普鸣提出的问题并作已有研究的反思检讨,而不是直接接受普鸣所回答的结论,这才是中国学者面对普鸣著作的应有态度。
2020年7月2日星期四
附:校者指出普鸣理解问题的页码
60/68/135/150/174/227/230/236/243/249/251/252/254/257/264/292/303/333/348/352/359/367/371/379/381/382/400/413/425
《成神》读后感(四):【摘录与整理】早期中国思想研究范式
【案】对普鸣《成神》中“导论”的“二手研究”部分进行整理和摘录,并撰写一个总结。
韦伯
韦伯对世界历史中各大文明的比较分析,关注的是对理性主义的研究:为什么理性主义活动的特定形式在西方发展了起来?为什么这样的活动在其他地区的发展程度有限?为处理这一课题,韦伯对经济、社会、政治、法律和宗教等领域进行了类型学划分,他将这些领域中的每一项看作是相对独立的,并对他们单独地加以研究。对韦伯来说,文明就是这些领域相互作用的结果。韦伯的比较方法是对文明中的上述各领域逐一进行比较,由此确定理性在每个文明所达到的水平,认清是什么阻碍了理性在非西方文明的发展。
韦伯对儒教与清教所作的理性化程度对比根据以下两个标准:
1、这种宗教对巫术的拒斥程度;
2、这种宗教将上帝与世界之间关系和它自身与世界的伦理关系系统性统一起来的程度。
清教达到了理性化的很高水准,其思维模式已将巫术完全彻底清扫干净,导致了对世界的彻底除魅。同时,清教导致了一种对世界的巨大、激烈的张力。儒教则在这两方面多远为逊色。甚至可以说,清教将世界理性化的要求与儒教适应世界的主张相反。
儒教对巫术的、泛灵论的观念都采取了容忍态度,并且将巫术世界观转化为一元宇宙论:“在以五为神圣数字的宇宙思想中,五星、五行、五脏等,联结起大宇宙与小宇宙的对应关系。中国这种普遍统一的哲学和宇宙生成论,将世界转化为一个巫术之园。”这种宇宙论思维仅仅在把巫术赋予条理和系统的意义上是理性化的,因此它从未超越巫术认识世界的方式。
另外,儒教的伦理系统要去适应这个世界及其秩序与习俗,将与此世界的紧张状态降至绝对的最低点。人与神的领域之间根本不存在紧张性。在自然与神之间、伦理要求与人类性恶之间、原罪意识与救赎需求之间、此世行为与彼世报偿之间、宗教义务与社会政治之间缺乏必要的张力。因此,儒教把宇宙和社会看成是完全联通的,道德律令仅仅在于使人顺应宇宙与社会环境。
韦伯比较研究里面的两个关注点:
1、根据理性演进发展来比较中国和西方;
2、通过比较各自传说中的独特宇宙论来比较中国和西方。
雅斯贝尔斯
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间,希腊、印度和中国都经历了一场“轴心时代”的哲学革命。这个时代是由“超越”观念的出现而得到界定的。这进而包含了理性对神话的反抗和一种针对“不真实的诸神形象”的伦理反叛。
雅斯贝尔斯更强调意识的普遍演进而不是不同文化的分疏和差异。因此尽管不同文明有不少具体的差别,但雅斯贝尔斯认为,中国和印度经历了与希腊相同的超越性突破。这一超越事实上创造了一种普遍的意识形式。
史华兹
史华兹采纳了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论,淡化了其中的进化论色彩。他接纳了“超越”概念,但重新定义了发生在不同文明中特定的超越类型。就中国而言,其超越类型是“此世的”类别,即将超越者与一种内在的宇宙和社会的秩序概念关联起来。因此,在中国,超越恰恰是发生在其内在主义的宇宙论之内的。
史华兹在整体上采纳了韦伯对中国宇宙论的描述,认为中国文明的特征是被内在主义主导的宇宙论、此世倾向和人神领域间张力缺乏等。(史华兹认为,中国之所以缺少人神两个领域的强烈紧张关系,是因为中国基于祖先崇拜的家族秩序导致了在哲学上的对人神关联的强调。)但是他又认为这种宇宙论应该从“理性”和“超越”的层面予以理解。因此史华兹确立了一种有别于西方的中国式的理性主义观念。(“理性主义”一词指的是秩序观念的首要性而言,是一种囊括一切、涵盖广泛的秩序图景,这种秩序既不否认某种被假定为存在的唯一原则,却也不可以被化约于其中。如同官僚主义的理性化那般,这一秩序将存在的现实加以分类,并将其包括在内。这是一个综合的而非分析的概念,自然之神和祖宗之灵并没有被遭到摈弃。实际上,中国思想从没有试图将对世界的“祛魅”进行到底。)
史华兹在韦伯与雅斯贝尔斯两种观点之间维持了某种微妙的平衡,尽管史华兹采纳了韦伯对中国文明宇宙论的基本论点,但他同时认同雅斯贝尔斯所主张的中国文明确实发生了某种超越的突破。
罗哲海
罗哲海试图提供一个普遍的标准衡量人类文明,这使他与韦伯式的普遍比较框架有了共鸣。但他明确引用雅斯贝尔斯反对韦伯,认为中国早期确实经历过一次超越的突破。与史华兹不同,罗哲海保留了雅斯贝尔斯思想中的进化论维度。他又坚守雅斯贝尔斯的普遍主义立场,反对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
韦伯将对自然的祛魅与对超越之神的信仰联系在一起。罗哲海要做的是解释这种观念如何能在没有彼岸之神信仰的文化中出现。他认为,这在中国发生在西周覆灭的灾难中,这一灾难导致了“天之尊严的丧失”。这次“神力的失败”导致了人类直接关注自身,宗教让位于新的思索。罗哲海据此为“从宗教到哲学”的世界观提供了一个变形:有神论的世界观主导了早期的时代,随着西周覆灭,有神论被摧毁。这导致了对神力的贬斥和对人的关注,以及对自然的祛魅和自然成为了人类征服的世俗对象。因此,与韦伯的观点相反,早期中国确实经历了伦理的理性化过程。
那么罗哲海要如何处理关联性宇宙论的出现?与韦伯一样,罗哲海把关联性宇宙论界定为一种较低形式的理性化。由于他认为关联性宇宙论的思维方式意味着一场通向启蒙的思想突破并未发生,这样,否认关联性宇宙论的重要性就构成了罗哲海为中国传统思维辩护的主题。所以罗哲海明确反对葛兰言那种把关联性思维看作中国主导思维模式的看法。而面对汉代关联式宇宙论的文献,罗哲海只好认为董仲舒抛弃了周代哲学发展起来并由荀子实现的理性的自然观。所以,董仲舒标志着儒家向“迷信”的复归和倒退。儒家的道德与认识水平回落到轴心时代哲学家出现以前的水平。
葛兰言
葛兰言认为中国拥有一种与西方彻底相异的宇宙观。中国思想并非“前逻辑的”或“神秘的”。被韦伯认为制约了理性充分发展的东西,恰恰是被葛兰言当做中国思想真精神一部分加以颂扬的东西。
中国思想缺乏“超越性原则”,不承认超越人类世界之上的真实世界,没有抽象的观念。中国人预设了完全一元论的宇宙观:“人和自然没有形成两个分离的领域”。葛兰言主要基于汉代的文献,这些文献以阴阳、五行和小宇宙、大宇宙的关系为基础,构建出复杂的关联性体系。葛兰言并未将这些宇宙论观念看作汉代特定的观念,而将之视为中国思想的一般预设。
李约瑟
李约瑟延续了葛兰言的论点,认为中国思想的关键词是“秩序”、“模式”、“有机体系”。在这一有机的世界构想中,万物自然地与其他事物相协调,创造出一种“无主宰的有序的意志和谐”。(那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关联物或相似物构成了庞大模式的一部分。万物以特定的方式运行,并不出于先在的行为或他物的刺激,而是因为它们在流转循环着的宇宙中所处的位置,使他们被赋予了内在固有的本性,这使他们必然如此运转。他们对他物的反应并非出于机械或因果关联,而是通过一种神秘的共鸣而相互激荡。)
像韦伯一样,李约瑟认为,中国没有那种西方极为重要的激进二元论(欧洲式思维作为一种“精神分裂或人格分裂”,只能按照德谟克利特式的机械唯物论或柏拉图式的神学唯灵论来思考)。但李约瑟反转了态度,明确站在同情中国这一边。(这一点与葛兰言也如出一辙)
牟复礼
牟复礼也将其理论奠基在类似的早期中国普遍“世界观”。在李约瑟所说的“无主宰的有序和谐”基础上,他认为在其中人和神都被概念化为一个更大的一元论体系的一部分。这在本质上是一种自然主义的观念,“神”与自然中的其他方面具有同质性,都遵循同样的自然进程。
郝大维、安乐哲
郝大维与安乐哲与葛兰言类似,把汉代的关联性思维看作所有早期中国思想的共同特征。他们明确批驳雅斯贝尔斯的观点,也批评史华兹追随雅斯贝尔斯,用“超越性”等概念解释早期中国思想的做法。郝大维、安乐哲没有对早期中国思想缺乏超越性进行批评,相反他们与葛兰言一样,认为这是值得赞赏的。
郝大维和安乐哲提出了“第一问题思维”与“第二问题思维”。第一问题思维基于“类比或关联性思维”,这一模式主导了中国思想。他的特点是:1、承认变化与运动过程相较于静止与永恒具有优先性;2、认为不存在最高主宰规定万物普遍秩序;3、将万物解释为一个相互关联的进程,而非决定性的主宰或律令。第二问题思维作为一种“因果性思维”在西方居于主导地位。其特征是:1、认为宇宙是由某种主宰力量进行安排的结果;2、相信形成“此世”的诸事件皆奠基在那主宰力量中。因此,把神力看作形塑世界的始因性力量的有神论体系是西方的思维方式,这种模式可被理解为“超越的”。
与葛瑞汉类似,郝大维和安乐哲认为上述不同的思维模式在中国和西方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因此他们认为中国思想可以完全为当代西方思想所吸收。他们明显对关联性模式抱有同情,因而也反对葛瑞汉等的那种把不同思维模式类型放置在一条进化论序列之上,并把关联性思维模式看作更原始或更低级思维的做法。雅斯贝尔斯、冯友兰那种启蒙主义式的、把从神话到理性、从宗教到哲学的运的过程看作人类文明进步普遍标准的解释,都被他们视为西方中心主义的谬误。
张光直
张光直认为,中国和西方在宇宙论上的差异源于对待萨满的不同态度。中国与西方的分歧,是由于近东从远古萨满传统中经历了一次突破,而中国(以及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却保留了萨满文化。西方由此发展出一个强调诸神分离之存在的宇宙论,而中国文化则建基于一个相互关联的统一世界的预设之上。中国之所以有别于西方,是因为其对人神领域之连续性的强调。
葛瑞汉
葛瑞汉认为,中西之别在于:西方起主导作用的是“分析性思维”,中国起主导作用的是“关联性思维”。两种思维都是普遍的思维模式。关联性思维是多数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初级认知模式,是作为高级模式的分析性思维之基础。这种差异在今天被理解为原始科学与现代科学之间的一种跨文化差异。
葛瑞汉反对葛兰言等把关联性思维看作中国独一无二思维模式的主张。相反,他认为公元前3世纪到前2世纪中国人建构复杂宇宙论体系的尝试,应该仅仅被理解为普遍理性模式的一种特殊发展。即中国文明这种关联性宇宙论是普遍的关联性思维模式的一个异域案例。
关联性思维与分析性思维在每一哲学传统中各自具有其相对的重要性。中国接纳了关联性思维;西方则最终将分析性思维从关联性思维中分离出来,并日益提升分析性思维的地位。
冯友兰
冯友兰把中国思想置于西方哲学的进化论框架内理解,并借助那些在古希腊研究里面普遍使用的语词来解读早期中国思想史。他以从宗教到哲学、从有神论到理性的转向来描述早期中国哲学。并主张人文主义、理性主义和自然主义是中国哲学的固有成分,他们在中国出现的时间与其记载中的古希腊出现的时间相同。而尽管由此发展出的中国哲学并未在逻辑和认识论上达到古希腊的高度,但它在修身之学等方面却独树一帜。
冯友兰认为,青铜时代原始思维的决定性特征是有神论宇宙观(在同时期的古希腊人也拥有类似的有神论宇宙观)。这一宇宙观在春秋时代被一种人本主义世界观取代,这是朝向理性主义转向的关键一步。
关联性宇宙论的产生是远离有神论的一步,也是迈向自然主义概念和全然理性主义思维方式的一步。(“以阴阳解释宇宙现象,虽仍不免混沌之讥,然比之以天帝鬼神解释者,则较善矣。”)
总结
对早期中国思想的论述,起到奠基性作用的是马克斯·韦伯和雅斯贝尔斯的两个框架。两个框架的共同点是:都以启蒙主义式的进化论作为出发点、都具有比较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并在此基础上以普遍历史的目光对不同人类文明进行广泛的比较。而差别则是,韦伯比较研究有两个前提:1、非常严苛地用现代西方的理性化标准和新教伦理作为比较研究的“理想型”;2、西方这种模式是唯一成功实现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的,而其他模式在开展现代性的任务上已然失败。在这两个前提下,必须通过比较研究找出其他文明未能开出西方式的现代性的原因。所以韦伯一开始就预设了理性化、超越性的新教伦理是西方独有的产物,其他文明则不可能存在。因此他的比较研究是以“西方例外论”为特征的。
与此不同,雅斯贝尔斯虽然也持有类似于韦伯的西方中心论,并且也同样以西方式的超越性观念、从宗教到哲学、巫术到理性的进化论式的观念作为比较研究的标杆。但由于他的问题意识和出发点与韦伯不同,他更倾向于不把西方模式看作是西方独有的,而是把西方模式直接看作是人类的普遍模式。他不是“西方例外论”的支持者,而是以西方模式为模板,看待其他的文明模式。因此他给出的标准没有韦伯那么严苛,他认为轴心时代在不同文明普遍出现了与西方类似的突破,虽然这些突破的具体形式或内容在不同文明体中不尽相同。所以,尽管实际上不同文明模式的差异性可能非常大,但雅斯贝尔斯都希望用西方的架构来理解,把差异性化约掉。不同文明的多样性在此框架性很容易被归纳为“其实与西方那种范式比起来也是大同小异”。
在此基础上,史华兹、罗哲海代表了试图同时接受韦伯和雅斯贝尔斯的折中主义。在两者之中,史华兹更多地偏向于雅斯贝尔斯,因为他虽然采纳了韦伯对中国内在主义宇宙论的描述,但是他试图将这种内在主义的关联性宇宙论也解说为一种特别形式的超越性突破和理性主义。因此他其实不接受韦伯那种主张西方独一无二的“西方例外论”。相比起来,罗哲海更接近韦伯,因为虽然他接受了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论,也认可中国发生过某种突破,但是他把这种超越性突破严格地限定在韦伯给出的理性化或祛魅标准中,一旦有违韦伯式的严苛理性化标准的“关联性宇宙论”出现,就被罗哲海判定为一种不符合超越性突破的倒退。罗哲海并没有为了论证中国发生过突破就把超越性突破或理性化的标准降低或多元化。这是他与雅斯贝尔斯和史华兹最大的不同,雅斯贝尔斯为了保证轴心时代突破的普遍性,不惜降低了突破的标准,而史华兹明确地认可了一种有别于西方的中国式的理性主义和中国式的超越性突破,这是韦伯以及罗哲海绝不能接受的。
接下来,与史华兹、罗哲海类似,同样遵循普遍主义立场的还有冯友兰、张光直、葛瑞汉三位。就冯友兰来说,他虽然并不受到韦伯和雅斯贝尔斯影响,但他相当自觉地以启蒙主义式的进步论为自己的前提,认可从宗教到哲学、从巫术到理性的框架,并把它应用到早期中国的思想解释中。他认为关联性宇宙论本身已然是某种理性化的体现,只是这种理性化有别于西方式的理性化。因此可以说他的观点与雅斯贝尔斯和史华兹异曲同工。
张光直和葛瑞汉则不同,他们两人虽然具体论点和论域都十分不同,但是在普遍主义框架下,他们都认为,实际上中国并未经过一场真正的超越性突破,而仍总体上停留在早期原始思维的某种状态(萨满主义或关联性思维)。相比起来,西方则摆脱了这个原始阶段,进入了更高的层次(分析性思维)。实际上他们又回到了类似于韦伯和罗哲海的立场上。
接下来,可以大致看做另一个阵营的是葛兰言、郝大维、安乐哲、李约瑟、牟复礼。他们并不以普遍主义为前提。并且明确地把早期中国思想的特征看做是与西方那种人神、此世与彼世二元对立的超越论模式截然不同的模式。他们大致以一种内在主义的关联性宇宙论概括之。这与史华兹的看法类似,但是与史华兹以及罗哲海不同,他们并不像雅斯贝尔斯、史华兹那样,一定要用某种“超越的突破”或“理性化”框架理解中国思想。更不像罗哲海、葛瑞汉那样,将之视为低级的(低于西方式的超越或理性)。相反,他们认为中国思想有别于西方思想正是其可贵之处,不能够用一种西方中心的普遍主义强加于中国,也不能用一种西方例外论或优越论加诸中国。他们强调的是中西有别的多元主义或文化相对主义,并从对中国思维方式的赞赏中透露出某种对西方思维模式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