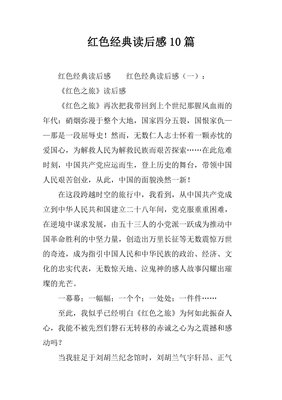
《在路上》是一本由[美]杰克·凯鲁亚克著作,博集天卷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8,页数:36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在路上》精选点评:
●家禽出在大学,虎豹出在山野,木心这样形容从“垮掉的一代”中脱颖而出的酒神精神的代表(其他“垮掉的一代”人物都被他称为酒鬼精神
●在路上当然不是爱情小说,爱情也不是这里面唯一的情感,但在凯鲁亚克的笔下,每一段爱情都有其动人之处,雷米和李安,老布尔和简,迪安和玛丽露,以及萨尔和特丽,吵得鸡飞狗跳,却也难舍难分。
●人生的精彩在于拥有无限种可能,我们也许无法过上某种生活,却可以在文字中畅想它。《在路上》代表着一种自由,是一种热气腾腾的生活,它更适合存在于我的想象当中。
●所谓的复兴,真的在我辈吗?如今,我们面临着死亡、欺骗和国王,一切都在下坠,意志被埋葬。所以希望在何方。我们难道也要成为“垮掉的一代”吗,在路上,年轻,狂奔,自由,先去挥洒,避免衰老。
●一代人的群画像,一个时代的微缩影,喜欢译者的文风,感受到了荷尔蒙的躁动和坦荡,虽然蓬头垢面,鸡飞狗跳,却坦荡自由,思绪自然流动,人生自有其逻辑,我们只需顺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就好,不必烦恼。2020年第一书,在路上。
● 说《在路上》是摇滚的精神圣经绝不为过,大卫鲍伊和鲍勃迪伦都是他的拥趸啊,一部文学作品能启迪不止一个领域的艺术创作,简直就是神作。
●喜欢这次能遇到一个懂BG的翻译
●多年前读过文楚安的译本,觉得非常好看,也因为那时候的年龄是正当好,真是好。收到这个台版的新中译本,仍然很开心,也很伤感。从人生的悲剧性旅途来说,我虽年近中年,仍然算是在路上,但唯独少了一样最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力气,挥霍的力气,狂妄的力气。
●受益匪浅。
●不认同所说这版翻译不文从句顺,它的翻译因为更追寻英语语法,显得更立体,这也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在路上》读后感(一):丛林会捕获你,让你成为它的一部分。
迪安 莫里亚蒂, 一个自由的灵魂,他的生命是无比之轻的。活着,是为了看遍这个世界,为了新鲜的体验,他活着,不为任何人,只为自己。他这样轻盈又有趣的灵魂也吸引了伙伴,包活第一人称的萨尔,他们结伴而行,想走就走,从来没有充足的准备,所以发生的一些都是意外,是惊喜。他们随处打工,只为了攒下个路程的积蓄。他们听着爵士乐,聊着天,找着喜欢的女孩。但有时,也会嫌责任太过沉重,而将其放在路边,不会带上路程。
萨尔一直都心心念念着迪安,想与他碰头,一起上路。迪安就是他们旅途中的精神领袖。不为任何人而活,不在乎他人的眼光,自由而有趣的灵魂,就是他的魅力吧。
我发现我读小说,有时候很慢热,总要读到后半段,才进入小说的世界,但是一旦进入了,就会被吸入作者的世界。这样疯狂而自由的生活方式,是一种难忘的体验吧。
《在路上》读后感(二):《在路上》愿我们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生活不是简单的是非,黑白,对错,善恶,成长也不是简单的提高和向好,而是逐渐懂得生活的复杂性,慢慢学会在坚持与妥协之间做出选择。《在路上》~愿我们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珍惜当下,做一个真实的人!我读的是台湾版何颖怡译本,感觉这个译本还不错。想读文楚安版本,没找到。 “我沉思,向四面眺望,就像我在山底的小世界不断探索一样。横在眼前的却只有我的美国大陆,广袤粗犷的大地上高山猛然隆起。极远处,阴郁疯狂的纽约正在喷涂吐烟尘与棕色蒸汽。东部自有它的棕色神圣况味,加州则雪白如晾衣绳,肤浅空洞--至少,这是我那时的想法。” “当夕阳落下美国大地,我坐在破旧的河堤码头,望着新泽西州的狭长天空,我能感觉到这块不可思议的粗犷大地一直绵延到西海岸,感觉到它的条条大路,以及在这广袤的土地上延绵无尽的道路和追逐梦想的人们,我知道此刻在艾奥瓦,小孩一定在哭,因为那儿的人们就是任由小孩哭。今晚,星星会露脸,难道你不知道上帝就是小熊维尼?今夜的金星一定低垂,暗淡的光芒洒落在草原上,不久,黑暗就会降临,给大地带来安宁,使所有的河流变得暗淡,笼罩着山峰,收纳最后一片海滩,谁都无法预知谁的将来会如何,只知道我们无法逃避年华老去这一凄惨的事实。我记挂着迪安·莫里亚蒂,甚至记挂着我们一直没找到的老莫里亚蒂,我记挂着迪安·莫里亚蒂。”最后一段文字很抒情,挺喜欢这段描述。
《在路上》读后感(三):只会在那个时代
我和她胡扯,说我毕业了要去当三个月流浪汉,问她要不要加入 我说我们可以一路搭便车去西藏,然后去内蒙古,然后去东北,再滚回去,取道中原 她就说她屁才艺没有真就只能乞讨,然后就说你上辈子一定是个没出过山的(我大声反驳我不就爱旅游了亿点点),许愿下辈子无忧无虑做个游子 太浪漫了,我都快信了 这小妞情话怎么张口就来 我就继续:到时候,我们就站在路边上,把大拇指一竖 她:然后吃一嘴的灰 我:对,还在太阳底下暴晒几十个小时,像条狗一样爬上别人后座,或者和货物一起坐,或者和一堆鸡鸭pig 她:当地人操着一口我耳朵竖尖了都听不懂的口音,非要拉着我们侃大山,我们就说老乡你说的都对! 我又问她,你觉得我们三个月能不能洗到三次澡,她觉得两次都奢侈 我转念一想:半夜我们在路边冻成傻逼,我在那跳大神取暖 她:我们可以去田地偷番薯打野兔,然后被吊起来打,被送进警察局的时候说这是紧急避险,再被狗追 我:美女你会爬树吗 她:当然不会啦 无语!于是我扯到西藏,我说我去登雪山的时候肯定会掉几根脚趾,她觉得她会先因为紫外线过敏当场去世 我特诚恳地问:那你要就地掩埋还是魂归故里 她:当然天葬啦这么好的机会不喂动物多可惜 我想了一下,就说,那我就在山脚下的旅馆打工,说不定还能接待外国登山队 她:然后某一天旅馆来了个全身裹得严严实实的客人,你叫住他问他要不要来一杯酒,只见我掀开帽子说道:“好不容易爬上来一次,当然要陪你喝个够啊。”
《在路上》读后感(四):道路就是生命:《在路上》的世界
首发于深港书评:https://appimg.allcitysz.com/template/displayTemplate/dist/index.html#/newsDetail/550669/82?isShare=true
“在路上”进行的三次测绘
“……我只觉自己变成另一个人,一个陌生人,有如鬼魂附身的幽灵人。我已经跨越半个美国,站在人生的分水岭,身后是我在东部的年轻岁月,前方是我在西部的未来时光……”很少有美国作家尝试将东部和西部并峙在一起谈论,凯鲁亚克是一个例外。在《在路上》中,迪安用喜剧性的口吻讲道,“东部厕所都是一些插科打诨、淫秽的文字与图画;西部人只会在厕所写自己的名字,到此一游,某年某月某日……”它所讲不止于地域。如果你用心倾听,你会明白它讲出了渴望,去寻找去征服的渴望,这样的渴望联结了欲望和梦想。
凯鲁亚克将讲故事的尺度扩大到了流动的美国版图,而不再是既定地追随密西西比河,像马克·吐温那样,他不再将自己视为作家,而是地理测绘师。
《在路上》便是凯鲁亚克对美国(最后一次有墨西哥)进行三次测绘的成果,它讲述了萨尔在往返于纽约和旧金山或者墨西哥城的旅途上的所见所闻。与主观视角下的第一人称叙述不同,它杂糅了日记和随笔的叙述方式,也从被美国文学本土化的成长小说中汲取了养料,但更随意和传统。
在很多故事里,主角是迪安,而不是萨尔。迪安是萨尔痴迷的“垮掉的一代”。在萨尔的心中,迪安可以成为任何他想成为的人,兰波、丹佛市长,但迪安也被卡罗尔戏言“俄狄浦斯·埃迪以饱受折磨的阳具扛起所有苦痛”。作为萨尔的那喀索斯对象,迪安对于女人、毒品、飙车、爵士乐和任何一种自由狂野都有着旺盛的欲求,他结了三次婚,现在却在玛丽露和卡米尔之间周旋,他把皮箱放在床下,随时准备被扫地出门和闪人。他在同伴中扮演着先知角色,就连随口而出的漂亮话也有着浪漫奇幻的召唤力,他这样说道,“烦恼乃上帝存在之处的总称”……“我们都了解时间的奥义”……
迪安之于《在路上》,就如凯鲁亚克之于“垮掉的一代”,海明威之于“迷惘的一代”。中国对于“垮掉的一代”的想象抹除了“Beat”作为至福的含义。在“垮掉的一代”的坐标轴上,“自由”作为定点,“垮掉”和“至福”作为另外两点,构成了“垮掉”的抛物线。
“垮掉的一代”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联系着“愤怒的一代”“回归的一代”,联系着二战后的文化政治现实、后殖民现实、后工业现实和革命现实,它通过将年轻人挤出既定的秩序而将自身置于生存和政治之间,而借由它,后现代潮流流布世界,尽管它不再与梦想和自由有强关系。毛泽东如是形容那个年代,“我们的民族像一个原子。当这原子的核被击碎时,(积聚的)热能将释放出惊人的力量!”全球的墒增释放出了巨大的能量。第三世界终结了,取而代之的是全球化,对于革命的好感和需求转移到生活之上。“精神在先,生活在后”的模式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生活在先,精神在后”,人们带着非凡的野心去生活,民权运动便是其中很重要的例证。
通过旅行,重新诠释自由
凯鲁亚克的公路旅行和文学写作正是其时一种能量流溢的路径。通过旅行,通过迁徙,通过爱,他重新唤醒了美国英雄。他重新诠释了自由。他将他所认可的自由地生活的人们塞进了这本他寄予厚望的作品里,除了迪安和他的两位妻子玛丽露和卡米尔之外,还有流浪汉吉恩、服务员丽塔、黑人雷米、采葡萄工特丽、传奇人士布尔、作家欣厄姆,以及众多在频繁切换的场景中闪现的美国公民。
丽塔和特丽和萨尔都有过一段爱情/婚姻生活,但没有涉及承诺、责任,爱情浮现在日常之中,然后将空间和光彩留给新的爱情。他这样写和特丽的恋爱,“我们就像两个疲惫至极的天使,绝望地搁浅于洛杉矶的礁岩之上,突然间,一起找到了生活中最亲密最甜美的东西……”老布尔或许是凯鲁亚克为“垮掉的一代”所安置的一个灯塔,他将“垮掉的一代”又往前追溯了三十年,且置于世界的舞台之上。老布尔的足迹遍布世界,他在芝加哥策划抢劫土耳其澡堂,在纽瓦克替法院送过传票,在大学时代因为宠物雪貂射出了一个巨大的洞,在1930年代和国际可卡因走私集团合过影,他热爱吗啡、大麻、傻瓜丸、安非明、烈精,在一个暗夜,他就着卡夫卡,吐露着对于官僚、工会的憎恨。
凯鲁亚克的描述并非幻想。在战后,随着战争和阴霾消失,人们的道德热情和传统信念与站前相比松动了很多,也真诚了很多。自由主义还是一个新生儿,冷战还没有到来,这时的世界有一种乌托邦式的乐观精神。青年作为一种崭新的力量得到了更广泛的确认,甚至可以说,青年成为了社会的主导。人们成立了“共在会”“共爱社”和“群居村”,在里面的人们秉持着最自由最富友爱的准则,“所有的女孩都是我的太太,所有的男孩都是我的兄弟,而婴儿都是我的,这就是爱。”与此同时,早期在文学中呈现出来的波西米亚角色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真实的游荡者和反叛者不再享有它们的荣耀,反叛被分发给每一个角色。
这位自称“奔跑的普鲁斯特”的橄榄球手也并未在作品中过分地夸耀自己,甚至将自己的身价放低,退隐在热情奔放的群像之中。这位冒险家看起来甚至有点蹩脚,他常常为了旅费而窘迫,在营区值班他醉酒把国旗倒挂了上去,因为无处投宿在影院的烟蒂堆、垃圾里睡了一宿,直到第二天黎明被清扫现场的人吵醒。这些故事很显然窃取自传统,或者现实中的素材。然而也正是在这有点呆板、古老的文体之上,一种新鲜带有锐度的乐观情调和故事激情发生了,一种与冉冉上升的世界一同加速的文学产生了。
和几乎同期发生的存在主义不同,凯鲁亚克展现了世俗生活所能激发的力量和可能。艾伦·金斯堡、鲍勃·迪伦处在同一个位置,处在美国文化的核心地带,如特里林所说的“强悍、凶猛、自信和好斗”。1955年,他们用由此发扬开来的诗歌朗读,将一种融合了神秘、政治和欲望的诗歌推广了出去,复兴了旧金山诗歌,复兴了集体体验,复兴了口头文学传统,也复兴了惠特曼的文学传统。而今,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世界再也不是那样了。我们不再那么自然而无畏地接受壮举和虚无。凯鲁亚克对于未来的猜想和许诺也失落了,过去成为一个被诅咒和被遗忘的过去。再也回不来了。
改变了文学,却与最好的想象背道而驰
凯鲁亚克所处的美国文学史正是第二代现代主义作家开始寻求一种新的未来的时期,他们没有因循T·S·艾略特和海明威的踪迹,而是各自寻求,开创了一个多元和丰富的文学局面,这是二十世纪美国文学最为汩汩的时期。凯鲁亚克既是传统的,又是激进的;他的传统表现在文体和叙述,他的激进表现在精神,用苏珊·桑塔格的话说,这是“一种新感受力”。从此后和当下的文学向前追溯,凯鲁亚克所表达的并不是一个乍现的潮流,而是一个文学的新的开端。
凯鲁亚克如是改变了文学,文学不再是一种世俗化的故事演绎,而成为一个改造意识、塑造新的感受力的工具。文学再一次地被前置,但并不是大陆学者所宣称的后现代之杂粹和狂欢。这一点可以从凯鲁亚克的写作方式上看出。写作之初,他将稿纸粘连成一个连续不断的卷筒纸,保证在写作中不被打断。在写作中,他调用了一种被称作自发性波普爵上乐写作法的写作方式,用近乎禅修和爵士乐的方式,不加句号、用思维速写、跟随节奏演奏,打出了120英尺的长度。在三个星期内,他非理性的贪欲席卷了他的记忆和灵感,他编纂了“狂野的,混乱的,纯真的,从心底里涌现的一切”。类似的信念伴随他一生,他在一篇文章里引述了《首楞严经》,“若指望理解更多至高启示,务必学会本能回答问题,不要寻求援助,歧视思维”。这或许就是当下文学在表层中流溢速度和美的原因所在。
而这连接着“beat”作为至福的一面,也连接着由禅出发的“因为我一无所有,所以一切皆归于我”( Everything belongs to me because i am poor),同时还连接着“地球乃印第安人所有( The earth is An Indian Thing)”。他设想了一种非凡的人类存在,瓦解掉了殖民问题、族裔问题、身份问题,这或许是有史以来文学对于人类作出的最奇妙、最美好的想象。
然而,凯鲁亚克却与他的想象背道而驰。就在完成《在路上》不久,这位法裔加拿大人就猝然终止了婚姻,强迫琼·哈弗蒂堕胎,并四处逃窜,拒绝妻子的抚养费诉求。他对毒品没有瘾,但他酗酒,酒后好斗,连金斯堡也招架不住他了。他是他的朋友中最不幸的人,孤苦伶仃,他从始至终都幻想着生活在大农庄里。他越来越不认同自己是“垮掉的一代”,而将自己看作是天主教徒,尤其是在晚期生活中,他的绝望让他依附于十字架,他画了很多基督主题的画作。他喜欢在深夜写作,当整个世界都在沉睡时,他独自一人在灯光烛火里畅游到清晨,但他逐渐厌弃了写作,也丢掉了寒山。他搬去了佛罗里达,安置了母亲和新的妻子,时间轻而易举地打发了凯鲁亚克。在最后的文章中,他写道,“我在午夜醒来时,我意识到他说的是对的,存在中肉体的痛苦是一种十分敏感的痛苦,这种感觉比政治上的愤怒和希望更加强烈,就像我正躺在床上慢慢死去一样……”他死于1969年10月21日,没有阳光,只有从收音机里播放出的大音量的《弥赛亚》。
就像历史中的那个年代的人们一样,凯鲁亚克被异化、孤独的人群、文化产业封堵在一个窘迫的现场中,来自俳句或禅或任何其他的智慧并没有让他活得足够长。和托马斯·沃尔夫和普鲁斯特一样,他将文学书写成一种包容了人生和未来的长卷。正如金斯堡在阅读他的《墨西哥城布鲁斯》所意识到的那样,凯鲁亚克开创了一种反对修改和未经修改的美学,而如今我们越来越继承了这一“存在即诗”“呈现即诗”的美学。后世的读者在追随凯鲁亚克在路上自由地游荡和生活时,总是会这样说,“我们突然觉得世界是个牡蛎,等着我们打开,发现里面的珍珠,珍珠就在里面。”他们分不清这是凯鲁亚克的话,还是他们自己的。
《在路上》读后感(五):《在路上》译者靠北(译后记)
何颖怡(译者,她翻译的台版目前在豆瓣 8.7 分,新版《在路上》用了她的译本,她还翻译了「垮掉的一代」另一本代表作《裸体午餐》。)
这是何颖怡在「博客来」发布的专栏文章,谈自己翻译《在路上》的经过。经出版方博集天卷授权发布,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翻译《在路上》,你才知道鸡寮不是鸡寮。翻译过程,人各有癖。我呢,偏头痛+音乐+考古。试举《在路上》(On the Road)为例。 翻译完,清理桌面,把原书影印稿(放大字体,老了,没办法)以及一、二校列印稿全部清掉,这是我每次完成一本书的例行工作。排在大病一场,及大声咒骂「我的翻译是个什麽鸟」之后。我是效率很差的译者,碰到跟我有仇的书,翻译期间,我一星期平均要偏头痛个二、三回。有时碰到难查的用语,得拼死命在网路上流浪,恨自己不是在玩 YouTube,而是在查什么是 chicken shack〔注1〕。
交稿后大病一场是必然的。因为长期的压力突然得到释放,感冒啦、头痛想撞墙啦、背痛到不能翻身啦、心脏怦动声大到双耳能闻啦,或者,躺下来马上睡著,两天内睡了 30 小时之类的。
病完后,另一种痛苦才开始,因为开始跟编辑对稿了。我一看到自己三校过才出手的稿子还有漏译、错译、白字、赘字、标点错误,就开始大声咒骂,什麽烂翻译,我大学才毕业吗,我第一次当翻译吗,我中文这麽超特烂啊,什麽鬼翻译会出现「我刚刚大病初愈」这种句子,「刚刚」不就是「初」吗,这么明显的赘字,我要到排成 PDF 档才看出来,我是猪吗?
如此这般,我跟翻译的爱恨情仇周而复始。翻译过程如此痛苦,我为什麽还继续翻译?
因为除了偏头痛,翻译有其他收获。翻译迫使我每天至少待在电脑前四、五小时,一次开八个网页,其中五个是字典网站,两个新闻,一个 YouTube。
唯有音乐能撑著我最后一口气。每翻译一本书,我就完成一个小小的音乐研究。
翻译《在路上》足足一年,我听完 Beastie Boys、Public Enemy、Run DMC、Digital Underground、Roxanne Shanté 等嘻哈先锋的作品,理解了嘻哈音乐互相挪用的传统与脉络,譬如听到 Beastie Boys 的 A-Rock 在演唱会唱《The New Style》这首歌,飙到「Let Me Clear My Throat」这句歌词,我忍不住微笑。因为 DJ Kool 的名曲《Let Me Clear My Throat》就来自 Beastie Boys 原始创意,现在成为 NBA 球赛的热门中场音乐。Beastie Boys 是白人团,出道时,因为挪借黑人音乐饱受黑人乐手抨击。DJ Cool 是黑人,却挪借白人 Beastie Boys,多么有意思,这就是嘻哈。
Let Me Clear My Throat9.1DJ Kool / 1996Dj Kool feat Biz Markie - Let Me Cl(DJ Kool的《让我清清喉咙》好经典。 DJ Cool 与 Doug E. Fresh 演唱的《Let Me Clear My Throat》是 NBA 球赛著名中场歌曲。 裡面还有 Biz Markie。)
我又想到《Let Me Clear My Throat》的现场录音版本最受欢迎是 DJ Kool 搭配 Doug E. Fresh,人称「史上第一个 human beatbox」,他著名的 dougie dance 才因 Cali Swag District 唱的《Teach Me How to Dougie》再度红起来。不过更重要的是他的成名曲《The Show》又称《Oh My God》,而 OMG(网路缩写)前几年才正式列入牛津字典。kudos 牛津字典!
音乐考古真能消解翻译过程的折磨。
也可能是翻译让我经常庆幸「友直、友谅、友多闻」我都有。《在路上》是垮世代(Beat Generation)三大文学代表作之一,名列《时代杂志》与美国图书馆票选的20世纪英语百大小说 〔注2〕。写作此书,凯鲁亚克创造了一种「自发性写作」风格〔注3〕 ,这种风格深受爵士乐影响(见注解),尤其是咆勃爵士(bebop)。不难想像本书许多章节都牵涉到爵士。我耳听嘻哈,笔翻爵士,当然阻碍重重。幸好我有小威老师、沉鸿元当靠山。要不是小威老师,我很可能将书中一个无名乐手 Prez 直接翻译为裴瑞斯。小威老师说那是李斯特杨(Lester Young)的绰号,总统(president)的缩称,意指 Young 威风八面。放在文内,应该是说这个萨克斯风手的风格模仿 Lester Young,所以作者才叫他 Prez,不代表此人名 Prez。好险好险啊。
Prez 不是裴瑞斯,是 Lester Young,好险。有时为了一个句子,我得跟朋友多边会议,譬如书中,凯鲁亚克的姑妈劝他少跟主角狄恩鬼混,凯鲁亚克说,他当然知道不好,但是 Life is life, kind is kind。这样一个句子,要抓意思,本来就不容易,要连对仗都翻译出来,更是难。朋友陈仪芬是中古英文高手,她说:命就是命,德性就是德性。作家朋友张让说,命就是命,听起来有宿命、认命的味道。或许应该翻译为:生活就是生活,臭味就要相投。因为 kind is kind 稍加衍伸,就有物以类聚的意思。我老公一觉醒来,突得一对联,说翻译成这样吧:人生如此,本性如此。马上,张让就说,什么「如此,如此」,太文言,简直看到梁山伯的老师在摇头晃脑。她常批判我笔下「太文」,不喜欢用「的」、「了」、「地」,行文没有呼吸空间,缺氧。友直排行榜,她始终是第一名。最后定稿的翻译是「人生就是人生,德性就是德性」。为了配合对仗,没办法,懒得理对仗的话,最简单明了的翻译应是「人生就是这样,我的德性就是这样」。
朋友陈仪芬,我们叫她「劲量小芬」,就是一堆人都倒了,她还在打鼓。她是少见的文艺复兴人,潜水、拍照、烹饪、气功、 针灸、各国基金股票、中古英文,她无一不知,无一不晓。《在路上》引用一句法国小说家赛琳(Louis-Ferdinand Céline)讲的 Nine lines of crime, one of boredom。我上网查了数小时,查到快哭了,都找不到正解(因为不知道它的法语原文是 什么)。只好跟文艺复兴人小芬求救,她连上下文都不知道,大约只花了两秒钟,就跟我说「应该跟十诫」有关,「十诫九条是罪,一条是穷极无聊」。是用存在主义者赛琳的话,来讥讽基督教。我从来没这麽嫉妒别人的学问,眼睛都绿了。友多闻是也〔注4〕 。
Louis-Ferdinand Céline 难得倒我,难不倒「劲量小芬」。翻译人必备之「友多闻」。越是不好翻译的书,我在翻译期的衍生收获就会越多。因为心情极端低荡,痛苦得寻找欢乐出口。翻译《在路上》的收获是我终于完成我的苗圃梦,种在小盆裡的水仙与郁金香球茎,经过三场大雪,居然抽芽了。我极端受不了加拿大人种郁金香像「站卫兵」,总是直直一排排,看起来像塑胶花。所以,我围著前院的大树种一圈,圆圈不是很圆,开花后,可能会被邻居投诉「不合群,破坏社区景观」。管它的,凯鲁亚克说「沙漠里不能没有岩石,历史的荒漠里也不能没有印第安人」。排排站卫兵的郁金香荒漠里,总要有几株是在稍息。
翻译《在路上》,我应该僵尸、吸血鬼双主修才对。第二个收获自然是我的「僵尸功」更上一层,看了同志僵尸片《Otto or Up with Dead People》 。老公说,僵尸已经很变态,我还要看僵尸做爱,不仅做爱,还是同性爱。我到底有什么毛病?没什么啊!如果你每天要跟凯鲁亚克笔下超高比例的 「分号」奋斗,既要保持他的自发写作特色,又不能每一句都是「我」开头,让读者以为你小学都没毕业,不看僵尸片,情绪怎麽会有出口?何况超好用的 window 7 偏偏与我惯用的汉音输入不合,被迫使用笨到极点的微软新注音,根本就该僵尸与吸血鬼双主修才对。
翻译过程的诸种靠北,往往化为考古性质的译者注。我们写得「正经八百」,其实内心想骂「妈的,耗掉我三个月 」。不信, 你看:
凯鲁亚克的 it 只有两个字母,耗掉我三个月。(译者干声不绝的靠北)翻译最怕 IT,它。垮世代作家崇尚咆勃爵士乐,那个时代的进步音乐。《在路上》经常大篇幅描述爵士表演现场,乐手如何进入「got it」的状态,观众如何感受到「it」,上下如何水乳交融于「it」中。翻译的人都知道越简单 的字越是难翻。乐手得到「它」,观众感受到「它」。这是什么狗屁呢?
最后,It 还是翻译为「那个」,但是配上一个我大约花了三个月看了数本有关垮世代的学术论文书,所得到的一个注解,如下:
(靠北后的假掰译者注)垮世代文人深受爵士乐影响,尤其是咆勃爵士。根据 John Lardas 在 The Bop Apocalypse: the Religious Visions of Kerouac, Ginsberg, and Burroughs 所述,对凯鲁亚克等人而言,咆勃爵士远离欧洲 音乐形式传统,它是一种酒神式的野性美国音乐,纯粹的感情与狂热传给观众极大的震撼与共鸣。就像「集体狂欢」(orgy),爵士乐让每个人爆发,最终合而为一。乐手有能力「洞察」他自己与众人「当下」的心理状态。 咆勃爵士的即兴让独奏乐手可以一边搭配整个乐团,一边追求自己的狂喜飞扬。这是在「群体里仍得以表达自我」的最终自由形式。换言之,咆勃爵士乐手进入精彩状态时,台上与台下既有共感(communal),又是一种极 端直觉的存在。这种感觉,主角狄恩·莫瑞亚提无以名之,只好称为「那个」(It)。详见 John Lardas, The Bop Apocalypse,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0), pp.108-110。并参考第一部第三章注释一。靠北心声⻑如裹脚布,我还是一本本翻下去,为什么?与我合作最久的编辑辜雅穗说「犯贱」。
这也是另一种友直。
〔注1〕翻译《在路上》认识的字,养鸡棚,意指只供应鸡肉料理的小小小餐厅。这个字,让我流浪网路三小时。之前的两个译本都翻成 「小如鸡寮的棚屋」。
〔注2〕垮文学三大巨著分别是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布洛斯的《裸体午餐》(Naked Lunch),以及金斯堡的诗集《嚎叫》 (Howling)。
〔注3〕凯鲁亚克的「自发性写作」(spontaneous writing)强调直接记录思想,挪用爵士乐的换气(或者冥想打坐的吐纳)技巧,直接在脑海或语言的既有架构上「即兴发挥」。伴随这种写作技术,是以大量的破折号取代句号,破折号内的插入思想就变成类似爵士乐 的即兴乐段,呈现一种节奏感。自发性写作不改写也不重写,类似意识流,也不免文法结构破裂。《在路上》的最原始手稿是用描图纸相连,⻑达120呎(30多米长)的卷轴,不空行、上下左右均不留白、文章也不分段,以此强调自发性写作的直觉成份。后来面世的书稿经过编辑与 作者的修改。卷轴粗稿则在 2007 年原样付梓。
〔注4〕友谅,自然是本书的责任编辑贝雯,忍受我延三个月截稿,经常得对我让步,譬如她说「忽焉」文言,我说不,如果连忽焉都看 不懂,应该不会买书。最后,我一二三校还不够,进了工厂排 PDF 档后,还要校,还要改。贝雯的惨,不是人人能体会的。
〔注5〕加拿大怪胚导演 Bruce LaBruce 的 2008 年电影,大大出乎意料,是以「艺术电影」手法拍僵尸,黑白片。
何颖怡
台湾政治大学硕士,曾任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性别研究专业研究员,现专职翻译。做过记者、编辑、唱片创意总监、爱乐电台主持人。企划出版过《索多玛120天》《猜火车》《裸体午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