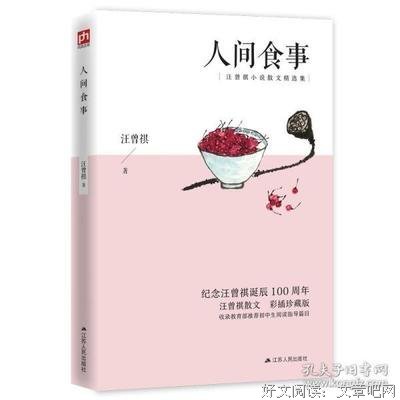
《人间食事(彩插珍藏版)谈吃美文,一茶一饭,锅边碗里,都是生活的滋味》是一本由汪曾祺著作,32.00出版的228图书,本书定价:平装,页数:2020-6-2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人间食事(彩插珍藏版)谈吃美文,一茶一饭,锅边碗里,都是生活的滋味》读后感(一):汪曾祺为何那么爱吃
by 夏学杰
我这篇个文章的标题,似乎有点歧义,有人该说了,食色性也,谁不爱吃呢?诚然,谁都爱吃。但是,像汪曾祺这样喜欢尝试各种食品,并且写下许多美食文字还由此总结出点人生哲学的,就不太多了。
《人间食事》是2020年江苏人民出版社为纪念汪曾祺诞辰100周年出的《汪曾祺小说散文精选集》中的一本。顾名思义,《人间食事》主要集中收录了汪曾祺的美食文章。
汪曾祺喜欢美食,自称自己敢于吃任何食物,汪曾祺的长子汪朗说:他去内蒙古,专门要试着生吃羊肉。他晚年去云南,就想尝一下傣族的苦肠——牛肠里没有完全消化的青草,傣族人生吃、做调料、蘸肉。当地人怕同去的作家接受不了,只做了一个苦肠加肉蒸丸子,让他觉得很不过瘾。北京的豆汁,外地人一般喝不惯,但汪曾祺不惧。他写道:“到了北京,北京的老同学请我吃了烤鸭、烤肉、涮羊肉,问我:‘你敢不敢喝豆汁儿?’我是个‘有毛的不吃掸子,有腿的不吃板凳,大荤不吃死人,小荤不吃苍蝇’的,喝豆汁儿,有什么不‘敢’?他带我去到一家小吃店,要了两碗,警告我说:‘喝不了,就别喝。有很多人喝了一口就吐了。’我端起碗来,几口就喝完了。我那同学问:‘怎么样?’我说:‘再来一碗。’”
他喜欢做菜,并且还洋洋自得,他写道:“美籍华人女作者聂华苓和她的丈夫保罗·安格尔来北京,指名要在我家吃一顿饭,由我亲自做,说是这样别致一点。我给做了几道菜,其中有一道煮干丝。这是淮扬菜。华苓是湖北人,年轻时是吃过的,但在美国不易吃到。她吃得非常惬意,连最后剩的一点汤都端起碗来喝掉了。”汪朗说:在家里,老头儿也常常做些杂七杂八的东西:炒麻豆腐、炒疙瘩皮、羊头羊蹄、热汤面就臭豆腐……全是北京平民吃的玩意儿,上不得大雅之堂。前些年,市面上还没爆肚卖,他就自己买个生牛肚,吭哧吭哧洗上半天,还得把牛肚里外都撕去一层,只留下中间部分,然后自己配制调料。折腾两三个小时,最后满打满算能爆出一笊篱成品,还嚼不烂。他倒是吃得挺来劲,用假牙一个劲儿磨蹭,一边还说:“爆肚就是不能嚼得烂。”有这回事?
汪曾祺的美食文章写得很粗略,如写腌笃鲜,“上海菜。鲜肉和咸肉同炖,加扁尖笋。”只有这么几个字,跟报账似的。除了是他自己做的菜,他是不大说菜的具体做法的,就连吃的感觉也写得极其简略。写狮子头的口感:“狮子头松而不散,入口即化,北方的‘四喜丸子’不能与之相比。”写长沙的腊肉:“我没有想到腊肉能蒸得这样烂!入口香糯,真是难得。”对此,汪朗是这样理解的:“他的这类文章和一般人不太一样,很少谈某种菜的具体做法,也不怎么谈自己的‘美食历程’,只是进行简简单单地介绍,让读者自己去想象其味道,这充分体现了他的写作主张:文章要留白。”这应该跟其个性有关,他不大擅长铺陈的文风。
建筑家王澍说:“不要先想什么是重要的事情,而是先想什么是有情趣的事情,并身体力行地去做。”我觉得,这句话很适合汪曾祺。他就是一个追求情致的人。苏北在《舌尖上的汪曾祺》一文中写:汪曾祺女儿的同事到她家玩,汪曾祺“在厨房忙活了半天,结果端出一盘蜂蜜小萝卜来。萝卜削了皮,切成滚刀块,上面插了牙签。结果同事一个没吃。”女儿汪朝抱怨说,“还不如削几个苹果,小萝卜也太不值钱了。”老头还挺奇怪,不服气地说:“苹果有什么意思,这个多雅。”
他大概是想在寻常烟火中寻觅点乐趣罢了。正如简·韦伯斯特写的长篇小说《长腿叔叔》所言:“生活本身已经够单调的了,你总得花很多时间吃饭睡觉。但想想看,如果在两顿饭之间再不发生点意料之外的事情,生活不仅是单调了,简直是了无生趣!”
不仅能勇于尝试各种食品,汪曾祺还想自圆其说,在吃上,总结出一点人生的道理。他在《口味》一文中说:“有些东西,自己尽可不吃,但不要反对旁人吃。不要以为自己不吃的东西,谁吃,就是岂有此理。比如广东人吃蛇,吃龙虱;傣族人爱吃苦肠,即牛肠里没有完全消化的粪汁,蘸肉吃。这在广东人、傣族人,是没有什么奇怪的。他们爱吃,你管得着吗?不过有些东西,我也以为不吃为宜,比如炒肉芽——腐肉所生之蛆。总之,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去尝尝。对食物如此,对文化也应该这样。”不仅如此,他还在《苦瓜是瓜吗》中进一步阐述道:“我希望评论家、作家——特别是老作家,口味要杂一点,不要偏食,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
《人间食事(彩插珍藏版)谈吃美文,一茶一饭,锅边碗里,都是生活的滋味》读后感(二):汪曾祺:没有什么比有趣更重要
by夏学杰
《人间有趣》是汪曾祺先生的文艺杂谈合集,共收录汪曾祺先生流传已久的文艺杂谈44篇,由“写字品画,论艺之道”“提笔翻书,学话小议”“幕后台前,戏如人生”“随笔偶得,杂谈文化”四章组成。汪曾祺讲述了自己在文学创作中的初心与历程,也中肯地评析了一些著名文人及其作品,其中也不乏他对生活、对文学的深度思考。书中带有配合原文的精美彩色插图,让你在阅读文字的同时,也可以从视觉上深刻体会汪老先生文字的魅力。 建筑家王澍说:“不要先想什么是重要的事情,而是先想什么是有情趣的事情,并身体力行地去做。” 我觉得,这句话很适合汪曾祺。 他就是一个追求情趣的人。 苏北在《舌尖上的汪曾祺》一文,写到汪曾祺女儿的同事到她家玩,汪曾祺“在厨房忙活了半天,结果端出一盘蜂蜜小萝卜来。萝卜削了皮,切成滚刀块,上面插了牙签。结果同事一个没吃。”女儿汪朝抱怨说,“还不如削几个苹果,小萝卜也太不值钱了。”老头还挺奇怪,不服气地说:“苹果有什么意思,这个多雅。” 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学生。汪说:沈先生不长于讲课,而善于谈天。他谈一位研究东方哲学的先生跑警报时带了一只小皮箱,皮箱里没有金银财宝,装的是一个聪明女人写给他的信。谈徐志摩上课时带了一个很大的烟台苹果,一边吃,一边讲,还说:“中国东西并不都比外国的差,烟台苹果就很好!”谈梁思成在一座塔上测绘内部结构,差一点从塔上掉下去。谈林徽因发着高烧,还躺在客厅里和客人谈文艺。他谈得最多的大概是金岳霖。金先生终生未娶,长期独身。他养了一只大斗鸡。这鸡能把脖子伸到桌上来,和金先生一起吃饭。他到外搜罗大石榴、大梨。买到大的,就拿去和同事的孩子的比,比输了,就把大梨、大石榴送给小朋友,他再去买!他总结道:沈先生谈及的这些人有共同特点。一是都对工作、好学问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二是为人天真到像一个孩子,对生活充满兴趣,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永远不消沉沮丧,无机心,少俗虑。 这些人的气质,正是汪曾祺所倾慕的,也可以说是他的人生追求,“会从生活中寻找乐趣”。
文字简约而不简单
汪曾祺的文字平白如话。看过那些用绚烂文字写就的文章,再看看汪曾祺的,可能会感到实在是太平淡了,简直有点寡淡无味。在平白如话上,也有别的作家,诸如老舍、余华等,不过他们做的都没有汪曾祺彻底。 汪曾祺在《寻常茶话》中说自己对茶实在是个外行,“因此,写不出关于茶的文章。要写,也只是些平平常常的话。”用“一些平平常常的话”来概括他的文字,我觉得颇为贴切。 “我们到巴金先生家喝工夫茶。几个人围着浅黄色的老式圆桌,看陈蕴珍(萧珊)‘表演’濯器、炽炭、注水、淋壶、筛茶。每人喝了三小杯。我第一次喝工夫茶,印象深刻。这茶太酽了,只能喝三小杯。”第一次品功夫茶,汪曾祺写下的茶感只有三个字——太酽了。要是让当下的美文作家来写,至少也得洋洋洒洒地铺陈上几百字的。而实际上,汪曾祺喝茶喝得很勤,“一天换三次叶子”,他哪里是写不出细腻,不过是不愿为之而已。 汪曾祺的美食文章写得很粗略,如写腌笃鲜,“上海菜。鲜肉和咸肉同炖,加扁尖笋。”只有这么几个字,跟报账似的。除了是他自己做的菜,他是不大说菜的具体做法的,就连吃的感觉也写得极其简略。写狮子头的口感:“狮子头松而不散,入口即化,北方的‘四喜丸子’不能与之相比。”写长沙的腊肉:“我没有想到腊肉能蒸得这样烂!入口香糯,真是难得。” 他在《泰山很大》一文中写道:“写风景,是和个人气质有关的。徐志摩写泰山日出,用了那么多华丽鲜明的颜色,真是‘浓得化不开’。但我有点怀疑,这是写泰山日出,还是写徐志摩?我想周作人就不会这样写。周作人大概根本不会去写日出。”话中透着自己对文字的喜好,他是反对文字浓艳之风的。 汪曾祺在《文学语言杂谈》一文中言:“它不只是一个一个字摆在那儿,它有个内在的联系,内在的运动。除了讲究间架结构之外,还讲究‘建行’、讲行气、要‘谋篇’,整篇是一个什么气势,这一点很重要。” 对于文字功夫,我对汪曾祺还是很服气的,很有古代士大夫的小品文之风采。 汪曾祺还说:“语言的奥秘,说穿了不过是长句子与短句子的搭配。一泻千里,戛然而止,画舫笙歌,骏马收缰,可长则长,能短则短,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关于这点,他是基本上做到了。
著书老去为抒情
“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这是在沈从文八十岁生日时,汪曾祺写的贺诗中的一联。这又何尝不是在说他自己呢?他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还是很有道理的。 对于抒情,他自己也是承认的。“我的小说大都带有一点抒情色彩,因此,我曾自称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称我的现实主义为抒情现实主义。我的小说有一些优美的东西,可以使人得到安慰,得到温暖。但是我的小说没有什么深刻的东西。”(《认识到的和没有认识的自己》) “我认为作家的责任是给读者以喜悦,让读者感觉到活着是美的,有诗意的,生活是可欣赏的。这样他就会觉得自己也应该活得更好一些,更高尚一些,更优美一些,更有诗意一些。小说应该使人在文化素养上有所提高。小说的作用是使这个世界更诗化。”汪曾祺在《使这个世界更诗化》一文中作如是言。 读罢此言,可大致了解他的艺术追求。汪曾祺的文字原先我是不大理解的,我一直迷糊于他为何那么热衷于抒情,甚至热衷于一些无甚意义之事。 他在《要有益于世道人心》一文中言:“我想把生活中美好的东西、真实的东西,人的美、人的诗意告诉别人,使人们的心得到滋润,从而提高对生活的信念。” 或许,是因为他与其师沈从文,有着一脉相承,都执着于人性。沈从文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言:“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活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做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体型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 汪曾祺的《受戒》与沈从文的《边城》,在气质上,是很相像的,都淡化了时代,淡化了环境,写出人性之美。
《人间食事(彩插珍藏版)谈吃美文,一茶一饭,锅边碗里,都是生活的滋味》读后感(三):烟火味里,才是人间
by毕亮
关于吃,汪曾祺会做,也会写,当然更会吃。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汪曾祺“赋闲”在家,心情苦闷,书画排遣之余,就是琢磨吃食。凡事就怕认真。对于吃这件事而言,汪曾祺是很认真的,在他琢磨出油条塞肉回锅后,忍不住写信和老友朱德熙分享,并邀请他来吃。1987年,他终于在散文《家常酒菜》中专门写出了这道“塞馅回锅油条”。
除了塞馅回锅油条外,汪曾祺还“发明”过菜谱所未记载的菜。有一年春节时,汪曾祺加了一道菜:新采未开伞的平蘑切成薄片,加大量蒜黄、瘦猪肉同炒。对这道菜,汪曾祺有一点沾沾自喜,因为“平蘑片炒蒜黄,各种菜谱皆未载”。据说汪曾祺老家高邮的一些饭馆有一桌“汪氏家宴”,是以汪曾祺饮食文章为食谱做出的“家宴”。我曾途径扬州,与高邮擦肩而过,汪氏家宴也未能如愿地吃到。
也是在给友人的信中,汪曾祺表达了退休后想“搞一本《中国烹饪史》”的计划。然而,终究只是想法,未见他动笔。但他平时看书,很注意搜集这方面的材料,对各种食谱菜谱以及写饮食的文章尤其留意。你看他写“脍”,便知留意此类文字久矣。他写《切脍》《宋朝人的吃喝》等文章,靠的都是平时阅读的积累,要知道那个年代可是没有网络检索。
1987年,汪曾祺去美国参加爱荷华写作计划,在给夫人施松卿的家书中,也常提到吃食。其中1987年9月4日的信,近乎一半都在说吃的东西,他不信“鸡据说怎么做也不好吃”的邪,告诉夫人要“做一次香酥鸡给留学生们尝尝”。在美国期间,汪曾祺和古华住一起,汪曾祺掌勺,古华负责洗菜刷碗。炊具不足,汪曾祺深感不便,在给施松卿的信中让施请人给他带“菜刀、擀面杖,一口小中国锅及铲子”。嗨,汪老头儿真讲究。他也有不讲究的时候,在广西参加文学笔会,他和贾平凹放着大酒店的饭不吃,跑到酒店外面吃老友面,三十年后贾平凹对此还记忆犹新。和林斤澜在四川乐山,其他作家都进了大馆子,他们却“钻进一家只有穿草鞋的乡下人光顾的小店,一人要了一碗豆花”。
在另一封信中,汪曾祺也不忘给夫人汇报:昨天我已为留学生炒了一个鱼香肉丝。美国猪头、鸡都便宜,但不香,蔬菜肥白而味寡。大白菜煮不烂。鱼较贵。——你看,吃货汪曾祺,走到哪里对吃都这么认真。南朝鲜人的铺子为汪曾祺在美国掌勺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因为这里佐料很多,“甚至还有四川豆瓣酱和酱豆腐”。汪曾祺发现“豆腐比国内的好,白、细、嫩而不易碎。豆腐也是外国的好,真是怪事!”美国的豆腐真的深得他心。汪曾祺可谓豆腐行家,对豆腐也有深情,专门写过散文《豆腐》,还写过不短的诗歌《豆腐》。在晚年,汪曾祺的食道有一小静脉曲张,不能吃硬的食物,连苹果都要捣碎了才能吃。这也难不倒汪曾祺,他在《<旅食与文化>题记》中提及此事时写到:“幸好还有‘世界第一’的豆腐,我还是能捣鼓出一桌豆腐席来的,不怕!”话虽如此,但对汪曾祺来说无疑是一种煎熬,在写完此文后不到三个月,汪曾祺逝世。
汪曾祺曾夸口说他什么都吃,于是遭到过两次捉弄。一次是因为香菜,汪曾祺原来是不吃香菜的,但海口已经夸下,只好咬牙吃了;之后他就开始吃香菜了。还有一次是不吃苦瓜的他,朋友请客只有凉拌苦瓜、炒苦瓜、苦瓜汤三个菜;从这顿饭开始,汪曾祺就吃苦瓜了。从吃香菜、苦瓜的经历,汪曾祺体会到了“有些东西,本来不吃,吃吃也就习惯了”,并进一步感悟到:一个的口味要宽一点,杂一点,对事物如此,对文化也应该这样。其实,在此前,汪曾祺就有过这样的观点,将吃和文学联系起来,总结出其中的哲理,并写下了《吃食和文学》《揉面》等文章。
当然,也有汪曾祺招架不住的,那就是鱼腥草的生鱼腥味。看他的文章,好像也仅仅是“招架不住”,还是照吃不误,所以他走在哪里都很习惯,走南闯北,上高原,去草原,都能尝鲜,吃一些未吃过的食物,听一些未听过的掌故。
看汪曾祺的饮食文章,容易让人“对吃过的东西有所回味,对没吃过的有所向往”。昆明东月楼的锅贴乌鱼,虽只有几笔,却写得很馋人。此外,还有家常的酒菜,诸如干贝吊汤煮干丝,拌菠菜,扦瓜皮,芝麻酱拌腰片……他的许多文章,也常能引起乡思。汪曾祺的故乡高邮离我的故乡桐城不很远,许多食物的吃法、叫法都一样,豌豆叫庵豆,将“煮熟的大粒蚕豆用线穿成一挂佛珠,给孩子们挂在脖子上,一颗一颗第剥了吃”,仿佛又回到了少年时代。他写到的地瓜,也是少时我们在乡村常吃的食物,或做菜炒着吃,或做水果,撕掉皮,直接啃吃。他写螺蛳,提及螺蛳弓,句子一拐,直接拐到了“我在小说《戴车匠》里对螺蛳弓有较详细的描写”,于是只好把《戴车匠》翻出来重新看一遍。这也是一种阅读的乐趣,如吃美食。在《食豆饮水斋闲笔·红小豆》的最后,汪曾祺来了这么一句:我的儿子会做夹沙肉,每次很都成功。简直是神来之笔。
到了一个新地方,汪曾祺最想逛的不是书店、不是百货公司,是菜市场,“看看生鸡活鸭、鲜鱼水菜、碧绿的黄瓜、通红的辣椒……”,这真是一种瘾。有一回,汪曾祺在菜市场买牛肉,遇到不会做牛肉的中年妇女,他于是“尽了一趟义务”,给她讲了一趟牛肉的做法,从清炖讲起,到红烧、咖喱牛肉……不知这位妇女是否会觉得眼前这个老人是哪个馆子的资深大厨。汪曾祺的家中常有客登门拜访,尤其年轻作家慕名而来,汪曾祺都要露一手,留客吃饭并喝几杯,此时的汪曾祺只是动几筷子,然后看着客人吃,偶尔抿几口酒。
汪曾祺是喜欢做一点菜的,他觉得对于长期伏案的作家来说,做菜是一种调剂,是一种休息。汪曾祺给《学人谈吃》《吃的自由》等饮食书写过序,还动手编过《知味集》,这是一本作家谈吃的书,请汪曾祺来编,再合适不过了。
(本文已发表于2020年10月17日《天山时报》)
《人间食事(彩插珍藏版)谈吃美文,一茶一饭,锅边碗里,都是生活的滋味》读后感(四):人间送小温
——《汪曾祺小说散文精选集》读后
(文/臧北)
汪曾祺先生有一首题画诗,开头四句是这么写的:
我有一好处,
平生不整人。
写作颇勤快,
人间送小温。(《<花草集>自序》)
前两句自言为人,后两句自言为文,都是明白坦荡。在那段疯*狂岁月,连沉默都不可得,“不整*人”之难可想而知,而在今天,“送小温”其实也殊为不易。那得有民胞物与的情怀与慈悲心肠。何谓“小温”?小者,淡也,亦有谦卑的意思。只是平凡的(也是平等的)人性的淡淡的温暖。如同冬天早晨或者傍晚的阳光,只能给人一丝暖意,让人于寒冷中有个盼头,不致失了希望——而希望恰恰是“人的一部分”(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在一个越来越冷漠的时代,动机难辨的“热情”和居高临下的“温暖”早就让人心生疑虑了,符合平凡人性——尽管现在也已罕见——的“小温”才愈显其珍贵。或许,这也是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近半个世纪,汪曾祺先生的文章一直深受大众喜爱的原因之一吧。
严家炎在《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中将汪曾祺归入京派小说家之列,并指出:“在京派作家来说,最基本、最核心的就是表现纯朴、原始的人性美、人情美。”可称的论。在汪曾祺先生的文章里,谈论的几乎都是凡尘俗事,人间烟火。他谈饮酒、谈美食,让人食指大动,但绝不会有微言大义;他谈人生,但人生就是人生,既不说哲学,也不扯思想;他谈花花草草,一往情深,也屑于夹带什么感悟或者道理。“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这是汪老对自己文章的评价,我觉得即使对于当下文坛,这十三个字依然不啻暮鼓晨钟。
也许是爱之太深吧,近年来对汪老的评价越来越高,甚至有人送了一顶“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的桂冠,让人颇有些茫然。其实,汪曾祺先生在文章中对自己早有过清楚的定位:
我曾自称为“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人道主义传统,大约始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学革*命,汪老的这种追求自然其来有自,而且最直接的来源,我想大约是乃师沈从文先生:
曾经有人询问我,“你为什么要写作?”
我告诉他我这个乡下人的意见:“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这点情绪促我来写作,不断的写作,没有厌倦,只因为我将在各个作品各种形式里,表现我对于这个道德的努力。人事能够燃起我感情的太多了,我的写作就是颂扬一切与我同在的人类美丽与智慧。……”(沈从文《篱下集·题记》)
然而时移世易,如今,抒情变得越来越虚伪,也很少再有作家愿意自称人道主义者了。
惭愧的是,笔者简陋,没能查找到“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这一说法的原始出处。我怀疑或许是来自汪老在一篇文章中说的“我觉得我受儒家思想影响更大一些”这句话——当然,根据《汪曾祺全集》出版前言(林斤澜整理)中的提示,1987年《北京文学》杂志召开的汪曾祺作品研讨会上,北大的几位年轻学者给汪老“定”了个“位”,大意是,汪曾祺“是士大夫文化熏陶出来的最后一位作家”,也许这就是“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的最初形态。——但是,在《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一文中,汪曾祺先生接下来一句的补充却明白地说:“我所说的‘儒家’是曾子式的儒家,一种顺乎自然,超功利的潇洒的人生态度。”
这里,汪曾祺先生说的曾子显然不可能是“日三省乎己”的曾参,他持身过于谨严,而应该是孔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的曾皙。事见《论语·先进》,“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
有一天,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陪孔子坐着。夫子让四个学生各言自己的志向,于是曾皙就说出了那句儒门历史上最为著名的话:“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听后,也被曾皙的这种潇洒胸襟所感染,喟然感叹:“这也是我的理想啊!”
然而,曾皙的这句话哪里是一个严格的士大夫的志向呢,只不过是士大夫的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罢了,所以孔老夫子才会喟然而叹。因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真正的士大夫要以天下为己任,是不可能有这份闲情逸致的。而“春服既成”一句公案,也就成了儒学历史上一支旁逸斜出的奇葩,固然美丽,实属空花。
或许只要读读汪曾祺先生撰写的回忆西南联大生活的系列文章即可明了,即使写跑日本飞机的警报,写联大教授的遭遇,汪曾祺先生也几乎无一语及国仇家难,更不会金刚怒目、苦大仇深,而始终对这世界抱着一种温柔的同情与善意。这实在是因为汪老具有一种极其强悍的能力,即使再苦难的生活,他也能从中发现出可亲可爱、美好温暖的面向来。
还是再引用汪曾祺先生的一段自我剖析吧:
作家就是生产感情的,就是用感情去影响别人的。……有的人曾提出,说我的作品不足之处是没有对这个世界进行拷问。我说,我不想对世界进行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严峻的拷问;我也不想对世界发出像卡夫卡那样的阴冷的怀疑。我对这个世界的感觉是比较温暖的。就是应该给人们以希望,而不是绝望。我的作品没有那种崇高的、悲壮的效果。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社会性·小说技巧》)
可见,如果汪曾祺先生在世,他老人家大概是绝对不会接受“最后一个士大夫”这顶高帽子的。我们为什么不能撕掉那些让人目眩的标签,为什么不能热爱一个真实的、活在平凡百姓中间的汪曾祺呢?
前不久,为纪念汪曾祺先生诞辰100周年,凤凰含章裒辑出版了这套《汪曾祺小说散文精选集》,共五册,含散文四(《人间食事》《人间草木》《人间有味》《人间有趣》)、小说一(《人间小暖》),以“人间”而总其纲,我猜测,其命名初衷,大概也是来源于那句“人间送小温”吧。先生百年,余温尚存人间,真好。
十六世纪法国伟大的人文主义作家蒙田说:“依我看,最美丽的人生是以平凡的人性作为楷模,有条有理,不求奇迹,不思荒诞。”(蒙田《论阅历》)用这句话来给汪曾祺先生其人其文作脚注,应当是恰如其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