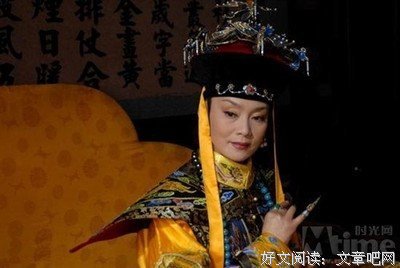
《我所知道的慈禧太后》是一本由叶赫那拉・根正著作,金城出版社出版的BBC书籍图书,本书定价:28.00元,页数:24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我所知道的慈禧太后》精选点评:
●作为一个中立者,我觉得可能口述者和慈禧的关系,他对慈禧的评价总是高于外界。不过抱着中立的角度看,这本书真的让我或直接或间接知道中国近代100+年的事。
●高中的时候读过,标题很吸引人。内容实则非常平淡。。。
●虽然她距离我们的历史并不长,但似乎越是传奇的人物就有越多的谜。我读过不少慈禧的传记,但这本格外不同,可能也是因为作者与慈禧太后毕竟还有些许亲缘关系,其中的叙述比史书更富有人情味,有血有肉、爱恨分明。我们当然无法裁定一直以来史书作为男权社会的产物是不是给站在权力巅峰碾压他们的女性许多恶意的揣测。但不可否认的是,从“牝鸡司晨"这个颇具贬义的词语就能看出,这种女性是不可能被后世公正对待的。我们也不能确定这本书就不偏不倚,但它确实给了读者另外一个角度思考,这就很难得。
●叶赫那拉氏眼中的慈禧。
●多多少少有些不客观吧
●来自慈禧后人的逆袭!!!噗哈哈~
●何必带着有色眼镜看人呢? 已经故去的就让个人保存自己想法吧~~~是黑是白已经不重要了,谁都无法改变历史!~~不要把自己的无能和懦弱归罪于一个女人!
●时间真是太久了,曾孙的口述也只是道听途说而已,历史资料不是很详尽,闪亮点不多
●确实不客观
●听的算不算,姑且mar一个
《我所知道的慈禧太后》读后感(一):有得有失之口述历史
这几年里口述历史类书出的着实不少,不少,真是不少,这种从个人角度出发,或写人或写事的书出了很多,有大人物身边的工作人员,比如<<宫女谈往录>><<待卫官杂记>>,也有不少异域见闻录,比如前几年某出版社出了一批清未、民国来中国的见闻录,这些业余作者或工作原因,传道的、当记者的、或生活原因,主要是外交官夫人们,于中国的所见所闻,当然,业余记者么,不能要求太多,有些甚至就是书信集,有些篇章真的没法要求什么文笔。内容也一如我们看外国,充满各种不可思异,这么说吧,比如有些书中写的北京,令俺这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看了如云里雾里,不知其所言何处。何谓其然,因为我们都是在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呐。所以当初那谁说开眼看世界,说的多好啊,说实话,到今天,我们也没完全做到这点哪,看什么都还是从自己的主观想法出发,不光是看世界啊。
比如你看这本书吧(众出了一口长气,这货终于说回来了),个人从自身主观情况出发,了解点儿清史,也看过<<宫女谈往录>>,看这本书基本无阻碍,就是踩着巨人的肩膀够苹果那种(众,这货怎么说什么都能说那么俗呢)。当然了,这本书客观上也是那种简单易读的口水体,以个人口述的语气,如夏天晚饭后大家伙拿着小板凳在胡同口乘凉聊天儿串闲话儿一般,娓娓道来,老妪都解。虽然这书上有些内容让个人主观有点子想呵呵,比如作者说道光是服毒自杀的,我大汗。除了这个,其它那些如慈禧出生地大讨论、慈禧与娘家人的感情,和珍妃那点事儿等等,大部分个人在其它资料或书里见过,几相对照,基本都同意的,当然了,书本身内容也不多,个人看的是TXT的,整体内容比较轻松,坐公交车上看也行, 刷碗的时候听也行,个人就是有一半在车上看完的。那位说你语文老师没教你要扣题吗,你题里说那得啊失的,说什么呢,其实这本书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这类口述历史,得者,可做正史之补充,失么,您也看见了,有些作者的一家之言还是挺惊人的。
《我所知道的慈禧太后》读后感(二):另一种慈禧
“报复敌人的最好方法,就是比他活得更长。”这句话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安慰,它可以治疗心理不平衡,也可以让打算铤而走险的人,接受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现实,很适合这个稳定压倒一切的时代。不过,就像好人不一定有好报一样,活得长的人也很可能是仇人,我们不想承认这个让人不爽的现实,又不得不承认现实常常就这样不爽。换句话说,我们不大愿意让坏人活得太好,如果坏人活得不错,又有几个有点说嘴的后代,这个现实就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了。
一直想写一篇恭亲王与咸丰的文章,所以看到可能有点关系的书,就忍不住想买过来看看,包括叶赫那拉·根正的<我所知道的慈禧太后>。书商的包装说,“从历史上看,慈禧在人们心目中一直是一个心胸狭窄、卖国求荣的娇奢太后;而从家族来看,慈禧则是一个有血有肉、孝道先行的封建女人。本书从一个侧面讲述了生活中的慈禧,入情入理。对现代读者来说,这对于认识一个真正的慈禧是不可多得的”。书中也确实写了不少慈禧的小事,试图证明慈禧并不是坏人,她也有不得不那么做的苦衷。
我看了之后,除了觉得这一家人的无耻之外,没有半点别的感觉。因为坏人不是写在脸上的,而且坏人也没有几个人认为自己是坏人,比如臭名昭著的李真,被关进看守所后就很恐惧,因为自己“跟8个坏人住一间”。所以,仅仅以她对身边几个人的小恩小德,或者渲染她个人的苦处,只是一种避重就轻的伎俩,并不能说明什么。历史已经过去很久,慈禧的旧账用不着再翻了,这时以“人性化”的写法还原“真正的慈禧”,虽然用心良苦,但这样的真实还是离真正的慈禧太远。<我所知道的慈禧太后>显然很想替慈禧涂脂抹粉,可是除了几件小的不能再小的小恩小德,大事上几乎没有一件。
坏的祖先也是祖先,在作者个人来说,这种出发点没有错。但是历史毕竟是历史,想抹杀是抹杀不了的。和这个根正一样,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严嵩的后人也想给严嵩翻案,甚至买通了江西社科院的人出来作证,说严嵩多么聪明,书法很好,也做了不少好事等等,很像那么回事。可惜的是,聪明或者书法很好,并不能证明就是好人,而坏人偶然也会做几件好事,只是使他不至于过早倒台而已,同样不能证明他其实是好人,所以最后也不了了之了,严嵩还是白脸奸相的面目。
《我所知道的慈禧太后》读后感(三):一部试图洗白的书
那根正先生的这部口述历史,意图很明显,就是为他的祖辈慈禧老太后洗白。整本书试图通过自己作为“叶赫那拉氏家族的内部人士”所了解的史料,为读者呈现一个不一样的“真实的慈禧太后”。从可读性来说,这本书写得还是不错的。里面所描述的故事,也有一定的吸引力。按照作者的叙述,慈禧太后是一位虽然贪恋权利的老太太,可是同时也是一位有有血有肉有爱有恨的女性。但是,我读完这本书后,并不觉得作者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反而觉得作者的叙述有明显的偏向性。尤其是在史料的选取上(包括各种相关人士的回忆、清宫档案等),并不是中立的,而是明显的选用那些对慈禧的形象有利的叙述。尤其是以下几点,足见作者在写作时的偏向性。
(1)关于光绪帝之死
根正先生在这本书内,提到光绪帝死因的时候,言之凿凿地说,光绪皇帝不可能是被害死的,他肯定是自己病死的。然后引述了各种材料(包括清宫的太医留下的诊断记录)来证明:光绪皇帝早就病入膏肓,所以死是时间问题。只不过,太过凑巧,恰好和慈禧太后死在同一时间。首先,清宫的记录有多少可信度就是存疑的。慈禧完全可以更改任何记录和档案,甚至不用更改,直接按照慈禧的要求写档案就可以了。第二,作者把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几乎同一时间去世,解读为一种巧合。那这个“巧合”的概率也太低了,低到无法让人信服。更重要的是,在2008年11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在北京举行了光绪帝死因研究报告会。2017年,《清光绪帝死因鉴证》一书也得以出版。现代历史学家通过现代技术手段得出了可靠的结论:光绪皇帝是砒霜中毒致死。虽然究竟是谁下的毒还有疑问,但是作者所述“光绪帝是病死的”已经被现代技术手段得出的结论直接否定了。
(2)关于珍妃之死
按照本书的描述,珍妃之所以死,是因为慈禧太后的一句气话“你说要死,那你就去死吧”,然后性格刚烈的珍妃就直接投井死了。这段内容,全部出自隆裕皇太后对作者的爷爷的口述。关于隆裕太后的为人,我不想评述。我也确实认为隆裕是一个历史的牺牲品,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但是作者在书中试图说明这样一件事情:慈禧太后在珍妃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轻时候的影子,所以喜欢珍妃。然而这一点实在是太主观了。首先,如果慈禧真的在珍妃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轻时候的影子,我想她的第一反应绝不会是去喜欢珍妃,而是把珍妃看作一个自己权力的威胁。第二,作者在书中并不否认慈禧打过珍妃,还把珍妃降级成贵人。那么这与“喜欢珍妃”不就矛盾了吗?作者自圆其说的方式是:珍妃喜欢照相,但是老太后不喜欢。老太后是后来才明白照相是怎么回事,才拍了那么多照片的。但是珍妃喜欢拍照的时候,老太后把这当作邪门歪道。那这还是说明老太后不可能喜欢珍妃。
(3)关于庚子事变
慈禧太后在历史上对中华民族造成的最大危害,就是庚子国难。甲午战争结束之后,中国已经元气大伤。可是没过几年,由于慈禧本人的任性,怼天怼地,向全世界宣战,已经羸弱不堪的中国又面临了庚子事变这么一场大浩劫。慈禧倒是好,溜之大吉。可是苦了老百姓,那么多赔款最后还不是从老百姓的血汗钱里掏。反正慈禧还是继续锦衣玉食的过完了人生的最后几年。恐怕作者本人也发现这件事情,实在是没得洗、无法洗、无从洗起,所以全书对于庚子事变慈禧太后的心态,和慈禧太后向全世界宣战的动机,是只字未提。其实作为一个对晚清历史很感兴趣的读者,在读这本书之前,我是很希望能知道一些关于慈禧在庚子事变期间的心态的事情。但是作者除了描述了一些慈禧在逃难过程的小事,完全没有提到这方面的事情。当然,也有可能是,只要提了这件事情,就和本书“洗白慈禧”(或者换个词,“改善大众心中慈禧的形象”)目的不相符,所以干脆不提。
当然,这本书也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也有很多观点我是认同的。比如,书中说,慈禧并不是一个顽固守旧的老太太,反而是一个勇于改革的政治家。对于这一观点,我还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认同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慈禧太后在那么多反对的声音中,敢于大胆的重用一批汉臣,大胆的开启洋务运动,足以说明她绝不是一个固步自封的顽固老太太。慈禧太后的治理,对于后来的所谓“同光中兴”起到了比较积极的作用。而且,在光绪帝试图进行戊戌变法的初期,慈禧太后对戊戌变法的大部分政策是支持的,这一点我也是相信的。没有慈禧太后的首肯,像《明定国是》这样的诏书不太可能颁发出去。只不过后来历史的走向让人叹息,戊戌变法莫名就走到了“围园捉后”的境地,光绪帝可能也大感意外。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来自作者的爷爷对作者讲的故事。作者的爷爷是隆裕太后的弟弟,是慈禧太后的侄子。所以作者从爷爷那里听来的关于慈禧的故事,的确是有一些价值的。历史本来就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所以每个人说出来的历史,都是基于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立场、自己的利益说出来的。历史的真相很多时候无从得知。但是,如果我们尽可能多的听到不同的人(不同的立场、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阶级)对历史的描述,看到各种版本的“被人打扮过的小姑娘”,也许我们离历史的真相就更近了一些。
《我所知道的慈禧太后》读后感(四):那根正先世考查(转帖)待考证
《中国档案报》“档案大观”2004年7月2日一版以“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慈禧”,副标题“近访慈禧的曾孙叶赫那拉·根正”;9月17日一版以“颐和园的金字招牌”,副标题“近访叶赫那拉·根正先生”;2005年2月28日《北京日报》副刊15版以“慈禧曾孙的传奇收藏”介绍了颐和园的那根正。
慈禧皇太后为中国妇蔚皆知的历史人物,他的儿子是同治皇。光绪皇帝为其妹所生,为子侄辈。末帝溥仪作为孙辈。慈禧太后是没有曾孙的。
我在1984年2月28日走访溥偀之子金良,3月20日拜访溥偀之妻叶希贤,她就是承恩公桂祥的后人。
我把相关考查等内容,分述如下,以飨师友。
一、纳兰性德后裔
2005年1月金城出版社出版那根正著《我所知道的慈禧太后》,自报家门“纳兰性德九世孙”。
海淀上庄有纳兰性德纪念馆,北京还有纳兰性德网站,承德有纳兰性德研究会,惟独没听说有纳兰性德后裔的线索。海淀上庄的大学士明珠墓“年代久远,又无后人扫墓”①。赵迅先生《纳兰成德家族墓志通考》第76页“有关纳兰成德家族的一些问题”提到上世纪30年代初,张任政编篡《纳兰性德年谱》,专访纳兰家族后裔,“有名锟钰者,先生之后裔也,前数年卒。有子一,年甫壮,飘沦无室家。初依其族伯,族伯亦贫甚,不堪久依。今且执挽夫之役,贾劳力以自为活,短衣黧面,奔走于通衢间。"
《辽海丛书·雪屐寻碑录》卷十三有两通纳兰性德长子富格的碑文。乾隆二年岁次丁巳仲秋上浣谷旦立“皇清浩赠光禄大夫提督直隶总兵官都督同知管辖通省兵丁节制各镇富公神道碑”,碑文长达1497字。富格墓地在“海淀以南双榆树之阡”。1989年4月7日下午2时,我与首都图书馆韩朴兄有约定拜访王佐贤先生。我上午9时半就到了双榆树北里,打听富格墓地沿革。到第三师范学校、海淀镇都打听不到。我穿过中国人民大学,到万全庄找到了几位老人。那文海(1939年生)、刘宾(1917年生)告之友谊宾馆旧址为富格墓地,因墓主后人为广忠,又称广大人坟。最后占地8亩,界桩为“叶赫纳兰氏茔地”。又请王宝禄同志问了他家老太太,得知广大人宅在西四帅府胡同(今名西四北二条)。
1989年4月8日上午,我去西四北二条拜访了叶宅王秀衡(女,1914年6月9日出生),北京人,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小学教员。她说叶广忠(1833年~1904年)官正一品,九门提督。叶广忠续弦史氏,北京人,1866年8月24日生,1952年去世。叶广忠第二子叶常敬,字正斋,1899年7月26日生,第一中学毕业,小学教员,1948年11月19日去世。叶广忠第三子叶常续,字绍先,1901年11月26日生,体育学校毕业,育英中学教员,1972年卒。叶常敬、叶常续二人都会武术,都是体育老师。王秀衡老师作为叶广忠的儿媳,不知道叶宅旧事。她说广大人宅老门牌36、37号,有40余间房。37号有门匾“恩周武库”。
叶常敬、叶常续子女情况不赘述,他们没说是纳兰性德的子孙。
二、承恩公桂祥子孙
承恩公桂祥之子在《清史稿》第十八册第5342~5343页有记载,名德恒。第5339页桂祥兄照祥之子,名德善。排字辈:德。
桂祥兄弟三人:长照祥、二桂祥、三佛佑。下辈五人。桂祥长子德恒,大排行行二。桂祥二子德祺,大排行行五。
请看1915年2月《爱国白话报》的报道,标题为“桂公府丢失珍珠玉翠等物并不愿报案”。本月10日,朝阳门内南小街方家园前清公爵桂祥府内,于前日夜间被贼窃去帽正珍珠一颗,重八分;汉玉镯一对、翡翠朝珠一挂、琥珀朝珠一挂、珍珠数十颗并烟壶玉器等物。已呈报提署。奉江(朝宗)正堂谕,伤派两翼侦缉队三翼小队上紧拿贼等语。
该府管事人赵树村声称,报载本府失物,确有其事。所失各物,均在后院本府老姨太太屋内收藏,房屋门窗均无痕迹,知非外贼。而本房只有随使女仆三口,佣工多年,均系可靠,是以不愿报案。面见本主人,五爷德祺出见,所述与赵树村大致相同,并出名片一纸,恳请毋庸置议。
这时桂公府的主人系“五爷德祺”。
桂祥第一子德恒,字健亭,1934年卒。夫人英氏,1947年卒,51岁。二女一子。1945年住炒豆胡同27号,现12号,租给了中医门诊部。德恒长女德淑敏,现名叶燕生,1930年5月22日生,现在西安。子德恩贤,1931年7月27日生,1982年卒,葬于太子峪陵园。德恩贤有四女:德欣欣、德温温、德明明、德迎迎。德恒第二女德淑琴,现名叶华,1933年8月12日生,现在南京。
桂祥第二子德祺,字寿芝,1897年4月3日生。曾住棉花胡同25号,1936年搬到东四八条111号。曾任东四八条居委会主任。1975年卒。夫人佟玉英,1900年6月5日生。夫妇葬于八宝山人民公墓。
叶德祺第一子叶恩印,第二子叶恩显,女叶希贤,1921年生,夫溥偀,住右安门外凤凰咀58号。叶希贤二子二女,子金承、金良;女金兰、金明。叶德祺第三子叶恩民,1930年6月1日生,曾任局长,妻胡俊娥,一子一女。子叶力,女叶薇。叶德祺第四子叶恩植,1931年8月23日生。叶德祺第二女叶希嬿,1938年8月19日生。
承恩公桂祥三弟佛佑,一子德口,字文伯,以字行,1887年3月9日生,原住双辇胡同27号。叶文伯一子叶恩铨,1908年8月9日生。妻佟为霦,1909年3月5日生。叶恩铨在崇内孝顺胡同颐中烟草公司工作,住大取灯胡同1号公司宿舍。叶恩铨三女一子:长女龙仙,1933年5月18日生。二女龙缳,1939年11月1日生。三女龙媒,1947年4月6日生。子龙驊,1942年10月19日生。侄女龙厚,1939年4月11日生。侄龙驶,1941年7月29日生。侄龙驹,1947年1月4日生。
三、那根正祖父增锡
那根正祖父增锡“小的时候在贵胃学堂读书,考到保定陆军速成学堂读书”,“宫里当了御前侍卫”,到清河陆军学堂“去教书,一直做到校长的位子”②。我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研究员屈春海查增锡或那增锡,没有他的履历表。有关陆军第一预备学校是这样记载:“清末,清政府曾建立陆军中小学,作为培养陆军军官的预备学校。中华民国建立后,将陆军中小学停办,设于清河陆军第一中学改为陆军第一预备学校。学制2年,作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预备学校。1920年秋停办。校长毛继承,教育长钱选青。后钱选青任校长”③。
2005年3月20日《北京晚报》连载文章“傅作义是我爷爷的学生”提到“在抗日战争时期……傅作义就派人给我们家用卡车送来一些面粉。当时是50斤一袋,大概有上百袋。”从《中国国民党九千将领》第763页傅作义条记载,1912年傅作义进入北京清河镇陆军中学学习确凿。但抗日战争时期,傅作义不在华北,主要在绥远。先后参加山西忻口战役、绥南战役、包头袭击战、五原大捷。抗战胜利后,接收包头、归绥,并抢占集宁。1946年12月任命华北剿匪总司令,1947年进驻北平。傅作义抗战时在绥远,所以连载所述一百袋面粉,至少是误值。
2005年3月19日《北京晚报》连载文章,提到孙中山、黄兴与增锡会见,增锡“答应一定支持他们。所以孙中山在会后送了一管铜箫”。查《孙中山年谱》,辛亥革命之前,未见孙中山来京记载。第45页记述,1912年8月24日孙中山应袁世凯邀请,由上海抵京。
2005年3月26日《北京晚报》连载所附图片注为“爷爷和李鸿章”。这位爷爷并不是增锡,是醇贤亲王奕譞
颐和园的那根正我并不认识,也没有通读他的作品。我认为他是位收藏家,绝顶聪明,但应该多用功学习。2005年4月1日《北京晚报》连载文章,说“到了民国十五年(1926)的春天,李莲英忽然得了急性肺炎,最后也就死在这个病上”。不知那根正依据什么?李莲英生于道光二十八年十月十七日,易于宣统三年二月初四日,年六十有四④。李莲英兄弟六人,六弟早夭。大哥李国泰,二为李英泰(李莲英原名),三为李宝泰,四为李升泰,五为李世泰。李莲英过继四子:福庆(成武)、福德、福康、福荫。不是连载说的两个。李莲英“购买了一所住宅”,实为李莲英三弟李宝泰购买棉花胡同宅。
2005在4月5日《北京晚报》连载附有桂祥夫妇像,补服图案不对,一品鹤头向右,五品白鹇头才向左。2005年4月1日连载图片注为“溥仪和身边的人”,什么叫“身边的人”?他们均为溥仪的弟弟和妹妹。这张图片见单士元先生编著《小朝廷时代的溥仪》第73页图40,在天津张园,有详细说明。2005年2月28日《北京日报》15版“慈禧曾孙的传奇收藏”下图“慈禧写的寿字”图片左下写有“不入八分辅国公”,只能证明他是收藏,不是家传。
2005年4月5日《北京晚报》连载“一只碗差点让我爷爷休妻”。提到“据说当时有人出2000块大洋,托人非要买不可”摔坏的碗。日伪时期,20块大洋可以去日本一个来回。不值2000块大洋。道光官窑现值几十万元。
注释:
①《海淀文史选编》第五辑,1992年6月于岱岩先生“关于纳兰性德墓的一些情况”第297页。
②2005年3月19日《北京晚报》23版连载“从国舅到平民”。
③《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上册第343页。
④《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3期第55页。
转自《北京档案史料》 作者:冯其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