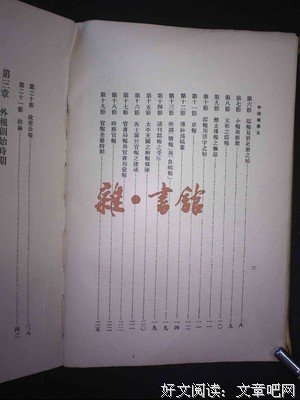
《中国报学史》是一本由戈公振著著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0.00,页数:24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报学史》精选点评:
●近代中国新闻发迹史,总括中带有细致之处,颇有历史价值。ps:当前面看到“戈公振一直想把此书翻译成白话文”的时候,我的内心是崩溃的。
●看到是民国16年商务印书馆那版。所谓报学,把从排版印刷到发行各个环节都包括了
●很有历史感的一本书 学新闻的学生都应该好好看一遍 哪怕看不懂(是的我没怎么看懂)结合知网论文和网上的感悟是能勉强读读完的 作者态度严谨求实 资料丰富翔实 虽然书中有156处错误 但仍是本好书 由衷钦佩戈公振先生
●不愧为中国报史研究的开山之作。有史有论,有理有据。面对中国千年之变局,给出了知识分子的思考。
●简略,旧派。
●新闻学必读书目
●2010.3.30
●全书共六章,第一章绪论,剩余五章按时间和类别依次划分为“官报独占时期 ”、“外报创始时期 ”、“民报勃兴时期”、“报纸营业时期 ”, 详细全面的梳理了从汉唐到1926年以前中国报纸和报业的状况,最早为中国报业的发展断代,也是中国报学和新闻史研究的开山之作。
●啊其实这书挺好的,但是本科毕业时被我以4块5的价格卖给一个外国留学生了……
●我仿佛看了到戈公振先生着长衫与青灯下研读老报的场景。。
《中国报学史》读后感(一):读得吃力
距戈公振先生离世已近80年,中华之社会早是沧海桑田,报纸也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变迁。如今,大多报纸与媒体或许再也无法如上个世纪20、30年代那般针砭时弊,一针见血。那曾抵过三千毛瑟枪的纸墨,终究怕也是折戟沉沙再无铿锵之势。
如此,回望往昔,尤觉珍贵。
《中国报学史》读后感(二):拓荒者
何为拓荒者?开拓疆土,前不见古人。甘做牛马,为后世铺路。全书看完,其研究方法和脉络可见明显的生硬和“原生态”,但一翻出版时间,不禁咋舌。20世纪20年代,有此著作,乃为中国报学史之福。其中,某些观点放置在现今,都能够适用。如报业经营的困惑,如报纸在资本属性和社会属性之间的博弈,如资本与舆论之间的关系等等。
《中国报学史》读后感(三):新闻史开山之作
《中国报学史》作为新闻史学的开山之作,构建了新闻史学的研究框架,也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史料,为以后的新闻史研究做出巨大贡献。就全书来说,有很多观点在今天仍然值得借鉴。
比如,对报纸特点的分析,戈公振先生从外部和内部对报纸的特点进行了分析。从外部形态来说,报纸具有公告性和定期性,从内容上来说,报纸具有时宜性和一般性。
在分析“定期性”时,戈先生谈到,报纸的定期性受到交通状况的影响。
关于“时宜性”,戈先生认为,“故现实性之于报纸,尤维持生命之血,舍此更无他物者”。虽然看到了时宜性的重要性,但对报纸来说,却把“时宜”放在了过于重要的位置,“真实”应该是新闻最基本的要求,是“维持生命之血”。在这一章节中,戈先生还分析了新闻失实的原因,认为新闻失实分为自然和人为两种。“自然之过,为新闻之机械化”,按作者的分析,即只“将新闻照所得者报告,并不加以思索”,“人为之过,则捏造事实”。
关于“一般性”,戈先生认为,一般性要求报纸内容齐全,书中列举了当时因内容专业化而停刊的报纸。对报纸做此要求在当时还能行得通,但反观当今社会,在信息洪流的冲击下,“得小众者仍能得天下”,很多报纸正是因专业化而获得了生存空间。
戈先生虽然没有直接说明报纸的功用,但散见于各章节,均有总结性的文字。比如,对报纸文化功能的叙述,“自报章之文体行,遇事畅言,意无不尽。因印刷之进化,而传布愈易,因批判之风开,而真理乃愈见。”对报纸舆论功能的叙述,“武昌举义,全国景从,报纸鼓吹之功,不可没也。”戈先生批判了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时期的报纸,指责其没有发挥舆论引导之作用,认为“若当袁氏蓄意破坏共和之时,各报即一致举发,则筹安会中人或不敢为国体文体之尝试,是以后纷乱,可以不作。”此外,还批判了报纸在外交,社会文化方面的失职。
当然,作为开山之作,由于时代,观点,视野所限,不免带有缺憾。
如方汉奇教授所言,“任何学术专史著作,应以时为经,以其发展为纬。戈氏强分中国新闻事业为官报独占时期,外报创始时期,民报勃兴时期,民国成立以后,报界之现状等立章,实属武断,与发展史实多所不合。”的确如此,戈公振先生在对中国报业进行分期时,侧重于以报纸类型来叙述,忽视了每个时间段报界的典型特征。比如民报勃兴时期,维新派报刊和革命派报刊,辛亥革命时期的报刊的特征明显不同,两次报业高潮可以作很好的区分。又比如民国成立以后,民国初年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时期,五四时期又可作很好区分。方汉奇教授的《中国新闻事业史》则按历史发展,以每个时期新闻界的不同特征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做了细致的区分。
又如李彬教授在《对新闻史研究方法的思考与建议》中所言,以往的研究形成了所谓的戈学及其范式,注重微观的记载,却没有呈现整体特征。此外,历史不仅是关于事件的学说,也是人的学说,在《中国报学史》中,关于报纸的罗列占了很大篇幅,缺乏了鲜活的报人,也缺少了对报纸和报人的客观评价。
这些都是缺憾所在。但总而言之,作为开山之作,戈公振先生的《中国报学史》,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报学史》读后感(四):行走在风口之上——报业的《史记》
风口,一方面因其是探索“风”的最佳窗口引得无数好奇者前来探索,另一方面因其系危险之在所在,靠之太近易化为齑粉,令人望而止步,然若求科学之真理,社会之进步,不得不行走在风口之上,戈公振先生的大作《中国报学史》正是如此。自《中国报学史》(以下简称《报史》)出版之日起,赞誉之声不绝于耳,有人说:戈公振在中国新闻史研究领域作了开创性工作,首次确立报刊史的研究是一门学问,并为后人的继续深入研究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和重要线索;也有人说:《报史》作为文化范畴的第一部报刊史专著,也是研究中国文化思想史的一部重要参考书。随着史料的日渐丰富,认识能力的日渐提高,学界对《报史》的价值与历史地位有了新的认识,学界普遍对这部开山之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对其史料之详实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是也要看到由于社会条件和作者能力所限,书中的某些理论今天看来已经过时,书中的某些史料也存在着明显的错误。全书分“绪论”、“官报独占时期”、“外报创始时期”、“民报勃兴时期”、“民国成立以后”、“报界之现状”六章,把从汉唐到“五四”前的中国报刊产生发展的概貌,清晰地勾勒了出来,对全面系统研究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史及客观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下文我将浅谈戈氏的报业思想以及我的所思所想。
首先谈一下戈氏的报业思想。他极为重视报纸的社会作用,“盖报纸者,人类思想交通之媒介也”,一面它是社会机体的血液,有沟通信息,加强交流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又是民意之机关、舆论之阵地。这些认识如今看来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在那个年代无疑是新奇的。
他认为报纸有四大特点:一是公告性,即公而告之;二是定期性,定期发行;三是内容的时宜性;四是内容的一般性。没用“时间性”而用“时宜性”,他认为现在发生事件的新闻价值是必然的,但是从受众角度而言,能引起他们兴趣的新闻价值不必局限于现在发生的事件。这里面涉及到了新闻价值,传、受双方的共同认可是新闻价值理念得以产生的前提。只被一方认为有价值的新闻,交流中没有被对方接受或得到回应,这个新闻对另一方来说是没有价值的。报纸内容的一般性主要是指内容的多样性,有政治、经济、文艺、社会、体育等方面,这样才能对更多的受众产生新闻价值,获得更多读者的阅读兴趣。今天看来这个理论显然有点“不合时宜”,随着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传播方式更加多样化,传播更加便捷化,人们不再希望通过报纸去了解综合性的新闻,同时受众的需求也在变化,经济地位、文化状况、生活观念、消费观念、价值观等的不同导致人们形成不同的阅读兴趣,而综合性报纸难以满足如此专业的受众需求,于是专门化报纸应运而生。这点戈氏恐怕没有想到。
戈氏认为报纸要想获得良性发展,就要避免陷入政治的漩涡,努力求得报馆经济的独立,这样报纸的言论才能公而无私。如今我国党报转型也是兼顾事业性和产业性,既要为人民服务,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引导社会舆论,塑造良好社会风尚,又要得到受众支持,扩大发行量,求得生存。如若中国报纸一直沿用戈氏此思想何至于党报转型如此困难。
下面我将谈一下戈氏基于史料之上的某些论断以及我由此而得的某些体会。也许可以说《报史》是报学界的《史记》,他的判断和评价往往一语中的,这点颇似《史记》每篇结尾处太史公的点评。
戈氏认为中国古代报业发展缓慢的原因是官报畸形发展,民报萎缩退步。他从思想文化角度立论,认为“与民阅,不与官阅”现象与儒教文化的“民可使由,不可使知”的愚民性有关,统治者利用儒家文化(即社会正统)钳制人们的思想,限制信息的交流与传播。中国古代社会传播是一种金字塔式的传播,社会传播受控于最高权力者皇帝,信息高度集中于上一级,然后从上至下信息拥有量层层递减,而且同层之间的传播是不被允许的,处于被防控、监视、堵塞的境地。这样的传播模式无疑不利于信息的自由流通,这大大限制中国古代报业的发展。
戈氏认为外国报纸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一方面西学流入中国,使国人能够开眼看世界;另一方面,补中国旧学的不足,尤其是一些汉学家致力于研究我国经籍,贯串考核,见解不凡。戈氏的认识着眼于宏观,有从微观角度入手者也许会认为东西方文化交流之始,就存在着西方文化侵略,宣扬西方资本主义腐朽价值观念的现象。对此,我想谈一点我的看法,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是牢固的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这是大前提。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十里洋场的大上海歌舞升平,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大行其道,这都与上海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有关。建国后广大人民尚不能解决温饱大事,哪谈得上享乐、拜金。文化的交流也并非全盘接受,而是有选择的,这是人主观能动性的重要体现,某些不适合国情、民族心理、习俗观念的文化是不能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上生根发芽的。文化有自滤功能,在跨文化对话中,由于文化传统、社会环境、审美习惯等的不同,接受主体会有意无意的对交流信息进行选择、变形、改造、创新,从而造成交流信息在内容和形式等方面发生变异。对于当代中国涌现的某些不良社会风尚,我们要相信随着国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人有足够的辨别能力;我们更要相信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有能力剔除某些消极、不健康的思想观念。
戈氏认为民国以来人民阅读习惯的养成,使得国民对社会国家观念理解日深。其实这种公民意识是近代宪政的产物,它有两层含义,当民众直接面对政府权力运作时,他们有权对其监督;当民众侧身于公共领域时,它是对自身利益的维护与认可。中国古代社会没有产生公民意识的可能,这是因为那样的社会结构中只有政治生活和家庭私人生活两极,两者之间没有一个既独立于庙堂又独立于家庭的公共性中间地带。西汉以来,国家意识形态儒教规定“三纲五常”,“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是一垂直隶属系统,“仁、义、礼、智、信”是一横向交往系统,两者交织的是独立的片面义务观。国民没有现代国家意识,故有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咏叹,有的更多的是夷夏之分,这也是中华文化保守性的一大体现,改朝换代老百姓早已司空见惯,好歹还可以继续作顺民;外夷入侵,则以死相抗,因为草原民族会将他们的耕地变为牧场。传统中国更注重的是家庭观念,及由此而形成的家族观念,只有科举取士才能光耀门楣,做官后一定要衣锦还乡,富贵后不可衣锦夜行,于是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整个儒家政治、社会视野中,始终不见独立于家庭结构和国家结构之间的公共地带,这是儒家学说最为令人不安的重大缺陷。
《中国报学史》读后感(五):何为“拓荒者”
何为“拓荒者”
——《中国报学史》读书心得
初闻吴老师提及戈公振先生撰写的《中国报学史》之地位,以及与方汉奇先生《中国近代报刊史》之联系,遥想硕士时期,囫囵吞枣读完此书,觉如教科书般,仅供我新闻学子研究查阅之用。而今再读戈公振先生的《中国报学史》,较之于硕士课堂,融合了从业经验,跨越了硕士学习,对于其内容的理解已经不局限于“教科书”和如“报学字典”类工具书,而是从书中体会戈公振先生的思想理念、研究方法、新闻观点、社会责任等,并站在当下,对于此书在当时社会背景下所进行的,针对研究方法和写作手法等问题产生了深入研究的兴趣。
戈公振先生是我国近代著名爱国记者,新闻史学家、新闻教育家。其被称之为“中国新闻业史研究的拓荒者”。何为“拓荒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人。《中国报学史》就是奠定其成为拓荒者的一部著作。作为我国第一部报刊史研究专著,《中国报学史》开创了我国新闻史研究的新时期,也代表着旧中国报刊史研究的最高学术水平。在此之前,我国学术界的新闻史研究主要以地方报刊史的研究为主。如《武汉新闻史》、《浙江新闻史》等等。此书的出版,系统的研究了当时中国报刊的历史和发展脉络,具有极高的价值。人们对于此书的第一印象,也如笔者一样,在于其资料性。该书第一次把从汉唐到五四运动前的中国报刊产生、发展的概貌,清晰地勾勒出来,搜集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为后人的继续深入研究开辟了道路,并为文化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而笔者此次更加重视的,是此书的思想性。无论从书写帝国主义外来侵略者对于我国进步新闻工作者的发动政策,还是其揭示了邸报的实质,以及评价全国各地的进步报刊等等方面,该著作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敢于正视历史,站在报刊发展的角度,客观、公正的评价,实属不易。
那么,如何成为“拓荒者”呢?除了“资料性”和“思想性”之外,使该著作成为“拓荒者”的,是研究新闻事业史过程中创新的分类报刊的方式。在此之前的研究中,许多的研究者通常把报纸的发展历史按照报纸的形成方式,将其分成“口头报纸”、“手写报纸”和“印刷报纸”三个阶段,突出科技进步性特征。而戈公振先生虽然赞成这一类型的分类方式,但在其自己的著作中,他将中国报刊史按照报纸的权属又分成“官报独占”、“外报创始”、“民报勃兴”、“报纸营业”四个时期。这种以传播的技术形式具体转化为按报纸所有体制和经营性质进行划分的方法,就更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显然是一大进步。戈公振先生站在价值链更高的一端对报纸的研究进行分类,可以看出其知识的渊博,对现今我们的研究框架的搭建都具有可借鉴的意义。而对于戈公振的这种分类方式,国内的一些学者也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这样的分期,仍然是在抹杀报纸作为阶极斗争的武器的基础上进行的”。报纸的本质是阶级斗争还是服务社会?就现代民主政治来说,答案不言而喻。但另一类学术探讨的声音,如方汉奇教授所言,“任何学术专史著作,应以时为经,以其发展为纬。戈氏强分中国新闻事业为官报独占时期,外报创始时期,民报勃兴时期,民国成立以后,报界之现状等立章,实属武断,与发展史实多所不合。”的确如此,戈公振先生在对中国报业进行分期时,侧重于以报纸类型来叙述,忽视了每个时间段报界的典型特征。比如民报勃兴时期,维新派报刊和革命派报刊,辛亥革命时期的报刊的特征明显不同,两次报业高潮可以作很好的区分。又比如民国成立以后,民国初年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时期,五四时期又可作很好区分。方汉奇教授的《中国新闻事业史》则按历史发展,以每个时期新闻界的不同特征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做了细致的区分。
此书对于新闻观点和研究视野的创新更坚固了其“拓荒者”的地位。对于上述报纸服务社会的职能在定义报纸时就有表述。其运用邸报,以小见大而强调了报纸要为受众服务,从而定义报纸为“报纸者,报告新闻,揭载评论,定期为公众而刊行者也”,突出报纸的服务功能。其研究视野充分结合了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特点:“其要点在研究其对于某特别时代之特定社会之文化所发生而反应之各种特色”,并不局限于报纸本身,而归根朔源的探讨报纸的本源及原质,“社会文化史”的方法也启发了后人对于新闻史学的研究。
距戈公振先生离世已80余年,纵观戈公振近20年的新闻实践,无论是从事报纸编辑,还是从事新闻采访、新闻教育研究,戈公振其强烈的社会责任也是他成为“拓荒者”,做成如此著作,获得如此荣誉的必要条件之一。在本书自序中,戈公振先生力言著此书和提倡报学的原因:“以记者为职业,在我国有时实较他国为难。……而就记者自身言之,亦多不明了其责任之所在,而思有以引起人之尊重者。欲除此弊,非提倡报学不可。”这正是戈公振研究报学和报学史的初衷。在对当时中国报业的种种病态的情况下,本书批评道:“从社会思想方面观,各种学说,纷纭杂错,目迷五色论其学理,无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然其果适合于我国国情否,果适用于我国今日之人否,是尚不能无所踌躇。身为记者,于此应先下一番研究功夫,以徐待事实之证明,若根据捕风捉影之谈,人云亦云,漫为鼓吹相攻击,其不为通人所齿冷也几希。从科学方面观,可谓最最无贡献。……今日之报纸,惟搜求不近人情之新奇事物,以博无知读者之一笑。其幼稚诚不堪言矣。”戈公振先生的社会责任感主要体现在其强烈的救国图强爱国主义精神上。无论是在日内瓦以《时报》主笔身份发问当时的英国首相张伯伦,还是淞沪战争时期发表的《中国著作者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以及在之后的东北调查中舍身忘我的精神,都为戈公振先生在日后创作此书过程中所遵循的立场和正确的观点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精神财富。
“拓荒者”,也意味着为他人之不可为,意味着与过去思想的对抗以及与现在思想的改良。戈公振先生的新闻观点和爱国主义精神放置在现实的语境下,也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首先,是爱国主义精神。作为新闻人,爱国是最起码的职业要求。在日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日益发展的互联网科技技术下,舆论场的“最大变量”能否变成“最大增量”,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是其基本的保障。保持正确的价值观和媒体观念,培养正确的媒介素养,也是面对纷繁的舆论战中,保持不败的秘诀。其次,是对待研究的辩证思考。做一个“拓荒者”,必须要有值得“拓荒”的地方,有其创新点和支撑创新的理由。其研究的站位应更高,并注重研究的整体性。在历史研究中更应该注重其社会大环境的变化所造成的影响。再次是对新闻业务而言,必须要有服务社会的奉献精神。坚守底线、洁身自好是新闻人最起码的职业操守。近日,公安部就关停了近4000个微信自媒体“水军”。戈公振说,新闻记者是最有趣的自由职业,在国外尤其神圣不可侵犯,在社会上(国内)也是(拥有)“小人之中不算大,大人之中不算小”的地位。“惟其如此,与各方面容易发生关系,即在此际,须得认清我地位,要有不屈不挠,所谓‘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之精神”。
仔细看来,这部著作从现在来看,也有其遗憾之处。如李彬教授在《对新闻史研究方法的思考与建议》中所言“以往的研究形成了所谓的戈学及其范式,注重微观的记载,却没有呈现整体特征。此外,历史不仅是关于事件的学说,也是人的学说,在《中国报学史》中,关于报纸的罗列占了很大篇幅,缺乏了鲜活的报人,也缺少了对报纸和报人的客观评价。”这些都是缺憾所在。但总而言之,作为开山之作,戈公振先生的《中国报学史》,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育辰
2018.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