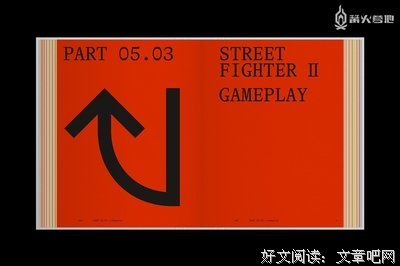
《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是一本由傅光明著作,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简裝本图书,本书定价:25.00元,页数:41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精选点评:
●我们都有意无意地过滤了历史,历史是唯一的,当然更是多样的,也许直达有一天。也许永远没有那一天。
●今天是老舍忌日,推荐大家看这本书,搜集了各种对老舍之死的口述资料:郝希如(北太平庄太平湖地区片警):早上6点接到电话,说湖里死了人……和太平湖养鱼场的韩文元驾着船,用竹竿把尸体拉到岸边,他怀里抱着一摞宣纸……上面写着老舍的名字……穿的是一件浅色的大褂……没有伤,衣着也整齐……太平湖里死过这么多人,印象中只有老舍是穿着长衫。
●与其说是探究老舍之死的真相不如说傅光明对口述历史方法论的阐述。他会让人觉得老舍之死的真相变得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去理解一些看似矛盾的事,然后跳出那个自己给自己设定的圈套,去发现那些不是真相的真相。对于同是梦想家的傅光明,必须保持敬意。
●吭哧吭哧一个月终于读完了。最后的注释竟然有1027个。严谨的躯壳中依旧有重复的解读和混乱的体系。
●也就前几章可以看看
●傅光明对较多涉及老舍之死的人物进行口述访谈,不同人的回忆构建起老舍之死的前因后果的分析,与其说这些碎片化的记忆本身可靠程度的有限性,不如反思正是这些个体化的记忆和记忆过程造成了口述历史独特性。
●这本书没被禁也是进步呢,看的过程中很吃惊,想起刘瑜说的一句话,我们比想象中更自由。这话是越来越觉得了。另外,这本书让我看到我的思维已定,不知下一次转变或推翻是几时,二十三岁有这样的思考,我还是蛮为自己骄傲的。
●很下工夫!
●老舍无疑是我最喜欢的近代作家,所以才会看到这本书。不论老舍自杀是为了抗争,还是因为绝望,抑或是对死亡美学的内在追求,我愿意相信这一定是他当时不得不做却又自然而然的选择。 这本书选择还原历史的方式是“口述史”,一方面几乎是最直接地未经加工的展现,另一方面却也因口述者之间的矛盾推断出“历史无法还原”的结论。关于“口述史”的概念在我也是第一次了解。 在“老舍之死”的背景下,当然也少不了对文革中知识分子际遇的梳理,这也是我看得最揪心的部分,时代已然,总有些人和事值得被铭记。
《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读后感(一):口述历史如同侦探小说
前些日子王朔出场,舒乙不知深浅地出来评论,被王朔骂了一顿。王朔问:老舍死的那天你干嘛去了?你在不在家?出来说清楚。王朔还说文联的人也都知道。听王朔这么一说,好像舒乙有什么不光彩的行为。
我正好看看到底是什么不光彩的行为。
这一看,才发现这本书真好。值得买回去看。
第一, 作者扎扎实实地考察了方方面面关于老舍之死的各种说法。发现,几乎每个人、几乎每个细节说得都不一样。比如,有三个人站出来说是自己把老舍打捞出来的。如果三个人说的都是实话,那就是老舍在同一时间和地点,被不同的三个人打捞出来三次。
第二, 作者进一步对口述历史的真实性等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很有启发性。比如关于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提议建立历史心理学的说法。
关于舒乙做了什么,书里没有明确说。但是书里一种说法是前一天老舍家里吵了架,而老舍夫任知道死讯后很冷漠,说死就死呗。当然,书里也有舒乙的说法,说前一种说法是胡说。
总之,故事部分如同侦探小说,引人入胜;理论部分(我没细读)呢旁征博引,引人深思。作者下了不错的功夫。
《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读后感(二):庋架小品(二):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
此前所寓目者,仅在勾稽“老舍之死”这一历史事件的史料上,尚没有任何一本书较此书更为详尽和鲜活,然而,倘若有人竟要藉此一窥“老舍之死”现场的真像,比如老舍在“八二三事件”后,究竟是在何日何时投了太平湖,投湖后又有哪些历史镜头可以复原等等,则注定要陷入尴尬的。因为作者压根就没有打算告诉你任何成说(尽管我认为他心里其实已经有了一个清晰的成说),他说他做的仅仅是“田野作业”,众口一辞的是历史上的确发生过“八二三事件”和“老舍之死事件”,此乃为历史1,至于哪些难辨的“众辞”则是历史2,至于真假虚实,读者自己判定好了;这就与历史上的周瑜和罗贯中笔下的周瑜同样是周瑜又同样不是周瑜一样,是非由你自己说了算,总之历史上确有周瑜此人,也就够了。然而可贵的是,作者在第一章勾梳历史谜团之后,能够于第三章、第四章调转笔头,进而做形而上的意义追索,这便增加了此书的分量,而在当下,意义的追索却犹如空谷足音般的寂寞,这又使我对作者增加了一份敬意。至于第三章《口述史未必是信史----老舍之死的史学意义》,我则宁可视为他的学术操练,对我来说没有太高的阅读激情。
此书傅光明著,大三十二开平装本全一册,山东画报社二零零七年一月初版七千册,定价二十五元。约略记得乃是今年三月某日以四折得诸位于海淀蓝旗营附近的豆瓣书店。
《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读后感(三):真相难白
搞不清先生去世的细节,那么探讨一下自沉的原因。又有了多种说法。一为“抗争说”,以死抗议文革;二为“绝望说”,对世界没有丝毫留恋,只有死路一条;三为“脆弱说”,先生解放后一帆风顺,无法承受文革这样巨大的政治漩涡。这些说法各有道理,都能自圆其说。你信谁?
而对于老舍先生本人,也绝非“人民艺术家”那么简单。他回国后,一面写文章骂美国,却同意加入美国作协,定期交纳会费;57年1月还提倡创作自由,反右开始马上狠批一样提倡创作自由的吴祖光;一面写非“主流”的《正红旗下》,一面不得不以“劳模”姿态深入人民公社体验生活,写《养猪快板》。哪一位是真实的老舍,老舍的真相又是什么呢?
作者深感我们头脑中的历史是何等幼稚和残缺不全,“它只不过是按照自身需要组合起来的拼图游戏,或者是仅供人们饭后谈资的随意杜撰”。人性的弱点会不经意甚至刻意渗透进历史,人写的历史由此带上了人性的弱点。
然而,老舍先生毕竟是“非正常死亡”了,抗争也好,脆弱也好,他毕竟用脚在责问:“新中国,我是那么爱你;你为什么抛弃我?”所以细节模糊,但历史的主线还在;老舍先生浓缩了中国一代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包含了他们的弱点,这意义还在。老舍之死将具有恒定持久的思想文化价值,这是毫无疑问的。
其实何止是“生死大事”,日常生活中,一件事,有时间、地点、人物、背景,你以为确凿无误;可是另一个人,同样有时间、地点、人物、背景,他的说法却跟你完全两样。从前总觉得对方有误,现在不会争啦,因为一句话——
真相难白。
搞不清先生去世的细节,那么探讨一下自沉的原因。又有了多种说法。一为“抗争说”,以死抗议文革;二为“绝望说”,对世界没有丝毫留恋,只有死路一条;三为“脆弱说”,先生解放后一帆风顺,无法承受文革这样巨大的政治漩涡。这些说法各有道理,都能自圆其说。你信谁?
而对于老舍先生本人,也绝非“人民艺术家”那么简单。他回国后,一面写文章骂美国,却同意加入美国作协,定期交纳会费;57年1月还提倡创作自由,反右开始马上狠批一样提倡创作自由的吴祖光;一面写非“主流”的《正红旗下》,一面不得不以“劳模”姿态深入人民公社体验生活,写《养猪快板》。哪一位是真实的老舍,老舍的真相又是什么呢?
作者深感我们头脑中的历史是何等幼稚和残缺不全,“它只不过是按照自身需要组合起来的拼图游戏,或者是仅供人们饭后谈资的随意杜撰”。人性的弱点会不经意甚至刻意渗透进历史,人写的历史由此带上了人性的弱点。
然而,老舍先生毕竟是“非正常死亡”了,抗争也好,脆弱也好,他毕竟用脚在责问:“新中国,我是那么爱你;你为什么抛弃我?”所以细节模糊,但历史的主线还在,老舍先生浓缩了中国一代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包含了他们的弱点,这意义还在。老舍之死将具有恒定持久的思想文化价值,这是毫无疑问的。
其实何止是“生死大事”,日常生活中,一件事,有时间、地点、人物、背景,你以为确凿无误;可是另一个人,同样有时间、地点、人物、背景,他的说法却跟你完全两样。从前总觉得对方有误,现在不会争啦,因为一句话——
真相难白。
《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读后感(四):“老舍之死”的史学思辨
课上老师提问,“有谁知道老舍是怎么死的?”
我晃了下神,心想,老舍嘛,要么就是死于建国前抗战加内战的贫病交加,要么就是流亡海外后寿终正寝,有什么特别吗?
同学回答说:“老舍是在文革期间投太平湖自杀的。”
我不禁愕然。我忘记了“人民艺术家”老舍的《茶馆》、《龙须沟》,也忘记了那场五十年前发生的血雨腥风,忘记了母亲少女时代学校停课、揪斗老师、红卫兵游行、家家关门闭户的身边事。我曾为文革的种种非人而愤怒、痛心,但那一瞬间,如此深刻影响中国知识文化命脉的大事件,被我的记忆彻底地忽视了。
没有被记录的历史,注定会成为虚无缥缈的烟雾,仅有的扑朔迷离也会随着时间被遗忘殆尽。我头脑中常出现的一句话是“新中国的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虽历经曲折,却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很少意识到一个“丰硕成果”遮蔽了多少“历经曲折”。在变革迅猛的中国当下,写出《考而不死是为神》的幽默率真的老舍、以《骆驼祥子》、《茶馆》对人性与社会痛定思痛的老舍、热情歌颂新中国的老舍离开的真相,竟随着那段被遮蔽的、讳莫如深的历史如烟尘般散去,不但难以追寻,恐怕也鲜有问津了。
被记录的历史虽未必是信史,但只有依赖大量的记录材料,历史才有可能自圆其说、自问自反,从而更接近真实。在读完傅光明先生的著作《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后,我在探求真相之外更意识到,“历史”的概念如同“戏剧”及其他学科的重要概念一样,如何去定义它,即“历史观”的确定,决定了对史实的挖掘和阐释方向,从而导向不同的真实,而在不同历史观的对照之下,被记录的历史才有可能成为活的历史。本文试以作者提及的不同历史观来观察“老舍之死”的各个侧面,通过纵向的梳理、归纳及思考,加深自己对“活的历史”的理解,以期反思民族的过往。正如作者所说,“过去既是像现在一样活生生的,又是像将来一样捉摸不定”,但“大中华的生,大中华的死,也许能在‘老舍之死’中找出点真消息。”
一、老舍之死的“古希腊时段”
古希腊人开创历史学之初,“历史”(Ιστορία)指的是“对真相的探求”。围绕着“老舍之死”的种种谜团正有待这种追问和探求。
将老舍置于时代大背景中,并联系他的人生经历、创作轨迹和作品,或许能够更清楚他的处境和心态。但资料愈加详尽,考察逐渐深入,老舍本人的形象也愈加复杂难辨,比如他回国时是一腔热情、不加思索还是始终有所顾虑?他在政策导向与艺术规律的挣扎间始终心口如一吗?他是否主要出于政治考虑修改自己的作品?他的死是冷静思索的、“天下无道,以身殉道”的屈原式的吗?是抗争、绝望还是脆弱?这些问题恐怕将永远是问题。
事实上,历史从来不是一场清清楚楚的戏。久远的流传为神话,稍近的变成了演义,眼前的存活于新闻。真相的本来面目只有一个,就是生活的复杂本质。“古希腊时段”的价值就在于让我们更接近了那段老舍身处其中的被遗忘的生活。
二、从古罗马到文艺复兴:以史为鉴
说到以史为鉴,中西方都有悠久的传统。古罗马的史学家李维说:“研究研究过去的事,可以得到非常有用的教益。”意大利文艺复兴时,布鲁尼认为:“历史一清二楚地记录了过去许多年前的行为和思想,我们可以方便地借鉴,学习好的,摈弃坏的…”中国古代漫长的封建时期,历代王朝都要修前朝史为鉴,形成正史二十四史。那么,使我们引以为鉴的那些经验教训是事件的真相吗?既然“真相”是复杂的,我们是用什么方式从中归纳出经验教训的?
从有史官起,历史就在不断地筛选它应当记载的东西,记载和忽略、记忆和遗忘始终相伴。古代帝王引以为戒的兴亡教训,多少来自前朝历史的春秋笔法,历史的叙述统摄在“开国皇帝英明、亡国皇帝昏庸”的思想观念下;被尊为正史典范的《史记》,也包括了用田野调查方法搜集的各地传闻。且它被称为“无韵之‘离骚’”,恰如其分地证明了历史叙述中文学性的重要,即“史以文传”。历史叙述体现了历史与诗、哲学的紧密联系。历史史料于史官而言,只是用于历史叙述有待选择与加工的原料。另一方面,依培根所说,记忆是历史的源泉,历史的流传无不依赖于群体记忆的传承与筛选。因此,我们引以为鉴的历史,既取决于书写者的叙述,又受到社会、民族群体记忆的影响。
考虑了这两方面因素,“老舍之死”历史真相的扑朔迷离就变得情有可原了。在舒乙的回忆中,还提到1966年8月的某天,被错化为“右派”的马松亭与夫人在什刹海遇到老舍,拉他一起坐坐。老舍表达了自己的苦闷,说要“走”,还说“马大哥,咱哥俩儿兴许见不着了!”他从父亲一生的生活轨迹出发,视太平湖为老舍有意选择的人生归宿。强调老舍离家前与孙女别有意味的道别。似乎老舍对“文革”有着清醒的认识和预感,他的死是冷静理智的无言反抗,堪比屈原。汪曾祺及一些日本学者,他们更愿意把老舍之死理想化。也有人认为老舍之死是受辱,事实是老舍建国后一直非常顺利,是身居要职的“人民艺术家”,是一个“外圆内方”的人,他只有处于极度绝望、激愤才可能自杀。甚至有人认为老舍听惯了赞扬的话,受不了委屈。巴金则意识到老舍之死抗争意味背后的复杂性,因为这个“有骨气”的行为,也包含着“幻灭”、“疑惑”、“痛苦”等许多无法说清的因素。他们的叙述,依据不同的事实和对老舍不同的看法而不同,他们的记忆,也无不受到各自在“文革”中的经历的影响和集体经历的某种裁剪。
三、几种“假定”:理性、真相、思想
黑格尔认为,“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这一种信念和见识,在历史领域中是一个假定…”这是历史学者研究各种史实时一以贯之的原则。但世界大战使人们失去了对理性的信任,克罗齐把所谓客观的历史真相推定为一种“假定”,要我们拒绝沉溺在无益的问题中,并认为”放弃客观的历史真相并不是消极的,却是新认识的起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科林武德则认为,“历史事实或事件,如果不被放在一个思想的网络或模型里,就不能获得任何意义。……史实只是数据,数据本身没有意义,它的意义是从它在一个更大的整体之中所处的地位而获得的。……数据只有在被纳入一个思想结构之中才能有意义;意义是被思想结构赋予的。”由此得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都是历史学家在自己心目中对过去的思想的重新体验。
“文革”是彻底的非理性的,而以单凭理性探求老舍为什么死显然得不出答案。正像任何一位决定毁灭自己的人一样,老舍的无法被简单解释为“警世型”、“不可辱型”、“动乱型”或归为“反抗说”、“绝望说”、“脆弱说”。太多相互矛盾的回忆已经使“老舍之死”的始末无法理清,于是我们只好投入克罗齐的阵营,放弃之前苦苦探求的真相。
在我看来,以上这三种“假设”的出现,印证了史学方法与观念的发展。正是因为人类掌握历史史实的方法、技术的进步,史实海量而庞杂,导致了历史真相的本来面目——复杂——的揭开,人们已经不满足与从古老单一的传说、记载中引以为鉴了。
四、口述历史的复兴:“能”与“不能”
结合本书的阅读和以往的感受,我想说一说口述史的“能”与“不能”。
口述史能否作为信史?亚伦·内文斯说,“任何人对于过去事件的回忆都是不值得信任的。”本书作者在田野调查时,虽立志要“拆开一层层记忆,向后挖掘到记忆的深处,希望达到隐藏的真理。”但在具体实践时依然无力地感到,“抽出被访者记忆‘最深层的秘密’几乎是不可能的”。受访者由于不愿提及让自己心痛的往事而有意识的回避,或者无意识地筛选、裁剪了记忆,甚至处于某些难以说清的原因使自己的讲述带有表演性,都有可能产生巨大的误解。从根本上来说,每个人“过去的记忆”与口述时“自我”对过去及现实的理解、现实的处境密不可分,任何人的口述,都无法逃脱自己对客观的篡改。如果“口述史”只强调“口述”,它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口述史之所以成为一种历史观和方法,在于所得史料要经历海登·怀特所说的论证、编织情节和进行解释三个阶段,这是历史学必须完成的任务。好在本书作者在“老舍之死”的问题上不但没有止步于搜集史料,在与其他历史观的互鉴中做出了开放性的阐释,而且把问题引向了更深的民族、文化心理层次。所以,口述当然不可信,但口述史却未必不是信史,就看操作者能否拿出做史学的严谨态度去勤奋治学了。
本书值得一读,有历史观、口述史的一些知识,也有相对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由表及里的、见微知著的学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