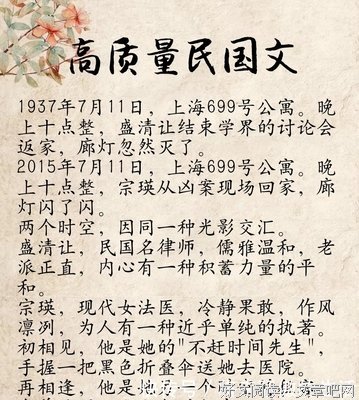
《与民国相遇》是一本由唐小兵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页数:30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与民国相遇》精选点评:
●书话章基本上是读书笔记。一节就是一本书。长处是文从字顺,短处是于一书之外,基本没有旁征其它史料。
●对历史的诠释很温暖,一个读史之人应有的情怀
●现在的我不是当年的我
●民国的流风余韵是一瞬的烟火,是绽放在黑夜里的烟火。
●就是篇章短了点。饱含深情。
●时代际会,高山仰止。存士人操守,书生意气;融现世安稳,独立精神。
●历史是由活生生的人创造的,我们现在认为的历史,就是当初的人们普通的生活。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唐小兵老师关于民国社会生活的随笔和书评集,描写对象涵盖了学者、作家、报人、官员、军阀等在民国历史舞台上活跃的各色人等,注重考察他们在新旧时代、思想潮流变换历程中的矛盾、纠结与抗争,文章多以两三千字篇幅为主,短小精悍而又微言大义,适合茶余饭后的闲散阅读。
●上厕所看看比较合适。不适合集中阅读
《与民国相遇》读后感(一):冀望
感觉对那个流逝的时代,作者报有怅然若失的向往。但青山留不住,毕竟东逝水。作为青年史学家中的优秀代表,如能从世界格局的角度,居高临下研究这段历史,以作者善于积累和分析史料的优势,这本书的格局和层次可以更高些。毕竟,清末以绛,中国的内政受制于各方势力,各种人物也困于各方利益和实力,很多表面现象,往往有各方势力的影响和诉求。冀望作者以后的作品,能让我们能有更加畅快淋漓的感觉,收获更多,看好作者!
《与民国相遇》读后感(二):钱理群、许纪霖等捧捧的新生代学者
钱理群作序言是2015年11月6日至8日
但这本书2017年才出版。
P18
屠格涅夫的小说《罗亭》的主人公罗亭的自责信,说明书生无用的普遍性: 我的天分似乎并不过薄,不过我的能力不足,所以不论什么都不能成就。即有天赋,毫无用处,即使下了种子,不是一定都有结果。 在我,没有能力使人们感动,尤其是没有能力使女人注意。只靠一点知识,是毫无益处的。很想热心地运身做事,但是事实上丝毫不能实 现:我的命运,真是可怜可笑!
《与民国相遇》读后感(三):唐小兵 历史的公共写作是投向未来的一束光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7-04/15/content_678086.htm?div=-1
历史学者唐小兵在微博上的名字是“沪版唐小兵”。在上海生活了14年的他本是湖南人,可师友们常打趣说,他不嗜辣不喝酒又性情温和,是“非典型湖南人”。而在学者许纪霖看来,唐小兵身上让他琢磨许久的是一种“贵族气”。
多年后,唐小兵回想起博士阶段老师对自己的这番评价,将“贵族气”归因于在他大学时代在岳麓书院静心自修的时光。北宋至今,岳麓书院有过“朱张会讲”的荣光,也曾在战乱中被毁。这座历经浮沉的书院给他的感觉,正如他读齐邦媛回忆录《巨流河》的感受:乱世中,文化仍有尊严,仍能带给人宁静与力量。
《与民国相遇》中也有一种相似的余味。2011年初到2013年底,唐小兵在《东方早报》文化版开设“野人献曝”专栏,聚焦知识分子、城市与中西文明相遇,钩沉民国往事。今年初,这些文章结集成书,民国热退潮之前,那个时代的温度会引发我们对这个时代的何种感触?
民国热的背后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唐小兵开设专栏那年,距离自上世纪90年代民国热初兴已有近20年,距离甘阳的《八十年代文化意识》和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双双出版也已5年。
在以西学热为主的80年代,热潮尚未波及民国历史。随着那场启蒙运动戛然中断,加之90年代市场经济的起步促使中国社会开始了全面的世俗化,在学术界,一场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催生了国学热与民国热。重回现代性发轫的晚清民国,成为那个时代人文学者在有限话语空间内为现实引入思想资源的一种路径。
90年代是唐小兵的大学时代,也是学院体制内民国知识分子历史研究成果大量涌现的时期。当时余英时、王汎森、罗志田、许纪霖、钱理群、陆键东等学者对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研究,如今已沉淀为该领域最为成熟的研究。90年代后期,傅国涌、谢泳等在学院之外对民国知识分子史兼具理性与私人情怀的述说,在当时的大学校园中也颇为流行。
这股民国热,既关注偏向自由主义的群体,也对民国文化保守主义者进行了重新书写。随着这一群体与个体的人格气象与真实面相逐步展开,民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呈现出内在的紧张与多元。“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唐小兵曾引用意大利学者克罗齐的话解释民国热的深层原因。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1905年废科举和1912年帝制崩溃后日益黯淡,又在20世纪一系列革命和运动中,在经济、政治乃至文化上被不同程度边缘化。因此,延续至今的民国知识分子热潮,目的在于通过对那个群体精神、学术、生活的书写,为当下中国知识分子乃至中国文化灌注“隔代的养分”,并与当代现实形成一种内在的对话。
“从90年代起,民国热成为公共文化的表征和内容,也催生出更有历史深度和维度的公共文化”,唐小兵说,“否则,消费主义下的公共文化很可能只是一种肤浅的泡沫文化”。
《与民国相遇》是唐小兵的一次尝试,他将在历史研究不能整合成鸿篇巨制的细节和感触,写成面向公众的平和文字。从提笔到面世,民国热已有退潮意味,唐小兵不无怅然,“与此伴随的是公共文化的式微”。
历史观念与写作
从细小路径进入历史人物的心灵
尽管学界启蒙风潮不断,唐小兵觉察,公众的历史观仍处在一个野史、传闻主导的蒙昧状态。他反思近20年来在公共领域畅销的晚清、民国历史作品,部分作品出于强烈的启蒙目的,对历史本身复杂面向有所取舍、甚至不加节制地剪裁。
“我们应对历史人物有一种温情和敬意,抛弃后见之明与道德裁断,才能与历史人物有真切的对话”,唐小兵说,尤其在公共领域,对复杂性的认识、理解与接纳,是公众通过阅读历史走向心智成熟所必不可少的阶段。
从2003年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师从学者许纪霖起,唐小兵对晚清、民国知识分子研究脉络开始有系统地了解。他的早期研究以《大公报》星期论文、《申报》自由谈为例讨论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对北平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上海左翼知识分子两个社群均有涉及。多年后,唐小兵才后觉出一种幸运:这种更平衡的研究架构冲淡了他自由主义的立场,避开了在公共历史写作领域中常见的以立场倾轧历史复杂性的做法。
《与民国相遇》运用了多元的史料,所谈及的知识社群包括左翼、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有钱穆、吴宓等常被视为保守主义代表的人物。唐小兵希望呈现的是一种“众声喧哗”的对话感,让“保守”的杜亚泉和“激进”的陈独秀相遇,也让殷海光、何兆武对西南联大的回忆与阐释——文化比权力更有尊严、在威权时代学人的有所不为——与当代形成对话。
对何谓历史研究的“洞见”,他有越发清晰的体认:不是一种冷酷的史料堆砌,而是要进入历史人物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对其在大时代的处境、意识、行动选择与命运有感同身受且完整的理解。他从1923年夏蒋廷黻父亲在湖南邵阳乡间去世入手,引出乡村葬礼中的传统之魅,或从抗战胜利后第一次校庆,清华女学生就女性如何为社会贡献力量对师母的采访开场,讲述陈寅恪妻子唐筼从新女性到家妇的人生转折。从细小的路径进入历史人物的底色与心灵,唐小兵试图去触摸隐含在历史深处那些伦理困境与文明碰撞。
尤其是在他一贯关注的左翼知识分子研究领域,既有的多数研究都从文本出发,他则希望从语境出发,探讨思想、历史与政治之间的互动与此间个人的处境和选择,从而为理解左翼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以及20世纪的中国提供另一种可能。这让同样研究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强调历史感性与温度的学者钱理群有“若获知音之感”。
文化乡愁的代际传承
先生点燃烛火,又约我们同守暗夜
从2009年留校至今,唐小兵开设的本科课程多是讨论课。“每一代人都有各自与时代相遇的方式”,他要传达给青年人的,是进入历史脉络的能力和在历史脉动中思考的勇气。
讨论有时和风细雨,有时则如狂风暴雨。比如,未经历过“80年代”的年轻人会勇于质疑,所谓“80年代”是否是已为成功人士的那一代人寻求自我慰藉,毕竟他们如今拥有、也可以强化这一怀旧的文化资本。
“80年代,我还在湖南乡村读小学”,唐小兵回忆,直到工作后重返校园,在人文底蕴浓厚且气象开放的华东师大,许纪霖、刘擎等师长一辈人的言谈举止才逐渐让他浸润到那个时代的遗产中,并一窥那一代人的精神群像。
时代逝去。近年来,随着查建英、甘阳、赵越胜等忆旧作品的出版,对那个时代缅怀性、反思性的追忆与讨论越来越多。唐小兵也曾在《危险的愉悦》一文中写道,《八十年代访谈录》在“80年代”与“后80年代”两个时代之间设置了一道“精神的鸿沟”,隐喻了深刻的“断裂”。对于七八十年代后出生的几代人而言,这种断裂具体地体现在理想主义的整体性缺失、公共生活和公共讨论在校园的缺席、以及人的超越性与世俗性之间完全倒向后者的严重倾向等。
许纪霖曾引用德国学者赫尔德的话,“乡愁是一种最高贵的痛苦”,唐小兵对师长一辈人的文化乡愁有自己的理解。断裂无可挽回,但仍有一种代际传承。就像许纪霖那代学者在大学校园仍能从师长一辈人身上比如陈旭麓、施蛰存、王元化感受到民国遗风,又如《燃灯者》中周辅成与赵越胜的师生之交,“先生已点燃烛火,又约我们同守暗夜”。
他有一个夙愿:作为一个70后学者,与杨国强、许纪霖等上一代学者做一系列长长的对话。如在长夜中燃起烛火,当两代知识人的精神世界形成创造性的对话,20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的内在脉络和流变得以呈现,也能为这个时代留下一个真诚而严肃的思想文本。很多次,唐小兵谈到那些已七八十岁的前辈学者至今仍耕读不辍,比如关注并洞察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的钱理群,比如以历史阅读、研究与写作而照亮晚清中国的人文主义史家杨国强。时代喧哗,沉疴遍地,但那一代人的治学精神和人格魅力,仍为认真对待这个时代的人提供了一丝光亮,正如韦伯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中所呼唤的那样。
与之相应,唐小兵在《与民国相遇》中写道,“最高的文字都是相通的,它会让人体会到文化与精神的力量,让人从喧哗与烦闷的现实无限撤退到一个平静的内心庭院,这种撤退不是犬儒,更不是逃世,而是为了充盈一个更为丰沛与强健的内心,以韧性来缓慢地穿透硬木板一般的现实”。
采写/新京报记者孔雪
更多详细新闻请浏览新京报网 www.bjnews.com.cn
《与民国相遇》读后感(四):与民国相遇,与文雅相叙
人与书的相遇,或金风玉露,或百感杂陈,或掩卷长嗟,或桃李江湖。得遇唐小兵老师的《与民国相遇》一书,应如作者所愿是故旧相逢、畅叙相宜的观感。其书的关怀在乎文与雅,并在写作中示范着文雅。
文质与雅致,终须归善于人,并只能由人来演绎。近代百年来,对于“文明社会中的人”存在多种称谓。如梁任公视角宏大、擅长论政者,谓之曰“民”。后世主要继受了这一传统,遂有“人民”一称流行、定鼎。
《相遇》关注的不是“人民”,而是“人”。一来,书中所察所写多为个体轶事,写及的人和事再多,也定然个个留名,耐心些总能数得过来,每一个故事也都细腻到可以走心;二来,著述暗含了去政治化的话语倾向,对小人物和小故事的刻画描摹有多重视,对大人物和大事件就有多不重视。
所谓不重视,其理略同“不要看他说了什么,而要看他没说什么”,或许悄悄完成了一种漠视,乃至否定。不踩“大人物”的热点,不作宏大叙事。不惟不追具体的大人大事,甚至不立伟大人格——只谈人之常情。
这也正是读史所感的“温情与敬意”,如钱穆先生《国史大纲》语。
《与民国相遇》之不同于《民国大人物》,更不同于《一本书读懂民国》(不必查,但看书名足矣)之流的书,就在于排除了人物形象、事件定性之类的预设,不作任何标榜。没有谁是天生的大人物,这应是常识。可总会有人不甘寂寞,定要在民国与新中国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比较,要么抬高民国以批判当代,要么丑化民国以找自信、暨颂圣。而要行这等事,当然都是从人物入手了。
事实上这两种路径都不大行得通。做历史还需秉持公心,进而怀温情、致敬意。对于能够证实的史料,须有基本的尊重以及自重。在这方面,本书就做得很好。能还原的历史尽都呈现,材料铺展开来是共享的,态度则儒雅平和。就事论事,不作神化、矮化,更不会简单化,不树立任何典型。不是树立对于名人、伟人、完人的态度,只是对“人”的知遇。致敬,而不必崇拜。
同样意态、同等水准的书,以我读过而言,可举《袁氏当国》。后者当然围绕袁大总统而展开。然而,本书竟可越过大人物这种易于上手的媒介,却以群像、列传、画集般实现这等意境,可说十分难得。这要对相当丰富的人、事、问题过脑走心,有序沉淀,方可为之。由此亦更可见作者治学的格调。
谈罢“人”的关怀,又话回梁启超的“民”。循梁任公的思想历程,其作为近代思想史的一座界碑,所提出较为成熟、典型的理论是“新民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摸准了国脉,还以此为名,出了相当优秀的一套书系。可见“新民”是个情结,在当时就有相当准度,并在后世证明是有相当生命力的一个论题。推陈出新是不错的,但它是基于何种样态?一定是在线性结构上,把“新旧”轻巧代以“前后”吗?
新旧之辨的问题,可能自始就有隐藏的一面观。
据本书“清末民初的新旧之争”一文载,清末一位署名“敢生”的作者在《觉民》杂志上发表《新旧篇》,针对“新国”“新民”的提法,认为新旧之争是伪命题:
“夫理岂能新,发明而已;学岂能新,进步而已;国岂能新,强之而已;民岂能新,智之而已。”
不论此言基于何种立场——批判反思或仅为保皇——这种腔调都很值得注意。因为这种跳出了“新旧”或其他二元对立的省察,其本身就有意义。沉疴久矣的清末,人心思变求新,且除旧唯恐不尽、立新唯恐不快,是彼大时代的主要气质。其激进者,惟盼朝廷一夜翻天,制度一朝而立,变革一蹴而就,国家成败只在翻手云雨之间。这显然是草率的看法,但在特定时期显然大有市场。立新,在事实上压过了守旧。
但在二者之间,或曰之上,还有另一种态度,就是暂搁对立、务实建设。新或旧,不重要,解决现实问题才重要。辨析眼前是何种问题也不重要,在民不聊生之际,让国家安宁、百姓安居,才重要。用回归常识的务实精神来冲淡某种认知偏执,并持久地提供一种出路:一旦谈不妥,就先放下。不惟政客如此致用,名头不见得多响亮的青年学人也有这番见地。
这是一种多么有底气的文雅。
我不以为长袖袍衫和西装革履新派旧派文人学者们,能够代替戎装的领袖来强国御辱。但在长久可期的和平年代里,唯有专注道理、文化、新民(不断更新)的社会,才有可能超越“强国”而谈“文明”。应思之:什么是真正的强大,什么才是目的。
在后记“穿越民国时光的交叉小径”中,作者对本书的写作有着浪漫主义的自述:
“试图从一条条迷人而交叉的小径,穿越时光的丛林,进入民国的心腹与血脉。”
写照栩栩。是否真的进入了“心腹”,我限于阅历无从验证,进入了“血脉”则是可感可信的。只因我是同样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我的祖先的后代,血脉中定有某些基因,带着年代的记忆,穿透时光而来。科学上或不可知,读入境的心绪上应可感。作者又说,
“这种面向公众的写作,是与一个更为宽广的公共文化视野衔接在一起的。公共文化包容事实,但又不为事实所拘囿,它应该具有超越与理想的品格。”
如此,又将我从感性带到了现实认知,这究竟是当代的写作,并且是可以且值得效仿的。公共文化视野往往要超脱于一家之事,而且谈任何时代的“公共”,其实都隐含当代关怀。需要呼唤的是那些文明年代里人们恒重的理想与品格,是为作者所吁之“超越”的内容。也即:
“而对于民国史的这种书写,其实就是在给当代中国的公共文化建设灌注一些来自20世纪的养分。”
说到这里,这不由使人想起孔子的复古复礼,以及唐代的古文运动。他们都试图从过去寻找养分。古文运动不仅是在文体上溯古,同样兼及道德情操、精神风尚。韩柳反对魏晋以来文学的浮夸风,而提倡古朴醇和。如此回首历史中汲养,较之韩柳,不仅取法相近,所取者亦近。
如上所引,旧时光里的养料取来,是为灌注于“当代中国的公共文化建设”。则关注在民国,关怀应在现实的公共文化。
如唐小兵老师在接受澎湃“文化课”记者专访时所说:
“其实民国是一个参照体系而已,它当然不是一个黄金时代。由于它正好处于古今中西之争的转折时代,各种异质性文明体系碰撞,以及在这种文明冲突、融合和竞争中所成长的个人和群体相遇。人们对民国的追寻实际有两个层面:一是追寻中国于晚清民国时期从西方引入的思想资源,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后民主、自由、平等、开放和多元的价值理念;二是追寻民国知识分子在其人生过程中所展现的人格。”
(澎湃文化课专稿 《别再戏说民国了,听历史学者认真负责地谈谈民国》,可点击左下[原文链接]查看)
书中言道民国是天地玄黄狼奔豸突的时代,未尝没有今喻。至少有意镜鉴。唐师专访中论及的这两点,我以为,西方的思想资源考虑到本土化问题固应以审慎对待,而民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则是经过一时人杰学习消化,既化于人格,应是最真诚的思想资源。对于这些仅仅几代以前知识精英的“先生之风”、独立人格、自由思想,今人读者应可放心,不妨以更开放的心态去了解。
以民国轶事为土壤,寻找文雅的养料,必经一番甄选。要筛掉的首先是陈独秀、罗家伦等壮怀激烈、讥讽怒斥之辈。譬如书中《“先知”杜亚泉》一篇有记:罗家伦在北大《新潮》杂志刊文嘲讽《东方杂志》道:“你说它旧吗?它又像新。你说它新吗?它实在不配。”
在罗家伦的话语中,“新”已具先验之正确,并且隐蔽了一个“凡事必有新旧之分”的条件。后者更为可怕。在我们的近代历史上,左右新旧、先进后进、革命或反动之分辨,并不稳定可靠,而是可以发生翻转易势的。“翻转”的基础,不正是强分新旧的基本立场吗。故此,为近代或当代的这种带有戾气的辨识心去火治病,釜底抽薪之计,就是要在总体上要找到一种“去五四化”的视角。借此,可去一去非此即彼的极端主义之毒。
这味药,或许就叫做文雅。
又可见,本书推重的是杜亚泉式的温柔敦厚。但是,如他这样“怀抱理性与温情,主张包容与多元的知识人”,却又“难免成为排他性和独占性的政治意识形态运动的敌人”。
作者未曾点明,但此书重拾“折中、温和而理性的接续主义(或曰调适主义)”的意向是不难发现的。这也正是当今需要的价值。毕竟,过去的我们实在不乏文化断代的惨痛经历。意识形态主导下惯被歌颂的五四运动,就是其中沉重的一回。或许,不经历此种阵痛,我们就没有恰当的机会得到诊断,也就不会在总结历史中得到此种认识。
甘阳曾道:“文化方面的重建不可能由政治来代替。不要以为民主化以后,自然而然就能有文化”,进而有问:“富的是经济,强的是政治。文化呢?”
一语中的又准又狠,令人信服赞佩,但不为美,表达思想的方式本身不得文雅之法。话太硬,像指挥棒,似“指哪儿打哪儿”的气概。
当然不应苛责,这只是学术方法的固有局限,从这里可以发现学者与文人的分别。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学者已不必然是文人了。与传统士人在治学和情操两方面的自高自觉相比,这样的新变化未免令人觉得可惜。难得的是唐小兵老师兼有学者与文人两种方法、两种风度,在文人风雅笔端,一篇篇、一句句娓娓道来,轻轻相遇,如逢老友畅谈,文质彬彬,雅量在叙在议,如此舒服受用。
第六辑书话,是唐小兵本人的文雅示范。在我读来,与评介高见同样受用的,是议论的姿态。作者很在乎公共写作,“试图将自己在历史研究与历史教学中不能整合成鸿篇巨制的细节与感触,发抒为一篇篇可以滋养人心的文字。”
在做论文的过程中,我也有相似的体会。或来自查阅的材料,或来自遐思,形成一些与题意无关但不失独到的见解看法,即研究的“副产品”,一概记下来。记下暂存以后,各人做法便大不相同了。许多妙思就此作为学术残片搁置蒙尘;有的能得到新鲜材料的接续,成为下一篇文章的发端;像作者这样收录起来整理汇辑,又能出版,实属上佳之选。如此不仅避免了思想资源的浪费,并且实实在在成为公共文化领域中的有用之文。
公共写作势必要求一种话题时效,过期之后,有效参与公共探讨就难了。时至今日,话题更新周期又短了许多。较之长文宏论,当然是短篇易得,也更能做到应时,因而成为公共写作的主要体裁。然而俗话说“时评速朽”,放眼媒体江湖,亦不乏“短平快”的文字产品,有热点就踩,即时投入,迅速收回人气,哪怕无甚新意、质量稍次,依此模式也有可观的关注度和阅读流量回报。
可是时评“王道”之外,也有如专栏这样的久耕(虽然未必尽能深耕)之地,在流量的大潮里,保持着自己哪怕微弱的声音。如此潜心耕作使我起敬。这样的做法,未始没有一日也能火起来、带动舆论。但不必有那样的期待,因为能够坚持一种题材和格调,本就已经实现理想。六辑、近百篇文章,显然是这种温情的坚持之成果。
钱理群先生在为本书所作序言中说:我们的历史研究的最大问题是“只有历史事件而无人;或者有历史伟人、大人物,而无普通人、小人物;有群体的政治,而无个体的心灵世界”。
此处所言的“人”,不是白板脸。后文又说:“而我的写作,也始终追求历史细节的感性呈现,具有生命体温的文字表达。”据此细细体察,亦是对文雅的诠释与呼唤。
唐小兵的书写即力行之,使我们得以观察到“人”、普通人、小人物、个体的心灵。画卷上布满了细腻的人像,促成读者与一个大时代小场景民国历史的相遇兼叙。
二零一七年六月九日 于京
----------------------
本文首发个人微信公号:文森堂笔记(tang121575)
感谢惠阅,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