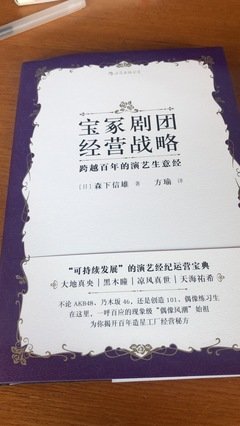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是一本由Yasheng Huang著作,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出版的Hardcover图书,本书定价:USD 38.00,页数:36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读后感(三):《新左派评论》里对黄的批评
首先声明,我并没有读这本书,虽然此书已经在书架上放了有些时候了。之所以这时候拿出来讨论,是因为读了在最新的一期《新左派评论》上Joel Andreas(安舟)写的对此书的长篇批评,颇为受益也深表赞同。
正如安舟所说,黄的这套说法很有蛊惑力。他看起来是站在弱者的立场上,为破产的小企业家、被剥削的农民工、福利丧失的城市居民说话,反对官僚集团里的特权势力,而同时又在为自由市场而摇旗呐喊,巧妙地结合了populism和free market ideology,因而在众多鼓吹自由市场的新自由主义学者中脱颖而出。但其实,黄是在贼喊捉贼。黄貌似所代表的那些弱势群体,其实恰恰是因为黄所鼓吹的自由市场的兴起而成为了弱势群体。
首先,来看看黄所说的改革的两个阶段的到底是怎么回事。80年代是农村的乡镇企业领军,这是肯定的。但使得乡镇企业能够发展起来的原因是什么呢?说到底是两点。第一,从历史根源来看,正是因为国家以经济上不理性的方式,将大量的工业资源转移和分散到广大的农村地区、建立了大量的社队企业、并通过这些企业在农村社会培养了一批有生产和管理方面的技术的人才,80年代的乡镇企业才成为可能。乡镇企业发展的这种历史基础,在任何一个自由市场的经济体里都不可能出现,这也形成了中国发展模式不可复制的一个特点。不过,这一点安舟倒是没有提到。第二,从当时的经济环境来看,乡镇企业获得了发展的空间恰恰是因为国家对城市里的国有与非国有企业都采取了种种的约束措施,使他们不得施展、无法与乡镇企业竞争,才使得既无技术又无资本的农村小作坊能够有立足之地。具体一点地说,城市中的国营企业要给自己的职工提供各种福利、又不能随便招收廉价的农村劳力,因而在劳动成本上无法与乡镇企业竞争。在市场方面,还要受到计划经济的种种制约。而城市里的私人企业直到87年之前都基本上只是个体户,聘用的雇工超过7人都是违法的,更谈何与乡镇企业竞争。
关于乡镇企业,黄还犯了个错误,就是认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是私营经济的发展。而其实他所列举出的数据所显示的农村企业中大量的“私人企业”其实都是个体户,谈不上什么企业。黄又把为了谋生而采取的self-employment活动跟为了谋利的企业混为一谈。真正的乡镇企业的主力,其实绝大多数都是集体企业。黄的这个说法实在是个奇怪的事情。想当年,这些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们还一个劲在说,这些集体性质的乡镇企业产权不明晰,将来要出问题,是靠不住的;何以今天居然又忘记了这些乡镇企业的集体所有制性质了?
那90年代后发生的变化又是怎么回事呢?江朱治下的经济政策说到底就是放纵市场、让国家撤退。朱主导的国企改革、抓大放小,不就是这么回事情?乡镇企业在80年代时所拥有的优势,在这一市场化、私有化的改革中也顿时丧失。第一、国企改革使得国企的福利负担大为减轻,大量员工下岗、各种福利被削减(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而这些措施的目的就是让市场来主导企业行为、也让企业在市场中有竞争力。其结果也确实使一些国有企业实现了市场化的转型,不仅成为了乡镇企业的直接竞争对手,也切断了原来国营企业对乡镇企业在人员、资源与技术上的大量支持。第二、城市里私营企业终于获得了身份上的合法性和资源上的可能性。而随着大量国营企业的私有化(资本市场的自由化),一些资本庞大、技术实力雄厚的私人企业,还具有座落在城市里这一优势,也成为了乡镇企业的竞争者。第三、国内市场对外资的开放日益加剧,不仅允许外资进来,还为本已强大的外资提供各种政策上的特殊待遇,那些小乡镇企业如何抵挡得住。最后,乡镇企业本身也被私有化的浪潮所波及,大量的乡镇企业变成了私有企业。如此四剑齐下,乡镇企业不死才怪。
在这上头,黄延续了前头的那个关于乡镇企业的古怪的观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早就在批评乡镇企业,说这些小企业产权不明晰、技术含量低、是粗放型增长,兔子尾巴长不了。如今这些预言倒是多少都实现了,黄却跑出来说乡镇企业的破产是因为政府在政策上的压制。
至于90年代政府的很多经济政策明显地偏向城市,这是对的。江朱两人的上海背景、在大工业部门任职的经历,都造成了他们个人对于农村、小企业的偏见。但他们治下的经济政策的城市偏向性并不是政策本身的目的,而是一个副产品。政策的目的,说到底还是放纵市场与放纵资本。而自由市场和资本自然是有城市偏向性的,因为大资本的生产自然是以城市为基地的。就连很大乡镇企业做大之后,很自然地也搬家到了城市里,摇身一变成了城市里的私营企业。
90年代里,国企的复苏当然也是有的,而且也确实是国家政策结果。而这些垄断型大国企肯定也是造成了黄所提到的一些恶果的,比如说对小企业的压制与剥削、通过垄断利润将财富从民众手中转移到特殊利益集团手中。这一点安舟有点回避。但他总的评价还是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总爱说自由市场会创造一个平等的竞争空间(a level playing field),这是自由市场的一个核心的myth。自由市场里从来不是平等的(其实也谈不上公平),或者用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说,只有形式上的平等、没有实质上的平等。自由市场的逻辑就是大鱼吃小鱼,而且大鱼吃了小鱼还不算,还会参与政治、影响政治决策,以更进一步创造一个偏离“自由市场”的、更有利于自身的经济环境。因此,如果放任自由市场主导经济活动,必然会出现黄所抱怨的大企业越搞越大、而小企业举步维艰的情况。相反,要想使小企业能有生存的空间,所需要的恰恰是国家对市场的适当干预和对大资本的约束。
黄还对社会不均的增加也做了分析,且认为是国家对市场的干预而不仅加剧、且恶化了社会不均。这个观点的问题在上头已经指出了:造成社会不均的主要原因就是小企业衰败而大企业兴旺、使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而空间方面,原来内地的小企业尤其被沿海地区的内资、外资的大企业所挤压,因而大量地破产,使得资源愈发向沿海和大城市集中。而造成这些趋势的原因,说到底还是自由市场在发威。
在证据上,黄又做了个奇怪的事情。现在全中国人都知道社会不均加剧,但他们比黄还多知道一点:最有钱的那些人当中当然有不少腐败官员,但更多的“富豪”则是私营企业家。没有私营企业的迅速增长、没有原来公有财富的流失,何来这么些富豪?何以这些富豪的出现以及社会不均的加剧这笔帐全算到了政府压制私营企业的头上了?
我以前倒是只知道黄是一直高唱要鼓励国内的私营企业发展的。在这一点上,我倒也同意他的观点,让本国的资本家发财,总比让外国的资本家发财好一点。但现在看来,黄是只披着羊皮的狼,他说到底是在为大资本说话,却还打着个关注民生的幌子。要十分警惕才行。
黄还有一个一贯的观点,就是中国的发展将不如印度。这倒是我从来就没有认同过的。印度的私营企业发展得确实不错,但这有其历史原因。而且,如果以同时起步,且在同一领域的中印企业,究竟孰强孰弱还未可知。至于印度的人口与政治制度的优势那更是胡说,这我在以前的文章里已多次提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市场自由化的程度。其实,中国市场的自由化程度看来远比印度要高。我目前还没有系统的数据分析,但直观来看是如此。比如说对劳动力市场的限制,印度的劳动保护法远比中国目前的严格。另外,印度还有诸多商品的市场都不是完全开放的,比如说化肥。印度政府至今仍有诸多的部门直接负责经济生产。比如说农业机械部,如此之细之专的政府经济管理部门,即便是在中国的计划经济时代、条块分割的体制下,也都没有。我并不认为这些约束市场的国家行为使得印度的本国企业更有竞争力,但起码这些可以表明,印度的私营企业如果更有竞争力的话,绝不是因为他们有一个更加放纵的自由市场。不过,反过来的结论倒是有可能:中国有更放纵的自由市场,而中国的私营企业也因此更有竞争力。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读后感(四):别的不说,先把它的得出来的观点抄在这里
全要素生產率一般的含義為資源(包括人力、物力、財力)開發利用的效率。從經濟增長的角度來說,生產率與資本、勞動等要素投入都貢獻於經濟的增長。從效率角度考察,生產率等同於一定時間內國民經濟中產出與各種資源要素總投入的比值。從本質上講,它反映的則是各國家(地區)為了擺脫貧困、落後和發展經濟在一定時期里表現出來的能力和努力程度,是技術進步對經濟發展作用的綜合反映。
全要素生產率是用來衡量生產效率的指標,它有三個來源:一是效率的改善;二是技術進步;三是規模效應。在計算上它是除去勞動、資本、土地等要素投入之後的“餘值”,由於“餘值”還包括沒有識別帶來增長的因素和概念上的差異以及度量上的誤差,它只能相對衡量效益改善技術進步的程度。
50年代,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伯特·M·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提出了具有規模報酬不變特性的總量生產函數和增長方程,形成了現在通常所說的生產率(全要素生產率)含義,並把它歸結為是由技術進步而產生的。)
全要素生產率是巨集觀經濟學的重要概念,也是分析經濟增長源泉的重要工具,尤其是政府制定長期可持續增長政策的重要依據。首先,估算全 要素生產率有助於進行經濟增長源泉分析,即分析各種因素(投入要素增長、技術進步和能力實現等) 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識別經濟是投入型增長還是
效率型增長,確定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其次,估算全要素生產率是制定和評價長期可持續增長政策的基礎。具體來 說,通過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對經濟增長貢獻與要素投入貢獻的比較,就可以確定經濟政策是應以增加總需求為主還是應以調整經濟結構、促進技術進步為主。--转自MBA智库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