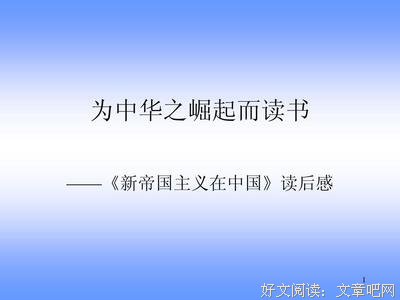
《新帝国主义》是一本由大卫·哈维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5.00元,页数:18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新帝国主义》精选点评:
●新马
●路转脑残粉~作为西方最负盛名的新马克思主义学家,哈维的字里行间都渗透着空间思想。
●在帝国主义推动下的美国(及其他国家),所采取的诸种措施和手段,一方面确实有迷惑性,另一方面也是相当可怕的。在这其中,资本的作用固然不小,但人性、组织偏好、国家利益等方面也值得思考。
●服用第三章疗愈经济危机。ps,貌似是时政吐槽之作=。=
●按需。
●运用哈维的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对帝国主义的再解读,认为资本主义在无法维持一定的利润的时候就必须进行“ 空间修复”,向外部进行“剥夺性积累”。哈维认为原始积累(即“剥夺性积累”)并不只是在资本主义的初始阶段,而是会在利润率下降时反复进行。虽然哈维对卢森堡的消费不足论持批判态度,但是这个思路感觉还是在罗莎的理论构造范围内。
●读了“资本束缚”一章,三级循环、资本积累的分子化、时间-空间修复、转移危机......这些概念整合起来,对国内和国际的资本流动都有体系化的认识。
●阿锐基的两条逻辑:权力的领土逻辑与资本逻辑之间的辩证关系(何种意义上的辩证,这两条逻辑是否可以结合起来——资本主义的欲望逻辑?)应该如何看待阿伦特的理论资源?老问题:卢森堡与阿伦特与卢卡奇的关系。卢森堡的老问题:如何区分剥夺性积累与原始积累之间的关系?最后,革命的希望何在?所谓第
●吾道一以贯之
●领土逻辑与资本逻辑、扩大再生产与掠夺性积累的辩证
《新帝国主义》读后感(一):帝国主义:仍然很有效的一个说法
我常常有个困惑,为什么世界上很多空难灾难发生时,都有中国人身陷其中.看了哈维这本书,我似乎有了一个答案.
我还有一个困惑,现在不都是"文化霸权"了吗?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国家要发动战争,搞点可乐汉堡什么的不就可以殖民过去了吗?看了哈维这本书,我似乎也有了一个答案.
马克思说,有两个因素,只有两个,可以带来资本,一个是土地,一个是劳动力.
哈维这本书是写给美国政府看的,他太可怕了.
《新帝国主义》读后感(二):为什么哈维的许多书都变成了稀缺品?
没别的,就这个问题。
好在新帝国主义入手早。
如今新自由主义简史买不到,好在台湾还能买到。
到底是版权问题,印数问题,还是哈维内容的问题。。。我猜。
比如剥夺性积累的问题,内部殖民问题,新自由主义应用在中国的问题,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新左翼定位问题、民族主义遇上共产主义的问题、汉族与少数民族的问题、宗教兴起的问题,经典工人阶级解体的问题、改革开放后经济转型的问题、金融资本兴风作浪的问题。。。。
期待大家赐教!
《新帝国主义》读后感(三):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读书记录
这本书是作者对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深刻描摹。基本观点是,帝国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的最高/最后阶段(列宁观点),现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仍然在实行一种帝国主义的发展方式来维持自身的持续增长。大卫·哈维称之为“资本帝国主义”,是一种新帝国主义。
作者借用阿瑞吉在《漫长的20世纪》里的概念,认为“资本帝国主义”是“权力的政治/领土逻辑”和“权力的资本逻辑”的结合。两个逻辑关系复杂,在本书中总体表现为“领土逻辑”对“资本逻辑”的追赶,即资本逻辑常表现为资本在贪婪而不受约束地在全球开拓新的盈利点,而政治/领土逻辑则通过自我的延伸、扩张为资本逻辑提供后备支撑(作者认为这样的领土逻辑就是“霸权”的本质)。因此二者并非齐头并进,从这个意义上作者也常说二者是存在矛盾的。
那么资本逻辑和领土逻辑的衔接点在哪里?这个问题其实与问题“资本主义如何在当今维持自己的生命”相关。针对作为资本主义危机的过度积累问题(包括资本和劳动力的过渡积累),作者提出“时间-空间修复”理论,认为这是吸收过度积累(或称“盈余”)的方式,也就是目前资本主义自我拯救的方式。时间修复:投资长期项目,来推迟资本价值重新进入流通领域的时间。具体表现为资本循环的变换,使资本跳出直接生产/消费领域的“初级循环”,进入固定资本/消费环境建设构成的“二级循环”或社会支出/科研开发的“三级循环”。而空间修复,则在于开发新的市场、劳动力、资源等,进行空间转移,包括商品输出(销售剩余商品)、资本输出(贷款给外国,然后让外国买本国的产品,如世界银行对落后国家的贷款。考虑到中国是美国最大债权国、中国生产的日用商品又在美国占领大量市场,似也可说中国在对美国进行这个意义上的“资本输出”?)。空间修复其实是全球范围内不平等空间的创造过程。因此可理解:帝国主义=非均衡地理关系+非对称交换关系。
而上述这两个资本逻辑的转换过程,自然是由领土逻辑(国家力量)来辅助的。由此,两个逻辑的衔接,就是资本主义的自我拯救,也就是资本帝国主义在全球的蔓延。
这种描述非常像马克思笔下的原始积累过程。事实上作者也是认为残酷、暴力、剥削的原始积累其实一直贯穿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直到现在。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是保守的。作者将马克思的原始积累大胆延伸到当代资本主义,称之为“剥夺性积累”。借用金融工具和国家权力,当代资本主义在全球进行的剥夺性积累其实依然残酷。借用新自由主义的话语,资本逻辑在全球寻求剥夺性积累的对象的过程,就是全球化的过程,也是资本主义寻找、甚至创造“他者”的过程。当然,这种“剥夺性积累”在国家内部也有表现,就是(公共服务)的私有化。
作者在最后也做了一波呼吁,提倡将资本逻辑摆脱新自由主义轨道,国家权力应更具干涉主义,使之成为“仁慈的”“新政”帝国主义。但此有多大希望,未得到充分论证。
全书语言清晰,非常好读。充满马克思的色彩,而全书内容在城市社会学领域中的大卫·哈维理论也是基本一致的(资本在城市的循环再生)。阅读全书还常可见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的影子,而这种非均衡空间的创造也是空间社会学的重要议题。“时间-空间修复”理论可视为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延伸(二者都在回答当代资本主义如何自我维持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哈维将这种地理空间理论和(领土逻辑与资本逻辑交织而成的)新帝国主义/资本帝国主义结合,显得更为深刻且有全球视野。但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的关系还需进一步加深阅读,只理解为“前者对后者的追赶”我觉得是不够的。可延伸阅读阿瑞吉原书。
《新帝国主义》读后感(四):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读书记录
这本书是作者对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深刻描摹。基本观点是,帝国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的最高/最后阶段(列宁观点),现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仍然在实行一种帝国主义的发展方式来维持自身的持续增长。大卫·哈维称之为“资本帝国主义”,是一种新帝国主义。
作者借用阿瑞吉在《漫长的20世纪》里的概念,认为“资本帝国主义”是“权力的政治/领土逻辑”和“权力的资本逻辑”的结合。两个逻辑关系复杂,在本书中总体表现为“领土逻辑”对“资本逻辑”的追赶,即资本逻辑常表现为资本在贪婪而不受约束地在全球开拓新的盈利点,而政治/领土逻辑则通过自我的延伸、扩张为资本逻辑提供后备支撑(作者认为这样的领土逻辑就是“霸权”的本质)。因此二者并非齐头并进,从这个意义上作者也常说二者是存在矛盾的。
那么资本逻辑和领土逻辑的衔接点在哪里?这个问题其实与问题“资本主义如何在当今维持自己的生命”相关。针对作为资本主义危机的过度积累问题(包括资本和劳动力的过渡积累),作者提出“时间-空间修复”理论,认为这是吸收过度积累(或称“盈余”)的方式,也就是目前资本主义自我拯救的方式。时间修复:投资长期项目,来推迟资本价值重新进入流通领域的时间。具体表现为资本循环的变换,使资本跳出直接生产/消费领域的“初级循环”,进入固定资本/消费环境建设构成的“二级循环”或社会支出/科研开发的“三级循环”。而空间修复,则在于开发新的市场、劳动力、资源等,进行空间转移,包括商品输出(销售剩余商品)、资本输出(贷款给外国,然后让外国买本国的产品,如世界银行对落后国家的贷款。考虑到中国是美国最大债权国、中国生产的日用商品又在美国占领大量市场,似也可说中国在对美国进行这个意义上的“资本输出”?)。空间修复其实是全球范围内不平等空间的创造过程。因此可理解:帝国主义=非均衡地理关系+非对称交换关系。
而上述这两个资本逻辑的转换过程,自然是由领土逻辑(国家力量)来辅助的。由此,两个逻辑的衔接,就是资本主义的自我拯救,也就是资本帝国主义在全球的蔓延。
这种描述非常像马克思笔下的原始积累过程。事实上作者也是认为残酷、暴力、剥削的原始积累其实一直贯穿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直到现在。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是保守的。作者将马克思的原始积累大胆延伸到当代资本主义,称之为“剥夺性积累”。借用金融工具和国家权力,当代资本主义在全球进行的剥夺性积累其实依然残酷。借用新自由主义的话语,资本逻辑在全球寻求剥夺性积累的对象的过程,就是全球化的过程,也是资本主义寻找、甚至创造“他者”的过程。当然,这种“剥夺性积累”在国家内部也有表现,就是(公共服务)的私有化。
作者在最后也做了一波呼吁,提倡将资本逻辑摆脱新自由主义轨道,国家权力应更具干涉主义,使之成为“仁慈的”“新政”帝国主义。但此有多大希望,未得到充分论证。
全书语言清晰,非常好读。充满马克思的色彩,而全书内容在城市社会学领域中的大卫·哈维理论也是基本一致的(资本在城市的循环再生)。阅读全书还常可见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的影子,而这种非均衡空间的创造也是空间社会学的重要议题。“时间-空间修复”理论可视为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延伸(二者都在回答当代资本主义如何自我维持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哈维将这种地理空间理论和(领土逻辑与资本逻辑交织而成的)新帝国主义/资本帝国主义结合,显得更为深刻且有全球视野。但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的关系还需进一步加深阅读,只理解为“前者对后者的追赶”我觉得是不够的。可延伸阅读阿瑞吉原书。
《新帝国主义》读后感(五):中国:全球资本的“海绵宝宝”
原文发表于《中国图书评论》(2010年第9期)http://qiuin.com/translation/261.html
奥巴马是在小布什政府对伊拉克战争业已陷入越南式的覆辙,美国国内的次贷危机彼已危及至实体经济的“内忧外患”之时上任,其后的政策也正是着眼于国内和国际这两方面危机的处理。国内方面,奥巴马转变了里根执政以来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而采取一种干预的新凯恩斯主义;国际关系方面,奥巴马放弃了布什的单边主义政策,特别是自上任起对中东地区的访问,显示了其试图通过认同而非强制来重塑美国形象。美国这两方面的“新政”似乎都像是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中所作预言的实现。
我们最熟知的就是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也是最后阶段,然而阿伦特则持相反的看法,她认为19世纪末帝国主义的兴起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权的第一个阶段,而非资本主义的最终阶段。阿瑞吉在《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中论述了帝国主义从荷兰到英国再到美国的两次转变过程中,政治结构经历了从城市联盟体系到民族国家体系再到全球化体系的变迁。哈维根据阿瑞吉的观点,结合自己的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理论分析了帝国主义的政治逻辑与资本逻辑牵扯勾连。
政治/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是哈维定义的“帝国主义”的两种矛盾融合的要素。前者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方案,其行为体的权利建立在拥有一定领土,能够动员其人力和自然资源来实现政治、经济和军事目标的国家和帝国的政治;后者作为一种在时空中扩散的政治经济进程,支配和使用资本占据着首要地位的资本积累在时空中的分子化过程。(第24页)
美国这个在“两战”中崛起的新帝国,其虽然遭遇或正在遭遇来自苏俄、日本、欧盟以及中国等方面的挑战,但它仍然是当今世界政-经体系的主导性霸权,这一点似乎没人可以否认。特别是小布什执政时期,美国俨然已成为“帝国主义”在当下的代名词,由此激起的不仅是来自伊斯兰国家和东亚国家以及俄罗斯这些宿敌的反对,而且也激起了原本是其“反共同盟体系”的欧洲国家的反对。这些反对的声音一方面是对“美帝国主义”的政治或领土逻辑的抵制,更多的一方面是对全球化即美国化的资本逻辑和文化逻辑的抵制。
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有其自身致命的缺陷,即资本主义危机。引起危机的部分原因是消费不足所导致的,这是我们熟悉的马克思关于财富两极分化的论述。但哈维认为,过度积累,即缺乏赢利性投资的机会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过度积累导致了两种盈余的产生:资本盈余和劳动盈余,其中资本盈余是主要问题。资本主义必须通过时空修复来解决此问题。时空修复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时间延迟,通过将资本的长期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来吸收,另一方面是空间转移,即扩大市场,地理扩张。如果赢余不能被吸收的情况下,只能通过贬值来解决危机,资本贬值的结果是通货紧缩,劳动贬值的结果是失业。以吸收的方式解决资本盈余是资本主义创造性的一面,而贬值的方式则具有极大的破坏性。
资本主义面临多次危机与重组,同时在左翼和右翼不断预言其即将终结的情况下,仍然如此顽强的生存了下去,丝毫没有走到尽头的征兆,这个谜题的谜底哈维用时空修复理论为我们予以揭示。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正是过度积累所造成的,美国战后一方面通过将其资本盈余转移至欧洲和日本等国家来振兴其经济,这是时空修复的空间转移;一方面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如高速公路网和固定资产投资等延缓其资本,是通过时间延迟的方法解决资本赢余问题。然而,在这时空修复过程中,也就是美国通过认同的力量建立霸权对抗共产主义阵营的过程中,又树立了其竞争对手,那就是欧洲特别是德国和日本以及东亚四小龙等国家地区的快速发展使得该地区资本出现大量盈余,资本与劳动市场双双达到饱和。随后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开始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也就是将原先资本不能进入竞争的领域予以开放,以吸纳盈余资本,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新自由主义成为横扫一切的力量,历史似乎又折回到了马克思所在的160年前。
目前,中国作为吸纳全球资本的“海绵”,正在吸收来自全球各地的资本盈余。资本逻辑要求国家政治的强势力量下建立全国统一市场,取消地区保护;资本逻辑动用政治逻辑压制其反对力量,在土地、劳动力以及自然资源进行商品化和市场化。从地区发展来看,在经历了30年代有偏向的地区经济发展后,中国制造了庞大的“劳动后备军”——农民工,中国东南部地区正是通过“创新性”(其新颖之处在于,中国的户籍制度使得这一部分人口并不纳入城市就业的统计之中,因此如果在出现劳动盈余后并不显示为“失业”)的引入这些来自中西部的廉价劳动力,积累起了大量的资本盈余。他们一方面将资本转移至海外地区如更不发达的越南、非洲等国家,另一方面又将这些通过廉价劳动力所积累的资本盈余投资到中西部去。最典型的如房地产领域,东南部作为城市地标的光鲜摩天大楼上刻意隐去了建造者的身影,而来自这些地区的资本又频繁的光顾内地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当地政府并不出于本地居民的权益保障其有能力购买本地房产,而是热情拥抱这些外地资本一步步抬升房价。在GDP作为政绩衡量指标的体制下,以发展作为整个国家政治中心功能的制度中,打造一个能够吸引各地、全球资本的良好投资“环境”才是最重要的,其他一切要求都需要让位。经济的发展最终并非成为改革集权体制的推动力,反而进一步强化了集权体制的弊病。
海绵吸的东西越多只会越来越自我膨胀,然而无论吸纳多少,也改变不了其本身的内在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