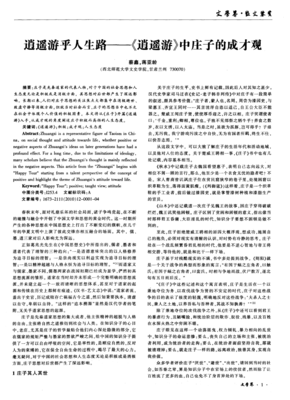
《逍遥游》是一本由班宇著作,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2020-5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夜莺湖》
羊汤
麻辣排骨串
炖豆角
《双河》
(这篇里基本都是半成品)
排骨
炸葱花
茄子过油
《逍遥游》
鸡蛋酱
丹东九九
炒面
酱板鸭
锅烙(韭菜鸡蛋馅)
鸡蛋饼
豆腐脑
《渠潮》(吃的最多)
小葱豆腐
炒土豆片
鸡蛋酱
虾皮
鸭溪窖酒
司考奇
运动糖
红烧肉
抻面
土豆炖豆角
高粱米水饭
天津糕点
榛蘑炖鸡
芹菜炒粉
干豆腐
黄牌啤酒
焦熘虾段
八王寺
炒白菜
馃子
豆腐脑
浆子(加白糖)
这几年一直有一个很“文学史”的提法,叫“东北文艺复兴”。班师这本书刚一出来,恰好几天前双雪涛《聋哑时代》再版,于是这个词语又开始满天飞。弄得我有点不太开心,因为一直以来,我都不大喜欢“东北文艺复兴”这个提法。主要出于两方面的原因吧。想在这里简单说说。
“复兴”这个词是有一个从衰落到再次兴盛的一个过程。可是东北的文艺工作者一直以来并不缺乏。最有名的就是早一点民国的东北作家群,萧红、萧军、端木蕻良等等。然后稍微近一点的有迟子建、梁晓声等等。我简单报这么一下菜名就是想说明东北其实一直以来都有很大一批优秀的小说家(电影等方面不很了解就不列举了,也列举不了)。所以说这个复兴的概念,相对过去的文艺来说,很难站得住脚。而如果说“复兴”是相对于东北的工业和其他一些方面来说,主语变化下,“复兴”的说法似乎也是显得有点牵强。工业不兴文艺兴,怎么能说是“复兴”呢?
第二个方面是,“东北文艺复兴”强调“东北”,而“东北”在现在似乎会给人一种刻板印象,也就是我们讲的标签化。
是不是提到“东北”,就一定是冷风与烈酒,绝望与斗争,荒诞与滑稽呢?我觉得在进行阅读的时候,不能事先在手边备好纸巾等待哭泣。如果带着“纸巾”去阅读,夜莺湖就仅仅是东北的夜莺湖,而难以看到它更深层次的(这个词不太好,不能说哪个就比哪个深,但大概是个意思)更多的城市里的那些处于困境的人们。并且,如果夜莺湖仅仅是东北寒冷的漏电的夜莺湖,对于我这样一个语言、语言节奏、生活、生活方式与北方截然不同的南方人来说,是很难打动我的,我可能会因为被强调的“东北”这个名词,更多地在感受“陌生化”带来的冲击。所以我觉得一个比较好的态度应该是像罗恩拉什说的那样,地域是一种个性,是通往共性的一把钥匙。并不是说通向共性就一定更好,但是如果能够去掉这个“东北文艺复兴”的标签化,或许能让我们看到更多的可能性。
这是我个人的一点想法,还并不是特别成熟,也不一定对。只是想作为一则简单的书评,既是自省,也是善意地提醒并期待将要读这本书的朋友们,去挖掘这本书中“隐藏在海面下的八分之七”的可能性。最后再次赞美一下《夜莺湖》和《山脉》两篇。
《逍遥游》读后感(三):有待而逍遥
据我所知,对庄子逍遥思想的理解有很多种,比如郭象对“小大之辩”的态度就是“小大同扬”,他认为“适性”就能逍遥,也就是说每个个体认识到自己本性的限度,努力达成自己的性分,就可以达致逍遥,因此小鸟和大鹏都是逍遥的;比如支遁的态度与郭象相反,他觉得庄子的原意是“小大同抑”,小鸟和大鹏都有需要依凭的东西,所以都没能逍遥起来,只有“至极”才称得上逍遥。庄子他老人家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恐怕没人知道。我倒是觉得,与其想那么多,还不如就站在第一层,按字面意思理解,“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大鹏逍遥而蜩与学鸠和斥鴳不逍遥,无他,大鹏巧妙地利用了自然条件使得自己能够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翱翔天地之间,积极地化有待为无待,不像小鸟们叽叽喳喳的,啰嗦。
但是仔细想想,郭象的理解说不上错甚至还很有道理,问题可能出在鲲鹏寓言本身。寓言总是要落到人类世界的,但是人和人之间又不像大鹏和小鸟之间一样有类的差别,难道有的人生来就和列子一样能御风而行吗?至少在班宇的小说里没有(终于到正题了)。人活在世上或多或少总是有牵挂的,有时候人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有这些羁绊。当这些有的没的真没了,人也就离死亡不远了。我很喜欢这本书的原因在于,作者对这种有无之间的方寸感把握得很好,再虚一些就抽象了,再实一些就无聊了。信仰、思想和观念就像无数的蚂蚁一样聚拢而成人形,人物的心里还有人物,故事的背后还有故事,读这种故事,佐酒大概是最好的。
对人来说,什么是逍遥呢,许玲玲登澄海楼想起“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那一段有些点题的意思。病弱的个体在面对浩荡无匹的磅礴自然时被它的美所震撼,一时间产生了随之而去纵浪大化的想法,然而就在这个晚上,她遭遇了好友和疑似追求者的双重背叛,从天堂到尘世只需一秒,但是那天堂毕竟是亲眼见过了的。回到家,看到家里亮着两盏灯,她就知道父亲和别的女人在家,虽然她平时是这么讨厌父亲和别的女人在一起,但最后还是没有回去,而是选择把最后一点时间留给父亲,自己置身于冰冷的黑暗中。我总感觉对许玲玲来说,身影隐没在孤独当中的那一刻可能才是最终的逍遥,因为只有在那一刻,父亲以往点滴的付出(包括一个人在家只点一盏灯)在眼前浮现,她感受到了爱,于是选择给予父亲以宽容和理解来回报这份爱,在被爱与爱之间,在有牵挂羁绊之时,人或许才能在俗世之中感受到一点点快意与逍遥。
《逍遥游》读后感(四):鼓手与圣徒
《逍遥游》这七篇小说的创作时间与《冬泳》互有交错,最早可追溯至两年前,最迟一篇完成于去年年末。临近出版,我又重新修整一遍,多是细节之处,改动不少,整体结构变化不大。之所以选择这些篇目,是我在重读时,觉得它们尚能信任,有些韧性,不止于虚饰,即便当时的情绪无法重置,也愿意再次投入进去,仿佛非如此不可。
如果说在之前的写作里,我尝试成为一位泳者,维持着某种精妙的平衡,向着彼岸,游过此季,“那可以毁灭他的深渊轻轻支撑他”。那么在如今,无论暴雨亦或潮汐,均愈发响亮、愈发迫近的时刻里,席勒的叙事长诗《潜水者》或许更为贴切,泳池必将化作深海,浪涛层积,沉没全部伟大的轻蔑,“泅水者已无踪无影,大海上面是一片寂寥”,跃入其中的侍童,有时可以返回,有时则不能。落水的金杯如同一次试探,人们总想着要与魔鬼做交易。
另一个不太遥远的传说里,落魄的布鲁斯歌手Robert Johnson也是如此。苦难过后,他在午夜离家,拎着一把破吉他,如受启示,来到密西西比南部的61号公路和49号公路交叉的十字路口,与魔鬼签订一份协议,这使他获得超人的天赋。当然,超人能使一条浊流重新融入海洋,变得自在而清澈。从此,他的琴技出神入化,深刻精湛,无可匹敌。相应代价则是失去自己的灵魂,将之交由对方处置,最终被一杯毒酒带走。他在歌里唱道:“我和魔鬼,肩并肩走着;我和魔鬼,噢,肩并肩走着。”
魔鬼有时不以你所理解的方式存在,可能要更温和、宽容,更有耐心,如同绅士,一语不发,坐在街口,礼帽置于膝上,微笑着聆听,点头或者摇摇头,然后站起身来,舒一口气,与你同行,肩并肩走着,在所有的长路与长夜。甚至无须需什么协议,你也会相信,大地无非群星的倒影,迷途犹如归途,他是你唯一的同伴,从而将灵魂拱手相赠。但请不要。你并不需要这样。真正的同伴永远不会紧步相随,他只是守望,只是等待,在所有路的尽头。而非十字路口。
我时常觉得,作品不属于自己,很难去解释,那些结局或者开始,声音与手势,意义和价值。冰山也即魔山。在那里,我们曾是智人、诗与天使,互换一场飓风,徜徉于所有语言的边界,先使其高贵,又使其焚,最终使其尽毁。如果我能说点什么,那也一定词不达意,与初衷背道而驰。而沉默从来不被认为是一种抗争,它被视作狡辩,或者许可,偶尔还是懦弱,时刻要被裹挟与撕裂。正所谓:一朝悲歌成金曲,愁容骑士更多余。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陷落在这种困境之中,文学,或者写作,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生命角色?也许不过是一束稻草的影子,没办法攀附,更谈不上拯救了,只是在漫长的、趋于空白的时间里,人与自己做的一点游戏。但至少,它可以让我在那些狭长曲折的夜晚,雷声隐隐的清晨,走得稍稍轻快一些。
以前读小说,有一句印象深刻:你们因狂傲、因双臂有力而自欺,上帝说,你们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必从那里拉下你们来。语出圣经,小说转述。必须承认,事实上,我从未如鹰,也从不逍遥,如果有一瞬间,徜徉于狂傲与自欺,那不过是一种卑微的幻觉。幻觉虽不真实,但却足够诚实。就像这些小说,被侮辱过也被损害过,甚至还可以是侮辱与损害本身。这几年里,我持续在抽打词语,繁衍句子,如一位种族的统领,爱抚或者施暴,将它们带至近前。驯服的同时也意味着彻底的丧失。唯余空无,在黑暗里猎猎作响。我不得不走入其中,这里没有魔鬼,只有无数的声音,无数的人,如矿脉一般持久深埋。
所以,这些小说并非羽翅,没有飞行的余地,仅是我在坠落时那不曾间断的痕迹,渡涉乌云、季节与旷野,独自一束,如远处的鼓声,拂过结冰的湖面,也许没这么孤绝,而是一些告解与叹息,空旷冷落,但彼此相依。至于谁是鼓手,谁又是圣徒,那并不重要。总会有光,驶于冰上。无论如何,永远在同一时刻,你们从此行过。
最后,致谢出版方,我的编辑罗丹妮女士,黄平丽女士。我从来都不是一个有多少力量的人,更谈不上缜密与细致,尽管无比渴求,但她们是。当然还有你,我以此书献给你。它是一封午后的长信,也是一次不倦的造访,我的诚挚的友人。
《逍遥游》读后感(五):且写写
花花世界迷人眼,没有故事别赛脸。
其实东北老工业这个时代背景是很有话题性的,因为那一时代的故事——工业家属区、下岗、集体企业、铁饭碗不只出现在东北,还出现在河北,出现在南方(轻工业)。这本书的几个故事仿佛是围绕东北特定时期的关键词所写的命题作文,盼盼、蚂蚁等(书刚到手,就看了两个故事《蚁人》《夜莺湖》)。不同于《冬泳》里囿于时代背景下的个人情绪,《逍遥游》所描述的东西更为局限,甚至无法跳脱网络给作者的评价——“东北文学代表”的桎梏。说局限,其实是更为神道,用词很绕,翻来覆去的一种情绪,当时《冬泳》给我的感觉是万青那张专辑的凌厉直白,那么《逍遥游》就是现代有点烂大街民谣的虚无缥缈。
给点劲儿,整瓶二锅头。
看完了,《逍遥游》之后渐入佳境。
花花世界迷人眼,没有故事别赛脸。 3.5吧,似曾相识的结构、似曾相识的语言、似曾相识的意向,像是三伏天闷热潮湿的天气,但又缺少一场突然而至的暴雨,不够闷热潮湿(《雨》),又不够大雨祛暑,差点意思。 词语之间的连接、没有主语的对话、和几乎在每篇都会出现的河流和水,整个把笔下的东北缠住,经过那个时代的读者可能感到窒息,而擦擦接触那个时代末尾的我感到窒息的原因是我不想被“水草”缠住,我也不是很想总看到这种氛围的东北故事。
记得早先三联出版了一本介绍东北的一期,有对三个近年大热东北作家的采访,以及对东北现在文化的报道,我很不喜欢。那期笔者仿佛自带偏见,眼里看到的感兴趣的就是作者笔下的东北,对话进一步加深了大众通过文章、电影、纪录片所得到的东北印象。打卡不止的万顺啤酒屋就是劣质啤酒而已、满是厂房的铁西工业只得在北四路略有窥探、味道难闻乱排乱放的卫工明渠现在早已能够养鱼。一些故事,写一写看一看就行,没有必要在现实中找到映射的实物。
《安妮》读起来有点像《白象似的群山》。
其实写的评论不太符合对整本书的评价,故事后几个都还行,在沈阳音乐串吧不停表演灌酒绝活的大哥会在回家的出租车后座上,往向窗外稀稀落落的灯光,眼里泛着光,透过去不知道是望着远在牡丹江的父母,还是看不到的未来,抑或是只是那好似把人吸进去的黑夜。
故事很像快手的“伤心社会摇”,读起来呜呜渣渣,合上书,真的有点“伤心”(伤心在于希望班宇下一本书写点别的,可以以最后一个故事《山脉》为接续,《山脉》的整篇格式不同之前,在探索,再写东北“小人物”就写无可写了)。 东北文学有两种吧,一种是带着东北特质的故事和写作技巧,粗旷凛冽;还有一种是写发生在东北的故事,特定时期对生活的迷茫颓丧。东北是作者的来处,不忘来时路,但我也祝愿他能带着“东北”走出东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