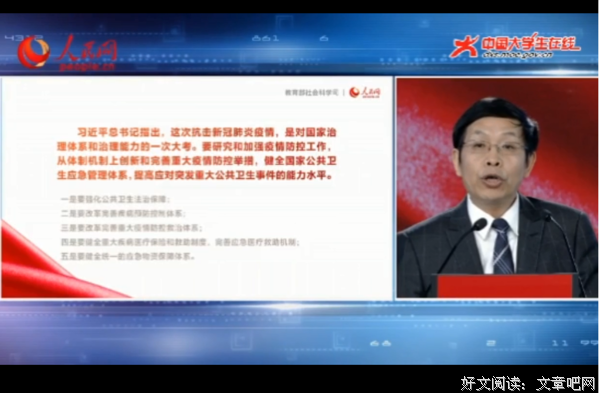
《绿窗艳影》是一部由弗里茨·朗执导,爱德华·罗宾逊 / 琼·贝内特 / 雷蒙德·马西主演的一部剧情 / 犯罪 / 黑色电影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观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多有趣的结尾啊,人如何用梦重组现实。猜想科恩兄弟应该从此类电影中受到不少启发吧,普通人如何因为欲望陷入万劫不复。
●虽然开头就有猜到这可能是一张美人画引发的梦境。但精彩的是,弗朗茨朗用极为细致的方式表明了人的负罪感与恐惧感如何能引发出一个无尽的入套解套再入套的幻想,让观众在代入了这个人物困境的基础上,可以看清这场梦境或者说这个故事的因果编织脉络。也让中段男主角的“自投罗网”,与女主谋害敲诈者的失败,这两个看似“愚蠢”的行动,都具有了一种因心理焦虑的所构建出的幻想性的叙述合理性。也反映了心理教授这个职业特有的思维如果过于复杂缜密,反而让自己脱不出焦虑各种线索暴露可能性的包围与纠缠。
●朗去美国了美国后,隐隐觉得锐气减退了很多
●讓影片顯得更為有趣的不是結尾的反轉,而是它和開頭的應和。中年男子對美人及冒險怯怯的幻夢。咦我是在期盼一個朗視聽風格的洪派故事嗎。
●黑色
●罗宾逊那常年不变的拙糙感可以让任何一部他主演的电影和精致无缘,就像成龙一样。
●穆赫兰道会不会有受到这片的启发呢
●无语.
●bampfa
《绿窗艳影》观后感(一):stop
在看起来要发生什么的时候戛然而止了,在高潮来临之前,射了。铺垫了很久,冲突即将点燃的时候,一切恢复0点。
当然可以是南柯一梦,无所谓。不过也许可以做到更好呢。老实说,我没有看出教授留出太多的痕迹,警察似乎也没有太多的证据,莫名其妙的出现一个blackmailer,然后他又死掉了。这个剧本真的写的挺奇怪的。
每个人从生下来的那一刻起就开始逐渐的走向衰老,二十岁的时候,看见年轻的姑娘或许会有一些想要的念想,而人过中年以后,得到与得不到其实已经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这些细碎的念想,让他们能够回忆起自己年轻的时候。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对美好的事物趋之若鹜是一种本能,在弗里茨.朗导演的《绿窗艳影》这部电影中,我们看见的是一个中年男人啼笑皆非的春梦。
一名大学教授为街边玻璃壁橱中的美女画像所痴迷,当他独自欣赏的时候,画中的人物突然出现在自己的眼前,就是因为这次偶然的相遇,让大学教授的生命轨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和美女单独相处的时候,不慎成为了杀人凶手,为了保护自己的名誉,他不得不选择毁尸灭迹,然而当案情逐渐水落石出的时候,观众看见的却是一场啼笑皆非的闹剧。
观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习惯性的拿弗里茨.朗和希区柯克进行对比,虽然没有一个高低之分,但是作为黑色电影大师,两位导演也各有特点。《绿窗艳影》的剧情比较简单,和后来许多诡异多端的其他黑色电影相比,本片的谋杀以及勒索丝毫没有悬念。而且演员和演员之间的对话很直白,作为一部悬疑电影,观众自然不难预料到故事的发展,当结果浮出水面的时候,我想大多数观众和我一样哑然一笑。弗里茨.朗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善于控制节奏,把一个简单的故事讲的如此引人入胜,通过镜头,把男女主角的困境一步一步展示在观众面前。
作为一部出色的黑色电影,自然离不开黑色电影应有的特点,本片的题材依然是来自社会的黑暗面,情欲催生的谋杀,名利催生的毁尸灭迹。黑色电影最为显著的就是光影特点,明暗之间的起承转合,通过阴影部分来切割画面或者演员的面部表情,通过明暗反差的视觉效果来营造氤氲晦暗的环境。黑色电影不管是电影形式还是内容都离不开社会或者道德上的阴暗面。为了让黑色电影更具有特点,所以很多黑色电影中的场景都是室内景或者夜景,在布景的选择上尽量迎合明暗的对比。
弗里茨.朗作为德国表现主义的代表人物,在他后来的电影中表现主义的成分在逐渐的削弱,但是细细观察之后,还可以捕捉到一些有关表现主义的蛛丝马迹。在《绿窗艳影》这部电影中,光线明暗对比很突出,男主角和画中美女呆在一起的时候,或者打电话的时候运用的布光和男主和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运用的布光完全不同,通过这两种方式反映出男主所处的环境以及心理活动的状态。灯光和摄影的完美结合,让人物之间的主观心态相互呼应。美国黑色电影的特点或多或少都有表现主义的影子,但是却没有德国表现主义的明显特征。而弗里茨.朗去好莱坞发展以后,本身的电影也逐渐开始迎合好莱坞的风格以及市场。
整部电影看完之后,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男人的中年危机以及潜意识中的阴暗与自私,爱德华.罗宾逊扮演的教授把中年男人面对的困境以及在道德上的挣扎表现的淋漓尽致。一个注重家庭观念的男人会因为一个迷人的女子走上不归路,暗潮汹涌的情绪在这里自然性的流露。虽然两个人没有直接性的接触,但是那份暧昧,让银幕之下的观众可以脑补很多内容。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挑战道德底线的事情不请自来,一旦触及到每个人心底最脆弱的部分,矛盾就会被激化。不过好在,弗里茨.朗拉着的这把道德之弓最终以玩笑的方式收尾,或多或少也让我们松了一口气。
《绿窗艳影》观后感(三):情节一般,氛围营造不错
镜子,朗最喜欢的道具之一。《M是凶手》中的彼得洛发现自己身份暴露,以及《狂怒》开始,屈赛和杨两人憧憬美好生活,都和商店橱窗的镜子密切相关。而本片的女主角琼班尼特(Joan Bennett),便是在纽约大学教授罗宾逊(Edward G. Robinson)驻足凝视着摆放在橱窗正中的一幅冷艳动人的女人肖像画的时候,第一次出镜。面对鬼魅般现身的神秘冷艳女子以及她出人意料的主动邀约,刚刚送别妻、子的罗宾逊,虽然一直理智地告诫自己“已经到了禁不起诱惑和冒险的年龄”,但依然不由自主地在午夜过后去了她的公寓。可浪漫还未开始,灾祸旋即降临。包养此女子的那位有钱男士不知何故突然返家。一进门便见到房中有其他男人,此公暴怒之下不由分说直扑过去要置罗宾逊于死地。仓惶自保中,罗宾逊抓住班尼特递过的剪刀向对方背部猛刺几下……一个标准的“蛇蝎美女”导致凶杀的黑色电影的开局。可是,故事的后续情节,真会如观众所猜测那样的发展吗?
爱德华·罗宾逊,好莱坞早期的演技派巨星。曾经凭借House of Strangers (1949)精彩表演获得嘎纳电影节最佳男主角。但是,在影片开始的男主人被诱惑的桥段,罗宾逊的表现不太投入,缺乏和女主人公的情感互动。特别是眼神上。这是否因为其外形象,塑造一个能被美艳女子一见倾心的成功中年男人,似乎稍欠说服力所致?哈哈。但在命案发生之后,当故事需要转而刻画出“凶手”的焦躁、绝望、时时刻刻怕真相败露等的情绪心态时,罗宾逊的表演便一如既往地出色和到位了。不过总体上说,还是不如其在同期上映的比利怀特的《双倍赔偿》中所扮演那个睿智机警的保险公司理赔经理的角色给人印象深刻。女主角的扮演者琼班尼特(Joan Bennett),形象的确具有那个时代好莱坞女明星所特有的古典冷艳之美,但表演只能说尚可。而两位明星的组合似乎比较受到朗的青睐。仅仅一年之后,他们又一起主演了朗的另一部影响更大的黑色影片《Scarlet Street (1945)》。
影片拍摄耗时不到2个月。取景大多在米高梅、RKO、派拉蒙的摄影棚。黑色顶棚,封闭的舞台为影片成功营造了幽闭的夜景氛围。RKO于1944年10月在洛杉矶安排首映。次年1月25人在纽约上映。影片的国内票房累计210万美元,而在战后刚刚复苏的海外电影市场的票房也达到了130万左右。
本片最大的争议在于它的结局。当时,就有评论家指出,影片另类结局手法的使用,目的不过是为了通过片审查以及票房。对此,朗给予了否认。他说不止是单纯的“和谐”收场,同时也作为一种手段,为故事发展的提供了一种出人意料的悬念!可某些始终存疑的影评家显然不同意导演的看法。他们认为是前面的叙事把朗逼入了死角,而****式的结局则可使其摆脱出来找到退路。对此朗同样予以否认。无论如何,这位老牌的大导演,期间是没少面对各种各样关于本片细节方面的媒体论战。当然,影评也不都是质疑。纽约某论坛就认为《绿窗艳影》的结局处理,使其很轻松地就成为同《双倍赔偿》一样出色的,充满悬疑色彩的谋杀神秘剧。
但不管是朗的有意而为,还是受到好莱坞类型片模式等外在因素的制约,这场争论本身,多多少少从侧面反映了朗在移居好莱坞后所处的较为尴尬的艺术创作境地。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7b619801000agi.html
《绿窗艳影》观后感(四):导演说
本片出自20世纪德国电影大师弗立茨·朗格之手,是黑色电影的早期作品。作为德国表现主义电影导演,朗格将德国表现主义风格融入美国好莱坞类型电影之中:强烈的明暗对比、不稳定的倾斜构图,以梦境、幻想、象征表现人物内心深处的黑暗面、恐惧心理等。本片通过一桩梦境中的凶杀案,表现了现实与梦境、欲望与压抑、道德与堕落、善与恶的主题,通过对男主人公精神危机、恐惧心理的视觉化呈现,表达了对理性力量的质疑以及对人性堕落的道德批判。
探索人类复杂的内心世界,特别是盲目冲动的一面,是朗格电影反复出现的主题。早在1931年,他就拍摄了德语电影《M》,对人类本性作了深刻的挖掘和表现。主人公M受到内心魔鬼的控制而无法自拔,最终陷入罪恶的泥潭。同样,《绿窗艳影》也是对人类无意识本能的展现。在影片中,我们看到人性的野蛮一面,它能使人脱离日常生活的温文尔雅,逞凶行恶,无法无天,对人类理性发出强大挑战。
在本片中,导演将关注的对象从普通民众转移到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上。万利教授的学者身份和社会地位,都表明他应当是中产阶级道德准则的执行者。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越轨行为的可怕后果。然而,万利仍旧无法控制自己的冲动,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理性力量、道德准则都没能帮助他打败心中的魔鬼。他只能听由内心私欲的摆布,一错再错,直至毁灭。影片最后将所有一切归结为一场梦,一场让万利体验到放弃道德约束会如何可怕的噩梦。这样的安排,表面上回避了万利教授滑向堕落深渊的现实,然而这只不过是好莱坞式的自我安慰。即使是梦,也足以让我们从中窥测到潜藏在万利教授心中的强烈欲望。虽然他的堕落只存在于梦中,发生在银幕上,但从梦里散发出来的血腥味,足以让观众切实感受到那股不安分的可怕。朗格企图传递的信息是,这样的欲望同样会发生在银幕之外,存在于观者的心中。
本片的另一重要主题是探讨人类恐惧感的根源。在朗格的影片中,恐惧感总是伴随着人性的黑暗面出现,表现为受社会道德约束的自我与黑暗面之间的冲突。换言之,朗格是将现实生活中善与恶的较量延伸到人的内心世界,转化为人性中两个对立面之间的激烈碰撞。两种心理力量的碰撞与交锋常常通过人类的恐惧感得到表现。本片中,万利因误杀行为而受到良心、道德的折磨,道德感督促他接受惩罚。但是,一旦真相暴露,他的身份、地位、名誉、家庭等都将毁于一旦,这又迫使万利选择隐瞒。如果说,谋杀是出于自我保护的防卫行为,那么销毁证据、弃尸树林就是有意识的精心策划。对万利而言,捍卫名誉地位的私欲直接与道德正义相冲突。而这种无法调和的冲突让他倍感恐惧,搅乱他的内心,扭曲了他的人格,最终导致他走向绝路,从一时失手演变到蓄意谋杀。计划失败后,万利更是无望。自杀成为他终结苦痛、自我解脱的唯一方法。而选择自杀实际上是在回避事情败露后将失去一切的事实。对万利而言,一时失误造成的良心不安,远不如失去身份地位的恐惧更难以接受。这样的结局,透露出朗格悲观主义的人生观,反映了他对挽救人类道德的不信任。影片最后,万利拒绝了眼前的女色,与其说这是万利在道德上的觉醒,不如说是为了躲避恐惧感造成的心理痛苦。
“蛇蝎美人”是黑色电影的重要元素,本片中女主角艾丽斯成为这一形象的代表。根据女性主义电影理论,黑色电影中的“蛇蝎美人”是男性性幻想的投射物,也是男性摆脱阉割焦虑的手段。为此,“蛇蝎美人”总是以尤物的形象出现。本片中,女主人公艾丽斯初次登场是以画像的形式完成的。临街的橱窗内,画中的艾丽斯半露酥胸,神情魅惑,吸引住了万利教授的目光。他停留在了画前,眼神暧昧,表情微妙。几个镜头在看似不经意,实则形象地阐释了女性主义的理论观点。这里,艾丽斯是万利目光的承受者,迎合并指称了长时间压抑在中年教授心中的熊熊欲火。之后,当艾丽斯犹如鬼魅般地从画中走出,以诱惑者的姿态出现在万利面前时,这份欲望更是获得了最直接的投射。万利陷入对艾丽斯的迷恋之中,并在迷恋中陷入危险境地。但需要指出的是,本片塑造的“蛇蝎美人”形象,相较于其他黑色电影中的同类形象还是比较温和的,因为艾丽斯并没有处心积虑地诱使万利犯罪。但她自私、神秘、性感,具有强烈的诱惑力,最终导致万利堕落,从这一点上看,艾丽斯足以担当“蛇蝎美人”的称号。
在视听方面,本片最成功之处在于对恐惧心理的视觉化呈现。正如前文所述,恐惧一直是朗格主题。在他的影片中,主人公总是陷入强烈的恐惧感中。本片更是以生动的方式把恐惧感呈现在观众面前。它让观众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并冲击着他们的心灵。通过低调灯光的场景设计,暴力事件的突发性以及镜像运用等手段,朗格完成了对恐惧感的视觉化构建。
首先,光线昏暗的室内戏和大量的夜景戏,使影片从整体上呈现一种阴沉、压抑的基调。表现主义风格的布光和对阴影的运用,更是在这种基调之上加重了不安定感。场面调度与人物心理相互呼应,很好地传达了影片的主题。以万利驱车离开艾丽斯家到收费站之间的段落为例。第一个镜头是从车子左外侧拍摄的中景。景框内四分之三的画面都被黑色占据,唯一的光源来自车子右侧的路灯。灯光透过车窗投射进来,在万利脸上形成了一个明亮的光圈。强光下,万利的表情被扭曲,显得异常狰狞。随后,机位转换到车内,一个从背后拍摄的特写镜头。狭小的车内空间里,万利的背影几乎与黑暗融为一体,占据了大部分画面。纯黑的色块,挤压的构图,让人觉得压抑、慌张。紧接着摄影机转到万利的正面。近景镜头下,万利脸部的不安完全暴露在观众面前。此外,挡风玻璃上不断滚落的雨水,路旁在风雨中摇曳着的树枝,都同时在万利的面部投下阴影。它们在万利的脸上不停地晃动,造成了强烈的不稳定感,更加凸显了万利的慌张。副驾驶座上,运动着的车刷的倒影,视觉上就像是来回摆动的钟摆。嘀嗒间,弥漫在车内的不安气氛被推向了最高点。虽然是短短的三个镜头,却因为对比强烈的布光、不稳定的构图、阴影等表现主义元素,自然而又准确地表现出了压在万利心头的那份巨大的恐惧,让观众也感同身受。
其次,对暴力瞬间的真实再现,也是朗格呈现恐惧的重要方式。突发性使暴力行为有一种幻梦般的感觉。于是,在似真似假的氛围下,恐惧、战栗、偏执等极端情绪被无限扩大,充斥在影片的角角落落,使观众在关切万利命运的同时,也会担忧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堕落行为。正是暴力行动引发的强烈共鸣,使影片完成了从呈现恐怖行为到警醒故事的转化。
最后,对镜像、玻璃映像的运用也是朗格表现心理的惯用手法。例如,艾丽斯透过走道的玻璃窗目送万利离开的段落。艾丽斯忧心忡忡的脸庞倒映在玻璃上,被滑落的雨水洗刷着,变得有些扭曲。这里,不稳定感的面部影像正是艾丽斯内心活动的反射,是对她担忧、害怕等复杂心理的视觉化表达。下一个镜头中,雨中万利的车子,因为玻璃的遮挡也显得模糊而失真。加上路灯的照射,雨水的反光效果等,画面变得混乱、无序。应当说,这些失真、变形的画面在此刻正反映了万利实际的心境,也是对他命运的一种暗示。朗格企图传达的信息是,在夜雨中启动的车子奔向的是一场梦魇。
本片的男女主人公分别由爱德华·罗宾逊以及琼·贝内特担当。爱德华·罗宾逊是早期好莱坞电影的实力派演员。他曾凭借在《陌生人之屋》中的精湛表演获得戛纳电影节最佳男主角的殊荣。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他出演了一系列黑色电影,包括《双倍赔偿》、《盖世枭雄》等。女主角琼·贝内特是朗格的御用女演员,她冷艳妩媚,非常符合黑色电影中常见的“蛇蝎美人”形象。值得一提的是,两位演员后来又同时出演了朗格的另一部黑色电影《血红街道》(1945),再次成功地分别演绎了女性的魅力和男性复杂的内心世界。
相较于同时期以探案为叙事核心的黑色电影而言,本片更关注男性主人公被压抑的内心欲望、人类恐惧心理以及个体异化、人性堕落等心理问题。朗格通过紧密的叙事、巧妙的细节设置,精炼的镜头语言以及表现主义风格的布光置景,将男性主人公的无意识情欲、恐惧感、道德困惑等心理因素以视觉化的形式展现在观众面前。朗格构建了一个梦魇般的、接近于自我毁灭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男主人公受到不安、恐惧等极端情绪的挤压,个体身份受到威胁,人性异化,最终陷入堕落。朗格通过黑色电影这一类型探讨人类的心理层面的问题,强调了对个体精神世界的关注。这无疑扩展了黑色电影的表现范围,增强了它的道德批判力度,对黑色电影类型的进一步拓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绿窗艳影》观后感(五):世界电影鉴赏——《绿窗艳影》
本片出自20世纪德国电影大师弗里茨·朗之手,是黑色电影的早期作品。作为德国表现主义电影导演,朗将德国表现主义风格融入美国好莱坞类型电影之中:强烈的明暗对比、不稳定的倾斜构图,以梦境、幻想、象征表现人物内心深处的黑暗面、恐惧心理等。本片通过一桩梦境中的凶杀案,表现了现实与梦境、欲望与压抑、道德与堕落、善与恶的主题,通过对男主人公精神危机、恐惧心理的视觉化呈现,表达了对理性力量的质疑以及对人性堕落的道德批判。
探索人类复杂的内心世界,特别是盲目冲动的一面,是弗里茨·朗电影反复出现的主题。早在1931年,他就拍摄了德语电影《M就是凶手》,对人类本性作了深刻的挖掘和表现。主人公M受到内心魔鬼的控制而无法自拔,最终陷入罪恶的泥潭。同样,《绿窗艳影》也是对人类无意识本能的展现。在影片中,我们看到人性的野蛮一面,它能使人脱离日常生活的温文尔雅,逞凶行恶,无法无天,对人类理性发出强大挑战。
在本片中,导演将关注的对象从普通民众转移到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上。万利教授的学者身份和社会地位,都表明他应当是中产阶级道德准则的执行者。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越轨行为的可怕后果。然而,万利仍旧无法控制自己的冲动,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理性力量、道德准则都没能帮助他打败心中的魔鬼。他只能听由内心私欲的摆布,一错再错,直至毁灭。影片最后将所有一切归结为一场梦,一场让万利体验到放弃道德约束会如何可怕的噩梦。这样的安排,表面上回避了万利教授滑向堕落深渊的现实,然而这只不过是好莱坞式的自我安慰。即使是梦,也足以让我们从中窥测到潜藏在万利教授心中的强烈欲望。虽然他的堕落只存在于梦中,发生在银幕上,但从梦里散发出来的血腥味,足以让观众切实感受到那股不安分的可怕。弗里茨·朗企图传递的信息是,这样的欲望同样会发生在银幕之外,存在于观者的心中。
本片的另一重要主题是探讨人类恐惧感的根源。在弗里茨·朗的影片中,恐惧感总是伴随着人性的黑暗面出现,表现为受社会道德约束的自我与黑暗面之间的冲突。换言之,弗里茨·朗是将现实生活中善与恶的较量延伸到人的内心世界,转化为人性中两个对立面之间的激烈碰撞。两种心理力量的碰撞与交锋常常通过人类的恐惧感得到表现。本片中,万利因误杀行为而受到良心、道德的折磨,道德感督促他接受惩罚。但是,一旦真相暴露,他的身份、地位、名誉、家庭等都将毁于一旦,这又迫使万利选择隐瞒。如果说,谋杀是出于自我保护的防卫行为,那么销毁证据、弃尸树林就是有意识的精心策划。对万利而言,捍卫名誉地位的私欲直接与道德正义相冲突。而这种无法调和的冲突让他倍感恐惧,搅乱他的内心,扭曲了他的人格,最终导致他走向绝路,从一时失手演变到蓄意谋杀。计划失败后,万利更是无望。自杀成为他终结苦痛、自我解脱的唯一方法。而选择自杀实际上是在回避事情败露后将失去一切的事实。对万利而言,一时失误造成的良心不安,远不如失去身份地位的恐惧更难以接受。这样的结局,透露出朗悲观主义的人生观,反映了他对挽救人类道德的不信任。影片最后,万利拒绝了眼前的女色,与其说这是万利在道德上的觉醒,不如说是为了躲避恐惧感造成的心理痛苦。
“蛇蝎美人”是黑色电影的重要元素,本片中女主角艾丽斯成为这一形象的代表。根据女性主义电影理论,黑色电影中的“蛇蝎美人”是男性性幻想的投射物,也是男性摆脱阉割焦虑的手段。为此,“蛇蝎美人”总是以尤物的形象出现。本片中,女主人公艾丽斯初次登场是以画像的形式完成的。临街的橱窗内,画中的艾丽斯半露酥胸,神情魅惑,吸引住了万利教授的目光。他停留在了画前,眼神暧昧,表情微妙。几个镜头在看似不经意,实则形象地阐释了女性主义的理论观点。这里,艾丽斯是万利目光的承受者,迎合并指称了长时间压抑在中年教授心中的熊熊欲火。之后,当艾丽斯犹如鬼魅般地从画中走出,以诱惑者的姿态出现在万利面前时,这份欲望更是获得了最直接的投射。万利陷入对艾丽斯的迷恋之中,并在迷恋中陷入危险境地。但需要指出的是,本片塑造的“蛇蝎美人”形象,相较于其他黑色电影中的同类形象还是比较温和的,因为艾丽斯并没有处心积虑地诱使万利犯罪。但她自私、神秘、性感,具有强烈的诱惑力,最终导致万利堕落,从这一点上看,艾丽斯足以担当“蛇蝎美人”的称号。
Joan Bennett(1910.2.27-1990.12.7)在视听方面,本片最成功之处在于对恐惧心理的视觉化呈现。正如前文所述,恐惧一直是弗里茨·朗电影风格的主题。在他的影片中,主人公总是陷入强烈的恐惧感中。本片更是以生动的方式把恐惧感呈现在观众面前。它让观众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并冲击着他们的心灵。通过低调灯光的场景设计,暴力事件的突发性以及镜像运用等手段,朗完成了对恐惧感的视觉化构建。
首先,光线昏暗的室内戏和大量的夜景戏,使影片从整体上呈现一种阴沉、压抑的基调。表现主义风格的布光和对阴影的运用,更是在这种基调之上加重了不安定感。场面调度与人物心理相互呼应,很好地传达了影片的主题。以万利驱车离开艾丽斯家到收费站之间的段落为例。第一个镜头是从车子左外侧拍摄的中景。景框内四分之三的画面都被黑色占据,唯一的光源来自车子右侧的路灯。灯光透过车窗投射进来,在万利脸上形成了一个明亮的光圈。强光下,万利的表情被扭曲,显得异常狰狞。随后,机位转换到车内,一个从背后拍摄的特写镜头。狭小的车内空间里,万利的背影几乎与黑暗融为一体,占据了大部分画面。纯黑的色块,挤压的构图,让人觉得压抑、慌张。紧接着摄影机转到万利的正面。近景镜头下,万利脸部的不安完全暴露在观众面前。此外,挡风玻璃上不断滚落的雨水,路旁在风雨中摇曳着的树枝,都同时在万利的面部投下阴影。它们在万利的脸上不停地晃动,造成了强烈的不稳定感,更加凸显了万利的慌张。副驾驶座上,运动着的车刷的倒影,视觉上就像是来回摆动的钟摆。嘀嗒间,弥漫在车内的不安气氛被推向了最高点。虽然是短短的三个镜头,却因为对比强烈的布光、不稳定的构图、阴影等表现主义元素,自然而又准确地表现出了压在万利心头的那份巨大的恐惧,让观众也感同身受。
其次,对暴力瞬间的真实再现,也是弗里茨·朗呈现恐惧的重要方式。突发性使暴力行为有一种幻梦般的感觉。于是,在似真似假的氛围下,恐惧、战栗、偏执等极端情绪被无限扩大,充斥在影片的角角落落,使观众在关切万利命运的同时,也会担忧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堕落行为。正是暴力行动引发的强烈共鸣,使影片完成了从呈现恐怖行为到警醒故事的转化。
最后,对镜像、玻璃映像的运用也是弗里茨·朗表现心理的惯用手法。例如,艾丽斯透过走道的玻璃窗目送万利离开的段落。艾丽斯忧心忡忡的脸庞倒映在玻璃上,被滑落的雨水洗刷着,变得有些扭曲。这里,不稳定感的面部影像正是艾丽斯内心活动的反射,是对她担忧、害怕等复杂心理的视觉化表达。下一个镜头中,雨中万利的车子,因为玻璃的遮挡也显得模糊而失真。加上路灯的照射,雨水的反光效果等,画面变得混乱、无序。应当说,这些失真、变形的画面在此刻正反映了万利实际的心境,也是对他命运的一种暗示。弗里茨·朗企图传达的信息是,在夜雨中启动的车子奔向的是一场梦魇。
本片的男女主人公分别由爱德华·罗宾逊以及琼·贝内特担当。爱德华·罗宾逊是早期好莱坞电影的实力派演员。他曾凭借在《无情世家》中的精湛表演获得第三届戛纳电影节最佳男主角的殊荣。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他出演了一系列黑色电影,包括《双重赔偿》、《盖世枭雄》等。女主角琼·贝内特是弗里茨·朗的御用女演员,她冷艳妩媚,非常符合黑色电影中常见的“蛇蝎美人”形象。值得一提的是,两位演员后来又同时出演了弗里茨·朗的另一部黑色电影《血红街道》(1945),再次成功地分别演绎了女性的魅力和男性复杂的内心世界。
冷艳、妖媚、魅惑。琼·贝内特与生俱来的气质完全符合艾丽斯“蛇蝎美女”的银幕形象。Edward G. Robinson (1893.12.12-1973.1.26)相较于同时期以探案为叙事核心的黑色电影而言,本片更关注男性主人公被压抑的内心欲望、人类恐惧心理以及个体异化、人性堕落等心理问题。朗格通过紧密的叙事、巧妙的细节设置,精炼的镜头语言以及表现主义风格的布光置景,将男性主人公的无意识情欲、恐惧感、道德困惑等心理因素以视觉化的形式展现在观众面前。弗里茨·朗构建了一个梦魇般的、接近于自我毁灭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男主人公受到不安、恐惧等极端情绪的挤压,个体身份受到威胁,人性异化,最终陷入堕落。弗里茨·朗通过黑色电影这一类型探讨人类的心理层面的问题,强调了对个体精神世界的关注。这无疑扩展了黑色电影的表现范围,增强了它的道德批判力度,对黑色电影类型的进一步拓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