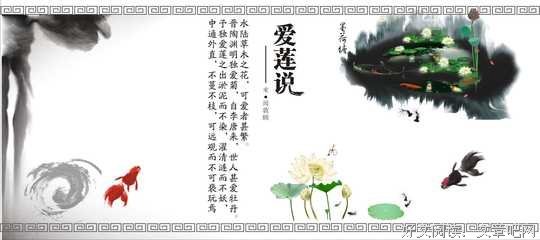
《知堂回想录》是一本由周作人著作,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9.80元,页数:88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知堂回想录》精选点评:
●周作人确实是小事上聪明,大事上昏头。
●春节假期虽不用上班,走亲访友却也是麻烦,偷空看过,印象不深,也就那样吧。。
●500页~补民国人物事迹再读
●了解周作人,不能不读的一部书。
●7 上:童年动人,长大无可取。大事不确,小事不屑,唯死事真切,述死时尤见其平和冲淡。非仅乐生,直并乐死。
●读来特别亲切,吴音越语,家庭琐事,故乡风物,以为是家乡的旧事。
●周作人的,下笔是精简的。虽然有叙述一件事情的『啰嗦』,却没有费词多句。鲁迅的笔下像是更市井更幽默些,他的冷峻,没有烟火气。感觉是受他所喜欢的几个日本作家的文风有点影响一样。同时,受他影响,也很喜欢他推荐的几个作家,或翻译家的作品吧,读着很清爽
●日夜书,案头床头书。
●毕业三年了,能再次找回阅读知堂的畅快,心里暗自窃喜!
●就像周作人谈完了他的一生,虽然他自己也在后序里讲的有没说的地方。比较留意他谈及鲁迅的地方,对于兄弟的失和,他只说“我也很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只有人的力量”可能如此,所以身为读者的自己还是很庆幸他会时不时提及鲁迅没有避而不谈。周作人晚年的回忆文章平平淡淡,行云流水,感觉有种经历世事的平静和故意不说的克制,读来倒没有让我觉得在读老年人的文章。七月读了几本周作人,本想雨天时候读,但偏巧都在上午或者傍晚,阳光热烈,却也温和,有时配着蝉鸣,倒觉得这个夏天不太热
《知堂回想录》读后感(一):《知堂回想录》
1、周作人的文章学识,早年的立场作为,都是堪当一代大师的。文风恬淡冲虚,有若《笑傲江湖》风清扬;
2、作为老二,自幼生活作文各方面受鲁迅照顾,性格里有懦弱妥协的一面。以至于最后出任伪职,在“不该错”处大错,无可挽回。与鲁迅的铁骨铮铮,到死都是“我也一个都不宽恕”性格对比鲜明;
3、看到网上周作人晚年简介,66年81岁被红卫兵皮带棍棒抽打,求安眠药自杀不得,‘寿则多辱’!人活一世,读过多少书,写过多少好文章,经见过多少世事,见识如何高明,如果不幸生在这样的权力和愚蠢主导的国度,那又有什么意味呢?深深一叹~
《知堂回想录》读后感(二):《知堂回想录》
本来在写敬佩周作人不说,但是,这只是一个做法,并不一定就得作为一个修行的标准,的想法渐渐浮现,因此《知堂回想录》的书评也作罢了。这个想法的出现有两个引子,一个是高尔泰的《寻找家园》,它的悲伤和它的强烈的说清这件事分不开。而在回忆录里说清楚一件事,例如《寻找家园》里高尔泰写女儿的去世,《巨流河》里写张大飞,大概都是生者对死者所怀的一种责任。这种感情其实周作人自己本身也有,如他遗憾没有能够为钱玄同编年谱之事。另一个只是余世存《非常道》里引用的余杰的一句话,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大意如此)当然这对我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我对周作人可以说充满尊重(尤其是读完《知堂回想录》以后)。
但忽然想起周作人讲日本人的席地坐在冬天,相比西式的高坐,两腿能够保暖,所以好。想起确实双腿的冷是我以前寒假没办法在图书馆和家里坚持看书的一个大的因素。必须得在宿舍里开足空调,其实那样也还是双腿冷。觉得回想录里这样的地方不记下来太可惜,就重新开始写,不过暂时也只有这一点。以后突然想起来了,就再记一下。
大学时代是我侨情盛极的时候。那时因为由于喜欢一个人而想要改变自己,可那时觉得改变似乎不可能,好像那是性格,由基因定下,物理的,无法更改。但渐渐发现,观念的可变使得当初的想要改变得以实现。观念改变,在同一块物理身体上,造成一种真正契合物理的一套环境。这环境可以说是自己营造,但也不得不说它很可能是一种回归,回归到本来的自我。这个过程我觉得极大地需要靠阅读以及实践,当我去找寻,比如说周作人,他的对于儒家的领悟,从何而来时。首先他的杂学兴趣绝对对于他的仁的理解至关重要,杂学这里就包含了一种兼容并包。然而除此,在实践方面,我认为极重要的,是与有可从善如流之处的师友的接触。并不一定是得着言传,但必是要有身教的。例如周作人屡次提及蔡元培,鲁迅,钱玄同的一些做事,这不仅是服膺,也一定是深受影响的。此外的实践便是自己的一人撑起的经历,例如在日本的生活经历。这则多半是去实践自己的观念了,同时也有改动。例如我只身在东京,我则就完全以自己的观念来和东京赋予我的生活相对照,磨合,探讨。
上面提及蔡元培,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里最长的一次抄书即是蔡元培回林纾的信,他为此甚至不辞辛苦抄下林纾的公开信原文(在周作人可能并不想把林纾这信摆进自己的回想录里吧,哈哈)以解释原委。我读了蔡元培的这封信,也能体会周作人该是怎样的敬佩蔡元培啊。读《知堂回想录》这样的传记,就会借着作者的评价,得到一个因缘际会,脑子里记着,也要去了解周作人评价甚高的这几个人。至少有蔡元培钱玄同。鲁迅则更不用说。
-------
2017.12.5
看了高晓松讲鲁迅尾声里对周作人的评价为贪图享乐,我心里是有点痛苦,因为我真是喜欢《知堂回想录》,而我又确实觉得高晓松没说错。大概我潜意识里一直在想着这件事,刚刚王安忆的一句话又浮出来,她大意说人(或者作家)是不该受到这么大的考验的。这个大考验我记得她是指文革。想到这里我又觉得我有什么资格去找一个说法,以使好像什么东西减轻了呢。毕竟我连使什么加重也不该去做的啊。
《知堂回想录》读后感(三):天知地知 知堂是否亦知?
以酒为衣
读《知堂回想录》所感
我向来是个俗人,彻头彻尾的那种。因此虽知自己乞巧之时多料不到成拙,凡事总该谨慎为上——但终归输给了那种带着点自得喜气的感觉,觉着身卧云山万事轻,虚幻而飘然,这种美好我是放不下的;且往坏里想,纵是镜花水月一场,也是做过梦的,未得多少遗憾,反倒释然多些。
出于私心,我向来对那些避让又有温吞的性子的人好感颇深,想着同类人的心总是相通的,于是也假装大公无私地盼他们点好。好似他们好自己就会好似的,着实可笑。但心底知道他们不那么好其实也无妨。本就是喜欢他们的懦弱与真实,若是太刚毅勇武总觉得完满却远在天边,取经辛苦,不愿过那八十一难强行接近。但申明是要的,对功德圆满的人我是心服口服地承认和赞美的,知道自己做不到这一步不敢妄言胡论,只是感叹罢了。因此下文避而不谈,只谈谈自己爱深责切的。
“周王寿考,遐不作人。”用这个典起名是很妙的,寓意不凡,言简意深,难觅瑕疵。纵使最后时局所迫无法署上“作人”之名,也还是念着这个典在译作上署上了“遐寿”。只人生难免趋时受惑,寓意再好也士林难期。国难时想避时局给自己于八道湾留一屋子清净,到最后还得借着故旧爱徒的薄面。如说怎么偷来的浮生半日闲不管,总算是有过一段清净日子的,虽然中间波折众多,本心尽失,但后来或许也未十分后悔。虽然收到《谢本师》之类的冲击, 但并非得意门生所作,伤害不深,不似当年自己那篇大义凛然字字诸心,还能安慰自己“作人”还是留下了点什么的。也算是没辜负了此句宏意。
但是否辜负我向来是不在意的。实不相瞒,我只想知道如何能避那么一会儿,好好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为自己造一场十年的尘梦。不管后来谁人不知是不对的,但人被琐碎闲杂压垮时,只觉且乐生前一杯酒实际些,反倒是把身后千载名抛之脑后,想着谁人顾得上便让谁人顾去,与我何干。再消极点,把责任往外推也未尝不可,想着人生由命非由他,最后倒春风得意也未可知。
可上文都是成千上万人想最后留给一人做的,我自知轮不上。那些观点纵使我没穿棉拖冻得有点僵的脚趾头同意,想吃泡面的胃也不会同意的。可梦还是得做的,不然心不同意,那可麻烦多了。
可在外边总不能如此。现今算是认清现实了,知道自己连避的本事都没有,抱关击柝还得排队,上策还是回头做老实人。可惨的是没做过,连经验也没有,只得亦步亦趋跟在别人后面,邯郸学步,想着爬也得爬回现世。现世收不收反正也到了,往城门口一躺,就当自己回去了。
还是希望自己有那么点福分,能在旧世无法避,新世融不进之时,收得几枚有趣的闲章,往自己脑门一盖,哐一声倒地,寿终正寝,快快活活地跑去海上仙山了。
茕茕白兔,东奔西顾,衣不如新,人不如故。时局定乱,世事难料,生逢盛世自然是好,但说是结局有无不同之处,却也都是人来人往总最后什么也不见了,。
人生穷途末路的时候多,未高瞻远瞩望尽天涯路的时候更多,大家都是凡人,无需苛责。寿则多辱,人避到最后什么也难避掉。自以为贪嗔痴尽散便能逃过劫数,不过笑话。可老虎桥的岁月再苦,还是难忘白酒和青梨。有留着一点趣,就够了。
《知堂回想录》读后感(四):一说便俗
这是周作人作品集中体量最大的一部,近四十万字,分作四卷。周作人生前自编文集,字数多在十万字以下的,篇幅如此长的作品极其少见。周作人完成《知堂回想录》的时间是1961年,最后一篇后记标注时间是1966年1月3日。几个月后,文化大革命爆发,周作人遭红卫兵批斗,第二年病逝,再也没机会写新的文章。因此,《知堂回想录》可以看作周作人一生的总结之作。
生命最后阶段的知堂,处在红旗之下,风格却没有太多改变。除了偶尔出现一些与时俱进的词语,如对国民党、胡适以当时大陆常见的语气描述外,仍能以平实的味道缓缓道来。连“文抄公”的特色也没变,只不过在《知堂回想录》中,周作人抄自己的东西多过抄别人的东西。往往大段引述以前文章中的话,甚至整篇文章八九成都是旧文摘录。这种“抄书”也有好处,让读者对他一生的重要创作有了粗略了解。再加上其中又引用了不少其他人的著述,让一部回忆录有了文献佐证,呈现更丰富的层次。
对于自己写回忆录的原则,知堂在《拾遗甲》里有论述:“一个平凡人一生的记录,适用平凡的文章记了下来,里边没有什么可取的,就只是依据事实,不加有一点虚构和华饰,与我以前写《鲁迅的故家》时一样,过去八十年间的事情只有些缺少而没有增加,这是可以确说的。”知堂是不愿意在回忆录加入“诗”的成分的,所谓“诗”的成分,是指抒情的、主观情绪强烈的修饰,甚至为了增加故事的感染力而不惜扭曲事实,周作人希望自己的回忆录中只是对事实的客观陈述。
但读者也不能因此以为周作人的回忆录便是完完全全真相的重现。整部《知堂回想录》里虽然陈述的多是事实,却做了大量剪裁工作,对许多内容,周作人或避而不谈,或含糊其辞。尤其在人物的评点,事件的冲突上,周作人往往将笔头一掉,轻轻划过。如果对周作人缺乏了解,只看回想录,他一生中很多重要事件就会消失无踪。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周作人文章中极少提自己的太太羽太信子。婚姻该是一个人一生中的重要事件,但周作人连对自己何时结婚也未作叙述,对与太太的感情更绝口不提,夫妻间的关系成了一片空白。而和周作人有过交往的人,都提到羽太信子对他的影响极大,包括周作人的失节,也有人认为和羽太信子有脱不开的干系。
家庭关系中,周作人和鲁迅失和绝交,是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公案。但周作人在回忆录只对失和先后的事做了一些描述,尤其几次提到兄弟失和后,鲁迅在给曹聚仁的书信中评价周作人五十自寿诗 “颇有讽世之意”,周作人大概想藉此说明“大哥还是懂我的”,但对于和大哥失和的来龙去脉却只字未提。
周作人虽然写了祖父、父母和亲属,包括早逝的妹妹,但对自己和家人的矛盾却从不提及。自己的另一个弟弟周建人后来也和他断交,他干脆在文章中一点不提这位弟弟的事,其实周建人娶的是羽太信子的妹妹,两家的关系应该非常亲密。总之,对于人事上的种种纠纷,周作人一概采取避而不谈的策略。
周作人在后记里做了解释:“并不是凡事实即一律都写的”。他几次提到倪瓒的故事,在《不辩解说上》里引用余澹心编《东山谈苑》里的话:“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元镇曰:‘一说便俗’”《不辩解说》上下两篇正是对兄弟失和事的解释,但纵观全文,不曾提到失和的缘由或事实,只反复申明“一说便俗”。为何“俗”呢,我们终于不知道,而成为无解之迷。
《知堂回想录》里有几篇特意谈自己在民国时和日本人操纵的《顺天时报》论战,又在《反动老作家》里,申说自己在日伪期间,撰文《中国的思想问题》,被日本鼓吹军国主义的文人称为“反动老作家”。特意把这种在其一生著作中并不具备太大分量的作品,又多是老生常谈的观点拿来说,可见周作人虽口称不辩说,对还是在意的,有意想法开脱,冲淡自己那一段失节的历史。只是周作人也知道,很多事是无法解释清楚的,尤其他本身就是一个集各种矛盾于一身的人,辩说起来,可能真会越抹越黑,自取其辱了。所以在《知堂回想录》里,周作人便将一生诸多行径,以“一说便俗”四字敷衍而过。看似无意争执,却在一次次的表态中透露出内心的强耿。不可说,不愿说,更是不屑说。周作人平和冲淡的文章背后,其实有着一颗叛逆不羁的心。周作人和鲁迅文章看似风格殊异,究其深处其实有诸多共通之处,这种不妥协的倔强即是其中一种。
对于自己经历的历史,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不做过多主观评点,多直书亲历之事,又辅以耳闻的资料,加上他的原则是不做诗化的涂抹,因此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十余篇《北大感旧录》篇篇精彩,对同时代文化名人辜鸿铭、黄侃、蔡元培等人的逸事野史,以寥寥数笔,从细微处勾勒而出,随意而潇洒,尽得神韵,可见知堂的功力非凡。
《知堂回想录》内最多的是周作人对自己一生著述与学问的阐释,除了获知他的个人历史,对他一生的著述与学问更能有全面的了解。无论对其个性、行为有何争议,周作人在学问上的造诣都深可佩服,《知堂回想录》是值得反复诵读的书。
书友请微信扫描,关注我的读书分享公众号“闲书过眼”
《知堂回想录》读后感(五):诗与真实
自从在大学时被老师逼着读了十几本周作人散文集后,周作人的文字就在我的心里留下了阴影。虽然那些文字讲的尽是草木虫鱼、风花雪月,如此地淡定风雅,但是我的心里却只盛满了赶任务的焦虑感,只不过是让那些字符在眼前快速地过一遍,未曾在脑子里唤起一光一影。
没想到多年以后,当我再次拿起周作人生平的最后一本著作——《知堂回想录》时,心里仍有一种难以走进书本的焦躁感。这种焦躁感或许是前述的“阴影”;也或许是双方秉性的天然不合。于是,看书就沦落为了翻书,从封面翻到尾页。在此之后,我仍然要写一份读书随笔——实在又有点当年完成任务的感觉。
一、文抄公体
既然说周作人的文字与我的生辰八字不合,那就不妨先以我最不耐烦的周氏文抄公体说起。
周作人是民国的散文大家,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颇有建树,鲁迅即称他为新文学史上最大的散文家。1921年5月,周作人在北京《晨报副刊》发表了《美文》一文,率先倡导“美文”写作,从表达方式和表现内容两个方面确立了现代散文的文体观念。此后,他又推崇明清小品文,提出了与“载道”派相对的、独抒性灵、表现自我的“言志”派小品文,与鲁迅的杂文分庭抗礼。至于他的散文作品,更是多不胜数,共出版有20多个散文集,共计三千余篇。
或许,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未必晓得周作人在散文史上的贡献及丰硕的创作成果;但有赖于义务教育的功劳,他的一二名篇我们总还是读过的,如《乌篷船》、《北京的茶食》等。在款款行文中,我们着实能感受到知堂老人的随兴洒脱,做起文章来,恰如闲谈,娓娓道来,舒卷自然。然而,在《知堂回想录》中,我们已不大能看到周作人最为人称道的闲话体。最常见到的乃是他的文抄公体。
周作人曾把自己的写作分为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便是“民国廿一年以后,只写随笔,或称读书录”。此处的“读书录”,大体上就是钱玄同所戏称的“文抄公体”,即是全篇以引述他人原文(大多是古人笔记)为主,其中间或穿插些自己的话来连缀。这种文体向来就饱受争议,否定者认为这是专抄古书、毫无己见,“文抄公体”这一称呼便已有些贬义;肯定者则认识这是一种非等闲所能的文体创新,不仅要有惊人的阅读量,还要有穿针引线的洞见。
文抄公体究竟有几许价值,这或许是一个专门的学术问题。但是就我的阅读感受而言,这实在是一种不愉快的体验。较之于周作人之前专抄他人文章的“文抄公体”,《知堂回想录》中的“文抄公体”则更多了些自己(还有鲁迅)的日记。可以说,但凡日记内容有与文章相关的,周作人必当不计篇幅地悉数引用。
由于对文言日记、古人笔记、现代小说的大幅穿插引用,《知堂回想录》的文体及文风便显得相当驳杂,忽而晦涩、忽而晓畅、忽而古奥、忽而悠容……就像五四时期的文学编辑看着一堆新旧交杂的文稿。然而呢,我们不是编辑,更不是五四时期的编辑,故而时时被周作人的文字驱赶出去,难以在斑驳的引文中自由穿行。
二、真实与诗
我们可以体谅知堂老人的记忆力,让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全凭自己的记忆来写回忆录未免有些强人所难,纵然写出来也是不大让人信服的。因此,周作人依仗日记来写回忆录是情有可原的。但问题在于:他为什么不把那些文言日记中的内容重新整合,更妥帖地融入到当下的文字中呢?对此,可以有这么些助其“辩解”的理由:其一,是没有足够的时间整合,只好麻胡地塞进去(有些篇目都是民国旧作);其二,是对“文抄公体”的痴心不改;其三,也是最值得论述的,是对真实的追求,原汁原味的日记最能呈现作者所见的历史原貌。
歌德有一本自叙传,名为“真实与诗”。歌德认为,生活中某些美好的事物是不可言传的,而某些可言传的东西未必值得作传。因此,《真实与诗》用的是一种半诗半史的体裁。真实是指现实中实际所发生和经历的事情;诗则是指虚构的或是经过艺术加工渲染的事情。周作人作《知堂回想录》时,便借用歌德的观点继续生发,认为自叙传中通常都有两种成分:即诗与真实。譬如由奥古斯丁、托尔斯泰、卢梭三人所写的带有自传性质的三大《忏悔录》,被后世研究者指出不少有违事实之处。
因为文人的自叙传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真实与诗两种成分,所以自称只会“据实而写”的周作人便把《知堂回想录》踢出了“文人自叙传”的范畴,从而不必卷入真实与诗的纷争中去,“里边并没有什么诗,乃是完全只凭真实所写的。”周作人在《后序》里借着歌德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其实想说的无非就是:我说的都是真的!
然而,欲觅得真实并非易事,横看成岭侧成峰,对于同一事物,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真实体验。为此,周作人巧妙地发挥了“世故老人”的一面,即如荀子所言的: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知堂”之“知”,正来源于此)。在《知堂回想录》中,周作人对于可能引起争议的“真实”都略而不谈:比如他与鲁迅的失和以及他在任伪职附逆期间的活动。
周作人不仅对自己的“真实”引以为傲,还对其长兄鲁迅的“诗”挑了些刺。他曾在写给曹聚仁的信中就谈到:“鲁迅写文态度本是严肃、紧张,有时戏剧性的,所说不免有小说化之处,即是失实,——多有歌德自传《诗与真实》中之诗的成分。”比如在《知堂回想录》的《父亲的病(下) 》中,他就对鲁迅《朝花夕拾》中《父亲的病》进行了两处关乎“真实”的纠正:
一是名医开了“平地木”一味药后,鲁迅描述如何询问多人都不知,得来颇不容易;周作人却说这是“诗的描写”,其实家人“扫墓回来,常拔了些来,种在家里”,“这是一切药引之中,可以说是访求最不费力的了”。另一处则是鲁迅叙述父亲临终之际,衍太太繁文缛节,要他大声呼叫父亲,加重了逝者临终的痛苦;周作人则称,其时并没有衍太太戏剧性的登场,“因为这是习俗的限制,民间俗言,凡是‘送终’的人到‘转煞’当夜必须到场,因此凡人临终的时节,只是限于平辈以及后辈的亲人,上辈的人决没有在场的”。
由此可见,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虽算不得好诗,但至少还是一份较为真实的史料。
三、出版风波
行文至此,其实已可结束,但出于对“三”偏好,我仍然要“滥竽充数”地再写一部分。谈及《知堂回想录》,若不知道与之有关的一段出版界佳话,委实是有些可惜的。此处,便略陈其史。
如周作人在《后序》和《后记》里反复提及的,若没有曹聚仁先生的督促与劝说,也就压根不会有所谓的《知堂回想录》。周作人与曹聚仁在30年代便已认识。解放之后,周作人被“供”起来专事翻译和鲁迅研究;而曹聚仁则是《南洋商报》的驻港特派记者。曹聚仁在1956年以后,多次以记者身份返回大陆,在海外华文报纸上宣传新中国。对于当时正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文化圈所孤立的中国而言,曹聚仁及其报道有着特殊的意义。曹聚仁本人也多次受到新中国领导人的接见。有一次,他就向接见他的周总理提出,想请北京的老文人为自己所主编的报纸写回忆录,其中就有周作人。(当时,没有组织上的批准,作家根本就无法向海外供稿)
在获得组织同意以后,曹聚仁走访了周作人,帮助他在海外出版了《过去的工作》和《知堂乙酉文编》。而周作人也终于在好友的几番盛情之下,于1960年开始写《知堂回想录》,前后历时两年,写作(亦有旧文拼凑)了208节,计38万字。然而,书可能是容易写的,但出版却不是件容易的事。
一方面是杂志连载,另一方面是书样排版校对。1966年春,《知堂回想录》即已付排,而彼时的曹聚仁也已是年近古稀,身体不济,并于1967年住院开刀,卧床两月,但期间他仍是不忘校对书稿,以不愧故友。1970年,《知堂回想录》在交稿8年之后,终于在香港出版,而周作人逝世业已有三年。曹聚仁在《校读小记》中说:“我呢,只求心之所安,替老人出了版,知我罪我,我都不管了”。
个人微信公众号:格拉底苏的下午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