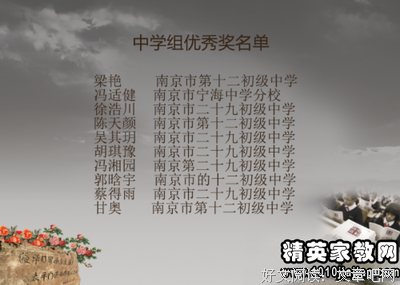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一本由[德]马克斯·韦伯著作,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9.00,页数:2019-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1.主观浸淫于禁欲的宗教意识的侧面予生活样式带来的影响。 2.立基于职业理念上的理性的生活样式,乃是基督教的禁欲精神所孕生出来的,而这就是本文所要加以证明的。 3.对于社会性的自尊自重之无比强烈的个人利害关怀,被清教教派秉持为陶冶那种特质的手段,因此也就是这种个人的动机与自我的利己之心被用来助成“市民的”清教伦理及派生结果的维持与传布。 关于中国地域性-信仰-民俗视域是否可以与宗教社会学做一定程度的结合?历史真实的解明与做研究准备工作,也同样不该该草草充作结论而作为“结果导向”的“工作”,“无灵魂的专家,无心的享乐人,这空无者竟自负已登上人类前所未达的境界” 附录4( 273页)p165页的注应该为p162页的注3。
●一半是引用,一半是韦伯的批注...
●鞭辟入里层层剥茧
●专家失却灵魂纵情声色者丢掉了心肝,而这种空壳人还浮想着自己已经达到一种史无前例的文明高度。
●禁欲新教伦理的世俗化推动市民阶层通过“天职”劳动获得救赎确证,此世的每一份劳动都是为了增添上帝的荣光,每一份财富都是上帝的祝福,由此营利的资本主义精神获得了伦理上的正当性,理性的经营方式的投资与理性的资本主义劳动组织成为决定经济行为取向的支配劳动。然自发组成的教派总是会堕落为教会,卡里斯马型的领袖缺位,“无灵魂的专家,无心的享乐人,这空无者竟自负已登上人类前所未达的境界”,资本主义精神化为钢铁牢笼禁锢出生于此机制的每一个人,世界的祛魅反而为物欲泛滥腾出了空间,“获胜的资本主义,既以盘踞在机械文明的基础上,便也不再需要这样的支柱”,“恐怕直到最后一车的化石原料燃尽为止”。以及,真实便是真理,唯物与唯心自然都是片面的,“对于历史真实的解明,两者是同样可能的”,于我自身也是对唯物主义的“祛魅”了。
●300多页的,正文占一半,剩下一半是韦伯的批注,以及韦伯批注的译注……
●新教伦理:人要信仰勤奋劳动才是改造自身命运的原动力;上帝告诉我们要完善自己品德。 资本主义:时间、信誉、知识、借贷都是潜在的金钱;资本的第一要义就是增值获利。 感想:资本是除了技术之外,对生产力提升最大的要素,利用资本可以改变贫困;资本要掌握在聪明人手中才可以好好利用。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一):什么样的土壤结出什么样的果实
在西方的近代土壤里,科学才处于当今我们所认知的发展过程中。严格意义上来说,习惯的经验性信念、对宇宙的存在及人生意义的思考,以及对神明的崇拜和生活问题的探究,都是哲学独此一门的重要学科,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属于科学的范畴。传递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的国度,怎么会有足够的养分滋养进步的思想。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二):一点总结
虽然此书遭到各种质疑,但是韦伯这种联系显得非常机智。新教伦理对于美国第一代移民影响非常大,他们确实带有韦伯所说的性质,看韦伯的书,让人耳目一新。 就对职业的态度来说,天主教认可圣经“不劳者不食”的主张,但是只把它看成解决肉体需要的条件,而且至少对人类总体来说,不针对个体,所以它倾向于靠冥想圣事等接近上帝,马丁路德则提出了天职观念,即职业是上帝对你的命运安排,但是却迂腐的要求人们满足于自己的位置和职业,不逾矩。到了加尔文教,职业开始闪现出不同的意味,因着肯定预定论,那么对于一个人来说,圣事,忏悔,教会都不能拯救他,甚至上帝也不能拯救他,因为基督耶稣只为选民而死,那么在此世确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便显得至关重要,怎样确定自己是选民,就应该表现出超自然人的特征,这就产生了一种推动力,即鼓励人们在世俗生活中恪守与上帝意志一致的理性,随之产生的便是职业具有了双重含义,第一他是苦行的方式,即劳动,第二,他是人生的目的,即为了上帝的荣光。这就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但是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一方面他允许一个人去转赚取大量的财富,保存大量财富和增加财富是为了上帝的荣光,是接受上帝恩赐的表现。另一方面他反对无理消费和个人享乐,这是堕落的表现,那么这势必导致资本的大量余积,新教伦理慢慢的便与世俗欲望的膨胀碰撞,最终被享乐主义,超前主义等取代。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三):没看太懂,大概其捋个思路
一、什么是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以挣钱为荣、以花钱为耻的态度。二、这种精神的形成与新教伦理有什么关系。个人总结逻辑如下:1.在西方,甚至到了十八十九世纪,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挣钱是贪婪的表现,肮脏,没有尊严,对商人充满鄙视。传统的天主教教徒宁愿收入微薄也不愿意从事商业,他们宁愿选择一种更安逸、宁静的生活方式,要在“挣得多”和“干得少”之间做选择的话,人们更倾向于“干得少”。2.从宗教改革运动开始,以路德为代表的教派,认为劳动是唯一能够取悦上帝的方式,他严厉批判了天主教瞧不起劳动的观点。因此,到了这里,劳动就开始变得有意义,它是在服务上帝,是道德的、光荣的。加尔文教派则更进一步,认为人们就是被上帝选中的人,因为上帝的恩宠,我们才能生存。人的职责天绶,参与的一切劳动最大的目的不是维持生存或追求赋予,而是要维护神在世间的荣光。所有的工作都不简单,所有的财富都没有以往的卑劣,而是人们代表上帝在世间掌管的资产,由此财富的积累就变得无上荣光。3.新教和传统天主教一样,也强调禁欲,赚钱手段不仅要纯洁,然后还要克制消费,以及用钱来做公益。但是更进一步,不但要减少物欲,在本职岗位上辛勤劳动也是禁欲的一种体现,所以鼓励人们拼命努力工作。4.新教派的形成,对教徒有一种身份认可和信用评级,只要加入了某教会,说明人品过关、信誉良好,就会积累更多的信贷资金和客户资源,而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发展所必须的。以上原因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作者认为只是有一定关联,并非是充分条件。 书的最后,作者批判了后来资本主义社会中新教信仰的沦落。这点我认为体现的韦伯的几个主要的哲学思想,一是祛魅,宗教改革祛除的迷信的魅影,而后来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祛除的是宗教的魅影,导致人们越来越功利主义;二是理性的铁笼,我们披上了理性主义的外衣,人与人之间、人与组织之间形成了一种商业的供求关系,我们了解到的,终究只是真相,但是却无法逃离这铁笼。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四):读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对韦伯本书的命题内容自然不必在此赘言。本文集中于我读完后对几个问题的重新思考。
1. 关于人们对“韦伯命题”的诟病。一些人基于“东亚四小龙”的资本主义崛起而认为儒家思想同样能发展资本主义精神,从而否定韦伯命题。读完此书,发现至少可从3个方面反驳这些诟病,来为韦伯“辩护”。
第一,最常见的辩护词是,韦伯一直在强调的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亲和性”而非“因果性”,因此在韦伯并非将欧洲特有的新教伦理看作发展近代资本主义的一个条件/原因,只是说新教伦理更容易带来资本主义精神,而这种精神催生资本主义。但他并没有否定非新教伦理的地区产生资本主义的可能性。
第二,韦伯命题讨论的是近代资本主义能否在某文化中起源问题,而非资本主义能否在某文化中发展的问题。东亚四小龙所能证明的仅仅是儒家文化地区也能借鉴/学习资本主义发展方式,但正如我们所见,资本主义并非起源于儒家文化地区,因此这个反例无法驳倒韦伯命题。
第三,韦伯在书中将旨趣姿态摆得其实很清楚了:“我们只是想明确指出:此种资本主义‘精神’在世界上的质的形成与量的扩张,宗教影响力是否曾参与发挥作用,并且发挥到何种程度?还有,奠定于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这种文化的哪些具体层面可以追溯到这一力量?”他追求的命题其实更为高远,致力于揭示宗教力量作为一种精神要素在多大程度上能催生出一种社会形态,而无论这种精神力量是儒家文化还是新教伦理,无论新的社会形态是资本主义还是封建主义。并且,此处我们也可清晰得见韦伯对二者关系“非因果性”的准确拿捏。
2. 韦伯本书中的“西欧特殊性”论断是不是欧洲中心论?
在本书前言,作者就论述了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西欧特有的现象,“只有在西方”“仅见于西方”“唯独西方才有”等字眼充斥了这几页。这才导向韦伯想问的问题,就是探究为何只有在西方(西欧)才能产生资本主义精神和资本主义。有人批评韦伯范式的欧洲特殊论是一种“欧洲中心论”,即非西方社会无法自生现代性而只能学习西方。许多学者都尝试拒绝这种“欧洲中心论”来做历史研究,例如以彭慕兰《大分流》为代表的“加州学派”。认为18/19世纪西欧和其他地区(比如中国)有相似的社会经济条件,都有可能孕育工业资本主义,只不过一些外部或偶发因素导致了大分流。但是这些标榜“文化多元主义”的作品,其实背后有一种假设:工业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的必然,即不论西欧或其他地区,到了18世纪左右都有发展为工业资本主义的潜力;换句话说,如果那些偶发因素发生在中国,那么中国也会发展为工业资本主义。这样,这些论断只不过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假设下去探讨其地区发展资本主义各自都有的可能性,我觉得反而是一种“欧洲中心论”,甚至有一种进化论色彩。而真正的“多元文化主义”,应该是指出每种社会文化可以发展出自恰的社会形态,因此认为儒家社会无法自生资本主义,才是真正的文化多元主义。所以讲中国“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似乎都是在马克思社会形态发展/进化理论影响下的一种欧洲中心论、欧洲文明想象。在这一意义上,韦伯才是真正的“非欧洲中心论者”:他去探索西欧社会内在逻辑,指出资本主义是西欧社会文化特色的东西。但需注意的是他并没有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的假设,也没有假定资本主义是一种更高级社会。我们对韦伯“欧洲中心论”的误会,也许来源于我们非西方社会面对资本主义强大生命力而产生的自卑。
3. 最后,我发现我非常喜欢韦伯这种打通欧洲中世纪与近代资本主义的研究视野。我们常常讨论的以启蒙运动为开端的现代性在欧洲的出现,并不是与欧洲中世纪完全割裂的,欧洲的中世纪也并非可一概而论的“黑暗的世纪”。既然这些现代社会元素能够在西欧发芽,自然应该在中世纪有适合它们的土壤,在变动中提供了条件。例如宗教唯名论革命为近代个人主义开辟的道路、经院哲学中的思辨为近代实验科学奠定的基础,这些是我们非西方人们不易感受到的,应该得到重视和更多的意识。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五):一知半解的未完成阅读小记
因为相关背景知识的匮乏,尤其是宗教方面的,以至于第一卷读得很吃力,最后也一知半解的。但好在现在的一知半解,也好过读之前的一片空白,留待以后再重读,希望以后会有更多新的收获。
第一遍一些粗浅的收获。
从交换到商业行为,殊途同归。挺妙的。
gt;> 也就是将罪人与神的关系比喻成顾客与店东的关系:无论是谁,一旦欠了债,或许能以一切功德的成果来抵消累积的利息,但本金却无法清偿。
将财货的取得合法化,甚至赋予神的旨意,关键转折点。
对每一份钱财有所交代,在对抗肉体欲望和解放个性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留有空间又不至于过度。
gt;> 而将财产做理性且功利的使用。这并不是要强迫有产者苦行,而是要求他们把财产运用在必要的、实际上有用的事情上。
比较巧妙的是,劳动既是获取财富的手段,又被视为禁欲的一种手段,这种统一性大概算是萌生资本主义精神的一个动力来源吧。
劳动创造资本(入大)——禁欲限制消费(出小)——资本累积(生产/投资)
在现世的世俗世界和来世的天国世界之间寻求平衡和内心的平和,纯善的良心大概是良心循环的一个重要环节,既是条件,也是结果。
gt;> 后来,当“兼顾两个世界”(to make the best of both worlds)的原则胜出时,结果必然亦如道登所指出的,纯善的良心就只能变成享受舒适的资产阶级生活的一种手段,正如“纯善的良心是柔软的枕头”这句德国俗谚所巧妙传达出的意思[插图]。
赋予历史累积的财富不均以宗教解释,算是为之后资本主义经济的起步和发展奠定精神基础。
gt;> 宗教的禁欲力量又将冷静、有良心、工作能力强、坚信劳动乃神所喜的人生目的的劳动者交在他的手中。这力量让他安然确信,现世财货的分配不均乃神之具有特殊用意的安排,借着此种差别,正如通过特殊的恩宠,神有他奥秘的、非人所能了解的目的要完成。
将蒙昧的宗教教义一步步衍生至此,不知是神谕还是天才,人的力量emmm。
gt;> 宗教的禁欲力量又将冷静、有良心、工作能力强、坚信劳动乃神所喜的人生目的的劳动者交在他的手中[插图]。这力量让他安然确信,现世财货的分配不均乃神之具有特殊用意的安排,借着此种差别,正如通过特殊的恩宠,神有他奥秘的、非人所能了解的目的要完成[插图]。
贫穷的原因来自神的安排——接受初始现状;贫穷促使劳动,劳动既是禁欲手段,又是增加神的荣光。
gt;> 加尔文有句经常被引用的话:“民众”,亦即劳动者与手工匠大众,只有在贫穷中才会继续顺服于神。荷兰人(彼得·库尔及其他一些人)将这句话“世俗化”为:人民大众唯有受迫于贫困时才肯劳动;而资本主义经济主要调性之一的这番定式化,后来便汇入到低工资的“生产性”这个理论的洪流里。
劳动者:视劳动为天职;资本家:视营利(剥削)为天职。→促进生产
gt;> 近代劳动者视劳动为“天职”的这种特色,正如同企业家视营利为天职的相应特质。
或许也是因为宗教文化本身相对久远,加之自己缺乏相关的文化背景,第一部分到了第二卷中后段才逐渐清晰。
gt;> 不过,这样我们就涉入了价值判断与信仰批判的领域,而这是此一纯粹历史陈述的论文所不该承担的。我们的课题毋宁是:进一步阐述出上文刚开始剖析的禁欲的理性主义之意义对于社会政策伦理的内容有何作用,亦即说明其之于私人宗教集会乃至国家等种种社会共同体的组织与功能所发挥的效用。然后,此一禁欲的理性主义,与其他诸领域,诸如人文主义的理性主义[插图]及其生活理想和文化影响、哲学上与科学上的经验主义的发展、技术的发展、精神的文化财等层面,到底有何种关系,也必须加以分析。最后,我们还要对禁欲的理性主义的历史演变,亦即从入世禁欲在中世纪时的萌芽开始,到它解体为纯粹的功利主义为止的这段历史,做一番史学的探究,而且是要深入到禁欲信仰的一个个普及的地方去追索。唯有如此,方能清楚评量出禁欲的基督新教,在和形塑出近代文化的其他要素相较之下,到底具有多大文化意义的分量。在此,我们不过是企图在某一点上,而且是在这真的重要点上,追溯出事实及其影响方式的心理动机而已。但接下来,就有必要对基督新教的禁欲本身,在发展过程中及其特质上,是如何受到整个社会文化条件特别是经济条件的影响做出说明[插图]。
诸如此类的文化背景,大概就是大多数留学生融入不了当地人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gt;> 应医生的要求,这病人躺到沙发上,以便鼻镜诊察,然后他一度坐起,威仪堂堂地强调道:“先生,我是……街上……洗礼派教会的一员。”茫茫然,不知道这事实对于鼻病及其诊治可能会有什么意义,这医生私下慎重地询问他熟识的美国同人,而对方则笑笑地给了回答:那不过意味着“您无须担心诊费”。
宗教伦理认可=商业信用
gt;> 也就是说,成为教派的一员意味着人格的一纸伦理资格证明书,特别是商业伦理上的资格证明。
从交换到商业行为,殊途同归。挺妙的。
gt;> 也就是将罪人与神的关系比喻成顾客与店东的关系:无论是谁,一旦欠了债,或许能以一切功德的成果来抵消累积的利息,但本金却无法清偿。
将财货的取得合法化,甚至赋予神的旨意,关键转折点。
对每一份钱财有所交代,在对抗肉体欲望和解放个性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留有空间又不至于过度。
gt;> 而将财产做理性且功利的使用。这并不是要强迫有产者苦行,而是要求他们把财产运用在必要的、实际上有用的事情上。
比较巧妙的是,劳动既是获取财富的手段,又被视为禁欲的一种手段,这种统一性大概算是萌生资本主义精神的一个动力来源吧。
劳动创造资本(入大)——禁欲限制消费(出小)——资本累积(生产/投资)
在现世的世俗世界和来世的天国世界之间寻求平衡和内心的平和,纯善的良心大概是良心循环的一个重要环节,既是条件,也是结果。
gt;> 后来,当“兼顾两个世界”(to make the best of both worlds)的原则胜出时,结果必然亦如道登所指出的,纯善的良心就只能变成享受舒适的资产阶级生活的一种手段,正如“纯善的良心是柔软的枕头”这句德国俗谚所巧妙传达出的意思[插图]。
赋予历史累积的财富不均以宗教解释,算是为之后资本主义经济的起步和发展奠定精神基础。
gt;> 宗教的禁欲力量又将冷静、有良心、工作能力强、坚信劳动乃神所喜的人生目的的劳动者交在他的手中。这力量让他安然确信,现世财货的分配不均乃神之具有特殊用意的安排,借着此种差别,正如通过特殊的恩宠,神有他奥秘的、非人所能了解的目的要完成。
将蒙昧的宗教教义一步步衍生至此,不知是神谕还是天才,人的力量emmm。
gt;> 宗教的禁欲力量又将冷静、有良心、工作能力强、坚信劳动乃神所喜的人生目的的劳动者交在他的手中[插图]。这力量让他安然确信,现世财货的分配不均乃神之具有特殊用意的安排,借着此种差别,正如通过特殊的恩宠,神有他奥秘的、非人所能了解的目的要完成[插图]。
贫穷的原因来自神的安排——接受初始现状;贫穷促使劳动,劳动既是禁欲手段,又是增加神的荣光。
gt;> 加尔文有句经常被引用的话:“民众”,亦即劳动者与手工匠大众,只有在贫穷中才会继续顺服于神。荷兰人(彼得·库尔及其他一些人)将这句话“世俗化”为:人民大众唯有受迫于贫困时才肯劳动;而资本主义经济主要调性之一的这番定式化,后来便汇入到低工资的“生产性”这个理论的洪流里。
劳动者:视劳动为天职;资本家:视营利(剥削)为天职。→促进生产
gt;> 近代劳动者视劳动为“天职”的这种特色,正如同企业家视营利为天职的相应特质。
或许也是因为宗教文化本身相对久远,加之自己缺乏相关的文化背景,第一部分到了第二卷中后段才逐渐清晰。
gt;> 不过,这样我们就涉入了价值判断与信仰批判的领域,而这是此一纯粹历史陈述的论文所不该承担的。我们的课题毋宁是:进一步阐述出上文刚开始剖析的禁欲的理性主义之意义对于社会政策伦理的内容有何作用,亦即说明其之于私人宗教集会乃至国家等种种社会共同体的组织与功能所发挥的效用。然后,此一禁欲的理性主义,与其他诸领域,诸如人文主义的理性主义[插图]及其生活理想和文化影响、哲学上与科学上的经验主义的发展、技术的发展、精神的文化财等层面,到底有何种关系,也必须加以分析。最后,我们还要对禁欲的理性主义的历史演变,亦即从入世禁欲在中世纪时的萌芽开始,到它解体为纯粹的功利主义为止的这段历史,做一番史学的探究,而且是要深入到禁欲信仰的一个个普及的地方去追索。唯有如此,方能清楚评量出禁欲的基督新教,在和形塑出近代文化的其他要素相较之下,到底具有多大文化意义的分量。在此,我们不过是企图在某一点上,而且是在这真的重要点上,追溯出事实及其影响方式的心理动机而已。但接下来,就有必要对基督新教的禁欲本身,在发展过程中及其特质上,是如何受到整个社会文化条件特别是经济条件的影响做出说明[插图]。
诸如此类的文化背景,大概就是大多数留学生融入不了当地人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gt;> 应医生的要求,这病人躺到沙发上,以便鼻镜诊察,然后他一度坐起,威仪堂堂地强调道:“先生,我是……街上……洗礼派教会的一员。”茫茫然,不知道这事实对于鼻病及其诊治可能会有什么意义,这医生私下慎重地询问他熟识的美国同人,而对方则笑笑地给了回答:那不过意味着“您无须担心诊费”。
宗教伦理认可=商业信用
gt;> 也就是说,成为教派的一员意味着人格的一纸伦理资格证明书,特别是商业伦理上的资格证明。